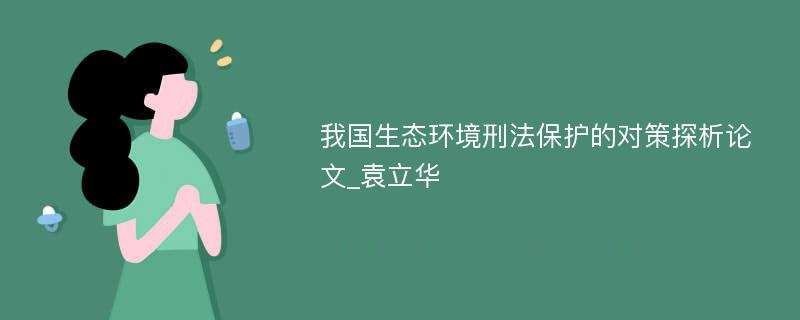
摘要:在今天,生态环境保护已经成为了全世界普遍关注的重大课题。如何保护生态环境,并不是一项简单的技术性问题,而已经或者说是必须上升为一种理念,即生态文明。生态文明,是指人类在改造自然以造福自身的过程中,不断克服其负面效应,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建设有序的生态运行机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所取得的物质、精神、制度等方面成果的总和。
关键词:生态环境;生态法益;刑法保护
1导言
2014年4月24日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新《环境保护法》”)自2015年1月1日生效。新《环境保护法》的颁布,是我国环境问题日趋严重的背景下生态文明建设的及时答卷。随着新《环境保护法》的施行,近两年围绕该法展开的研究深度不断拓展,质量明显提升,新著佳作纷纷发表,获得广泛重视。
2刑法介入环境保护的必要性
生态问题与环境问题的蔓延、加剧,已经对人类的基本安全形成了严重威胁,这也迫使人们不得不开始反思传统的自然观和旧式的生产方式,同时也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挽救和保护生态环境。就国家层面而言,环境的保护主要是通过立法来规定相应的民事、经济赔偿和行政、刑事处罚来实现的。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刑法是其他部门法的保障法,如果把其他部门法比作“第一道防线”,形法则是“第二道防线”,没有刑法做后盾、做保证,其他部门法往往难以得到彻底贯彻实施。因此,刑法介入生态环境领域具有其自在的必要性。
3完善生态环境刑法保护的有效措施
3.1确立生态法益在刑法中的独立地位
犯罪价值判断的重要标准就是法益,不同的法益选择会直接导致犯罪构成设计和罪状表述的差异,并最终决定某些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欲发挥刑法对生态环境严格而有效的保护,就应在环境犯罪中首先确立优先保护生态利益的价值准则,即把对生态利益的损害作为定罪和量刑的标准。
我国刑法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是以生态利益为主要保护目标的,未将环境严重损害的情况包括在内。有关生态环境犯罪的刑法规定也多表现为对人身和财产利益的保护,这正是传统的人本主义价值观念导向的结果,更是我国刑法中生态法益缺失的客观表现。
3.2完善刑法关于环境犯罪的犯罪形态及罪名的设置
3.2.1增设危险犯
由于生态环境污染的危害性不仅容易使众多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遭受损害,而且经污染、破坏后欲消除危害、治理污染往往要花费巨大的财力、物力。因此,在对待环境问题上应树立“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全过程控制理念,这是与现行的环境犯罪结果犯所体现的“末端治理”相对应的一种环保理念。生态环境犯罪的危险犯是指行为人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所实施的危害生态环境的行为,足以造成生态环境的污染或者破坏,而使自然和人的生命、健康和公私财产处于危险状态。对于危险犯,我国的环境资源法仅规定了追究行政责任的条款,而无追究刑事责任的条款。这就使我国的法律制裁落后于实践的要求,不利于及时有效地保护环境。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
3.2.2确立环境犯罪严格责任制
严格责任是指对于某些特殊的案件,只要检察官证明有犯罪事实存在且是由被告实施的,即使主观无罪过,被告也要被定罪。将这种责任应用在环境侵权领域,则是指对那些严重污染或破坏环境的行为不论主观罪过如何,一律加以刑事制裁。目前我国的环境犯罪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迫切需要采取行之有效的保护措施。但是有学者指出,我国不应确立环境犯罪严格责任制。因为严格责任制违背了我国刑法学总则所规定的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将无过错行为人定为罪犯处以刑罚,会造成“超犯罪化”的倾向,会给刑罚的威慑力带来极大的消极影响。
3.2.3完善环境犯罪罪名设置
我国的环境犯罪采用的专章(节)式,将其集中设置在刑法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一节中。但是由于环境犯罪行为的复杂性、多样性,以及环境犯罪危害所具有的影响的长期性、后果的灾难性、方式的隐蔽性、危害的潜伏性等特点,仅用一部稳定的法典将包罗万象、复杂多变的环境犯罪全部囊括其中是不切实际的。目前,我国刑法所规定的环境犯罪罪名仅限于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环境要素,仅倾向于对人类利益的保护,这已不能适应我国环境保护的现状。因此,在刑法中确立独立的生态法益之后,应增设客体为环境要素的罪名,如废物危害环境罪、非法从事核设施罪、非法处置核燃料罪、污染水域罪、污染空气和噪声罪等。
3.3改革现行环境犯罪的刑罚措施
3.3.1扩大罚金刑的适用
在环境犯罪中,国际上以罚金刑代替自由刑的立法趋势表现比较明显。一方面,是因为环境侵权犯罪中过失犯罪占绝大多数,而且单位犯罪比较突出,对于无生命实体的单位来讲,适用罚金刑更为适宜。另一方面,环境犯罪作为一种贪利型犯罪,与自由刑、生命刑相比较,罚金刑更具有惩罚的严厉性、经济性,也有利于弥补环境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危害后果。
3.3.2增设资格刑
生态环境犯罪大部分都是单位犯罪,而适用资格刑对单位进行惩处较自由刑及罚金等现存的附加刑,更有针对性和实效性。但我国刑法中对于资格刑的规定仅限于剥夺政治权利,这显然不够。为此我国刑法可以增设资格刑的规定,如禁止从事某种营业、解散犯罪法人、剥夺荣誉称号、禁止向公众募捐、暂时或永久剥夺从事某种职业的权利、禁止从事特定业务、剥夺荣誉称号等。
4结束语
总之,刑法,作为社会秩序维护的最后一道屏障,也是现代法治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承担构建生态文明重任上责无旁贷。生态文明视域下,环境刑法必须培养起生态法益的独立认知,这是刑法之于环境问题的当务之急,更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长远之计。同时,在具体保护路径上,刑法的内部构造与相关设计应当有所改良,如此才能有效地应对复杂多变而又前路艰难的生态环境问题。当然,正如培根所言,“对于一切事物,尤其是最艰难的事物,人们不应期望播种与收获同时进行,为了使它们逐渐成熟,必须有一个培育的过程”。生态文明的建构与环境刑法的成长亦是如此。
参考文献:
[1]张梓太.环境法律责任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215.
[2]黄锡生,张磊.生态法益与我国传统刑法的现代化[J].河北法学,2015,(11).
[3]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第七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581.
论文作者:袁立华
论文发表刊物:《基层建设》2017年第21期
论文发表时间:2017/11/1
标签:刑法论文; 环境论文; 生态论文; 生态环境论文; 罚金论文; 我国论文; 环境问题论文; 《基层建设》2017年第21期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