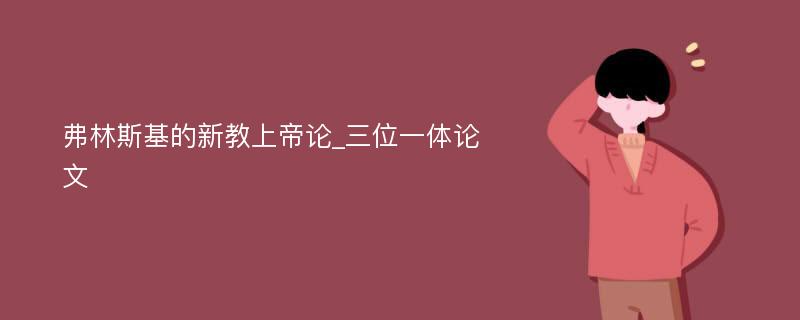
弗洛林斯基的神正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正论论文,弗洛论文,林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帕·阿·弗洛林斯基于1882年出生在高加索地区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尽管他有亚美尼亚人的血统,但他的双亲已经完全地俄罗斯化了。弗洛林斯基很早就表现出数学方面的才能。中学毕业后进入莫斯科大学物理数学部学习。在大学学习期间,他就开始研究哲学和神学。1904年大学毕业后,毅然放弃在数学方面做进一步研究的机会,到莫斯科神学学院学习。此间与埃林(1882-1917)等人一起建立“基督教斗争联盟”,其目的是彻底改变社会秩序,但不是在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等时髦学说的基础上,而是以索洛维约夫(1853-1900)的神权政治思想为基础,实现国家“自愿地服从教会”的理想。后来因1905年的革命失败等原因,他发现了这个组织的乌托邦性,很快与之分道扬镳,该组织不久解体。在神学院学习期间,他就酝酿一部重要著作,这就是后来著名的《真理的柱石与确证》,毕业前,该书的大部分已经写完。1908年神学院毕业,这时他已经是个宗教哲学家,留在神学院讲授哲学。1911年接受神职。1912年任神学院杂志《神学通报》编辑。1914年他的《真理的柱石与确证》出版,给他带来了巨大的荣誉。十月革命爆发前后的几年,是他的创作的又一个高峰,1918-1912年他完成了另一部重要的神学著作《思想的分水岭》,出版一系列宗教哲学方面的著作,《崇拜哲学概论》(1918),《圣像壁》(1922)等。但是,后来他在神学方面的研究最终被彻底中断。1917年他在《神学通报》的编辑职务被撤消,在这之前他还写出了一些很有影响的文章,其中主要有《唯心主义的一般人类根源》、《唯心主义的含义》等。20年代中期以后,他的研究活动不得不局限在技术领域。1928被流放到下诺夫格勒,在朋友的帮助下,于同年返回莫斯科。但在30年代初,开始了对他的大规模的攻击。1933年2月被逮捕,5个月后被判处10年监禁,于1937年被处决。
弗洛林斯基被称为“俄罗斯的列·达芬奇”。他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涉及哲学、神学、宗教、艺术、语言学、文化学、科学、技术等等,而且,他在所有这些领域里的研究都达到了专业水平,有很多的研究成果在当时已经被承认。他在电介质方面的教科书长期被当作典范教材使用。在苏联政权时期,官方让他讲授数学和理论物理学方面的课程。在被流放期间,他仍然坚持从事科学研究。苏联整整一代学者都是在他的科学技术方面著作的影响下成长的。直到生命的最后他也没有中断对数学的研究。但是弗洛林斯基的主要兴趣还是宗教、哲学和神学。大学毕业后他没有把数学当作自己的职业,而是选择了神学院,这是他内在心灵上的需求。据说他在这个时期一直想进修道院,只是他的教父没有支持这个想法,所以他才进入神学院学习。他在神学院所在地——三一一谢尔盖修道院(这是东正教教会的中心)里找到了自己精神上的故乡。他对自己的信仰和选择始终不渝,在苏联政权时期坚持不脱自己的长袍,不放弃自己的神职,宁可被流放、镇压、处决。
弗洛林斯基最主要的著作是1914年出版的《真理的柱石与确证:东正教神正论的12封信》。该书的出版是当时俄罗斯思想界的一件大事,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无论是在神学界,还是在哲学界。弗洛林斯基自己设计该书的封面,亲自选择字体,绘制书中的插图和每一封信前面的花饰图案。在写作方式上也十分独特,不是抽象的说教,而是采取书信形式,其中到处是抒情的插笔,大量烦琐引文和注释(全书839页, 注释和补充占了345页)。作者一直是以教会的名义发表见解, 甚至涉及到自己的意见时亦然。但是无论是写作风格,还是内容和观点,都引起人们对他的“正统性”的猜疑。该书的书名取自信徒保罗的一句话:“倘若我耽延日久,你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的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与确证。”(提摩太前书3:15, 中文《圣经》一般都把“确证”一词翻译为“根基”,我们选择“确证”,一方面是根据俄文《圣经》,另一方面根据弗洛林斯基在这本书里使用这个词的意义,在这里该词没有根基的意思,主要是指确证、证实等。)因此,作者在这本书里讨论的主要是教会问题。至于副标题里的神正论,是基督教神学里的一个重要分支,按照弗洛林斯基的理解,是从人出发向神的上升之路,而这本书就是作者自己走向神的历程和宗教体验的叙述。与神正论相对的还有人正论(或具体的形而上学),弗洛林斯基尽管没有最终完成自己的人正论,但其主要问题已经得到了充分地论述,这就是他的《在思想的分水岭》等书的主题。在这里我们按照《真理的柱石与确证》的体系结构介绍他的神正论的主要思想。
1.两个世界问题 绝大多数宗教里的最基本问题之一是对两个世界的承认:此世和彼世。此世是外在的,是变动的不居的;彼世是内在的,是永恒的安宁。我们活着的人都在此世,死去的人都在彼世,我们这里是永恒的喧哗,死去的人的世界里是永恒的寂静。在这两个世界之间是无限的深渊。然而,在我们世界的背后有一个不动的地方,它是这世界的中心,一切都趋向于它,依靠它。我们内心深处有一种归向它的愿望,它就是“真理的柱石”。这个真理不是我们平时所说的众多真理中的一个,它与其中的任何一个都不相象,我们的真理是分裂的,是个别的。这里所说的真理是大写的真理,它是完整的,是永恒的,是统一的,是神的真理,是“世界的太阳”。万物(包括我们人)都靠着它而生存,它给万物以生命。“真理的柱石”就是沟通此世和彼世的桥梁,是我们活着的人的希望。
那么,怎样才能达到真理的这个柱石?
自从近代哲学产生以来,理性几乎成了认识真理的唯一的工具。理性和科学成了认识的标准。然而,弗洛林斯基认为,科学和理性,“如同盐水,只能唤起人们对知识的渴望,永远也不能满足人的充满欲望的理性”(帕·阿·弗洛林斯基:《真理的柱石与确证:东正教神正论的12封信》,莫斯科“真理”出版社,俄文版,1990年根据1914年版影印,第13页。以下凡引此书,只注页码)。人们被自己的理性知识的沉重包袱所压迫,反而不能认识真理自身(大写的真理)。永恒的真理只能靠耶稣基督来认识,完满的认识(即对大写真理的认识)只能来自于他。所以,认识的唯一途径就是宗教体验。耶稣基督是达到真理的柱石的唯一道路,因为他自身就是真理,就是通往这个真理的道路。人的理性不能认识这个真理,就是因为它是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弗洛林斯基几乎到处都在证明这个道理。书中的第一句话是:“活生生的宗教体验是认识教义的唯一方法。”(第4页)
2.怀疑 在这里,弗洛林斯基主要讨论的是真理问题。他首先探讨了真理的词源学上的意义,结果各个民族语言里关于真理的理解,这里也出现了各类真理,真理的标准还是不统一,有理性主义的真理,有现实主义的真理等等。在理论领域,一般把“真理的柱石”看作是可靠性。但是经过分析表明,这些都是小写真理的标准,都是相对的。甚至许多神学学说里对真理的理解都是相对的和令人怀疑的。那么,如何找到无可怀疑的真理呢?即,什么是绝对的真理或大写的真理(在本节如不特殊说明,均指大写真理)呢?
弗洛林斯基是B.C.索洛维约夫的继承者,但不是盲目的追随者。这一点明显地体现在对真理的理解上。索洛维约夫把真理定义为“一切统一的存在者”(《索洛维约夫选集》,两卷本,“思想”出版社,俄文版,1988年,第一卷,第692页)。 弗洛林斯基认为这个定义不能真正地揭示真理的全部内容,所以应该发展它。不过这里的问题是,弗洛林斯基正是以这个定义为出发点来发展索洛维约夫对真理的理解的,这一点很重要,正因此,弗洛林斯基才被归为一切统一学派。
弗洛林斯基认为,绝对真理应该具备以下属性:“第一、绝对真理是存在的,即它是绝对的现实;第二、绝对真理是可认识的,即它是绝对合乎理性的;第三、绝对真理是作为事实给定的,即它是有限的直觉;但它还是绝对可以被证明的,即它有绝对合乎理性的结构。”(第42页)所以,弗洛林斯基的结论是:“真理就是理性——直觉”(第43页)。正是“理性”与“直觉”这对矛盾,才彻底地揭示了真理的本质。“理性的直觉应该在自身里包含一系列无限的被综合了的基础论证;直觉的理性则应该把自己的一系列无限的基础论证综合为有限、统一、单一。理性的直觉是分化到无限的直觉;直觉的理性则是综合为统一的理性。”(第43页)真理不仅是存在的,而且主要地是矛盾的。这个矛盾性直接体现在“真理是现实的理性和理性的现实;是有限的无限和无限的有限,或者用数学语言来说,真理是现实的无限……。真理是不动的运动和运动着的不动。真理是对立面的统一。”(第43页)
至此,弗洛林斯基都是用哲学的语言来表述真理的。下一步,他通过把真理定义为“自我证明的主体”的方式,过渡到对真理的宗教理解。这样,真理这个主体就可以“通过自己而存在并通过自己而被认识”(第45页)。这个真理显然是唯一的,确定的,超越一切有限的,自身完满的。“真理在自身里通过自己而直觉自己。这个绝对直觉行为的每一个阶段都是绝对的,都是真理自身。因此,真理是在‘三’里通过他者直觉自己的,这个‘三’就是圣父、圣子、圣灵。……真理的主体是三者的关系,但这个关系是实体,是关系—实体。……真理是在‘一’中的三者的无限行为。……所以,真理是三个位格的统一实质。这实质不是三个,而是一个;位格不是一个,而是三个。”(第47—48页)这就引出了三位一体问题。
3.三位一体 真理是三位一体,是三个统一的位格组成的整体。这是上边对真理的定义。这个定义是不是理性的要求呢?一般地说,真理是否存在?换言之,真理是三位一体,但是三位一体是什么?如何理解三位一体的概念?
在基督教历史上,三、四世纪关于三位一体的争论对基督教教义的确立和教会的统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三位一体”概念自身在《圣经》里从未出现过,它是由德尔图良(第145—220页)首次提出的,但是,基督教意识必须以这个概念为基础。围绕这个概念的理解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的焦点是三个位格的同质性问题、实质与位格两个概念的关系问题。三个位格中,圣灵是受到忽视的(下面将专门涉及这个问题),因此,三个位格间关系集中在圣父和圣子的关系上,即他们是不是同一个实质。尼西亚会议(325年)解决了这个问题, 会上通过的信经里确立了圣父和圣子的同质性。但是,圣父和圣子明明是有区别的(阿里乌斯派就是以这个明显的事实为依据说圣父和圣子是不可能同质的),这个问题是靠引入位格的概念解决的,同质性问题在尼西亚会议上被明确地解决了,但是关于“位格”的问题,却费了一番周折,主要是实质与位格之间的关系问题。从古希腊时代开始,直到尼西亚会议之前,无论是哲学思想,还是宗教意识,都把实质等同于位格。甚至尼西亚会议上的教父们对这两个概念也没有作出区分。三位一体教义的首倡者之一并为之作出巨大贡献的亚历山大的阿凡纳西(296-373)在尼西亚会议35年之后还坚持实质与位格的意义是相同的。在实质与位格之间作出明确区分的是亚历山大之后的另一个神学中心——小亚细亚的卡帕多奇亚地区的几个著名的神学家,特别是伟大的瓦西里(330 -379)和尼斯的格利高里(约335-394),他们冲破层层阻力, 冒着被指责为多神倾向的危险,坚持圣父和圣子同质前提下,断定神的三个位格是不同的。弗洛林斯基指出,这里的关键还是如理解同质概念,“同质的意思是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具体的统一,但绝不是形式上的统一;……如果说在术语上,在形式上,位格与实质是有原则区分的,那么在内容上,从位格的逻辑意义上说,它与实质是同一个东西。”(第53页)。这是理解位格与实质之间关系的关键所在,对于理性来说,位格的含义是反理性的,即它代表着矛盾。同质自身要求必须承认这个矛盾,也就是说放弃理性的理解。弗洛林斯基认为,尼西亚教父们用信仰战胜了理性,理性在这里遭到致命的打击。在围绕三位一体的争论中,尼西亚教父们的功绩是显著的,其中尤以亚历山大的阿凡纳西最为突出,他被认为是关于三位一体教义的“教会意识的绝对的代表”。尼西亚的教父被认为是“教会的救星和东正教的柱石”(第57页)。确实,对三位一体教义的各种异端的理解直接威胁着教会的统一,排除异端,确立三位一体的信仰是几次大公会议的主要任务之一。
三位一体教义自身与理性思维是格格不入的,对理性来说,它是荒谬的,因此,三位一体是个信仰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人的个性意识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因为荒谬,我才信”。这是由德尔图良在二世纪提出的,它表明信仰不能向理性妥协,信仰宁可违反理性。第二个阶段是“信仰,然后理解”。这是过了9 个世纪后由中世纪著名神学家安瑟伦(或安瑟尔谟,1033-1109)提出的,它表明理性应该以信仰为基础,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理性和信仰的冲突。针对第三个阶段,弗洛林斯基说,这是他自己的信仰问题,他的信仰“是对,‘可见的上帝’的崇拜,我不仅信,而且还知道我所信的。因此,知识和信仰的界限合一了。”(第63页)在这个阶段上,理性和信仰和解了。第三个阶段的实质是信仰的行为,这是生命体验的领域。三位一体教义的最大敌人就是“理性的信仰”,弗洛林斯基认为,理性的信仰就是死亡(他在这里批判了托尔斯泰的理性主义的信仰)。理性信仰的对立面是“信仰行为”,然而,信仰的行为并不能保证行为的结果,即不能保证肯定能够找到所信仰的对象,即真理,因为信仰行为毕竟是人的行为。所以信仰真的如同帕斯卡提出的是“关于上帝的赌博”。“信就是所希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证。”(希伯来书11:1 )难道信仰真的如此荒谬,真的没有任何光明吗?
4.真理之光 弗洛林斯基说:“如果上帝存在,这对于我是毫无疑问的,那么他必然是绝对的爱。……换言之,‘上帝是爱’(准确地说是大写的爱),而不仅仅是‘爱着的’,哪怕是‘完善地’爱着。”(第71页)爱就是上帝的存在,上帝的爱就是绝对真理发出的光。我们如何接近这个光?接近这个存在?哲学家毫不犹豫地靠着自己的理性来认识这个绝对的真理。然而理性是什么?“理性是人的器官,是人的活生生的活动,是人的现实的力量。”理性不是某种独立的东西,知识也不是某种独立自在的东西。“因为如果理性与存在无关,那么存在也与理性无关,这是不合逻辑的。这样,幻想主义和各种虚无主义就是不可避免的。这个相对性的泥潭的唯一出路是,承认理性与存在相关,存在与理性相关。这样,认识的行为就不仅是认识论的,而且还是本体论的,不仅是理想的,还是现实的。”(第73页)在这样的认识里,认识的主体与客体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融合的,互相参与的,这就要求认识的主体必须走出自身。弗洛林斯基认为这是认识绝对真理的唯一方式。这种认识方式是理性主义所不允许的,因为它把理性独立了,并在认识的主体和客体之间划了一条严格的界限。因此,理性主义无法获得对绝对真理的认识。既然绝对真理是绝对的爱,那么对这个真理的认识就是参与这个绝对的爱。参与这个爱的先决条件是认识的主体必须改变自己。“对真理的实在认识,即获得这个真理,因此就是现实地进入神的三位一体的内部,而不仅仅是理想地触及它的外部形式。所以,只有通过人改变自身,通过人的神圣化,通过获得作为神的实质的爱,真正的认识,即对真理的认识才是可能的:谁不与神同在,谁就不能认识神。在爱里,而且只有在爱里,对真理的实在认识才是可能的。”(第74页)弗洛林斯基认为,在对真理的认识过程里,真、善、美和爱获得了实质的统一,或实体的统一。“对知识的主体来说是真理的东西,对知识的客体来说就是对它的爱,对直觉着这个认识(主体对客体的认识)的主体来说,就是美。‘真、善和美’这个形而上学的‘三’不是三个不同的原则,而是一个原则。这是同一个精神生活,但是从不同的角度看的精神生活。精神生活是从‘我’出发的,在‘我’里有自己的中心,这个中心就是真。被理解为他者的直接作用的精神生活就是善。被第三者客体化地所直观的这个精神生活,是向外发射的,就是美。”(第75页)因此,爱获得了本体论意义,这个爱不是心理状态,而是本体论意义上的行为。“换言之,基督教的爱必须坚决地从心理领域解放出来,转移到本体领域。”(第83页)
爱的本体论意义要求爱的主体必须走出自身,超越自身,走进新的、与自己不同的(即他所爱的对象的)现实之中去。因此,人的存在、人的认识、人的爱、人的信仰都是由上帝本体地决定的。上帝就是爱,就是光。人应该接受这爱和光,打开自己的心灵,让神的爱和光进来(本体论意义),让神的光照耀自己一切:理性、意志和情感。在这个意义上,静修主义者(禁欲主义者)是人类的典范,他们认识神的光,并靠这光生活,最终,他们改变了自己,使自己神圣化。静修主义者们生活在真理之中,靠着圣灵的指导。
5.保惠师 从《创世纪》开始,圣灵一直出现《圣经》之中,无论是在《旧约》里,还是在《新约》里,圣灵都起着不可代替的作用。但是直到《新约》,圣灵才与圣父、圣子并列(如马太福音28∶19)。在圣灵、圣父、圣子的关系中,圣灵一直被忽视。甚至当基督教意识注意到圣父和圣子的关系,并因此引起了著名的三位一体的大争论时,人们也没有注意圣灵。基督徒很少关心圣灵,甚至教父对作为一个独立位格的圣灵知道的也不多。弗洛林斯基指出,在教会的著作里,有一个奇怪而必然的现象,所有的教父和神秘主义作家都提到,神灵的思想在基督教世界观里占有的重要地位,但是谁也没有对圣灵做过清楚的说明。他认为,显然,教父们关于自己对圣灵的体验是了解的,但他们无法表达这个体验。甚至连本该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思想的教义学家们对圣灵的解释也是含混不清的。比如,著名的德尔图良在圣灵与圣言之间不做任何区分,常常互相代替使用。奥利金(第185-254页)一方面强调圣灵是基督教的独特的思想,但另一方面他常常忘记这个重要的思想。在其他教父那里,对圣灵的含混观念是常见的事情。如果说在尼西亚会议后,人们对圣父和圣子智慧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二者与逻各斯之间的关系,还没有任何清楚的观念。所以,弗洛林斯基说:“在阅读教会著作时,必然就有这样一种普遍的直观的印象,如同看一幅画:它的一个部分已经结束,而另外一个部分还仅仅是不清楚的草图。”(第115页)
经深入的研究,弗洛林斯基发现,对圣灵做出明确阐述的是亚历山大的阿凡纳西。阿凡纳西首次断定,圣灵与圣父、圣子必须也是同质的,尽管他还不清楚圣子与圣父之间的“生于”关系,更不用说圣灵与圣父的“来自”关系了。在他之后,卡帕多奇亚的神学家尼斯的格利高里和伟大的瓦西里也研究了圣灵,但是他们都是在圣父和圣子的前提下研究圣灵的,而没有把圣灵独立出来。至于哲学上对圣灵的各种理解的企图,都导致对圣灵的独立性的否定。神秘主义者把圣灵与索菲亚直接等同起来。弗洛林斯基承认,对圣灵观念的淡漠不是神学史上的偶然现象。因为圣灵主要地表现在礼拜仪式之中,如祷告、圣歌、三位一体日的礼拜等等,而不是在神学思辩里。
由于人们对圣灵没有清楚的认识,所以对被造物的神性本质的认识也十分浅薄。弗洛林斯基认为,这都是正常的,因为对圣灵的认识从根本上说是不可能完满的,因为完满的圣灵时代意味着世界历史的结束。只要历史还在继续,对圣灵的认识就只能是逐渐的过程,只能是个别人在个别的时刻的顿悟。
弗洛林斯基指出,综观历史,人类对圣三位一体的认识大致是这样一个过程:在古代,人们认识的三位一体的第一个位格,对其他两个位格几乎是无知的;在近代,人们认识的主要是第二个位格,即逻各斯,人类用理性的形式把世界理性化,秩序化了;最后,人们自由地追求美,以爱为目的,这是未来世界的保证,在这里,圣灵才作为一个位格而被认识。圣灵是保惠师,是喜乐,是我们的天国,所有的被造物都将被圣灵神化。与这三个时代相对应,有三类科学:古代的科学是神圣的、秘密的,近代科学是道德的、严格的;最后是快乐的,面向未来的。(第127-128页)在此基础上,弗洛林斯基坚决反对托尔斯泰和新宗教意识的代表们,指责他们不接受圣灵,主要表现在他们都在教会之外,而在教会之外是无法认识和找到圣灵的。因此,他们的宗教意识是反教会的、反基督的。
6.矛盾 如同有两个世界一样,真理也有两类,一类是大写的真理,一类是小写的真理。关于大写的真理已经讨论过了。本节主要探讨的是小写的真理(如不特别声明,本节的真理均指小写真理)。小写真理为什么存在?弗洛林斯基说:“只要与神并列存在着被造物,那么与大写的真理并列就无疑地存在着小写的真理。”(第143 页)神是永恒的,无限的。被造物相反,是暂时的,有限的,即是处在时间和空间之中的,弗洛林斯基认为,作为被造物的人是在作为个性多样性的时间和作为共性多样性的空间中认识真理的。时间和空间这两个形式直接地限制了人对真理的认识,并决定了人所认识的真理必定是有限的,即小写的真理。结果,“对大写的真理的知识就成了关于这个大写的真理的知识。而关于大写的真理的知识就是小写的真理”(第142页)。因此, 只有超越时间和空间,进入永恒的,才能获得对大写真理的反映,如果说被造物是变动不居的,那么小写真理则不应该是变动的。换言之,被造物有生有灭,但是小写真理作为大写真理的反映应该具有永恒性。这是大写真理和小写真理的关系。
任何知识都是一个判断,真理亦然。真理之所以具有永恒性,不仅是因为它是永恒真理的反映,而且还因为真理都是对事物各个方面的反映,而不是对事物的一个侧面的反映。因此,真理应该是不怕争论的。既然真理是对事物的所有方面的反映,那么它内在地就必然地包含着矛盾的方面。所以,“对理智来说真理是矛盾的,而这个矛盾只有在真理获得语言的表达形式时,才能明显地表现出来。……正题和反题共同构成真理的表达方式。换言之,真理是二律背反,而且也不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况。”(第147页)这样, 小写的真理与大写的真理内在地一致了。弗洛林斯基认为,真理是二律背反,这是一个重要的结论,而且这个结论要求建立一种“二律背反的形式逻辑理论”。
弗洛林斯基指出,尽管二律背反的概念在康德那里最先出现的,但对二律背反的认识从古代希腊就开始了,而且他认为“对二律背反的认识以及对二律背反的爱好,加上希腊的怀疑主义,也许是古希腊所能取得的最高成就。”(第157 页)赫拉克利特对矛盾的思想有了清楚的认识,柏拉图的作品是用对话的形式写成的,这表明他思维是矛盾式的。后来欧洲的哲学史上还有许多人对矛盾的认识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库萨的尼古拉,德国的黑格尔、费希特和谢林等等。《圣经》里也到处都是矛盾和对矛盾的体验。弗洛林斯基认为,实际上宗教的奥秘都只能用矛盾来表达。“矛盾总是心灵的秘密,是祷告的秘密,是爱的秘密。与神越近,矛盾越明显。但是在高高的耶路撒冷就没有矛盾。”(第158 页)只有在神那里,在天国里才没有了任何矛盾。因此,矛盾是人的理性的产物。为什么会如此呢?因为理性的本质在于对所研究的事物的分化,分化就意味着矛盾。“无论我们研究什么,都必然地把被研究的对象分开,分割为互不相容的方面。”(第158页)
对于理性来说,作为信仰对象的教义也是矛盾的,但是对于净化了心灵的理性,或神圣化了的理性,这个矛盾就不存在了,教义对神圣的理性而言是自明性的公理(第160页)。这当然是禁欲主义者的理性,至于一般人,特别是各类的异端,教义仍然是矛盾的,它们正是以矛盾的一方为普遍真理,从而排斥其他。这是任何异端、派别的总特征。总之。“二律背反是宗教的构成元素,只要理性地思考它。正题和反题就像经和纬一样,构成了宗教体验自身。”(第163页)
7.罪 基督耶酥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约翰福音8:32)认识真理可以获得自由, 是相对于什么的自由?基督耶酥接着指出,是相对于罪的探讨。
人世间有两条截然相反的路:一条是通往善的路,另一条是通往恶的路。前一条路所达到的是真理、生命、神圣、秩序、存在者;后一条路所达到的是虚假、死亡、罪、混乱、非存在。弗洛林斯基断定罪是存在的,但是毫无疑问的是,罪不是存在者。就是说,罪存在于某处,它自身不具有存在,它的存在不在自身,而在他者那里。罪是寄生的,而且就寄生在神圣那里,哪里有神圣,哪里就有罪。存在者与非存在者的区别是,存在者自身拥有存在,而非存在者尽管存在,但自身不拥有存在。拥有存在的就是拥有生命,否则就没有生命。换言之,存在者创造生命,非存在者破坏生命。如果上帝是一切,是存在,那么罪就是非存在,或者说罪依靠存在而存在。破坏性是罪的本质。作为寄生(自身没有存在)的,罪所破坏的首先是它的主人的生命,最终它也将破坏自己的生命,这是从结果上看。但是从过程上看,罪有很强的力量,这个力量的实质是肯定自己的力量,为了自己的“此时”、“此地”而否定和破坏一切不是自己的事物。因此,罪在任何有机体里的作用就是分裂。所以约翰把罪定义为“违背律法”(约翰一书3:4)。关于罪的来源,弗洛林斯基说:“罪就在于不愿意从‘我=我’的自我同一状态中走出来,或准确地说,这个同一就是‘我!’。把自己肯定为自己,而不要同他者的关系,即没有同上帝和被造物的关系,不走出自身而以自己为支点,就是根本的罪,或是一切罪的根源。”(第177页)
从罪的来源可以看出,罪是自我肯定的结果,自我肯定就是与他者的分裂,这个分裂不仅仅是指被造物之间的分裂,而且主要是指被造物(人)与上帝的分裂。针对个性而言,弗洛林斯基直接断定,“罪是精神生活中的无序、离散、分裂的因素。在罪的状态下,灵魂将丧失自己的实体统一,丧失对自己创造本质的意识,陷入自己的分裂状态的混乱之中,灵魂不再是这些分裂状态的实体。”(第174 页)那么无罪的精神生活应该是个什么样呢?与罪的精神生活相反,无罪的精神生活是纯洁中的心灵之聚合与稳固。弗洛林斯基解释到,关于精神生活中的纯洁的实质问题,其实是两个问题,“第一,在人自身的意识中,作为一种体验的精神纯洁是什么;第二,如何理解本体论意义上,即作为思维的客体,来理解纯洁。”(第184页 )前一方面是指精神上的一种安宁状态,或是极乐,无上幸福的状态,在这个状态时,心灵不再混乱,不再追求,不再有不合理的欲求,类似于佛教中的涅磐状态。后一个方面主要是“永恒的记忆”问题。永恒的记忆是对时间的战胜,是对死亡的战胜。作为被造物的人希望神永远地记住自己。因此,精神生活的完整性一方面体现在精神的安宁,不再分裂,另一方面体现在永恒之中。然而,人世间的矛盾到处存在,只有在“高高的耶路撒冷”,矛盾最终才能被消除。然而,此世的生活毕竟不是“高高的耶路撒冷”,其中必然地充满矛盾。矛盾象征着分裂,是罪的表现。罪的结局是地狱。
8.地狱 普遍的拯救是否可能?关于这个问题,弗洛林斯基得出了两个完全相反的结论。首先从上帝的方面看,上帝是爱,上帝爱一切被造物,因此他会拯救每一个人,结论是“普遍拯救的不可能性是不可能的”(第208页)。但是,若从人的主观看, 即从人对上帝的爱的方面看,可以说没有人对上帝的爱的参与,拯救是不可能的,因为拯救是神与人双方的事情。然而,人对上帝的爱是自由的,非被迫的,意思是人完全可以不爱上帝(这与上帝必爱人不一样),上帝的爱因此得不到回应,结论是“普遍拯救的不可能性是可能的”(第209页)。 这两个结论一起构成了二律背反。所以“作为实质的爱的三一上帝的思想,从被造物的角度说,被表现在相互排斥的术语中:宽恕和惩罚、拯救和死亡、爱和戒律、救主和惩罚者……”(第209页)一方面, 上帝对人的爱是真正的,另一方面人对上帝的爱的自由也是真正的,这就是说上述的两个结论作为正题和反题同时是有根据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显然问题在人的身上。
弗洛林斯基在人的身上区分出了人的个性和性格两个方面。关于个性,它是上帝的造物,因此是纯洁的,是绝对有价值的,个性是自由的,是生命,因此拥有“自由创造的意志,这个意志表现在一组行为之中,这就是人的性格”(第212页)原则上说, 个性与性格应该是一致的,然而从根源和结果上看,他们是不同的。个性的根源在神那里,是“神的形象”,而性格是由个性决定的。个性常常表现在人的神圣性和纯洁性之中,而性格则常常表现在人的欲望和理性的高傲之中。个性是自己的个性,但它是相对于他者而言的,是“关于自己”的存在,而性格是自己的性格,但它则是为了证明自己,是“为了自己”的存在。为了自己的存在要否定他者包括三一的上帝。而“否定三位一体的教义就是地狱”(第213页)。因此,“作为上帝的造物的个性应该被拯救; 但恶的性格就是阻碍个性获得拯救的东西。”(第212 页)恶的性格(而不是一般的性格)就是地狱的根源。
个性是上帝的创造,是上帝的赐物。人应该如何对待这个赐物?弗洛林斯基引用马太福音中关于塔兰的寓言(25:14-30)来说明这个赐物。作为天赋的个性如同塔兰,是上帝赋予每一个的“神的形象”。作为附加条件,人应该使之增加。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马太福音25:29)增加应该是“精神的行为”(第216页), 然而实际上一般的人所增加的不是精神上的,不是个性天赋,而是“经验的内容”(第217页), 它不是个性自身,而是“个性的空洞的外壳”,这些就是最后审判时所要针对的东西,就是罪。
上帝是如何对待人的罪的?上帝爱罪人,但不可能容忍人的罪,因为“上帝不为荒谬证明。”(第219页)所以,最后审判时, 上帝把罪和罪人分开,把人的“个性”和人的“性格”分开,把人和他的事业分开。“上帝审判的神秘过程就是分离、分割、分化。”(第219 页)仿佛是一次大的“普世手术”(第222页)。这就是说, 人不是整个地被判而进入地狱,人的个性作为上帝的造物永远是被拯救的,被“切除”的是人的罪。弗洛林斯基提到了《圣经》里建造房屋的寓言(哥林多前书3:10-15),用来说明人应该如何增加自己的天赋。 上帝将用大火来试验(考验)人的工程,如果人增加的不是天赋,而是罪,那么这罪将被大火毁灭。“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哥林多前书3:15)得救的是人的个性,被烧毁的是人的罪过。 在这里,弗洛林斯基提出了东正教和天主教在最后审判问题的严重分歧。天主教增加了炼狱说,认为人被拯救是靠痛苦和折磨的考验,靠炼狱的严酷的法规的惩罚,而且是整个人都拯救。但是东正教的观点(或弗洛林斯基所坚持的观点)是,人“自己”被拯救,即人中的“上帝的形象”被拯救了,人的“事业”将被烧毁。“第二死亡”就是指这个“事业”的被毁而言的,而当灵魂脱离肉体时,是肉体的死亡,是第一死亡(第243-244页)。人在自己的生命中,应该把自己的“天赋”和自己的“罪恶”区分开来,“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地狱。”(马太福音5:30)
9.被造物 弗洛林斯基认为,地狱是罪的上限,在这里一切罪都将被毁灭。罪还有下限,在这里罪也将遭到毁灭,但不是靠“地狱之火”,而是靠“神圣”和“纯洁”。“地狱是罪的上限,神圣是罪的下限;或者:地狱是精神的下限,神圣是精神的上限。”(204 )地狱的下限和精神的上限就是被造物。在被造物里,人是最高的。
作为被造物的人是多方面的,多侧面的,但最基本的是人的身体(不仅仅是物理意义上的身体)。“我们首先把人的身体称为人。”(第264页)弗洛林斯基把人的身体分为三个基本的部分:脑部、胸部、 腹部。如果人体是个整体,那么每一个部分也可以作一个相对的整体,而且都有自己的独特机能:脑——意识;胸——感性;腹——供给。这三个部分与人的神秘意识有关。任何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神秘主义者,对应于人体的三个部分,有三类不同的神秘主义者:脑的神秘主义,胸的神秘主义和腹的神秘主义。其中只有胸的神秘主义是正常的,是教会所允许的,与教会相容的。其他的神秘主义都在教会之外,在圣三位一体之外,是偏离了正常轨道的神秘主义,如腹的神秘主义,它是古代和现代,部分地还有天主教的神秘主义,脑的神秘主义瑜伽术神秘主义。广泛地流传于东方,特别是印度。“教会神秘主义是胸的神秘主义。自古以来胸的中心就被认为是心,至少是以这个名字命名的一个器官。如果胸是身体的中心,那么心则是胸的中心。自古以来教会神秘主义的全部注意都在心上。”(第267 页)而且禁欲主义者生活的主要任务——纯洁性,可以看作是心的纯洁性。“心是我们精神生活基础,我们的精神化就指‘规划’、‘完善’、‘纯洁’我们的心。”(第268—269页)只有净化了我们的心,才有可能与上帝在一起,即成为神圣的个性,这是禁欲主义者们所追求的。
人是被造物,人的神化与整个被造物的神话有密切的关系。因为“人以自己的身体与世界的整个身体相连,这个联系是如此的密切,人的命运和整个被造物的命运是不可分割的。”(第272 页)《圣经》不是上帝单单与人所立的约,而是同整个被造物所立的约(创世纪9)。 人的堕落必然引起整个被造物的堕落,人的神化必然引起整个被造物的神化。人的神化或洁净在此世就可以实现,如禁欲主义者。他们全力净化自己的心,爱一切被造物,所以他们在被造物里看到了永恒的、神圣的一面,甚至看到了魔鬼和“真理的敌人”的永恒与神圣的一面。他们发现了被造物的真正的美,这个美反过来加深了他们对被造物的爱。禁欲主义者就是沿着这样的一条通往神圣的路前进的,结果他们使整个被造物也神化了,即他们发现了被造物的永恒性的根源,被造物因为有这个根源,才与神的世界相连,才得以神化。这是禁欲主义者的伟大的功绩。对被造物的爱来自于禁欲主义者的信仰行为、他们的洁净的心、他们的充满圣灵的心。那么,被造物自身是什么?这是索菲亚问题。
10.索菲亚
索菲亚问题在俄罗斯著名神学家和哲学家索洛维约夫(1853—1900)的神学思想里已经被涉及到了,但他没有给出一个完整的和一致的认识。弗洛林斯基直接继承了研究索菲亚的这个传统,发展了关于索菲亚的学说。在弗洛林斯基这里,索菲亚是被造物,但不是一般的被造物,而是全体被造物的根源,被造物依靠这个根源而与三位一体相连。为了准确地转达弗洛林斯基对索菲亚的理解,我们还是引用他自己的说法。
“索菲亚参与三位一体的神的生命,进入三位一体的深处并参与神的爱。但作为第四个、被造的、也就是与三位一体不同质的位格,她(索菲亚被当作女性——译者)不‘构成’神的统一,她不‘是’爱,她只是进入爱的交往之中,因神的无法言表的、不可认识的、不可思议的谦虚她才被允许参与这个交往。
作为第四个位格,索菲亚因神的宽容(但绝不是因她自己的本质)而在她与神的三个位格活动的关系里表现出分别,但她相对于三一的神来说仍是同一个东西,她在与三个位格的关系中自身才表现出分别;关于她的思想将获得什么样的意思,这取决于我们主要地把注意力放在那个位格上。
从圣父的位格的角度看,索菲亚是理想实体,是被造物的基础,是被造物存在能力或力量;如果我们注意圣言这个位格,那么索菲亚是被造物的理性,是被造物的意义、真理或真实性;最后,如果我们从圣灵的位格的角度看,索菲亚就是被造物的精神性,是被造物的神圣性、纯洁和无罪,即是被造物之美。基础—理性—神圣性这个三一性思想在我们的理智里是分裂着的,相对于我们染了罪的理性,这个思想表现在三个相互排斥的方面:基础、理性和神圣性。事实上,在被造物的基础与被造物的理性或神圣性之间有什么共性呢?对堕落的理性来说,即对理智来说,这些思想无论如何是不能连结为一个整体形象的:根据同一律,这些思想相互间是不可渗透的。”(第349页)
以上对索菲亚的界定是针对圣三位一体的。弗洛林斯基同时还指出了索菲亚相对于圣子在人间的事工方面的特征,这些特征使得关于索菲亚的完整的思想分裂为众多的教义上的概念。“首先,索菲亚是被救赎的被造物的开端和中心,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即是接受了神的圣言的被造的存在物。”(第350页)其次,索菲亚是天国意义上的教会, 同时还是人间的教会。此外,从索菲亚使被造物神化的角度看,她是圣灵、童贞、圣母玛利亚。
“如果索菲亚是整个意义上的被造物,那么被造物的灵魂和良心——人类,则主要的就是索菲亚。如果索菲亚是整个人类,那么人类的灵魂和良心——教会,则主要的是索菲亚。如果索菲亚是教会,那么教会的灵魂和良心——圣徒的教会,主要的是索菲亚。如果索菲来是圣徒的教会,那么圣徒的教会的灵魂和良心——被造物在圣言(它审判被造物并把被造物一分为二)面前的代理人和庇护人神的母亲玛利亚(世界的净化之所),则主要地仍然是索菲亚,”(第351页)另外, 索菲亚还是美,是被造物里的实在的美。
弗洛林斯基通过大量的经验事实(特别是圣像画和教堂方面)解释了索菲亚观念在宗教生活中的特殊的作用。最后他指出了历史上的在三个不同时代对索菲亚的三种不同理解。第一种是拜占庭的思辩的理解,把索菲亚当作认识对象,在其中增加了思辩的内容。第二种是中世纪的俄罗斯对索菲亚的整体理解,把她当作是纯洁和童贞。第三种是当代俄罗斯(19世纪—20世纪初)的理解,在教会的意义上解释索菲亚的含义。弗洛林斯基认为,这三种不同的理解分别解释了索菲亚的三个不同的方面:神学的方面、内在纯洁的信仰行为方面和教会方面。但实际上这三个方面是统一的,只是在我们的意识里才是分开的。
11.友谊 哪里有真理的柱石与确证?弗洛林斯基说,在友谊里。 “友谊,作为‘你’的神秘的诞生,是一个环境,真理的启示就在这里开始。”(第392页)真理是三位一体,真正的生命是统一。分裂、 分化等是死亡的标志。认识真理就是认识真理的统一性。“爱是一种精神的现实,在这个现实里,借助这个现实才能认识真理的柱石。 ”(第395页)弗洛林斯基是从爱的意义中考察友谊的含义的。他指出,在希腊语中爱有四个方面的含义:感情的自然欲望、有机的连结、抽象的和理性的爱、内在的友谊。弗洛林斯基在这里所讨论的爱接近第四种含义,即友谊的爱。
弗洛林斯基认为,宗教团体是靠着两个东西连结在一起的,一个是个性的联系,这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联系,另一个是作为爱的对象的团体自身。在基督教社团最初的各类组织形式里,团体联系占主导地位,在圣餐礼中个性的联系较为突出。教会生活的这两个方面分别被称为兄弟团结和友谊,团结所标志的是团体的联系,友谊则是个性联系。在圣餐礼中,这两方面达到一种融合,这是基督教神秘的实质。但是,它们毕竟是原则上对立的,实际上它们是矛盾的。基督教生活就是克服这个矛盾和对立。
两个人的友谊是相互的需要和帮助,人正是通过友谊认识自己的,“友谊让人自我认识;友谊向人指明,在什么地方以及如何修炼自己。”(第441页)尽管两个人的友谊是最基本的友谊形式, 但是它还需要一个第三者。“友谊是通过他者的眼睛,在第三者面前,即在上帝的面前看自己。”(第439 页)两个人的友谊不排除第三者(他者和上帝),因此,人们必须生活在教会之中,借助于圣灵与其他人交往,与上帝交往。因为“友谊是教会性在人的本性方面的最高成就,是人性的最高峰。只要一个还是孤独的人,他就必须寻找友谊。因为友谊的理想不是与人格格不入的,对人而言友谊是先天的,是他的本质的组成元素。”(第443页)人只有在教会里才能找到真正的友谊, 克服和缓解个人和团体的矛盾,因为“在教会生活里,爱是普遍的基础,这个爱不仅是团体的,而且是个性的。”(第461 页)如果说在教会里爱和友谊是凝聚的力量,是教会所必须的,那么教会还需要一种力量——嫉妒,这是分离的倾向、独立的意识,是限制和分化。这个力量也是教会所必须的,“因为没有它就没有具体的教会生活及其确定的制度,那将是新教的、无政府主义的、共产主义的、托尔斯泰派等等的一切在一切之中的混合物——完全的混乱和无序。”(第462页)一句话, 有爱和友谊的地方就有嫉妒。
12.嫉妒 弗洛林斯基指出,一般地, 人们是在贬义上使用嫉妒这个概念的。而且人们都没有意识到嫉妒的理论意义。在哲学里,嫉妒概念遭到冷落。然而,嫉妒概念在这里是如此的重要,因为没有对它的深入理解,就不能彻底地理解友谊和爱。
一般地,在理论上,都把嫉妒理解为一种缺陷。“知识界通常把高傲、虚荣、自大、怀疑、不信任、疑惑等看作是嫉妒的主要内容,一句话,就中没有道德优点。”(第465页)弗洛林斯基指出, 要正确地理解嫉妒,必须把它与爱联系在一起。为此,首先应该把对嫉妒的不合理的,带有贬义的理解排除掉。于是就有,“嫉妒是爱的一个侧面,是爱的基础,是爱的背景,是最初的黑暗,从这里发出爱的光。 ”(第470页)爱是一种选择,选择对象可能很多,但成为被爱者的往往只有一个。爱的个性意义就在这里,没有这个个性,爱与物质性的情欲就无法区分,在物质情欲里,被爱的对象是可以被代替的,同样,对神的爱也存在这个个性,即唯一性。尽管爱是个性的,但是它却是无限的,“既不受地点的限制,也不受时间的限制,爱是普世的。”(第474 页)所以,爱一方面是个性的,排他的,独立的,另一方面爱是普世的,这就是教会里的爱的特征。
如果爱有本体论意义,那么嫉妒也有本体论意义,而不是心理的,也不是伦理学的。凭着嫉妒我们追求真理的柱石与确证,因为嫉妒里包含着无限的精神力量。在嫉妒的观念上,弗洛林斯基确实是很大胆的。
以上我们根据弗洛林斯基的最重要的神学著作《真理的柱石与确证》介绍了他的主要神正论的基本思想。对两个世界的承认必然引出对两类真理的承认,对人类理性而言,矛盾是两类真理的共同特征。要解决矛盾,必须改变我们的理性。改变我们自己,要靠三一真理之光。人间充满矛盾和罪恶,人要与自己斗争,避免陷入诱惑而犯罪,罪恶的结果是地狱。人可以神化,而且人的神化还会引起整个被造物的神化,因为被造物有被神化的基础——索菲亚。禁欲主义者的生命道路——精神修炼的道路是人和世界达到神化的唯一道路。世人只有在教会里,在圣灵的指引下,才能像圣徒那样达到神化。作为基督身体的教会就是“真理的柱石与确证”,教会的生命是靠伟大的爱来维持的,这个爱就是友谊。但是,嫉妒是爱的一个方面。这就是我们所介绍的弗洛林斯基神正论的逻辑线索。
弗洛林斯基的神学思想是针对当时的世俗化实现的。同时,他还反对另一个针对世俗化现实所产生的运动——新宗教意识。然而,弗洛林斯基自己常常被认为是这个新宗教意识的代表,这是因为他的神学思想在很多方面与正统的东正教有很大的区别。弗洛林斯基的神学思想对后人的影响是巨大的,如他对索菲亚的研究,直接影响了布尔加科夫,索菲亚思想在布尔加科夫那里获得了相对完整的阐述。当然,后人对弗洛林斯基的神学思想的评价很不一致。有人认为他的思想从头至尾是东正教的,还有人则直接怀疑他的神学思想的正统性。别尔嘉耶夫指责弗洛林斯基的神学是“模仿的”,保守的。
应该指出的是,弗洛林斯基对理性主义的批判贯穿在他的整个神学思想里。他时刻在拷问理性的合法性问题。最后,他仿照康德,提出:“理智是如何可能的?”他回答到:“理智在自身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自己思维的对象才是可能的。理智应该有自己的思维对象,在这个对象里理智活动的两个矛盾的规律,即同一律和充足理由律得到一致,当且仅当这时,理智才是可能的;换言之,只有这样的思维中理智才是可能的,在这里理智的两个基础,即有限的和无限的基础事实上成为一个……”(第487—488页)。在反理性主义的立场上,只有另一位俄罗斯哲学家和神学家列·舍斯托夫(1866-1938)才能与之相比,后者更加极端和彻底。
*收稿日期:1999年4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