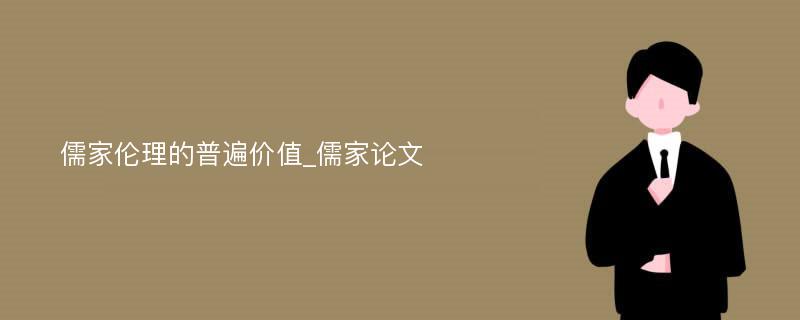
儒家伦理的普世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伦理论文,价值论文,普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07)03-0012-07
所谓普世,应该有时间与空间两个方面的含义。就时间方面讲,普世是指超越一切历史,不局限于某个具体的时代,具有永恒性;就空间讲,普世是指超越一切地域,不局限于某个种族,具有普遍性。那么,当我们提出儒家伦理的普世价值这个命题时,当首先说明儒家伦理何以具有这样的永恒性与普遍性。换言之,要确立儒家伦理的普世价值,其合法性何在?
列文森的“儒学博物馆说”以及曾经广为流传、现在尚有影响的“儒学封建说”、“儒学腐朽说”,虽然持论各不相同,但立论主旨并无二异,都是旨在否定儒学具有普世价值。如果儒学不具有普世价值,那么说儒家伦理具有普世价值,当然就不合法,因为儒家伦理毕竟只是儒学的部分内容,不能设想儒家伦理可以独立于整个儒学。问题是,无论是“儒学博物馆说”还是“儒学封建说”、“儒学腐朽说”,在我们看来,都是从政治的层面、从制度的层面看儒学,没有把握儒家学说在精神方面的超时代价值。儒学之所以不能比之于陈列在博物馆里的供人欣赏的文物,是因为儒学的精神价值并不随着古代政治制度的消亡而消亡,它完全可以与时俱进,在新时代发挥其精神价值;儒学之所以也不能等同于封建思想,是因为儒学本是官学下移、学术民间化的产物,它并不必然地同封建制度联系在一起,它之成为封建社会的官方哲学,是封建统治者有目的地利用儒学,并不意味着儒学自始就合乎封建专制性;儒学之所以亦不能同腐朽划等号,是因为它既不鼓吹糜烂的生活方式也不推崇消极的生活方式,而是提倡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与生活方式,体现了人之生命精神的积极取向。人的生命精神必然表现为积极与消极二种取向,消极取向取消人生价值,积极取向追求人生价值。从根本上讲,人的存在,并不是为了取消人生价值,而是为了实现人生价值。既然实现人生价值是人的本质追求,那么,提倡积极人生的儒学,就不会随着历史的变迁而过时,必定随着人的存在、人之良心的存在而存在。
如此看待儒学的超时代价值,在以往被批判为反历史唯物主义,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基本原则,以为意识形态可以脱离特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而独立存在。这种批判所以不合理,就在于将儒学看成封建意识形态,而没有将儒学看成生命的学问。作为封建社会的官方哲学,儒学一旦脱离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的扶持与卫护,当然就不能发挥其意识形态的制约与导向作用,但是,如果不是将它看成封建意识形态而是将他看作生命的学问,那么儒学就能长久地发挥其现实作用,为人指出其生命应有的积极方向。
作为一种生命的学问,儒家伦理所以具有超时代、超地域价值,起码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证明:一是人不可能不是一个道德的存在;一是人不可能不是一个类的存在。人作为道德存在,最为贵重的价值就是良心,人无良心,就变得如同禽兽,甚至禽兽不如。人既然不可能没有良心,那么儒家伦理对人具有永恒的价值就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儒家伦理所关涉的都是人要有“良心”(也就是指仁爱道德,乃是人所以为人的最基本的道德),这是任何时代的人都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的,除非一个人丧失了人性,他才有可能回避儒家伦理。而作为一个人,所以不可能回避儒家伦理,又是由人作为“类”的存在来决定的,因为人既然也是一个类的存在,他就必然有相同的道德要求,从而都能认同儒家伦理。过去只将人的本质规定为社会性,非但不从“类”的层面把握人的本质,甚至批判“人有类本质”的主张,这是很奇怪的事,只能归咎为出于理论上的极度迷失,竟不知任何事物都是“类”的存在,人如没有类本质,岂不是成为怪物。既然人有类本质,那么无论什么地域的人,无论什么时代的人,毕竟都是人,在基本人性上必定是相同的、相通的。既然人在基本人性上相同、相通,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人具有相同的伦理要求。体现人之道德相同要求的那种伦理,就只能是关涉人之“良心”这一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基本的伦理。儒家伦理所以不为一时一地所局限,具有永恒、普遍的价值,正因为它就是这种性质的伦理。
关涉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基本的伦理,就儒家伦理而言,称为五常,具体指仁、义、礼、智、信。五常之中,仁为体,其余四常为用:义者,宜也,是指人的行为合乎仁的规范;礼者,“节之准也”[1] 229,“所以正身也”[1] 23,是指以仁约束人的行为,使之不违背做人的准则。义与礼的不同,仅仅在于义内礼外:义是人主动、积极地求自己的言行合乎仁,所谓“贵贵、尊尊、贤贤、老老、长长,义之伦也”[1] 444;而礼则是人被动、消极地约束自己使自己在言行上不至于背离仁的规范,所以颜渊问什么是仁的具体条目,孔子回答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第1章);“智者利仁”(《论语·里仁》第2章),智是指人真正懂得合乎“仁”才是人之生存的根本利益之所在,在利益面前,“以义制利”[1] 293不动摇;信者,诚也[2] 52,信是指人与人交际之时真诚待人。真诚待人在儒家看来也就是以“义”待人,所以孔子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也”(《论语·学而》第13章),强调讲信用要符合义,只有符合义,其所谓信用才行得通,否则,徒有讲信用的空名,其所言所语并不能真正得以实行。
由五常的体用关系可以推论,儒家伦理最为核心的道德原则就是“仁”。所谓“仁”,无论孔子还是孟子,都强调它就是“爱人”(《论语·颜渊》第22章,《孟子·离娄下》第28章),是指对别人的关爱。对别人的关爱,在墨家那里,在资产阶级那里,被说成是“兼爱”、“博爱”。无论是“兼爱”还是“博爱”,都是标榜爱人无差等,不分亲疏,不分敌我,对任何人都付出同等的爱的情感。这固然说得动听,但不合理性,因为人人都得到同等程度的关爱,则关爱对于人也就没有特别的价值,岂不等于人人没有得到关爱。儒家所提倡的“爱人”,与这种泛爱主义的空谈所以有别,就在于它强调“爱有差等”,承认爱的情感付出因人而异的合道德性。在儒家看来,人付出爱,根源于人有爱的情感;而人之爱的情感,又系于血缘纽带。由于人之血缘关系构成纽带各异,则人势必依血缘上的远近关系而付出情感程度不等的爱,对父母的爱胜过对兄弟姐妹的爱,对兄弟姐妹的爱胜过对亲戚的爱,对亲戚的爱胜过对朋友的爱,对朋友的爱胜过对陌生人的爱。儒家认为,人之有爱却又如此爱有差等,既是事实也合乎道德,因为合乎理性的道德决不会违背人之常情;凡违背常情的所谓爱(如爱兄弟姐妹胜过爱父母,爱朋友胜过爱兄弟姐妹),因为其矫情,恰恰是不道德的。
问题是,照儒家所说,既然爱的深浅依血缘的近远而定是合理的,那么儒家所谓超越血缘关系的“爱人”(爱别人)岂不等于无根据的妄说?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儒家虽然讲“爱有差等”,但并不因此否定普遍爱心的存在及其意义,反倒强调从对亲人的偏爱(爱有差等)走向对别人的普遍关爱(爱无差等,即对亲人之外的人付出一样的爱)既是可能的又是合理的。其所以可能和合理,是因为人之为人从本质上讲可以做到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儒家之所以提出以“忠恕之道”作为“为仁之方”(《论语·雍也》第30章),正是要告诉人们,从亲情之爱可以合理地推及普遍爱心。按照孟子的说明,这种推及的合理性在于虽然爱有差等但爱的对象都是人,具有相同的类本质。“凡同类者,举相似也”(《孟子·告子上》第17章),则人既爱自己的亲人,就自然可以联想到有必要爱别人的父母,否则,人人都会因不关爱别人的父母而失去了别人对自己父母的关爱,使得自己的爱父母流于空谈,没有实际的社会意义。所以,正如孟子所说,“爱人者,人恒爱之”(《孟子·离娄下》第28章),儒家始终强调应该将对别人的关爱视为自爱(广义,包括爱亲人)的合理的推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第7章)。像这样“善推其所为”(《孟子·梁惠王上》第7章),在儒家看来,普遍适用,譬如从爱父母可以推及必爱祖国,因为祖国是父母之邦;从爱自己(狭义)可以推及必爱朋友,因为朋友与我志同道合。这看似空谈,但诚如孟子所讲,“推恩足以保四海”(《孟子·梁惠王上》第7章),它确实是落实普遍爱心、保证天下和谐太平的最现实最实际的设想。
为这个设想所驱使,儒家认为要切实地做到“爱人”,在方法或者说在途径的设立上,绝不能过于理想,而必须“能近取譬”(《论语·雍也》第30章),就人自己推断为人之常情所必然认可的做法。正是基于这一考虑,儒家从孔子开始,就规定唯有“忠恕之道”① 才是保证人与人和谐相处的最起码的道德原则。作为人之和谐交往的最低的道德准则,“忠恕之道”之所以在当代仍有现实意义,就在于它所体现的道德理性是当今人类最有可能普遍认同的道德理性。“忠恕之道”,按照儒家自己的解释,是实行“仁”的方法。这个方法,被孔子具体规定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第30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第2章;《论语·卫灵公》第24章)。所谓“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是要求尽力地帮助别人,是付出爱心的主体对自己的积极诉求;所谓“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不要将自己所不愿干的事强加给别人,是付出爱心的主体对自己消极的约束。就个体美德讲,为了实现“爱人”的价值,“忠”和“恕”都是必要的,但作为社会交往的规范伦理,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做到尽力地帮助别人,却必须要求按“恕”道行事,决不可将自己的“不欲”强加给别人。这应该成为人类社会交往的最起码的道德准则,失去了这个准则,人类除非不交往,若交往的话,那么只能遵行“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将自己混同于禽兽。
“恕”并非为儒家所独有的理念,在世界主要文化传统里都有与儒家“恕”道相通的提法,例如:佛教就强调“我既爱生而不欲死,喜乐而不欲痛”,我岂能害人性命,将死亡和痛苦“加之于人”②?印度教也这样说:“毗耶婆冰说:你自己不想经受的事,不要对别人做;你自己想渴求的事,也该希望别人得到。”③ 在《新约》中也有同样的说法:“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你们也要怎样待人。”(《马太福音》8.7)犹太教则说得更明白:“你不愿施诸自己的,就不要施诸别人;”④ 而伊斯兰教却这样说:“人若不为自己的兄弟渴望他为自己而渴望的东西,就不是真正的信徒。”⑤ 既然如此(世界主要文化传统里都有与儒家“恕”道相通的精神传统),那么,只要当今世界各地的人民真诚地相信儒家的“忠恕之道”,尤其“恕”道乃人类交往必须遵循的起码准则,真心愿意按“忠恕之道”解决人与人之间的争端,决不失却最低限度的自制心(以不人道为耻),就必定不选择仇恨与报复,因为选择仇恨与报复明显地违背“忠恕之道”,是将自己极想避免的不幸强加给别人,不符合康德道德理性所确立的普遍规律,是对人的理性的公然蔑视,极不人道。由此可见,在当今这个崇尚价值多元的时代,“忠恕之道”才是保证人与人、国与国、民族与民族和谐相处的必由之路。这无须做深奥的理论证明,除非不愿遵循它(这意味着人类的不和谐),一旦遵循它,它就会“为万世开太平”(朱熹等编《近思录》二),引导人类走上永久和谐相处的光明大道。
儒家伦理具有普世价值之得以证明只是从理论上回答了儒家伦理有可能发挥现代意义、现代价值,并没有回答怎样使儒家伦理得以实现现代意义、现代价值。众所周知,可能存在并不等于现实存在,对于儒学的现代化来说,说明儒家伦理怎样才能实现现代价值要比说明它何以具有现代价值重要得多。那么,怎样才能实现儒家伦理的现代价值呢?我的基本观点是:这有赖于儒学的普世化,而儒学实现普世化的根本途径在于儒学世俗化。关于儒学普世化与儒学世俗化问题,我已分别发表了《儒学普世化的基本路向》、《儒学世俗化的现代意义》⑥,为篇幅所限,这里就不再赘述,读者如有兴趣,请参阅两文。在这里,我想侧重针对反儒学世俗化的主张谈谈自己的不同看法,以促进有关儒学现代化问题的深入讨论。
在我看来,与我的儒学世俗化主张构成尖锐对立者,要数现代新儒家所强调的“草根儒学说”以及“儒学具有宗教性说”。“草根儒学”的问题,比较复杂,一时难以简单说明,容以后专文讨论,这里暂且先讨论“儒学宗教性”问题。
儒学本来反神文主义而坚持人文主义的立场,所谓儒学就是宗教的断言,对于儒学来说,不是儒学自身发展所引出来的问题,而是儒家为了应对西方学者责难中国没有宗教而提出来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由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东方情结,所以一再受到批驳,从未赢得大多学者的赞同。也许是出于东方情结,现代新儒家虽然觉得将儒学直接断为宗教有诸多不妥之处,但仍然出于抗衡西方的需要,将这个问题换了一个角度重新提出来,以强调儒学固然算不上制度化的宗教,但儒家伦理完全可以“证明中国民族之宗教性的超越情感,及宗教精神”[3]。从这样的角度来挖掘儒学的宗教意义与作用,可以说是现代新儒家三代代表人物的共同追求,但较之前二代,第三代代表人物更看重“儒学的宗教性”,以至于认为儒学只有充分发挥其宗教性才有可能克服其现代困境,产生现代作用,使儒学获得长足的发展。
儒学究竟有没有宗教性以及从什么意义上把握儒学的宗教性,不是本文所应讨论的问题,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是,即便承认儒学有宗教性,那么从发掘儒学宗教意义的层面来寻找儒学的现代出路是否妥当?现代新儒家当然认为是很妥当的,但在我们看来,这并不妥当,因为它不可能为儒学有效地克服其现代困境找到出路。所以这么认为,基于以下理由:
首先,在把握儒学现代意义问题上,无论是“草根儒学”的立论还是“儒学具有宗教性”的立论,对现代新儒家第三代代表人物来说,都是根据普遍主义的原则,重在发掘儒学超时代、超历史的精神,所不同的是:一个(草根儒学)侧重关注儒学底线伦理,一个(儒学的宗教性)侧重关注儒学超越精神。前一个方面,是希望证明儒家的底线伦理可以为构建全球伦理提供精神资源;后一个方面,则是希望证明儒学的超越精神完全可以适应现代宗教精神的发展趋势。尽管表面地、孤立地看,这两方面似乎没有什么不合理之处,可仔细地推敲,仍然会产生疑问:超越精神属于理想范畴,不属于底线伦理范畴,则根据矛盾律,从超越性、宗教性层面抉发儒学的现代意义与从底线伦理的层面抉发儒学的现代意义,在逻辑上是背反的。既然如此,我们究竟是从“草根儒学”的层面把握儒学普世性的精神价值好呢,还是从“儒学具有宗教性”的层面把握儒学普世性的精神价值好呢?如此困境势必造成民众的难以选择,而难以选择又势必令民众对儒学的现代意义产生怀疑,甚至产生厌倦,从而自觉不自觉地拒斥儒学。
其次,在发展儒学的途径问题上,阐发“儒学的宗教性”的目的在于反对以世俗化的路向来发展儒学,将儒学的现代发展的重点放在架构儒家的“道德的形上学”以及确立儒家的终极关怀上。现代新儒家重在从架构儒家“道德的形上学”和阐发“儒学的宗教性”方面发展儒学,当然不是为学术而学术、为理论而理论,而是有很现实的目的,即为了将儒学的现代发展引向“超越”的路径,将儒家的道德确立为现代民众的道德,将儒家的终极关怀确立为现代民众的终极关切。既然无论是架构儒家的“道德的形上学”还是确立儒家的终极关怀,对现代新儒家来说,都是为了给儒家的道德确立一个超越的根据,以便循“超越”的路径发展儒学,那么这个路径就要保证现代民众注定会以儒家的道德为道德、以儒家的关切为关切。可事实是,它并不能保证由儒家的关切变为民众的关切这一转变的实现,因为它无法证明以儒家的关切为关切才是民众合乎生存之目的的合理选择。按照康德在《道德形上学原理》中的揭示,行为选择的合理性,与选择之合乎目的是一致的,因此任何合乎人蕲求之目的的选择,其合理性必然体现在它是根据普遍规律作出的选择。那么,这个预先决定人之选择必然合理的普遍规律是什么?康德回答说,它就是当人根据某原则去行动时他相信他所遵循的行动准则一定是别人也普遍认同的准则:“一个什么样的规律,它的表像能规定意志,而不需预先考虑其后果,使意志绝对地、没有限制地称之为善的呢?既然我已认为,意志完全不具备由于遵循某一特殊规律而来的动力,那么,所剩下来的就只有行为对规律自身的普遍符合性,只有这种符合性才应该充当意志的原则。这就是,除非我愿意自己的准则也变为普遍规律,我不应行动。如若想使责任不变成一个空洞的幻想和虚构的概念,那么,这样单纯的与规律相符合性就一般地充当意志的原则,不需任何一个适用于某些特殊行为的规律为前提,而且必须充当这样的原则。人的普通理性在其实践评价中,与此完全一致,而且在任何时候,都把以上原则作为准绳。”[4] 根据康德所确立的这一普遍规律,现代民众要先验地确定自己选择儒家的道德和儒家的关切是否合理,就必须首先确定他人是否也普遍地选择儒家的道德和儒家的关切。姑且不论对于生活在经验世界的民众来说,由于其价值选择多基于情感上的好恶,根本就不可能做到如此的理性,即便假定他们能如此理性地做出合理的取舍,那么他们之如此地有理性恰恰保证了他们绝不会选择儒家的道德和儒家的关切,因为理性告诉他们,现代社会是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谁也无法保证自己的价值选择同样也是别人的价值选择。既然现代民众无论谁都无法先验地保证其价值选择的普遍意义,那么有什么理由可以断言:只要儒学的宗教性得以确立,儒家的终极关切就注定会成为民众的终极关切?
再次,探讨“儒学的宗教性”,其根本目的无外乎为现代民众确立一个与儒家理想相一致的终极关怀。这一目的若要实现,起码应具备一个前提,即现代民众的终极关怀与儒家的终极关怀就本质讲相吻合,但事实表明儒家的终极关切与民众的终极关切有本质区别,因而欲将儒家的终极关切转化为现今民众的终极关切简直不可能。儒家讲“为己之学”,追求的是“孔颜乐处”,终极关切在于“成贤成圣”。这也就是说,“成贤成圣”是儒家精神生活中终极的、无限的、无条件的方面,其他方面(诸如求利、立功、立言,乃至治国平天下、成就帝王大业)即便为儒家所关切,也都是暂时的、有限的、有条件的。正因为儒家强调“成贤成圣”这一关切具有终极性、无限性、无条件性,所以他们实际上所关切的也只能是一个永久期盼的理想。尽管对儒家来说,这种对“成贤成圣”理想的永不停止的期盼比“成贤成圣”本身更具有人生的正面价值,但在普通民众看来,这未必不是将人生的价值归结为不切生活实际的乌托邦,因为普通民众基于自己的生活感受从来就不憧憬远离生活的神圣价值,而只关切对自己生活有实际意义的世俗价值。民众根据自己的世俗价值之认同,最为关切的就是如何“趋利避害”,尽可能减少人生的痛苦以获得人生的最大幸福。既然这两种关切性质如此不同,则导致相异的价值取舍就是必然的。例如,从儒家所追求的“孔颜乐处”来讲,千方百计聚财敛财对于实现人生价值就是不合理的,必须反对;而从民众的“趋利避害”的愿望来讲,千方百计聚财敛财就是合理的,不必反对。既然民众的关切与儒家的关切如此的背反,那么从发掘儒学宗教性所确立起来的儒家的终极关怀如何能转化为民众的终极关怀呢?这只有一个可能,就是民众放弃自己的关切而真诚地认同儒家的关切。可问题是,民众凭什么自觉放弃自己的关切而认同儒家的关切?要让民众放弃自己的“现实”关切而认同儒家的“超越”关切,其前提是民众必须体悟到:就对生活的意义而言,儒家的“超越”关切要比他们自己的“现实”关切更实用。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儒家的关切之所以称为“超越”的关切,正在于此关切是超现实的,所注重的恰恰不是实用价值而是超越价值。超越价值只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理想预设,其显著特点就是非实用性,因而它的作用只能通过对现实生活的超越来实现。这就决定了它为民众所指出的应当如何生活的方向,实际上就变成了要求民众不要一如既往地生活下去,要将自己的平庸生活改变为高尚的生活。这其实就是对民众实际的现实生活的干预。从道理上讲,这种干预也许有意义,但对于为日常生活所忙碌的民众来说,这未必不是一种不知生活之艰辛的蛮横干预,毫无道理可言。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对日常生活的关切总是第一位的,企图改变之,使他们关切于超越价值,也只能是现代新儒家美好的愿望罢了。
最后,即便假定民众愿意放弃自己的关切而认同儒家的关切,那么仍然需要确立切实可行的途径才有可能实现这一转变,否则再怎么愿意也不可能真正实现这一转变。那么,民众通过什么途径才能实现这一转变呢?按照杜维明先生的解释,民众要实现这一转变,前提是必须体会“日常生活的终极意义”[5] 248。而按照刘述先先生的解释,则“直接通过生命的强度表达出来”[6],没必要经过曲折的体证过程。且不说确立“生命的强度”对于忙碌于生计的普通民众来说是多么的神秘,即便就民众所熟悉的日常生活来讲,要让民众从柴米油盐之类的日常生活之中去体会其“生活的终极意义”,他们未必不会将柴米油盐视为其生活的终极意义。可见,要让民众认同儒家的关切,不以柴米油盐为生活的终极意义,而追求高尚的道德生活、艺术生活,还必须让民众自己掌握能够体会出日常生活之终极意义的方法与途径。对这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杜维明先生的确没有回避,而是做出了明确的回答:“自我的充分实现,无须任何外在帮助。从终极意义上看,自我的实现就意味着天人合一的充分实现。但是,达到这一步的方式,永远不应该被理解成在孤立的个人与上帝之间建立一种关系。”[5] 249杜维明先生的这一回答,告诉我们以下意思:人不能靠外在的启示了解自己日常生活的终极意义,人对自己日常生活的终极意义的把握意味着人之“自我的充分实现”;人一旦充分实现了自我,就意味着天人合一的充分实现,世俗的日常生活于是获得了神圣的宗教意义;但这种“天人合一”的关系,不是说每一个特殊个体都与上帝建立一种信仰与被信仰的关系,而是指每一特殊个人都必然地与人之“自我”构成密不可分的关系。这种关系,从本体论意义上讲,意味着人对自己“人性的固有的‘信仰’,是对活生生的人的自我超越的真实可能性的信仰。一个有生命的人的身、心、魂、灵,都充满着深刻的伦理宗教意义。就儒家意义而言,成为宗教,就是进行作为群体行为的终极的自我转化,而‘得救’则意味着我们人性中所固有的既属于天又属于人的真实性得到充分实现”[5] 252。杜维明先生论说得很深刻,但理解起来并不难,它无外乎是说:民众无法求助于外在的启示完成由自己的关切向儒家的关切的转变,人只能靠自己“进行作为群体行为的终极的自我转化”。而这种自我转化,就形式讲意味着个体按照群体行为的标准来确立自己生活的终极意义,就内容讲其实就是人自己去体知“人的自我就在其自身的真实存在之中体现着最高的超越”[5] 249。这样看来,民众能不能做到对于人之固有人性的“体知”就成为他们能否实现由自己的关切转向儒家的关切的关键。那么,如何去“体知”?“体知”在杜维明先生的论述里,被解释为人“从事道德实践必备的自我意识”[7]。他使用必备一词,就是要明确无误地表明这个自我意识是先验的,是先于具体道德实践的预设意识。而这个先于道德实践的预设的自我意识,在杜维明先生的论述里,其实就是指“德性之知”。这样一来,“体知”无论说得多么深奥,它实际上就是指根据“德性之知”先验性地体悟人之日常生活的终极意义在于实现人自己的良知与爱心。尽管杜维明先生强调这一道德实践过程是知行合一的,对良知的体悟就意味着实践着良知,但“体知”既然不同于经验感知、理性推知,完全是先验的道德体验,则“体知”的效用就完全依赖于个体的道德悟性,也就是说没有个体的高度的道德悟性,道德的“体知”就无从谈起。“体知”的有效性既然取决于个体的高度的道德悟性,那么企图让民众通过“体知”的途径去把握其日常生活的终极意义——就是说要让民众完全靠自己的道德悟性体知人之先验的德性之知是人之生活在价值上的“最高的超越”,懂得人只要恪守先天的良知、“爱心”,就能确保由世俗关切走向神圣关切,实现人性与神性的相通——就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因为普通民众为自己的生活经验所局限,他们既不可能必然先验地具备高度的道德悟性,又不会轻易放弃自己所推崇的实用价值而认同儒家所谓超越价值。
注释:
①《论语·里仁》第15章有云:“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②《相应部》第333卷,转引自《全球伦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③《摩诃婆罗多》“圣教王”113.8。转引自《全球伦理》。
④《答木德》“安息日”3,转引自《全球伦理》。
⑤《圣训集》,转引自《全球伦理》。
⑥分别见《中国哲学史》2003年第3期、《孔子研究》2000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