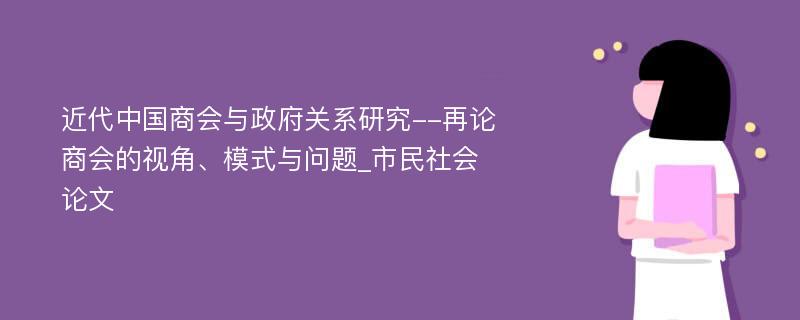
近代中国商会与政府关系的研究:角度、模式与问题的再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商会论文,角度论文,近代中国论文,模式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商会性质研究中的商会与政府的关系
史学界关于近代中国商会与政府关系的探讨在早期并不是独立的,而是包括在对商会性质的研究之中,这是商会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对各种基本问题尚未有成熟看法和一致意见的反映。
1.官商关系:早期的争论与总结
对于近代中国商会的性质,学者们最初正是从所谓“官商关系”的角度着手研究的,而且主要是针对清末的商会。争论的焦点,在于商会本身“官”的成分与“民”的成分各占多少比例,亦即:商会是官方机构还是民间团体?对此史学界意见颇有分歧。
以日本学者仓桥正直、法国学者白吉尔等人为代表的一种意见,认为商会是“官方机构”。仓桥正直断定“商会是在官府的坚强领导和大力庇护下设立起来的组织”,即“官办的组织”(注:仓桥正直:《清末商会和中国资产阶级》,《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1984年下半年。):白吉尔更干脆直指商会是“帝国政府的下属机构”(注:白吉尔:《辛亥革命前夜的中国资产阶级》,《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4辑。)。这种意见强调国家政权与社会组织的同构性,商会只是挂着社会组织名义的变相政府机关。据此,商会与政府的关系,实际上是政府内部下级机关对上级机关的隶属关系,及同级政府机关之间业务往来的关系。而且,正是因为这种非正式“政府机关”的地位,商会才“一方面接受官府的领导,另一方面可以合法地对地方官府采取以往所没有的强硬态度”(注:仓桥正直:《清末商会和中国资产阶级》,《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1984年下半年。)。
以邱捷等人为代表的一种意见,认为商会是“半官方机构”。邱捷认为“商会虽也算商人的组织,但他们一般来说并不能满足资本家参与政治的要求”,“各商会的总协理及会长均受官府的札委并颁发关防,俨然衙门”,因而商会是“半官方机构”(注:邱捷:《辛亥革命时期的粤商自治会》,《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3期。)。美国学者Edward G·M·Rhoads也认为,商会是一个经官方核准的商人团体, 它们根据国家的规定组成并接受工农商部的控制,所以“具有半官方的职责”(注:Elvin,Mark & Skinner,G.William.eds. 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1974,p.105.)。这种意见虽然承认商会在一定程度上的民间社团属性,但强调指出政府对商会的直接控制,以及商会所履行的半官方的职责。商会在政府施加有效政治控制下为政府利益服务,部分地发挥着类似政府机关的性质和作用。
以徐鼎新等人为代表的一种意见,则认为商会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间社团。徐鼎新认为,商会是真正代表工商界利益的工商业者自己的团体,它的设立,就是因为原有的官办商务局仍属封建衙门,为了振兴商务,必须改变“局为官设”的局面。商会设立后宣布的一系列措施和规定,都证明它同官办的商务局是有根本区别的。这种意见强调商会在性质和职能上相对于政府部门的区别与独立。徐鼎新后来在《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一书中,进一步肯定上海商会“基本上是在官方难以完全控制的情况下按照它所代表的上海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意志进行自主活动的”(注:徐鼎新、 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以上三种意见长期以来一直相持不下,直到朱英经过对晚清苏州商会的个案研究,分析各种意见的长短,提出“官督商办”的观点并为较多学者接受后,才算获得了比较统一的认识。
朱英指出,清末商会基本上是一个商办性质的新式民间社团组织,但又具有一定的“官督”色彩,这主要是指清政府在权限及活动范围等方面对商会实施某些限制和监督。不过,这种限制和监督多半是间接性的,清政府并不在商会中委派督办直接予以控制。有关商会的一切具体事宜,概由商会内部的商人自己筹划施行。所以,商会虽然带有“官督”色彩,仍应视为商办民间社团组织,因而具有“官督商办”的性质特点(注:马敏、朱英:《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233页。)。据此, 商会与政府的关系,是在不妨碍商会自身独立运作的前提下,政府对商会实行间接监控的关系。就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而言,它一方面强调社会本身的自主性,另一方面也承认国家对社会存在一定程度的软性控制。
朱英“官督商办”的观点,调和了商会性质研究中的“官”和“民”的成分比例之争,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于从官商关系角度研究商会性质的总结,但就商会与政府关系的研究来说,这一观点所包含的相关内容相对于前人而言并没有很大的突破,而且探讨的对象也过分集中于清末的商会。所幸不久以后,超越“官商关系”思维框架的另一个更有说服力的创造性见解终于被提出来了,这就是虞和平关于近代商会的“法人社团性质”的观点。
2.法人社团:超法的控制与反控制?
虞和平从社会学和法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商会依照政府的法定程序经由政府的批准而设立,有自己固定的组织机构和职能部门,有广大的会员,有自己能独立支配的经费和财产,有法定的权利、义务和活动范围,又由自己自愿发起,自定章程,自选领袖,自筹经费,因此,商会基本上是一种商办法人社团。而商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政府依据商会法规对商会进行管理,商会则在商会法规规定的权利、义务范围内进行活动,并服从政府的管理。所以商会与政府的关系应该是法律关系,即依据法律规定而发生的管理、被管理关系。
虞和平进而指出,在近代中国的现实环境里,这种关系是难以实现的,双方实际上主要是超法的控制与反控制的关系。或因政府的失去控制,使商会超越其法人权利而成为社会政治运动的一个重要角色;或因政府的强权控制,使商会的法人权利严重受损而失去社团法人的社会意义和作用。究其原因,一是政府不能妥善处理和适时调整与商会的法律关系,二是双方的根本利益相矛盾。在他看来,近代中国商会与政府关系的各阶段演进过程,就是由法律关系向超法的控制与反控制关系反复演进的过程,其中,法律关系主要表现为各种利益合作关系的形式”(注: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6—92页。)。
虞和平对商会法人社团的定性及由此推导的商会与政府关系模式,目前已广为史学界接受。那么,如何进一步理解商会与政府之间的利益合作?这就需要对利益合作的形式及内容作具体分析。笔者在此提出一个修正的概念:超法的利益合作关系。
我们知道,商会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完全超越了正常的法人社团所应扮演的角色,它和政府的利益合作,在许多方面涉及到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政权的存亡,重大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决策,等等。这些“合作”是正常的、和平环境下的现代法治社会所不可想象的,也是管理与被管理的法律关系所无法解释的。合作超越了法律,它不但不能被归结为正常的法律关系,也不能被归结为一般的利益合作关系,而应被视为超法的利益合作关系。因此,准确地说,近代中国的商会与政府的关系,除了超法的控制与反控制以外,还存在着超法的利益合作关系。双方的实际关系,是由超法的利益合作关系向超法的控制与反控制关系的反复演进,以及两者的并存。
3.利益团体与政治:一个新视角
就商会性质而言,笔者在此尝试提出一个研究商会与政府关系的新视角:从政治及行政学的角度,探讨商会作为利益团体在政府决策过程中的作用。
政治及行政学中的利益团体理论是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中最早出现的重要理论流派。1908年,美国政治学家本特利在《政治的过程》一书中最先提出并做系统论述。这种理论认为,所谓利益团体,是指社会上各行各业的人士,对某些问题有共同利益者,为使政府维护其利益或实现其主张而组成团体,以采取共同行动。这些团体为了达到目的,有时要对政府施加压力,故又称压力团体。
本特利把“行为”、“团体”和“利益”三者按“系列的原则”来解释社会过程和政治过程。在社会过程中,各个团体相互影响、相互排斥和相互作用,使作为系统的社会处于不断运动中;而当团体试图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采取与此相适应的手段和措施而产生行为时,它们就成为政治团体,并以其行为推动政治进程。在现代社会中,利益团体总是基于自己的利益需要而凭借其实力和手段深深地卷入政治过程而发挥其权力中心的作用(注:谢宗范等编:《政治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44—151页。)。
那么,近代中国的商会性质是不是利益团体?它与政府的关系是否可以从利益团体的理论或角度去解释?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毋庸置疑,商会是由近代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为维护自身共同利益而组成的团体,从一开始它就以工商业者的当然代表的身份发挥影响,力求政府的决策最大程度地符合自身利益。然而,从事商会史研究的学者,过于强调商会在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中对政府和时局造成的影响,忽略了它作为一个利益团体在政府日常的施政和具体决策中所起的作用,而实际上这一作用远比商会在重大历史事件中扮演的角色重要。因此,从利益团体的地位和作用出发,对商会与政府的关系进行重新定位和评价,应该成为研究者的重要工作。
不过,必须特别留意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利益团体政治”就西方政治社会学的概念而言,指的是“多元主义”架构下的利益团体政治。多元主义架构下利益团体政治的运作有四个前提:一是不同团体有接触政治过程和决策过程的同等机会;二是决策是通过冲突和竞争所达致的平衡;三是政治市场上力量的分散化;四是国家保持中立。显然,这种政治能否顺利运作,是以建立一个正常而良好的民主政治秩序为前提的,只有在较为成熟的现代西方社会中才能实现,而近代中国社会则没有这样的政治条件。更有甚者,当时的中国除了商会以外,其它社会团体实力大多较弱,难以在政府决策过程中发挥较大影响,亦即商会缺乏利益竞争的对手。因此,近代中国的“利益团体政治”必然是很不完全的,商会作为利益团体在政府决策过程中的作用也就必然有其限度。我们要重视近代中国包括商会在内的利益团体在政府决策过程中的作用,但不能因此断定近代中国出现了西方意义上的“利益团体政治”,这正如我们要重视近代中国市民社会问题的研究,但不能因此断定近代中国出现了西方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一样。
二、市民社会架构下的商会与政府的关系
近代中国市民社会问题是近年来中外史学界关注的热点。以罗威廉等人为代表的部分西方学者运用“市民社会”或“公共领域”的概念和方法,对近代中国某个城市或地区作个案研究,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但也惹来了以魏斐德为首的另一些西方学者的猛烈批评和争议。最近,不少中国学者也纷纷对此表示兴趣和关注,就此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使“市民社会”的话题在中国近代史领域中蔚成一股风气。其中,商会已被公认为近代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市民社会组织,商会与政府的关系自然也受到论者的关注。
1.商会是西方式公共领域的一部分?
从事近代中国市民社会个案研究的西方学者虽多,但由此明确论及商会者只有David Strand一人。他在《北京人力车:20年代的城市居民和政治》一书中,以20年代的北京为例,描述了早期中国公共领域的发展。他认为,晚清时期中国新兴的经济和社会力量催生了一个由新旧公共团体合成的“新的政治舞台或公共领域”(注: Strand, David.Rickshaw Beijing:City People and Politics in the 1920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p.168.)。这一公共领域不仅给旧绅士和商界精英提供了参与城市政治和活动的渠道,而且给诸如人力车夫、挑水夫等新市民提供了保护他们劳工权益的渠道。而商会便是这个中国公共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由国家正式认可的整理商业、管理城市公共事务的实际权力渐增,商人变得更富于阶级意识,更富于政治独立性,以及“立即利用新的组织促进他们自己的利益”。Strand还指出了这方面的地区差异:在内地和行政城市如北京,商人组织“倾向迁就甚至屈从于官方权力”(注:Ibid,p.100.)。 Strand坚持这个萌芽中的中国公共领域类似近代西欧早期的公共领域,但同时也承认这个公共领域永远不可能达到相对于国家的充分自治或完全独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公共领域内部充斥着派系斗争和私利冲突,且对国家存在一定的倚赖,削弱了公共领域的自治。
Strand的上述观点可以说代表了萧邦齐、罗威廉、Rankin等人对近代中国市民社会问题的典型看法。这种看法认为,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或“市民社会”,就算不是等同于,至少也是类似于近代欧洲早期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其显著特征即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自萧邦齐发表关于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的第一本个案研究专著以来,上述看法已遭到许多学者的怀疑和批驳,以致持此看法的学者也大都修正了自己的立场,对西方“公共领域”或“市民社会”概念是否适用于近代中国持较多的保留态度,许多后来的学者更转到另一条途径上去了。
2.“第三领域”模式:价值判断先行的谬误
在这场学术争论中,美国学者黄宗智提出了一个“第三领域”的模式,用以理解近代中国国家和社会的互动关系。他认为,研究近代中国市民社会问题的学者沿用哈贝马斯有关“公共领域”的较为狭隘的空间定义,预设了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对立,但就中国的实际而言,哈贝马斯的三元概念——国家、社会和介乎二者之间的公共领域更为可取,这个介乎二者之间的公共领域就是“第三领域”。他声称:“第三领域是一个不带价值判断的范畴概念,因此可以避免哈贝马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带有价值判断的目的论色彩”(注:黄宗智:《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第三领域》,载哈贝马斯等:《社会主义:后冷战时代的思索》,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6—79页。)。
黄宗智的“第三领域”模式,立即得到另一学者张晓波的赞同,并将这一概念运用到他的博士论文研究中。他通过对1904至1928年天津商会个案研究后认为,“20世纪初,中国的商会及其它专业社团构成了一个由国家和社会共同参与和互动的中间领域”(注:Zhang, Xiaobo.Merchant Associational Activism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China:The Tianjin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1904- 1928.PhDDissertation,Columbia University,1995,pp.685-686.)。
但“第三领域”真的是处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一个不带价值判断的领域吗?且让我们先看看黄宗智是如何形成关于“第三领域”的想法的。
黄宗智关于“第三领域”的想法,首先来自他对清朝司法制度的研究。他发现,在官府审讯的正式司法制度和民间调解的非正式司法制度之间,存在着由两者互动形成的庭外“和息”解决诉讼的方式。此外,他对华北农村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也显示,清代国家的行政管理止于县一级,县以下的地方公共事务,都由国家和社会透过半官方机构共同参与进行。黄宗智由此受到启发,认为这种由国家和社会合作形成并共同参与的庭外“和息”制度及半官方机构等等中间地带,就是“第三领域”的一部分。黄氏进而认为,在清末民初社会整合及国家缔造的过程中,中国“最明显的变迁,是国家和社会在第三领域不断加强合作。”“新式商人会所便是国家和社会同时卷进第三领域的好例子。新式商会由商人组成,但却是由政府规定成立,并且是在政府的指导之下运作”,它“与地方政府机关紧密合作,获得正式权力,管理官方、半官方的大量活动。”(注:黄宗智:《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第三领域》,第81—85页。)按照黄氏的观点,“第三领域”,尤其是商会,实际上是国家与社会进行互动合作而形成的一个空间。
由此可以见到,黄宗智的所谓“不带价值判断”的“第三领域”,实际上本身就带有强烈的自相矛盾的价值判断成分。因为既然第三领域是国家与社会进行互动合作而形成的一个空间,它的存在就必然要以国家和社会彼此实现合作这一“价值”的“判断”为前提。一旦国家和社会停止合作,“第三领域”也就不复存在。很明显,黄宗智回避了一个既简单而又非常重要的事实:近代中国国家和社会之间,特别是政府和商会之间,除了合作以外还存在大量对立和冲突。因为一谈到对立和冲突,便会接近哈贝马斯国家和社会二元对立的西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模式,从而使他的立论基础发生动摇。如果说罗威廉等人的关于近代中国“公共领域”或“市民社会”的研究带有“结论先行”或“目的论”的色彩,预设了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那么黄宗智的“第三领域”模式则是犯了“价值判断先行”的错误,预设了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合作。
笔者还要指出的是,“第三领域”的模式如果不加区别地滥用,将会给近代中国史研究,特别是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研究带来极大的混乱和危机。因为如果按照黄宗智的概念,则近代中国的一些势力强大的黑社会帮会组织也具备“第三领域”的基本特征和功能,它们也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间地带,与政界人士关系密切,有时也与政府合作处理社会问题。那么我们能不能说,这些黑帮组织是“第三领域”或“市民社会”的一部分,甚至把黄金荣、杜月笙之流奉为市民社会的领袖?显然,“第三领域”模式仅指出问题的一面而忽视了另一面,其分析应用的实效性是十分有限的。
3.“市民社会雏形”和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第三领域”作为一种分析框架或许行不通,但这种模式隐含的主要意念——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论,支持者却大有人在,马敏和朱英两位学者即为代表。
马敏和朱英通过对晚清苏州商会的个案研究后认为,晚清商会组织已经把自己的影响力渗透到城市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以商会为核心,众多民间社团组织纵横交错,从而形成一个官府以外的在野市政权力网络,控制了相当一部分市政建设权、司法审理权、民政管理权、公益事业管理权、社会治安权以及工商、文教、卫生等多方面的管理权,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城市经济和社会生活。两位学者认为,这个在野市政权力网络就是市民社会的雏形,其背后的推动者就是新兴的近代资产阶级(注:马敏、朱英:《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233页。)。
那么,市民社会雏形与国家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朱英指出,市民社会雏形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对国家的特殊依赖性,双方保持着较好的良性互动关系,另一方面也确实对国家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制衡作用(注:朱英:《关于晚清市民社会研究的思考》,《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马敏也认为, 晚清市民社会雏形与封建国家之间形成的是一种既互相依赖,又互相矛盾、磨擦的复杂关系,其中,依赖的一面又占据着主导地位(注: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1页。)。
或许正是意识到“市民社会”或“公共领域”的理论和概念本身的混乱,朱英在他研究市民社会问题的新著中,竭力回避直接或间接套用西方“市民社会”或“公共领域”的理论框架从事研究,而在商会史研究的丰富史料和大量成果的基础上作实证性的探讨。其中,他以商会与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为典型,阐明近代中国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为了避免“价值判断”,他对“良性互动论”也给予了相当大的修正。
朱英指出,近代中国市民社会雏形自清末形成以后,社会与国家两方面均已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开始建构一种新的互动关系。
从国家的方面来看,清末民初的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依赖社会实现新的动员与整合,因而它给予社会某些扶植,成为独立的市民社会雏形孕育萌生的重要因素,但由于近代中国始终未能实现国家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根本变革,无法对社会的发展提供真正的制度性保障,统治者又担心社会权力扩张危害其统治地位,因而国家在对社会予以扶植的同时,又加以各种限制,甚至在自身力量比较强大时即对社会进行扼杀。
从社会的方面分析,近代中国市民社会雏形在清末形成后,取得了相当一部分自治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制衡国家的作用,至民初又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是,近代中国的市民社会始终面对着一个不愿真正放弃既有权力的国家政权,更重要的是本身发展不充分,自始至终都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对国家的特殊依赖性,难以与国家长期抗衡,也无力抵御国家的侵蚀,最终也就难以摆脱被国家强制扼杀的厄运(注:朱英:《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93—494页。)。
朱英对于近代中国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分析建基于从事商会史研究的深厚功力,相当精辟透彻。这样的实证研究,在国家——社会二元互动的分析框架内作传统史学性质的探讨,刻意回避“价值判断”,或许可以避免直接使用“市民社会”或“公共领域”的概念所可能导致的混乱、失误和偏颇,也很容易得出一些结论,但却存在着一种把近代中国纷繁复杂的历史问题和社会现象两极化、简单化的倾向,因而不可避免地仍然带有一定程度的局限性。
三、1928年以后的商会与政府的关系
1.极权主义模式的滥觞与反思
1928年以后,中国进入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对这个时期的商会研究长期以来处于空白状态,几项著名的研究成果均在1928年左右截止,学术期刊上的相关文章也很少。
学术界的上述状况,主要是因为对1928年以后中国商会与政府关系的发展已形成一种定论或共识,即认为这一时期的商会在政府的严厉控制下,原有的地位、作用、影响急剧下降,从事研究已经没有价值。例如,徐鼎新写道:“在整个国民党统治时期,商会与政府之间的法律关系名存实亡,商会完全处于屈从政府意志的附属地位。”(注:徐鼎新、钱晓明:《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400页。)张晓波认为:“至30年代初, 国民党政府透过各种整顿活动, 把天津商会置于其严厉控制之下。 ”(注:zhang,Xiaobo.Opcit,p.686.)朱英也指出:“由于国民党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采取强制手段对市民社会团体进行整顿和改组,并对保存下来的民间团体实施严格的监督与控制,使这些团体大都丧失了原有的市民社会特征。因此,近代中国自清末萌生发展而形成的市民社会雏形,受到极为严重的摧残,可以说已遭到国家的强制性扼杀。”(注:朱英:《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34页。)
徐鼎新、张晓波、朱英等学者对1928年以后商会与政府关系的论述,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而言实际上就是“极权主义”模式。这种模式适用于意识形态和政治控制的一体化社会,认为国民党政府权力全面渗透、有效地组织并控制了整个社会,因而在中央权力之外,任何影响秩序的社会力量都难以存在。
西方学者也持类似看法。Parks Coble Jr指出:“对上海资本家来说,国民党统治的第一年是一个灾难——他们在1927年以前十年中在上海所享有不受政治控制的局面,因近似恐怖的统治而突然结束了。”(注:小科布尔:《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6页。)只有Joseph Fewsmith 运用“合作主义”的分析框架对上海商会作了研究。他认为,1930年上海商会的改组是国民党南京政府企图建立一个合作主义社会的尝试,目的是给予商会及其它社团以垄断性的利益代表的资格,作为对它们在新的政治秩序中服从及合作的回报(注:Fewsmith,Joseph.Party,State,and Local Elites inthe Republic China:Merchant Organizations and Politics inShanghai,1890-1930.Honolulu:Un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85,p.164.)。但Fewsmith也承认,在独裁政权之下, 合作主义的架构是无法真正运作的,商会“不仅不能发挥上达意见和参与政治的功能,甚至成了国家控制社会的工具”(注:Ibid,p.202.)。
极权主义模式真能圆满解释并概括1928年以后政府与商会关系的状况吗?至少在笔者看来答案是否定的。笔者认为,当时国民党政府刚取得全国政权,基础远未稳固,它的权威面临着中国共产党、地方军事实力派和日本三个方面的严重挑战,其它种种内政、外交问题也对它造成极大困扰。在面临重重内忧外患、百废待兴的严峻形势下,国家对社会的强权控制至少在短时期内不可能达到很高的程度,而商会作为当时中国的一股根基深厚、实力强大的独立社会力量,国民党政权对它更是难以实现极权主义控制,即使可以,也只有在南京、上海等国民党政权的统治中枢或接近统治中枢的地域,以及国民党基层势力强大的少数地方(如北伐的根据地广州)才能实现。至于当时国民党势力较弱的中国其它广大地区,商会与政府的关系应该呈另一种形态,这种形态也不是仅采用“合作主义”的分析框架就能解释的,究竟如何,有待于研究者继续探索。但无论如何,这一时期的商会仍应有其发展余地与生存空间,仍应在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和影响。
由此便引发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即商会与国家统治中枢之间的空间距离和商会自主性及其政治能量的相关程度问题。我们知道,天津和上海这两大商会一向是研究者的热门选择,而在地理上,天津邻近北洋时期的首都北京,上海邻近国民党统治时期的首都南京。目前的研究和有关资料已经表明:在北洋时期,远离北京政府的上海商会在政治上的作为以及自主性,比天津商会不知要强多少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当时北洋军阀的势力范围所决定的,而且,天津的长芦盐商正是北洋军阀的经济支柱。但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情况正好相反。上海商会遭到近在咫尺的南京政府的严厉控制,变得无所作为,而远离南京政府的天津商会,在政治上的作为和自主性虽然不及北洋时期的上海商会,却比同时期的上海商会要好得多。当然这除了时空差距以外,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当时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权与华北地方实力派及北洋残余势力之间的矛盾。这就进而引发出了笔者的一个构想:如果分别对两个时期的上海和天津商会作详细的比较研究,会不会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呢?在笔者看来,这样的比较研究是可以为商会与政府关系的学术课题带来突破性进展的。
2.建立一个新的分析框架的尝试
回顾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民族主义和现代化毫无疑问是近代中国最强大的社会思潮,这既是自19世纪中叶西方势力入侵后,中华民族饱尝屈辱、亟思雪耻图强的真实写照,也是近代中国社会内部变革在思想文化层次的集中反映。这股思潮最后自然凝聚为一个强烈的要求:把中国迅速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近代民族国家,跻身世界强大民族之林。这是长期以来几乎所有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共同愿望和要求。当然这个愿望和要求不是凭空就能实现的,必须具备一定的社会和物质条件。所谓的物质条件,即国家的天然资源和为工业化积累的资金、技术和设备;而相对更重要的所谓社会条件,则是指拥有一个领导全国人民建设近代民族国家的政治精英集团和一个占有社会多数财富、能为建设近代民族国家作出实际贡献的经济精英集团。
那么,1928年以后的中国社会是否存在上述两个精英集团?答案是肯定的。北伐战争结束后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就是这样的政治精英集团,是当时中国最强大的政治力量。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声称,要按照孙中山制订的“军政——训政——宪政”建国三步骤,建设“三民主义新中国”。在这一方针指引下,国民党政府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都开始了建设近代民族国家的艰难进程。
而20世纪前期中国社会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便是以商会团体为代表的中国民族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兴起。至1928年左右,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已拥有2000个商会团体、数万个同业公会、数十万商会会员。各地商会的全体成员往往占有当地60%以上的社会财富(注: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28—1937)》,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前言第4页。)。从任何角度去衡量, 以商会团体为代表的中国民族工商业资产阶级都是当时中国的一个实力雄厚的经济精英集团。这个经济精英集团同样拥有把中国建设成为近代民族国家的强烈愿望和要求,并有能力为达到这一目标作出实际贡献。
此外,从1928年北伐战争结束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9 年里,虽然中国面对重重内忧外患,但相对于近代中国的其它岁月,这一时期的国际国内环境仍然算是相对和平及稳定的,这就为建设近代民族国家赢得了一段最起码的时间。
但是,虽然当时中国以国民党为首的政治精英集团与以商会为首的经济精英集团在建设近代民族国家方面怀有共同愿望和要求,但从这一愿望和要求出发,双方在认识上和利益上不可能完全一致。在许多事务上总是既存在共同点,又有着分歧和差异,这就导致两大精英集团形成了一种既一致又冲突的矛盾倾向,为国民党统治时期商会与政府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基本动力。
这一矛盾倾向是在三个层面上展开的:首先,在政治层面上,它表现为政治精英集团力图实行极权主义统治与经济精英集团希望建立合作主义社会之间所存在的一致与冲突。
1928年以后,国民党政府汲取苏联一党专制的治国经验,实行“以党治国”的党治国家模式,对政治和社会生活进行全面控制,目的在于强行组织并调动“党治国家”的全部资源应付对其统治权威的挑战及从事现代化建设,然而这势必引起当时以商会团体为首的独立社会力量的强烈反弹。鉴于近代中国的惨痛经历,以商会团体为代表的中国民族工商业资产阶级其实并不反对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但也绝不认同当局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高压政策,它希望在承认国家控制的前提下建立一种利益表达的机制,争取本身的代表地位和一定程度的政治参与。后来的事实表明,商会团体在这场较量中赢得了胜利,国家与社会之间实际建立的是一种“国家合作主义”的制度。
其次,在经济层面上,它表现为政治精英集团力图推行国家资本主义与经济精英集团希望维护民族资本主义之间所存在的一致与冲突。
现代化首先意味着工业化和经济增长。在如何从事经济建设方面,两大精英集团之间也出现了与政治层面类似的一致与分歧。 本来, 1928年以后国民党政府实行关税自主、提倡国货等措施,对发展民族工商业十分有利,颇受资产阶级的欢迎和好评。但是,国民党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却是“发达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亦即国家要在经济现代化中担负重任。1932年,国民党政府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稍后改组为资源委员会,开始筹措国家资本,进行以国防工业为重心的重工业建设。而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国家金融资本的扩张,国民党政府以发行债券、改组银行、改革币制等方式,逐步把私人资本从金融体系中排挤出去,垄断了金融业。接着,站稳了脚跟的国家金融资本以各种方法向私营工商业渗透,至抗战爆发前夕,中国的许多大型私营企业,特别是经营运输和通讯事业的一些私营大公司,都已收归国营或拥有相当数量的国家股权。国家资本无孔不入的侵蚀严重威胁着民族资本的生存和发展,进而给这一时期商会与政府关系的发展增添了不稳定的变数。
最后,在社会层面上,它表现为政府行政管理职能与商会替代性行政管理职能之间的一致与冲突。
这实际上与前两个层面的一致与冲突存在联系。国民党取得政权后,首先要做的便是按照“党治国家”的模式,建立并强化政府行政机构,特别是社会局的建立,大大加强了政府的市政管理和经济管理的职能,同时配合运用各种技术手段,强化对社会的控制。然而众所周知,由于1928年前中国政局动荡,军阀混战,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基本上处于软弱涣散的状态,很多应由政府行使的行政管理职能,实际上是由商会代替行使的。国民党政府加强行政控制的后果,便是与商会的替代性行政管理职能造成直接性的职能重叠,这就无可避免地要发生冲突。不过,由于商会势力根深蒂固,而且并不想挑战政府的权威,加上国民党政权本身基础未稳,对很多地区、很多事务鞭长莫及,需要借助商会的力量和影响处理行政事务。因此,除了在国民党有效强力控制下的统治中枢与周边地域难以做到,在其它地区双方都能做到互相妥协,协调一致。事实上,1928年以后国民党政府许多重要经济政策,如币制改革、税制改革等都是由商会具体组织实施的。
标签:市民社会论文; 公共领域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社会互动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政治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黄宗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