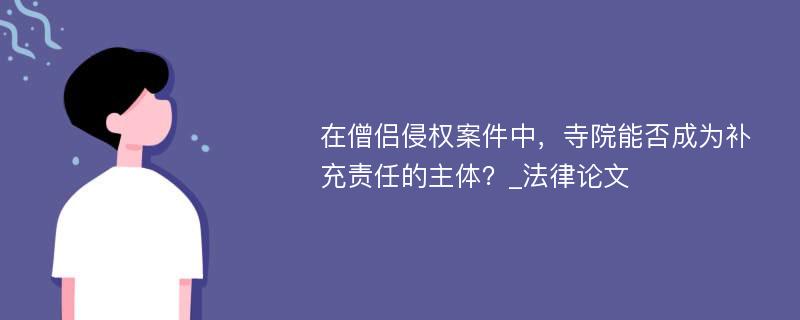
寺院在僧人侵权案件中能否成为补充责任主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僧人论文,寺院论文,主体论文,责任论文,侵权案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汉传佛教僧人作为加害人导致他人人身损害的案件中,如何确定责任主体,是比较棘手的问题,因为它触及了长期被忽视的如何看待寺院、僧团组织、寺院财产和僧人在现代民法上的法律地位等基本问题,涉及对寺院、僧团组织、僧人法律地位的佛教教义解释与现代法律规定的冲突。本文以僧人侵权案件中责任主体的确定为视角,通过剖析现行司法实践中对僧人侵权案件处理,以协调佛教教义解释与现代法律规定的冲突,尝试回答寺院、寺院财产和僧人的法律地位等基本问题,并最终回应僧人侵权案件中责任主体的确定问题。
一、问题之提出
在2008年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何树碧诉成都昭觉寺等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中,终审法院最终确认了一审法院的观点,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12月4日通过的《关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①,认为:“昭觉寺作为社会团体组织,对其管理的寺庙内的游客应尽到合理限度的安全保障义务;同时,昭觉寺作为僧人的管理者,对寺内发生僧人侵害游客安全行为应当承担相应的管理责任”②,因此,昭觉寺应当对受害人在昭觉寺内受到的侵害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
该案件的论证方式和论证结论,直接提出了寺院的法律地位问题和寺院与僧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即寺院内部结构问题。首先,将寺院的法律地位社团组织化;其次,将寺院与僧人之间的关系界定为垂直的隶属性管理关系,而非平等的自治性管理关系;最后还隐含了将寺院财产私人所有化的处理,即寺院财产像私人所有的财产那样,可以承担民事责任。由此引发了一个问题,即这种佛教教义外的解读和认知是否符合佛教教义学说?将这种认知强行施加于寺院是否会损害寺院的利害关系人(佛教信徒及未来信徒)的信任与利益?而僧人是否具有私有财产主体的地位,出家为僧在现代民法,特别是财产法上究竟产生何种法律后果?
二、寺院作为责任主体之证伪
寺院之所以被认为是社会团体组织,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寺院里有僧人居住修行,因此寺院似乎就应当是社会团体。但是从佛教教义的角度看,则未必尽然。寺院可以从两个层面予以解读,一是寺院中人的因素,即僧团组织,二是寺院中物的因素,即寺院财产。笔者认为,无论是从人的因素,还是从物的因素,寺院都不能作为僧人侵权案件中的责任主体。
(一)从僧团组织看,寺院并非社会团体组织。
从僧团组织的功能上说,僧团组织属于自治性僧人组织,也就是说属于平等的自治性组织,而非垂直的管理性组织。因此,有学者指出,原始的或者说理想的僧团组织强调“依戒律共住,依戒律作为处事及行为标准”③,结构上非常松散,基本属于无政府状态。从僧团组织的成立上说,僧团组织并没有自己的财产,僧人“经父母同意、政府批准、合法加入寺院的僧人团体”并不需要缴纳任何财产或者会费之类的给付。因此,可以说僧团组织更强调人的集合,缺少或者说是根本没有财产的因素,且僧团组织更为松散,仅仅追求共同修行的精神性目的,而非任何赢利性或者带有财产性利益的目的。从僧团组织与寺院财产的角度看,僧团组织并不拥有寺院的财产,不享有对寺院财产的所有权或者处分权,寺院财产是无数佛教徒通过捐献、功德等方式捐赠给寺院的,确切地说是捐赠给佛教的宗教活动目的的,而非为其他目的。通过利和同均的分配制度,辅以个人行持与戒法之助成,构筑互敬互利,和合无争的佛教僧团,令僧人在衣食所需不虞匮乏的情形下,专心修行,趋向解脱④。
因此,单纯因为寺院中有人的因素存在,就将寺院看作是社会团体组织,无论是社会团体法人组织⑤,还是非法人社会团体组织,都是有违僧团组织本质的,是强行在僧团组织与寺院财产之间连接了所有权关系,是对社会团体所有权的误解。更重要的是,将寺院解读为社会团体并适用私人所有权的规则,可能严重违反并损害寺院财产的安定性与目的性,动摇信徒对寺院的信任,从而造成对宗教活动的信任危机。所以,对寺院的定位不能从作为所有权人的社会团体组织角度去定位,对寺院财产的定位也不能从按照或者参照私人所有权的定位去思考,必须追问:寺院财产在本质上或者说在法律上应当有何种特殊性?
(二)从寺院财产看,寺院并非寺院财产的所有者。
从新中国建立后国家的行政与立法实践的角度看,对寺院财产的定位隐隐约约地呈现出“从私有财产到公共财产”运动的轨迹,但是这种声音并不是立法的主流声音,而且在《民法通则》、《物权法》等民事基本法中也没有得到体现。如上海,建国初,寺庙的房屋在停止宗教活动后,城镇的房屋一般由还俗僧尼及其家属居住,在农村的,由该寺庙的还俗僧尼于土改时集体或者个人登记取得房屋所有权凭证。这无异是对寺院财产的私有化,其背景在于政治社会对宗教的否定性态度,由此产生严重后果,即私人可以对寺院财产提出所有权主张,有些还俗僧尼因死亡、嫁人或下落不明,部分继续居住的僧尼要求将房屋所有权全部归其所有,有些则是还俗僧尼的子女要求继承房屋产权。⑥1963年中央批准的《第七次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纪要》中指出:“教会、庙观出租的房产,应按私人出租房屋改造的规定办法”,其后,对于宗教房产在政策的掌握上也一向是以私人所有的房屋做参照的⑦。但是在1981年国家最高司法机关和最高宗教事务管理机关的视野中,对宗教财产的法律地位看法已经有所改变,认为,寺庙、道观不论当前是否进行宗教活动,其房屋大都是由群众捐献而建造的,因此,除个别确系私人出资修建或购置的小庙,仍可归私人所有外,其它房屋的性质均应属公共财产,其产权归宗教团体所有。僧尼一般有使用权,但均无权出卖、抵押或相互赠送。而对虽然登记为僧尼道士所有的土改时仍在进行宗教活动的寺庙,应视为僧尼以管理者身份代为登记,仍属公产,不能作为他们的私有财产⑧。不但明确了寺院财产的公共财产性质,而且明确了寺院财产的非流通性、不可转让性、不得私有化性。
2005年3月生效的《宗教事务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32条则明确规定,用于宗教活动的房屋、构筑物及其附属的宗教教职人员生活用房不得转让、抵押或者作为实物投资。由此,寺院财产在国家宗教行政立法上被明确定位为公共财产,而非私有财产。尽管转向公共财产的定位,是我国宗教财产立法的一大进步,但是对该类公共财产的法律特性并没有揭示得完全明白,仅规定了僧尼只能使用而不得出售、抵押和赠与,但对于该财产是否具有可执行能力,即是否可以作为责任财产的定位则不明确。而且对于将寺院财产定性为宗教团体(佛教协会)所有是否妥当仍有待深入研究,其仍然维持了对宗教财产归属的混乱状态,没有回答宗教财产到底是“归社会所有、教会所有或信教群众集体所有”。⑨《条例》第37条关于注销或终止并清算后的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剩余财产应当用于与该宗教团体或者宗教活动场所宗旨相符的事业的规定,又似乎有将宗教财产作为公共信托财产予以规制的意思存在⑩。由此也进一步明确了宗教财产的公共性的内容,即“宗教团体或者宗教活动场所宗旨”的目的性用途。
对于寺院通过出售门票等方式获得的收入,是否足以成为寺院承担僧人侵权的民事责任基础,值得考虑。笔者认为,根据《条例》第21、26条的规定,允许寺院从“经销宗教用品、宗教艺术品和宗教出版物”、从风景名胜区等获得部分收入,但是对所获得的合法收入要求遵守两点强制性要求:一是应当纳入财务、会计管理,二是必须用于与该宗教团体或者宗教活动场所宗旨相符的活动以及社会公益事业(第34条)。因此,可以说,即使寺院可以从某些经营活动中获得收入,也不能成为寺院的责任财产,该收入一方面受到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约束,另一方面受到严格的目的性用途限制,即须用于“与宗教团体或者宗教活动场所宗旨相符的活动以及社会公益事业”,而对僧人的侵权行为承担财产责任显然不能归入该目的性用途之列。
因此,从寺院财产的来源角度看,寺院财产的主要来源为信徒的捐献,而非僧团组织的劳动所得,因此不能成为僧团组织所可自由支配的对象;从寺院财产的目的性用途限制来看,寺院财产的使用应当符合寺院的宗教活动宗旨,寺院财产不能在此目的性用途之外使用,否则即构成对目的性用途限制之违反。综前所述,寺院财产不能成为为僧人承担侵权责任的财产基础。
(三)寺院财产的法律地位:公共财产定位。
综上,寺院财产应定位于公共财产,且应为公共信托财产。按照公共财产在法律地位上的一般特征,结合《条例》的有关规定,可以发现寺院财产作为公共财产,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寺院财产原则上不具有可流通性,也就是说,原则上不得被私有化。这一点已经为我国的最高宗教事务管理机关和最高国家司法机关所肯认。《条例》第32条规定寺院财产“不得转让、抵押或者作为实物投资”,就是为了防止该财产通过市场方式逃脱宗教财产的目的性限制,蜕变为追逐商业利润的营业财产;
第二,寺院财产原则上不得为强制执行的标的。也就是说,在寺院财产管理人被依法强制执行时,寺院财产不得成为强制执行的对象,防止寺院财产被通过非市场方式脱离目的性用途拘束,损害寺院财产的利害关系人(佛教信众)的合法利益。但无论是《条例》,还是《民事诉讼法》并没有规定这一点,因此造成了司法机关认为宗教财产可以得为僧人的侵权行为而被强制执行的局面,寺院财产的该特性应当得到立法的尊重;
第三,寺院财产原则上不适用取得时效的规定。寺院财产作为公共财产,既然供公共使用,则作为一种取得所有权方法的取得时效制度适用于该财产就会导致该财产所有权或者其它财产权利的移转,会危及到该公共财产所负担的宗教性目的用途的实现,使得寺院财产可以通过私法方法逃避为宗教用途使用的目的性限制,危害宗教活动的公共利益。(11)这一点由于我国《物权法》并未规定时效制度,因此,虽不需要言明,但是,在观念上必须明确,无论是任何人占有寺院财产,也无论占有的期限有多久远,均不能取得寺院财产的所有权;
第四,寺院财产原则上不得公用征收。对于公用公物除先废止其公用外,不得进行征收。“没有必要对那些不用征收即已处在全社会公用中的物适用征收”。(12)《条例》第33条对宗教不动产的征收(即所谓的拆迁)有特殊的规定。首先,在征收程序上,要求因城市规划或者重点工程建设需要拆迁宗教团体或者宗教活动场所的房屋、构筑物的,拆迁人应当与该宗教团体或者宗教活动场所协商,而且应当征求有关宗教事务部门的意见。在该协商程序中,宗教团体或宗教活动场所以及宗教事务部门的同意具有实质性意义,即不同意则不能进行拆迁,这一点与普通的拆迁情形有别;其次,在拆迁补偿问题上,各方协商同意拆迁时,则拆迁人应当对被拆迁的房屋、构筑物予以重建,或者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按照被拆迁房屋、构筑物的市场评估价格予以补偿。值得注意的是,颁布在先的《条例》第33条与颁布在后的《物权法》第42条在补偿问题上有明显差别,《物权法》只是强调“依法给予拆迁补偿”,没有规定补偿的标准,而《条例》则不同,不但明确了要给予“按照被拆迁房屋、构筑物的市场评估价格”的补偿,而且还增加了“重建”的补偿方式,也就是特别强调完全补偿,这一点与《物权法》的“适当补偿”立法意旨迥异。
因此,可以说,无论是从寺院的人的因素,即“僧团组织”,还是从寺院的物的因素,即从“寺院财产”角度看,寺院不具备成为民事责任的主体资格与财产基础。
(四)追寻寺院安全保障义务的边界。
2009年12月26日通过的《侵权责任法》第37条的表述,脱胎于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将安全保障义务人的责任定性为补充责任,即只在侵权责任人不能承担的财产责任部分承担赔偿责任(13)。但是也有所不同:首先,将适用范围从“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进一步扩大为“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其次,将“其他社会活动”更加明确为“群众性活动”;最后是将责任主体更加明确地表述为“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而非司法解释所谓的从事“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对于寺院是否要承担安全保障义务,首先应考虑,寺院是否属于第37条第1句前段所谓的“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其次考虑,寺院是否属于该句后段所谓的“群众性活动”?从该句前段的列举来看,所涵盖的公共场所均属于商业性质的公共场所,是为了吸引潜在的消费者而开放给不特定公众自由造访的商业活动进行场所,而寺院虽然也开放给不特定公众造访,但是寺院不是从事商业活动的场所,其开放公众造访的目的不是为了吸引潜在的消费者,而是开放给信仰或者不排斥佛教信仰的善男信女(游客)为精神目的而进行的自由精神性活动,而且寺院的开放亦非自由开放,也就是说并非是任何人均可无需许可而进入的,寺院往往为了出于文物保护、人流控制等目的而设置进入许可,如出售门票、付费进入等。因此,寺院不属于第37条第1句前段所列举的公共场所。从该句后段的表述来看,群众一词是政治用语,不是法律术语,由此导致在实践中如何定义“群众性活动”,如何如何界定组织者责任,是一个颇具争议性的难题。具体到在寺院进行的宗教活动而言,需要具体分析相关情况。一般情况下善男信女入寺上香游玩不属于有组织性的“群众性活动”,而是善男信女自发自主的个人行为。若是在寺院举行佛经宣讲会、佛学研究会等目的性、群众性和组织性较为明显的活动时,则宜认定为有组织的“群众性活动”。在本文所研讨案例中,并未证明受伤害的游客是为着参与寺院举办的有组织的群众性活动而来,其游客身份恰好证明了其入寺是普通善男信女的自发自主行为。因此,不宜将寺院列为承担安全保障义务的组织者之列。
但是,应补充说明的是,寺院作为公共财产的管理人需要对所管理的寺院财产发生的物件损害承担责任。如寺院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倒塌造成他人损害,从寺院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寺院中的堆放物倒塌造成他人损害,以及因寺院中的林木折断造成他人损害等情形须承担安全保障义务。这也是符合寺院作为公共信托财产管理人的角色所应承担的义务,在管理人履行职责没有过错的情况下,对公共信托财产所导致的物件损害,可以寺院所获得的动产,特别是以货币资产承担责任。
因此,可以说,寺院的安全保障义务主要侧重于对物的安全保障义务,仅在寺院专门举办的有组织性的群众活动场合,才承担组织者的安全保障义务。
三、僧人作为责任主体之证成
在身份关系上,按照佛教“出家无家”的教义,出家为僧,即意味着脱离父母家庭,断绝尘缘,直至断绝与世俗家庭的关系(14),离家潜心修道。在民国时期,大理院仍有将和尚(僧侣)出家脱离家族关系作为继承开始的原因,认为:“出家为僧,即为法律上脱离家族关系之一原因,其俗家之得为立继,自系条理上当然之结果”。(15)由此导致在理论上僧人在出家后实际上不能继续拥有家庭财产。此外,在财产关系上,除按照佛律可拥有三衣六物外,禁止僧人私蓄财物。僧团实行财产共用,排斥僧侣私人所有。(16)
但是在长期的弘法实践中,僧人在出家期间又可能取得相当的财产。其取得途径包括:经忏收入,即通过为活着的施主消灾祈福,为死去的灵魂超度诵经、讲经、做法事所得报酬;知识产权收入,有部分僧人具有渊博的佛学知识,通过著书立说、出版佛教音乐作品等拥有知识产权,获得相应的收入;受赠财产,僧人个人接受馈赠所取得的财产(但寺院住持等作为寺院代表人所接受的赠与财产应属寺院所有而非其私有财产(17);其他合法所得,如存款利息等。(18)
但是无论是现行《宪法》,还是《民法通则》均保护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由此导致僧人身份与公民身份所产生的权利义务的不一致。我国行政与司法实践比较关注的是僧人的遗产继承问题,也就是僧人死亡后,其遗产应由俗家亲属继承,还是由寺院取得?综观近30年最高人民法院和国家宗教事务局的实践,可以发现:最高司法机关虽屡受僧人遗产继承问题之困扰,但是由于其涉及佛教的宗教教义,其意见逐渐转向拒绝作出司法解释,但指出了自己的倾向性意见。在《答复》(19)中,最高司法当局虽然同意作为继承纠纷不能否认僧人继承人的继承权,但是却暗示下级法院最好作调解处理,主要是考虑到宗教事务的特殊性,特别是强制执行中的问题。但是没有回答,倘若是双方不愿意调解,又当作何处理?也没有说明,如果按照继承纠纷审理后,能否强制执行寺院财产,是否违背了佛教的宗教教义?而在《复函》(20)中,最高司法当局一方面坚持僧人亲属的继承权不能否定,另一方面又将僧人个人遗产继承问题归结为立法上的空白,属于法律的缺位,需要从立法上的解决,拒绝依据宗教教义和教规作出有利于寺院的司法解释。两个司法解释的立场均是一致的,即依据保护私有财产的理念,强调对圆寂僧人亲属继承权的保护。但我国最高宗教事务机关则倾向于认为僧人遗产应当由寺院继承处理,而否定俗家亲属的继承权。笔者认为,对二者之间矛盾,可以采取如下方式解决:
第一,僧人在出家期间积蓄的私人合法财产应受法律保护,而且可以成为其责任财产;
第二,僧人在出家期间积蓄的私人财产,俗家近亲属不得继承。根据佛教教义,出家需经过父母(家庭)同意、政府批准、寺院接纳等程序,以此要求僧人及其继承人慎重考虑是否加入僧团组织。一旦加入僧团组织,对僧人而言,意味着僧人与俗家亲属脱离家族关系,也脱离经济权利义务(特别是抚养、赡养)关系,僧人从此归属于僧团组织,与该组织发生身份上的、信仰上的和经济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僧人即受寺院的供养,而与俗家亲属无关;对其近亲属而言,意味着俗家亲属与僧人脱离家庭关系和经济关系,放弃对僧人在出家后所积累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也不承担对僧人在出家期间生老病死的抚养、赡养义务;对寺院而言,意味着寺院承担支付僧人在出家期间生老病死的一切费用的义务,并取得对僧人遗产的继承权。因此,若将僧人遗产由僧人俗家亲属继承,势必造成不公平之结果,而且对于僧团组织的维持与发展产生消极性影响。(21)
因此,可以说,僧人私有财产的主体地位虽不容否认,但其私有财产地位具有特殊性,即其私有财产可以为僧人在生存期间使用、支配,但不能为其俗家亲属所继承,而应在其去世后由寺院取得。一方面,这符合佛教教义和传统仪轨,也符合僧人本人、僧人俗家亲属、寺院僧团、政府四方就出家为僧问题达成的事实契约;另一方面,也符合《继承法》的立法本意。全国人大法律工作委员会有关法律专家曾明确表示:从立法思想上说,僧人的遗产其俗家亲属不能继承。(22)
综上可以说,在本文所研讨的案例中,僧人应为侵权行为的责任主体,应当以其所有的私人财产承担对受害人的赔偿责任,而寺院对一般游客入寺游玩并不承担安全保障责任,因此,不应当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四、结论
寺院财产具有公共财产的性质,尤其是具有公共信托财产的特性,僧团组织和不特定的、显在的和潜在的、现在的和未来的善男信女为其受益人,寺院对该财产而言居于受托管理人的地位,不能任意处分该财产,该财产只能用于与佛教教义相符的宗教活动,而不能用于其他目的。对游客而言,寺院仅对该财产所可能造成的物件损害承担安全保障义务。只有在寺院自己举办的有组织性群众佛事活动中才对活动的参与者承担《侵权责任法》上“组织者”的安全保障义务。而对个别僧人的侵权行为寺院不应承担安全保障义务。这是因为僧人即使加入僧团组织也不丧失其在现代民法上的私有财产主体资格,对其在出家期间合法取得的私有财产,与其他公民的私有财产一样,享有法律赋予的对占有、使用、收益和有限处分权能的保护,因此可以成为其承担责任的基础财产。但僧人在出家期间合法取得的私有财产,具有与其他财产不同的特性,即在僧人合法财产的继承问题上,应当按照佛教教义和传统仪轨处理,其俗家亲属不能继承,而由寺院取得,这是由于出家为僧的所导致的身份关系、供养关系的变化所导致的。
注释:
①该条规定,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第三人侵权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由实施侵权行为的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有过错的,应当在其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赔偿权利人起诉安全保障义务人的,应当将第三人作为共同被告,但第三人不能确定该条规定,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第三人侵权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由实施侵权行为的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有过错的,应当在其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赔偿权利人起诉安全保障义务人的,应当将第三人作为共同被告,但第三人不能确定的除外。
②参看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成民终字第893号民事判决书。
③济群法师:《佛法修学次第》,福建省新闻出版局2007年准印,第13页。
④李佳静:《早期佛教僧团管理的经济制度——利和同均》,《宗教学研究》2006年第2期,第186页。
⑤洪源:《关于寺院、僧侣、活佛的法律法地位与财产所有权刍议》,《西藏研究》1999年第1期,第78页。
⑥参看《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宗教事务局关于寺庙、道观等房屋产权归属问题的请示报告》(1980年11月11日)。
⑦参看《上海市宗教事务局关于宗教房产不宜列入公房进行出售的请示》(沪宗请字[1995]第03号)。
⑧参看《最高人民法院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关于寺庙、道观房屋产权归属问题的复函》(1981年1月27日)。
⑨参看《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关于对宗教房产不宜列入公房进行出售问题的复函》(国宗函[1995]059号)。
⑩参看《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2001年4月28日通过)第72条。
(11)翁岳生主编:《行政法》,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467页;王利明主编:《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及说明》,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273页;梁慧星主编:《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条文、说明、理由与参考立法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18页。
(12)[俄]M.B.维涅茨安诺夫:《从民法的角度看征收》,张建文译,《私法》(总第14卷),第231页。
(13)杨立新:《侵权责任法草案20大争论焦点》,《法制日报·周末》,2009年1月9日第6版。
(14)佛教主张无君无父,不敬王者,不拜父母。在传统的儒家学说统治的社会中,断绝家庭关系被视为对儒家孝道理念的背弃与对抗,因此受到统治者的严厉谴责和镇压(参看鲁统彦《从出家无家到出家而有家——唐代僧尼孝道伦理现象略析》,《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第80页),如明代就规定了僧人与其生父母的关系,认为即使僧人遁入空门而不尽孝道,作为化外之人也须拜认父母及祖先,全其“亲亲、尊尊”的大义(参看任晓兰《论明代的僧人群体及其法律规制》,《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第76页)。尽管统治者从外部施加压力,以求佛教教义与儒家学说的圆融洽和,但是相对于外部压力的非持久性,作为内生的佛教“出家无家”思想仍然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
(15)刘春茂主编:《中国民法学·财产继承》,北京: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
(16)丁菁《佛教僧侣财产权探析——宗教财产权研究之一》,《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第47页。
(17)浙江绍兴石佛寺住持本耀立下遗嘱将名下现款与存款除办理后事所需开支外,均归生前服侍其生活起居的原告朱水花所有。后被继承人去世,原告要求继承所遗存款66万多元,被告绍兴县佛教协会主张该住持的存款属于石佛寺共有,该住持无权对寺院的共有财产进行处分,所立遗嘱无效。两审法院基于原告无法证明该存款为被继承人的个人合法存款且其僧人身份特殊而拒绝支持其诉讼请求(参看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03)浙民一终字第134号民事判决书)。
(18)丁菁《佛教僧侣财产权探析——宗教财产权研究之一》,《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第47页。
(19)参看:1987年10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关于钱伯春能否继承和尚钱定安遗产的电话答复》([1986]民他字第63号)。
(20)参看:1994年10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对国务院宗教事务局一司关于僧人遗产处理意见的复函》。
(21)张建文:《汉传佛教僧人的遗产继承问题》,《佛教文化》2009年第3期,第89页。
(22)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教协会关于僧人遗产处理问题的覆函》,《法音》,1993年第3期,第4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