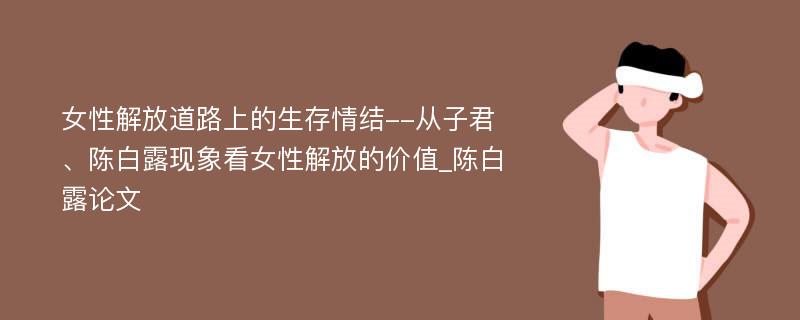
女性解放道路上的求生情结——从子君、陈白露现象看女性解放价值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性论文,情结论文,价值观论文,现象论文,从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子君和陈白露,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学中两个女性解放失败的典型,前者被称为“回到家庭中的娜拉”,后者被称为“堕落的娜拉”。至今为止,中国现代文学女性价值观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女性生存情结问题,一直被某种道德观念若隐若现地束缚着,要打开这个理论上的禁区,首先需要改变观念,也需要回顾一些历史的话题。
1923年12月,鲁迅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作了《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注:《鲁迅全集·坟》,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8页。 )。鲁迅指出,娜拉出走之后,如果不能在社会上取得经济独立自主权,不能独立生活,摆在她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堕落,一条是回来。1925年,鲁迅在小说《伤逝》中,用子君追求婚恋自由终于失败的故事,较早地揭示了女性解放道路上出现的坎坷和倒退现象。1936年,曹禺在著名话剧《日出》中,塑造出一个高级交际花陈白露的形象,又从另一个角度,丰富证实了鲁迅提出的“堕落”、“回来”理论的正确性。大师们的理论和作品,对现代文学和女性文学形象的研究,一直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由于中国社会的文化环境过于复杂,女性解放的道路上充满了崎岖和痛苦,光使用一种现成的理论模式来套评和分析女性文学作品,在今天看来就显得单调而不适用了。因为即使在子君和陈白露这类的女性文学形象中,也包含着现代女性走上解放道路时,所遇到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即女性的生存情结问题。这些女性,在走上初期的反抗道路的同时,首先必须学会怎样自己养活自己,怎样在社会上取得经济独立的自主权,由此而产生出来的女性悲剧性格,引发出来的复杂多变的女性心理意识,往往比她们的悲剧故事结局更加引人注目,更能透视出旧时代的中国妇女在社会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所处的真实地位。如果我们把研究视点集中到这方面来,对早期女性文学形象,就会得出一种符合时代精神的新看法。
一、女性解放道路上的天然怪圈——无奈的人身依附
“回到家庭中的娜拉”曾经是子君的代名词,子君之所以遭到涓生的抛弃,回到她反叛过的父权家庭,被折磨而死,从表现上看,是她性格上缺少像涓生一样寻求新生活的勇气,而把自己的追求目标,全部放在当好家庭主妇上面。当这个小家庭的吃饭生计问题发生危机、负担全家经济收入的涓生不得不下决心毁掉“爱巢”的时候,子君便成为这个破裂家庭的牺牲品。实质上,子君的悲剧是因为她没有能力在社会上取得经济独立的自主权,从父亲的家庭到涓生的家庭,她都依附于男人,靠男人的供养来生活,一旦这所建筑在沙滩上的房屋倒塌下来,首先毁灭的当然就是她自己。
从男性方面来说,涓生抛弃了子君,虽然也有寻求新路和自我超脱的一面,实际上同样隐含着一个经济方面的重要原因,就是他失业了,没有经济收入来源,投出去的稿子又不被采用,陷入了走投无路的生活困境。小说虽然没有明写涓生不愿意再养活子君了,但读者完全可以感觉到,如果经济条件稍微好一些,涓生做出抛弃子君的决定,可能会更迟缓一些,至少不会那样坚决地把子君推向绝路。
由此可见,鲁迅在讲述一个青年婚恋故事的同时,也透露出另外一种社会生活信息,即对“五四”时期的青年一代在社会上所处的经济地位问题,进行了深切的反思。青年是最富于革命激情的,他们往往是一些社会先进思潮的追随者和代表人物。但当这种思潮结束时,他们的理想和幻想,也会在社会现实面前被碰得粉碎,留下的只是像诗一样的独白和叹息,子君和涓生走过的正是这样一条理想破灭的道路。同时,青年一代又因为没有社会地位,没有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一旦在生活上失去了短暂的支撑能力,就会陷入比精神上的失落更加严重的打击。对涓生来说,支撑一个小家庭的开支,显然要比餬住自己的一张嘴要困难得多,可以说,他是在经济上不堪负重的情况下,做出毁灭这个小家庭的决定的。鲁迅在《伤逝》中,不仅揭示了“五四”青年在精神素质、心灵差异方面产生的悲剧,而且写出了他们在社会上挣扎奋斗,最后不得不败下阵来的经济能力低下的悲剧。
青年一代中的男性涓生,尚且不能冲破社会为他们设置的经济生活的网,不能随心所欲地取得经济独立的自主权,那么,完全没有取得经济独立自主权的女性子君,也就更谈不上去进行更高层次的反抗斗争。在“五四”时期,追求个性解放婚姻自由和男女平等,男女两性同时享有经济独立的自主权,是知识女性应该使用的反封建斗争的双重武器,而子君却完全没有睁开她的第二只眼睛,当她在追求婚恋自由方面的斗争遭到失败时,她无法保护自己不受到男权社会的再一次伤害,终于走进了女性解放的死胡同里。
从理论上说,20年代旧中国的社会环境对女性取得经济独立自主权的压迫,决不比古代社会更轻松些。然而时代变迁了,在20年代,也有一部分先锋女性,成功地踏上了社会解放斗争和经济解放斗争的道路。尽管这种女性为数不多,但她们的人生道路和斗争结果都表明,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女性不但可以获得人格自由和婚姻自由,还可以用自己的智慧劳动换取一定的经济收入,取得或部分地取得经济独立的自主权。如20年代活跃在文坛上的女作家丁玲等,不但赢得了爱情的自由和幸福,而且还能够靠写文章挣稿费来维持自己的生活,至于40年代的女作家张爱玲,还能用稿费资助别人的生活。在其他社会行业中,为经济独立自主权而奋斗的女性也颇有人在。离开知识分子的生活圈子,考察一下下层市民阶级中的女性,她们因为没有文化,社会地位更加悲惨,但在争取女性的生存权力和经济独立自主权力方面,则表现出比知识分子更加顽强的意志和乐观精神。由于出身低下,这些女性天生就养成了为每天能吃饱一顿饭而抗争的性格,如郁达夫笔下的20年代的上海烟厂女工陈二妹,许地山描写的在京城里以拣破纸为生的女人春桃等。她们的劳动,虽然最多只能维持生存,甚至常常饿肚子,但从社会效果来衡量,这些下层女性通过劳动,确实取得了自己的经济独立自主权。事实证明,只要女性的自身觉悟和求生意识提高到一定程度,无论社会为女性提供的经济生存的空间多么狭窄,多么可怜,女性都有可能在困境中找到一条出路,相对地取得自己应该得到的那部分经济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女性的自身素质、生存欲望和抗争精神,又是决定女性能不能坚持斗争,能不能取得经济独立自主权的关键因素。而子君的悲剧,就在于她一直到死,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究竟缺少什么,失去了什么,没有觉悟到自己应该和涓生们一样,去争取女性的经济独立自主权。
二、女性解放道路上的人为怪圈——逼良为娼
旧中国的社会制度,不仅对懦弱的子君们进行剥夺经济独立自主权的压迫,使她们在死亡线上葬送青春生命,而且对怀着强烈的求生欲望,为女性的生存权力忍辱奋斗的下层妇女们,施加种种精神上的凌辱,把她们逼上社会生活中的另一个怪圈,走上做舞女做暗娼的道路而不能自拔。这类女性的精神状态、内心世界以及她们在女性解放运动中发生的作用,更应该引起我们的特殊注意。
1936年,老舍在著名小说《月牙儿》中,讲述了一对无辜善良的母女为生活所迫沦为娼妓又被社会所不容的悲惨故事。“小说中的母亲是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苦苦挣扎,最后为不使自己和女儿饿死才沦为暗娼的。女儿更有意识地向命运反抗过,她为了不走这条使她憎恨的道路而离开了母亲。但残酷的现实使她明白了,她生活着的是个地狱似的世界,为了不饿死,许多妇女都逃脱不了被玩弄的命运,她也终于走上了她母亲所走的那条道路。”(注:钱谷融、吴宏聪主编:《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第449页。)通读作品, 我们发现,这对母女在沦为暗娼的过程中,为坚守社会道德而作的心灵搏斗,远比她们出卖肉体、挣钱换饭更令人感到压抑和痛苦。如果说在“饿死”和“做暗娼”之间进行选择,她们选择了后者,这非但不能说明她们没有道德良心,而是表明这些下层妇女为了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力,在进行合法的抗争。
在旧中国的男权制度中,女性惟一的生活出路和归宿,就是被捆绑在家庭中做贤妻良母。即便这种严重扼杀女性生机活力的灰暗生活,也并不是所有的女人都能过得上。像《月牙儿》中的母女二人,她们做梦都想嫁一个男人,好好过日子,可是因为穷,没有哪个男人愿意娶她们为妻,她们也就只能依靠自己的能力生活。即使走上了做娼妓的道路,也是自立自强的一种表现。面对这类妇女的特殊遭遇,我们往往一边诅咒黑暗的旧社会逼良为娼,把人变成鬼,一边又在思想深处认为她们的行为不道德,不能理解她们的无奈的选择,岂不是有点自欺欺人,滑稽可笑?从人格上说,无论哪一种女人,只要她们有一种坚强的生存意志,靠自己的劳动创造了财富,又能保护自己不被旧社会吞掉,就总比她们在男权家庭里含泪讨生活、要饭吃更令人敬佩。因为女性解放的基点是要建立一个最起码的人格价值尊严的底座,要争取女性的人格独立和人格尊严,首先要保证女性能够在社会的重压下活下来,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真正落实在行动上,并不是所有的理论家都能接受和认同的。
在女性解放的斗争史上,女性革命运动的先驱者和风云人物,往往都是像秋瑾一类的女知识分子或大家才女闺秀,而那些最下层的市民阶级的女子,非但没有能力登上女性解放的政治舞台,崭露头角,甚至连最起码的生存权力都要受到践踏,求生无路,求死无门。这些女性,从来没有喊过什么激动人心的口号,甚至也没有意识到自己为求生存而进行的挣扎奋斗,是女性求解放的一种最直接的精神欲望的表现。但她们的抗争行为,从实际意义上来说,确实是支持和顺应了女性解放的伟大目标,等于是间接地参与了女性解放的斗争过程。因为沦落的生命不等于零。有了生命才能达到更高层次的觉醒,进而达到更高层次的追求。而子君们的默默死亡,最多只能换来几滴同情的眼泪,甚至连同情的眼泪也没有。相比之下,那些被迫沦为娼妓之后仍然顽强求生的女人,是下层女性中的勇敢者一族的代表,她们的生活是血泪斑斑的,她们的精神灵魂却应该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
如果从经济效益方面来考察,这类妇女的劳动,也产生了一定的社会价值。在旧社会的北京城里,一个贫苦的市民家庭中,有一个女人去做暗娼,来养活一家老小的生活,是小说和文学作品中经常描写的普遍事实。《骆驼祥子》中的小福子,《日出》中的翠喜,都是典型的下等职业妓女,她们不但要负担全家人的经济收入,生活开支,还要忍受自己家人的侮辱打骂。在旧北京城里,一个下层市民家庭中的男人,不过是靠拉洋车、糊棚、卖艺、当巡警等下等劳动,来养家餬口,维持生活;那些沦为娼妓的妇女,也做到了和男人同样的事情,也充当了家庭生活的顶梁柱。面对这种现实,我们还有必要站在所谓的社会道德的立场上,去讨论这些为娼妇女人格价值的高低上下吗?当然,为娼生活从来不是中国妇女求生存求解放的光明之路,中国妇女求职就业的理想,只有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够真正得到实现,全面合理地进行解决。但在历史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与其让那些妇女和家庭在死亡线上挣扎、死去,还不如对她们的特殊劳动形式和劳动价值做相对的肯定,把它看作是特殊的历史时期里女性生存就业的一种不得已的行为方式。因为这种劳动既养活了自己又养活了家庭,确实取得了某种社会经济效应,不能因为她们的劳动方式的不正常、不体面,就一并给予批判和挞伐,忽略了女性在求生存求解放过程中付出的不同寻常的代价,这不是女性文学研究的科学方法。
现代女性的生存观和价值观,与生俱来就应该是丰富多彩的,多元化的。而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中国女性只能固守着同一道德观念,同一生活方式,在男权制度规定的极其有限的生活空间里挣扎着活下去。到了现代社会,那些规范禁锢女性的传统道德观念,传统社会思想意识,在商品经济较先发达的大都市里,已经开始被无情地打破了。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加速了城市生活的贫富两极分化,选择以经济价值为中心的人生道路。《月牙儿》中的女儿,在沦为暗娼之前,曾经有过一段非常激烈的内心活动,很能引起我们的深思:“什么母女不母女,体面不体面,钱是无情的。”人在没有饭吃的时候,什么道德,良心,自尊,一律变成了空话。这充分说明娼妓职业现象的产生,绝不仅仅是因为良家妇女的道德沦丧,而是现代社会的经济生活结构发生变化之后,带来的女性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方面发生变化的必然结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中的传统道德观念、社会思想意识,早已发生了深刻的裂变和解体。当前,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的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就是卡拉OK歌舞厅的繁荣和“地下性产业”的兴起。从正面说,都市人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去歌舞厅消遣娱乐,恢复精力,再投入到更加紧张的生活节奏中去,这是正常的现代化生活的需要。从负面说,歌舞厅和啤酒屋的增加,也相伴带来了色情服务和“三陪”现象的屡禁不绝。“三陪文化”和“地下娼妓文化”现象的产生发展,已经引起了整个社会文化界的注意,并加以严肃的理论探讨(注:参看潘绥铭:《存在与荒谬——中国地下“性产业”考察》,群言出版社1999年1 月版。)。笔者无意涉及“三陪”和娼妓问题的讨论,只是由此联想到,当年北京城里出现的暗娼(暗门子)和今天歌舞厅里的“三陪”暗娼现象之间,究竟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今天的“三陪”暗娼们,在加入“地下性产业”大军队伍之前,她们的生活处境、社会地位、经济条件和《月牙儿》中的母女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无论什么原因使她们步入了“性产业”的行列,但总之绝不是因为饥饿得生活不下去才端起这个饭碗。今天,我们也很少听到社会上有人用道德观念指责她们,反而能够站在商品经济观念的立场上,去认真研究对待这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这说明,无论在哪一种社会形态中,商品经济的价值规律,都会对中国女性的生存意识、道德观念及心理行为方式,产生极为重大的影响。老舍在30年代的《月牙儿》中传达出来的故事信息,竟和中国当前社会现实生活的娼妓现象问题发生了如此联系,这不能不触发我们对女性文学作品中的有关娼妓题材的问题,包括娼妓文学形象,进行严肃认真的再思考。
三、怎样评价陈白露的形象——为“堕落的娜拉”正名
把一个交际花和一个女性解放的典型形象联系在一起,称陈白露为“堕落的娜拉”,这种说法本身就非常耐人寻味。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对陈白露形象的评价,一般都强调她“身陷魔窟而不甘堕落”(注:辛宪锡:《曹禺的戏剧艺术》,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27页。)的矛盾性格,或者把她当作一个“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受害者,一个宁愿自杀,也不在群鬼圈子中厮混下去的年轻交际花。一个过着“舞女不是舞女,娼妓不是娼妓,姨太太不是姨太太”的荒唐生活的女性形象,能够得到上述评价,也算是有了一个公正的说法了。然而在这些“怜花惜玉”般的措词里,我们仍然发现,过去的评论观点,并没有把陈白露的人生道路的选择和女性解放的大前提大背景结合起来,因而忽略了陈白露性格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即她对方达生规劝她“从良”时,表现出来的那种斩钉截铁的态度,在拒绝方达生的“爱情”时,陈白露为自己的生活作了一番颇有自信的辩白:
你知道什么叫名誉!我这里很有几个场面上的人,你可以瞧瞧,形形色色银行家,实业家,做小官的都有。假若你认为他们的职业是名誉的,那我这样弄来的钱要比他们还名誉得多。
陈白露告诉方达生,她即使用出卖色相换来的钱养活自己,也比社会上那些所谓体面人物靠杀人害命挣来的钱都干净,都名誉,她付出了一个女人最可怜的义务,她享受着女人应该享受的权力,方达生却根本无法理解陈白露的人生价值观。流落风尘的陈白露,并非像方达生想象得那样不堪救药,她在群鬼面前周旋时,仍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高傲的个性,她对落入虎口的下等妓女充满同情,用自己的全部能力和黑社会势力进行较量,企图把“小东西”救出来,因失败而绝望,在厌恶自己,厌恶生活的强大内心压力下自杀,结束了23岁的年轻生命。陈白露用死来否定了自己的生活道路,用死来反抗了黑暗腐烂的脓疮社会,也用死来回绝了方达生对她提出的“从良”要求,这最后一点,正是陈白露性格中最值得注意的闪光之处。
陈白露经历过“平淡,无聊,厌烦”的婚姻生活,受过丈夫的打骂。在离家出走时,她的精神状态和《玩偶之家》中的娜拉有些相似。她们都不是因为生活贫困被丈夫抛弃,而是主动觉醒,要到社会上去寻找出路。娜拉出走之后的结果如何,我们不知道;陈白露出走之后,把自己推向社会,当上了红舞女、电影演员、交际花。为此方达生才给陈白露指出一条远离“放荡”、“堕落”的黑暗生活的光明之路,让她再次回到家庭中去,做贤妻良母。也就是说,陈白露并不是一个走投无路的女人,她也不一定非要去自杀,如果她想活下去,她还可以再找一个有钱有势的靠山,或者考虑一下方达生的建议,但她还是宁愿选择死亡,也不愿去过丧失女性人格的人身依附生活。她说:“我一个人闯出来,不靠亲戚,不靠朋友,能活就活,不能活就算。到了现在,你看我不是好好活着,我为什么不得意?”这段话中自然包含着很多无奈和痛苦,但确实是脱离了旧家庭生活的保险圈之后,取得了独立人格尊严的女性发自内心的一种感觉。她没有依靠任何人,凭着自己的能力活到今天,而且她还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地死去。正是这种任性任情的性格,培养了陈白露的傲气和自尊,使她对社会人生始终怀有一种强烈不安的挑战欲望。无论如何,她已经在险恶的魔窟里生存下来,驾驭着自己的生活,并且掌握了自己的经济命运的自主权。
方达生自认为是陈白露的风尘知己,主动扮演“英雄救美”的角色,要把陈白露拉出火坑,读者和观众不禁要问:他们在一起,结果一定会幸福吗?如果陈白露从良之后,不改变她的高傲本性,方达生怎么能够驯服她,把她变成贤妻良母?如果方达生和陈白露的结合失败了,他会不会翻过脸来,骂陈白露是婊子、娼妓、本性难移?这完全有可能。因为在搭救陈白露之前,方达生已经为她设计好了一套“从良”之后的生活方式,他希望陈白露能像他想象得那样生活,如果陈白露不像一个泥娃娃那样,任由别人去捏弄塑造,方达生的满腔希望破灭,他还会喜欢她吗?他不把这个“泥娃娃”砸烂就不错了。一个根本就不再是泥娃娃的女人,怎么可能再去做回贤妻良母呢?与其说陈白露是因为过惯了“放荡”生活而无法接受从良生活的约束,不如说她用死来结束了自己的“放荡”生活的同时,也用死来抗拒男人为女人设置的死活都冲不破的家庭生活的陷阱,这种选择是非常明智的。这正是陈白露反叛性格的最真实的表现,是陈白露反叛性格的焦点,陈白露的自杀爆发出的震撼人们心灵的力量,应该在这里。
现在,我们不能用“冰清玉洁”来形容陈白露的一生,但用“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来给她的人格和品格下一个相对的定论,总不至于抬高了这个舞女的身份地位,硬把一个倡优说成是节妇,从而践踏了传统女性都应该恪守不变的封建妇德吧?至于那些有幸从来没有沦为娼妓,一直过着纯洁贤良生活的女人,虽然没有在历史上留下过人生污点,却也未见得是什么节妇,因为“节烈”二字,是专指女人的一种高尚正义的品行,一种为追求人格不惜付出生命代价的激烈壮举,而这些有声有色的记载,我们总是在有关倡优故事的传奇中读到,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李香君血染桃花扇”等等。
所以,如果跳出传统女性的贞节价值观,我们就根本无法指责陈白露之类的女性丢弃了所谓的传统美德,硬要去过那种荒淫无耻的放荡生活。所谓“堕落”,也许正是逃离了旧的家庭生活圈子的女性,在向新的人生价值观念和价值选择方面探索时,表现出来的一种不自觉的迷惘和沉落。当女性解放的社会条件和文化条件尚未完全成熟时,从旧的传统生活轨道上最先分离出来的那部分女人,因为不可能一步到位地找到她们的理想的生活归宿,她们总是徘徊迷惑,甚至要为寻找出路付出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双重代价,像陈白露这样的女性,最后连生命也作为代价交出去了。面对这种在时代生活裂变的夹缝中挣扎生存的女性形象,我们不应该一概而论地要求她们一下子达到女性解放的革命目标,而应该设身处地地理解她们的真实处境。正是这种与众不同的特殊遭遇,造成了这些女性的性格裂变和心灵裂变,从而真实地反映出时代和社会的道德风貌发生的变化,在女性文学形象中折射出来的突出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