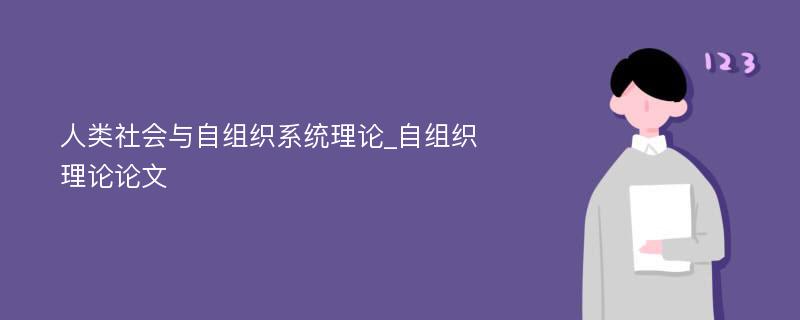
人类社会与自组织系统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类社会论文,理论论文,组织论文,系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类在实践过程中,很早就自发地意识到自然和社会的系统性。现代系统论产生以后,人们开始自觉地运用这一理论认识自然和社会。但是,一些学者在谈到社会系统性时,主要是论述社会的部分与整体、结构与功能、稳态与秩序等系统的一般性质,而未能揭示出社会系统的特殊本质。本文试图从大系统论中的自组织系统理论出发,论证社会系统的特殊性即超自组织性。
所谓自组织系统,是指能够从环境吸取能量和信息,以补偿自然增熵所失去的有序,无须外来指示便使系统要素产生共同行为,从无组织到有组织,从低程度到高程度复杂组织的开放系统。这种系统的动力来自于它对外的开放性和内部的自组织能力,在功能上具有自我复制循环的自维生特性,它的结构是远离平衡态的耗散结构,是一个不断进化的系统。远古时代的系统思想萌芽,近代智者对系统的哲学探索,特别是现代科学对系统自组织内在机制的揭示,为我们沿着维科、马克思、洛特卡、坎农和维纳所开辟的用系统观研究社会领域的方向,深化对社会自组织系统的理解,同时也为我们把社会规定为一个超自组织系统奠定了基础。人类社会具有自组织系统的一般特点,同时又有着超自组织的特殊性质,是自组织和超自组织的统一体。
冯·贝塔朗菲最早把系统区分为封闭系统和开放系统。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现代系统科学从系统与环境关系的角度出发,把系统分为孤立系统、封闭系统和开放系统。所谓孤立系统是指与周围环境不存在物质、能量和信息变换的系统,所谓封闭系统是指与环境只存在能量变换的系统,所谓开放系统,则是指与周围环境进行着物质、能量和信息变换的系统。
现代科学证明,一个不与环境进行任何物质、能量、信息变换的孤立系统,由于系统内部要素间的相互作用而不断地消耗物质和能量,熵的增加成为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必定会走向无序和混乱,最终会逐渐退化和瓦解。封闭系统从环境中输入负熵以抵消系统内的熵增趋势,从而使系统能够保持它的有序结构,形成一种既无退化又无进化的平衡态结构。与此不同,开放系统则不断地从环境输入能量和信息,不仅可以使系统维持原有的有序、结构和稳定,而且还可以由于输入的增多,对原系统形成“偏离”、“涨落”和“扰动”,当它达到一定的阀值,便使系统逐步离开它的平衡态,原有的结构因失去维持自身的能力而瓦解,为新的结构所取代,形成新的有序和稳定。普里戈金把这种耗散熵的不断进化的系统称之为耗散结构。社会系统就是这样一个具有耗散结构的开放系统。社会系统开放性的第一个维度表现在社会系统与自然界的变换方面,第二个维度则表现在民族国家之间的交流亦即特定的民族国家与世界的交流方面。
一、社会系统与自然界的变换
人类社会作为一个开放系统,必须从自然环境中不断地输入物质、能量和信息,当这种输入超过一定的度时,原有的社会结构必定为新的结构所取代,由此构成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但是,人类社会作为一个复杂的开放系统,又有着它不同于一般开放系统的特殊性。社会系统同自然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变换,不只是一个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过程,它在本质上是一个社会过程。
(一)社会系统与自然环境变换过程的特殊性
首先,社会系统与自然环境的变换过程是一个有目的的过程。动物系统同自然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变换是盲目地进行的,而社会系统同自然界的变换则是一个有目的、有意识的自觉过程。马克思曾用蜘蛛与织工、蜜蜂与建筑师作对比,形象地说明了人类社会活动的自觉性特征。人类活动的目的性发端于现实世界不能满足人的需要,因此,目的所指向的不是现实存在物,而是可能存在物,是符合人类需要而在现实世界中又不存在的东西。所以,社会系统同自然环境的变换实质上是人类把“自然存在物”变为“为我存在物”的自觉过程。例如,工业把矿石、煤变成金属,把金属制成机器;农业把土壤的肥力、阳光、水分变成谷物,把谷物制成食物,等等。
其次,社会系统与自然环境的变换过程是通过中介完成的。动物同自然界的变换仅仅通过它们自身的天然器官来完成,因此,动物只能接受现实世界的给予,没有选择的可能,它们与环境之间的变换只能在非常狭窄的领域里进行。社会系统则不然,它是通过使用工具的劳动同自然进行变换的。人类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使作为目的事物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创造了把可能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联结起来的中介系统——劳动工具。劳动工具是人类的文化创造物,它既是目的的指向物,又是目的的实现物,它的存在使得人类同自然界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变换具有了动物同自然界的变换所不可比拟的广度和深度,而且随着这种文化创造物的增多,人类同自然变换的方式和领域也会愈来愈多,人类可能选择的空间也就愈加广阔。
最后,社会系统同自然环境的变换是一个多点、多维、多层次的复杂过程。动物由于受自己内部的生理结构和天然器官的限制,同自然界的变换是一个直接的简单过程。与此不同,社会系统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创造物,它具有多种结构和层次,这就使得它同自然界的变换在本质上说是间接的,因为各个子系统和系统层次同自然界的变换是经过诸多中间环节完成的。例如,就同自然界变换的直接程度而言,经济系统比政治系统更近些,就经济系统本身而言,直接的生产过程近些,流通领域则远些。而且随着人类文化创造物的增多,把自然界的物质、能量、信息转化为社会能量的转换器就愈多,它们之间的变换关系也就愈复杂。
(二)社会系统与自然环境变换结果的特殊性
社会系统同自然界变换的特殊性不仅表现在它们之间变换的过程中,而且表现在这种变换的结果上。自然界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经过社会系统的转换必然发生形态和性质的改变(不然的话,就称不上是一种社会系统的变换)。首先,自然的物质形态经过社会系统的改造,它的形态和性质都要发生变化。“只有人才办得到给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迹”,“他们不仅迁移动植物”,“甚至还改变了动植物本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2版,第4卷,2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使它们由自然的存在变成一种对象性的存在。而且,人类用一种自然力量去改造另一种自然力量,并给它们插上理想的翅膀,创造原本不存在的东西。
其次,自然的信息经过社会系统的变换,其存在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信息是事物联系、变化、差异的表现,单一、孤立、静止的事物没有变化和联系,也就不存在信息,所以,艾什比用“变异度”来指称信息。无论是动植物还是人,获取信息都意味着对不确定性的消除或减少。生物的繁衍有遗传信息,群居的食草动物有警报信息,蜜蜂的寻食有舞蹈信息,等等。这些信息经过社会系统的变换,其载体、传播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本质特征是符号化。自然信息的存在方式是实物的或形象化的,而人类社会无论是从自然获取信息,还是相互间传递信息,本质上都是符号化的,所以,从信息论的角度看,卡西尔有理由在《人论》里把人界定为“符号化的动物”。站在社会系统论的角度看,自然信息向社会系统的变换过程,就是人类认识自然的过程。
最后,自然的能量经过社会系统的变换将会转化为社会能量。所谓社会能量,是指人类以文化创造方式所运用的一切能量。它是一般能量的转化形式,或者说是能量的社会形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它像称呼人化自然那样称之为人化能量。社会能量是人类通过文化创造的各种方式从自然界中获取的,但是,人类文化并不创造能量,它只是创造变换能量、运用能量、聚散能量的方式,这种方式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它能不断地从自然界吸取愈来愈多的能量,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经过人类文化吸收到社会系统的能量,无论是保持其原本形态(如水能、电能),还是改变原来形态(如石油分解为汽油、煤油等),都已纳入人类文化系统,因此其存在状态、性质和运用都因受人类文化的支配而改变成为社会能量。总之,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物质、能量、信息变换的结果,深刻地表现了社会系统的特殊性和自然系统的属人性质。正是在社会系统的作用下,在社会系统对自然系统的变换中,才显示了自然系统的升华的活力和发展的前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本主义”。(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文1版,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社会系统在同自然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变换的过程中,无论是这种变换过程的特殊性(变换的目的性、中介性和复杂性),还是这种变换结果的特殊性(变换后物质的人化、信息的符号化和能量的社会化),都不仅表现了社会系统的耗散结构和它的开放性,而且更为突出地表现了它的超自组织性,即社会系统的自觉性特征。
二、民族国家与世界的交流
(一)民族国家是一个开放系统
根据系统论分类标准,从本质上说,所有的社会系统都是呈耗散结构的开放系统。有的学者不是从系统论的角度谈论封闭社会和开放社会,如卡尔·波普在1962年出版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把自由、平等、宽容及提倡理性批判精神和实行改良的社会称之为开放社会,把与之相反的社会称之为封闭社会。虽然他的分类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但作为学术见解是成立的。而有的学者则不然,他们虽然用孤立系统、封闭系统和开放系统的范畴,但又离开系统论的基本标准,根据“一个社会同其他社会系统没有任何来往”,把它称之为“对其他社会系统关系上的一种封闭系统”。这种应用系统论范畴而又离开系统论的分类标准的界定,是违反逻辑的。我们可以把一个闭关锁国的民族社会称之为封闭的社会,而不能说成是封闭的系统。因为任何民族国家都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即使那些远离世界文明大道,同任何国家没有往来,至今仍然过着狩猎、采集生活的原始群落,依然同自然环境进行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变换,虽然这种变换是以非常落后的方式进行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民族国家与社会只有开放维度的多少、开放程度的大小之分,没有开放与封闭之别。
从社会系统开放性的第二维度,即民族国家与世界关系的角度看,所有国家也都是开放系统。这些民族国家虽然有着不同的发源地,最初也是孤立地发展着,但是,它们在第一个维度的开放中所积累的社会能量愈来愈大,就会导致这些民族国家系统的向外输出,或者开疆拓土,掠夺资源,或者友好交往,相互学习,开始与其他民族的交往,任何困难和力量都不能阻止这种交往。从人类历史上看,这种交往包括战争、商贸、文化传播等多种形式。正是这种多样化的世界交往,才使得民族国家的发展日益迅速。古代中国,在黄河中下游华夏人居住区以北,是浩瀚的戈壁沙漠、干旱的草原和人类难以生存的西伯利亚寒原;在它的东部,是比沙漠更严峻的一望无际的东海。当华夏文化发展到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并与当地文化充分交融之后,迤南丛林的烟瘴之地、金沙江、怒江和险峻的横断山脉以及高不可攀的青藏高原,依然是横亘在古中国与古印度文明中间的障碍,使这两个文明难以接触和交流。只是随着各自社会能量的增长,人们驾驭牲畜的能力的提高和航海技术的发展,古中国人才跨越了束缚他们的地理屏障,开始了与“四夷”及周边国家的交往。古埃及也有着类似古中国的地理环境,西部是无法逾越的撒哈拉大沙漠,东部是阿拉伯沙漠高原,南部尼罗河上有六个湍急的瀑布屏障,北部濒临地中海,浅滩密布,暗礁罗列,船只难以靠近。但是这种阻碍古埃及进行民族交流的地理屏障终于为新兴的古希腊罗马文明所打破,两个古文明的“对歌”于公元前五世纪后在地中海东南沿岸拉开了帷幕。
如果说古代民族国家之间的交流是一个文明与另一个文明、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交往的话,那么,近代则是一个民族国家与整个世界的交流。因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个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
从民族国家交流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
第一,随着社会系统开放第一维度的深入发展,社会能量的增强,民族国家之间的交流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就一个特定的民族国家而言,不是由于自身社会能量的增强而主动地与其他民族进行交流,就是被比它更强大的民族国家拉入交流的行列之中。这种民族国家交流的必然性源于社会能量的增多,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同上书,第276页。)
第二,民族国家之间的交流是社会系统的自组织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民族区域必然由于自组织的协同走向真正的世界史。历史证明,一个民族国家一旦与其他民族进行了交流,特别是与先进的文明交往之后,就再也不可能关闭已开启的大门。虽然历史上多次出现过统治者试图终止交流的努力,但没有一次不是徒劳的。古埃及晚期王朝到托勒密王朝这一千年的时间里,几经努力也没有终止与先进文明的融合。晚清中国康乾时期的“海禁”与“闭关”并没有锁住国门,最终为西方文化的坚船利炮所冲毁,国人从此像其他民族一样,在器物、制度和观念上步西方现代化的后尘不辍。正如社会学家吉尔伯特·罗兹曼所说:“现代化一经在世界上任何一地展开,其影响便无可避免地渗及全球各处,不管这种影响靠的是武力还是人心所向,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中文1版,6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协同学的创始人哈肯认为,仅仅由于集体行为,就可常常引起决然不同的客观状态,“这种没有外来指示的共同行为是自组织的”。(哈肯:《协同学》,中文1版,33页,上海,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88。)这位自然科学家和前一位社会学家用不同的语言表达了一个同样的思想,即民族国家交往产生的社会自组织性必然使各个民族形成新的结构整体。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也阐述了这种民族交往的原因和结果:“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种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8页。 )一百年后的今天,民族国家交往导致的社会系统整体性的图景愈来愈清晰了。
第三,民族国家与世界交流导致的社会自组织过程具有着不同于一般自组织过程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代表系统新质的力量对原系统旧质影响的机制和方式上。在自然环境里,“环境条件的稍微变化可以引起完全新的序参量系统。可以是必须先有一个新种类的序参量,如一个才产生的新物种;在激光是自发产生一种光波,在液体运动是微小的热振荡,在化学反应里是原始反应或自发产生一种新分子”。(哈肯:《协同学》,第78页。)这些系统新质通过示范性影响其他旧质,自组织成一种新的有序状态,完成系统的转换。与此不同,在社会系统里则存在示范性影响和强迫性同化两种自组织方式。每一个民族国家都是一种主体性的存在,有着自己的文化和选择的权力,如果它们认同新文明的优越性,那么,它们追随系统新质的自组织过程就是通过示范性方式完成的,如近代日本的“脱亚入欧”就是如此。也正是因为民族国家是一种主体性存在,它们也可以拒绝先进文明的同化,抗拒追随世界潮流,在这种情况下,它们纳入新社会系统的自组织过程,就采取了强迫性同化的方式,如近代中国就是如此。由此可见,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自组织方式的多样性和特殊性,是由社会系统的超自组织特殊性决定的,即由民族国家是一种主体性存在所具备的自觉选择性这一点决定的。如果从历史的角度考察社会系统自组织的这两种方式,我们就会发现,古代、近代民族国家间相互作用的自组织过程更多地是采用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武力征服的强迫性同化方式,到了现代,特别是本世纪后半叶,这种自组织过程更多地采用了示范性影响方式,如欧洲共同体贸易圈、亚太经合组织的贸易圈和北美贸易圈的形成,都是由少数国家率先发起、示范,其他国家先后认同、逐渐加入而发展起来的。本世纪民族国家间自组织方式的变化,显示出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也显示了社会系统自组织水平的提高。
(二)民族国家与世界交流的意义
民族国家与世界的交流所表现出来的社会系统的自组织特性,不乏战争中的刀光剑影、鲜血腐尸,商贸中的利欲熏心、尔虞我诈和传教中的攻心夺志、欺骗利诱等恶行,但这是社会自组织过程中所要付出的特殊的和必要的代价,相对于一个民族在这种交流中所获得的益处来说,这种代价是次要的。
民族国家与世界交流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下述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
从民族国家自身的角度考察,国家之间的交往加速了一个国家的发展进程。交往、相互作用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和原因。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曾从元哲学的高度说“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终极的原因”,既是事物存在的原因,也是事物发展的原因。一些社会科学界学者从具体学科的角度探讨了事物的相互作用。例如,美国文化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拉尔夫·林顿在《个人的文化基础》等著作中,把文化传播看作是人类联合发展的一种创造力,心理学家米德把社会发展看作是人类交往形式的进化过程,社会学家库利在《人类本性和社会秩序》一书中认为,文化传播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机制。社会哲学是在承接元哲学的原则和依赖具体科学成果的中间层次上解释国家之间交往的意义的。从社会哲学着眼,可以说,国家之间的交流之所以推动了一个国家的发展进程,是因为这些国家从这种交流中获得了新的社会能量和学会了获取社会能量的方式,这样,它们就缩短了独自探索所耗费的时间,节约了为进行这种探索而付出的投入和代价。恩格斯曾列举东方文明向西方文明输入的磁针、印刷、活字、亚麻、火药、眼镜等,认为这些东方文明的输入,“不仅使希腊文学的输入和传播、海上探险以及资产阶级宗教改革真正成为可能,并且使他们的活动范围大大扩展,进展大为迅速”。(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文1版,1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马克思曾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道路的三大发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7卷,4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当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以后,它们向美洲大陆、东方古国的商品输出、资本输出和科学技术输出,也为这些国家的迅速变更和发展,提供了催化剂。
从整个人类社会系统的角度考察,民族国家这些子系统间的相互交流和作用,有助于整个人类的文化创造和文化积累。就文化创造而言,文化社会学认为,文化的发展是以产生新特质的文化创造为标志的,而这种新质文化的产生是通过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化特质或要素的接触、结合完成的,就像两种植物嫁接产生一种新植物一样,这叫做文化突变。从微观的角度说,石斧捆上木棍,木筏子装上蒸汽机,幻灯和照相技术结合成电影等,都可以称为文化突变。从社会哲学的角度看,一个民族文化的突变性发展也必须在同其他民族文化的接触、交流中才能完成。可见,民族文化之间的接触、交流是文化创造的必要条件。古欧洲文化发展是与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经常接触和交流密切相关的,地中海北岸的希腊文化、南岸的尼罗河文化、离地中海不远的巴比伦文化这三个古老的文明通过海路密切联系、相互交流,雅典的戏剧大师阿里斯芬曾用“我们是一群围绕着池塘的青蛙”来形容爱琴海四周诸城邦在文化上的呼应。借用这一生动的比喻,希腊、罗马、埃及、巴比伦诸文化恰似围绕地中海这个更大池塘周围的一群青蛙,它们彼此鸣叫,相互应和,组成奇特的文化交响。正是在这个交响中,才不断创造出新的文化乐章。相比之下,古中国文化的对外交流要少得多,西汉的张骞,东汉的班超、甘英,唐代的玄奘,14世纪威尼斯的马可波罗,这些沟通异邦的文化使者,几乎要间隔数百年才出现一次。但是,只要有文化的接触和交流,就会在吸纳、借鉴中产生文化创造,如佛教与中国文化的融合产生了有中国特色的禅宗。民族文化间的交流可以防止文化遗失,保证文化积累,而且交往得愈广泛,这种积累就愈有保障。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7页。)如果交往比较狭窄, 那么许多发明都会在不同的地方重新开始,这不仅会造成资源和时间的浪费,而且还会由于灾害和战争造成文化的遗失。如古代西亚腓尼基民族由于亚力山大的征服和继之而来的衰落,他们的大部分发明都失传了;中世纪玻璃绘画术和中国古代的炼金术、地震仪、指南车、火器制造术,都因战争而毁失或中断。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当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同上书,第108页。)人类文化才会越来越丰富, 社会发展的速度才会越来越快。
民族国家与世界交流的必然性揭示了社会系统的自组织特性,民族国家与世界交流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社会自组织方式的特殊性,说明了社会的超自组织特征,而且,民族国家与世界交流的意义,确证了中国共产党人近二十年来的对外开放政策既符合民族国家自身发展的逻辑,也符合社会系统自组织能力逐步提高的趋势,是振兴中华民族的一种历史性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