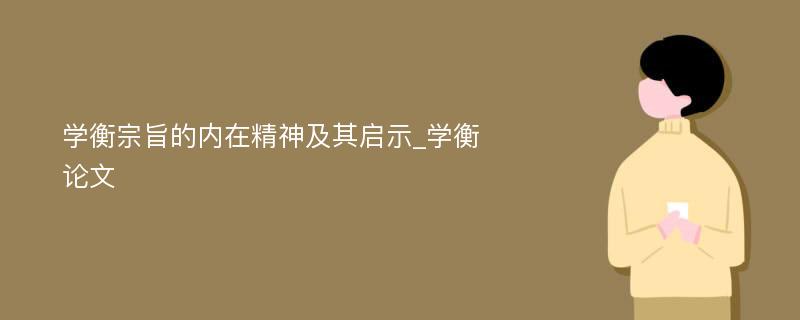
《学衡》办刊宗旨的内在精神及其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启示论文,宗旨论文,精神论文,办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39.29;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38(2013)05-0123-04
1922年创刊的《学衡》,起初是一个同仁杂志,没有政治背景和经费支撑,在吴宓、柳诒徵等人的维持下,运转至1933年,共出版79期。围绕《学衡》杂志,形成了学衡派,其中有一批重量级的学者,如吴宓、柳诒徵、梅光迪、胡先骕、缪凤林、景昌极、汤用彤、陈寅恪、刘永济、张荫麟、李思纯、王国维、向达等。学衡派没有严密的组织,“由散在各地之同志若干人,担任撰述”,[1]只是基于共同的学术观,围绕《学衡》杂志,发表己见,以独特的人文气象屹立于学界。
翻开《学衡》第一期,杂志名称下面赫然用英文写着“THE CRITICAL REVIEW”,“CRITICAL”一目了然,表示《学衡》杂志重在推进学术批评。学术批评是学术研究的另一种路径,既要树立批评目标,也要紧密围绕批评对象讨论的内容,进行逻辑严密的论证,告诉学术界一个切实的主张。为此,《学衡杂志简章》明确地回答了《学衡》办刊宗旨是:“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
近年来,由于《吴宓日记》的出版,陈寅恪先生学术精神的发掘、学衡派后人的推动等诸多原因,学界对《学衡》文本和学衡派研究日益重视。乐黛云、汤一介、茅家琦等几位顶尖学者对学衡派的思想进行了宏观勾勒。学界对此专题研究也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文化保守主义谱系下的学衡派、学衡派与新文化派的关系、学衡派的文化思想、学衡派的地域思想支撑、学衡派人物研究等等。上述专题研究呈现两个特色:一是着重叙述学衡派与新文化派的冲突;二是多从文化保守主义的角度切入,用了大量的文学理论解释学衡派的思想,对学衡派主体精神的揭示显得不足。笔者认为,对《学衡》办刊宗旨内在精神的理解是读懂《学衡》、理解学衡派的重要前提,本文将做出努力,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是《学衡》杂志和学衡派的安身立命之本。如何“论究学术、阐求真理”?他们有自己的理解和实践。《学衡》创始人之一、美国西北大学博士、东南大学副校长刘伯明在《学衡》第一期开篇写道:学者之精神,究其实际,实为一体。但若不得已而强分之,其中所涵,可为五端。一曰学者应具自信之精神;二曰学者应注重自得也;三曰学者应具知识的贞操也;四曰学者应具求真之精神;五曰学者必持审慎之态度。[2]纵观《学衡》杂志,从专题的策划到内容选择,始终以学术性为第一标准。学衡成员整体坚守这一原则,严谨于学术研究。例如,柳诒徵先生的很多作品陆续发表于《学衡》杂志,柳先生行文,每说一个观点,都有数条资料佐证,附录相关注释,辩证分析之后,得出一个中肯的结论,可以说是中国学界学术规范践行的先行者和楷模。上述理解和实践,概括起来就是要求做到“精审之眼光”,“吾非言纯粹保守之必要也,然对于固有一切,当以至精审之眼光,为最持平之取舍,此乃万无可易之理”。[3]
学衡派认为缺乏“精审之眼光”,学术和社会都会变得浮躁,难以实质性推进新文化的进步。“今日吾国所谓学者,徒以剽袭贩卖为能,略涉外国时行书报,于其一学之名著及各派之实在价值,皆未之深究,即为枝枝节节偏隘不全之介绍。故一学说之来,不问其是非真伪,只问其趋时与否。所谓‘顺应世界潮流’者,正彼等自认在学术上不敢自信,徒居被动地位,为他人之应声虫之宣言也。……以彼等而言提倡新文化,岂非羊蒙虎皮乎”?[4]
学衡派的这种担忧,立足于学术、着眼于社会:“学风关乎士风,士风关乎国运,其意义不可轻觑”。[5]因此,他们坚信,为师者学风不正,也会影响人才培养。学生在大学期间如果没有养成精审训练的习惯,将难以承担精确估计一切价值、进而促进文化和社会的进步的重任。“故革命党昔日力言中国人民之有共和程度,而今则坐叹国民之不能去恶政治,此由未精确估定价值而下断定之言故也”。[6]
“精审之眼光”,是一种研究态度,更是一种研究方法。不仅要求研究过程严谨,也要求结论严谨。“在以精密之眼光,洞观古今作者之得失,下以正确之评判,以为一般社会之指导,决不容轻于许可”。[7]因此,在学术批评的实践中,要以学术至上为绝对标准,无需在乎私人感情,也不要畏惧权威。例如,对待新文化运动领军人物胡适,他们冷静地进行了批评。在对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进行了整体的解剖之后,指出胡适将新旧古今当作为一个旗帜来鼓吹,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推进文学革命,是不恰当的。与此同时,强力指责胡适“输入欧化,亦卑之无甚高论。于哲理,则膜拜杜威、尼采之流,于戏剧,则拥戴易卜生、萧伯纳诸家。……不知欧美实状者,读今日报章,必以为莎士比亚已成绝响,而易卜生为雅俗共赏;……在言者固以一己主张而有去取,在听者依一己之辞而不免盲从,此所以今日之受学者多流于固陋也”。[8]当胡适大力介绍易卜生思想时,学衡派直言不讳地指出易卜生只不过是欧美文学界的一个普通作家。
梁启超先生是那个时代有影响力的学者,对待他这样的学术大师,《学衡》也不留情面,柳诒微就公开撰文指出梁启超的不足:“梁氏之论史,向来有一成见,即孔墨为北派,老庄为南派,无论何处,皆须穿凿附会,以合其意。”[9]接下来更是指出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一书对顾亭林的评价错误很多,原因在于梁启超原始文献读的不够细致,随意采用后人之说,违背了“博学于文,行己知耻”[10]的为学之道。
在对很多学界名流进行逐一点评之后,学衡派指出现今的学术研究有两大病症,“时学之弊,曰浅,曰隘。浅隘则是非颠倒,真理埋没。浅则论不探源,隘则敷陈多误。时学浅隘,故求同则牵强附会之事多,明异则入主出奴之风盛。时学浅隘,其故在对于学问犹未深造,即中外文化之材料,实未广搜精求。旧学毁弃,固无论矣,即现在时髦之东西文化,均仅取一偏,失其大侔”。[8]上述点评虽然有挑剔之嫌,但这种“精审之态度”是建立在学理之上,是对学术研究规律的自觉遵守,对学术的发展也有促进作用。
“昌明国粹,融化新知”是《学衡》杂志和学衡派学术批评的目的。那么如何才能“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呢?学衡派有自己的理解和实践。他们认为“国粹”和“新知”是一个矛盾共同体,二者和谐相生,不能是此非彼,更不能简单地将其纳入中西古今的框架进行任意评判。对待任何命题,都要正本清源,给予“正名”,博采中西古今文明之精华,为我所用。
“正名”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由来已久。在政治动荡、思想活跃的时期,面对形形色色的各家思想,让人眼花缭乱,不知所措,这时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多会站出来呼喊给社会“正名”,旨在从一字一词一事的基本定义出发,澄清混乱,确定一套价值标准,为健康社会秩序的确立奠定基础。春秋年间,孔子喊出了“必也正名乎”,东汉的许慎目睹社会动乱,是非思想混乱,编辑了《说文解字》,力求从文字的规范入手,给社会订立一个标准。
上述时代都是学衡派常常提起的“博放时代”。五四新文化运动迎来了历史上的又一个“博放时代”,一时间百家思想,各国理论相至沓来,主义满天飞舞,连军阀势力也附和着学者高喊“社会主义”。[11]学衡派意识到了当下社会是非不分的严重问题,“18世纪中叶,近代各种革命未发生之先,字典已先大变革,良知一字,即在此时,渐训为其今日之意义。昔以良知为内心细微之声响,今乃以良知为在社会间,大声疾呼之事业。昔之良知为戒己,今之良知为责人”。[12]
面对社会现状,学衡派无力设计一套政治改革方案。只能在学术研究和教书育人的岗位上,给一切理论“正名”,澄清是非。当面对“今之批评家,犹有一习尚焉,则立言务求其新奇,务取其偏激,以骇俗为高尚,以激烈为勇敢”[13]的现实时,学衡派诸君“又回思孔子之言,其门人问以治国之道,孔子乃以正名为先务。今当效苏格拉底与孔子之正名,而审察今日流行之各种学说”。[12]他们主张社会在接受一个新名词、新思想之前,应该进行一番考证,做到有理有据,不能信口开河,这才是严谨的态度、爱国的态度,“是故正名者名家之责。救国者,其道莫要于正名”。[6]
学衡派的“正名”思想不仅受到了以孔子为核心的儒家思想的影响,也受到白壁德的影响。白壁德是《学衡》主编吴宓的导师,也是一位“正名”思想的拥护者和践行者,例如,他面对西方社会对“人文主义”的滥用,围绕“人文主义”一词相关或容易混同的词语——人文的(humane)、人文主义的(humanistic)、人道主义的(humanitarian)和人道主义(humanitarianism)进行细致的分类和定义,指出了“孔德、卢梭与赫尔德这三个人却不是人文主义者”。[14](P5)
以“正名”为切入点,《学衡》杂志和学衡派开始切实地“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他们认为新文化派对“新旧”的定义极不负责,以“新旧”定“是非”更是荒唐,“自民国六年以来,国人对各事物,心目中悉有一种新旧之印象。新旧之印象既生,臧否之异同遂至。其臧否也,不以真伪、美恶、善否、适与不适为断,而妄蒙于一时之感情与群众之鼓动。……夫新旧不过时期之代谢,方式之迁换,苟其质量之不变,自无地位之轩桎,非可谓旧者常胜于新者,亦不可谓新者常优于旧者也”。[15]接下来,强力批评新文化派高举“新旧”大旗的目的是为了成为万众心目中的英雄:“凡事但名之曰新,必可不胫而走。举业归依,于是革命家遂为万众心目中的英雄。”[16]
以“正名”为杀手锏,他们对新文化派话语的批评来了个釜底抽薪,指出新文化派很多所谓的“创造”,本质上是“捏造”。“今之国中时髦学者,亦盛言科学方法,然实未尝知科学方法为何物,特借之以震骇非学校出身之老儒耳……彼之所谓创造,非真创造,乃捏造也。又以深通名学,自夸于众,然其用归纳法,则取不完备之证据;用演绎法,则取乖谬之前提。虽两者所得结论,皆合于名学原理,而其结论之失当,无可免也”。[14]此番论证着实触碰了新文化派内在逻辑。
《学衡》杂志和学衡派以“正名”为武器,全盘解构新文化派思想,不是为了全盘回归传统,因为这与中国追求现代化的目标是背离的。多有欧美留学背景、对西方社会有着深入了解的学衡派,同样明白学习西方的必要。但是西方是个宽泛的概念,空间上有英美法俄等国,时间上有古典与现代的差异,到底该向谁学习、学习什么?学衡派认为这也需要“正名”。于是他们提出了“全面了解西方”的理念,旨在更加有效地学习西方。首先,他们主张要有选择的学习。其次,他们认定要多学英国、美国这些西方文明的精华,少学法国、德国和俄国,这些国家的现代化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为此,当新文化派对法国文化和法国革命气质推崇至极时,他们高呼“彼盎格罗撒克逊民族者,非一般社会学家所认为最宜于民治主义之民族。而英国民治主义之甚,且远在法兰西共和国之上乎”。[13]最后,他们主张,确定学习目标之后,要认真地学、持续地学,不能走马观花。
《学衡》杂志和学衡派以“正名”为武器,围绕“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宗旨,在解构他者思想的同时,也有着强烈的建构精神。
“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是《学衡》杂志和学衡派立论的方法。那么如何才能做到“中正”呢?
学衡派认为,“中正”思想的养成需要中庸之道思想的浇灌。他们认为中庸之道是中国的立国之本,“凡世界上的事,惟中庸则无弊”。[17]做到“中正”,还需要“新人文主义”的滋养。新人文主义是哈佛大学教授、吴宓导师终生推行的理论,它有一个简单的话语逻辑,就是在物质进步的同时,人们也该从古人、古代学术思想那里寻找精神的营养,在调节“古今”关系时,要遵守“适度法则”。在白壁德的理解中:“远东最杰出的圣人——佛祖,在他第一次训诫的起首几句里便说,极端的即是野蛮的。希腊或许是最为人文的国家,因为他不仅清楚地阐明了适度的法则,而且还认识到复仇之神会惩罚任何一种狂妄的走向极端的形式或违背这项法则的表现。”[14](P17-18)
以“中正”标准为评判,《学衡》杂志和学衡派破立结合,言之有理、持之有据,从事学术批评。新文化派是他们首要批评的对象,纵观他们的言论,的确做到了“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例如,他们肯定新文化派发起的新文化运动,但对新文化派激进推动新文化运动的方式方法表示不满,认为他们的行为类似于“把婴孩连洗澡水一起倒掉”,有不够精细之嫌。
学衡派对新文化派言行的批评并非仓促上马,以“中正”之眼光批评新文化派的观点也不是在实践中逐步摸索出来的方法,而是在批评之前就定下的基调,这一基调在《学衡杂志简章》中明确的写道:“(甲)本杂志于国学则主以切实之功夫,为精确之研究,然后整理而条析之,明其源流,著其旨要,以见吾国文化,有可与日月争光之价值。而后来学者,得有研究之津梁,探索之正轨,不至于望洋兴叹,劳而无功。或盲肆攻击,专图毁弃,而自以为得也。(乙)本杂志于西学则主博览群书,深窥底奥,然后明白辨析,审慎取择,庶使吾国学子,潜心研究,兼收并览,不至道听途说,呼号标榜,陷于一偏而昧于大体也。(丙)本杂志行文则力求明畅雅洁,既不敢堆积,古字连篇,甘为学究,尤不敢故尚奇诡,妄矜创造,总期以吾国文字,表西来之思想,既达且雅,以见文字之效用,实限于作者之才力,苟能运用得宜,则吾国文字,自可适时达意,固无须更张其一定之文法,摧残其优美之形质也。”
以“中正”之眼光进行学术批评,既是《学衡》办刊的宗旨,也是学衡派的一贯态度,这是中庸之道的态度,更是新人文主义的践行。既是对学者的定位,也是对学术的定位,更有引导社会的意识。
近代以来,面对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等与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相关的主题,困扰着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为此,杰出之士有的投身教育,有的投身科学,有的投身实业,追求国家的现代化。现代化源于西方,是文明的根本转化,“现代化是一次巨大的社会变动,是人类文明的一次转换,他在工业生产力取代农业生产力的基础上,实现了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化。换句话说,现代化是一种新的文明形式(工业文明)逐渐确立的过程。”[18]现代化需要大批人才,出国留学成为年轻人成长成才,学习本领的捷径。辛亥前后清华留美预备学堂成批派遣留学生为中国社会转型提供了推力,1915—1917年是这批留学生集中学成回国的第一波,新文化运动是在此背景下启动。留学生的归来带来了新思想、新方法,同时带动了高等教育转型。自此以后,持续数年,中国学术界百家争鸣、百花开放。长期以来,大家认为新文化派是进步的学术流派,学衡派因为批评新文化派,属于保守的派别。其实,学衡派和新文化派都是百家争鸣、百花开放的一支力量。新文化派主张先破后立,直达目的。学衡派主张先立后破,为共和社会打基础。二者都有其合理性,辩证统一于中国发展进步的实践。
新文化派和学衡派都是知识分子群体,均以学术为利器,影响社会,一个追求短平快,一个放眼长远。不能简单地是此非彼,更不能轻易认定学衡派保守、乃至顽固。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学衡派同样有着卓越的建树,在学术史上群星璀璨。学术有两个层面的含义,有功利的一面,也有纯粹的一面。近代伊始,面对传统学术的远离喧嚣,我们积极鼓励实用功利之学,这是必要的。但是在功利实用盛行的当代,我们也应有所节制,学衡派从学术研究的规律出发,秉持精审精神,以“正名”为武器梳理问题的来龙去脉,以中正的态度评价是非,这是《学衡》办刊宗旨的内在精神,也是学衡派学术研究践行的原则,更是融入了学衡派教书育人的实践中。他们的思考、选择和实践值得当今学界深入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