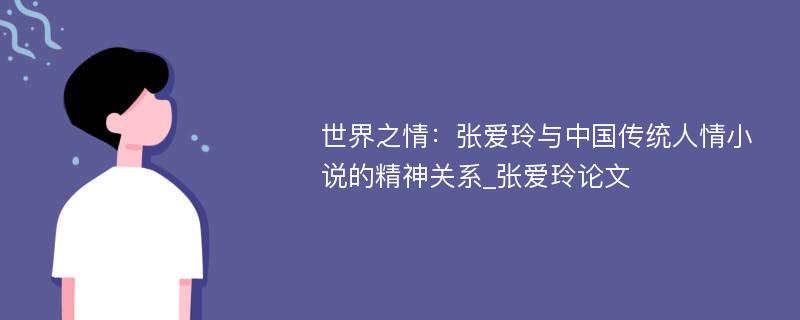
言情与世情:张爱玲与中国传统人情小说在精神上的内在联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情论文,精神上论文,中国传统论文,人情论文,内在联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89(2006)03—0034—008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像张爱玲那样自觉地从传统小说中汲取营养的小说家,并不多见。她自述《金瓶梅》与《红楼梦》“这两部书在我是一切的泉源,尤其《红楼梦》”[1—p4]、推崇《醒世姻缘》和《海上花》一个写得浓,一个写得淡,但是同样是最好的写实作品”,“总觉得它们应当是世界名著。[2—p307]”有一次胡兰成竟敢说出《红楼梦》、《西游记》胜过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或歌德的《浮士德》,张爱玲却平然答道:“当然是《红楼梦》、《西游记》好[3—p150]。”张爱玲对中国传统小说的偏好与推崇,由此可见一斑。事实上,她对传统小说的了解,也是较为全面的,传统小说诸体,举凡野史、传奇、话本、笔记、章回,她都有所涉猎。①
T.S.艾略特曾认为,品鉴一个诗人或艺术家,就是品鉴“他和以往诗人以及艺术家的关系[4—p130]。 ”这种历史意识对于理解和评价张爱玲这样的作家更为重要,因为她明确意识到历史如何延续到现在,她曾这样写道:“只有在中国,历史仍于日常生活中维持着活跃的演出[4—p23]。”事实上,张爱玲的小说,也是这“活跃的演出”的一部分。中国传统人情小说中的“世情传统”与“言情传统”,都融化在她的血液里,这二者之间的张力,则成为她的小说在精神构成与文本构成上的基本因素。
一、虚无的世情:“世情”传统在张爱玲小说中的体现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当神魔小说盛行时,记人事者亦突起,其取材犹宋人小说之‘银字儿’,大率为离合悲欢及发迹变态之事,间杂因果报应,而不甚言灵怪,又缘描摹世态,见其炎凉,故或谓之‘世情书’也。”[6—p179] 由于世情小说的这种特点,早期研究者多借用西方文学史上的“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等概念加诸其上,但这些概念有其特殊的含义及演变过程,很难完全与“世情”的观念密合无间。仔细琢磨“世情小说”中的“世情”,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小说的兴趣并不在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也不在于借用自然科学的观念解释社会现象,正如中国的“清明上河图”的散点透视不同于西洋写实主义绘画的焦点透视,中国的“世情小说”也并不设定一个唯一的透视中心,与其说它关注的是某种人物某种现象,不如说它关注的是中国人的生存样态及其情感行为方式。
张爱玲研究最深且对她影响也最显著的四部小说——《金瓶梅》、《醒世姻缘传》、《红楼梦》、《海上花列传》,前二者属于“世情书”,后二者可看作“言情+世情”。这些书的作者的“洞达世情”及书中“通常的人生的回声”[5—p343],颇与她的文学观念心心相通,其核心也正在于这种对世俗的中国人的生存样态及其情感行为方式的洞察与体认上。张爱玲的小说得益于“世情小说”之处是非常明显的。夏志清说:“她受旧小说之益最深之处是她对白的圆熟和对中国人脾气的摸透。《传奇》里的人物都是道地的中国人,有时候简直道地得可怕;因此他们都是道地的活人,有时候活得可怕。”[7—p260] 这是很有见地的看法。张爱玲的作品没有“新文艺腔”的毛病,很大程度上,便在于“世情小说”教给了她“人情世故”,也培养了她观看和表达世界的独特方式。
譬如说,从“世情小说”的叙述来看,作为它们的叙述基础的,乃是“熟悉琐事”。前人评《金瓶梅》,谓其“乃隐大段精彩于琐碎之中”[8—p1];“琐碎中有无限烟波”[9—p224];清人刘廷玑比较“四大奇书”后,亦谓:“若深切人情世务,无如《金瓶梅》,真称奇书。……其中家常日用,应酬世务,奸诈贪狡,诸恶皆作,果报昭然。而文心细如牛毛茧丝……”[10—p184] 对于“世情小说”的这一方面,张爱玲有深刻的体认,她很重视生活中日常、凡俗的一面,曾经这样为自己辩护:“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没有这底子,飞扬只能是浮沫。”[5—p173~174] 所以,大多数传统小说,由于情节太过传奇化,为她所不取,她欣赏的是有“细密真切的生活质地”的《金瓶梅》、《红楼梦》,以及“平淡而近自然”的《海上花》。她从它们对“每天平凡生活的现实世界”的关注里,感受到了“通常人生的回声”。②
不过,虽然重视“日常生活的况味”,张爱玲的小说却并不会让人觉得“淡出鸟来”,这在很大程度上便得力于她对“传奇”与“日常”出色的调节。《传奇》中的小说,有的从传奇故事中探测到普通人性的涌动,如《金琐记》中七巧的故事;有从普通人身上探测到深刻的心理戏剧,譬如《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终振保的故事。这种旨趣,张爱玲自己称为“在传奇里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这种宣称已经成为她的小说最有名的标签,在现代文学中听起来也颇有新意,但放到“世情小说”的传统中来看,这只不过是对这派小说的旨趣一次非常聪明且有概括力的重新宣示。③ 世情小说固然以家常日用的叙述为基础,但另一方面,它们叙述的故事整体,如《金瓶梅》中西门庆的放浪生涯,《醒世姻缘传》中的两世恶缘,却无论如何不能说是普通的、正常的,所以这一派小说虽然所述皆家人父子日用饮食往来酬酢之细故”,整体上却常常要表现的是世事无端、人情莫测,作家“举凡缺陷世界,不平之事,遗憾之情,发为奇文”[11—p11],以显其针世砭俗之意,或者搜罗闾巷异闻,一切可惊可愕可欣可怖之事,“以描画世之大净”、“描画世之小丑”、“描画世之丑婆、净婆”[12—p216]。
这种对“常”与“奇”的调节,相应于对中国人的生存样态及其情感行为方式的“规则”的一面和对规则的破坏的一面的发现与调节。曾经有人认为,就传统中国人的生存样态及其情感行为方式来看,它典型地体现了中国文化的自然主义性质(哲学伦理学意义上的),即在价值之源上没有超验的“神圣”的状况。④ 一些知名学者也持这种看法。如余英时就认为:“中国人认定价值之源虽出于大而实现则落到心性(人)之中,所以对‘天’一方面往往存而不论,至少不十分认真”;“整个地看,中国文化只对价值源头作一般性的肯定,而不特别努力去建构一个完美的形而上的世界以安顿价值,然后再用这个世界来反照和推动实际的人间世界。”[13—p16、18] 这样的判定,不论是意在支持还是意在批评,都有笼统和隔膜之嫌。不过,如果把这样的意见,用在世情小说所表现的市井世界上面,则比较合适。世情小说中表现的世俗的中国人的生存样态和情感行为方式,由于超验的价值之源被悬置,常常表现出重复的形式。成穷在《从〈红楼梦〉看中国文化》中这样认为:“《红楼梦》细腻地描写了此种中国人的生存样态及其情感行为方式:如何入世,如何遁世;如何做官,如何为民;如何作恶,如何消遣;如何争斗,如何妥协;如何失望,如何期盼;如何耗殆,如何再生;……(这种模式)是作为有类‘游戏规则’或数学公式那样的普遍性来表现的:游戏者可以不断地更替,但游戏规则却始终保持一致;运算数据可以每次不同,但数据之间的基本关系和运算规则没什么两样。”[14—p24~27] 这种描述,移用到纯粹的世情小说身上,也相当合适,它们的视野容量或有广狭之分,但对这种世俗社会的普遍模式的揭示是同样的。⑤ 张爱玲研读这类小说,其得益最深的地方亦在于此。她的世界同样有自己繁重的规矩与“狭小整洁的道德系统”,人物虽生存在一个破败的文化环境中,却仍顽强地遵循亘古以来的模式。她自己对此未尝没有自觉的认识,在《洋人看京戏及其他》中她就这样写到:“最流行的几十出京戏,每一出都供给了我们一个没有时间性质的,标准的形势”,“历代传下来的老戏给我们许多感情的公式。把我们实际生活里复杂的情绪排入公式里,许多细节不能不被剔去,然而结果还是令人满意的。”[5—p25]
不过,所谓的“世情书”中的“世情”,不仅在于对规则化的世态人情的描绘,也在于对“规则”破坏时的世态人情的描绘,这后一点甚至更加重要。《金瓶梅》描绘末世世情,可谓入木三分,而所谓末世,其实就是价值瓦解、规则崩溃的时代。这与张爱玲所处身的时代极其相似:“这时代,旧的东西在崩塌,新的在滋长中。……人们只是感觉日常的一切都有点儿不对,不对到恐怖的程度。……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5—p175] 这样的时代,整个社会价值体系的紊乱、失落使个人的文化宗奉与精神寄托失落,个体的生存处于一种悬浮状态。缺少有力的精神支撑,个体生命的升华即很困难,人的欲望因之泛滥而横流四溢。如果说《金瓶梅》、《红楼梦》、《醒世姻缘传》中的世情描写渲染出一幅颓废奢靡的文化末世图,张爱玲的《传奇》世界同样以此为底色,只是更加阴暗没落。《传奇》中租界旧家的角色,在新、旧文化冲突的时代,传统的进身之道既已此路不通,他们又赶不上新的时代,年长的只能在“欲”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如《金琐记》中第一代的九老太爷与第二代的三爷姜季泽),年轻的则被旧时代拖着作为殉葬品(如《茉莉香片》中的聂传庆,《金琐记》中的姜长白、姜长安,《花凋》中的郑川嫦)。对于这种末世风情的描绘,使得她的笔下常常产生“下沉”的意象。像《中国的日夜》所写的:“嘈嘈的烦冤的人声下沉。/沉到底。……/中国,到底。”[15—p393~390] 也因此,她与世情小说作家共同分享着对于人性阴暗的看法。人性的软弱、自私、卑劣,在他们笔下暴露无遗。而基于对末世俗人身上阴暗乃至邪恶的因素的发现,他们描绘的他们的生存样态与情感行为方式,就很少注意向上的超越一路,而是以现实的态度呈现出一幅幅基于盲目的欲望基础上的“无明”、“不觉”的阴暗世情。陷于欲望之网中的人物,既无法肆意满足而不付出代价,又不能奋然而起、冲破欲望的罗网,他们只能在其中越陷越深,直至最后沉落下去。《金瓶梅》、《醒世姻缘传》等书中描绘的昏暗阴郁的世情,整个是一片荒凉的世界,让人不寒而栗。张爱玲的《传奇》世界也是如此,她虽描绘的是软弱的凡人的世界,但由于其中弥漫的乱世、末世感和对人性的悲观看法,导致她笔下的世情也是一片阴暗荒凉。
由于整体上的对世情的荒凉感,《红楼梦》、《金瓶梅》都笼罩着非个人的大悲。张爱玲曾经敏锐地指出,“就因为对一切都怀疑,中国文学里弥漫着大的悲哀。只有在物质的细节上,它得到欢悦——因此,《金瓶梅》、《红楼梦》仔仔细细开出整桌的菜单,毫无倦意,不为什么,就因为喜欢——细节往往是和美畅快、引人入胜的,而主题望远悲观。一切对于人生的笼统的观察都指向虚无。”[5— p111] 由于对人性的阴暗的看法,世情的虚无荒凉感乃是这类小说叙事的必然结论。而这同样弥漫在张爱玲的作品里。她的人物,不知何时都会面临着巨大的变故,他们没有天长地久的打算,只有抓住一点点现实的东西。他们无论是作恶多端还是小奸小坏,整体上其生存都处于一种“无明”的状态,没有意义地沉下去、沉下去。这种对世情的虚无感,甚至常常上升到宇宙性的层次,成为人物对世界的基本感受。《第一炉香》的结尾,葛薇龙在“密密层层的人,密密层层的灯,密密层层的耀眼的货品”中,感到“无边的荒凉,无边的恐怖”[15—p259]。《倾城之恋》中,流苏在战后的香港,夜听悲风,像“三条骈行的灰色的龙,一直线地往前飞,龙身无限制地延长下去,看不见尾。‘喔……呵……呜’……叫唤到后来,索性连苍龙也没有了,只是三条虚无的气,真空的桥梁,通入黑暗,通入虚空的虚空。这里是什么都完了。剩下点断墙颓垣,失去记忆力的文明人在黄昏中跌跌绊绊摸来摸去,像是找着点什么。其实是什么都完了”。[16—p82] 乱世体验当然是张爱玲产生这种虚无感的直接原因,但没有对世情荒凉的感受,她的感悟不会上升到这种世界性的层次。这种感受,直接导致了世情小说与张爱玲小说中的世界,都是一片荒凉的没有意义维系的世界。这是像《金瓶梅》这样的世情因素最为浓厚的小说的终点,像张爱玲所说的,对于中国人来说,“这‘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的感受总像是个新发现,并且就停留在这阶段。”[5—p111] 但是并非所有的中国小说就止于此,《红楼梦》与张爱玲都企图由此前进一步,他们企图籍“言情”来抵制虚无,虽然由此招致了更大的幻灭。
二、苍凉的言情:“言情”因素在张爱玲小说中的变迁
除了以《金瓶梅》为代表的世情传统之外,以才子佳人小说(佳话)为主体的言情传统在人情小说中也占有重要地位。这类小说的渊源可上溯到唐传奇中以爱情为主题的作品,而以繁荣于明末清初约一百年间的“佳话”为代表。其所叙述“大率才子佳人之事,而以文雅风流缀其间,功名遇合为之主,始或乖违,终多如意。”[6—p189] 结构上它们一般由“相爱——波折——大团圆”三元素组成。它们对以后的小说、戏曲乃至民间文学的影响绝不能低估,其“才子”、“佳人”的形象以及结构上“相爱——波折——大团圆”的模式,常为这类作品所继承。更为重要的是,它们描写的几近神秘的“情”,即使在并不承袭这类作品套路的作家那里,也常常被毫无保留地接受。如《红楼梦》就是如此,书中仍然可以认出才子佳人小说的影子。
才子佳人小说属于晚明以降文学中(尤其是戏曲、小说中)的写“情”潮流。这一潮流,明目张胆地为“情”正名,肯定“情”的合理性,但对“情”的理解,在当时作家当中存在着不同的层次。在最低层次,这种“情”只是基于男女才色之上的相悦,如清拼饮潜夫《春柳莺·序》中所谓:“男慕女色,非才不韵;女慕男才,非色不名,二者具焉,方称佳话”[12]。在较高层次上,这种“情”上升到不仅相悦而且相知的类似近代爱情的层次,如《玉娇梨》中的苏友白谓:“有才无色,算不得佳人;有色无才,算不得佳人;即有才有色,而与我苏友白无一段脉脉相关之情,亦算不得我苏友白的佳人。”[18—p36] 《定情人》中的双星谓:“性一兼情,则情生情灭,情浅情深,无所不至,而人皆不能自主。必遇魂消心醉之人,满其所望,方一定而不移。”[19—p5] 这就在仅仅才色相悦的基础上提高到了男女情感、思想交流的两心相知的层次。在最高层次上,“情”表现为一种神秘的力量,《牡丹亭》、《长生殿》等戏曲以及《红楼梦》等小说,莫不表现了这种神秘的、主宰性的“情”,这种“情”不仅主宰了主人公在现世的行动,从而使他们置功名富贵、纲常伦理乃至皇位江山于不顾,而且甚至可以超脱现世,与幽冥世界或蓬莱仙境中的相亲相爱者沟通,所谓“情之为情,虽非心而仿佛似心,近乎性而又流动非性。触物而起,一往而深,系之不住,推之不移,柔如水,痴如蝇,热如火,冷如冰。当其有,不知何生;及其无,又不知何灭,夫岂易定者耶!”[19—p154]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之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20—p1] 这种感天动地的神秘的“情”,远远超越了近代建立在个性解放及男女情爱基础上的爱情范畴,而升华成一种价值意义的尺度乃至形而上的东西。它可以赋予世界意义,甚至可以创造世界(如《红楼梦》)。
张爱玲对这一言情传统并不陌生,但是与“佳话”所代表的言情传统主流不同,张爱玲所写的,主要是“软弱的凡人”的凡俗之“情”。在特定阶段,她不否认“情”的重要性,但却很少把它理想化、神秘化。“情”的内质(男女二人的相悦相知)并未改变,但很少像“佳话”中那样具有伟大的力量。“佳话”中的男女真情战胜了种种阻挠而得到了“大团圆”的结局,在张爱玲的小说中,男女真情则因种种外来的或者内在的因素的摧折而破灭。可以说,前者是“言情”战胜了“世情”,在后者中,则是“世情”破坏了“言情”。虽然张爱玲吸收了“言情”传统中“情”的观念中的某些重要因素,她却并不接近这一写“情”传统的理想化主流,而更接近《红楼梦》与《海上花》的“言情+世情”的传统。⑥
在《自己的文章》里,张爱玲写到:“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真的革命与革命的战争,在情调上我想应当和恋爱是近亲,和恋爱一样是放恣的渗透于人生的全面,而对于自己是和谐。 ”[5—p175] 这也许可以代表张爱玲对“情”的观点,也可能渗透了她自己当时的亲身体验在内。可以看出,这段话中对于“情”的重视,虽然还没有达到中国戏曲小说中的“言情”传统赋予情以主宰一切的重要性以及由此而来的神秘性,至少它像这个传统一样,承认“情”在人生中的重要地位。但是作家自身的这种对“情”的体验,并没有蒙蔽她“冷眼看世情”的清醒的目光。她的小说描写了各种各样的“情”的破灭,对“情”的存在与否,也经历了一个由怀疑到肯定到彻底幻灭的过程。就其小说创作来看,我们可以据此把她的“言情”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传奇》一书为代表,着意描写了人间情爱的残缺与破灭,可以称为“无情的言情”。就她理解的“更素朴”、“也更放恣”、“渗透于人生的全面,而于自己是和谐”的情爱来说,可说在这一阶段她的创作中并不存在,遑论传统佳话中的理想化的“情”或神秘的“情”了。这一阶段,她着力描写的其实是各种各样的畸形的、盲目的情欲,在这个情欲的世界中,人物一旦有“爱情”的幻想,便会付出惨痛的代价。《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薇龙对乔琪的“爱”,是她在梁府这个鬼气森森的世界中生存的唯一精神支柱,一旦幻灭,不能不给她以致命的打击。失却了“情”(或“情的幻想”)的支持,她的未来不能不想起来只有“无边的恐怖”。假如说薇龙还存在“爱”的幻想,《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刚一开始就不对“爱”抱有什么幻想。她追求的只是婚姻,以及由此而来的经济保障,所以她与范柳原,两个算盘打得精刮上算的人,都始终不肯冒失。他们最后“平凡地”结成了夫妻,可是基础却并非奠基于爱情之上。《传奇》世界,便是这么一个爱的残缺的世界。《封锁》里的一对男女,在短暂的封锁期间的电车上,打开层层包裹着的伪装,有着短暂的心灵的敞开,几乎是“恋爱”了,但封锁一结束,一切随之而去,“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21—p107] 这也仿佛在暗示,对《传奇》世界里的人来说, 真正的“情”就像梦一样,代表了一种渴望,却并不真正存在,甚至在现实里显得“不近情理”。在《传奇》阶段,张爱玲不仅写了“情”的破灭,而且进一步写了各种各样变态、疯狂与畸形的情:压抑变态的曹七巧(《金琐记》),爱上了父亲的许小寒(《心经》),对丹朱既羡又妒、得不到她的爱就转为疯狂施暴的聂传庆……张爱玲以异常冷静细腻的笔触,展示了人世间各种各样畸形、变态的情感。
平心而论,《传奇》世界中的人物,由于生活在荒诞、冷酷、没落的世界中,他们最需要的便是代表着人与人的真正和谐、关怀的情爱,而他们也确实并不缺少对“情”的渴望。《倾城之恋》中的范柳原,给白流苏读了《诗经》上的几句诗:“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16—p71],暗示了他对真正爱情的渴望。《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佟振保看着荒凉的街景,突然感到了凄惶:“这世界上有那么多人,可是他们不能陪着你回家。到了夜深人静,还有无论何时,只要是生死关头,深的暗的所在,那时候只能有一个真心爱的妻,或者就是寂寞的。”[16—p135] 这些人物,可以说都期待着类似古典“言情”传统中真正的情,但由于荒凉的世情因素的介入,以及这些人自身的自私,他们得不到真正的“爱”。所以,《创世纪》中的紫薇,才觉得:“小说里有恋爱、哭泣,真的人生里是没有的。……像书里的恋爱、悲伤,是只有书里有的呀!”[16—p262]
张爱玲《传奇》时期的创作,整个呈现出的是一片无“情”的世界。但此后张爱玲却“蜕蜕对情爱的质疑甚而否定,蜕变而为深信不疑的肯定”,朱西宁并推测《传奇》一书,其中篇篇“无不言情,却篇篇无不所言皆是尔虞我诈的周旋或误植的虚情假意,因也个个人物一概的可悯可怜,全不可爱可喜,此即爱玲先生根底上质疑不信甚而否定人间有所谓的情爱。”然而这种否定,在她第二阶段(1947年至1955年),却来了个大转弯。这一时期,她以《多少恨》、《十八春》、《小艾》、《秧歌》、《赤地之恋》为代表的中、长篇小说,都赋予“情”以为重要的地位。这与《传奇》中对“情”的否定,成为鲜明的对比,可以说,张爱玲在这一阶段致力的一个主题,便是对世情包围之中的“情的意义”的思索。⑦
笔者认为《十八春》并不仅仅是一部“温婉、感伤、小市民道德的爱情故事”。世钧、曼桢二人的情爱,一方面有着张爱玲自己的人生体验,另一方面,书中荒唐、恐怖的世情因素对人间真情的摧残,也是典型的张氏笔法。与传统“佳话”不同,许、顾二人的恋情,有其现实的基础。而在小说整体上的阴暗氛围中,他们的恋情是彼此唯一的慰藉。“他所爱的人也爱他,想必也是极普通的事情,但是对于身当其境的人,却好像是千载难逢的巧合。”[22—p75] 这种难得的真情,是他们借以抵抗“世情”的荒凉、寒冷的唯一的东西。《秧歌》与《赤地之恋》,同样浸透了这种意图。虽然从整体叙事上看,两部小说都带有强烈的冷战政治色彩,但撇开这种色彩不谈,张爱玲关注的仍然是动荡不安的时代中的软弱的凡人的命运。《秧歌》一书中最感人的,乃是金根、月香这对患难夫妻的感情。《赤地之恋》中,刘荃被土改中的“左祸”震惊,在爱情中寻找慰藉:“他也像一般人一样,面对着极大的恐怖的时候,首先只想到自全。他拥抱着她,这时他知道,只有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是有一种绝对的安全感,除此以外,在这种世界上,他根本没有别的安全。只要有她在一起,他什么困难都能想办法度过。他一定要好好地照顾她,照顾他自己,他们一定要设法度过这凶残的时代。”[23—p84] 在这里,“言情”典型地体现为一种抵抗世情虚无的因素,也是小说中人物唯一的慰藉。爱情被表现为一种伟大的力量,它不仅体现了人们之间的信任与和谐,而且真正达到了为了所爱的人“可以生,可以死”的牺牲精神,这与古典“言情”传统赋予“情”的意义,已经相当接近。
不过,在这一阶段,张爱玲虽然赋予“言情”以抵抗“世情”虚无的意义,她同时也写了这种“情”的脆弱与无力。与前一阶段类似,这一阶段她笔下的人物,虽有“情”的支持,仍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世钧、曼桢相爱着,但他们的相爱却被祝鸿才、顾曼璐的诡计所破坏,他们的家庭也设置了种种阻碍。他们十八年后再相见时,已经历了许多人生波折,他们现在知道,那时候他们对彼此都是一心一意地相爱着,但已无济于事,“回不去了”。《赤地之恋》中,在风云变幻的时代面前,刘荃不但不能保护黄绢,反而要后者牺牲色相来救护自己。面对世情的虚无,“言情”显得多么渺小、无力,这好像寒冷的街道上一支小小的蜡烛的火焰,随时都可能被扑灭。《十八春》等书中,虽然赋予了言情以意义,但言情最后被荒凉的世情所侵夺、扑灭,越发显出世情的虚无。
张爱玲移居美国后发表的几个短篇,尤其是《五四遗事》和《色,戒》,可以看作她的小说中“言情”因素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即反讽的言情。在这两篇小说中,“情”被表现为一种反讽的因素,主人公寻找着人世间的爱情,也自以为找到了这种“情”,其结局却对人物的信念,形成一种强烈尖锐的讽刺,显示出这种信念的似是而非。《五四遗事》里的罗文涛,为了他与密斯范的恋爱,先后两次离婚,结果却发现,他理想中的“新女性”,“崇拜雪莱数十年如一日”的密斯范,结婚后日益平庸懒惰,似乎与旧女性也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失望之余,他变得世故、妥协,别人劝他将离婚的两个太太接回来,他也就无可无不可了。小说结束在朋友的打趣上:“至少你们不用另外找搭子。关起门来就是一桌麻将。”[21—p279] 罗所追求的,本来就是一种虚无缥缈、感伤造作的罗曼蒂克的爱,这是“恋爱刚来到中国的时候”,一种出于审美而非基于人生之上的天真的感情,一旦落实于现实人生,便形成强烈的反差与讽刺。《色,戒》中的王佳芝等人,巧设美人计,企图刺杀大汉奸易某,然而在最紧要的关头,王佳芝却陷入了自恋自伤,看着他脸上“温柔怜惜的神气”,她突然想“这个人真爱我的”,“心下轰然一声,若有所失”,放走了易某。易某当天即下令捕捉、枪毙了王佳芝一伙人。他想着与佳芝的一番经历,不禁心中得意,暗思佳芝是他生平“第一个红粉知己”,“得一知己,死而无憾。他觉得她的影子会永远依傍他,安慰他。虽然她恨他,她最后对他的感情强烈到是什么感情都不相干了,只是有感情。他们是原始的猎人与猎物的关系,虎与伥的关系,最终极的占有。她这才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21—p264、268] 佳芝所认为的易某对她的爱,其实只是她自己自怜自恋的一种想象,她却假戏真做,动了真情,而正是她的这种真情,成了她的致命弱点,送了她的性命。易某最后自得的想法,对于她一刹那间的真情流露,形成一种残酷而尖锐的讽刺。在这两篇小说中,“情”都被表现为一种虚无缥缈、若有若无的存在,某种意义上,甚至仅仅只是人们的想象制造出的幻象。人物越是执意寻求这种感情,最后越是对自己形成一种残酷的讽刺。“情”因而也形成了一种对“人性的盲目”的反讽。从另一方面看,这也是对“情”本身的幻灭。
三、“言情”与“世情”的关系
有人说张爱玲“破坏佳话,所以写得好小说”[3—p147]。这种对“佳话”的破坏,便表现在她具体描写了各种“情”的残缺与破灭,这也使得她的言情更接近于《红楼梦》与《海上花列传》所代表的“世情”与“言情”结合的传统,而非以佳话为代表的纯粹理想化的“言情”传统。
而就整体来看,不论是人情小说中的“言情传统”还是“世情传统”,对张爱玲对世界和人的看法,都影响颇深。她的小说中的某些因素,也只有在这两个传统的脉络里,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从小说史来看,“人情小说”中的“言情传统”(佳话)的兴起,对于“世情传统”来说,本来就是一种“温柔敦厚”的“反动”(鲁迅语),其区别是甚为明显的。这种区别,归结为最主要的一点,就是理想化的“言情”对世俗化的“世情”的超越意义。这尤其体现在像《红楼梦》这样继承了这两个传统并同时将它们发展到高峰的小说巨著里。余英时认为:“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创造了两个鲜明而对比的世界”,即“乌托邦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具体到小说中,即是大观园的世界和大观园外的世界,“作者曾用各种不同的象征,告诉我们这两个世界的分别所在,譬如说,‘清’与‘浊’,‘情’与‘淫’,‘假’与‘真’,以及风月宝鉴的反面和正面。”大观园的世界是作者的理想世界,它以“情”为中心,里面的人物,也按其在“太虚幻境”中的“情榜”上的名次排列高下,在书中主角贾宝玉的心中,它可以说是唯一有意义的世界。大观园以外的世界,则“代表肮脏与堕落”,充满形形色色的肮脏世相的现实世界,在这里,“情”之所以形成一个理想世界,端在作者赋予它的超越意义,整部《红楼梦》作为“形而上之意义上的‘情案’,它不过是力图要尝试一下:‘情’能否在大荒无稽的世界中确立起来。”它要给无情的世界补“情”。事实上,“言情”传统在传统中国一直处于非正统、非主流的地位,“情”的世界与世俗世界一直处于一种紧张关系之中。而从另一方面看,它既是对世俗的超越,却又始终与后者分不开:作为“情”的理想世界的大观园的干净,本来就建筑在会芳园的肮脏的基础之上,并且在它的产生、发展与破败的过程之中,它也无时不在承受着园外一切肮脏力量的冲击[24—p31~56]。大观园的最后破败说明“世情”的力量吞噬了“言情”的努力,“补情”的意义最终归于徒劳。
这种“世情”对“言情”的冲击、侵蚀、破坏,也同样体现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只是在她的小说中,“情”仅仅是“缩小而又缩小的怯怯的存在”,像《红楼梦》中那样豪华的“情”的“理想世界”,已不可能存在。这一方面说明了时代的剧烈动荡已不容许有这样的幻想,另一方面也说明,张爱玲虽然感到“言情”的必要,但她对“言情”与“世情”有更冷峻的看法。在张爱玲的“言情”世界中,由于不存在大观园那样的理想世界,她的主人公们,就必须直接面对冷酷的“世情”。在她中期较纯粹的“言情”之作中,“情”被表现为主人公之间一种相亲相知相慰的烛火一样温暖而渺小的力量,而它却要经受“世情”冷酷的重压。“言情”最终被“世情”吞噬,这也导致了她的小说最后对“情”的彻底幻灭。这种幻灭最终说明了张爱玲对人性的看法:一方面,人是一种渺小的动物,它无力抗拒外在世界的力量;另一方面,人性本身也是自私与软弱的,它本来就是构成冷酷世情的一部分。所以,企图给无“情”的世界“补情”,企图借“言情”拯救“世情”,本来就是一种徒劳的努力。而这也正是张爱玲向《红楼梦》这部综合了“言情”与“世情”两个传统的古典小说杰作学习最深的体会(这也与她自己的人生体验契合颇深,所以她借鉴传统小说显得特别浑然天成)。从整体上看,则又说明了她与传统人情小说杰作内在精神上的契合之处:一种共通的对人生的悲慨,一种共通的对世间的绝望,其最终的结果,便是他们小说中的荒凉的世界,失落了价值的世界。
注释:
① 有关书目可参看张爱玲文章中的自述、胡兰成为她弟弟张子静的回忆、水晶对她的访谈,这些资料中提及的阅读情况自然是挂一漏万,但已足以让我们看到她对传统小说的各种类型都有所涉猎。
② 事实上,张爱玲对中国小说史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她的评价标准很大程度上便是“细密真切的生活质地”与“日常生活的况味”,可参看《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红楼梦魇〉自序》、《忆胡适之》等文。
③ 当然张爱玲也有自己独到的发展,如对心理层面的探测等。
④ 参成穷《从〈红楼梦〉看中国文化》一书,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本文中“中国人的生存样态及其情感行为方式”一词也借用自该书。
⑤ 当然,要补充的是,这类小说中的杰作,也常常产生对这种重复的世间模式的怀疑与超越的愿望,如《红楼梦》中的神话结构和色空思想,《金瓶梅》、《醒世姻缘传》中借用佛家的轮回思想作为小说的结构,即使这种结构是外加的,它仍反映出解释和超越这种现象的冲动。
⑥ 事实上,张爱玲阅读《红楼梦》,也很少注意其中的情的神秘因素。在晚年所写的《红楼梦魇》中,她把《红楼梦》一书理解为“成长的悲剧”。这样,宝、黛二人“情”的破灭,就不再是因为外来的因素(如百廿回本中所写的“调包计”),而是在长成过程中不得不离开伊甸园的必然结局。她对《海上花》的理解,也与一般研究者仅仅把它归入狭邪小说不同,而认为其主题是“爱情”。就她对这部小说的阅读来看,她更倾向于关注其中所写的情的破灭。由此可见,张爱玲与《红楼梦》、《海上花》的契合,“言情”固然是一个因素,情的破灭却可说是更为重要的因素。
⑦ 朱西宁曾经注意到这个转折,他说此中原因,在于张爱玲经历了与胡兰成的一场传奇式的情爱,由此也体会到了个中三昧。参阅朱西宁《爱玲的爱》,收陈子善编《作别张爱玲》,文汇出版社,1996年。
标签:张爱玲论文; 小说论文; 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醒世姻缘传论文; 读书论文; 金瓶梅论文; 红楼梦论文; 海上花论文; 赤地之恋论文; 秧歌论文; 十八春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