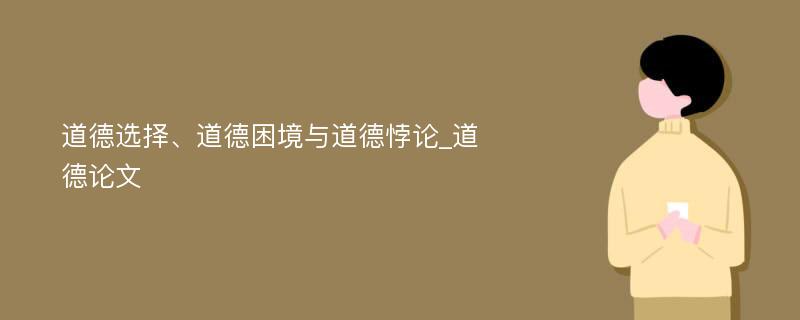
道德选择、道德困境与“道德悖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德论文,悖论论文,困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09)09-0043-08
一 道德选择与道德信仰
道德选择通常指个人的道德选择,集体选择涉及极为复杂的关系,不在本文论述范围之内。个人的道德选择大多是基于个人的道德判断的。而个人的道德判断与个人信奉的道德原则和标准密切相关。我们信奉的根本道德原则就是我们的道德信仰。因此,个人的道德选择与个人的道德信仰密切相关。研究道德选择不能回避道德信仰问题。
在道德信仰方面,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有根本的不同。在传统社会,人们的宗教信仰基本一致,道德信仰就内蕴于宗教信仰之中,如西方中世纪,人们的道德信仰就寓于基督教信仰之中。那时,人们诚然也要用决疑法去做出具体的道德抉择,但决疑法的运用是在基本一致的信仰框架中的运用。现代社会则不同。典型的现代社会是民主法治和市场经济的社会。现代社会的道德信仰是多种多样,而不是一致的。首先有多种宗教,如在西方民主国家,有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其次,不信教的人们的道德信仰也是五花八门的,仅人道主义就可分为好多种,如科学主义的人道主义、反科学主义的人道主义、素食主义的人道主义、生态主义的人道主义,等等,今天又有形形色色的女性主义。
在中国传统社会,人们的道德信仰也大体上一致,儒学既是最基本的政治意识形态,也是多数人的道德信仰。当然,儒学在古代中国统一信仰的作用没有基督教在西方中世纪那么大。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的历朝历代,道家、佛教仍有一定的影响力。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同志才把思想统一(信仰统一)推到极致。在那个时代,人们认为,善恶是非是判然分明的,判断善恶是非的标准是绝对权威、无可置疑的。所以,人们在这一时期一般不会有什么思想(信仰)的困惑,因为“毛泽东思想照耀着我们永不迷航”①。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渐入佳境。与此同时,我们也从毛泽东时代的思想统一(信仰统一)逐渐走向信仰的多样化和价值多元化。对2008年汶川地震时的“范跑跑”现象的评论典型地印证了这一点。有人强烈地谴责“范跑跑”,也有人竭力为之辩护,双方都能说出一番道理,其不同道理源自不同的道德信仰。对婚前性行为的道德判断也是如此。有人认为婚前性行为是不道德的,有人认为婚前性行为并非不道德,双方也都能说出各自的道理,各自的道理同样源于不同的道德信仰。
在信仰多样化和价值多元化的今天,个人不仅无时不面临具体的行动选择,还面临道德信仰的选择。这与传统社会大不一样。在传统中国,一个人极有可能一辈子都生活在同一个地方(一个乡村或一条胡同),这个地方的道德风俗是十分稳定的,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不变。人们的基本道德信仰是一致的,所以,个人一般不会面临道德信仰的选择。一个人只是从小到大接受道德风俗的熏陶,逐渐把外在的行为规范内化为自己的行为习惯而已。而现代人生活在各种道德信仰并存的社会中,我们不仅要做种种具体的道德选择,还得通过选择、反思去确定自己的道德信仰。一个年轻人可能因受长期的灌输而坚信一套道德信念,如果这种道德信念过于理想化,那么他随时都会因为市场经济的现实而陷入信仰危机。如果他相信,应该做高尚的、纯粹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后来发现现实中的人们大多总是力图用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而且这些人成功的机会较多,他就可能质疑自己长期持有的道德信仰,从而陷入信仰危机。这时,他如果勇于独立思考,便会通过阅读或与他人(老师、朋友)的交流而反省自己的道德信仰,从而重新确立新的信仰,逐渐走出信仰危机。在这一过程中,现实社会中已有的(即赢得一定数量信众的)各种信仰体系都有可能对他产生影响。他可能到马克思的原著中去寻找解惑的答案,从而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也可能恰好遇见一位高僧而遁入空门,也可能因偶然参加一个基督教家庭教会而信仰基督教,等等。
在信仰多样和价值多元的现代社会,没有万众景仰的能指引所有人的救世主(或大救星)。每个人都应该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去确立自己的信仰,这种独立思考的过程将会是一个选择信仰体系的过程。我们无法逃避选择,如萨特所言,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个人选择的无条件性源自个人的自主性。自主性(autonomy)是康德等思想家十分重视的价值。最有自主性的个人特别富有批判精神和怀疑精神。当然,任何人的批判或怀疑能力(高级思维能力)都是在特定共同体中通过较长时间的学习而培养起来的。以中国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为例:他们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思想长期灌输的过程中完成了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受教育过程,后来又亲历了从1978年开始直至今天的改革开放阶段。其间,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经历了信仰危机和信仰的改变。其中,最具有自主性的个人始终在进行思想求索,他们不轻信任何一种信仰体系,无论是基督教,还是自由主义。他们用自己独立的批判精神去审视各种信仰体系,最终确立自己的信仰。② 那些缺乏批判精神的人们,则可能轻易地接受一种现成的宗教。而最坏的选择莫过于不要任何超越性的信仰,而把市场经济的“逻辑”③ 当做人生真谛。在当代中国,恰是这种人居多,他们什么都不信,④ 只信钱和权;他们不再服膺任何道德,只服膺作为科学的经济学。实际上,这些人是最缺乏自主性的。如果说这类人是对道德信仰不做选择的人,那么他们的不做选择恰是一种对道德信仰的选择,而且是最糟糕的选择。详细论证这一点涉及对现代性的全面分析,这已超出本文的论述范围,故不在此展开。
今日我国少数怀念“以阶级斗争为纲”年代的人们把信仰多样化和价值多元化指斥为思想混乱,并认为思想混乱正是社会混乱的根源。在他们看来,真理体系是唯一的,凡不能纳入统一真理体系的思想全是谬误;只有统一所有人的思想,或者统一除阶级敌人以外的绝大多数人民⑤ 的思想,才能使社会秩序井然。显然,统一真理论是统一思想的哲学基础。但20世纪的分析哲学以清晰的逻辑表明,人类无力凭自己的理性发现或建构统一的真理体系。⑥ 历史和现实也一再证明,没有任何先知或思想精英,能用纯粹说理的方式统一人们的思想。统一思想的唯一途径是思想专制或军事暴政,即对“异端”的残酷镇压,如西方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和20世纪30-40年代的德国纳粹。罗尔斯说,现代民主社会中合情理地整全宗教、哲学和道德信仰的多种多样不只是将很快消失的历史性现象,而是民主公共文化(public culture of democracy)的永久性特征。⑦ 而且“合情理的多元主义(reasonable pluralism)这一事实不是人类生活的不幸条件”⑧。也就是说,我们不该把信仰(包括道德信仰)的多种多样看做令人厌恶的思想混乱,更不该把它视做可怕的社会分裂,而应愉快地把它接受为民主公共文化的常态。当然,不同信仰者都应该具有尊重他人自主性的德性,如果信仰某种宗教的人,仅坚信自己的信仰才是真理性信仰,而且在生活中敌视持不同信仰者,那么信仰的多样性确实能成为社会混乱甚至暴乱的根源。
自由主义者想把信仰归人私人生活领域,但公共事务的变化经常会牵涉人们的信仰。如果说公共道德就是各种合情理的整全性信仰(包括宗教信仰)的“重叠共识”,那么,生活世界的改变常常要求改变公共道德,而公共道德的改变势必引起不同信仰者的不同程度的反应(支持或反对),并引发激烈的道德争论。我们正处于道德争论日趋激烈的时代,也正处于要求改变公共道德的时代。
在道德争论日趋激烈、公共道德需要改变的今天,存在许多貌似道德困境的道德难题,例如,吃动物的肉是否不道德?该不该克隆人?人们就这类难题进行激烈的争论,主要因为人们持根本不同的道德信仰。马丁·科恩(Martin Cohen)在《101个人生悖论》⑨ 中列举的伦理困境(ethical dilemmas)大多属于此类。对于一个受动物权利论一定影响而又并不坚信动物权利论的人来讲,可能一度对该不该素食产生困惑,但如果他能深入思考,并进而深信汤姆·里根(Tom Regan)等人提出的动物权利论是对的,从而深信吃动物的肉是不道德的,就能立即走出道德困惑,做一个坚定的素食主义者。如果他通过学习生态学和利奥波德等人提出的生态主义伦理学,他便会觉得动物权利论是站不住脚的,从而不认为吃肉是不道德的,这样,他仍可走出道德困惑,摆脱两难选择。所以,走出此类困境的关键,是明确自己的道德信仰。在西方社会争论得十分激烈的堕胎问题也是这样。如果一个对基督教将信将疑的少女未婚先孕且不想要自己怀的孩子,她便陷入了困境,因为堕胎是违背基督教道德的,而不堕胎自己又无力承担抚育孩子的责任。她走出道德困惑的关键仍在明确自己的道德信仰。她如果有了坚定的基督教信仰,就应该勇敢地生下孩子。她如果放弃了基督教信仰,就可以去堕胎。
就此类问题而产生的道德争论会影响公共道德,进而会影响公共政策和法律。如果动物权利论产生了巨大影响,使绝大多数人皆确信,吃肉是不道德的,民主社会便会通过一项禁止吃肉的法律。当然,现实远非如此。尽管动物权利论有较大影响,也没有使绝大多数人深信吃肉是不道德的。但反对虐待动物的人们确实越来越多,公共道德也因此发生了变化,于是,不少国家有了动物福利法。天主教坚决反对堕胎,认为受精卵一旦在女性子宫内着床,就形成了一个有人格的个人,所以,堕胎就是谋杀。但西方社会的信仰是多样的,持世俗人道主义信仰的人们,主张给怀孕的女性以自主权。双方的争论影响了公共道德,从而在立法上达成某种妥协,例如,判定怀孕多少周以后堕胎是违法的,但之前堕胎是合法的。可见,这类表现为不同信仰之间的分歧的道德争论,可通过对话商谈和民主程序而得到暂时的解决。
二 道德选择与道德困境
对于有明确的道德信仰或宗教信仰的人们来讲,也会陷入具体道德选择的困惑之中。西方中世纪的神学家之所以重视决疑法,原因就在于此。如果一个人为履行某项道德义务就会导致他对另一项或多项其他道德义务的背弃,而且他不能逃避选择,则说他陷入了道德困境(moral dilemmas)。如果他必须履行的道德义务是两项,则可说他陷入了两难困境;如果他必须履行的义务是多项,则可说他陷入了多难困境。麦金太尔在《道德困境》一文中曾列举了三类道德困境。
第一类:一个道德上严肃的人发现自己履行一种社会角色的责任就不能履行另一种社会角色的责任。例如,作为一名军官,在终生有生命危险的事业中担任领导是其责任。但作为一个有严重疾患的孩子的父亲,他有责任守在家中照顾孩子。他无法同时履行这两种责任。⑩ 这一困境就类似于中国人常说的“忠孝不能两全”。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一文中提到的他的学生所陷入的困境也是这一类困境。(11)
第二类:一个道德上严肃的人陷入这样的境地,他不能按人们(不管他们的角色是什么)一般接受的道德规范行事,这与他的角色要求没有关系。例如,一个人因自己的承诺和另一个人对他的信任而必须保守机密。比如,某人不经意地泄露了关于股票市场的机密信息,并被要求做出承诺不再进一步扩散机密。但后来又知道,只有把这一情报透露给帮助重病儿童的慈善机构的代理人,该慈善机构才能摆脱一次财务上的灾难。在此,因两条或多条相关规范的明显不可归约性(incommensurability)而产生了困境。保守秘密和信守承诺的要求与避免伤害无辜的要求相冲突,为避免伤害无辜就不能信守承诺。
第三类:这一类涉及人格品质的不同理想。假如一个人认为自己为达到某个方面(如打网球或绘画)的卓越就必须不顾一切地专心致志。但他也充分认识到,他这种不顾一切的专心决定了他不可能培养帮助好朋友或同情穷人的品质。重视友谊和同情穷人的品质与追求事业之卓越的品质是不相容的,而且他觉得如果没有事业上的卓越生活就没有意义。为培养一种品质必须放弃对另一种品质的培养。于是他免不了人格发展上的缺陷。一种人格理想的美德是导致另一种理想的邪恶。(12)
麦金太尔认为,以上这三类道德困境是真正的道德困境。它们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某些责任冲突,例如,应约参加朋友的音乐会和按时批改学生作业的冲突。这样的责任冲突可通过个人计划的调整或向有关方面做适当解释而得到解决。它们也不同于发现两个人落水而你只能救其中一个的情境。这种情境根本就不是什么困境。在这种情境中,道德上重要的是你必须救一个,不能一个也不救。正当行动的方式是明显的。一个医生在只能救新生婴儿和产妇中的一个时所面临的境况也是一样的,这时的选择也不涉及道德困境,它有明确的正当行动的方式,选择其中任何一个都是对的。时间若不紧急,以抛硬币的方式做出选择也不失为一个办法。但在上述三类困境中,采取抛硬币的方式做出选择是不合适的。因为在这三类情境中,每一种选择的道德风险都差不多是同等严重的,当事人无论怎么选择都注定会做错事情(在第三类境况中,未来会做错事情),而且他(或她)将不可避免地感到内疚(guilt)。依范弗拉森(B.C.van Fraassen)之见,恰是事后内疚而非遗憾才把道德困境与其他困境区别开来。身处真正的道德困境意味着要不可避免地做道德上的错事。陷于道德困境中的个人似乎无法找到正当行动的出路。(13)
不过,就是否存在麦金太尔所说的真正的道德困境,即当事人无法找到正当行动之出路且不可避免地犯道德错误的困境,西方伦理学家有不同的观点。
在理性主义伦理学家看来,没有什么真正的道德困境,一个人只要有充分发展的理性,例如,信持一种合理的道德理论,有足够好的推理能力,那么他在任何情境中都能做出正确的道德判断,进而做出正确的道德选择。理性主义者把行动或口头的特殊道德判断看做是由某种普遍道德判断合取关于当事人所处境况的判断而推出的判断,把道德判断当做理性的命令。真的道德判断就是恰当推理的结果。(14) 根据这种观点,有些人觉得自己身陷道德困境,只因为他们还缺乏理性所要求的能力,如果他们获得了这种能力,便能摆脱困境。理性主义的基本预设是,所谓真正的道德困境对应着道德思维中的逻辑矛盾,一个真正有理性的人总能排除其道德思维中的逻辑矛盾,从而走出所谓的道德困境。附带的结果应该是,实践中的当事人不必为自己所做的选择而内疚,因为走出了道德困境,就意味着当事人能就正当行动做出明确判断,从而有了明确的正当行动的方向。按照理性主义者的思路,排除了道德思维中的逻辑矛盾,也便排除了现实生活中的二难或多难选择,这样,如果当事人是诚实的、严肃对待道德的,他便能确定不移地做道德上正当的事情,从而不必对自己之所为心存内疚。简言之,“对一个理想的有理性的当事人(他即使不是无所不知的,但至少知道每一个实践上相关的事实)来讲,不可能有道德困境。”(15)
理性主义的错误是把实践中的责任冲突与思维中的逻辑矛盾混淆起来了,或过于简单地设定了责任冲突与逻辑矛盾之间的对应关系(例如,设定两者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实际上,逻辑矛盾是命题之间的矛盾,是思维过程中的矛盾,这种矛盾与时间和思维者的实际生活能力没有什么关系。而道德困境中出现的责任冲突与实践者(或当事人)活动的时间性和活动能力的有限性密切相关。道德实践是人的实践。人是有死的存在者,即人存活的时间是有限的,这就决定了人永远只能花有限时间去从事各种活动,包括履行各种道德责任(或义务),人的许多行为选择恰恰就体现为把自己的有限时间分配于从事不同的活动。如果人是不死的存在者,那么他至少可轻易摆脱麦金太尔所说的第三类道德困境,例如花若干年时间去追求绘画的卓越,再花许多时间去帮助朋友和穷人。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他在同一时刻只能做一件事情。如果人有上帝般的全智全能,他就可轻易摆脱麦金太尔所说的第一类困境。其实一个人只要有孙悟空的分身法,即可摆脱第一类困境,可人没有分身法,故难免陷入“忠孝不能两全”的困境。显然,第一、第三类道德困境与道德思维中的逻辑矛盾没有关系。
第二类道德困境似乎可能是一个道德体系中不同规范之间的矛盾造成的,但如麦金太尔所说,即使我们排除了道德规范体系中的不一致(即矛盾),也不能排除实践中的道德困境。(16) 在一般的社会道德体系中,都包含着要求人们信守诺言和善待他人的规范,从逻辑上,我们看不出这两条规范之间的矛盾。在实际生活的多数情况下,信守诺言正是善待他人的前提,或说信守诺言与善待他人一点也不冲突。思维中的逻辑矛盾总是该被排除的,存在逻辑矛盾的语句是无法构成行动命令的。如“画一个圆正方形!”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常常一边信守诺言,一边善待他人。所以,“信守诺言且善待他人”是个可执行的行动命令。在麦金太尔所说的第二类道德困境中,“信守诺言”与“善待他人”之间的矛盾是由特殊的生活情境引起的。可见,第二类道德困境也与道德思维的逻辑矛盾无关。
正因为麦金太尔所说的真正的道德困境与逻辑矛盾无关,所以,我们不能用逻辑的方法去界定道德困境,更不能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去排除道德困境。麦金太尔赞成把事后内疚看做道德困境的标志之一,当事人之所以内疚,因为他认定自己做了道德上的错事,而这又是不可避免的。当事人之所以因内疚而痛苦,就因为他确信自己有责任发现正当行动的方式,如果没有这样的信念,他就不会有应负道德责任的负担,也不会因内疚而痛苦。(17) 身陷道德困境时的选择是两难的或多难的,就因为当事人无论怎么选择都觉得不对,做出选择之后还会因内疚而痛苦。你又不能不做选择,不做选择就成了“布吕丹的驴子”。
按说“应该”蕴涵“能够”。一个人应该做的事必是他能够做的事,他不能做的事就不是他应该做的事。那么面临道德困境的人能否据此而为自己开脱呢?例如,就第一类困境而言,当事人可否说,我没有能力兼顾我身患重病的孩子和军队的指挥工作,只好放弃其一,这不是我的错,我没有什么好内疚的!如果当事人竭尽一切努力都不能兼顾,局外人当然可以原谅他,毕竟我们不能说一个人应该做其做不到的事情。而当事人会不会内疚,以及会内疚到何种程度,则与其境界密切相关,也与其如何看待道德责任和道德规范有关。
如果你把一个道德体系中的每一条规范(对应着一种道德要求或道德义务)都当做绝对神圣的律令,那么在第二类困境中,你就绝对无法不犯错误,做出任何一种选择都是错误的,你甚至无法分辨错误的大小,都是绝对的道德错误。然而,在现实中连基督教道德都不能这样要求人们。不许撒谎,不许通奸,不许杀人,都是“摩西十诫”中的道德命令。按基督教的通常理解,每一个命令都是绝对命令(上帝的命令),即违背了命令就是错误。托马斯·阿奎那曾考察过发誓通奸或杀人的例子,并追问该人是否无论是否通奸或杀人,都犯了道德错误。通奸和杀人当然明显违背基督教道德,但这个发了誓的人若不通奸或杀人,就违背了自己的誓言,这相当于撒谎。陷入此种情境的基督徒可能真的很困惑。但阿奎那认为,这不该是令人困惑的情境。因为发誓干一件不道德的事情的誓言不具有约束力,违背这种誓言不是什么道德上的错误。(18) 可见,为了使一个道德体系具有可实践性,必须适当弱化道德命令的绝对性。在评价人们的道德行为时不能不考虑当事人所处的具体情境。
在帮助人们理解道德困境方面,现代伦理学中的道义论似乎不如目的论。因为道义论倾向于把道德责任(或义务)绝对化。但在真正的道德困境中,有限的人必须通过放弃一种责任(或义务)而做出选择。就第二类困境而言,如果你坚持道义论,就会认为无论怎么做,都是绝对错的。但你不能不做选择,选择是无法逃避的。于是,不是你想犯道德错误,而是你所处的境况迫使你犯道德错误。这样,道义论者之内疚的痛苦是无法减轻的。与此不同,目的论把道德行为界定为能带来较大善(积极价值)或减少较多恶(消极价值)的行为,可以区分不道德行为的不同程度,即同属不道德行为,有些行为更不道德。这样,当一个人陷入困境时,他可通过权衡不同选择带来的善(价值)的大小而做出选择。这样,就第一类困境而言,当事人可根据具体情境而做出较正确的选择。例如,在和平时期,他可以放弃军队的职务,而找一份与照顾孩子不相冲突的工作;在战争期间,如果没有他的指挥,就会造成巨大伤亡,他就应该放弃照顾自己的孩子,而履行自己指挥员的职责。当然,会有两种选择后果之价值难以比较的情况,就此而言,目的论也不能免除所有陷于困境中的当事人的困惑。
以目的论理解道德困境的关键是,对选择(行动)后果的好坏以及好坏程度的评估。每一种道德选择都为了实现某种价值目标。善恶有大有小,在道德困境中,我们应该两害相权取其小,或者说,可把人类追求的价值目标按高低大小排一个序列。当你深陷忠孝不能两全的境地时,如果你认为忠重于孝,你便会放弃尽孝而尽忠;反之,你就会放弃尽忠而尽孝。传统社会的礼法制度规定了一个大致的价值等次序列,个人在面临困境时可依此做出选择。我国“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的集体主义原则规定了一个较明确的价值等次,先国家,后集体;先集体,后个人。坚定信仰集体主义的个人很容易走出困境。假如一个人是“抗美援朝”时期的进步青年,他幼年丧父,又是独子,这时即使母亲病重,他也会毅然决然地奔赴朝鲜战场。
中国传统儒家关于“经”与“权”的论述,对于我们理解道德困境不无帮助。“经”指合于天道的礼法,“权”指具体情境中的价值比较和行为变通,亦指经(礼法)的灵活、恰当的运用。《孟子》中有著名的“嫂溺援之以手”的故事。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曰:“礼也。”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19)
按礼教(经),小叔子和嫂子不能拉拉扯扯,那么嫂子落水且会被淹死时,小叔子该不该伸手相救呢?这似是个道德困境。孟子的回答毫不含糊,必须伸手相救,见死不救就不是人了。在危急时刻向嫂子伸出双手是行权。孟子认为,道德伦理(道)比礼法(经)更重要,在两者发生冲突时,宁肯违背常礼,也不可违背道。违背常礼就是反经,但反经未必悖道。“嫂溺援之以手”就合于“仁者爱人”的仁道。
汉儒根据孟子经权相分的思想而提出了“反经合道”说。《春秋公羊传》桓公十一年记载:“古人之有权者,祭仲之权是也。权者何?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祭仲是郑国国卿,他为郑庄公娶夫人邓曼,生太子忽。宋国国卿雍氏把女儿雍姑嫁给郑庄公,生公子突。鲁桓公十一年(公元前701年)五月,郑庄公死,祭仲立太子忽为昭公。但当时宋强郑弱,宋庄公及其宠信的雍氏,想让祭仲立突为郑国国君。于是密谋设计,将路经宋国的祭仲拘捕起来,并以死亡威胁说:“为我出忽而立突”。如不立突,必死。此时,如果“祭仲不从其言,则君必死,国必亡;从其言,则君可以生易死,国可以存易亡”。在这君与国生死存亡的关头,在这守经还是反经的二难困境中,祭仲深知国重君轻之义,便选择了反经的非常措施,与宋国订盟,同年九月迎突归郑,立为厉公。昭公忽只得出走卫国。按照宗法制度,立长不立幼是“守经”,立幼而黜长是“反经”。祭仲为使郑国免遭君死国亡的危险,不惜黜长立幼,出忽立突,反经行权,以确保君生国存。故公羊家称祭仲为“知权”。在公羊家看来,行权可以反经,但必须“合道”。反经即违反当时的礼仪制度,合道即合乎道德道理。道高于经。据此,公羊家对行权规定了界限:“权之所设,舍死亡无所舍。行权有道,自贬损以行权,不害人以行权。杀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为也。”即在不害人、杀人、亡人的条件下,才能行权。(20)
公羊家的这一思想也可为目的论提供重要启示。目的论似乎只重视善(或积极价值),为了善的最大化,任何原则似乎都可以违背。其实不然。对人间之善的理解不能不诉诸特定的原则,为了追求善,不能不设定某种绝对的手段选择界限。公羊家讲的不害人、杀人、亡人,就是求善的绝对界限。或说“仁道”是求善的绝对界限。你可以根据具体情境而违背任何具体的道德规范以获得较大的善,但你不可突破“不杀人、不害人”这一道德底线(绝对的道德律令)。(21)
程颐批评汉儒的“反经合道”说,认为把经与权对立起来,会使权变流于权诈或权术。其实“权即是经”,即经权一体。朱熹对汉儒和程颐的经权思想都有所批判,提出了“常则守经,变则行权”的命题,主张经权异用说。朱熹说:“经是常行道理,权则是那常理行不得处,不得已而有所通变底道理。”“经是万世常行之道,权是不得已而用之,大概不可用时多。”“经毕竟是常,权毕竟是变。”(22) 显然,朱熹把经与道看成是同一的,是万世常行的,通常是不能违背的,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如在身处道德困境时,才可反经行权。
明代的高拱则对先儒的经权思想进行了全面批判,认为既不能像程颐那样认为“权即是经”,也不能像朱熹那样把行权看做违背常理的不得已选择。依高拱之见,既不能抹杀经与权之间的区别,又不能割裂经与权之间的内在联系。经与权是相互为用的关系。经不离权,权不离经;离权无经,离经无权。(23)“一时无权,必不得其正也。”“一物无权,必不得其正也。”(24) 也就是说,为确保选择合于道和经,必须时时灵活处变,这才是《中庸》所谓的“时中”。时时处处行权而不离道(反经)是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只有圣人才能达此境界。能达此境界,必不会再陷入道德困境。
高拱关于经权的论述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我们不能指望任何道德体系(抑或伦理学理论)能时时处处直接指导我们的道德选择,任何一次道德选择都要求选择者根据具体情境而做出具体的决定。
值得一提的是,博弈论所说的“囚徒困境”与道德相关,但它不是道德困境。“囚徒困境”是现代经济学所说的“经济人”(或“理性人”)的困境。“经济人”是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善于运用投入—产出分析法进行算计的人。在“囚徒困境”中,如果两个人的道德高尚一点,即超越了“经济人”的道德,各自为对方考虑,那么就会走出困境,得到最好的结果。(25) 即“囚徒困境”只是自私者的困境而不是有德者的困境。
三 道德困境与“道德悖论”
近几年学界刊出了不少论述“道德悖论”的文章,为理解当代社会的道德境况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逻辑学家把逻辑悖论界定为在公认正确的背景知识中合乎逻辑地推导出的矛盾等价式,即合乎逻辑地得出一个命题:P与非P互相蕴涵。可见,逻辑悖论是思维中的特殊的矛盾。苛刻的逻辑学家认为,矛盾只存在于思维之中,现实生活、经验世界和自然界中都没有矛盾。他们认为,只有“光是粒子”与“光不是粒子”这样的两个命题才构成矛盾,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并不构成矛盾。但辩证唯物主义在辩证矛盾和逻辑矛盾之间做出了区分,于是允许说现实生活和自然界中的矛盾,如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光的粒子性与波动性之间的矛盾。苛刻的逻辑学家会说,没有什么道德悖论,只有逻辑悖论。如果伦理学家用“道德悖论”这一概念,那么其中的“悖论”只能是借喻意义上的“悖论”。
有论者说:道德悖论本质上不是道德悖“论”,而是道德悖“行”。它不是被“论”出来的,而是被“行”出来的;不是思维理性的发现,而是“实践理性”的产物。道德悖论本质上是实践逻辑悖论,不是逻辑学意义上的思维逻辑悖论。(26) 在这里,论者用了“实践逻辑”一词。我想,这也是在借喻的意义上而不是在演绎逻辑意义上用“逻辑”一词。
“道德悖论”研究者们曾说,花大力气研究“道德悖论”的主旨,与其说是想“帮助人们在理论上认识和把握它的‘反逻辑’特性”,不如说是想“在‘实践理性’的平台上帮助人们科学地反思人类社会道德文明发展的‘疾病史’(卢梭语),客观地看待当代社会存在的‘道德失范’现象,适时地引导人们逐步排解‘道德困惑’,推进社会和人的道德进步”(27)。简言之,研究者们体现了对现实道德生活的关怀,而不仅是对道德思维方法的关怀。
他们列出的三类“道德悖论”的“结构模态”是:不当选择的结构模态、两难选择的结构模态和无意选择的结构模态。(28) 实际上就是一些个人选择或社会选择的错误和困难,其中“两难选择的结构模态”就相当于道德困境。
有论者分析:两难选择结构模态的成因不是主体选择某种道德标准和行为方式所致,而是主体面对难以选择道德标准和行为方式的“困境”所致,其悖论情境特别明显。它属于临境自知的两难选择,给主体的感觉是“不知所措”,由于是基于既定的道德标准和行为方式的价值比较和冲突,所以善与恶自相矛盾的悖论感觉特别强烈。生活表明,人们给这种模态的道德悖论“解悖”,除了依照既定标准和方式选择“两难”中之一“难”而外,通常是选择不选择。后者又有两种不同情况,一是选择放弃,对“两难境地”采取视而不见、自欺欺人的回避态度;二是选择变革,即更新既定的道德价值标准和行为方式。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而出现的新旧道德的价值冲突,在一些人心理上的反应就是“不知所措”的“道德困惑”,它是典型的“两难选择”的道德悖论。面对这种悖论情境采取视而不见、自欺欺人的回避态度,不论是社会还是个人都是不明智的,理智的态度应当是选择变革和更新,在积极提升道德智慧和能力的过程中寻求最佳的“解悖”方案,以促进社会和人的道德进步。(29)
显见,麦金太尔所说的真正的道德困境是典型的“道德悖论”,但“解悖”的方法不可能是纯粹的逻辑分析。为“解悖”,个人需要思与行,不能采取自欺欺人的回避态度,因为“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社会需要变革,需要用新道德取代旧道德。
“悖论”是逻辑学的典型用语。逻辑学是最硬的学科之一,向最硬的学科借用概念,似乎能产生很强的震撼力。但逻辑学对解决“道德悖论”没有太多的帮助。为解决“道德悖论”,个人需要通过慎思力行而培养实践智慧,进入尽可能高的境界。达到儒家的圣人境界,就不会有什么道德困惑了;达不到圣人境界,亦应努力达到“由明至通”的境界。把人生意义和道德理解明白(明)了,就能正确面对道德困境,“道德悖论”也就自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道德选择是知行合一的事,唯有实践智慧者才能时时做出正确选择。
注释:
① 这是“革命样板戏”《平原作战》中的一句唱词。
② 通常是审视几个最有影响力的信仰体系,没有人能一个不漏地审视所有的信仰体系,因为没有人有足以完成此种全面审视的时间和精力。
③ 市场经济最讲究的是资源的最佳配置,而这里的“佳”(即“好”)被定义为“高效率”。参见戴维·弗里德曼:《弗里德曼的生活经济学》,赵学凯等译,中信出版社,2003,第231页。所谓高效率,是由最少的投入(资本、时间、精力)获得最大的效用(偏好的满足)。于是有人就把市场经济的逻辑概括为投机取巧的逻辑。
④ 他们也许相信存在鬼神,知道自己不能绝对主宰自己的命运,所以他们中有许多人烧香拜佛(未必真信佛教),或者在自己的公司里供着财神。
⑤ 人民与阶级敌人、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的区分是“文革”时期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区分,那时人们认为,敌我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但在人民内部是一定要统一思想的。
⑥ 参见蒯因、库恩、罗蒂、普特南等人的论述,普特南对形而上学实在论(metaphysical realism)的批判就包含着对真理统一论的批判,可详见Hilary Putnam,Reason,Truth and Histo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p.22-74。
⑦⑧ John Rawls,Political Liberalism,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96,p.36,p.144.
⑨ 马丁·科恩:《101个人生悖论》,陆丁译,新华出版社,2007。
⑩(12)(13)(14)(15)(16)(17)(18) Alasdair MaCintyre,Ethics and Politics,Selected Essays,Vol.2,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86,pp.86-87,pp.87-88,p.90,p.93,p.92,p.94,p.98.
(11) 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周煦良、汤永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第13-15页。
(19) 《孟子》。
(20)(22)(23)(24) 引自岳天雷:《高拱的权变方法论及其实践价值》,《孔子研究》2001年第3期。
(21) 面对暴徒、暴君当然不能恪守“不杀人”的命令,杀暴徒、暴君是为了制止更多的人被杀。这再次表明,我们不能舍弃目的论和后果论的道德思维方法。
(25) 关于“囚徒困境”可参见罗伯特·艾克斯罗德:《对策中的制胜之道——合作的进化》,吴坚忠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第6-8页。
(26)(27)(28)(29) 钱广荣:《道德悖论的本质与模态》,《光明日报》2008年9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