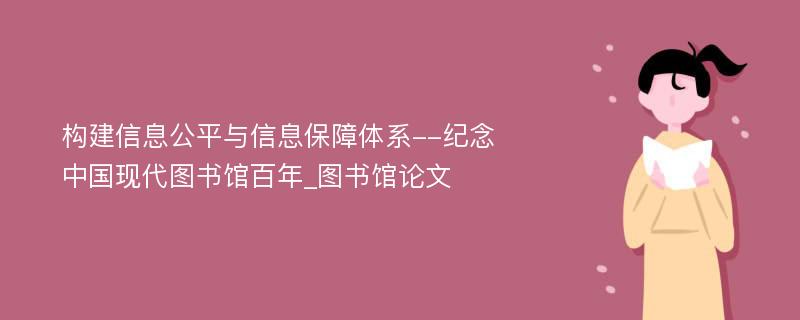
建设一个信息公平与信息保障的制度——纪念中国近代图书馆百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信息论文,中国近代论文,公平论文,图书馆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近代图书馆诞生于100年前,其标志是公共图书馆的出现。1902年,绍兴乡绅徐树兰办的古越藏书楼对外开放。古越藏书楼虽然名称上仍保留了“藏书楼”,但其对社会公众开放的特征明显,已具备了公共图书馆的形态。此后,1904年在湖南、浙江出现了较为正式的公共图书馆。它们的出现更加符合“公费支持”的公共图书馆定义。旅美著名图书馆史学家严文郁称湖南图书馆“为新图书馆的先声,亦是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端。从此清廷对图书馆的建立,有了积极的支持行动,各种类型的图书馆次第产生”〔1〕。随后,清政府颁布《京师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使公共图书馆的建设和对读者开放有法可依。从此,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完成了从封建藏书楼到近代图书馆的艰难跨越。
公共图书馆是一种现代社会特有的机构,对现代社会的意义,则是建立了一种实现信息公平与信息保障的制度。只要公共图书馆能够坚持基本的公共图书馆精神,社会成员就可能通过公共图书馆得到获取信息机会的公平;而如果公共图书馆能进一步开展针对信息弱者的特殊服务,则它就从制度上实现了信息保障。19世纪中叶,经爱德华兹的努力,英国出现了以国家法律保证、公费支持、免费服务、以及对社会成员无区别服务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公共图书馆。这种公共图书馆的出现使得历史上主要为统治阶层或社会精英——皇室成员、贵族、神职人员、政府官员、知识分子——服务的图书馆,将其服务对象扩大到了平民阶层。而一旦有了这种跨越,图书馆的社会意义就完全改变了。在社会精英眼中,图书馆仍然是获取知识或信息的场所;普遍民众眼中,图书馆仍然是“借书的地方”。但实际上,公共图书馆的出现改变了社会信息分配机制。新出现的机制就是政府通过法律和财税,保证每一位纳税人都有了公平地获取信息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图书馆代表了一种制度,一种保证社会具有起码的信息公平的制度。信息是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必备条件,不能保证公众自由地获取各种必须的信息,民主就只是一句空话。因此,公共图书馆代表的信息公平制度,对于现代民主社会是必不可少的。
对于公共图书馆的这种社会意义,爱德华兹本人似乎并没有意识到。爱德华兹对公共图书馆的执着更象一种直觉,他凭直觉意识到现代民主社会需要这样一种机构/制度,但从文献中,人们很难看到爱德华兹对他倡导的这种公共图书馆的职能有更清晰的描述。杜威也一样。19世纪末,杜威喊出了“人民的大学”的口号,给公共图书馆的职能一个醒目的标志。但杜威希望公共图书馆“教化”人民的愿望并不是公共图书馆精神的科学表达,1939年《美国图书馆权利宣言》确立了“图书馆自由”的原则,表明美国图书馆界放弃了这种愿望。尽管在1949年颁布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共图书馆宣言》中,仍然强调公共图书馆的教育功能,表明公共图书馆是“人民的大学”,但该《宣言》的思想核心,却是“公共图书馆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物”〔2〕的新认识。
二战结束后,社会逐渐意识到公共图书馆对现代民主政治的意义。1947年,美国图书馆学会发表了SH.Ditzion的著名专著《民主文化的武器库》〔3〕。这部著作第一次将公共图书馆的职能与对社会底层人士的人文关怀联系在一起,深刻揭示了公共图书馆与现代民主政治的关系。这部著作实际为《公共图书馆宣言》的问世奠定了理论基础。在1970年代公共图书馆“收费对免费”大讨论开始前,“民主文化的武器库”是西方国家图书馆学家描述公共图书馆职能的最流行用语。1948年,联合国将“信息权利”作为人权的一个方面写入《世界人权宣言》。该《宣言》官方中译本第十九条为:“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4〕。该条款中“消息”一词原文为information,也就是说,它表达的是人的信息权利。这一思想,已被公认为是《公共图书馆宣言》的思想基础。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共图书馆宣言》(1949)第一次以超出图书馆界的国际组织的名义,认同了“公共图书馆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物”。此后该《宣言》几经修改,但强调公共图书馆与民主的关系不变。1994年修订的《公共图书馆宣言》表明:“人民对社会的建设性参与和民主的发展依赖于良好的教育以及知识、思想和信息的无限开放”〔5〕。该《宣言》将保证民众有“良好的教育”和信息对民众“无限开放”这两项任务当作民主政治的重要前提,这两项任务曾经都是公共图书馆的重要职能。现在,前者已经越来越多地由国家义务教育机构/制度来承担,而知识与信息的开放(可自由获得),自19世纪开始就是由公共图书馆制度承担的。进入信息时代后,便利的网络与无所不能的信息服务商在信息提供方面承担了许多以前图书馆所承担的职能,包括在某些方面实现了信息公平。但是,由于最需要得到信息保障的信息弱者缺少利用网络信息服务的技术与经济条件,直到现在,这一社会群体的信息保障仍然必须由公共图书馆这一机构/制度来实现。
了解了公共图书馆对现代社会的意义,我们才能在纪念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百年之际,能够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图书馆事业与其应该承担的职能之间的距离。
百年前出现在中国的近代图书馆,是在“维新”、“变法”思潮推动下出现的新事物,它们朝着“平民化”图书馆走出了重要一步。但对照普勒100多年前那个经典性的公共图书馆定义:“公共图书馆是依据国家法律建立的,是受地方税收与自愿捐赠支持的,是被当作公共信息管理的,每一位维护这个城市的市民都有平等地享有它的参考与流通服务的权力”〔6〕,应该承认,中国当时的公共图书馆距真正的公共图书馆还有一定的差距。那时中国的公共图书馆一般是收费服务的,办图书馆的目的更多地是弥补社会教育的不足。公共图书馆出现后,推动图书馆事业的主要是一批留学归国人员。他们归来之时,世界公共图书馆理论处在杜威的“社会教育”理论阶段。中国社会教育的极度落后很自然地使早期图书馆学家们更看重图书馆的社会教育功能。至于图书馆在实现信息公平和信息保障方面的职能,在一个连人的生存权、生命权都得不到基本保障的极度贫穷落后的旧中国社会里,不可能有人考虑这样深层的问题。由于不能从保证民主政治的理论高度考虑公共图书馆的社会职能,当时大多数公共图书馆的运作极不规范,很难说它已成为一种实现信息公平的“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公共图书馆事业得到了普及与发展。杜定友先生1951年在《新图书馆手册》中说,“中国图书馆为人民服务,对于读者,不分阶级,一视同仁”,这一表述虽未说明是对公共图书馆的,却是符合早期公共图书馆精神的基本理念的。但是,对于二战结束后公共图书馆理论的发展,在整整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图书馆学家没有足够的关注,甚至没有基本的了解。在“文革”前的社会政治环境中,与外部世界缺少交往的中国图书馆学家不但很难了解《民主文化的武器库》、《公共图书馆与政治作用》这类战后公共图书馆理论经典,甚至不了解1949年颁布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共图书馆宣言》所定义的公共图书馆精神的新内涵。在“阶级斗争”激烈的环境中,定友的话甚至招来严厉的批判〔7〕。
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政治环境发生了根本变革。制约公共图书馆理论更新的思想束缚已不再存在。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加强,一大批硬件出色的公共图书馆出现在全世界各地。但是,理念的落后仍然制约着公共图书馆的发展。例如,公共图书馆精神主张的是“每一个人都有平等享受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权利”,提供特殊服务的对象是儿童、残疾人、囚犯等“不能享受常规服务和资料的用户”〔8〕。而我们的公共图书馆管理者习惯性地将“为领导决策服务”、“为科学研究服务”作为服务优先的目标,有些此类口号甚至被写入了全国性公共图书馆会议文件中。这些看似合情合理的口号的实质,其实是使公共图书馆的信息服务向信息强势人群倾斜。这很难说符合公共图书馆精神。在多年的关于图书馆“有偿服务”、“图书馆经营”的研究或讨论中,理论家们一般只着眼于它们对个别图书馆发展的利弊,从不考虑社会是否需要信息公平,以及“如果公共图书馆收费服务,谁来保证社会信息公平”的问题。
因此可以说,在过去的百年中,不论在实践中还是在理论上,中国图书馆界都没有将公共图书馆当作一种实现信息公平与信息保障的机构/制度,而给予认真严肃的对待。我们最多地将它当成一种普遍类型的图书馆——它保存文化遗产,为读者提供信息,是读者文化娱乐活动或接受社会教育的场所。然而,当前两个社会趋势却必须使我们重新考虑以往这种对公共图书馆的认识。
第一,国家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步伐走向民主政治,而实现社会的信息公平则是实现民主政治的前提。
改革开放初期,从极度贫困中走出来的中国人几乎将经济建设作为了唯一的发展目标。为了经济目标,甚至部分牺牲了社会公平。当前我们对公共图书馆的许多认识,既有西方“收费对免费”大讨论的影响。又有1980年代“经济第一”思潮的影响。中国经济取得了初步的成功后,国家领导人与社会精英越来越多的将社会发展目标从单一的经济目标转向了更加体现现代化国家实质的目标。尽管仍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无疑是前所未有的。图书馆在提高公民文化素质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这种素质是社会民主化的基石之一。此外,民主化要求所有民众可以参与社会管理决策,这就必须保证广大民众可以得到决策所必须的知识与信息。民众获取信息的渠道,除了人们关注的大众传播外,还有图书馆。谢拉在比较大众传播和图书馆这两种渠道时,称“大众传播是专制的,而图书馆则是民主的”〔9〕。谢拉的说法固然有些片面,但他所说的理由——图书馆可供人自由挑选信息——的确表明了图书馆这种渠道的重要性。
在这种大的社会背景下,有必要将图书馆发展的定位与社会的民主进程更加紧密地相联系,将图书馆建设纳入社会民主化进程,并通过公共图书馆这一实体在某一社会层面上实现信息公平,保障民众的信息权利,为推进社会民主化进程作出自己的贡献。也就是说,图书馆界的决策者与理论家们理应回到以人文精神为本质的公共图书馆精神。
第二,网络技术的发展,逼迫公共图书馆退出信息服务的产业化竞争,回到维护信息公平的原有职能。
100年前,图书馆是社会唯一的公共信息服务中心。二战结束后,出现了情报服务机构,但它们与图书馆是同类服务,可以相互吸收对方的服务模式。在这种信息环境中,图书馆投身开发信息资源的产业化竞争,具有一定的优势。最简单的例子,图书馆订了一种一般读者订不起的外刊,当图书馆有意对该刊实行收费借阅时,读者一般必须接受。在信息化的初期,这一趋势甚至还得到加强。如图书馆可以订购联机检索服务,对读者有偿服务。但网络技术的发展完全改变了这种状况。网络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之一就是读者有了家庭终端,通过它可以获取大量的免费与付费的信息。这一状况改变了读者对以往图书馆稀有资源的依赖。举例说,现在图书馆订购的《中国期刊网》很难有偿服务,因为清华同方同时也对个人用户出售并不昂贵的个人上网卡。因此,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除极少数大型公共图书馆外,一般公共图书馆可收费服务的资源是越来越少了。
但另一方面,社会中存在的信息弱势人群,他们一般不能将信息作为一种竞争性资源,因而也不可能接受付费信息服务,他们对图书馆的依赖却没有减少。网络技术普及为社会公众带来的大量可获取的信息,但对于信息弱势人群,他们由于缺少利用网络的经济基础与技术能力,无法自由地利用网络。上网技能及搜索网上信息的技术对信息弱者而言无疑是新的障碍,其影响甚至大于以往“文化教育程度”对获取信息的障碍。因此,公共图书馆在提供传统的纸质文献信息服务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对这部分人的上网辅助服务。1994年版《公共图书馆宣言》在“公共图书馆的使命”中写上了“促进信息的发展和计算机应用能力的提高”〔10〕,是发现了新的信息技术障碍后对公共图书馆服务提出的新要求。
由此,我们的结论是,不论社会信息环境如何变化,不论西方图书馆界是否继续他们的公共图书馆制度,对于处在民主化进程起步之初、民众文化素质与信息能力相对低下的中国,我们的确需要真正的公共图书馆制度——一种足以维护信息公平、保障民众信息权利的社会信息保障制度。这是中国图书馆界的百年未成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