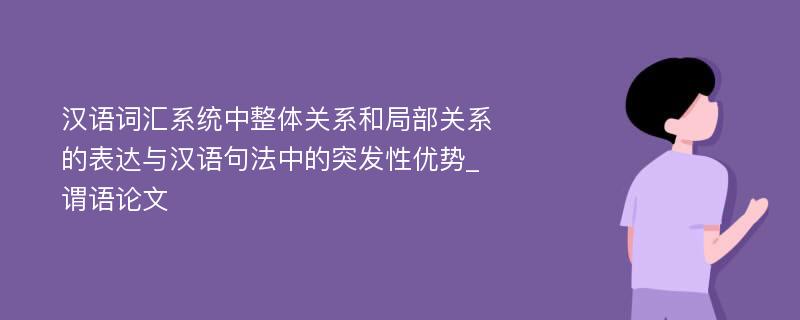
整体与部分关系在汉语词汇系统中的表现及在汉语句法中的突显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句法论文,词汇论文,关系论文,系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整体与部分关系
整体与部分关系在客观世界中普遍存在,也是人在认知过程中可以较为容易地把握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可以反映在一个语言的词汇系统中,具有整体和部分关系的词可以形成一个词语类聚(Cruse,1986:157-180;Murphy,2003:230-235)。
词汇学家对于同义聚合、反义聚合、上下位聚合等词语类聚研究较多,但对于具有整体部分关系的一些词语形成的类聚研究较少。Cruse(1986:157-180)用了一章来讲整体与部分关系,这是非常与众不同的。
关于整体部分关系的定义,其实不像看上去这么简单。Cruse(1986:157-159)区分了“部分”(part)和“断片”(pieces)这两个不同的概念。首先,部分具有自主性,断片不具备。断片必须属于某个整体,对于一个断片的完全复制不能成为某个整体的断片。而部分不必依赖于整体,比如展台上的打印机的部分,可以不必属于某个特定的打印机,对它的复制可以称为部分。第二,部分之间的边界是有道理可言的(motivated),断片之间的分界则是任意的,比如一个花瓶打碎之后裂成的断片在形状上可能是各种各样的。第三,部分相对于整体有固定的功能,而断片则没有。可见,Cruse所定义的部分是整体的自然的组成部分。本文也采用这样的定义。
整体部分关系在汉语词汇的组织结构中具有非常突显的作用,在汉语的句法层面,也有一些结构可以突显整体与部分关系。可见,整体与部分关系在汉语中得到了比较显著的编码。
二 整体部分关系在汉语复合词构成中的表现
刘叔新(1990/2005:356-363)描写了现代汉语词汇系统中的各种词语类聚,但并没有专门描述由整体部分关系构成的词语,而是将其归人了“分割对象组”这一类别之下,具有整体部分关系的词语(如“树根—树干—树枝—树叶”)与具有分类关系的词语(如“公猪—母猪—小猪”)被不加区别地放在同一类中,都看作是对某一对象的分割。实际上整体与部分关系(meronomies)和分类关系(taxonomies)在性质上很不一致(参看Cruse,1986:136-180),不宜放在一起处理。我们认为,整体部分关系在汉语词汇系统中的地位非常突显,应该给予专门的描写。
在现代汉语中,很多偏正式复合词是以整体部分关系为基础构成的,其中表示整体的语素充当修饰成分,而表示部分的语素充当中心成分,词义是指称整体中的某个部分,我们把这种词叫作“整体+部分”式的定中复合词。本文所说的“复合词”都是从句法角度定义的,都在句法上是一个最小的可以自由运用的单位,但不一定是词汇词(lexical word),因此不一定被收入词典。如:
手指 衣领 房门 眼皮 嘴唇 勺柄 表链 瓶盖 鞋帮 象牙 马脚 脚踝 胳膊肘
指称部分的成分可能是由隐喻得来的,如:
山脚 桌腿 壶嘴 笔帽 碗口 眼球 脚面 书脊 墙根 车身 船头 鼻梁
一个物体相对于另一个物体来说是部分,但这个物体本身可能又能分出不同的部分。可见整体部分关系是有层级的。在“整体+部分”式复合词中,充当修饰成分的整体必须是部分功能域(functional domain)内的整体而不能是其功能域之外的整体(功能域的概念参看Cruse,1986:165-167)。如:门是房的一部分,把手是门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只能说“门把手”,而不能说“房把手”。这是因为“把手”的功能域即其发挥作用的范围是“门”,因为把手的作用就是使门打开或关闭,而“房”作为整体已超出了“把手”的功能域,因此不能做“把手”的修饰成分以构成复合词。实际上人们感知到的整体部分关系一般都是在功能域之内的,而对于功能域之外的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则一般不太注意,这反映在语言中,人们可以说:这扇门有一个把手,但不说:这间房子有一个把手;人们可以说:把手是门的一部分,但不说:把手是房子的一部分。“N1有N2”和“N2是N1的一部分”是判断N1与N2之间有整体部分关系的形式框架(Cruse,1986:160-165),很明显,超出功能域之外的整体与部分不能进入这样的形式框架。
在汉语构词中,不同的整体中在结构上或功能上具有相似之处的部分可以有相同的名称,如:手腕/脚腕(在英语中分别是wrist、ankle,形式上完全不同)、手掌/脚掌(在英语中分别是palm和sole)。
由于汉语中“整体+部分”式定中复合构词模式的存在,汉语同属一个整体的部分在词汇形式上可以得到类似编码,如:树干、树根、树皮、树叶、树枝、树冠,从形式上也可以看出它们属于同一个聚合,构成了“同语素词语族”(刘叔新,1990/2005:386-388),而在英语中这些词在形式上没有共同的组成部分。
将汉语和英语的相关词语对比,可以看出汉语“整体+部分”式复合词突显了部分所隶属的整体。上文所举的很多词在英文里都不包含表示整体的语素。
“整体+部分”格式是汉语复合词中一种能产的构词模式,整体的主要部分都可以方便地得到词汇编码,词汇空缺(lexical gap)较少。而在英语中,整体中的主要部分往往缺乏专门的词语来表达(Cruse,1986:171)。如teapot(茶壶)有sprout(壶嘴),但装水的主要部分在英语中却没有专门的名称,在汉语中则有专门的词语“壶身”或“壶肚”。由于英语中表示整体和其部分的词往往采用互不相干的编码方式,即用没有相同语义组成部分的词来表达,因此为了经济起见,整体中发挥功能的主要部分是默认的成分,往往不会被词汇化(lexicalization)①,而其余部分则更可能得到词汇化。
从形式上看,汉语中表示整体的词语可以是较为简单的,表现为单纯词形式,而表示部分的词语往往是较为复杂的,表现为复合词形式,其中包含一个表示其所属整体的语素。这从上面的举例中就可看出。可见,这里体现出一种整体先于部分的认知观念:人们在认识部分时是从整体的角度来加以确认的,在汉语中这种观念就直接反映在词汇的编码中。
汉语中表示同一整体的不同部分的词也可以相互结合构成并列式复合词,如:枝叶、手脚、腿脚、心腹、嘴脸(这里的“脸”可能是用的较早时期的语义,指面颊部分,而不是指整个脸部)、耳目、血肉、筋骨;眉目、眉眼、领袖、爪牙、要领(“要”最初指“腰”,“领”最初指脖颈,其成词过程参看董秀芳(2002))、体面(最初指“躯体”和“脸”)等。这类由表示同一整体的部分构成的并列式复合词的语义,多是表示部分表现出来的共同特征或由部分所承担的功能,其中不少具有隐喻意义。
有时一个物体和另一个物体之间是位置上的依附关系,同时也有功能上的相关性。比如窗帘和窗户,窗帘虽不是窗户的一部分,但是在位置上依附于窗户,而且在功能上与窗户相关,窗帘可以看作窗户的附件(attachment)。附件与部分是相近的概念,因此表达附件的词在汉语中也类似于表达部分的词,可以构成与“整体+部分”式复合词具有类似构造的“整体+附件”式偏正复合词。如“窗帘、门帘”中的“窗”和“门”可以看作整体,而“帘”可以看作附件。这种“整体+附件”式复合词也可以看作一种广义的“整体+部分”式复合词。同类例子还有:灯罩、桌布、椅垫、床单、枕套、眼镜等。注意,这些词里两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不能概括成整体和部分关系,比如“椅垫”,垫子不是椅子的一部分,也不能概括成单纯的位置关系,对比“台灯”,台灯是放在桌子上的灯,“台”(桌子)仅仅是表示“灯”的放置位置,灯对桌子不发挥功能,而附件会对其附着体发挥功能,如“眼镜”中“镜”不仅是戴在眼上,而且是对眼(视力)有作用的。因此,把这类词中的中心成分看作修饰成分的附件是最好的语义解释。由于词汇编码形式上的相似,我们可以把汉语中物体与其附件的关系看作准整体部分关系。
三 在词义与词形的历时演变中部分义与整体义之间的关联
部分与整体在概念上密切相关,部分这一概念离不开整体的概念,如在对“手指”的定义中一定会参照“手”的概念,而在定义整体时,也往往会提及部分。因此整体义和部分义之间具有一定依赖性和关联性,二者在历时发展中存在变化关系。
从历时的角度看,一个词的意义可以通过转喻的机制而从指称部分变成指称整体。比如,“眼”从指称眼球变为指称眼睛,“脸”从指脸颊变为指整个面部。从部分义演变为整体义的规律是:词语最初表示的部分是整体借以发挥其功能的重要部分,显著度高。
整体变为部分的变化相对于部分变为整体的变化来说是很少的。虽然在话语中有些词可以从指称整体变为临时指称部分,如:我的铅笔很尖。这里的“铅笔”实际指的是铅笔尖,而不是“铅笔”这个整体,不过这种意义只是在特定语境中的解释,并不是固定的词汇义。整体转指部分可以看作是由于语境对于词义的调节作用而自然得到的,不需要固化为词汇义。比如,在“我洗了车”和“我保养了车”这两个句子中,“车”的不同部位被指称,洗的是车的外部(车的内部零件不能洗),而保养的主要是车的内部零件(有时也可以是外部的,如对油漆面的保养),但“车”并没有两个不同的固定的义项对应于这两个句子中的用法,“车”在这两个句子中的语义解释是由于语境的调节作用而自然得到的(通过与不同动词的搭配)。
还有一种情况是同属一个整体的部分之间的语义变化,即从指称整体的一个部分变为指称整体的另一个部分,这两个部分往往是相邻的,如“脚”从指小腿变成指足。
以上这些部分义与整体义间的词义变化以及部分义与部分义之间的词义变化也引起了一些常用词的词汇替换:某个新词所具有的意义原来在词汇系统中由另一个词来表达,该词作为后来者替代了原有者的位置而成为常用词,而原来的词则往往降格为语素而仍保留在词汇系统中。比如,在汉语史上,“眼”代替了“目”,“脚”代替了“足”,“脸”代替了“面”。在现代汉语中,原来表示“脑髓”的“脑”正在取代“头”(吴宝安,2006)。
部分义与整体义之间以及部分义与部分义之间的变化可能在很多语言中都存在,因为这是由普遍的认知机制转喻所决定的,而下面的一点则体现了整体部分语义关系在汉语词汇系统中的特殊重要性。汉语史中一些原来指称部分的单音词通过添加表示整体义的限定语素而发生了双音化(董秀芳,2004:134),比如:唇→嘴唇,指→手指,踝→脚踝,轮→车轮,枝→树枝等。胡敕瑞(2005)也举到了一些这样的例子,并把这种变化看作是原来词中隐含的义素“呈现”出来了,认为这样的变化是从上古到中古汉语词汇语义的一个重要变化。我们发现,有时添加的修饰语部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整体,而是像附件所依附的对象,如:发→头发,眉→眼眉,槛→门槛。大部分情况下,双音化发生后,原来的单音词不能再自由使用了,而是降格成了语素;但有时添加上表整体的限定成分后只是造成了一个复合词变体,原来的单音词仍可以作为独立的词使用,而没有变成语素,这样表达相同的意义就有了单音形式和双音形式两个选择,如:桨→船桨。有时添加的整体部分是两音节的,这样就造成了三音词,如:肘→胳膊肘。还有些个别情况好像是用一个相邻的部分作修饰成分,如:臂→手臂,腕→手腕,这可能是由于一时无法找到合适的表示整体的成分,而相邻的部分在认知上又是非常突显的。
上举不少例子都是表示人的身体部位的词。这不奇怪,因为人体就是一个可以清楚地分为几个部分的整体。部分不是随意切分的断片,而必须有自然的分界以及功能上的独特性,人体是可以按这样的定义找到部分的。从外观上看,人体可以分为头、躯干、四肢等,其中每个部分又可以分为更小的部分。着眼于内部构成的一致性,人体可以分为肌肉、骨骼、神经、血管等。人对于自身的认知是最早的,因此,整体与部分关系首先在人对自己的身体的感知上得以建立,表示身体部位的词也成为基本词汇的一部分。随后,与整体部分相关的词义演变也集中发生在表示人体部位的词上,并可作为进一步隐喻引申的基础。
四 整体部分关系在汉语句法中的反映
袁毓林(1994)提出了一价名词的概念。一价名词在表示某种事物的同时,还隐含了该事物与另一事物之间的依存关系,要求以另一名词为其配价成分。一价名词在句法上有一系列特殊表现。在袁毓林(1994)所讨论的三类一价名词中有一类是部件名词,表示某种事物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类一价名词涉及到本文所讨论的整体部分关系。袁毓林(1994)讨论了与一价名词相关的句式,以下要提到的三种句式袁文都有涉及,本文主要是从整体部分关系的角度来论述。②
4.1 分裂式移位:整体移前做话题的结构
汉语中有一种句法格式,可以把表示整体的部分移前作话题,而把表示部分的词语留在原位。如:
(1)那把椅子折了一条腿。
(2)蝴蝶他折断了翅膀。
(3)他把桔子剥了皮。
(4)他被人剪去了辫子。
沈阳(1996、2001)认为这种结构是名词短语的“分裂移位”造成的。③这些句子相应的非移位式格式是:
(5)那把椅子的一条腿折了。
(6)他折断了蝴蝶的翅膀。
(7)他剥了桔子的皮。
(8)他的辫子被人剪去了。
在这种非移位格式里,整体充当部分的修饰语构成偏正结构。虽然移位格式与非移位格式所表达的命题意义基本相同,但描述的出发点是不同的,在分裂式移位句中,描述的出发点是整体,句子表达的是整体经历的变化。这种结构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是突显了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部分的变化被当作整体的一种变化来描写④。而在非移位格式中,描述的出发点是部分,讲的是部分的变化,这种变化对整体的影响没有被突显。
4.2 主谓谓语句
汉语中主谓谓语句使用很多,如:
(9)这棵树,叶子大。(10)大象鼻子长。
这种格式也是通过对部分的描写来说明整体,以上句子可以变换成:
(11)这棵树的叶子大。(12)大象的鼻子长。
同样,在作了这样的变换后,整体的地位不如在主谓谓语句中突显了。
4.3 描写性名词谓语句
汉语中“形容词+名词”构成的名词性短语可以充当谓语构成名词谓语句,如:
(13)那个人,黄头发。
这样的格式有点像是主谓谓语句的变式,可以转换成主谓谓语句:
(14)那个人,头发黄。
与主谓谓语句一样,描写性名词谓语句也是通过描写部分来说明整体。这样的句子可以转换成普通的动词谓语句:
(15)那个人长着黄头发。
描写性名词谓语句的特点是显得更简洁,所描写的特征更为突出,在口语以及文学作品中出现较多。
描写性名词谓语句的谓语部分可以并列出现很多表示整体的某个部分的名词性成分,如:
(16)那个人,黄头发,蓝眼睛,高鼻梁,大嘴巴。
袁毓林(1994)指出,由质料名词和一价名词组成的偏正结构也能作名词性谓语,如:
(17)这双鞋塑料底儿。(18)这件大衣皮领子。
描写性名词谓语句中作谓语的名词指示的一般是主语所表示的事物的部分(或属性),如果不是主语的部分(或属性),就比较难进入这一格式,如:
(19)*那个客人,重箱子。(想要对有很重的箱子的客人做出描写)
以上三类句法格式都是汉语中较为特殊的句式,它们的使用表明:汉语在句法上可以通过部分来描写整体或整体的变化。表示部分和整体的词可以都占据比较突显的句法位置。比如在分裂式移位句中整体占据主语位置,部分占据宾语位置,在主谓谓语句中,整体和部分分别占据大主语和小主语位置,在描写性名词谓语句中,整体占据主语位置,部分占据谓语位置。如果把分裂式移位结构或主谓谓语句改成对部分的直接叙述,整体就不再占据突显的句法位置,而仅仅成为定语了,如果把描写性名词谓语句改成普通的动词谓语句,表示部分的名词性成分就由谓语位置变为宾语位置了。谓语位置比起宾语位置来讲,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是更为重要的,因为有宾语就有谓语,但有谓语不一定有宾语,谓语位置是更为关键的。因此可以说,以上三种句法格式提升了整体部分关系的突显性,使得表示整体与部分的词语不仅在句子层面出现,而且占据重要的句法位置。这与汉语构词层面的情形是平行的。
而且,在以上三种句法格式中,都是表示整体的词语在前,表示部分的词语在后,在语序上与“整体+部分”式的复合词的词内成分顺序平行。
另外,汉语在表示地点和时间时,在语序上是把指称范围大的放在前面,把指称范围小的放在后面,如: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2009年1月9日等。指称范围大的类似于整体,指称范围小的类似于部分,在这里,汉语句法同样反映了整体在前部分在后的顺序。
从语义焦点上看,以上三种句法格式的语义焦点都是在表示部分的词语上,表示整体的词语只是叙述的起点,是话题⑤;在“整体+部分”式复合词中,整个复合词的意思指的是部分,所以表示部分的词语或语素是焦点或语义上的主要成分,表示整体的词或语素只是修饰成分。由此看出,在汉语句法结构和词汇组织中所反映的整体部分语义关系中,部分都是焦点。
对比英语,英语在构词层面不具备“整体+部分”式的复合词形式,在句法层面也不具备以上提及的三种句法格式。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这样一个假设:一个语言的词汇与句法有着密切的关联,在词汇组织中重要的、得到词汇编码的语义关系,在句法中也是突显的,会体现在专门的句法结构中,而且在词汇组织与句法结构中所突显的侧面也是一致的。
五 结语
在汉语中,整体部分关系是一种突显的语义关系,在词汇与句法上都得到了显著编码。在现代汉语词汇系统中,有一批“整体+部分”式的偏正复合词,指称的是整体中的一个部分,这样,同一个整体的部分可以得到类似的词汇编码。从历时角度看,在双音化的过程中,一批“整体+部分”式的复合词逐渐替代了原来表示部分的单音词。在句法层面,汉语中有一些句法格式可以突显整体与部分关系,其表现形式是使表示整体与部分的词语处于突显的句法位置,而且,从语序上看,表示整体的词语先出现,表示部分的词语后出现。不论是在词汇层面还是在句法层面,部分义都是焦点。
语言是对世界的编码,在编码时不同社团的选择是不同的。全人类都能感知的一些语义关系在不同语言中被编码的方式有可能存在差异:在有些语言中得到了显著的、系统性的编码,而在另一些语言中则没有得到明确的编码,从而造成了语言的差异。对于这方面差异的研究,在理论上,对于探讨语言类型是有价值的;在应用方面,对于外语教学也会有帮助。
注释:
①这里的“词汇化”是在共时意义上使用的概念,指的是概念内容体现为词语形式的方式,参看Talmy(2000)。
②王洪君(2005)在对由动物、身体两义场单字组成的两字组的对比研究当中也发现,两义场单字在两字组组构中的差异主要与身体类单字具有[+隶属]特征、属于一价名词有关。我们认为,身体义场中单字构成的复合词不少也涉及到了整体部分关系。
③沈阳(1996、2001)讨论的分裂移位结构包括的类型比较多,有些结构中移位的成分和留在原位的成分不能用整体部分关系来概括,如:
小鸟落树上了两只。
动物园跑了一只狗熊。
沈阳认为移位成分与留在原位的成分大都可以看成具有领属关系。领属关系与整体部分关系实际上也有相似之处。不过,本文只讨论移位成分与留在原位的成分具有整体部分关系的分裂移位结构。
④袁毓林(1994)指出这种句式一般表示丧失义。原因是部件名词和整体名词之间有“局部—整体”的关系,这个“局部”是整体不可让渡(inalienable)的一部分,“整体”以原型的形式贮存在人的记忆中。报道某一部件从整体上消失很自然,但如果说在整体上再添上一个不可分割的部件就有悖常理。
⑤袁毓林(1994)指出,部件名词表示某种事物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可以触发关于某种事物的原型场景,而其本身成为这个原型场景的透视焦点。沈阳(2001)也指出,在分裂移位结构中,位于动词后的所指范围小的名词成分是焦点。
标签:谓语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