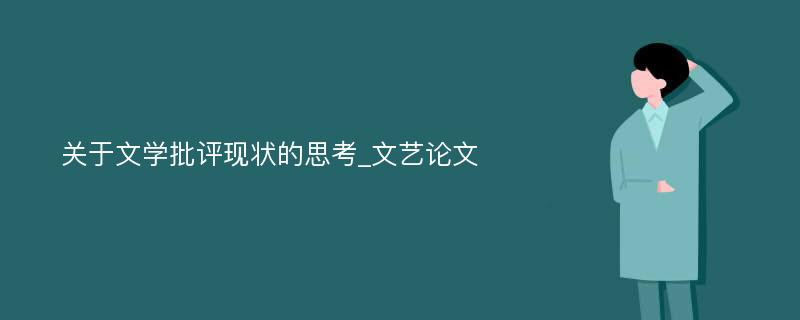
对文艺批评现状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批评论文,现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文艺批评现状的不满由来已久,从起初的颇有微词,到现在成为持续不断且日趋尖锐的话题;从来自高层的批评,扩展到来自读者、作者多方的责难,其中也包括批评界自身的反思;从局部的不满,上升到对整体的不满。
当然,新时期以来文艺批评的成绩是不可抹杀的,它不仅引导过创作和欣赏,也对思想解放运动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后来之所以发生逆转,有着诸多复杂的原因。因此对批评的批评,仍有一个历史的观点,不仅要指出其症状,也要分析其成因。明乎此,庶几可扭转批评式微的局面。
庸俗化与玄奥化
在对文艺批评的所有批评中,老作家孙犁的话大概最能代表多数人的意见,也最一针见血。他说:“近年文论,只有两途,一为吹捧,肉麻不以为耻;一为制造文词,制造主义,牵强附合,不知究竟。”又说:“近年来,文艺评论,变为吹捧。或故弄玄虚,脱离实际。作家的道路,变为出入大酒店,上下领奖台。因为失去了真正的文学批评,致使伪劣作品充斥市场。”后面几句连带批评了创作,并指出了由于批评的失责在创作上导致的严重后果。
孙犁指出的“两途”实为庸俗化和玄奥化,这确是近几年来人们触目所见的文艺批评的两大弊端。它使文艺批评丧失了公正性、科学性、实践性这最基本的品格,大大损害了文艺批评在新时期中树立起来的信誉和威望,也使文艺批评失去了大众。
文艺批评的庸俗化始于小兄弟之间的廉价吹捧,虽然未必关乎金钱,却也是一种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的交易。对一部作品是否置评、给予怎样的评价,有时以批评者与作者的交情深浅为转移。批评的冲动不是由作品激发出来的,而是由哥儿们义气、私交乃至派性引起的。当批评活动受私人关系左右时,就不可能对作品作出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评价。不少评论充满了溢美之词,对显而易见的败笔也不予指摘,还寻找种种理由为之开脱辩护,乃至赞红肿为桃李,这就把自己变成了吹鼓手。一旦与作者交恶,便变捧为骂,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捧杀与骂杀看似两个极端,实则一以贯之,是批评庸俗化的一对挛生兄弟。批评的庸俗化发展到近几年,又衍生出一种“红色批评”。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代替了温情脉脉的私人交情,成了驱动某些批评的有力杠杆。于是企图赢得名声、打开销路的作者、导演、制片人成了变相的行贿者,批评者成了变相的受贿人。请权威为自己的画册作序先要送上可观的润笔,请字画鉴定家瞒天过海,把膺品“鉴定”为真迹,更是以大把金钱作为润滑剂。更有名目繁多的“出场费”,成了众多文艺记者的生财之道,各种有偿评论成了90年代报刊、电台、电视新闻和评论的一大景观,简直成了支配舆论的主流批评。这种在金钱直接驱动下的有偿评论使90年代的文艺批评迅速走向商业化广告化,使大量伪劣作品得以借媒介的宣传欺世盗名,而有些好作品却湮没无闻,寂寞地等待伯乐的降生。真伪不分、美丑莫辨、是非颠倒,使文艺批评背负了不良的名声。
与庸俗化不同,文艺批评的玄奥化往往披上新潮的学术外衣,表现出前卫的姿态。一些批评者最初出于更新观念和批评方法的学术动机,这有其合理性。问题在于很快地变成了赶时髦,仿佛一年四季的时装表演。以文学观念而论,不少人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完成了从再现论到力主表现自我再到鼓吹形式主义的三级跳,唯先锋派的马首是瞻。至于批评方法,更是在短短的十年中翻了十来种花样。除了老三论、新三论外,还有心理批评、本体批评、原型批评、结构主义批评、解构主义批评、新马克思主义批评、女奴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等等,不一而足。而现代西方在文学观念和批评方法上的更迭转换,用了几乎一个世纪。这种与国际接轨的赶超精神固然可佩,然而如此喜新厌旧、猴子吃桃式的尝试,当然不可能在学理上有多少长进,更多的是一茬又一茬的名词术语的轮番爆炸,如同每乔迁一次新居都要炸它几百响一样。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文坛(包括创作和批评)成了各种主义和方法的演练场,几乎各种新式武器都操练过了,说“玩”也玩得差不多了,可究竟留下什么杰作,是很可怀疑的。批评的玄奥化正与此种追新猎奇、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有关。借来的或杜撰的各种主义纷至沓来,人们竞相搬用、竞相炫耀,而在学理上又未真正弄通弄懂,又如何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呢?而在具体运演时,又不问某种主义或方法的适用性和局限性,往往脱离实际、不分青红皂白地生拉硬扯。在一些起劲地鼓吹后现代主义的学人笔下,似乎中国一下子进入了后工业社会,经过他们的理论魔棒的挥舞,几乎所有的当下作品都带上了后现代的斑斓色彩,可谓天下尽入其彀中矣。对这种脱离中国国情和创作实践的超前运作,引用一下美国学者佛克马的话也许是颇有针对性的。他在专门为《走向后现代主义》一书的中译本写的序中说:“后现代主义作家表现出对无选择性技法的编好,而这一点似乎正是十分顺应经济兴盛的形势。西方文化名流奢侈生活条件似乎为自由实验提供了基础。但是后现代对想象的要求在饥饿贫困的非洲地区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在那些仍全力为获得生活必需品而斗争的地方,这也是不得其所的。”当然,现在的许多中国人都是喜欢超前消费的,创作和批评上的风气亦然。可是正如佛克马在同一篇序中又指出的那样:“包括后现代主义在内的任何文学思潮都有着自己的地理学的、年代学的以及社会学方面的局限”,“后现代主义文学是不能摹仿的,它属于一个特殊的、复杂的传统。”物质是可以通过技术的引进加以复制的,而精神的生产则要复杂得多,仅靠输入一种观念或依样画葫芦加以仿制,都是强加的、人为的,因而也是不自然的。早在前几年现代派盛行中国时,已有识者目为“伪现代派”,至于现在的诸多“后现代”,不免多为膺品了,包括在批评界正成为显学的“后学”,也难逃“客里空”的恶名。
失语与失衡
“失语”症也是文艺批评一再被诟病的一个症状,只是仔细论证起来却有不同的表现。
对当前的创作很少听到批评界的声音,这是一种“失语”,也就是所谓“批评的缺席”或批评的空位。批评的不介入和不干预,与“纯文学”、“纯艺术”逐渐为通俗文艺所取代有较大的关系。不少批评者对文艺的现状和前景感到失望,缺乏批评的欲望与冲动,不再把文艺批评当作自己挚爱的工作,渐渐与创作疏离,并从批评界隐退。另一个原因是传媒包揽了批评的大权,炒作式的新闻批评代替了学术性的批评,而一些作者也愿意通过红包或包版面的方式直接宣传自己的作品以扩大影响,使批评日益走上了商业化的道路。这种倾向甚至要求对文艺评论的性质、任务作出新的界定。一位著名影评家认为要挽救影评的危亡,就是要匡正以往的观念。他说“影评的目的非常明确,对读者而言是指南,告诉大家哪部影片的精彩之处是什么等等;对制片人而言则是宣传,有助于提高影片的卖座率。抨击劣片,告诫读者不要去看某片,则不属影评员的职责。”这种要求文艺评论放弃“赞优批劣”、引导创作和欣赏,而只需“做好宣传员”的言论,说明在批评界内部已出现了向商业化妥协投降的趋向。然而当评论家充当作品的吹鼓手和推销员时,还有什么独立性可言?又怎能坚持实事求是的评论呢?据说这样来规定评论的任务是为了同国际接轨,我看充其量也只是同国外的广告式评论接轨吧。事实上国外严肃的书评、影评,有不少还是很有见地的,评论的尺度也是相当严格的。在这方面倒是可以作些译介,以免珠被鱼目所混。
“失语”的另一层含义是批评失去了自己的理论话语。批评界并非都做隐士去了,有时也挺热闹。只是许多批评者所操持的话语,从名词术语、范畴命题,到表达方式,几乎都来自西方。话语的西化,使许多文章写得洋腔洋调,不知所云,且生涩难懂,如同拙劣的译文。当然,在不再与世隔绝的中国,要完全承袭传统的话语系统已不再可能,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要求尽量吸收已经实现现代化的西方文明成果,其中包括有价值的理论话语,这样才可能与世界进行交流,同时促进自身的学术繁荣,所以任何抱残守阙的思想都是错误的。但现在的主要倾向却是对西方的文学艺术的思潮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推崇。对西方文化的借鉴只能立足于中国本土的现实,并且参照自己固有的文化传统予以吸收融合,而决不能完全摒弃民族的传统亦步亦趋。无论用西方的眼光看世界,这是用西方的眼光看中国,都只可能落入西方文化霸权的怪圈,把自己置于“他者化”的后殖民语境,剥夺了中国学界与世界平等对话的话语权利。文艺批评中出现的理论失语症,正是这种全盘西化、鹦鹉学舌、邯郸学步的结果。
“失语”症的根本原因,我以为是价值判断的失衡。自从中国决心向昨天告别,走向开放和现代化以来,确实发生了许多变化。以前不允许办的事,现在可以办了;以前被视为天方夜谭的事,现在发生了;以前被列为思想禁区的地方,现在不仅可以进入,而且可以形诸笔墨了。这说明原有的许多束缚社会进步和束缚人的思想行为的规范被冲破了,隐藏其后的旧的价值体系受到了正在变化中的现实和日益增长中的欲望的严峻挑战,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轰然解体。这发生在社会的重要转型期,并不是反常的现象。事实上,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也参与了对旧的价值体系的解构。另一方面,新的价值体系又不可能一下子建立起来,于是在新旧交替的时代,往往出现价值的真空。没有权威,缺乏统一的认识和意志,缺乏行为的准则和道德的约束,价值观念出现混乱,价值判断的标准和取向产生分化。所谓多元化、多元的选择实际上是种种无序状态的结果,它既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机会和自由,也使许多人感到无所适从。显然,文艺批评的“失语”症就同这种价值判断的“失衡”有关。传统的真、善、美的命题,在今天可以作出完全不同的、甚至歧义百出的答案。什么是艺术?艺术是神圣的?是一种游戏?还是一种商品?什么样的作品才是好作品?凡此都可能有不同的回答,即使同一个批评家也往往出尔反尔,自相矛盾。既然传统的价值体系已经解体,而从事批评的人又不能没有价值判断的标准,于是向西方学习,以西方现成的价值观为自己的价值观便成了一些人自动的或无可奈何的抉择。然而西方的文化学术也非铁板一块,不同的国别、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学派都有不同的主义和倾向,一律拿来,照本宣科,不仅相互抵牾,且于创作也无益。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中国文坛的主将就曾批评过批评界的浮夸和混乱。他说:“中国文艺界上的可怕的现象,是在尽先输入名词,而并不绍介这名词的函义”,又说:“就耳目所及,各专家所用的尺度非常多,有英国美国尺,有德国尺,有俄国尺,有日本尺,自然又有中国尺,或者兼用各种尺。”“看见作品上多讲自己,便称之为表现主义;多讲别人,是写实主义;见女郎小腿肚作诗,是浪漫主义;见女郎小腿肚不准作诗,是古典主义;天上掉下一颗头,头上站着一头牛,爱呀,海中央的青霹雳呀……是未来主义……等等。”而现在的尺度和主义更是名目繁多,如果统统借来作为中国的尺度和主义,势必加剧价值判断的失衡,也令人头脑发昏。在这一点上,批评界的现状与鲁迅时代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批判与重建
在弄清当前文艺批评的症结和成因之后,就可能达成共识,通过批评界的自省和努力,逐步改变令人不满的现状。
当前的批评界首先要增强批判的意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批判性,20世纪一些新兴的哲学流派也强调否定性和批判性。只是此批判不是那批判,即不是文革式的深文周纳、罗织罪状的批判,而是一种理性批判。当前中国的批评界最缺乏的就是理性的批判精神,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正如前面所说,对西方的文化艺术思潮和理论,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崇拜。在这一点上还不如某些西方学者。如法兰克福学派的弗洛姆虽然充分肯定了弗洛依德思想的贡献,但也一再指出其不足。在有关的著作中,他一上来就指出弗氏失误有两个根源:一是资产阶级唯物主义理论,他把性作为所有内驱力的根源,以为这样一来就揭开了灵魂力量的生理根源;二是资产阶级的态度和父权制的态度。弗洛依德认为男女平等是不可思议的思想,直接导致了他的妇女心理学。他还批评弗氏“常常用琐碎的证据来进行理论的建构,而那些琐碎的证据却往往导致简直可以说是荒谬的结论。”应该说弗洛姆的这些批判都是有根据的,而他对资产阶级理论的阶级分析,在我们这里现在倒是很少见了。
第二,对创作讲好话的多,吹捧得多,很少指出存在的问题,特别对一些倾向性的问题,批评界未予正视,更缺少分析研究。比如创作上的形式主义倾向、脱离现实的倾向、玩世不恭的倾向、伪历史伪民俗的倾向,以及宣扬性消费、性开放的倾向,都是比较突出的。文艺批评不该对这类倾向视而不见,或采取不负责任的折衷主义和客观主义的态度,而应该通过有说服力的分析研究,引导创作扭转这些倾向,找到更好的发展方向。现代社会较为宽松的创作环境使不少有才华的作家得以脱颖而出,他们可以较为自由地选择题材,发挥自己的艺术想象力,并在形式风格上获得充分发展的可能。另一方面,社会转型期的巨大变迁,价值观念的急遽变化,又使作家仿佛一下子同生活脱了节,离开了原来熟悉的轨道。如果他们中的一些人不能及时地跟上时代的节拍,把握变化了的生活的真谛,建立起健全的价值观,那么他们会更敏感到种种困惑、迷惘和失落,与现实产生疏离感,甚至不惜自我放逐、自我幽闭,走向消极颓废。在这种状态下,自然不可能写出与时代相呼应、与大众相共鸣的作品。文艺批评有责任帮助一些有才华的作家走出这种状态,调整好创作心态,创作出无愧于读者,也无愧于自己的优秀作品。
第三,批评缺乏自审意识。文艺批评文章由于研究广泛的文艺现象,带有更多的理论色彩,所以比一般的评论文章远为严肃和审慎。可是有些批评者往往把写批评文章看成是一种自我表现、自我炫耀,灵感一来,兴之所至,或生造主义,或发表爆炸性观点,只求轰动效应,而不考虑可能给创作和阅读带来不良的后果。立论毋需论证,便是这类批评文章的一大特色。某些主义或观点可能也有一些似是而非的创作现象可以印证,但一经理论概括,并予鼓励提倡,其弊往往大于利。如“感情的零度”、“自我阅读”、“放逐评论”等提法,固然颇为新奇,但经不起推敲,于创作并无益处。“严肃的批评家最关心的不是自我表现”,白璧德的这句话倒不失为至理名言。文艺批评多一点自审意识,多一点科学精神,少一点炫耀卖弄,也许不至于如今天这般混乱。
鉴于批评的混乱失衡,有必要重建批评的价值判断系统。文艺批评虽以文艺为批评对象,却涉及方方面面。一个批评家如果对社会历史、人间万象、艺术百态没有自己比较成熟的看法,没有相对稳定的价值取向,那么就无法对文艺作品的价值和质量作出令人信服的评价,更无从对不断涌动的艺术思潮作出清醒的判断。然而批评的价值系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某个个人随心所欲的创造,它总是与一定时代和民族所面临的历史课题与文化指向相关联,与人们的审美体验相吻合。在今天,批评的价值系统只能以现代化的文化追求为指归,在批判性阐释的基础上整合传统批评理论和外来批评理论中有价值的部分,予以创造性的转换。这样,中国现代诗学的话语系统和表达方式才可能真正产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