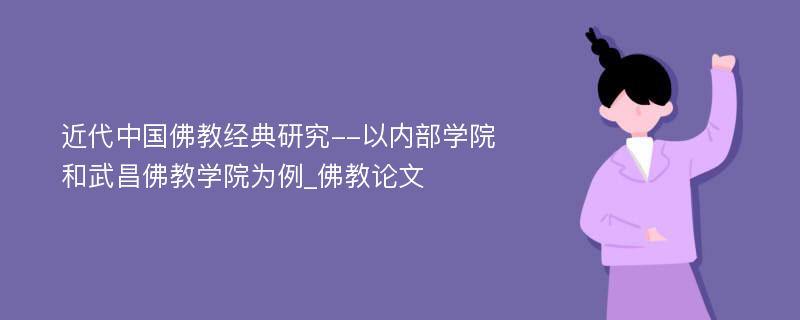
近代中国佛教经学研究:以内学院与武昌佛学院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武昌论文,经学论文,为例论文,近代论文,中国佛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晚清以来中国经史之学的兴衰与佛学的复兴存在密切的关联,类型各异的佛教学术运动背后都与经学之间发生了密切的互动,此为近代学术思想史及佛学史研究者不可不注意的问题。从民国佛教经史学的研究来看,支那内学院与武昌佛学院可以看作最有代表性的两个学术共同体。①可以说,他们虽然都有条件地接受近代学术的法则,而最终还是要保持住经学的优越地位。 1.两院经学之异同。对于内院与武院的佛学研究来说,经典之学成为他们的核心,他们无论在研究方法或结论方面,都参考了近代学术研究,特别是日本近代佛学研究的成果,而又能够自立权衡。他们重视教史,但与新史学派以史化经的立场不同,而着力最深的还是经典文本与经典史的探究。他们也不同于传统佛教经学,而重视的是在历史的源流探究中,去解读经典的思想及开展,以史抉经。在他们看来,圣典教义也是在历史中开展出的法流,与历史阐明可以取得一致。如印顺就说“契合于根本大法(法印)的圣教流传,是完全契合的史的发展,而可以考证论究的”。② 这表现在经论的研究上,两院都力图突破传统宗门意识和判教方式,而有系统地重新组织和抉择教典教义。内院与武院对于佛教经论疏解虽然都各有倚重,倾向上也都尽量做到不拘一宗一派,而对法义作出整体性的判释。 大致而言,内院以恢复印度佛教,特别是那烂陀寺的佛学教育为理想,在佛教经论的研究范围上,努力包含小大、空有、显密诸宗,“以期成一整体之佛教”。③关于大乘经教的方面,内院与武院都革新传统经教的判教体系而别抒新意,不过,内院与武院在佛教圣典的组织结构或判释方面表现出明显不同。内院坚持印度大乘只有般若、瑜伽两系,并不承认如来藏思想为独立一系,因而其判论经典,都会归到此两系中来进行疏解。武院则坚持以大乘三系来组织大乘经典,这样,他们就分别从不同佛学构架来组织经典体系及论疏。 近代史学对于内院与武院经学研究的影响之一,表现在古史探源的意识左右着他们对于印度佛教,特别是原始部派佛教圣典研究的热情。两院都批判了中国传统佛教思想中重大(乘)轻小(乘)的倾向,重视到印度佛教经史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先明小乘部派之学,才能够历史地理解大乘法义,于是特别提倡对于原始及部派佛教圣典的研究。欧阳竟无就说;今人对于大乘立义,每有望尘莫及之叹,而小乘思想接近,亦可藉以引导也”。④吕澂的佛教学研究与教学,基本就是在这一大纲下来作细密的经学抉择的。他所治的经论中,就有专门关于《阿含》及部派教典的。吕澂认为,对于佛教经典要获得正解,必须历史主义地推到原始佛教,特别是《阿含经》传统之中。他还指出,中国化佛教义学一向重大乘而轻视小乘,就是不尊重历史,而对法义也易产生错误的理解。如他作《杂阿含经刊定记》,就认为《阿含》“实乃三乘共教”,是一切大小乘佛教所共同依循的法义,因而也成为理解一切佛法经义的基础和根本所在。⑤ 武院一系的情况有点不同,太虚在宗系上虽然不是某一宗派的徒裔,而于印度佛教与中国佛教的关系方面,却是显有偏重的。对于近代史学影响而导致学界重印轻中的倾向,他表示了不同的意见。⑥他仍然要以中国佛教传统为宗主,而对经论的判释也大都在中国佛教义学的基础上来作开展。印顺则不同于太虚,而坚持从印度佛教法流中去抉发经教的真趣。印顺重视印度教史,他对有关圣典形成流变的历史考察,再到他有关经论的各类注疏与专论,都鲜明地表示了他佛学研究的倾向性。他批评过去学界重大轻小的倾向,主张初期圣典才是大乘佛教思想的法源。⑦这一点上,印顺与内学院立场较为接近,表现了民国佛教史学研究的一种探源性观念。⑧于是,在佛教治经方面,他特别重视对《阿含》及原始部派圣典进行经史学的探究。当然在研究方式上,内院专精而严密,更具论师的风格,并能够广泛应用近代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来勘定经典文本;而武院则重博洽,倾向于通过历史的演化去理解经论的思想,在手段上只能充分利用汉译典籍来作比勘研究。⑨ 2.从启蒙到内学。近代意义上中国佛学经史的研究都离不开杨文会。因此讨论两院佛教经典学研究,首先要对杨文会的佛教经史学观念略作了解。杨文会有感于晚清佛教的凋敝即在于经学衰微,而大力倡导佛学经典研究之风。他特别批评当时禅门“目不识丁,辄自比于六祖”的作风是滥附禅宗,妄谈般若。⑩因而,要求学佛者一概丢开从前学禅见解,“俟经论通晓后”,才能“处处有着落”。(11) 杨文会在佛学经典阐释方面也形成了一些新的观念。他强调经教研究在佛法修学中的重要性,重视“文字般若”、“三藏教典”的作用。(12)在佛典研究方面,他重视网罗散逸经论,并对古本经论“讎校再三,重加排定”(13),作细致的文本考订工作。他并没有广泛注疏经论,除了《大宗地玄文本论略注》外,他对佛典的研治主要是通过经论的叙、跋、题词及别记,或是书信等传统书写方式来加以表现的。杨文会治经取径上遵循了汉学一套由训诂而义理的路线,从文本的勘定而直接到经义的阐明,所以夏曾佑就说他“移士夫治经学小学之心”来研治法相一学。(14) 就是说,杨氏仍然是在经学的范围内来治经,而并没有触及到史学的方面。他甚至批判西方近代史学对印度初期佛教史的考证方法是“但求形迹”而已。(15)如他指出,西方近代学术在考究佛陀出生年代等问题上计较真妄,而导致“多种不同,莫衷一是”的争论,认为这类没有结论的佛教史学探究“亦不能得其真,但如烟云过眼而已”。(16)不难发现,杨文会治经的经学立场,使他对于新知的接受是有很大的设限的。他把新学的价值仅仅局限在与经典理解密切相关的小学方面,具体说即是西方近代佛教学研究中比较语言学的那种方式。他在给南条的信中曾表示,经教的研究“非深研梵本者不能道”。(17) 内院更愿意以传统的“内学”一词来称呼佛学。欧阳竟无治学的重点即在经学,“而尤致意捡除伪似,以真是真非所寄自信”。虽然他在佛学的立场方面与他的老师杨文会有很大的不同,甚至是对立(如对于《起信论》的态度)。不过,仔细比较他们处置佛教经史学的方式,的确也可以发现许多一脉相通的地方。如他们都重视经典文本的勘定、比较语言的应用、求之于法相学而弥补传统经解的笼统颟顸,以及对近代史学的怀疑等。 欧阳竟无的经学是以宗教性为前提的。从根底上说,他认为内学研究是“内证为内,推度为外”,即必须以现量亲证为法度的。只是对于大多学者无现量之经验,才必须下转为圣言量,即经学的探究来阐明法义。(18)关于这点,欧阳在《与章行严书》中谈到内院研究的目的与“求学之方法”时,讲得非常明白,可以参考。 研读经文最难通其大意,而得其全体。欧阳竟无治经,形式上看主要还是沿袭传统“经叙”的方式,但是细究其有关经义宗旨的阐明及其经论系统的论述方面,实在有不少新的发明,而这是解经方面难度很高也颇见其功力的一面。欧阳竟无根据他对印度大乘思想的系统判释,而就他所认定的几部在佛教思想系统中至关重要的大乘经论(如《大般若经》、《瑜伽师地论》、《大般涅槃经》、《维摩诘经》等),皆作了详密的经叙,以阐扬他对大乘思想、思想系统及其释经方法等问题的理解。 表面上看,欧阳竟无拒绝以西方的科学和哲学来讨论佛教,这在他的《佛法非宗教非哲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不过,在佛学的建立上他并不是一味反对西方现代性的人物。他恰恰非常重视西方近代以来通过比较语言学所建立起的那套佛教学研究典范,并贯彻在他所领导的内院教学和研究当中。经典的思想或经义虽然是治经的旨趣,但是欧阳竟无特别强调要辅以汉学的考辨为基础。在“今日之佛法研究”中就提到,内学研究需要对经典文本进行“简别真伪”、“考订散乱”及“借助梵藏文”来对文本作出勘定。(19)他还批评明清以来佛教释经学缺乏汉学的根本而“随情立教”,指斥这类笼统的解经是“随手拾一经一论,顺文消释,就义敷陈”。(20)另外,对于佛教经典的体系,欧阳竟无已经形成了他特有的架构,他研治大乘经学的大纲即由《瑜伽》而《般若》而《涅槃》。(21)这可以说是对传统佛教经学教判形式的一种突破。 与传统佛教经学及新史学治经皆有不同,近代史法的以史化经,意在颠覆经典的神圣性,对于经典好作怀疑主义之批判。欧阳有意识地针对近代史学的这一风气,而提出内学研究“不可轻易违反旧说”,仍然恪守经学优先的意义。他指出“故于旧说,须抱发明主义,不可抱违反主义”。即是说,对于佛教经论的论究,只能在确保经典至上的条件下“推阐发挥”,而不能够“外于已定之结论”而别为新说。这就是他著名的“结论后之研究”方法。欧阳阐明经学的方式并不需要特别经过史学方式的淘炼,因为经是“由无漏智等流而出”,具有超越时空的一面。(22) 于是,欧阳竟无治经重在小学与义理,而不是史学。他还特别强调了小学(比较语言学)在佛学研究中的基础地位。即是说,欧阳对经典文本探究由语言文本的考订,所指向的并不是史学的问题,而仍然是义理或哲学性的问题。虽然他自称其治学方式是“由文字历史求节节近真,不史不实,不真不至”。(23)而实际上,与其说他重视以历史治经,毋宁说他在治经的取径上采用的是传统汉学那类训诂明而义理明的路线,由“文字般若”下手而会通经义。他在叙及自己学术的“晚年定论”时还是坚持对于佛教经论的研治分为两段,即“前考据,后义理”。(24)即是说,欧阳在经学的阐明上强调的是文字而义理,并不是由史而通教义。他这样说治经的为学次第:“文字般若能娴,而后观照般若不谬;——故文字之功,斯为至大”。(25)又说“一字不真,全体皆似;一语或歧,宗祧易位”。(26)可见文字的判读对于经义的理解是多么的重要。据学者研究,欧阳所设立的“内学院”,其对内学的解读就不是一般相对于外学的意义而言,对欧阳来讲,内学表示了形上学或性理学的意味。(27)于是,他对于佛教经典的判释通常不是以史为断,而恰恰是以教理为断的。“今之言学则不然。处处须得真相,即处处须以教理为断”。(28) 3.吕澂以史论经和经学上的“性寂”观。吕澂的佛学研究也是以经学为主轴而又以史为辅论的,他认为“佛教研究之根本典籍,首当推藏经。所余之古人撰述,类皆由是流出派生”。(29)所以其研究成果也大多是围绕着经论方面而展开的。与传统治经,甚至与他的老师欧阳竟无不同,吕澂的佛教经学研究具有了比较鲜明的近代性特征,这表现在他把治经与近代史学结合起来。他明确表示,佛教经学的研究“一方依义理推阐,一方依历史开展”,这样“理事兼至”才能够得尽其学。(30) 欧阳竟无所立定的从考证而义理的解经原则,吕澂特别加入了历史的维度。他认为经教的义理是“佛教研究之主眼”,但是在对教理研究的取径上,吕澂综合文本考证、教义及历史于一体,而能够对西方近代佛教学所提倡的比较语言学与文本学的研究方式善加应用。他坚信,圣贤寄托在经典中的原义,是可以通过历史考证、语言学分析等方法得到真传的。故而其由研究汉文佛经进而回溯到研究梵文和巴利文、藏文佛典。关于此,吕澂作了很明确地说明: “今谓教理由文字研究势不可废,训诂、达意二法亦不应偏重。但训诂应有比较的研究为之依据。译籍则异译之比较,原典之比较,得文句精确之解释,而后训诂为无病。又达意应由批判的见地尽其运用,或则以一部前后所说为批判,或则以著作家根本思想为批判,或则以当时一般思潮为批判,乃至典籍流传之地域写本,古今学说之变迁交涉,种种方面皆当理解。而后观一部大意不致偏失,通全体之理论亦端绪可寻。如是得佛教教理,其真相矣”。(31) 吕澂治经通常就是以汉、藏、梵等不同译本互勘,“比较研求,复备数益”而发现许多但从译文而无法觉察出的问题,同时他又能够“出入注疏,彷徨旁论”以传统论疏为参考,对经典教义进行“章句义解”。(32) 在治经的形式上,吕澂已经突破了传统以来经学注经的格式,也不同于欧阳以经叙来阐明说经。他除了以“讲要”的方式来疏通经义,不少论著都是以现代学术专题或论述的方式来表达他对经教的意见。在他为各类经论所作“讲要”中,也没有统一的体例格式,如《法句经讲要》就以“总辩经体”、“解析品次”、“抉择要义”而对经典进行三番讲述;而在《阿毗昙心论颂讲要》中,则又分别从“文献源流”、“学说系统”和“研习资取”三方面来开展论述。(33) 关于大小乘经论的判释,吕澂依其修习阶梯分为五门,即毗昙、般若、瑜伽、涅槃四科,另外单立戒学一门。在这里,毗昙限定在佛说范围,为声闻乘之学;般若科则谈智慧为主,瑜伽则言禅定,《涅槃》“乃佛学究竟之目标”,而戒学经典则为实践之基。(34)对每一科,他又根据同类学说之经典,而作浅深不同的安排。吕澂的经典判释体系,基本是从欧阳竟无的思想中沿袭而来,不过他对此作了细密的具有近代学术史意义的论述。 内院虽然努力于整体佛教教义的组织与阐明,而实际是有着鲜明法相学的倾向,并对台、贤两家中国式的佛教义学进行了严厉批判。在经教思想的判释上,欧阳是以法相为衡准来加以阐明。如他在对一大藏教进行新的分类判释时,就批判传统经类的分法缺乏圣言量的根据,而主张以法相门的《瑜伽师地》五分、《摄大乘》三类来“严部”通括经律论的分判。(35)他认为法相学最鲜明的优势即在于论理精密而不笼统,“唯识、法相,方便善巧,道理究竟。学者于此研求,既能洞明义理,又可药思想笼统之弊,不为不尽之说所惑”。(36)为此,他多次批判天台,其中很重要的一项指控,就是认为天台释经“率意随情,不顾经论”,即于经论的研判上“不事翔实”,过于“笼统而风谈”,从而导致对于经义“尔犹悬度”,于“词语处处乖违”。(37)吕澂也着重批判了台、贤两宗对于经典的判读。如从历史方面看,他批判台贤疏经缺乏历史的观念,而一味判《阿含》为小宗,而不加重视的观念。而从大乘经论来说,吕澂认为,台、贤也多所误判,如他指出天台的止观、华严的缘起等中国式佛学思想就是受到《楞严》、《圆觉》和《起信》一流如来藏思想影响而误入歧途。(38)最可圈可点的是,天台以《法华》为宗经而详为之解,而吕澂在其所著《妙法莲华经方便品讲要》中,多次对天台的《法华》释义进行批判,认为天台注《法华》“但拘泥文字,于此(法华)要义,多所淹没”,又说《法华》之观门“非天台家所执之空假中”,而是“法性平等观”,这些都可以说是想对台宗作釜底抽薪式的拆解。(39) 吕澂还明确和系统化地把这一观念作了论述,他的经解对于中国传统义学思想充分应用了“批判的见地”,并把批判的重点聚焦于“性寂”与“性觉”两个心性学的中心观念上。他提出“印度佛学精华,萃于法相、唯识”,在治经的思想和方法上,他一以贯之地以法相学的性寂观念来疏解和判释经论的真伪高下。如他对如来藏系经典的判释就鲜明地表示了这一宗趣,他对如来藏系的重要经典《胜鬘经》所作的唯识学化的诠解即是显例。他对该经中如来藏自性清净义的解释是,如来藏就是阿赖耶识的自体,而“所边赖耶法尔自性本寂,不与所执相符”。又说“如来藏义当以此经归之自性净心为最主要之解释”。(40) 这一思想倾向尤其鲜明地表现在他对《楞严》、《起信》思想的批判方面。吕澂通过他对经教的判释,以为印度佛教的法流在心性论上都是心性本寂(或本净)的传统,他甚至认为这一性寂说是“全部佛学之根本”,从原始论典《阿含》到大乘经的《般若》、《华严》、《涅槃》等“皆作是说”。(41)而《起信论》以来中国佛学之所以偏离印度正统佛教思想的方面,就是错误地理解如来藏的概念,而引向了心性本觉的方向。(42)吕澂认为,《起信论》的错误根源在于对《楞伽》误读。在实践的观心方面,《楞伽》的法门是以观妄为要旨,而不是以真心为所缘的。而在“《起信》与《楞伽》”和“《大乘起信论》考证”两文中,则更从译文、文本流变等方面,试图表明《起信》真心的观念乃是由于跟着魏译本《楞伽经》的误译而错上加错,以至于影响到中国佛学主流“成为一种消极保守的见解”。(43) 于是,他专作“《楞伽》如来藏章讲义”、“《楞伽》观妄义”来阐明《楞伽》的真正法流是性寂而非真心论的,并以此批判《楞严》、《起信》真心论。 内院的佛教经史学重于对中国佛教思想的批判,但我们不能把这些批判简单归约为宗派主义的论述,却可以看成是一种具有强烈学术统系和经学立场的修辞。 武昌佛学院对佛教经史的研究,无论是在学术思想、教史的观念及研究方法等方面都与内院有交叉也有不同,甚至在不少思想方面有所对峙而相互评破。他们之间在佛教经史学上论辩与互究学理,实际上推动了民国佛教经史学的发展。武院的佛教经学研究,可以说是民国教界中首屈一指的典范。 1.太虚与经学护教。太虚早年就曾在西方寺做过系统阅藏而获得佛教经学的入门之道,(44)可以说,治经之学终其一生不辍,《法相唯识学概论序》中说“盖大师殚志内典,历时二十余年”。(45) 太虚对于经教的疏解,与内院不同。内院专深,在方法上也是经由汉学的文本考据、语言比较学而转向义理的论究。太虚注经并没有就经论的语言与文本考证方面下功夫,乃是直探经义而重于经论思想的阐明。他自己就说“其本因仍在从佛学的心枢,自运机杼,随时变化,不拘故常以适应所宜,巧用文字而不为文字粘縛,原不着脚在文字中讨生活”。(46)这种夫子自道表白了一个教徒式的治经姿态。 对于教史,太虚一面维持中国佛教思想的合法性,而对历史上汉传佛教各宗大体都以包容而统摄的姿态来看待。于是,他对于佛教经论也试图不偏局于一宗一家,而对义教的各宗经论都有所抉择和疏释。他说自己解经“尤于会合台、贤、禅的起信、楞严著述,加以融通决择”。(47) 释经形式在民国佛教经学中可以说是不拘一格的,太虚经释在体例上也分别有“义脉”、“讲录”、“经释”、“述记”、“讲义”、“释义”等多种种形式,而格式上大都分为“悬论”与“释经”两大部分。所谓悬论,一般都是就该经的宗趣、经题及译史等进行阐明;而释经部分则科释经文,依据经文进行科判,标明经义主题,而后随文释义。也有依传统释经之缘起、正说、流通三分来组织架构和解说的,如他的《佛说八大人觉经讲记》就是这样的格式。 在教相判释方面,太虚并没有接续传统义学的判教,而是别具一格地因应时代变迁有所新创。在《般若波罗密多心经释义》“悬论“中,他抉择天台、华严两家释经的判教,而认为这些判教“皆为适应当时的思想环境”,不符合当今的需要。所以他要重新对佛说教理进行判释,而大分为三,细分为六类。即从大小乘教统观可分为三教,分别为五乘共教、三乘共教和大乘不共法。(48)有时,他又分别以五乘共学、三乘共学和大乘共学三类来加以说明。而大乘经教又可细分为“特胜大乘”、“普为大乘”及“适应大乘”,又称“圆融大乘”三科。(49)他在《摄大乘论初分讲义》中又以“法空观慧”、“法相唯识”与“真如净德”三宗来说大乘三教,这种三教判释逐成为他及武院判说佛教经学的基本定式。 太虚教判表示了与内院以来鲜明不同的立场,他的教判乃有所针对近代佛教史学研究中回归印度佛教为尊,而贬斥中国佛教的倾向,有意识地把中国佛教各类经教都合法性地纳入教判的体系内,甚至推为至尊。他对民国学界共推法相,贬斥台、贤的时流还特别作了评破。针对内院以批判如来藏思想来否定中国式佛教的倾向,太虚则特别抬高如来藏思想的地位。他提出如来藏思想不仅是一系统独立的佛学体系,而且为大乘诸系中最为圆满究竟的一系。(50)在他看来,内院等一系所激烈批评台、贤二宗在经教方面颟顸笼统之弊,正是其圆融周至的妙境。他说“此宗所明者,乃法空观慧所生、所显,法相唯识所明、所证之体也。摄有为无为一切无漏清净法”。(51)太虚对经解的判教,特尊如来藏的法流,可以说是近代佛教经学中最鲜明的中国佛教的护教体系。 对于中国式佛教的护教还表现在他对疑伪经所作的信仰诠释学。有感于近代佛教经史学中的疑经主义思潮,太虚对塑造中国佛教思想上有重要影响的经典,都一概采用了教徒式的辩护。如近代学界对《四十二章经》存有怀疑,太虚则在《四十二章经讲录》“悬论”中,对于近代学界的怀疑之论一一都作了评破。(52)最鲜明的例子莫过于他对《起信论》的辩解了。值得注意的是,他对《起信》的辩护不仅有教义教法上的考虑,同时也试图对近代性学术史方法进行颠覆。他批评日本望月等学者考证起信论方法,认为这是“以毒迷于西洋人思想学术发达进化之偏说——即所云进化之史论及科学之方法“。(53) 内院在佛法研究上保留了证量为上的合法性,而在经史研究的具体取径上则接受近代新知。太虚则不同,他认为佛法即为内证之学,原则上就不应该进入近代史学论列的范围。他曾多次严厉批判以西方近代史学观来研治佛教经论:“用西洋学术进化论以律东洋其余之道术,已方柄圆凿,格格不入,况可以之治佛学乎?吾以之哀日本人、西洋人治佛学者,丧本逐末,背内合外,愈趋愈远,愈说愈枝,愈走愈歧,愈钻愈晦,不图吾国人乃亦竞投入此迷网耶!”(54) 原则上讲,太虚并没有一味地反对教史研究,如他于1930年代发表的《佛法概论》中也提到“教史”研究的必要性,而认为经教的研究包括了“佛教史料的编考”,“各种文体经典的校订”等。(55)只是涉及到经教,尤其是中国经教的合法性问题时,他就非得挺身而出,护教般地硬要在经史学之间划出一道鸿沟。而作为他后学相知的印顺,在佛教经史学上的出发点恰恰是试图去重新弥合这一裂缝。 2.印顺与经史之间。印顺对于佛教经典的研究,重视了史学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而把经典放置到文本流变中去作抉择。他与教界一味“深闭固拒”地反抗近代历史考证方法的倾向不同,对所谓“史的科学之方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佛法本身就是“出现于一定的时空中”,而具有“世谛流布”的一面。于是对佛教经典、思想与制度等事相,历史考证的方式还是必要的。(56)如他研究原始佛教圣典集成时,就本着历史主义的态度,以为原始经典并非佛的亲口宣说,而是经过由“说”到“集成”的历史过程,因而只能看做是“佛说的影象”。(57)而当胡适《坛经》研究引起教界一片哗然,而广为争论的时候,印顺就对胡适的历史考据学方法以恰当的肯认,并指出佛教史的作家(除了玄学家)“还是会采取胡适的论断”,“否则,即使大彻大悟,也于事无补”。(58) 对于佛教经学的研究,印顺的论述大致可分为史论与经释两部分。在史论方面,他对佛教经典史的论究受到近代史观的影响,重视对印度教史上原始圣典到大乘经典集成与形成作历史的论述。所以他对教典与教史的研究重心还是放在印度的方面。印顺有关教史与圣典的研究是融合在一起的,他的教史著述,如《印度之佛教》、《印度佛教思想史》、《初期大乘之起源与开展》及一些相关教史论文,都有专门论述印度佛教圣典之形成及其性质方面的内容。而他的《杂阿含》汇编及《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等,更是以经典专论的形式,旨在“探究佛教的原始法义”。(59) 经释的部分,印顺一面仿照传统论师的著论方式,对于大乘三系的圣典思想和宗义作整体的论述,而不是依文帖释。这类作品中有关大乘空宗的,如《性空学探源》、《空之探究》、《中观今论》,唯识学的有《唯识学探源》,如来藏系统的则有《如来藏之研究》等。从份量的分配上看,印顺对于般若中观一系的经论是有所倚重的。另一方面,他还择选了若干大乘经论,作具体而微的释经学研究。如《般若经讲记》、《宝积经讲记》、《胜鬘经讲记》、《药师经讲记》、《中观论颂讲记》、《摄大乘论讲记》、《大乘起信论讲记》等,就属于这类释经的作品。在这里,武院系统所判大乘三系的经论大致都有照顾到。 从格式上说,印顺经解“讲记”基本就延续并综合了六朝以来科判三分的方式,即把全经结构分为“序分”、“正宗分”和“流通分”三部来进行分疏和章句。(60)同时,他还在每一经论的“正释”前标列类似于“玄义”的“悬论”,以对该经论之经题、传译、宗要,甚至关于该经在近代学术史上之研究状况等,都略加辨明。此外,印顺对部分佛教经典,还进行了重新整理与校排,最重要的如《杂阿含经论汇编》及收录在《华雨集》(一)中的《精校敦煌本坛经》,这一类的研究,他除了重新校订经典文本,也根据自己对教义的体会来作重新排编。 印顺对经义的解释,并不因循传统义学经解,也不偏向于某一宗门的思想来作融会,而是历史化地予以阐释。他明确表示自己不作一宗一派的门徒。(61)所以他对经论中的义理疏通,就表示不能够以一家一派的思想为标准来作抉择,而更多是本着佛教史的观念来作论究。 经典是历史形成的,同时也是思想的载体。印顺提倡佛教史的研究一面从事史的考证,“以探求真实为标的”,而同时也“应重视其宗教性”。(62)具体说,史的考证只能够涉及到佛法事相的部分,而关于道体的层面,还是需要以义理来加以阐发。印顺就表示,他探究印度佛教就重在分别解说,以“确定印度经论本义,并探求其思想的演化”。(63) 他对经典义理或思想的理解与传统经学之“玄义”略有不同。他认为经典的义理阐解虽然是思想的,但是探究不能够只作哲学性的玄论,而要用历史考证来作阐明。可见义解与历史考证在印顺的解经策略中是互资为用的。印顺之治佛学重于经史,而于经论的思想,除了用史学的方法来探讨,也是重视其思想义理的论究的。他提出佛教圣典中的论藏是“基于哲理基础的”“分别经法、整理经法、抉择经法”。(64)他对于早期印度部派佛教论书的研究,就分别从论书形成史与法义两个方面加以综合论究。他自己就说其治学的方法是“从论入手”而“重于大义”,这正是宋学的方法。(65)如他在解释《起信论》时就一面主张义理不能够直接从考证历史学中引出,而必须从法的高度来进行判释,但同时又坚持“用考证方法研究佛法……这种治学方法,是不应该反对的”。(66)印顺就这样透过融经于史,来阐发佛教经典中的内在真理性。 在经教的判释方面,印顺不仅在思想上不拘于传统教史上的某一宗派,而且他对传统经学的判教方式也相当的轻视,而更倾向于用印度佛教中大乘三系这一“学派的系统”的划分,去判释诸经在佛教思想史上的位置。如他就以三系平等,义理阐明,而不是别、圆分判的方式,来判摄《起信论》在教史中的位置。他在《起信论讲记》这样说:“大乘法也有学派的差别,但分别大乘学派,要从义理去分别”。(67) 作为学问僧,印顺与太虚在经学的取径上不同,而于护教方面却有内在的一致性。与近代史家治佛典而惯于走向疑经的路向不同,印顺并不是要通过历史学的手段来对佛教圣典作怀疑论的解读,相反,他试图通过解经而把经学研究引向一种信仰的诠释方向。可以说,他的佛教经史学重在以“释古”而信古。印顺对于印度佛教圣典史作了较为详密的“推演、抉择、摄取”,从原始圣典的集成到大乘经典的流出,都作了细密的经典史探究。不难发现其重视的是经典思想源流方面的阐明,即是说,他对于经典史的研究是偏向于思想史的论究,而不是近代历史学强调的语言、文本与历史的考察。其经典史论的目的论即在于说明,从声闻经论到大乘经论,如一定要完全用历史考证的方式去说明其真实性是不可能的,印顺把这一切的流变都看作是“释尊的三业大用”,因而都具有宗教合法性的价值。(68)于是,佛教圣典是历史的,不是本质主义的,“无所谓真伪,只有了义不了义,方便与真实与否的问题”。(69)这类经学史述与经释的结合,别有意味地把圣典史的论述诠释成为佛教护教的一种策略。 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由经入史,史学一时间成为学术研究的典范。经与史、旧学与新知间的交错与紧张关系给传统的经学研究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冲击,也带来了新的视域与融合。于是,近代中国佛学的知识生产就经常游移徘徊在经与史、新知与旧学之间,而呈现出异常复杂的学术现象。传统佛学中经学独尊的局面已经成为陈迹,但经学并没有消亡。近代中国佛教知识史的重塑,大都可以从经史学的交织与复杂关系中去获得部分的体认。 中国近代佛教经学最初的缘起,与晚清以来不同类型儒家经学的复兴存在着深刻的关联。可以说,晚清以来儒家经学运动都程度不同地援用到佛教,而使佛教成为晚清思想界的一大伏流。与传统佛学不同,近代重要的佛教知识生产不再是以教界为主导,而多数都是出自于世俗的知识共同体,或有知识的居士群体中,他们大都有过出入儒家经学的经历,因此有必要从更宽广的思想史视野,尤其是近代经学史的历史流变中,去重新审查近代中国佛教知识的形成及其形态。 内院与武院是一群具有信仰为背景的佛教知识群体,他们试图在有条件地接纳新知的同时,以史论经或以史扶经,而努力在新的知识系谱中维系住佛教经学的命脉。内院与武院在佛教经史学的新知与旧传间,努力于寻求融合与平衡。在他们看来,学术不必因缘主流而兴替。对于佛教经史的研究,他们有激于身心而出的一面,故当他们转求于道问学的方式来扶翼德性的时候,一开始就为自己知识的研究设定了某种超越的价值期待。因而他们并不想为了学术而牺牲信仰,为了历史而抛弃经学。他们发现,佛教经典虽然是历史产生的,但其价值与意义并不能简单或化约论式地从史学中引出。于是,在经史学的关系方面,他们持有一种谨慎的姿态,而并不象现代主义者那样全盘接受近代西方的知识概念。 对他们来讲,经典的研究并不是恪守现代知识学所要求的那些规矩就可以了事,而是要转升到存在性的宗教期望。正如尼采(Nietzsche)所说,历史研究“是为了生活和行动”,“服从于历史的同时,恰恰是要借历史而服务于生活”。(70)正是这种要把知识与价值融贯态度,使得他们在以新知论究经典,以史论经的同时,保留住了对于经典的思想与价值的关切,这给他们的经史学研究带来更丰富的面向,同时也造就了一种深刻的紧张。 这一紧张在欧阳竟无身上表现得非常强烈和有代表性,如欧阳竟无在有关文字与经义阐解的关系上一面批判传统经学颟顸笼统,不加精严的学风,而主张治经要“异文研求”,以近代比较语言学为治经的下手处;而同时他又认为语言所涉无关道体,提出“语不足阐义,迹不足达旨”,“三世佛冤,如言取义”,(71)这样实际又取消了他在治经学上所厘定的规矩和基础。在抉择经义的方面,他也一面主张“废除科判法,以文法叙次”,并抛弃传统义学解经时“各溺其所宗而诬盖全局”的宗派主义偏见;(72)而其谨守法相为尊的经学立场,又使他于自觉不觉间,以法相之学而涵盖一切经义,“教止是谈法相”,同样陷入宗派主义的泥潭。(73) 应该这样看,内院与武院的佛教经学研究,虽然努力于融摄近代史学的方法,而终究无法摆脱经学独尊的心态,于是经常在新知与旧学、现代与传统的纠缠中游移不定。可以说,这种紧张表示了近代中国佛学研究中难以克服的宿命。 ①欧阳竟无也提到民国佛教研究与教育机构中唯有武院与内院能够秉承杨文会以来的学术传统。他在“法相大学特科开学讲演”中说:“今兹所存,惟武昌佛学院与本院,实承衹园精舍而来也”。见《欧阳竟无佛学文选》,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4页。太虚也说“唯从民国八年起,我与欧阳渐突起为佛学界的双峰”。见《太虚大师全书》第十九编文丛,《太虚自传》,第260页。 ②印顺:“游心法海六十年”三“治学以佛法为方法”,《华雨集》第五册,第33页,《印顺法师佛学著作全集》第12卷,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 ③欧阳竟无:“谈内学研究”,《欧阳竟无佛学文选》,第33页。 ④欧阳竞无:“今日之佛法研究”,《欧阳竟无佛学文选》,第30页。 ⑤参考吕澂著《杂阿含经刊定记》,《吕澂佛学论著选集》一,济南:齐鲁书社1991年版。 ⑥如太虚就批评印顺以原始佛教经典为依归,乃是“以声闻为本”,而不是“以佛陀为本”。有关太虚与印顺关于此问题的论辩,参考太虚为《印度之佛教》写的评论,及印顺的回复“敬答《议印度佛教史》”(1943年),其中印顺说他与太虚格量佛教之不同在于“其取舍之标准,不以传于中国者为是,不以盛行中国之真常论为是,而著眼于释尊之特见景行,此其所以异乎”。《无诤之辩》,台北:正闻出版社1992年版,第122,123页。 ⑦印顺:《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序,台北:正闻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 ⑧印顺:《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序,第4页。蓝吉富教授也指出,印顺教史的研究是“直接从原始佛家经论之《阿含》、《毗昙》、及印度空、有、真常三系经论去探求释迦本义,而不象旧式佛学者之但守中国古代高僧大德之注疏“。见其著”印顺法师简介“,印顺编《法海微波》,台北:正闻出版社2005年版,第326页。 ⑨印顺就说他治学博而不精,重于考证和历史演化去了解佛法,参考其著“游心法海六十年”四,《华雨集》第五册,第34页。 ⑩杨文会:“释氏学堂内班课程刍议”,见《杨仁山全集》,合肥:黄山书社2000年版,第334页。 (11)杨文会:“答释高质疑十八问”,《杨仁山全集》,第412页。 (12)杨文会:“般若波罗密多会演说二”,《杨仁山全集》,第340页。 (13)杨文会:“会刊古本《起信论义记》缘起”,《杨仁山全集》,第370页。 (14)参考夏曾佑与杨文会书,收录在“与夏穗卿书-附来书”,《杨仁山全集》,第447页。 (15)杨文会:“与夏穗卿书”,《杨仁山全集》,第448页。 (16)杨文会:“与释遐山书”,《杨仁山全集》,第429页。 (17)杨文会:“与日本南条文雄书二”,《杨仁山全集》,第319页。 (18)欧阳竟无说“内学所重在亲证也。然学者初无现证,又将如何?此惟有借现证为用之一法,所谓圣教量也”。”欧阳竟无:“谈内学研究”,《欧阳竟无佛学文选》,第31,32页。 (19)欧阳竟无:“今日之佛法研究”,《欧阳竟无佛学文选》,第30页。 (20)欧阳竟无:“法相大学特科开学讲演”,《欧阳竟无佛学文选》,第26页。 (21)吕澂在“内院佛学五科讲习纲要讲记”中说欧阳竟无治经体系为“初讲《瑜伽》,次究《般若》,后阐《涅槃》”。见《吕澂佛学论著选集》二,第585页。 (22)欧阳竟无:“支那内学院研究会开会辞”,《欧阳竟无佛学文选》,第25,26页。 (23)吕澂:“亲教师欧阳先生事略”,石峻、楼宇列等编,《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三卷、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55、356页。 (24)欧阳竟无:“覆陈伯严书”,《欧阳竟无佛学文选》,第337页。 (25)欧阳竟无:“支那内学院院训释”,《欧阳竟无佛学文选》,第144页。 (26)欧阳竟无:“得初刻南藏记”,《欧阳竟无佛学文选》,第287页。 (27)微慈(Holmes Welch)即考察了“内学院”之内学的特殊含义。关于此可以参考Holmes Welch,The Buddhist Revival in Chin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P319. (28)欧阳竟无:“支那内学院研究会开会辞”,《欧阳竟无佛学文选》,第24页。 (29)吕澂:《佛学研究法》,扬州:广陵书社2009年版,第1页。 (30)吕澂:《内院佛学五科讲习纲要讲记》,《吕澂佛学论著选集》二,第642页。 (31)吕澂:《佛学研究法》,第60页。 (32)参考吕澂:“安慧三十唯识释略抄引言”,“论奘译《观所缘释论》之特征”,《吕澂佛学论著选集》一,第145,149,51页。值得注意的是,吕澂对于传统注疏也大多采取批判的方式,而以梵藏本经义为中心来勘定旧疏得失,抉择经义。如他作“入论十四因过解”就批判传统论疏“不获传其真”,而以梵藏诸本“治学探源,无拘拘于注疏附益”。《吕澂佛学论著选集》二,第637页。 (33)吕澂:《吕澂佛学论著选集》二,第643,675页。 (34)具体论述可参考吕澂:《内院佛学五科讲习纲要讲记》,《吕澂佛学论著选集》二。 (35)详见欧阳竟无:“精刻《大藏经》缘起”,《欧阳竟无佛学文选》,第290页。 (36)欧阳竟无:“唯识抉择谈”,《欧阳竟无佛学文选》,第37页。 (37)欧阳竟无:“《大般涅槃经》叙”,《欧阳竟无佛学文选》,第256,258页。 (38)参考吕澂“《楞严》百伪”,《吕澂佛学论著选集》一,第370页。 (39)吕澂:《妙法莲华经方便品讲要》,《吕澂佛学论著选集》二,第1108,1145页。 (40)吕澂:《胜鬘夫人师子吼经讲要》,《吕澂佛学论著选集》二,第943,945页。 (41)吕澂:《内院佛学五科讲习纲要讲记》,《吕澂佛学论著选集》二,第609页。 (42)吕澂在《大乘法界无差别论讲要》中说“安宁寂静者,心之本性原自尔也。——谓觉与不觉,以心位判。非性也,《起信》、《楞严》性觉说,可知其妄”。《吕澂佛学论著选集》二,第950页。 (43)参考吕澂:“《起信》与《楞伽》”,“《大乘起信论》考证”两文,《吕澂佛学论著选集》一,第292-269页。 (44)《太虚大师全书》第十九编文丛,《太虚自传》,第189页。 (45)《太虚大师全书》第十久编,文存《序跋、外序》,第980页。 (46)《太虚大师全书》第十九编文丛,《太虚自传》,第219页。 (47)《太虚大师全书》第十九编文丛,《太虚自传》,第216页。 (48)他解释说:“五乘共教者,即人乘,天乘,声闻乘,辟支佛乘,菩萨乘所共同之教理。——此为全体佛法之大宗,其中最要者,为异熟因果的业报法,合乎此者即是佛法,违此者即非佛法,故为五乘所共之正法的法印”。见《太虚大师全书》第五编法性空慧学,《教释》,第547页。关于三乘共教,是指“声闻、辟支佛、菩萨皆由此而得解脱生死,平常称此为小乘法,其实是三乘的共法”。见《太虚大师全书》第五编法性空慧学,《教释》,第549页。 (49)特胜大乘是指即指般若经类,太虚解释说“特胜大乘者,就因缘所生法中特明究竟皆空之最胜义,遍破外小及世俗相,即诸部明甚深空义之般若经是”。见《太虚大师全书》第五编法性空慧学,《教释》,第549页。普为大乘即指“深密、华严、法华、涅盘等所说者是”。见《太虚大师全书》第五编法性空慧学,《教释》,第550页。而圆融大乘即指“中国之台、贤圆教,即从法华、华严中大发挥斯义”。见《太虚大师全书》第五编法性空慧学,《教释》,第550页。 (50)应该指出,太虚判如来藏系统为圆教,对法相一学也是融摄而重视的。有学者研究发现,他所创办的武昌佛学院早期还是重视经的,1935年之后则转向了对于法相论典的教学研究,这表示了他从作为宗教的佛教向作为哲学佛学的转向。见Holmes Welch,The Buddhist Revival in Chin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P113. (51)《太虚大师全书》第六编法相唯识学,《教释》,第465页。 (52)参考太虚:《四十二章经讲录》,《太虚大师全书》第三编三乘共学,《教释》,第6、7页。 (53)《太虚大师全书》第十六编,书评《佛学》,第28页。 (54)《太虚大师全书》第十六编,书评《佛学》,第30页。 (55)太虚:《佛学概论》,《太虚大师全书》第1册,第267页。 (56)印顺:“以佛法研究佛法”,《以佛法研究佛法》,台北:正闻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谈入世与佛学”,《无诤之辩》,台北:正闻出版社1992年版,第229,230页。 (57)《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台北:正闻出版社1983年版,第11页。有学者也认为,印顺之《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即“纯持严格治史的方法而成”。见张曼涛:“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印顺编《法海微波》,第96页。 (58)印顺:“神会与《坛经》”,《无诤之辩》,第58,59页。 (59)印顺:“《杂阿含经论汇编》序”,《杂阿含经论汇编》,《印顺法师著作全集》第20卷。 (60)学界认为,六朝时道安法师始创此三分的科判格式,关于此,参见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十五章,第550,551页。 (61)在《空之探究》“序”中,印顺说他佛学的一贯“方针”就是“不适于专宏一宗,或深入而光大某一宗的。”印顺:《空之探究》,台北:正闻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62)印顺:“游心法海六十年”三“治学以佛法为方法”,《华雨集》第五册,第33页。 (63)印顺:“游心法海六十年”一,《华雨集》第五册,第9页。 (64)印顺:《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第一章,第1-3页。 (65)印顺:“游心法海六十年”三“治学以佛法为方法”,《华雨集》第五册,第27页。 (66)《大乘起信论讲记》“悬论”,《印顺法师著作全集》第3卷,第4页。 (67)《大乘起信论讲记》“悬论”,《印顺法师著作全集》第3卷,第10页。 (68)参见印顺:“大乘是佛说论”,《以佛法研究佛法》,台北:正闻出版社1992年版,第179,188页。 (69)印顺:《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序、第十二章,第3、876页。 (70)转引自Michael Mahon,Foucault's NietzscheanGenealogy:Truth,Power,and the Subject,New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2,P95. (71)欧阳竟无:“《内学》序”,《欧阳竟无佛学文选》,第79页。 (72)欧阳竟无:“覆陈伯严书”,《欧阳竟无佛学文选》,第337页。 (73)欧阳竟无:“与章行严书”,《欧阳竟无佛学文选》,第335页。标签:佛教论文; 经学论文; 太虚大师论文; 大乘佛法论文; 中国佛教论文; 佛学论文; 传统观念论文; 读书论文; 如来藏论文; 佛法论文; 圣典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