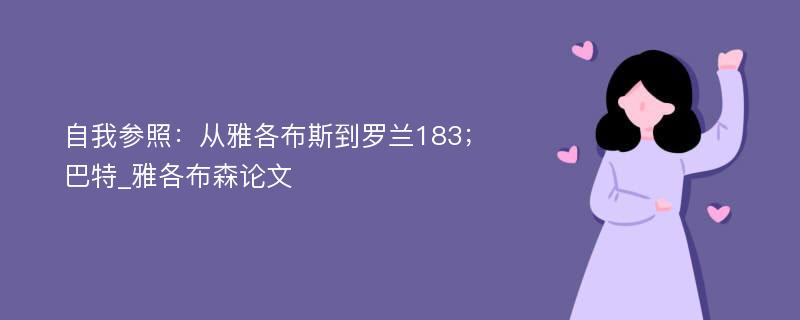
自我指涉性:从雅各布森到罗兰#183;巴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雅各布森论文,指涉论文,巴特论文,自我论文,罗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 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06)05—0073—07
“自我指涉性”(self-referentiality), 作为语言学引入文学研究而产生的一个重要概念和思想,贯穿于从俄国形式主义到法国结构主义乃至后结构主义的历史过程,在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思想建构和学术转变中皆有十分复杂而深刻的意义。当然,相对于后者的庞大实体而言,它只是露出水面的一个小小的冰山尖顶,但在它的内部和周围,却汇聚着一些极为重要的观念、思潮及其运动的线索,由此出发,可望探得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某些根本性的思想倾向。有鉴于此,本文将沿着从罗曼·雅各布森到罗兰·巴特的线索,梳理这一思想的萌芽及发展的历史脉络,并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中考察其来龙去脉。
一
“自我指涉性”这一概念通常有几种不同的语词表达形式。例如,在詹姆逊的《语言的牢笼》一书之中,就使用了self-referential、autodesignation和autoreferential等几种说法,而在霍克斯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中,也同样有self-reference、autoreferential等不同的名称。这一命名上的摇摆不定,很容易让人忽略其潜在的一致性及其重要意义。 后来,它采用了self-referentiality① 这个较为固定的说法,并在后现代小说的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② 综观之下,我们可以将20世纪70年代看作“自我指涉性”的命名阶段,而此前,这一思想却早已酝酿了半个世纪之久。
罗曼·雅各布森于1958年发表的著名演讲《语言学与诗学》在许多方面影响深远,广为征引。关于文学自我指涉性的论述,最早即见于该文。文中区分了语言的“诗的功能”(poetic function)与“指称功能”③(referential function),认为“诗的功能”即“朝向信息本身的倾向,因为信息④ 自身的原因而聚焦于它”。(Jakobson,1987:69)文学语言这种将读者注意力指向(refer to)文学自身(self)的特性,即被后来的学者追认为文学的“自我指涉性”(self-referentiality),或简称为“自指性”。⑤
雅各布森此处的分析,无异于在“自我指涉性”与“诗的功能”之间划上了等号,而“诗的功能”和“指称功能”之区分,又是出于界定文学性的需要。⑥ 可见,自我指涉性的思想源出于对文学性问题的探索。而文学性这一问题又是俄国形式主义的中心课题之一,“整个形式主义的所有理论宣称都直接或间接地解决文学性的问题”,(Erlich:172)于是俄国形式主义时期就是“自我指涉性”概念得以产生的第一个重要环节。当雅各布森在20年代初将“文学性”定义为诗歌语言对日常语言“有组织的变形”(Eichenbaum:127)时,就暗含着上述两种功能的区分,同时也就隐含着“自我指涉性”思想的萌芽了。此后,从20年代初到这篇演讲发表的1958年这近四十年时间里,“文学性”问题一直贯穿于雅各布森的理论探索,自我指涉性思想也就一直同步地隐含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之中。⑦
分析起来,“自我指涉性”思想又包含着两个基本要点,其一是“将注意力吸引到文学自身”,其二是所谓“更新意识的功能”。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所谓“信息自身的原因”或诗歌语言“有组织的变形”究竟指的是什么?或者说,自我指涉是如何实现的?关于这个问题,雅各布森的回答是:“诗性表现在哪里?表现在词使人感觉到它作为词而存在,而不是作为所指物的表示或情绪的爆发而存在。表现在词、词的组合、词义及其外部和内部形式自身获得分量和价值,而不是直接指涉外部现实。”(Jakobson,1976:174)词有两种用法,一种是指称用法,也就是“作为所指物的表示或情绪的爆发”而存在;一种是诗的用法,也就是词“自身获得分量和价值”。而“诗性”,也就是文学性,就表现在诗的用法中。比如诗歌的节奏构成一种重复,而重复的倾向“特别引起雅各布森的注意”。(托多洛夫,2004:381)重复就是语言自身获得分量,吸引注意的一种方式。再比如我们熟悉的一句诗,“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海子:236)其诗性就表现在不寻常的“词的组合”中。“温暖”和“名字”的反常组合,使得我们不得不注意到它作为表达的存在,并进而思考为什么要采用这种特殊的表达方式。语言的特殊用法,构成一种近乎强制性的力量,将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表达方式自身。对此,雅各布森还从符号学角度加以说明:“除了将符号等同于客体(A即A1)的第一感觉,我们还必须敏锐地意识到这种看法之不足(A非A1)”。(Jakobson,1976:175)“符号等同于客体(A即A1)”,说的是语言符号的指称用法,而“这种看法之不足(A非A1)”, 说的是指称用法之外的诗的用法。由此不难看出,这和《结束语》中的区分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在指称用法中,符号等于客体,人们的注意力会越过符号直接达到它的所指。因此,符号为了吸引注意,就必须防止这种倾向的发生,其方法就是“诗的用法”,诗歌语言“有组织的变形”。
既然诗的用法“将注意力吸引到文学自身”,那么其目的是否仅仅为了使表达形式成为关注的焦点呢?文学还指涉外部现实吗?这就引出自我指涉性的第二个要点:自我指涉性的功能不止于吸引读者的注意力,而是进一步地导致文学“更新意识的功能”。这一点虽然在“自我指涉性”术语本身没有体现,但仍然是内在于这个概念之中的。两个要点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第二个要点可以看作是第一个要点的自然延伸:将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文学自身,目的是什么?
其实上面的分析已经触及到这个问题了。特殊的语言用法很自然甚至是必然地引导我们思考,为什么会这样?关于符号与客体的对立,雅各布森认为:“如果没有这种对立,概念(concept)就会一成不变,符号(sign)就会一成不变,概念(concept)和符号(sign)⑧ 之间的联系也就会变得自动化(automatized)。 就不再有人的活动,不再有对现实的意识。”(Jakobson,1976:175)联系上面的分析,这种“对立”的意思是诗歌用法中符号首先将注意力指向自身,而不是直接指向客体,因而指称用法中的同一关系(A即A1)遭到了破坏,符号与所指之间似乎“对立”起来。这样,从表面上看,雅各布森似乎有因自我指涉性而否定指涉维度之嫌。⑨ 但是实际说来,他反对的是建立在指称用法基础上的直接指涉,而不是指涉现实的维度。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对抗“自动化”,进而更新人们“对现实的意识”,因为在指称用法中,符号与客体的联系是自动化的,无须反思的,这将导致意识的自动化。而在诗的用法中,符号不直接指涉外部现实,而是将注意力停留于自身、经过反思后取得指涉现实的维度。正是自我指涉引起的这一反思,导致其更新意识的功能。不难看出,这正是什克洛夫斯基所阐述的“陌生化”思想:“艺术的手法是将事物‘奇异化’的手法,是把形式艰深化,从而增加感受的难度和时间的手法,因为在艺术中感受过程本身就是目的,应该使之延长。”(Shklovsky:12)“自动化”(automatic/habitulization)吞噬了我们对生活应有的感觉。 艺术的陌生化则“恢复我们对生活的感觉”。(Shklovsky:12)在这里,什克洛夫斯基对读者一方的感受过程描述得更为详细,可作为雅各布森的补充。在自我指涉性导致的这种间接指涉中,文学不是对现实的直接描绘,而是提出关于现实的新观点,这也启发我们超越传统上文学—现实的“模仿指涉”关系。
上面我们提到,自我指涉性思想发源于俄国形式主义,而其进一步发展,是在布拉格学派时期。在这一阶段,雅各布森和他的同事们引入了符号学的概念,试图用符号和客体的关系来更准确地界定文学性,而不像俄国形式主义时期那样笼统地界定为“有组织的变形”,这可以从上文所引雅各布森对符号与客体关系的阐述中见出。而且这不仅是雅各布森一个人的观点,也是贯穿于整个学派的发展线索。比如布拉格学派的穆卡洛夫斯基就认为:“正是这种对标准语言准则的违反,这种有系统的违反,使诗歌式地使用语言成为可能”,(Mukarovsky,1964:18)“在诗歌中,语言的实际功能……较之美学功能退居其次,这时符号本身成为注意力的中心”。(Mukarovsky,1976:162)显而易见,这与雅各布森的观点极为相近,也反映出该学派的共同倾向。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以俄国形式主义为最初的萌芽期,中经布拉格学派的过渡,而成熟于法国结构主义,自我指涉性成为20世纪上半叶西方文学思想中暗含的一个重要概念。而雅各布森正是其中的穿线式人物。
二
对于巴特而言,“自我指涉性”有两种意义,其一是他作为批评家所实践的,以批评的眼光所见出的自我指涉性。其二是他作为批评家提倡的文学创作的自我指涉性,集中体现于布莱希特和格里耶两位作家的创作之中。这两种自我指涉性吸引注意力的方式各不相同,但其共同特点是,“自我”指的不是文学的语言层面,而是超语言层的文学程式,这与雅各布森形成鲜明的对比。
和雅各布森一样,巴特也是在对比之中突出文学的“自我指涉性”的。在巴特的理论中,这个观点就是“二重性”(duplicity):文学既是通往内容的手段,同时又作为自身而存在。这一思想最早出现在《写作的零度》(1953)中,写作是二重的:“我一边向前走,一边指着自己的面具。”(Barthes,1968:40)也就是说,既要看到写作的内容,又要看到写作本身。巴特用拟人的方式所表达的这一思想,詹姆逊作为阐释者倒是说得更明白。在他看来,这种二重性是“巴特整个理论的基础”,(Jameson:198)并分别在符号和文学整体两个层面上阐发了这一思想:“符号既有某种意思又指向其作为符号的自身存在”;(Jameson:198)“每一部文学作品除了其自身特定的内容外,也说明整个文学的情况”。(Jameson:155)
不过在巴特看来,“二重”的地位并不相当。他提出这个区分,正是为了反对把文学看作通往内容的手段,而提倡“文学作为自身的存在”这一重。他说,写作“其作用不再只是去交流或表达,而是强加上了某种语言之外的东西,它既是历史,又是我们在历史中采取的立场”。(Barthes,1968:1)为了强调这层意思,他不惜出以极端之辞:“写作绝不是交流的工具。”(Barthes,1968:19)这一思想也可以在他的其他论述中见到,例如在《文学与元语言》(1959)中他就说,文学是“指向自身的面具”。(Barthes,1972:98)用的还是“面具”这个比喻,但明显是在突出“自身”这一重。
“二重性”的思想表明了巴特对雅各布森的继承。对此,霍克斯指出:“很明显,巴特在某种程度上吸取了俄国形式学派的原则,特别是吸取了雅各布森对语言的‘指称’功能和‘美学’功能所作的区分。”(Hawkes:91)雅各布森反对的是只有语言的指称用法,只把语言当作通向所指的工具;巴特反对的是只把文学看作通往内容的手段。二者都要求将注意力转向文学作为自身的存在,不同之处在于对前者而言“自身”是文学语言,后者是超语言层面的文学程式。
巴特强调文学作为自身的存在,集中体现在他对现实主义写作不透明性的揭露。一直以来,现实主义写作被人们认定是对现实的透明再现,这种“形式的透明性”既是作者的追求,也是读者的信念。作为创作的诉求,出现了以加缪为代表的所谓“中性写作”(neutral writing),一种“对最终可能达到‘天真’(innocence)状态的写作模式的追求”。(Barthes,1968:67)对这种以“天真”为目标的中性写作,巴特(以加缪的《局外人》为例)说“没有什么比白色写作⑩ 更不真实了”。(Barthes,1968:78)资产阶级将这种写作标榜为“自然的”、“天真的”,“巴特将这种天真的假定看作是资产阶级特有的堕落”。他认为:“现实主义写作远非中性,恰恰相反,其中充满了最蔚为大观的编造的迹象。”(Barthes,1968:67—8)而这正“暴露了资产阶级最后的历史野心,即急于把人类的全部经验都纳入自己对世界的特定看法之中,并把这标榜为‘自然的’和‘标准的’”。对于读者来说,“响应这种写作就是接受那些价值,就是证实并进一步论证那种生活方式的本质”。因此,要想抵抗这种影响,就要揭露“天真”背后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这正是文学批评的任务。这种批评活动后来被巴特称为“去神秘化”(demystifying)。在此后的1957年出版的《神话学》(Mythologies)中,他进一步将这种意识形态的批判锋芒扩展到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的领域。正如霍克斯所评价的:“巴特的全部著作可以看作对‘天真无邪’(innocent)这一假定的攻击”。(Hawkes:86—8)
巴特将批评的目光指向文学本身,揭示了文学程式隐而不彰的意识形态含义,打破了写作的自然的、天真的、透明的幻觉,让我们批判地看待文学程式以及文学中所描绘的现实,这可以说是它更新意识的功能。巴特将这种去神秘化活动看作“一位知识分子采取政治行动的唯一有效方式”。(卡勒,1988:40)但是是否真的有效呢?对现实主义作品的意识形态揭露确有启发作用,但是对当代文化的去神秘化却未必。卡勒一针见血地指出,其结果不过是“使自己成为自己所攻击的对象的同谋”。(卡勒,1988:38)
对雅各布森而言,“将注意力吸引到文学自身”是通过语言的特殊用法实现的,是文学作品本身对阅读作出的一种规定,而在巴特这里却表现为一种批评的眼光。同样是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此前人们看到的是它的内容,是透明的文学媒介,而巴特不仅把文学看成是反映外部世界的,而且更重要地看成指向自身的、指向其意义生成的机制。这样便深入到了文学的不透明性及其意识形态根源。这是巴特批评活动的独到之处。
巴特作为批评家,对同时代文学创作中所体现出来的自我指涉性非常赞赏,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戏剧家布莱希特和小说家罗伯特—格里耶。他们在创作中意识到了文学程式的存在,并通过运用不同的意义机制对其进行挑战,从而对文学和与之相连的哲学基础提出了质疑。卡勒说:“文学已经不再被人们看作是一个作家用自然的表达工具得出的表达形式:文学成了人们胜过约定的传统的一种反意的创作方法。”(卡勒,1983:39)这非常适合这两位作家。他们赖以传达意义的手段,不再仅仅是语言的意义——所谓“自然的表达工具”,而是将超语言的文学程式作为一种能指,来传达相应的意识形态所指。
正如詹姆逊所指出:“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从字面意义上正是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Jameson:58)二者的含义也是相通的,只是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主要发生在文学程式的层次上,其更新意识的功能主要体现在文学程式的意识形态批判力量。巴特在评论时说布莱希特“摈弃所有导致逼真的风格”。(Barthes,1972:35)逼真是传统的意义机制,“间离效果”就是对这一传统程式的挑战。布莱希特的戏剧阻止观众与人物的共鸣,观众为了理解戏剧,就必须在一定的距离之外,反思其艺术手法。在反思中,逼真这一文学程式将在与“间离效果”的对比中遭到质疑,进而这种质疑也将扩展至戏剧所讲的故事。所以,“布莱希特的形式主义是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错误的‘自然’观(11) 做出的一种激烈反叛。在一个隔膜的社会,艺术必须是批判性的,必须消除各种幻象,即使是‘自然’的幻象”。(Barthes,1972:75)反叛的矛头指向文学的“自然观”,以及与之相连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反叛的途径,就是通过意义程式的“陌生化”,以突出的特点引起观众的注意,从而达到更新意识的目的。而其更新意识的对象,既包括文学程式本身,也延及文学所讲之事。
法国新小说派的代表作家罗伯特—格里耶,也是通过挑战传统的文学程式来对抗与之联系在一起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其矛头所指,是现实主义写作中赋予文学以固定的意义这一程式。甚至追求意义本身都是需要抵制的倾向,格里耶认为,要警惕“形而上的危险”,也就是警惕赋予作品以意义这一程式。其实格里耶反对的不仅仅是意义程式,更深刻的是反对这种程式背后的世界观。在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中,“精确丰富的描写”使得小说看起来构成一个“稳定的世界”,“这个世界确保其中的事件和人物活动的真实可靠”。(Herman:155—6)资产阶级通过赋予文学作品以固定的意义,暗示这个世界有着固定而清晰的秩序,读者则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受到这一思想的控制。而作家则有义务以迥异于传统甚至是惊世骇俗的写作方式来吸引人们注意,告诉人们现实不是那样的。格里耶的小说,如《橡皮》和《嫉妒》,正是以不寻常的人物塑造技巧和清晰情节的缺失写成。看上去很难抽象出一个固定的意义,而这正是作者的用意。这样的反常手法迫使读者反思,现实主义文学所描绘的秩序井然的世界其实是作者所为,并进一步看到这样做背后的意识形态动机。格里耶将小说看作“探索新的现实的工具”,对现实主义文学程式以及与之相连的世界观提出了挑战。巴特说:“这种活动(12) 是真正革命性的, 因为拒绝固定意义,归根结底就是拒绝上帝和其同体物——理性、科学、法则。”(卡勒,1988:92)这种精神贯穿于巴特的批评中和布莱希特、格里耶的创作中。
比较而言,在雅各布森那里,自我指涉性暗含的更新意识的功能,针对的是人们对于文学作品所谈之事。而在巴特这里,则主要针对文学世界之隐蔽构造机制,针对与现实主义幻觉相关的那些文学程式的意识形态含义。文学程式在它的差别系统中获得意义,就像词在语言系统中获得意义。在讨论雅各布森的观点时,我们说更新意识的功能意味着文学提出关于现实的新观点,文学与现实之间是一种间接指涉的关系。在巴特这里,由于更新意识的功能主要针对的不是文学所讲之事,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方面。也正因此,其批判的锋芒也更见锐利。
三
置之于西方文学思潮发展演变的历史脉络之中,我们可以看到,“自我指涉性”思想的出现实在并非偶然。就雅各布森的“自我指涉性”的两个要点而言,皆明显地植根于两个背景之中,一是“向内转”的理论倾向,二是在向外指涉中获得重要性的诉求。而这两者,归根结底又都是“身份危机”的产物。
“向内转”的倾向,始于18世纪末德国浪漫主义以降对文学本身的关注。在19世纪的唯美主义、象征主义的宣言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思想倾向。比如,戈蒂耶在唯美主义的纲领《莫班小姐·序言》中认为艺术与政治无关,也与一切实用的功利目的无关。这是针对当时将文学看作政治和道德的工具的观点提出的。而文学沦为外在目的的工具,就是我们所说的“身份危机”。正是意识到这种危机,才有了“为艺术而艺术”这样的口号。象征主义的旗手马拉美和瓦雷里认识到了日常语言和诗歌语言的分别,并借此区别来确立诗歌之所以为诗歌的特性。这一思想明显启发了雅各布森对文学性的探索。瓦雷里明白地提倡“使诗摆脱功利性、实指性和目的性,成为脱离外在世界的自足的审美艺术形式”,(马新国:330)这就是著名的纯诗论。为了争取文学独立的身份,出现了上述从摆脱外在的目的,到摆脱“实指性”的吁求,其结果必然是将目光转向文学自身。
把文学看成文学自身,而不是外在目的工具,这一“向内转”的倾向从德国浪漫主义经象征主义一直延续到雅各布森,托多洛夫发现了这条影响之链:
诺瓦利斯和马拉美这两个名字的确在雅各布森最初的作品里就已经出现了。而后一个来源又出自前一个,尽管这种联系是间接的:马拉美生在波德莱尔之后,后者十分欣赏爱伦·坡,而坡又大量阅读过柯尔律治的作品,后者的理论著作又概述了德国浪漫派,因而也是诺瓦利斯的学说……在雅各布森关于诗歌的定义中我们的确可以毫不费力地发现诺瓦利斯和他的朋友们在《独白》和其他断片里提出的不及物性这种浪漫主义思想。是诺瓦利斯,而不是雅各布森把诗歌说成是“为了表达的表达”。(托多洛夫,2004:374)按照时间的顺序,这条线索就是:诺瓦利斯——柯尔律治——爱伦·坡——波德莱尔——马拉美——雅各布森。
与此同时,人们对语言的认识也出现了注重语言本身,而不是作为表达工具的倾向。 如巴特说的, “自从18 世纪末, 语言……自身获得了一种重量”。(Barthes,1968:3)这种潜流在俄国形式主义这里彰显为一种重要的观点,什克洛夫斯基说:“词不是(客体的)影子,而是事物。”(Erlich:184)厄立克在《俄国形式主义》这本书中也多次用“自我价值”(self-valu-able)来表示这一观点。词作为自身而不是客体的影子,文学作为自身而不是外在目的的工具,这两者之间显然是相通的,它们在俄国形式主义者尤其是深受语言学影响的雅各布森这里形成合力,在寻求文学独立身份的动机下,促成了对自我指涉性的最初认识。
“向内转”的倾向到了雅各布森所代表的俄国形式主义阶段,发生了一个重大转折。在上述19世纪各家的宣言中,只是要求我们看到文学作为自身的存在,不要把它看作外在目的的工具。而从俄国形式主义开始,不再止于让大家注意到文学自身的形式方面,而且还要注意到形式引发的意义。这也就是自我指涉性的第二个要点:更新意识的功能。
对于雅各布森和巴特来说,文学在具有自我指涉性的同时,都具有这一功能。对雅各布森而言,文学语言将注意力吸引到文学自身,为的是让人们注意到特殊的语言用法所表示的对现实的新看法。对于巴特和他赞赏的作家来说,文学程式吸引注意,为的是引导人们看到它的意识形态含义。这种向外指涉的倾向,其根源其实和“向内转”是一样的。身份危机的焦虑当初表现为“为艺术而艺术”这样凌然不可侵犯的声音,其结果不仅没有实现争取独立身份的预期目的,“反而削弱了艺术的哲学和社会权威,使得艺术本来就处于边缘的社会地位合理化了”。(13) (徐秋红:5)艺术的孤傲最终走向孤芳自赏和孤立无援,这必然导致身份危机的另一种表达:向外指涉。艺术的重要性,需要由它对现实发表看法获得。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从俄国形式主义开始就有的,与自我指涉性伴随的更新意识的功能。艺术回归价值关怀,这也是托多洛夫在《批评的批评》(Critique de la Critique,1984)中表达的主要思想。作为罗兰·巴特的学生和结构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托多洛夫由关注作品本身、关注形式方面转而拥抱真理与价值,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在身份危机的焦虑中,我们看到有“向内转”和“向外指涉”两种声音,或者说两种出路。自我指涉性正是这两种声音交织的集中体现。它一方面是19世纪“向内转”的发展,一方面又可以看作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向外指涉”倾向的前奏。而在此之间,正如本文谈到的,从俄国形式主义到法国结构主义,以雅各布森和巴特为代表的理论,是两种声音交织的集中体现。
强调自我指涉性,难免给人以形式主义的错觉,似乎视野之内只有文学本身,没有向外指涉的维度。但是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看到其实从俄国形式主义开始,自我指涉性所展现给我们的,并不否定文学指涉外部世界,只是否定了单一的模仿指涉模式,却隐含着另外一种指涉模式。自我指涉性不是孤立存在的,或者说一直没有脱离过“指涉性”这一维度。也只有在指涉性的框架下看待自我指涉性,才会看到它特定的针对性,才会免于偏执。前面我们提到,自我指涉性的问题一直到后现代小说研究中,都是很关键的一个概念。其中自我指涉和向外指涉的关系,仍然是很重要的问题。而本文所关注的,是自我指涉性在萌芽和发展阶段的含义及相关问题,并试图在更大的背景中观照其来龙去脉。至于70年代的命名阶段以及80年代以后的应用阶段,则需另做探讨。
注释:
① 相应地有形容词形式self-referential,名词形式self-reference。
② 比如在下列文献中:Richard Todd,The Presence of Postmodernism in British Fiction:Aspects of Style and Selfhood in Douwe Fokkema and Hans Bertens,eds.Approaching Postmodernism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1986).Linda Hutcheon,A Poetics of Postmodernism (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1988).Mark Currie,Postmodern Narratology (New York:st.Martin.Hs Press Inc.,1998).
③ 一般来说,在语言学中,译作“指称”,在文学研究中,则多作“指涉”,在英文中是同一个词。
④ 需要说明的是,雅各布森的用语不同于通常的用法。“信息”在此相当于“能指”,不应误解为“内容”或“所指”。赵毅衡《文学符号学》第47页即作此解。
⑤ 赵毅衡《文学符号学》第49页用的是self-reflexity,可视为self-referentiality的另一种说法,意思相同。
⑥ 在《主导》(1935)中,雅各布森说“诗歌就是美学功能占主导地位的语言信息”。(Jakobson,1987:43)在《语言学与诗学》(1958)中,他说“诗的功能……是语言艺术主导的、决定性的功能”。(Jakobson,1987:69)其中“美学功能”和“诗的功能”意思相同。
⑦ 对这一过程的梳理可参见托多洛夫《象征理论》第372页。
⑧ 上文中说“符号”与“客体”,这里说“符号”与“概念”,可见雅各布森在“客体”与“概念”之间没有做严格区分。这和索绪尔以符号的二分法(“能指”和“所指”)取代三分法(“符号”、“概念”、“所指物”)的影响有关。
⑨ 又如在《结束语》中,他谈到诗的功能时说“这种功能通过提高符号的可触知性,加深了符号与客体的分裂”。
⑩ 在此书中,“白色写作”、“中性写作”、“写作的零度”,为同义语。此处参考李幼蒸译文。
(11) 所谓“自然”,意即上文中现实主义文学模式中认定的文学是对现实的自然的、没有掺入偏见的再现。
(12) 指文学。
(13) 见徐秋红为《自我作对的文学》所作的译序:《对先锋思潮的透彻关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