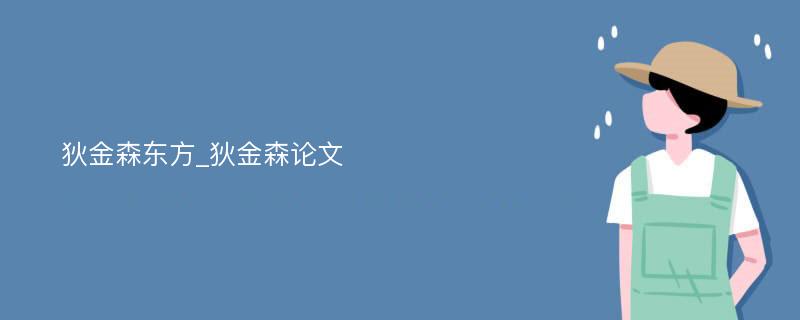
狄金森的东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狄金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12)05-0033-07
在西方作家与东方关系的研究方面,萨义德(Edward Said)的经典著作《东方主义》能给我们提供有益的启示。萨义德聚焦于19世纪以降英、法、美对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东方学研究,指出西方通过建构堕落、低劣的东方,来标榜其智力的高超与品德的高贵。这种东方主义是西方试图征服、压迫、控制东方的产物,体现了狭隘与霸道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萨义德的观点产生了广泛影响,也引起不少批评和争议。波特(Dennis Porter)指出,萨义德把西方的文化霸权本质化、绝对化,无视西方文化中各种形式的反霸权思想与声音。(153)希尔克(Sabine Sielke)在2009年出版的论文集《美国诗歌与诗学中的东方及东方主义》的序言中特别强调,该论文集所考察的美国诗人并未拘泥于萨义德所说的“西方优越、东方低劣”的态度,而是采取了“含混”立场。(13)
美国诗人狄金森(Emily Dickinson)的文本①展现了西方文化多条脉络关于东方的观念和视角,以及多种东方态势的角逐。对此,狄金森研究界已有零星探讨。尽管希尔克编辑的论文集无专文论述,编者在序言的开端特别提到这位自称本土视角、却又禅味盎然的隐居诗人,指出她对印度意象的挪用体现了“对东方的文化迷恋”,而这恰恰是美国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诗歌的推动力。(9—11)米勒(Cristanne Miller)在今年出版的专著中有一章讨论狄金森对东方意象的挪用在她创作生涯中的变化,这是研究界对这一问题的重要创获。本文全面考察狄金森的东方想象与东方对她的意义,重点放在学界忽视的问题、或者有争议的个案,包括她的伊斯兰想象、对马来人的文化书写,揭示她对东方的挪用与清教传统的关联、她对殖民主义话语系统的个性化改写,并探究她思想内涵的东方特质与美国超验主义的隐性联系。
阅读狄金森的诗文,可以发现东方是她生活中的真实存在,其中涉及传教活动、商业往来、文化旅行以及战争等。她曾在十六岁时参观过波斯顿的中国博物馆;她将小表妹伪称为“东印度的朋友”;有朋友拟来“上海”(其实是去叙利亚)作牧师,要“向异教冲刺”;她的挚友杰克逊(Helen Hunt Jackson)远赴日本;当地教堂为远东国家的孩子举办义卖,有从阿尔及利亚来的马戏团表演。她说花园里有“亚洲的花”以及不服水土的“东方品种”。她在诗中提到过“青花瓷”、“武夷茶”、美轮美奂的“克什米尔的布料”、“东方布料”等东方物品。狄金森在晚年的一封信中曾说“东方在西方”,(978)寥寥数语勾画了“东方”渗透入美国社会的现实与想象的文化景观。尽管如此,狄金森了解、想象东方的方式并不是依托身临其境的经验,而是通过语言文本来实现。她屡屡提及《天方夜谭》。她的阅读范围涵盖《圣经》、莎士比亚、笛福、约翰逊、德昆西、济慈、狄更斯、勃朗特姐妹、勃朗宁夫妇、艾略特、丁尼生、朗费罗、霍桑、詹姆斯、爱默生、梭罗、俄国作家屠格涅夫以及当时的期刊杂志等。这些文本都不乏对东方的想象、描述与建构,都可能滋养了她对东方的想象。其中期刊杂志不时报道现实的东方,让她知晓东方的事态,如1877-1878年的土俄战争(Russo-Turkish War)、艾哈迈德·阿拉比(Ahmed Arabi)1882年被捕事件,以及戈登(General Gordon)1884年在埃及的危险处境等。
在狄金森的世界地图里,地球的另一边是亚洲,从她的家乡艾默斯特到克什米尔,是最广阔的疆域。关于非洲,她提到过埃及、撒哈拉沙漠、通布图(Timbuctoo)、苏丹、埃塞俄比亚、突尼斯、利比亚等。亚欧大陆的临界地,她提及地中海、红海、里海、博斯普鲁斯海峡,并向东延伸至第聂伯河、顿河、亚述海、亚洲东北部的堪察加半岛等地。关于亚洲,她提到过印度、锡兰、香料群岛(Spicy Island)、克什米尔、喜马拉雅山、缅甸等地。她也提过有世界尽头之称的范迪门地(Van Dieman’s Land),也就是澳大利亚南面的塔斯曼尼亚,真可谓无远弗届。遥远的东方常代表美丽、富有、丰富与异国情调等。例如,“东方集市”的颜色最美,(696)克什米尔是对应“受难地”的人间天堂。(749)“(东)印度”等词汇取其富庶,但狄金森把它们应用于精神层面,表示心灵的富有与喜悦,诸如:“看着你一/就是印度”;(418)拥有一点爱情也胜过“印度”;(1509)“缅甸的辉煌”既代表黄莺之乐,也表达了观鸟者的心醉神迷。(1488)
阿拉伯、伊斯兰是狄金森想象东方的突出焦点。米勒指出《天方夜谭》对她的影响巨大,她许多涉及转变、变形的诗篇都与这些她觉得“不可思议”的“东方故事”有关。(136—38)例如:表达灵感丧失,狄金森挪用《神灯》中阿拉丁偶获意外之财的狂喜,以及由于巫师作怪又顷刻之间重归赤贫这一情节。对狄金森的影响同样深远的还有《天方夜谭》在西方文化中的衍生文本。狄金森两次在信中提及郎费罗诗中阿拉伯人叠起帐篷悄然离去的意象,并把它嵌入激情的马戏表演之后清场离去的空明之境。(257)霍桑描绘过一幅阿拉伯风景图:沙漠如海,一列商队在烈日下骑着骆驼跋涉。(549)狄金森则借助“红色的商队”描述夕阳,用沙漠驼铃表达风的空灵之乐,以穿越沙漠象征精神历练,盛赞骆驼的韧性与节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阿拉伯人的形象。约翰逊(Samuel Johnson)在其东方故事中说阿拉伯人既“和平”又“好斗”,他们“居无定所”,“全部的财富在其牲口”,“然而绝不觊觎他人财产”。(20)梭罗赞誉身居帐篷、四处流浪的阿拉伯人的“简朴”,甚至称他们能实现“最伟大的真正的跳跃”。(352—53)刚柔相济的阿拉伯形象是狄金森塑造理想人格的重要原型,如鹪鹩兼具“孩童”与“女英雄”的气质、松鸦既有邻居的亲切又有“武士”精神等。
千娇百媚的“土耳其后宫”(seraglio)或者“伊斯兰的妻妾群”(harem)是西方读者想象东方的重要场所。狄金森的伊斯兰想象也聚焦于这女人的花园。她使用“苏丹”(Sultan)、“元老”(Viziers)、还有“伊朗王”(Shah)等意象描述她的花朵,表达柔弱之强。1861年的一封信,体现了她对安适享乐的土耳其花园的最集中的想象。她声称愿“如土耳其人用背心抓蝴蝶”,称比邻而居的哥哥住在“东方”,并用深锁闺中的“苏丹女眷”(Sultana)静候恩宠的模式,描述花鸟交会,进而描摹自己的幻想与心境:“我有一株美如苏丹女眷的天竺葵—当蜂鸟来时,我和天竺葵闭眼一神游。”(235)佐纳纳(Joyce Zonana)指出在许多19世纪的西方文学作品中,东方主义和女性主义缠结在一起,通过批判伊斯兰后宫对女性的禁闭与压制,重新确认西方的自由与优越。例如,约翰逊在他的东方故事中抱怨东方后宫女人极其空虚无聊,只能从事“孩子气的游戏”;(77)简·爱(狄金森非常喜爱的小说女主人公)挑战罗切斯特以苏丹自居,扬言要向众女眷宣讲自由。(271)我们可以发现,与这些文本不同,狄金森采取的是非政治化视角,她强调内在的力量超越外界的拘禁,认为徜徉于自然中就能获得此处的天堂,即便身处这代表囚禁的东方后宫,也无碍心灵的自由与飞升。她甚至认为面纱隔离“侵扰的眼睛”,(1437)具有“欲露还藏”的“魅力”,(430)在信中坦承“需要更多的面纱”。(107)
狄金森以肯定的方式挪用东方意象,赋予其意义,如果要探究其深层的文化动因,还应当联系她对清教的批判与反思。这一点类似狄金森同时代的其他美国作家与作品,如霍桑的《红字》与詹姆斯的《欧洲人》等。《欧洲人》中的格特鲁特·温特伍斯厌恶清教的沉闷,拒绝去教堂,在花园里痴读《天方夜谭》,把活力四射的菲力克斯视为从天而降的阿拉伯王子。(25)狄金森也抱怨“清教花园”的禁锢,推崇“异教”的“快乐”,常以异教徒自居,并向真主安拉祈祷。诗141把欣然去死表述成“快乐的土耳其人/眠入群芳的卧床”。阿拉伯、土耳其所代表的伊斯兰与古老的非洲重合,表达激情、放达的人生姿态,对抗清教的严苛:鲍尔斯(Samuel Bowles)的“阿拉伯式的存在”来自“努米底亚之乡”;匍匐在三叶草上的蝴蝶身着“努米底亚的袍”。(1395)她推举“非洲的激越”与“亚洲的休憩”,(1563)犹如波德莱尔在《恶之花》中向往“倦怠的亚洲”与“激情的非洲”。(23)
狄金森一方面抱怨清教的严苛阴冷遏制了生命的勃发,同时也坚信清教的节制冷峻具有激活、安顿生命的力量。当她从这一角度理解、张扬清教精神时,她常常挪用以后宫为象征的女性化、羸弱的东方这一否定性的东方话语与之对峙。狄金森曾在信中说:“戴披肩的‘苏丹’是地球上的变态”。(655)这种挪用就如梭罗讽刺“后宫的娘娘以及天国娘娘气的臣民”沉醉于奢侈品;(352)这也如惠特曼批评某些诗人犹如“闺房中的娘娘”,关在香气逼人的房间唱着“熏香的思想”,不能谱写“健康、振奋、简朴的曲调”。(1022)狄金森的态势更为暧昧不明的是,她把对清教的肯定也借助东方意象予以表达,因而很难说她在宣扬西方优越论。例如,她常以“雪”象征清教精神,诗400歌咏铁杉傲立白雪的“冷峻”(Austerity),鄙夷地提及奢侈浮华、精神萎靡的“锦衣种族”(satin Races),以此对照茁壮的“顿河上的儿童”与“第涅伯河上的格斗师”。同样,她推崇“吉普赛人”实现生命潜能的坚毅,不若东方闺房中“缎子”、“银子”、“玫瑰红”的娇弱不堪。(131)狄金森最有否定东方主义嫌疑的举措是她对“东方异教”(Oriental heresies)这一概念的挪用。诗1562中,蜜蜂经历“东方异教”后筋疲力尽,匍匐于“平常”的三叶草,清教的理性与节制获胜。该诗移植了《简·爱》中英国式的冷静击败东方的狂野,从而沾染其中的否定性的、东方主义的遗毒,但其主旨不在于对东西方做出价值判断,而是探索欣赏平凡的条件。(康燕彬:52—54)
狄金森对殖民主义的东方话语的批判性改写,是她的东方态势的重要层面。如果“走向印度”蕴藏了西方征服东方的欲望和扩张野心,狄金森主张内在的超越,有效地消解了向外扩张的驱动。她在信中称门前每棵树都是印度一景、手持的鲜花为手中的印度,或曰通往印度的航道。她颠覆了鲁滨逊的殖民主义探险英雄的形象,把不能享受此地之乐、依靠投向远方驱散空虚无聊的众生喻之为“可怜的鲁滨逊”。(685)在西方19世纪的世界观念中,东方与西方,白色人种与有色人种,文明与野蛮这三种二元对立秩序重合,互相映射,构成了帝国主义的话语谱系。(周宁:87—89)狄金森超越了西方优越、文明、进步,东方愚昧、野蛮、落后等预定的文化偏见。诗247挪用农奴为神龛的长明灯添灯油的细节,指出当奴隶离去,“灯光”也会随之熄灭,披露西方文明之“光”的虚假的辉煌。狄金森的反殖民姿态最有力的证据还在于她对落后的、麻木的、奴隶的、女性化的东方这一话语系统的驳斥。德昆西贬损马来人是“魔鬼”、“皮肤蜡黄”、“小眼睛凶狠、焦躁不安、薄嘴皮、奴颜婢膝”;嘲弄“鸦片”能给嗜好鸦片的马来人带来“一夜的安息”,免除其“漂泊之痛”。(50—51)狄金森对这种赤裸裸的种族主义书写做了直接回应。诗276严词抗议“文明—贬斥—豹子!”列举豹子在东方本土包括亚洲、非洲备受尊重的美丽与威仪,申明其“褐色”衣袍有“斑点”,那是“本性”使然,有力揭露作为“看守”的“文明”扭曲人性的强暴本质,并对来自亚洲的劳工表达了深切的同情:豹子离开“她的亚洲”,“麻醉剂—不能压制—”她的思乡之痛。
更多的时候,狄金森关注的重点不是政治批判,而是对理想的精神境界的探索,她对马来采珠人的形象塑造就是一例。米勒对这两首诗做了重点考察,指出狄金森挪用了当时报刊杂志流行的采珠人形象,说明追求人生价值的条件。诗417以迟钝的马来人比喻无视身边宝库的人类,然而创造性行为离不开冒险精神与梦想的能力;诗451的语言策略犹如勃朗宁的《我的公爵夫人》,通过一位有种族优越感的“伯爵”的自白,暴露其所代表的话语系统的武断与荒谬。“伯爵”预设具有海底珍珠的拥有权,马来人获取珍珠属于僭越,他讽刺马来人地位低下、皮肤黝黑、茅屋与服饰寒酸不配获得珍珠。和“伯爵”形成对比,马来人是勇于探索、敏捷干练的自然人,且浑然不知西方白人的欲望、无能以及野心。(133—37)
狄金森的诗451的阐释存在争议,研究者常认为狄金森以否定的态度塑造马来人。本内特(Paula Bennett)批评狄金森重写了报刊流行的讥讽黑人与白人的结合的种族套话:粗俗不堪、性欲旺盛的黑人把白人妇女偷回他的茅屋,但不懂珍惜后者。(53—61)波拉克(Vivian R.Pollak)察觉到狄金森把“白色”视为负担,但她认为诗人按照传统东方主义话语强调有色人种“性能力上的自信”。(90)米勒强调狄金森对马来人的认同与肯定,这一形象代表狄金森浪漫的东方主义,但她仍然认为马来人的“无知”属于刻板形象的重现。(134—35)
关于马来人潜水采珠、尤其是其“无知”的内蕴,道家视角能给予更加充分的阐释。就如蜜蜂、蝴蝶和飞鸟游弋在“夏日空气的汪洋”中,(1199)马来人海底“游”水是其精神自由的表征。《庄子·达生》说“至人”“潜行不窒”,是“纯气之守”,而非“知巧果敢”;(354)又说“醉者之坠车,虽疾不死”,这是因为“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坠亦不知也,死生惊惧不入乎其胸中”。(356)狄金森推崇的不是潜水的技巧与勇气,而是忘怀得失之道。她不拘一格地用“无知”、“无意识”表示最高的精神境界。例如,夏日野草回归“被嘲笑的家园”,“不知地位卑微/也不知羞辱的名姓”;(1617)自由的心灵“不再知道贫穷/也不知身本尘土”。(1593)朴素的马来人“不知道”“伯爵”的虎视眈眈,意味他超越了利害之端,超越了竞争,获得了真正的坦然:“获得,或是失去—/对他—完全一样—”。(451)诗417中也把马来人塑造成圣者。该诗敦促以得失的偶然,克服患得患失的焦虑,守护“简单的日子”,再次用对财富的超然描述最高的境界,明确把马来人树为楷模:“对于财富—浑然无识/如古铜色的马来人/无视东方水域的珍珠”。马来人的“悠缓的思维”确保了狂欢的“节日”和虚浮的“幻想”也不能扰乱他的心灵。他的迟钝意味其淳朴纯真之态,远离贪婪的攫取,永葆愚笨之心。《庄子·天地》以黄帝丢失玄珠而象罔独能找到,寓意屏除智巧聪明,无心乃得道。(210)狄金森的马来人就是守浑噩而黜聪明的象罔,从而获得了圆满的心珠。
在19世纪的西方文化中,马来人惨遭诋毁,被视为凶残、缺乏自制力、心智幼稚的低劣种族。除了德昆西对马来人的妖魔化,爱默生调侃“马来厨师”的“爆炸性脾气”,称其“不能忍受一小时的宁静”。(979)更有甚者,他吹捧工于计算与逻辑的英国人时,讽刺地说:“千百万的马来人和穆斯林中也必然会有那么一两个具有天文头脑的人”。(951)而狄金森强调这是东方的马来人,而非欧洲的“伯爵”获得珍珠,赋予马来人高超的精神境界,让马来人获得前所未有的智慧与尊严,充分体现了她的反殖民主义的文化姿态。采珠马来人获得珍珠,也因为这一意象符合狄金森水底采珠、获取智慧而逍遥游的隐喻。因而,更确切地说,这一形象塑造表明诗人更愿意让现实的种族偏见服膺于诗歌的隐喻需求。
东方对狄金森最重要的意义还在于为她的创作提供了思想资源,虽然这种影响未必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潜移默化的。其表现并不明显,却深入骨髓。钱钟书、茅于美、林建隆、陈元音等学者都曾指出狄金森诗歌在思想内涵、创作方式上与道家、禅宗、中国古典诗词的契合。随着狄金森研究的全球化,更多的研究者跨越英语文化的局限,求助于东方文化资源阐释狄金森诗歌的特质。本菲(Christopher E.G.Benfey)把她的“简朴主义”、“瘦削诗学”、“隐士姿态”、“非个人化角色”等归结为“亚洲美学实践”。(90)她表达清静无为与大默无言的思想,她的诗歌尤其是晚期诗具有祥和空寂、不落言筌的道风禅味。(Kang:60—79)在利用中国视角重新阐释狄金森诗歌的同时,我们必须思考她的东方特质的生成机制。有研究者考察过狄金森十六岁时参观过波斯顿的中国博物馆,指出博物馆的旅游指南对中国的儒、释、道有所介绍,其中提及的诸如“克制”、“无”等概念给狄金森留下深刻印象,这一趟经历也许“让她放弃社会、欣赏诸如沉默、白色尤其是‘无’等消极概念”。(Uno:43—67)即便不夸大诗人早年的一次经历,渗透入美国文化的东方文化因素仍可能对她产生巨大影响。
融会中西文化的超验主义是培育狄金森的东方智慧的温床。(Benfey:87)这是恰中肯綮的评论。随着超验主义的兴起,“走向印度”这一存在于美国集体无意识的隐喻增加了精神向度。爱默生与梭罗都把东方圣哲树立为生命智慧的典范。梭罗曾写道:“哲学总是依稀却紧密地和真理、和东方联系在一起。”(116)狄金森在信中邀请朋友栖息自己居住的“东方”,(20)申明不能“弹劾”“珍珠”,而应“瞄准东方”,(242)也提议“更精明的做法是走山路”。(220)尽管狄金森特立独行“走山路”,不像其他的超验主义者一样热情阅读东方文献,(Miller:129—30)然而,她的词汇与思想暗示她与超验主义共享一个东方。
狄金森奉为“事业”的“周缘”(Circumference)概念具有东方哲学的渊源。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联系与“周缘”相关的另一概念——“迂回路径”(Circuit)。在诗1090中,她使用“东方之径”(Oriental Circuit)这一表述,明确标志“迂回路径”的东方性质,透露了她对东方哲学或者思想的一些理解。“亚洲的休憩”(Asiatic Rest)是另一例。她宣称理想的精神境界意味“非洲的激越”与“亚洲的休憩”。(1563)虽然亚洲在西方文化想象中与休憩联系在一起和伊甸园密切相关,例如,惠特曼说伊甸园是“亚洲的花园”,人类离开了故园,堕入焦躁的流浪。(534)狄金森也重写过离开、重返伊甸园之喻,指出我们都是回不去昔日天堂的“东方移民”。(326)不过,“亚洲的休憩”在十九世纪的美国也回应了梭罗对“亚洲人”的建构,即“在无限的悠闲与自然的安息中”摆脱焦虑和劳累的生活方式。(102)梭罗的建构就并非和伊甸园直接相关。
联系超验主义者对东方的建构,可以发现狄金森的清静无为等思想可能具有隐性的东方来源。爱默生赞誉“亚洲的统一”与“亚洲心灵的无限”。(640)他推荐“虔诚、静观的东方”,(785)试图用“东方的大气”治疗“英国式的拘谨”。(906)梭罗认为“西方哲学没从东方意义上认识静观的重要性”。(111)他指出西方人“活动不停”、“追赶落日”,东方人“超然无事”、“凝视太阳”,还说“这静观的月中人在万物醒时酣睡”,(114)在《瓦尔顿湖》中亲证“东方人”所言的“静观”之乐。(411)狄金森崇尚静观无为,盛赞“正午的休憩”,喜听清风松韵、观落日、看夜空。在她的笔底,蝴蝶“无目的”悠游,“无事可做”,思忖在“月下安顿”。(655)此外,诗769曾说拥有“心灵的新价值”,“我停止算计—心满意足—”,“欲求”与“寒冷”如同“幻影”。这种以否定的方式获得平静的方法,类似梭罗提到的“亚洲式的焦虑”,也就是遵循“不可变更的规律”,从中实现“极大的慰藉”。(109—10)
道家的无为还意味无我、无名、“不自恃”以及“功成而不居”。狄金森推举没有“目的”和“报酬”激励的善行,代表性意象有幽谷的花朵、不自知完美的晨曦、普照大地又静静隐退的太阳等。梭罗大段地引用印度经典《薄伽梵歌》,强调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自足独立”、“不求回报”、“免除欲望的驱使”,甚至有类似《老子·六十三章》中的“为无为,事无事”的表述。(113)狄金森的诗1576阐释圣者无为而治,其隐喻模式犹如《论语·为政篇第二》中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70)狄金森未必阅读过《论语》中的相关段落,但类似的思想为梭罗所反复表述。梭罗曾挪用波斯故事,宣称“睿智能干之士”的治国之道在于“不掺和”。(105)他引用《论语·颜渊篇第十二》中孔子的话语谴责滥用权利:“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460)此外,当狄金森用牧童和牛朝向“湮没的牧场”隐喻“政治家的雏形”说明无为无我乃为政之道,(1549)这俨然是在回应梭罗诗意的描述:“日落时分,人心闲散、归于沉思;牧童赶着牛从牧场归来,哨音意味深长。”(317)由是观之,狄金森的悠闲、静观、清静无为等思想,其实是在推崇东方人的心态与境界。把超验主义者的东方作为理解狄金森的生命智慧的语境,联系她日常阅读的报刊杂志对东方哲学的报导,可以进一步考察狄金森的东方意蕴之源,这种研究是美国现代主义诗歌与东方关系的不可或缺的一章。
注释:
①本文里狄金森引文出自参考文献所列的诗歌与书信两部作品。如无特别说明,即选自诗歌。为避免繁琐,以下只视需要出注。夹注中的数字指序号,不是页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