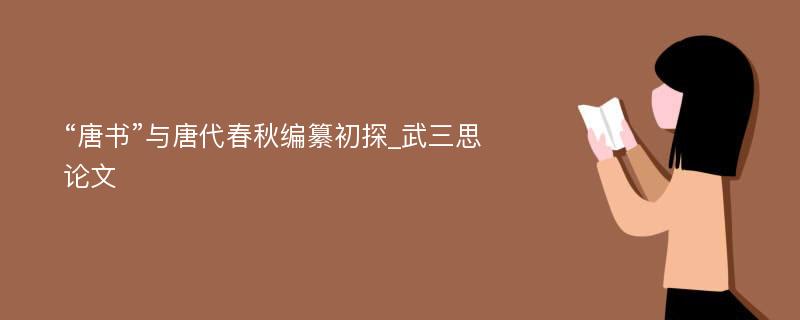
《請總成國史奏》考索——吳兢撰《唐書》《唐春秋》事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吳兢撰论文,請總成國史奏论文,唐春秋论文,唐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爲唐代著名的史學家,吳兢以其傳世之作《貞觀政要》而爲治史者所熟知。歷來關于吳兢的研究,也多圍繞著《貞觀政要》展開。①吳兢自武周長安三年(703)參與編修唐史起久任史職,不但參與了《則天實録》、《中宗實録》、《睿宗實録》和武周朝修唐史的編纂工作,而且還私撰《唐書》、《唐春秋》等若干史書,其中《唐書》由私人撰述轉爲官方修史,成爲後來韋述、柳芳等進行國史修撰的重要基礎。②在當時,吳兢的史學成就更多體現在參與編修國史、實録與私撰《唐書》、《唐春秋》而非《貞觀政要》上,但惜乎史稿不存,因此今人只能就存世者論其撰史理念及編纂方式,而對《唐書》與《唐春秋》的考察,更多是在唐代國史編纂的框架下被討論③,一些相關的細節問題則鮮有論者。本文將以吳兢《請總成國史奏》爲核心,對《唐書》與《唐春秋》的撰寫機緣、吳兢個人政治觀念對兩書撰寫的影響等問題進行考察。 一、《唐書》《唐春秋》始撰時間推測 《唐會要》卷六十三《史館》上“在外修史”類收録有吳兢《請總成國史奏》,在文中,吳兢對其私撰《唐書》《唐春秋》的的原因有簡單的介紹: (開元)十四年七月十六日,太子左庶子吳兢上奏曰:“臣往者長安、景龍之歲以左拾遺、起居郎兼修國史,時有武三思、張易之、張昌宗、紀處訥、宗楚客、韋温等相次監領其職。三思等立性邪佞,不循憲章,茍飾虛詞,殊非直筆。臣愚以爲國史之作,在乎善惡必書,遂潜心積思,別撰《唐書》九十八卷,《唐春秋》三十卷,用藏于私室。雖綿歷二十餘年,尚刊削未就,但微臣私門凶釁,頃歲以丁憂去官,自此便停知史事。竊惟帝載王言,所書至重,倘有廢絶,實深憂懼,于是彌綸舊紀,重加删緝,雖文則不工,而事皆從實。斷自隋大業十三年,迄于開元十四年春三月,即皇家一代之典,盡在于斯矣。既將撰成此書于私家,不敢不奏。”④ 此段文字是吳兢對私撰《唐書》與《唐春秋》歷程的回顧,學者們多以“國史之作,在乎善惡必書”作爲吳兢直筆書史的代表性觀點,而文中的若干細節則少有人注意。 吳兢自云撰寫這兩部史書的時間“綿歷二十餘年”,從開元十四年(726)向上追溯,如從長安三年吳兢初任史職開始計算,已有二十四年,而若從景龍二年(708)紀處訥、宗楚客等“監修國史”時計算⑤,則不滿二十年。“二十餘年”雖爲約數,但從吳兢私撰《唐書》與《唐春秋》的緣起來看,這一工作的起始時間至遲也應在神龍年間(705-707),而不致從景龍二年纔開始。 長安三年,武曌頒下敕書命武三思等修唐史,吳兢名在修史官之列⑥,據劉知幾《史通·古今正史》記載,此次修成《唐書》80卷,而按照《舊唐書·徐堅傳》所記,此次只是對此前牛鳳及所修唐史的“删改”,且“會則天遜位而止。”⑦按照吳兢的描述,“三思等立性邪佞,不循憲章,茍飾虛詞,殊非直筆”是他私撰唐史的原因,杜希德也認爲,武三思“對修史的無休止干擾使得纂修者無所措其手足”。⑧不過,除了吳兢的這段自述之外,武三思對長安三年修唐史之事的干預並不見諸其他史籍,只能存疑。若是依照《舊唐書·徐堅傳》的說法,這次修史只是在牛鳳及《唐史》的基礎上删改,那麽到武曌退位時新的唐史未能修成恐怕也可以理解了——劉知幾在《史通·古今正史》中對牛撰《唐史》全盤否定,認爲此書取材不當導致內容不可讀,編纂不當導致記載錯亂。⑨將這樣一部拙劣之作“删改”成劉知幾、吳兢等認爲可以傳之後世的史書,即便没有監修者的干涉,也實爲不易。無論是因爲受監修干擾還是因政局變動導致的工作中止,這次修史活動都是無果而終。 另外一個應該注意的細節是,按照劉知幾所述,這部從長安三年開始新修的《唐史》完成了八十卷,已經接近此前牛鳳及所修的百卷《唐史》五分之四的篇幅。短短兩三年間有此速度,而且還是在拙劣的牛氏《唐史》基礎上修改而成,不能不說有些奇怪。參與修史者如劉知幾、吳兢與徐堅交好,撰史理念也較爲接近,他們堅持著史應直書⑩,卻在牛鳳及《唐史》的基礎上匆匆修出八十卷的新唐史,這與劉、吳日後修史累年不就的狀况有如天淵之別,不得不令人懷疑是因爲監修者急于完成,于是史館衆人攢以成篇,遂使劉、吳與徐等無法踐行自己的撰史原則。 由此可知,或是因爲監修者的干擾,或是因爲五王政變的影響,導致長安三年開始的唐史修撰中斷,參與這次編修的吳兢卻不願放弃對唐史的寫作;而史館修史的體制,竟造成了在短期內修成八十卷史稿的結果——這次寫作或許正是“茍飾虛詞,殊非直筆”,也讓吳兢覺得通過史館修撰的形式根本無法實現“直書”的著史理念,便開始退而私撰《唐書》與《唐春秋》。據此推測,其撰述的起始時間有幾種可能:第一種可能是長安三、長安四年,即修唐史開始后不久,監修者對史書內容與歷史評價的干涉促使他開始私撰;第二種可能是神龍元年,張柬之等發動政變迫使武曌退位,修史工作的意外中止令吳兢想要以一人之力完成此書;第三種可能是神龍二年,武三思等監修的《則天實録》僅用數月便告完成(11),令參與此事的吳兢對史館修撰愈發失望,轉而追求“成其一家”。 至于景龍年間的諸監修對修史工作的干擾可能對吳兢造成的刺激,因年數上與“綿歷二十餘年”不合,且文獻闕載,故在此不論。 二、“立性邪佞”與“殊非直筆”之辨:監修者名單體現出的吳兢政治觀念 《請總成國史奏》中臚列了一份“相次監領其職”(即監修國史)者名單,即武三思、張易之、張昌宗、紀處訥、宗楚客、韋温。論者往往未曾注意其中的問題,而籠統稱諸人皆爲干擾直書、輕慢史官之輩,並根據《請總成國史奏》之言,認爲這批監修左右史書編寫的情况導致吳兢私撰《唐書》與《唐春秋》。吳兢撰二書的時間問題,上節已做分析,現對其所列監修諸人之事略作考釋,以補充上節所論。 吳兢所謂“往者長安、景龍之歲”修史之事,應該就是長安三年至神龍元年修唐史、神龍元年至二年修《則天實録》與景龍年間修史(可能是中宗朝實録)等事,這一期間的史館監修,除了《請總成國史奏》中已列出的人員外,還有蘇瓌、唐休璟、豆盧欽望、張柬之、魏元忠、韋安石、韋巨源、蕭至忠、李嶠與楊再思等。(12)這些未被吳兢在《請總成國史奏》中提名之人,似乎都無直接證據說明他們與“殊非直筆”無關,僅在劉知幾致蕭至忠書中痛陳史館修撰“五不可”時有“楊令公則云‘必須直詞’,宗尚書則曰‘宜多隱惡’”這一斷語(13),似可說明楊再思堅持據實直書。吳兢在此期間長期任史官,且在玄宗時參與了新修《則天實録》與《中宗實録》的編纂,無論從個人經歷還是對武后、中宗時期史料的瞭解上,都不致漏掉這些監修者姓名。他在上奏中未提及這些宰臣,或有其他原因。 若從武后、中宗朝政治的角度去考察,就可以發現,在《請總成國史奏》中被吳兢稱爲“立性邪佞”的諸監修,二張爲武曌親信,雖以男色見寵,其左右政局之能力,前代恩幸莫能過之。而武三思、紀處訥以下數人,全爲中宗朝武、韋勢力的核心人物;吳兢在上奏中未提及的監修者,則在政治上與他們並非一黨,或依附武、韋但在政治表現上與之存在距離。 本文所謂“武、韋勢力”,主要就中宗朝政治角逐中圍繞在武三思、韋后身邊的政治力量而言,純爲具體政治事件中的黨派劃分,與陳寅恪所說“李武韋楊婚姻集團”及黄永年所用“李武政權”概念不同。 張柬之有除二張之舉,又遭武三思構陷;魏元忠、韋安石與武、韋勢力不睦,且元忠爲宗楚客等排擠乃至貶死;蘇瓌在中宗時數挫韋后之謀,蕭至忠在中宗時亦有匡正之舉;豆盧欽望、李嶠及楊再思等雖或依附强權者或獨保其身,亦無大惡。以上諸人之表現爲治史者熟知,無須贅述。而與二張、武三思、宗楚客、紀處訥及韋温等武后統治後期至中宗時的當權者相比,以上諸人在宰臣中也處于相對弱勢地位。 作爲這一段歷史的親歷者,吳兢自然瞭解這種政治狀况,茲舉一例試作說明。李重俊誅殺武三思后,宗楚客、紀處訥授意侍御史冉祖雍構陷時爲相王的睿宗與太平公主,當時蕭至忠在中宗面前陳說冉祖雍之說不可信,他不但點明冉祖雍之言“咸是虛構”,而且還從李唐皇室安全的角度勸誡中宗:“陛下富有四海,貴爲天子,豈不能保一弟一妹,受人羅織?宗社存亡,實在于此。”(14)宗楚客等欲藉李重俊案剷除睿宗及太平公主,是武三思死後政壇一大焦點事件,朝臣中擁護李氏者多支持睿宗,蘇珦辯于前,蕭至忠諫于后,岑羲與吳兢也參與其間。作爲此事的參與者,吳兢自然瞭解蕭至忠與武、韋黨派之差別。 另外,楊再思、韋巨源等人在中宗時雖未與當權宰相公開對立,但也未與其黨沆瀣一氣,《舊唐書》所謂“時宗楚客、紀處訥潜懷奸計,自樹朋黨,韋巨源、楊再思、李嶠皆唯諾自全,無所匡正。至忠處于其間,頗存正道,時議翕然重之”之語,正是當時群相政治表現差异的最佳證明。(15)因此,蕭至忠、李嶠等數人雖與武、韋之黨有交往,但吳兢知其與武三思、宗楚客等有別,故不將這批監修視爲“邪佞”。 如前所述,吳兢在《請總成國史奏》中所稱“殊非直筆”的監修者,與那些不在此名單的監修者最大的區別,並不全然因爲修史觀念不同,也應具有政治上的分野。(16)故而吳兢在上書中直斥武、韋勢力領袖“立性邪佞”,而未遭其指斥者,並非倡言直書,只因非武、韋死黨且政治實力較弱而得以免責。這種政治分野,是當時政壇上實有之情况,而稱武、韋領袖爲“邪佞”,則與吳兢個人的政治態度有關。 吳兢本人在政治上與那些和武、韋勢力保持距離的大臣相類,甚至在有些事情的態度上和武、韋勢力的反對者相近。且不說他得以參與修史是因爲魏元忠的推薦(17),因而對魏懷有感激、同情,在一些敏感的政治問題上,他也能直陳己見,表明與武、韋勢力的對立。前文所提到的冉祖雍構陷睿宗事,吳兢曾上書駁之,稱羅織睿宗罪名之人爲“賊臣”、“邪佞”(18),此態度正與《請總成國史奏》相吻合。 當然,“邪佞”與否的評價標準,並非全然出自吳兢一家之言。自玄宗誅武、韋黨,上述兩類監修國史之臣本來具有的政治地位差別與黨派分野日漸隨著對武、韋勢力的政治定性而被視爲正、邪之別,而武、韋勢力的反對者也從道德的角度將這種區別進一步强化,如李邕在議韋巨源諡號時上書列巨源“四罪”(19),史書稱李邕之文一出,“論者是之”(20),正可視爲政治評價與道德評判在武、韋黨羽定性問題上的合流。(21) 評價某個政治群體,自然不能簡單以“正/邪”名之,且武、韋勢力作爲武后至玄宗初年的重要政治力量,是這一時期政權發展與政治演變的關鍵因素,陳寅恪將其納入“李武韋楊婚姻集團”範圍之中,黄永年亦將其視爲“李武政權”中的一部份。(22)陳、黄之說皆爲高明之論,不過需要說明的是,他們的觀點是後來者對較長一個時期(相對于當時人的感受而言)政治史的歸納與分析,且不涉及道德評判,又非基于各勢力成敗的評價,因此與歷史當事人的觀點不免存在差异。 在個人的政治態度與時代觀念之外,用“邪佞”形容武、韋勢力的代表人物似乎還有其他原因。恢復貞觀政風,是中宗復位后極具影響力的政治思潮,不過,當時也存在著對武周之政的維護。中宗景龍元年權若訥上書,反對“神龍元年制書‘一事以上,並依貞觀故事’”(23),此後至玄宗時期,關于用“貞觀故事”還是繼武周之政的争論一直在繼續。當時維護武周之政的主要人物,就是《請總成國史奏》中被吳兢斥爲“立性邪佞”的武、韋勢力代表(除了在五王政變中被殺的二張)。作爲貞觀之風的支持者,吳兢不但在政治立場上與他們勢同水火,在政治理想上也與之截然不同,恐怕這也是他將這批堅持武周之政者視爲“邪佞”的另一個原因。(24) 總之,從吳兢個人政治態度、中宗以後的時代評價與吳兢所認同的政治理想幾個方面,武三思、宗楚客等在《請總成國史奏》中被提及的諸監修,都站在吳兢及其時代的對立面,所以吳兢稱其“立性邪佞”。至于“殊非直筆”,恐怕並不是他們與未列入此名單的監修們在修史態度上的區別,吳兢以其政治立場衡量長安、景龍中諸監修官,故産生此份不完全之名單。 吳兢退而私撰《唐書》與《唐春秋》,除去史館編修之弊以外,亦與其政治立場有關。唐史與武周、中宗朝政治關係重大,吳兢與武三思等政治立場有別,則修史態度自然有异。此差异在長安、神龍時業已出現,自不待景龍年間纔最終爆發衝突,故此二書之修撰或從長安、神龍時開始,亦可從此獲一證據。 小結:吳兢與玄宗的當代史 在《請總成國史奏》中,吳兢回顧自己撰寫《唐書》、《唐春秋》的歷程時,未直接否定史館修撰的作用,而是對武曌、中宗時期作爲武、韋勢力代表人物的若干監修予以指責。前文已指出,出現這種指責的一個背景,就是吳兢與他們在政治立場與政治理想上的强烈衝突,故而“邪佞”之稱,可視爲吳兢對已經塵埃落定的當代史的評價。不過,這種評價出現在開元十四年,武、韋勢力早已被滌蕩殆盡,且宗楚客、紀處訥與韋温等監修國史時,《唐書》、《唐春秋》已經開始寫作,爲何吳兢還要將他們與武三思、二張並列,再做批評? 與《請總成國史奏》同年,吳兢又有《大風陳得失疏》,認爲“恐陛下左右有奸臣擅權,懷謀上之心”,稱“陛下承天后、和帝之亂,府庫未充,冗員尚繁,戶口流散,法出多門,賕謁大行,趨競彌廣”,並直言“此弊未革,寔陛下庶政之闕也”(25),正可說明他所盼望的貞觀政風並未建立,“邪佞”所支持的武周政治模式並未終結。而開元十三年,玄宗東封泰山以紀功,如此功業,並非吳兢所認可,故其在《大風陳得失疏》中直諫,“願斥屏群小,不爲慢游,出不御之女,減不急之馬,明選舉,慎刑罰,杜僥幸,存至公”。(26) 值得注意的是,開元十四年六月玄宗因“大風拔樹,壞居人廬舍”下詔令群臣言得失,故吳兢上《大風陳得失疏》;而《請總成國史奏》上于同年七月,正是在同樣的政治情境之下。此時吳兢在叙述自己撰《唐書》及《唐春秋》的背景時提到武、韋勢力領袖的“邪佞”,應非無心之筆。 吳兢曾任諫官,自中宗時起至玄宗之世數次上疏勸諫(27),匡正帝王的諫官責任感一直在他身上得以體現,故回顧私撰國史事時,不忘對武周之政的維護者予以批評,正是從剛剛過去不久的歷史中尋找證據,與《大風陳得失疏》中所言“奸臣擅權”事相應和。所謂“讀《唐鑒》,知范祖禹有臺諫手段”,正可用以形容吳兢此處之用意。 簡言之,吳兢撰述《唐書》與《唐春秋》,應在長安、神龍中,而《請總成國史奏》中提及景龍年間史館監修妨害直書之事,與其私撰唐國史無大關涉,因兢與諸監修中武、韋勢力代表政見不同、立場有异、理想有別,且與開元十四年進諫玄宗之事有關,故爲事實陳述之外,以臺諫手段勸誡君上之言。 ①在《貞觀政要》研究中,也有若干涉及吳兢生平的論述與研究,如瞿林東:《吳兢與〈貞觀政要〉》,《河南師大學報》1979年第6期;謝保成:《試解〈貞觀政要〉成書之“謎”》,《史學月刊》1993年第2期;謝保成後來又將對吳兢生平的研究予以增補,收入《〈貞觀政要集校〉叙録》,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李萬生對兩《唐書》中《吳兢傳》的記載進行了考辨,見《新舊唐書〈吳兢傳〉史實辨證》,《貴州師範大學學報》1989年第4期;李萬生又有《新舊唐書〈吳兢傳〉史實辨證(二則)》,《貴州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2年第2期。 ②關于《唐書》《唐春秋》與韋述修唐國史的關係,見《舊唐書》卷九十二《韋述傳》的記載:“國史自令狐德棻至于吳兢,雖累有修撰,竟未成一家之言。至述始定類例,補遺續闕,勒成《國史》一百一十三卷,並《史例》一卷。”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3184頁。柳芳修唐國史與韋述《國史》的關係,《舊唐書》載爲:“(柳芳)與同職韋述受詔添修吳兢所撰《國史》,殺青未竟而述亡,芳緒述凡例,勒成《國史》一百三十卷。上自高祖,下止乾元。”見《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九《柳登傳》開篇對柳芳事迹的追記,第4030頁。 ③從唐代國史編纂角度對吳兢《唐書》與《唐春秋》進行論述的專著有謝保成:《隋唐五代史學》第五章《國史的系統修撰》,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此書最初由厦門大學出版社于1995年初版,2007年版爲修訂新版,故列于前);岳純之:《唐代官方史學研究》第二章第四節《唐代史館的撰述活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美]杜希德:《唐代官修史籍考》第二部份《歷史記録的纂修》,劍橋大學出版社,1992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1月中文版;相關論文有李南暉:《唐紀傳體國史修撰考略》,《文獻》2003年第1期;另有從歷史書寫角度研究吳兢《唐書》與其後韋述、柳芳之作關係的論著,如徐冲:《〈舊唐書〉“隋末群雄傳”形成過程臆說》,載《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25輯,后收入《中古時代的歷史書寫與皇帝權力起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6。其餘通史性質的史學史著作不再一一列出。 ④《唐會要》卷六十三,北京:中華書局,1955年,第1098~1099頁。 ⑤《唐會要》記劉知幾致書蕭至忠事,稱景龍二年爲紀處訥、宗楚客與韋巨源、楊再思、蕭至忠等“並監修國史”,見《唐會要》卷六十四《史館》下“史館雜録”類下,第1106頁。《史通·忤時》記此事與《唐會要》同。 ⑥《唐會要》卷六十三《史館》上“修國史”類,第1094頁。 ⑦《舊唐書》卷一百零二,第3175頁。對此次修唐史之事的研究,可參杜希德《唐代官修史籍考》第150~151頁,又可見李南暉:《〈史通·古今正史〉唐史箋證》,《文獻》2000年第3期。 ⑧杜希德:《唐代官修史籍考》,第150頁。 ⑨劉知幾著,浦起龍通釋:《史通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47頁。 ⑩劉知幾與吳兢、徐堅相友善之事,見《史通·自叙》,《史通通釋》第269頁。他們在撰史理念上相近,可以稱爲一個“學派”,最早由白壽彝提出,見《劉知幾的史學》,《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59年第5期,后由王光耀在《關于吳兢與貞觀政要的幾個問題》中進一步論證,載《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87年第2期。與這種觀點稍有區別的,是對劉知幾等人撰史理念背後的史官職權理念的歸納,如雷家驥認爲,武周後期史臣們所提出的修史理念,是館院史臣“史權論”的表現,見其《中古史學觀念史》第十一章《唐朝前期官修及其體制的確立與變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0年。 (11)神龍元年修《則天實録》事,可參《册府元龜·國史部》“選任”類,見王欽若等編纂,周勛初等校訂:《册府元龜》卷五百五十四,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年,第6343頁。修成《則天實録》上呈事,見《唐會要·史館》上“修國史”類,《唐會要》卷六十三,第1094頁。 (12)蘇瓌、唐休璟監修國史事,見《舊唐書》卷八十八,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2879頁;豆盧欽望監修國史,見同書卷九十,第2922頁;張柬之監修事,見同書卷九十一,第2942頁;魏元忠、韋安石、韋巨源及蕭至忠監修事,見同書卷九十二,第2953、2956、2965、2970頁;李嶠監修事,見同書卷九十四,第2995頁;楊再思監修事,見同書卷一百零二,第3168頁。今人對唐代宰相監修國史也有相關研究,如張榮芳《唐代宰相監修國史表》,收入其著《唐代的史館與史官》附録,臺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84年;又如岳純之《唐代監修國史制度考》附《唐代監修國史名録》,《史學史研究》2002年第1期。 (13)見《唐會要》卷六十四《史館》下“史館雜録”類下,第1107頁。《史通·忤時》與此同。 (14)《舊唐書》卷九十二,第2968~2969頁。 (15)同上,第2970頁。 (16)《新唐書·吳兢傳》稱:“始,兢在長安、景龍間任史事,時武三思、張易之等監領,阿貴朋佞,釀澤浮辭,事多不實。”見《新唐書》卷一百三十二,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4528~4529頁。按:此段文字中“釀澤浮辭,事多不實”之語,似可說明當時監修官干預修史,導致所記不實,亦有學者因以爲據。然細究史源,整段文字應是改寫《請總成國史奏》文字而成。此段描述,于他處不見,且時間、監修人員姓名次序皆與《請總成國史奏》一致,至于“阿貴朋佞”云云,應爲改寫“立性邪佞”等數句而成。 (17)見《舊唐書》卷一百零二,第3182頁。 (18)《新唐書》卷一百三十二,第4525~4526頁。按:《新唐書》此處未明言宗楚客與紀處訥授意冉祖雍構陷睿宗,僅言“奸臣構陷安國相王與謀”,據《資治通鑑》卷二百零八中宗景龍元年八月事及《舊唐書·蕭至忠傳》可知。 (19)此事見《舊唐書》卷九十二,第2965~2966頁。 (20)《舊唐書》卷一百零二,第2967頁。 (21)韋巨源依附于韋后及宗楚客,諂媚阿上,故李邕等非之。這是武、韋黨誅滅后,其反對者在道德批評上的擴大化,可視爲一種受遏制已久后的情緒反彈。其他如劉知幾對蕭至忠之觀感亦有過激之處,見《史通·忤時》,《史通通釋》,第558~559頁。 (22)陳寅恪之說見氏著《記唐代之李武韋楊婚姻集團》,收入《金明館叢稿初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黄永年觀點見氏著《六至九世紀中國政治史》第六章《李武政權》,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年。 (23)《資治通鑑》卷二百零八,中宗景龍元年二月事,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6727頁。 (24)關于吳兢對貞觀政風的推崇,謝保成已有詳細的論述,可參看《〈貞觀政要集校〉叙録》。 (25)《新唐書》卷一百三十二,第4528頁。 (26)《資治通鑑》,第6727頁。 (27)吳兢任諫官事,見《新唐書》卷一百三十二,第4525頁。标签:武三思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