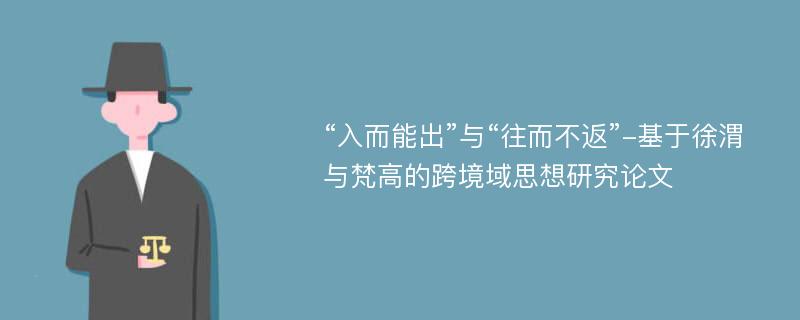
“入而能出”与“往而不返”
——基于徐渭与梵高的跨境域思想研究
黄琳12,
(1.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陕西西安7100492;.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西安710072)
[摘 要] 徐渭和梵高尽管在中西方艺术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其思想并未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欧洲浪漫主义运动是对启蒙运动的反动,主张文化与价值观念的多元,是西方知识史上一场真正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推崇“价值由心创造”与严苛的加尔文宗教超然决断的“神”之间,所展现的自由与独断、有限与无限,人与神间超绝、超离,二元对立的预设性架构,无从安顿中国传统思想“内在超越”的一元论立场。缘于心学精神的融通与良知的内在超越,徐渭未曾遭遇梵高的“人、神两分”与“心、理两分”问题,在分析二者异同的基础上,可以对中西方思想文化具有更清晰、深刻的认识。
[关键词] 心学;浪漫主义;内在超越;超绝超离;徐渭;梵高
梵高(1853—1890年)与尼采(1844—1900年)的生卒年几近同时,其所面临的时代问题、生存问题亦颇相近:浪漫主义时代精神由“心”创造价值,抑或听从超绝“神”做出的价值判断?尼采“重估一切价值”的判断振聋发聩,梵高则试图用“爱”的行动统合二者,认为通过对自然、艺术、孩童、生活的爱,可以理解上帝赋予人类灵魂的美好,从而在更深刻的意义上感受上帝的存在。梵高的一生都在追求“高于我”的超越存在,但是,浪漫主义所推崇的由心而发的价值判断,“价值由心创造”,与严苛的加尔文宗教超然决断的神,自由自律的“心”与独断超绝的“神”,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二者间的矛盾张力,令梵高撞见一片虚无。与之形成对照的徐渭,此处涉及中国文化“内在超越”的思想灵境,“所谓‘超绝’‘,超’虽超矣,却与人世隔‘绝’,二元对立‘;超越’则指浩然同流,一体融贯。”① 方东美:《中国人的人生观》,冯沪祥译,台北:幼狮文化事业1980年版,第13页。 中国传统视域下的神性,超越又内在,良知即有限与无限、内在与超越的合一。在这样形而上与形而下融贯统一的思想架构下,现实人性纵有气质气禀的先天限制与外在昏明开塞、私意欲念之玷染,人无须承担西方宗教中无可超脱的“原罪”负累与“命运”“必然”的永恒“大箍”,人的本然善性充扩至极,便可上达至无限与超越之境。
“绿色”的与“保护地球、环境及其各种生物的安全和可持续性发展相关”的意义内容在“绿色2”的基础上获得了长足地发展,渐渐突破像“绿色革命”、“绿色和平组织”、“绿色食品”类的固定模式,进入到更为广阔的构词领域。
糖尿病外周神经病变发病机制之一可能是由于糖尿病患者持续的高血糖环境导致施万细胞或背根神经节神经元上的CAV-1表达量下降,进而导致Erb B2受体失去CAV-1对其功能的抑制作用,Erb B2受体信号通路异常激活,机体神经传导速率减慢、机械敏感性和热敏感性降低,从而导致糖尿病外周神经病变的发生。然而,这种高血糖导致的脱髓鞘变化可被p75通过活化其下游的c-Jun氨基端激酶信号通路所拮抗,抑制高血糖导致的施万细胞上CAV-1表达量下降,从而在DPN中起抑制病程进展的作用。
一、由艺术以观思想,由思想反观时代精神
徐渭和梵高同是中西方艺术史上熠熠生辉的人物,其身心性情又带有强烈的性格决定命运的色彩。梵高对精神生活有强烈的追求,无论是早期加尔文信仰中的上帝,还是后期浪漫主义时代精神,回转至主体内心,肯认自我有做出道德价值判断的能力,价值规范源于我心能动的创造影响之下的,对于自然、艺术抑或他称之为“生活之爱”的,都曾热切地去追求,但这些都无法带给他内心的归宿与宁静。徐渭精神失常,偏离传统儒家的中庸之道,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本属少见,但即便这样,这位“中国的梵高”亦未像西方的梵高那样自行了断此生,而是从传统文化的浸濡、体认中获得精神的滋养与归宿,调养身心以颐养天年。徐渭注重纯个人的精神修为,懂得身心交关,天人一气,注重儒家道德实践与道家内丹“治心治气”的工夫实践,打通“身心”之隔,使天理下贯至灵明良知指导下的意志行动、价值判断,身心方能谐和一贯。
史学家缪钺曾言,汉、魏以降,中国传统诗人莫不出于“入而能出”与“往而不返”两类。这样两极的分类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实属少见,多是其不同程度之和合,不可粘滞求之,但用“入而能出”与“往而不返”来形容徐渭与梵高,反倒贴切。两位同为天才横溢、个性偏激的艺术家却有着不同的人生结局,出入之间,堪值玩味① 缪钺论及中国传统的两类诗人,吾国古人之诗,或出于《庄》,或出于《骚》。盖诗以情为主,故诗人皆深于哀乐,但同为深于哀乐,又有两种殊异的方式,一为入而能出,一为往而不返,“入而能出者超旷,往而不返者缠绵。”庄周与屈原恰好为此两种诗人之代表,庄子深于哀乐而能不滞于哀乐,虽善感而又能自遣,屈原则不然,其用情专一,沈绵深曲,潺湲流涕,不能自已。故庄子用情,如蜻蜓点水,旋点旋飞,屈原用情,则如春蚕作茧,愈缚愈紧。缪钺,叶嘉莹:《灵溪词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29页。 。纵有着相似的生命艺术与人生磨难,却有着迥异的思想及人生结局,若逆溯其源,便会发现其时代思想背景与属于个体的思想人生暗相契合。二人分属相距遥远的文化传统,且各自都与其时代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生活于欧洲19世纪中晚期,缘自18世纪末欧洲浪漫主义运动对启蒙运动的纠拨,主张文化与价值观念的多元,认为真理不是被发现,而是为人所创造。浪漫主义精神这种反启蒙运动,对欧洲思想重要的影响在于,使人们认识到科学与理性并非能解决所有问题,对于道德伦理、社会政治的价值判断存在多种有效的解决方案② 黄琳,张再林:《价值规范由心生出如何成为可能——浪漫主义道德价值判断的心学解读》,《学术界》2016年第8期,第31页。 。西方思想文化界由此产生了剧烈的震荡,梵高的思想展现出浪漫主义时代精神与自幼秉赋的严苛加尔文宗教传统的碰撞,而徐渭的思想与人生展露出阳明心学与明代中晚期“三教合一”思想的印记。于是,梵高与徐渭“其同不胜其异”的思想人生与艺术精神,可由浪漫主义与心学,并两个思想文化传统——西方的“二元分离”与中国文化的“混融气象”的比照探寻究竟。
对加尔文宗教来说,正因人类的罪愆,使上帝不可视的存在愈发模糊不清,无论自然、艺术,抑或哲学都无法根本将人引向上帝,《圣经》是“教堂生活的唯一权威”④ Cliff Edwards,“Van Gogh and God:A creative Spiritual Quest”,Chicago:Loyola University Press,1989,p.40. 。“过程哲学”创始人怀特海曾针对加尔文“上帝意志”的专断与明暗断然两分这一特点,认为其类似于摩尼教关于世界明暗二分的教义,世界由明暗、善恶的两极组成,上帝是绝对的善,人世是绝对的恶。加尔文教义认为,《圣经》是宗教真理绝对的权威,人类生而有罪,需要通过自我牺牲和服侍上帝来获得自我救赎。加尔文教义最基本的原则包括“选民前定论”“无条件拣选”,是上帝意志任意决断的体现,神将世人分为两类:少数人是上帝的选民,在“此世”替上帝行道;另一类芸芸众生,他们将是永远沉沦的罪人。但在最后的审判未到来之前,惟有上帝知道谁获入选,为此,人人都努力争取此世的成就,以获得“选民”的身份。早期的加尔文教徒和后来的清教徒都对自己的人格怀有极大的自信,他们的目的是要在此世建立一个“神圣社区”,并坚信这一神圣的使命是上帝赐予的,马克思·韦伯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据此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出现与之相关⑤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18页。 。
尚融和,则其异不胜其同;尚分离,则其同不胜其异,徐渭既是文人、画家、书法家,亦是诗人、戏曲家,于军事、品茶、医道诸“技艺”相当精通,兼修“三教”,百无禁忌。不仅如此,徐渭懂得身心交关,天人一气,注重儒家道德实践与道家内丹“治心治气”的修身养性工夫,使心体、性体、知体遥契天道,内外和谐,贯通身心,徐渭文集中呈现的思想矛盾,在他本人却是“道通为一”的圆融无碍③ 在明代,炼就“内丹”并非一定是为了得道成仙、长生不老,通常是为了变化气质,稳定“一时乍得之景象”,亦即靠顿悟悟得良知本体的辅助工夫。“内丹”修炼通过心气兼治,打通身心的过程中,定住顿悟悟得的“一瞥之慧”,从道德修养角度以观,“内丹”的修为及调息养气实收延年益寿之功。黄琳:《心气兼治:王龙溪对徐渭思想的影响》,《中国哲学史》2017年第2期,第94页。 。从儒家道德实践与道家内丹“治心治气”两方面下工夫,体现出对季彭山与王龙溪思想的兼收并蓄,呈露出“居时处中”知人论世的融通混一,两种有差异的思想在圆融活转的徐渭处实无矛盾,出入于往返之间,在“境域之中”糅合二者。
梵高的一生都在追求那“高于我”的超越存在,但是,浪漫主义所崇尚的内心价值判断与神的超然决断间,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内在自由自律的“心”与外在他律的“神”所产生的强烈矛盾与张力,二者间超绝、超离的关系,梵高撞见一片虚无,结局早已注定,只需真诚、勇于直面传统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时代冲突的人来出演。方东美先生曾对“超越”与“超绝”做过词语上的区分,“所谓‘超绝’,‘超’虽超矣,却与人世隔‘绝’,二元对立;‘超越’则指浩然同流,一体融贯。”③ 方东美:《中国人的人生观》,冯沪祥译,台北:幼狮文化公司1980年版,第13页。 虽一字之差,意义却大不相同,西方哲学常常混淆不清,在中国哲学却清晰条畅。
牟宗三曾言,儒家的尊严及其所以为正宗处,完全靠“天命、天道下贯之为性”的“客观性原则”提挈并纲维,孔孟又别开生面,由仁、智、圣及性善开出“主观性原则”,由人通过道德修为,向上定住传统中天命、天道下贯而为性的纲维于不坠,并经此一转进,“主体性与客观性取得一个‘真实的统一’,成为一个‘真实的统一体’”① 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5年版,第41页。 。如果没有一种真实的道德生命与超越感,坠落是很容易的,“就好比西方基督教中若没有耶稣,那上帝亦是易于坠落的,上帝的光辉亦难于展现。”② 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第61页。 但是,中西方的差异很明显,耶稣终究是神而非人,所以,在西方宗教的思想体系下,人无法用主体的内在性遥契外在之神,“人”与“神”之间的超绝、超离和隔断是不可避免的。
二、“人、神两分”与“心、理两分”:超绝与超离
19世纪荷兰宗教改革后的教堂,梵高全家信奉的是严苛的加尔文教派,把《圣经》作为“上帝的旨意”而遵奉。他早期的宗教经历与训练极其严苛,生活持续地围绕在《圣经》及对其解说的事件周围。全家人参与由父亲主持的崇拜活动,葬礼、洗礼和特定的节日庆祝,参与教会学校举办的圣经课程。梵高在写给弟弟提奥的信中说,“还记得父亲每天早晨怎样为我们做祷告吗?‘请将我们引领,远离邪恶,尤其是罪恶的邪恶’……”① Vincent van Gogh,“The Complete Letters of Vincent van Gogh,with Reproductions of All Drawings in the Correspondence”,3volumes,London:Thames and Hudson Ltd,1978,p.98.《梵高书信全集》中存有大量与提奥往来的信件,提奥是成功的画商,与梵高感情深厚,在经济与精神两个层面给予梵高毫无保留的信任与支持。在梵高自杀后半年,提奥精神崩溃,死于严重的精神病爆发,两人被合葬于一处。 。人生中最初的珍贵时光浸濡在《圣经》的存在中,宗教精神对梵高一生的影响实难估量。随着他日后远赴海牙、阿姆斯特丹、伦敦、巴黎等时代大都市,所处的是西方思想发生剧烈变革的欧洲19世纪,在浪漫主义精神的影响下,对于真诚信仰的宗教传统与时代精神,梵高会做出怎样的回应,他付出生命的代价来回答。
《中国老年人潜在不适当用药目录》判断PIM情况 在795例社区老年患者中,有230例 (28.9%)存在PIM合计275项,其中存在2项以上PIM的患者36例。202例患者 (25.4%)使用了A级优先警示药物共226项,其中高风险强度29项(12.8%), 低风险强度 197 项 (87.2%)。 44 例患者(5.5%)使用了B级常规警示药物共49项,其中高风险强度 36项 (75.5%),低风险强度 13项(26.5%)。具体情况见表 6和表 7。
正如存在主义始祖克尔凯郭尔在《旧约》中找到了亚伯拉罕,并从中发现了“个人选择自己”的原理,梵高在《约翰福音书》中找到了“爱”,作为内在的心与神相感通的方式,梵高自由选择的价值判断是用“爱”的行动统合自然、艺术、文学与宗教经验。与克尔凯郭尔相类,梵高不满意僵化、生硬、冰冷与制度化的宗教教条,淹没了内心真实的感受与道德律令,直觉到制度、规范淹没了自由与“真诚”。他们都认为,宗教信仰不应拘泥于形式,而应回归主体内心的意志自由,个人与上帝间的真实往来与直接联系才是真正的宗教精神。这种人、神之间的,相互缘构发生的关系,正是后来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存在本身”的境域意义① “缘构发生”是海德格尔的核心理念之一,“自身的”缘构发生,是一种居有且揭蔽的发生,海德格尔一直避免引入那种预设静态的哲学观或形而上学,存在即它本身,“自身的”缘构发生暗含运动。 。梵高赞同浪漫主义文学家维克多·雨果“宗教逝去,神性永存”的观念② Vincent van Gogh,“The Complete Letters of Vincent van Gogh”,p.386. 。在他看来,神无论如何不应局限于“宗教”,神化身于人、家庭、有爱的人以及新生的生命,只要能够带给心灵“庄严华美”“无限”的真切感受,即可使他联系到上帝的存在,这样在时间中开显存在“境域在先”的灵动活转,绝非外在固化、僵化、制度化的宗教教条所能达到。
浪漫主义精神贵意志而贱理智,重内观而轻外索,尊个性而斥普遍,主创辟而贬发现。20世纪西方思想史家以撒亚·柏林称之为“浪漫主义革命”,乃欧洲二千余年来思想上最大的转折点。心学风气中的明代士大夫,重情轻理,主动不主静,若强行与泰西比附,则似远于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而近于反启蒙的浪漫主义③ 严寿澂:《近世中国学术通变论丛》,台北:国立编译馆2003年版,第10页。 。明代心学与西方浪漫主义,其同不胜其异,若以“格义”之法比附,与以“启蒙”说明代思潮,其失相等。若以明代心学即为“浪漫主义”,抑或浪漫主义精神为“心学思想”,这种生硬的比附最终落入皮相,只会距离实情更远。
然而,浪漫主义精神强调,价值由我心创造,价值是我自由意志的选择,“神性与灵魂真实存在,它可以存在于不同的地方,无论是通过自然还是艺术都可以感受到神性的在场。”⑥ JacquesBarzun,“From Dawn to Decadence:500years of cultural triumph and defeat,1500to the present”,New York:Harper Perennial,2001,p.491. 早在浪漫主义风行的18世纪末期,黑格尔在对启蒙理性纲领的首次阐发中,就提出审美直观不但是“理性的最高行为”,而且“真和善只在美中协调一致”。对新艺术及主体性的推崇、高扬,尼采直接将艺术家及艺术本身确立为“新的价值设定原则”。梵高与尼采的生卒年几近同时,其所面临的时代问题与生存问题亦颇相近,听从超绝神做出的价值判断,抑或依循浪漫主义时代精神由心创造价值?尼采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已经给出了答案,该问题进而内化为,由心而发的价值判断,抑或价值由心创造与上帝的独断间究竟可以有怎样的联系?梵高显然感受到二者间强烈的矛盾张力,试图用“爱”的行动来统合二者,他认为对自然、艺术、女性、孩童的爱,可以理解上帝赋予人类灵魂的美好,透过人类灵魂的活力、爱、希望以及信仰,可以在更深刻的意义上感受上帝的存在。
出生于传统的基督教家族,梵高曾热切地期盼继承牧师的事业,“父亲总是寄希望于我,总有一天那是会实现的,愿上帝为此赐福”② Vincent van Gogh,“The Complete Letters of Vincent van Gogh”,p.99. 。他在给弟弟提奥的信中说,从现在起到三十岁之间,“一定要努力生活,并意识到我们的罪恶”③ Vincent van Gogh,“The Complete Letters of Vincent van Gogh”,p.120. 。如果说梵高对原罪的焦虑与不安显得过于强烈,根本的原因在于他把加尔文主义宗教传统深植心中。正如加尔文主义宗教期待的,人由内心深处的软弱、气质缺陷与内在邪恶的认知,感受到对外在上帝信仰的必要。直至1881年前后,当梵高的宗教思想发生转折性改变时,他深切意识到,加尔文主义宗教传统有“黑色丝”与“白色丝”之分,正是受到“黑色丝”——加尔文宗教关于人世邪恶预设的影响,自己的青年时代才会变得如此贫瘠、冷酷、幽暗无光,他逐渐感受到,加尔文主义传统中的光明正在逐渐变为黑暗。
三、天道内在而为人之性:“内在超越”“感通遥契”的良知
徐渭是大写意水墨花卉的创始人,在中国传统艺术史上,不亚于梵高在西方艺术史上的地位,一生的坎坷经历亦不逊之。他数罹不幸,为狂疾,又因狂疾而身陷囹圄,在中国文化艺术史上是很极端的例子。由艺术以观思想人生,由思想人生反观时代精神,因为,艺术从人生中流出,成为人生中重要的一部分,故贵能从人生来看艺术,亦贵能从艺术来看人生。“人生不同,斯艺术亦不同。东西文化不同,人生不同,而东西双方之艺术亦有不同。”⑤ 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台北:东大图书1993年版,第212页。 梵高自幼精力过人,敏感颖悟,随时都有为宗教、“爱”、艺术献身的热情与真诚,个人生活艰辛不幸,生前做了许多事情却很少成功。1890年,他在法国奥维举枪自杀时,终其一生年仅37岁。梵高深刻的自我探寻呈露于留存于世的大量书信集及画作中,其中倾注了他深层的情感激流与含义深刻的内省思想,打开了一扇藉以了解他深潜澎湃的思想,与奋斗一生追寻“爱”、成功、被理解、被接受以及失败后深感绝望内心世界的窗口。
梵高有缘自超绝神与自我自由意志间的隔断,亦即“人神两分”的超然决断问题,与之形成对照的徐渭,此处涉及中国文化“超越性”的一番思想灵境。牟宗三在论中国哲学特质时谈到,天道高高在上,有超越意,天道贯注于人身又内在于人而为人之性,这时天道又是内在的。中国传统思想视域下,神性“超越”而非“超绝”,天道与人之间是一种“内在超越”“感通遥契”的关系④ 康德“超越”一词与“超绝”或“超离”的用法不大相同,“超越”是指某种先验(apriori)的东西,先乎经验而有,却不能离开经验而又返过来驾驭经验,此便是Transcendental 之义,往而复返。超绝或超离Transcendent,则是与经验界隔绝,完全隔离,一往而不返。牟宗三:《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5年版,第41页。 。传统视域下的神性,既超越又内在,心学思想秉承一以贯之的文化精神,良知是有限与无限、内在与超越的合一,在这样形而上与形而下融贯统一的思想架构下,现实人性中纵有气禀之限制与外在昏明开塞私意欲念之玷染,中国人无须承担西方宗教中无可超脱的“原罪”的永恒负累,认为人的本然善性充扩至极,便可上达至无限与超越之境,阳明曰:“心即理”,良知即天理,正所谓“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二程遗书·卷六》)。
朱熹的“理”,是一外在高悬、客观公共的法则,要用明净如鉴之“心”去合此外在公共的“理”,其中的断裂、隔离与伪诈的流弊不述。陆象山、王阳明将此理此法则直接放入人心,所谓“心即理”,“知善知恶是良知”,将明觉感应的超越良知内化至主体内心当中。在心学的哲学架构中,价值判断的主体惟有一个,那就是与天理、天道绵绵感通的人心,亦即天理天道辉映下的明觉良知。阳明“心即理”之“心”,并非梵高杂糅着理、气、情、欲于一炉的的混沌心灵,既非普通意义上所谓的“心”,而是从心中提取出超越灵明的存在名之为“良知”。心学思想肯认此良知心体的神圣超越,人人皆具此心,皆具此神圣的道德本体,故皆具此成圣之潜能,展露出此良知本体,人即可入超凡圣境。固然,自常识可知,现实中的一般人并非神圣,但惟人具有此神圣超越的良知本体为己之性体、心体、知体,当此良知、心体、性体、知体朗现,人即可至圣境。心学精神延续儒家传统,对人之本性怀有绝大的信念。“良知即理”,具有内在超越性,理与内在主体之心休戚相关,我之所思所为可遥契天道,是西方古典哲学家康德渴求并欲以揭示的真正的自由自律与责任义务。天道、天命既在我心,虽时常只是时明时昧,但本体自性具有“惺然复觉”,不容易涌现的自振力,而绝非永不可朗现的理想基型。
试验以P6为测试压头,分别在10,20,30mm/min速率下对果实进行压缩。果实在不同速率下的压缩曲线,都会出现明显的屈服极限点,压缩达到破坏极限时试样迅速破裂。不同压缩速度力——变形曲线如图3所示。从图3中可以看到各个压缩曲线的斜率相差不大,压缩速率越大其破裂极限越大。压缩速率为30mm/min时,变形量最大。
我院70例高血压患者进行此次研究(2015年12月7日至2018年3月5日),以随机基本原则为依据,均分为两组。
思想史上畸轻畸重的一丝偏倚会带来极不相同的路径与发展方向,作为阳明心学的直系后学,“从意之发用处说物”与“从明觉感应处说物”,会得出对本体与工夫的不同理解,现成派的龙溪与正统派的彭山业已产生了思想分歧。徐渭的思想深受阳明及其后学,特别是王龙溪与季彭山的影响,彭山是徐渭心悦诚服、亦师亦友之人,龙溪则与徐渭不仅是年岁相差颇大的姑表兄弟,更是他内心仰慕的老师。在徐渭看来,二者的思想并非本质上的冲突,而是对“见性明道”工夫论理解上的不同。明末心学“三教合一”的融贯精神与打通“身心之隔”切实有效的工夫论,徐渭自然结合了二者相异的思想。从晚年冲淡的诗文和时人的记述中,徐渭显然别有自得,“难以世谛测”。
对于精神追求颇高,尤其是有慧根并天赋异禀之人,其对精神的追求远超出其对普通物质的追求。当生命的层次超出世俗的名利,进入对纯精神追求的绝高层次时,就更容易领悟生命的无常与人世的无奈,于是,他们会更注重纯个人的精神修为、对纯精神的追求或者走向真正的信仰。牟宗三先生曾说,对于内心生命力强的人,内心不安宁正在于心灵未找到归宿,故任何事足以吸之,又不足使之安。东倒西歪,纷驰杂流,盖因所谓烦闷困惑即极度的不安所致④ 牟宗三:《生命的学问》,台北:三民书局1984年版,第159页。 。一般人或可安于某事或职业以系其身,但对精神生活有强烈追求的人则实非易事。徐渭与梵高同为天才横溢,个性偏颇又屡遭不幸的艺术家,却拥有曲径通幽处似是而非的人生结局与思想势态。
上文论述了田子坊空间中的民俗特征,可以看出,这些民俗与我们所熟知的民俗不太一样。在民俗主义泛化的背景下,我们需要面对这样的现实,并思考这样的民俗是否应成为民俗学关注的对象或带给民俗学新的视角。
四、结语:跨境域的中西思想品格
儒学传统中从来就有“敬”的观念,但即便在周初“敬天”的观念中,“敬”仍然不似基督教对上帝的敬畏,要求消解人的主体性而彻底皈依于神,反而是主体性愈发地凝重和凸显,将超越者内化到主体性当中。徐复观先生认为,周初强调的“敬”观念,与宗教的虔敬,近似而实不同,宗教的虔敬,是消解掉人自身的主体性,将自身投掷于神并彻底皈依于神。周初强调的“敬”观念,与之完全不同,是人内在的主体精神,向内消解、祛蔽官能的私意欲念于自己所负的自由自律的道德责任义务之前,从而极大地凸现主体道德理性、心体、性体、知体的积极作用④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台北: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2页。 。李泽厚先生对现代新儒家虽多有批评,但对儒家“敬”观念的理解,与徐复观、牟宗三相一致,认为“敬”不是指向对象化的外在神的确立与崇拜,而是在“敬”活动过程中,产生“神人一体”的感受和体会。从这里生发不出“超绝”“超离”的客观存在的上帝观念,而是将此“与神同在”的神秘畏敬的心理状态,理性化为行动的准则、规范与内在品格① 李泽厚:《己卯五说》,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9年版,第54页。 。
天命流行之体直贯下来而为人之性,“天命之谓性”,人又势必通过乾乾不息的努力,尽性知天,通过纯化“意”“念”的道德工夫,绵绵感通、遥契天命天道之下贯,这是一种双向交通、双向感通的过程。这其中的精义至明末清初大儒王船山处,得以更为精确地阐发,道德本体做出的价值判断,是君子之本分内事,不容不做乃是“义”,君子所务在“义”,不在不可知的“命”,“义”乃命之在我、义不容辞的自由自律、责任义务,这其中所蕴涵的类似于宗教的超越精神,远在西方哲学家所探讨的诸如“德福关系”的功利主义之上。秉承心学精神的徐渭,统合儒释道三者,懂得通过“致良知”以诚意的“意”之纯化工夫,使那“一点灵明”的天理良知下贯,未有曲折遮蔽,以天理、天道统合于我心,是为主体价值判断之所能及,既无梵高价值判断之“人、神分离”,亦无“心、理两分”的纠结困顿。
心学思想延续儒家传统精神,深信人的本然善性充拓之极,便可上达至无限与超越之境,尽管现实会有昏明开塞流行之气、私意欲念之习染,但人终无须承担永无超脱的原罪负累。后期的梵高用激烈、冲动的行动反抗加尔文宗教传统带给他黯淡的青年时光与原罪审判,徐渭一生坎坷:庶出、幼孤、入赘、八次科举落第,至死还是一个秀才,痛恨严嵩而被其党羽所用,精神失常,杀妻获罪,历尽了坎坷磨砺② 徐渭:《徐渭集》,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639页。 。出狱后已53岁的徐渭,艺术创作与生命的高峰方才启幕,晚年堪称适意,终以73岁高龄辞世。徐渭用和谐统贯的儒释道思想滋养心灵,陶铸修养并健全人格,点化现实生活中的酸辛苦楚,方有他“大乘闻讲后,小水看鱼流”③ 徐渭:《徐渭集》,第207页。 的自适自得,“脱屐尘缘,别有胸襟洒落。结庐人境,不妨车马喧阗”老庄、陶渊明式的道家隐居出世情怀④ 徐渭:《徐渭集》,第1169页。 。
方东美借肖伯纳之语,“生命中有两种悲剧。一种是不能从心所欲,另一种是从心所欲。”⑤ 方东美:《科学哲学与人生》,台北:黎明文化1989年版,第196页。 前者是古希腊神话被“命运的大箍”所钳制的悲剧,后者是欧洲近代浪漫主义精神影响之下,“上帝已死”,重估一切价值的从心所欲的悲剧。古希腊人的“命运”,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一切都被超绝之神规定,在此“命运”的“大箍之下”,人类无从逃离。叔本华认为,悲剧不在戏中英雄个人的自取咎戾、企图悔改,根本在于生存本身的罪根——“人之有生,罪孽深重。”⑥ 方东美:《科学哲学与人生》,第203页。 “命运”是西方哲学中孜孜以求的本质,至基督教产生后,“命运”转化为上帝。梵高的悲剧,恰恰源于近代欧洲浪漫主义“我心创造价值”之“从心所欲”,与加尔文宗教观念中“不可从心所欲”的双重悲剧。
浪漫主义精神预设了多元价值观的存在,所谓的“真诚”,即要誓死捍卫自己的真诚信仰的价值观,不惜与持有他者信念与生活方式的人抗争,决断彻底,直至一方或双方死去,妥协或调和是唯一不被接受的行为⑦ Berlin,Isaiah,“The Romantic Revolution:A Crisis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Thought”,收入其“The Sense of Reality:Studies in Ideas and Their History”.New York:Farrar,Strauss and Giroux,1996,p.186.并参见其“The Essence of European Romanticism”,收入其“The Power of Ideas”,p.200. 。偏重向外的对峙与抗争,终使内心深处“一点灵明”的良知混沌、遮蔽,不仅加重了价值判断“人”与“神”的对立,亦加剧了“心”与“理”的分裂。
梵高觉察到牧师“一点灵明”“良知明觉”的黯淡,牧师们在梵高“离经叛道”的某些特异行动中看到了彻头彻尾的“罪恶”。梵高认为牧师父辈心灵中的美好被错置,相互间的冲突与不理解源自根本相异的价值判断标准,他们的指责均未能击中要害,令彼此信服。梵高无从区分内在的本体之性与本能之性,更不愿谈到祛蔽私意欲念的干扰,复其良知性体,升进至天理、天道贯注人之本性的从善去欲工夫论。当人“日在世法中求性命”,在世俗世界中“头出头没”,遭遇“五欲熏染”之时,更难以相信内心之光明,良知之明觉,只得返回去重新依赖外在的信仰,认为人类灵魂的活力、爱、生命、希望以及信仰都是上帝所赐予的,人的罪恶、痛苦惟有依赖信仰方能得以减缓。无论是加尔文主义宗教,还是浪漫主义时代精神,最终都令他失望,一如尼采,梵高发掘到了一片虚无。
Entering with Confident Departure and Going with No Return:A Study of Cross-Border Thought of Xu Wei and Vincent Van Gogh
HUANG Lin1,2
(1.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Xi ’an Jiaotong University,Xian’710049,China;2.School of Marxism,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Xian’710072,China)
Abstract: Despite the prominence of Xu Wei and Vincent Van Gogh in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art history respectively,their thoughts have not drawn adequate attention among the academia.European Romanticism,as a revolt against the Enlightenment,holds the pluralism of culture and value,leading a real revolution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knowledge.Romanticism highly praises freedom and monopoly as well as finiteness and infinity,the uniqueness and detachedness of man and god,and the presupposed connection of binary op⁃position,which are displayed between value created by the heart and“God”who is aloof and absolute in rig⁃orous Calvinism,and it hence holds no space for the monism emphasizing internal transcendence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thought.Starting from the integration of Heart⁃Mind learning(Xin Xue )and internal transcen⁃dence of conscience,Xu Wei never experienced the dilemma of man⁃god and mind⁃reason separation.The analyses of their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can promote the clearer and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ideology and culture.
Key words: study of mind;Romanticism;internal transcendence;uniqueness and detachedness;Xu Wei;Vincent Van Gogh
[中图分类号] G0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4-1710(2019)02-0105-07
[收稿日期] 2018-09-03
[基金项目] 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5C007)
[作者简介] 黄琳(1980-),女,陕西西安人,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2015级博士研究生,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西思想史、文化史的比较研究。
[责任编辑:吴晓珉]
标签:心学论文; 浪漫主义论文; 内在超越论文; 超绝超离论文; 徐渭论文; 梵高论文;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论文; 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