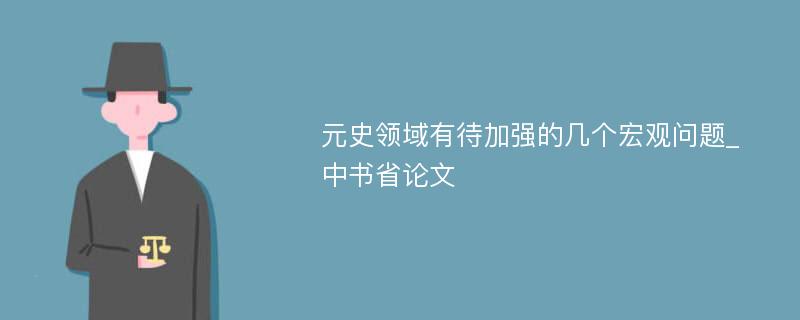
元史领域有待加强研究的几个宏观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论文,领域论文,元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元史研究,经过东西方学者数百年的努力,无论是微观还是宏观方面,都取得了相当多的重要学术成果(注:中国的元史研究,从明初修《元史》起,至今已逾600年;国外的元史研究,可以上溯到17世纪欧洲东方学初兴阶段。李治安、王晓欣先生著《元史学概说》(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一书对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的国内外元史研究成果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陈得芝师在白寿彝先生总主编的《中国通史》第八卷《元时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中对1995年以前的东西方元史研究重要成果作了甚为公允的评价,见该书上册第92—241页。);但是,由于蒙元王朝的独特性,使得元史研究的难度相对比较大(注:杨志玖先生认为元史具有世界性、多民族性和由它们带来的研究上的困难性等三个特点,见《关于元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原载《历史教学》1985年第4期,后收入其著论文集《陋室文存》,中华书局2002年版。),到目前为止,不论是微观的考订方面,还是宏观的论述方面,元史领域都还有不少研究相对不太充分的地方。就宏观方面而言,前辈学者已经指出了不少研究中的薄弱之处,如元代思想史、元代法制史、元代的医学、元代在中国史上的延续性等(注:陈得芝师说:“思想史写到元代就有点不够劲了,只剩下北许南吴,谈到理学只是提宋明理学。”见周少川:《元史研究的师承与创新——陈得芝教授访谈录》,《史学史研究》1998年第1期。陈高华先生在《20世纪中国的元史研究》一文中认为,“元代法制的研究,还只能说处于起步阶段”;“元代卫生医药状况,内容丰富多彩,可惜的是,迄今为止没有得到史学界的青睐”。该文载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所编《元代文化研究(第一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萧启庆先生在《近五年来海峡两岸元史研究的回顾》一文中指出:“对元朝在中国史上延续性之探讨应该是未来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该文收入其著论文集《元朝史新论》,台湾允晨文化公司1999年版。)。笔者在最近几年的元史教学和研究中,感觉还有一些宏观方面的问题有待深入探讨,笔者把它们写出来,希望和读者一道来考虑如何加强研究。
一、大蒙古国与历史上蒙古高原游牧政权有根本区别的社会制度是怎样形成的?
历史上有不少游牧民族在大漠南北建立过或暂或久的政权,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后确立的几项重要制度,如千户百户编组、分封、成立怯薛组织、编制成文法等,除了编制成文法以外,表面看来,其他几项制度在以前的游牧政权中也都出现过类似的现象。但是,如姚大力师指出的那样,此前游牧政权十进位的军事编制形式是以血缘外壳下的氏族部落为单位编组和调度游牧民战士的组织形式,是与氏族外壳并存、相对于氏族外壳处于补充和附属地位的军事性质的编制;而大蒙古国的千户百户编组则使得漠北历史上“氏族血缘外壳现在第一次被另一种划分游牧居民的组织形式所取代,原来的氏族核心家族的领属权被剥夺”(注:姚大力师:《塞北游牧社会走向文明的历程(一)》,张树栋、刘广明主编《古代文明的起源与演进》第十二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巴托尔德认为,游牧政权都有家产制的特性(注:巴托尔德(B.B.Barthold):《蒙元入侵前夕的突厥斯坦》(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米诺尔斯基(T.Minorsky)英译本第三版,伦敦1968年,第268页。),一方面把政权控制领域内的所有,主要是游牧部众看作仅属于核心部落集团统治家族——单于或可汗家族——的私产,另一方面,又将对游牧部众的统治权在这些家族成员以及往往与单于或可汗家族具有联姻关系的少数异姓显贵家族成员间进行分配。据姚大力师研究,蒙古之前的游牧政权实行分封时不打破原有的社会组织,分割的单位不是单个的游牧家庭而是被征服部族原有的社会组织,即氏族,分封的结果,形成上下两层领属权,“前者指核心部落集团首领家族对征服或归附各部的间接的政治、军事、统治的权力,后者则指处于上级领属权约束与限制之下,保留在臣服诸部原有君长手里的那一部分对部众的直接领属权”(注:姚大力师:《塞北游牧社会走向文明的历程(一)》,张树栋、刘广明主编《古代文明的起源与演进》第十二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学界公认,成吉思汗的分封在前述千户百户编组的基础上进行,结果使得领属权只在黄金家族成员间分割和继承(注:笔者认为,这种领属权后来还越来越集中到大汗或皇帝手里,参见拙文:《试论元代中央官制的本质和历史影响》,载刘迎胜主编《元史及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4辑,南方出版社2001年版。)。大蒙古国的怯薛制由建国前的那可儿制发展而来,此前的游牧政权首领也大都建立过首领军事侍从制度,但是蒙古族的那可儿制与它们相比有两点根本区别:其一,首领的那可儿除充当战士外还履行首领的其他使命,包括首领屯营内的诸色家务;其二,主要那可儿的来源是首领的斡脱古·孛斡勒,即因功而蒙恩的被使长看作亲信骨肉的家族世袭奴隶,由于斡脱古·孛斡勒是个荣称,所以那可儿成员中其他成员也会自动或努力使自己处于斡脱古·孛斡勒的地位。那可儿制发展成人员庞大的、职掌世袭的、帝国重要政务由其成员为之的怯薛制后,不仅主奴观念延伸到全体蒙古属民中,怯薛制本身更是巩固并加强这种主从隶属关系的工具(注:参见萧启庆:《元代的宿卫制度》,收入其著论文集《元代史新探》,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版;另参见拙文:《元代怯薛新论》,《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通过以上三种制度的建设,加上成文法的保障,一方面漠北高原上游牧民族的社会组织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根本性的变化,另一方面,大蒙古国大汗的权力也得到空前加强(注:笔者认为,由于斡脱古·孛斡勒制度、那可儿制度、怯薛制度的实行,使得蒙古大汗和其臣僚间形成主奴关系,这种主奴关系影响了后来元朝的君臣关系。见拙文:《论元朝君臣关系的主奴化》,《江海学刊》2004年第1期。)。
巴菲尔德认为,成吉思汗建立的大蒙古国与其说是漠北高原游牧政权的继续,不如说是它们的异数(注:巴菲尔德(Thomas Barfield):《危险的边界:游牧帝国与中国》(The Perilous Frontier: 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Blackwell 1989年版,第191页。)。萧启庆先生认为,大蒙古国的制度,一方面继承了北亚游牧民族的历史遗产,另一方面又融入了很多成吉思汗的创造(注:萧启庆:《蒙元支配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修正版)》。2004年天津元史会议期间,萧先生惠赠笔者此文打印稿,不详是否已正式出版。)。根据学界普遍的对蒙元王朝的认识,巴菲尔德所说的异数或萧先生所说的成吉思汗的创造,较之前的历史传统,对后来历史的影响更大。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根本变革是怎样形成的?简单地说,我们可以认为是成吉思汗个人的历史作为,但是如果能够在考虑历史的突变和个人的突出行为等因素之外,再从历史长时期的演变过程中进行分析,我们也许会得到更为合理的认识。这里,至少有两点因素值得考虑:第一,在大蒙古国政权之前,在漠北立足的游牧政权大多为操突厥语族语言的族群建立或其民众主要操突厥语族的语言,而据姚大力师研究,后来16世纪的哈萨克部落仍以血缘氏族为基础(注:姚大力师:《塞北游牧社会走向文明的历程(二)》,前揭张树栋、刘广明主编《古代文明的起源与演进》第十三章。);第二,蒙古族在建立大蒙古国之前,在漠北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渗透和与各部落融合的过程,这与之前游牧民族由壮大到建立国家政权相对比较迅速形成较为鲜明的对比。由于史料的缺乏,早期蒙古社会的研究目前做的实际上还很不充分,如何解释大蒙古国的制度建设就比较为难。我们是否可以在依托历史史料的基础上,充分借鉴人类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来对这一问题做进一步的研究?像《元朝秘史》以及中国历代正史中少数民族的传记材料其实是很好的人类学研究素材,但从人类学角度对这些材料进行分析目前做得似乎不够。也许,当我们换一个角度,从人类学视角切入,再来分析这些材料时说不定会得到意外的收获,从而对本节所提的宏观问题作出比突变论更为合理的解释。
二、大蒙古国的政治制度是如何过渡到元朝的政治制度的?
大蒙古国的主要政治制度除了上述的分封、怯薛外,还有一项大断事官制。大断事官群体及其属僚——最重要的属僚是作为文书官的必阇赤——形成大蒙古国最重要的行政机关。这种政治体制学界没有异议,认为是蒙古制的。忽必烈继位后,成立了中书省,此后除了少数时期和尚书省并立且其职权大多被后者侵夺外,中书省一直是元朝重要的中枢机构。学界普遍认为忽必烈建国后,在中枢机构的设置上采行汉法,即中原王朝传统的政治制度;他所建立的中书省是中原王朝宰相制度的发展,在元朝各种机构中处于核心地位,尽管保留了一些蒙古制的残余,但已经不占主导地位。现在的问题是,蒙元王朝的政治制度是怎样由以大断事官群体为行政中枢的蒙古制变化为以中书省为核心的汉制的?和上面一个问题一样,我们也可以认为是忽必烈的个人所为,但是用突变论解释历史往往会把复杂的历史过程看得过于简单。
一些学者曾经试图对这一变化作深层次的解释。李涵、杨果先生认为中书省由大蒙古国时期的燕京行尚书省和中书省演变而来,这两个机构是汉式的(注:李涵、杨果:《蒙古前期的断事官、必阇赤、中书省和燕京行省》,收入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编《元史论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但是,大蒙古国时期所谓的中书省其实是一帮必阇赤的群体,燕京行省则是汗廷大断事官群体在燕京的行署,大蒙古国时期并不存在汉式的中书省和尚书省,一些官员身上的所谓丞相、中书令等名号都源于汉人的比附。张帆先生认为汉式中书省的建立,是因为大蒙古国大断事官机构中作为主要幕僚的必阇赤游离了出来(注:张帆:《元代宰相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7页。)。但必阇赤如何游离,又有什么证据,他都没有详细说明。姚大力师认为,忽必烈即位之初建立的中书省仍然是之前大断事官群体的继续,但随后其中的必阇赤(很多是当时地位较高的汉人)就从中游离了出来;由于他们地位较高,受到忽必烈的信任,得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建立汉式的中书省(注:姚大力师:《从“大断事官”制到中书省——论元初中枢机构的体制演变》,《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笔者认为,姚师的论述高估了忽必烈对汉文化的理解和对汉人臣僚的信任,因而影响了文章的结论(注:参见拙文《论元代中书省的本质》,《西北民族研究》2003年第3期。)。
笔者看法,要不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合理的解释,要不我们是否可以换一个角度,重新审视一下元代的中书省到底是以汉制为主的还是以蒙古制为主的?我们可以找到一些证据,说明元代的中书省与中原王朝历史上的宰相机构有较大区别,而与大蒙古国时期大断事官机构则有不少共同之处,很可能中书省只是大断事官群体的继续,而不是中原王朝宰相制度的自然发展;也就是说,中书省更多体现的可能是蒙古旧制而不是汉制(注:参见拙文《论元代中书省的本质》,《西北民族研究》2003年第3期。)。
通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笔者觉得还可以对元代的政治制度作更深的研究。当今的元史学界一致认为,忽必烈建立的元朝,其政治制度是二重的,并没有简单地采用汉法;具体到某一项政治制度,是汉制为主还是蒙古制为主,需要仔细分析。姚大力师认为元朝政治制度中的二重因素是镶嵌在一起的(注:参见其博士论文《论蒙古游牧国家的政治制度——蒙元政治制度史研究之一》,南京大学博士论文打印稿1986年。),这一看法似有些含糊。根据笔者的思考,元代在临民层次更多采用了中原王朝的政治体制,即比较多地采用了汉法,但临民层次之上,情况未必(注:参见前揭拙文《论元代中书省的本质》、《试论元代中央官制的本质和历史影响》。)。
三、元代的经济在中国经济史上的地位如何?
元代经济史的一些具体领域,如土地占有状况、水利事业、手工业、商业、畜牧业以及交通运输等,中外学者已经做了相当精深的研究,农业发展的基本情况和区域经济学者们也做了有益的探讨(注:参见前揭李治安、王晓欣著《元史学概说》,第121—147页。)。但元代经济在中国经济史上的地位如何,则是一个明显的研究不够深入的地方。李剑农、漆侠等先生认为元朝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与宋代相比,出现逆转现象(注: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9页;漆侠:《中国经济通史·宋代卷(上)》,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33—35页。);国外学者伊懋可也认为在14世纪的某个时候,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开始发生改变,导致中古经济活力消失(注:伊懋可(Mark Elvin):《中国过去的模式》(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斯坦福1973年版,第203—204页。)。经济逆转说由于过多想当然的推理,已经逐渐被学者们放弃。韩儒林先生认为,元代社会经济北方逐渐恢复,江南与南宋持平,部分地方有所增长,尤其是边疆地区;经济发展形势是前期由恢复到发展,中后期由发展到停滞、衰敝(注:韩儒林主编《元朝史》,序言,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韩先生的看法分析中肯,说服力较强,已经为多数学者接受。但是韩先生实际上并没有对这一观点做详细的论证,他主编的《元朝史》及此后主要由其门人参加编撰的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元时期》均采纳此观点,但也都没有做深入的论证(注:两书都对元代经济的各个具体方面做了尽可能详细的阐述,对韩先生的论点也做了一定的说明,但都显得不够深入。)。再有,韩先生的观点有一些含糊的地方。“恢复”、“增长”、“停滞”、“衰敝”,具体到什么程度?江南与南宋“持平”,标准是什么?总产量、人均产量还是亩产量?抑或是经济效率,即产出和投入的比例?韩先生观点中含糊的地方不加以解决,实际上就很难回答元代经济在历史上的地位问题。比如,我们就算知道元代几种产量和宋代都持平,但估算不出经济效率,就不能肯定地说元代经济是比南宋落后还是发展或者持平。新近出版的陈高华、史卫民先生著《中国经济通史·元代卷》(注: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对这一宏观问题也没有做细致的讨论。
李伯重先生认为,“过去我国学者一向偏重于从生产关系,特别是阶级关系出发来研究经济史。如果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这种做法实际上只是从一个视角来看过去的经济实践,而过去的经济实践绝非仅包括生产关系”(注: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页。)。元代经济史的探讨,笔者觉得,在经济实践的生产关系之外,主要是生产力方面,也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研究不足,这直接导致了对元代经济地位如何这一问题的回答显得有些不够底气。
笔者认为,生产力方面包括投入、生产过程、产出和经济效率这几个因素。以农业为例,投入方面,有人口、耕地、农耕技术等。人口方面需要考虑总人口、城乡人口比例、农村投入农业人口比例、人口年龄层次比例等;耕地方面,需要考虑耕地数量、品质等;农耕技术方面,需要考虑水利、农具、肥料、耕作技术以及各方面的配套等问题(注:参见李伯重《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0—126页。)。生产过程方面,有气候变化、种植制度、经营方式等因素或环节。气候变化以及伴随而来的水旱、蝗虫等灾害对农业的影响,在中国古代是很明显的。种植制度中要考虑作物品种、轮作休耕制度等。经营方式方面,要分析是把土地转租还是自己耕作。另外还要考虑家庭的经营规模,比如有多少劳力投入了农业生产(如果从事商业更有利可图,就会有一部分人脱离农业),耕作能力如何。产出方面,要考虑总产量、亩产量、人均产量等。经济效率是最难估计的,也是最能反映元代经济地位的,需要对投入和产出的各个因素进行综合统计、分析。学者们对元代经济与生产力相关的诸多因素,有的已经做了透彻的研究,有的虽做了研究但显得还很薄弱,有些问题甚至可以说基本上没有涉及。笔者认为,对这些问题的研究,除了依靠历史学的传统史料考证方法以外,还需要借助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以及自然科学的一些成果,不然可能会出现研究上的失误(注:比如,李伯重提到,许多学者根据史料记载认为南宋江南水稻亩产达到三四石、五六石乃至六七石,“从物质能量转换的角度来看是无法解释的”。参见前揭《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第5页。)。
四、元代汉族智识阶层是怎样看待蒙元王朝统治的合法性的?
由于资料的零散和限制,元代社会史的研究一直比较薄弱。相对而言,社会生活这一块解决得比较好。史卫民先生著《元代社会生活史》(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陈高华和史卫民先生合著《中国风俗通史·元代卷》(注: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是目前最重要的两部研究论著。此外,相关的学术论文还有不少。特别是近年来,由于社会史研究受到史学界的重视,各种刊物上的元史论文,也较多涉及社会生活内容。但是社会史不仅仅只是一般的衣食住行方面的社会生活,它还有更广泛的内容,比如民众的生存状态、社会意识、彼此之间的关系等。这些方面的成果应该说也比较丰富。邵循正先生的《元代的文学与社会》(注:此文重刊于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82年。),尽管作于半个世纪以前,至今仍为经典之作。陈高华、萧启庆等学者对元代儒户、军户、站户的生存状态作过精细的研究(注:陈高华:《论元代的军户》、《论元代的站户》,均收入其著论文集《元史研究论稿》,中华书局1991年版。萧启庆:《元代的儒户:儒士地位演进史上的一章》,收入前揭论文集《元代史新探》。)。阶级关系的研究在中国大陆更是有比较深厚的基础,尽管不少结论值得推敲。但总的来说,对社会生活之外的广泛的元代社会史的研究,力作比较少一些,正如《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所说,“重构元代社会史的任务艰巨,现在刚刚开始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注:史卫民等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30页。)。比如,妇女在丈夫死后不许再嫁的陋习在元代,尤其是在元代的江南地区,比起前代来,大为盛行,并且直接影响了后世。妇女贞节观的盛行,理学官方化自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元代普通妇女的生活状况,例如婚姻的稳固程度、家庭成员间的感情状况、家庭和妇女本身的经济能力等也是重要的原因,但至今我们尚未见到对这一现象有深度的研究。
在社会意识方面,元代汉族智识阶层是怎样看待蒙元王朝统治的合法性的,这一问题也没有得到系统的梳理。由于蒙金战争的摧残和其后儒士入仕途径的大幅受阻,元代汉族智识阶层的地位大大不如其他中原王朝,但是,他们在民间社会仍然作为精英阶层存在,他们对蒙元王朝政府的认同或抵触无疑会直接影响到一般的民众(注:《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说:“外族上层掌握真正权力的现实,既没有消除中国社会对文人的崇尚,也没有完全摧垮被征服者中原来属于社会上层的那些人的经济实力。就是说,汉人士大夫们尽管与高官无缘,但仍旧被百姓看做是地方社会的领袖。”见前揭该书中译本第722页。)。中国历史上有过多次非汉族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的事,按照很早就形成的“文化至上主义”和“天下中国观”的理念(注:关于“文化至上主义”和“天下中国观”两种理念的形成,参见兰德彰(John D.Langlois Jr):《中国文化至上主义和元代的类似性》(Chinese Culturalism and the Yuan Analogy),《哈佛亚洲研究杂志》(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卷40,1981年;罗志田:《先秦的五服制与古代的天下中国观》,收入其著论文集《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版;姚大力师:《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国家认同》,载刘东主编《中国学术》第12辑,商务印书馆2002年。),即只要能够坚持“用夏变夷”的文化策略,坚持天下中心地区理应唯有一国可忠诚、分裂状态以及一个民族集团或政权对另一民族集团或政权的征服战争都只是为实现那个唯一的国家作预备的信念,那么汉族人从政治上接受被认为是蛮夷的非汉族的统治是完全可以的,尤其是对于生活在北方的亡金儒士来说,这一地区本来就长期经受过非汉族的统治,他们接受蒙古人的政权应该不成大问题。对于南宋儒士来说,尽管他们也抱有传统的文化至上主义和天下中国观的理念,但两个明显的事实使得他们接受异族统治会显得困难一些:其一,从北宋开始对一姓王朝忠诚的理念以及明“华夷之辨”的思想都得到加强;其二,蒙元王朝对南宋的征服使有史以来中国第一次整个地置于非汉族的统治之下,汉族儒士服膺的汉文明遇到从未经受过的可能会在它业已退守的南部中国被完全摧毁的严峻挑战。当然,总的来说,原先南宋地区的汉族儒士也大多承认了蒙元王朝的合法性,虽然产生了一定数量的遗民;只是他们的调适过程学界还没有研究清楚。
南北智识阶层大多承认蒙元王朝的统治,显然同“能行中国之道,则为中国之主”的思想意识有关。问题是,蒙元王朝的各种典章制度、统治方式尽管从表面上看来,很大程度上纳入了中原王朝的政治传统(注:忽必烈和其后的元朝政府主要采纳汉法,只是保留着一些影响不大的蒙古传统残余,一直是学术界流行的观点。另一部分学者则对此作了修正,认为元代各种典章制度、统治方式均可看作是蒙古传统和中原汉法的二元混合,二元之中,很难笼统地说哪一种因素占有主导地位。不论是流行观点还是修正观点,其实都没有对汉法和蒙古传统作出严格的界定。笔者认为,在对元朝的总体认识上,对汉法内涵未作明确界定是目前学术研究中一个比较大的缺憾。),但是蒙古人的政府始终未能与汉人的理想模式合拍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就是说,蒙元政府在行中国之道上,是大大打了折扣的,处于其中的汉族智识阶层又是怎样看待政权的合法性的呢?华涛先生认为,公元10世纪以后,“汉人社会在弱势环境中发展出了一种对本民族制度、思想、文学、艺术、生活、社会、情趣等各方面的全面的崇尚,并在这种全面的文化崇尚中寻找精神寄托和精神避难所”(注:华涛:《文明对话与中国传统文化范式中的障碍》,《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这一观点对我们有很大启示。元代政府没有汉化,但在汉人于自己本民族文化中寻找精神避难的过程当中,是可以用汉文明吸引蒙古、色目人的,包括他们中的上层人士。笔者猜测,这可能是在元朝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内,汉人儒士的一个相当普遍的想法。元代的事实也显示用汉文化吸引外族个人是可以有很大成效的。随着各族士人的相互交往,出现了不少汉学修养相当突出的蒙古、色目士人,上层集团也越来越多地受到汉文化的影响(注:关于元代色目人的汉化,参见陈垣先生的《元西域人华化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关于蒙古人的汉文化修养,参见萧启庆先生:《元代蒙古人的汉学》、《论元代蒙古人之汉化》,二文均收入其著论文集《蒙元史新研》,台湾允晨文化公司1994年版。),元朝政权的合法性在士大夫意识中仍然能够得以维系。不过,元代蒙古、色目上层的观念意识尽管不断受到汉文化浸润,但种族意识的反弹也是非常强烈的,南坡之变、伯颜要求杀五姓汉人便是突出的例证。这无疑会让汉人儒士大为失望,而元政府内部屡屡发生的上层倾轧更会使其合法性产生危机。《剑桥史》作者因此认为,元代后期,只有很少的汉人还对蒙古人受命于天的正统性表示怀疑,“更多的人则开始预言蒙古人将很快失去天命”(注:前揭该书中译本,第712页。)。关于元代汉族智识阶层对蒙元王朝统治合法性的认识,以上仅仅是个相当粗疏的概括,而且不一定准确,实际的细节还有很多值得探讨的地方。比如,元朝后期政府合法性的危机,在不同的人意识中肯定程度不一,而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士人又当如何处事、如何面对王朝更替,其心态如何,这些都是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