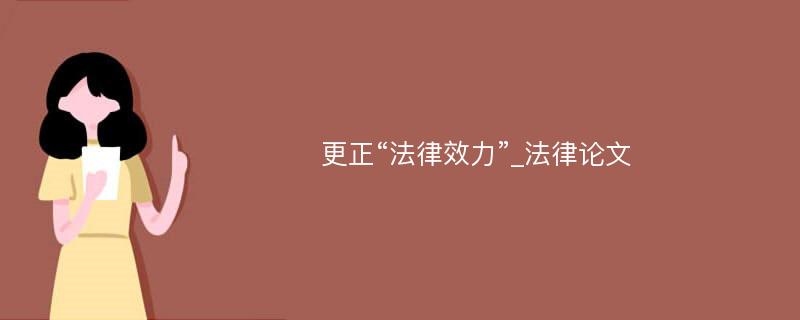
“法律效力”辨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律效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法律效力”是法理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历来被作为一个自明概念使用,释为“法律的约束力”。因此,在一般教材、专著及工具书中,当述及“法律效力”时,大多直接讲述其时间、空间和对人效力范围。《法学研究》1994年第4期刊载了陈世荣同志《法律效力论》, 1995年第2期又刊出了李琦同志与陈世荣同志商榷的文章, 双方观点大相径庭。看来,“法律效力”并非自明概念。对此,笔者不惴冒昧,直抒管见、以求辨正。
1、对立的“两说”
陈世荣同志文章(以下简称“陈文”)认为:“法律效力是指,法律及其部分派生文件、文书所具有的,以国家强制力为保证的,在所适用的时间、空间范围内,赋予有关主体行使其权利(或权力)的作用力以及约束有关主体履行其义务(或责任)的作用力之总和。”在具体阐释这个定义,说明法律效力的表现形式时,陈文认为,法律的基本成份或核心内容是法律规范,因此,法律效力是法律规范所具有的,也必须通过法律规范才能体现其效力,即法律效力是法律规范所具有的各种作用力之总和。对于此种观点,笔者将其称之为“法律效力的规范说”,简称“规范说”。为了加强这个观点,陈文否认行为具有法律效力,指出:“行为,无论违法行为还是合法行为,都一概不具有法律效力。”并对此作了不少论证。
李琦同志的文章题为:《法律效力:合法行为发生法律上效果之保证力——兼与陈世荣商榷》(以下简称“李文”)。李文认为:“规范性法律文件及其派生文件、文书所具有的法律效力实质上是立法行为和法的实施行为所具有的法律效力。如果抽去了合法行为,则绝没有所谓法律效力的存在。”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李文的意思当是:法律规范及派生法律文件、文书本身并无法律效力,其所以有法律效力,不过是合法行为的法律效力派生的;所以,如果抽去合法行为这个源头,就绝没有法律效力的存在。对于这种把法律效力归之于合法行为,否认法律规范自身具有法律效力的观点,笔者将其称之为“法律效力的行为说”,简称“行为说”。
“规范说”肯定法律效力是法律规范所具有的,只承认法律规范才具有法律效力,否认行为自身具有法律效力。“行为说”则肯定法律效力是合法行为所具有的,离开了合法行为,就根本不存在所谓法律效力。显然,两种观点是根本对立的,没有调和的余地。对此,我们该怎么办?
2、从语义说起
法律效力,从语义上说都是指“法的效力”或“法律的效力”。不妨作一些引证:
《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中无“法律效力”,有“法的效力”,指“法的生效范围,即法律规范对什么人、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间发生效力。”[1]
孙国华主编:《法学基础理论》中,无“法律效力”,有“法律规范的效力范围”,主要讲“法律规范在时间上、空间上和对人的效力范围。”[2]
沈宗灵主编:《法学基础理论》中,表述为“社会主义法律效力”,认为法律效力有广狭两义解释:“从广义上说,法律效力是泛指法律的约束力。……狭义上的法律效力,是指法律的具体生效的范围。”[3]
张贵成、刘金国主编:《法理学》中,专章讲“法律效力”,分别讲述了法律的时间效力、空间效力和对人的效力。[4]
张文显著:《当代西方法学思潮》中,专章叙述当代西方“法的效力”问题,亦无“法律效力”,认为“法的效力,即法对其所指向的人们的强制力或约束力。”[5]
周永坤、范忠信著:《法理学》中,无“法律效力”,有“法的适用范围——法律效力”,认为法的适用范围就是法律效力,指“法的约束力所及的范围。”[6]
从以上引证看,很多著名学者都不直接提为“法律效力”,而将其表述为“法的效力”、“法律的效力”、甚至“法律规范的效力”。所以,夏华、倪振锋同志早就指出:“‘法律效力’、‘法的效力’或者‘法律的效力’这些词,在法学中是指同一概念。”[7]
由此可知,法律效力从语义上说就是指法律的效力。在这里,“法律”一词从语法上说是作定语来限定“效力”的,表明这种“效力”不是其他什么东西的效力,而只能是“法律的”效力。既然“法律效力”从语义上说是指法律的效力,对法律效力的“规范说”和“行为说”从语义上就比较容易辨正了,因为,我们现在只要明确“法律”这个定语是什么就行了。什么是法律呢?不管怎么限定,法律总是“……规范的总和”,而不是“……行为的总和”。所以,原则上我们选择了支持“规范说”。法律效力只能是法律规范所具有的某种力,离开法律规范,才真正不存在任何所谓法律的效力。当然,如果接受西方之现实主义法学,将法律理解为法官的行为(判决)或人们对判决的预测(行为)的话,“行为说”也许有了依据。不过,这并不是将效力赋予行为,而是将“行为”等同于法律而已。
3、陈文之失误
我支持“规范说”,并不等于陈文就没有问题。恰恰相反,陈文之所以受到挑战,就在于陈文有问题,其主要失误,就在于存在理论上的矛盾性和不彻底性。
陈文的理论矛盾在于:一方面,肯定“法律效力及其表现形式,基本上都要通过法律规范得以体现”,从而坚持了“规范说”的基本观点;另一方面,又承认“派生文件、文书”等非规范性法律文件也自身具有法律效力,将其和规范性法律文件等同起来,这又背离了“规范说”的基本观点。李文抓住了陈文的这一矛盾,是非常准确的,确实值得商榷。
陈文理论上的不彻底性在于:既然肯定了法律效力及其表现形式都要通过法律规范得以体现,就不应该将法律效力赋予非规范性法律文件自身。这样,在定义中就应该删去“及其部分派生文件、文书”,才能坚持彻底的“规范说”。
一句话,陈文的主要失误在于在肯定法律效力是法律规范所具有的同时,又承认非规范性法律文件、文书自身也具有法律效力。那么,我们如果只承认法律规范或规范性法律文件自身具有法律效力,否认非规范性法律文件自身具有法律效力,在理论上是否成立呢?其实,这个问题早就有同志解决了。夏华、倪振锋同志曾写道:“非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法律效力是从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法律效力中引伸出来的,是一种次生状态。”[8]显而易见的是,任何非规范性法律文件, 如果没有规范性法律文件作依据,或者违背了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法律规范,就绝没有法律效力。例如,一份判决书,如果不是依法判决,何来法律效力?一份合同书,如果违反了法律规范,也决无法律效力而只能是无效合同。一切派生法律文件、文书之所以具有法律效力,只在于它“依法”,其法律效力完全是所依之“法”派生出来的。所以,非规范性法律文件自身并不具法律效力,它的所谓法律效力源于所依之规范性法律文件包含的规范,它的法律效力不过是法律规范的法律效力产生实效的手段而已。
基于此,我认为在为“法律效力”下定义时,应将“及其部分派生文件、文书”去掉,只需“法律具有的”就可以了,甚至直接提为“法律规范所具有的”,也未尝不可。遗憾的是,陈文没有这样做,以至造成理论上的矛盾性和不彻底性。并且,正由于有这样的严重失误,使李琦同志不得不去寻求法律和派生文件、文书在“法律上的同一性”,并由此提出了“法律效力的行为说”。
4、行为自身也不具有法律效力
李琦同志认为,既然陈文将派生文件、文书和规范性法律文件都作为法律效力的发生根据,那么,从逻辑上说它们就必然存在“法律上的同一性”作为其具有法律效力的最终共同根据。这一思路无疑是正确的!但仅有正确的思路并不等于就有正确的结论。因为,真正说来,这个“法律上的同一性”不是别的,正是法律或法律规范自身。遗憾的是,由于李文同样忽视了规范性法律文件和派生文件、文书的效力等级,而认为这个“法律上的同一性”是“合法行为”。因为,法律及其派生文件、文书都是因特定的合法行为而生成的,离开了合法行为,绝没有法律及其派生文件、文书的存在。因此,法律效力应该是合法的立法行为和合法的法律实施行为的效力,合法的立法行为与法的实施行为才是法律效力本质性的存在。
将“合法行为”作为法律效力的发生根据,存在着以下明显的问题:
首先,什么是合法行为?一个行为合法与否,必须首先有一个所合之“法”作为判定之根据,否则,我们绝对无法判定此行为是合法还是违法。正如李文自身所指出:“只有立法行为合法(程序与实体二个方面),作为该行为结果的法律规范才能具有‘法律效力’”。明显地,立法行为要合法,就必须有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的法律(规范)根据,如果没有这个根据,或者这个根据自身都无法律效力,哪来合法行为?当然,这个根据(法律)的效力,也许还可以推到更高的“合法行为”。但是,不管我们怎样推,只要是“合法行为”,就必有所合之“法”作根据,即便是“神法”,亦或“自然法”,也不可或缺。因此,只能说法律是合法行为的根据,而不能说合法行为是法律的根据。国家制定和认可的只是法律,不是行为;行为只有依据法律才会具有合法性。所以,合法行为本身也不具有法律效力,它如果有法律效力,也不过是从所合之法中引伸出来的;如果没有法律,合法行为自身都不存在,还有什么合法行为的法律效力?
其次,法律效力的作用对象是什么?法律效力作为一种力,它必有作用对象;如果没有力的承受者,我们何以知道会有这样一种力?那么,法律效力的作用对象是什么呢?不是别的,正是行为!大家都会说:法律是“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行为规范的总和”[9]。 既然是行为规范,它强制调整(规范)的就是人们的行为。因此,法律效力作用的对象是行为。这里的行为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它不仅指人们一般的作为和不作为,而且也包括立法行为和法律实施行为。可见,是法律的效力作用于行为,而不是行为的效力作用于法律。既如此,立法行为和法律实施行为都必须受法律效力的作用,我们怎么能说合法行为是法律效力的发生根据呢?
再次,如果说合法行为是法律效力的发生根据,那么,法律的地位何在?根据李文的观点:“法律效力既为合法行为所具有,复又作用于特定行为”,而所谓“合法行为”又无所合之法作为其效力的法律根据,即自身就具有法律效力,那么,还需要法律干什么?国家就根据无效力根据的所谓“合法行为”去调整各种关系就行了。所以,断言“合法行为作用于“特定行为”,否认合法行为的法律效力来自法律的观点,是一个可能危及法律的权威的危险结论,是难以令人接受的。
因此,我认为,合法行为本身并不具有法律效力,如有法律效力,也不过是它所合之“法”所包含的法律规范赋予的。只有法律规范才是法律、派生文件、文书及合法行为的法律效力在“法律上的同一性”。
5、法律效力的表现形式
按陈文的意见,法律效力既然“基本上都要通过法律规范得以体现”,因此,按法律规范的分类就可以找到体现法律效力的相应表现形式。这在逻辑上是成立的,其结论也基本正确。但李文对“职权性规范”的作用形式有质疑,认为“并非所有的职权性规范都包含了‘约束的作用力’,那么绝对地认定法律效力‘在职权性规范里,则既表现为赋予的作用力,又表现为约束的作用力’就显为不妥了。”其实,这一质疑意义甚微。因为陈文并未断言“所有的……都包含有……”,只是说“……具有……”。陈文并未绝对,这正如我们说“砂子中有金子”,并不等于说“所有的砂子中都有金子”一样,是可以理解的。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李文为我们提供了认识法律效力表现形式的更好思路。
只要是现行法律,就必有法律效力。但法律效力要真正表现出来,却只是在其发生实效的时候。任何法律,当人们自觉或不自觉的遵守时,其效力内含于法律规范之中,无从表现。实际上,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并未清楚地意识到法律效力的存在。只有当法律在运行过程中发生障碍时,法律效力才发生实效,有了现实的表现形式。所以,李文认为:“法律效力实际上是对合法行为的保证力,是为合法行为提供了一种保证功能。”不过,李文认定“对合法行为的保证力”是法律效力的实质又是不妥的。因为,保证合法行为的正常实施,对受到侵害的合法行为提供法律保护或救济,对与合法行为相关的其他行为给予约束,这些,都是法律效力在作用于行为、产生实效时的现实表现,将这些现实表现概括起来,就是“对合法行为的保证”。因此,“对合法行为的保证力”应该是法律效力的表现形式之一。
与此同时,法律效力还作用于违法行为。它对违法行为发生实效时是一种追究力,给违法行为主体以应有的惩治,对违法行为的追究力也是法律效力的表现形式。法律效力正是以对合法行为的保护力和对违法行为的追究力这两种形式,使“应有秩序”变为“实有秩序”,从而实现法律的目的。李文对法律效力对违法行为的作用是有所忽视的,因为就李文所说的约束力而言,只针对了“特定合法行为之外而与之相关的行为”,其目的是“使合法行为的法律效果处于安全状态”。然而,很多违法行为却没有与之直接相关的合法行为,例如,走私、贩毒、盗卖地下文物、以及某些不当得利,等等。对这些违法行为的追究和惩治,都是法律效力的重要表现。由于这些违法行为没有与之直接相关的特定合法行为,给予追究就不是“使合法行为的法律效果处于安全状态”,而只是实现一种“应有秩序”。所以,仅强调法律效力是对合法行为的保护,忽视其对违法行为的追究是不妥的。由此,我认为,法律效力的表现形式是:对合法行为的保证力和对违法行为的追究力。
6、法律效力的实质
笔者既然把“对合法行为的保证力”理解为法律效力的表现形式,自然就不同意说“法律效力的实质是合法行为发生法律上效果的保证力”,因为这种保证力是在法律运行时发生实际法律效果而明白表现出来的。
效力是法律的特征,而不是行为的特征。那么,法律为什么会有效力呢?它的实质到底是什么呢?回答只能是:法律效力来自国家权力,它的实质是“国家强制力”。
对此,西方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观点颇耐人寻味。在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家看来,法律不过是一个规则(规范)体系;一个规则体系之所以能成为法律,就在于它能生效而具有法律效力。拉兹就把“是否法律”看成是法律“借以生效并认定其内容的那些事实”[10],这就是把能生效(有效力)视为“是否法律”的标准。那么,法律何以能生效(有效力)呢?凯尔逊主张是“基本规范”之层层授权,哈特则主张是“承认规则”之认可。他们都受其规则体系的限制,走不出规则的圈子,因而不知道法律生效(有效力)的真正源头和实质,反而不及奥斯丁将其归之于“主权”有说服力。因此,拉兹感到,要解决这个认定法律的标准问题,即“法律的同一性”问题,必须把法律与国家联系起来才说得清楚。由此,他断言:“以国家权力为后盾是国内法的一个特征。”[11]
这是一个走了一圈才走出凯尔逊最高基本规范是一个“假定”的怪圈的正确结论。它告诉我们,要认识法律效力的实质,仅着眼于规范体系之内是无法解决的。在这一点上,我国法学界历来没有误入歧途,将来也不会误入歧途。夏华等早在《法律效力新论》中就将法律效力定义为“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约束力”,陈文也分析了法律效力与国家强制力的关系。在我看来,离开了国家权力,就没有真正的法律;离开了国家强制力,就绝没有什么法律效力的存在;法律效力不过是国家强制力的法律表现而已。因此,国家强制力才是法律效力最根本的存在,才是法律效力的实质。
7、结论
综上所述:法律效力的载体(发生根据或实体性主体)是法律,法律效力的实质是国家强制力,法律效力的表现形式是对合法行为的保证力和对违法行为的追究力。因此,我对法律效力作如下定义:“所谓法律效力,是指法律所具有的、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对合法行为的保证力和对违法行为的追究力的总和。”*
注释:
[1][9] 《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9月版,第85页、第76页。
[2]孙国华主编:《法学基础理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414页。
[3]沈宗灵主编:《法学基础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392页。
[4]张贵成、 刘金国主编:《法理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12章。
[5]张文显:《当代西方法学思潮》,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391页。
[6]周永坤、范忠信:《法理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6月版,第320页。
[7][8]夏华、倪振锋:《法律效力新论》,载《政治与法律》,1988年第3期。
[10][11]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207页、第21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