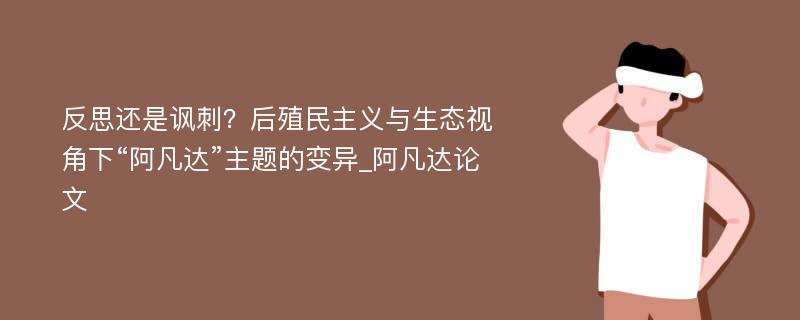
反思还是反讽?——后殖民与生态主义视野中的《阿凡达》主题变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变奏论文,视野论文,生态论文,主义论文,阿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十二年一轮回!如果说1997年卡梅隆(James Cameron)的《泰坦尼克》(Titanic)因其所展现的灾难中的人性光辉而被西方媒体誉为最接近共产主义思想的好莱坞电影之一的话,那么该导演蛰伏十二年之久,于2009年年底所推出的《阿凡达》(Avatar),却试图在另一个星球从根本上彻底解构人性——凭借着批判西方殖民历史,抨击资本主义扩张中的文明冲突,甚至是对人类中心主义与文明进步论的质疑与解构,该片从伦敦——这一人类历史中头号殖民帝国首都——的首映式出发,一月内挑战着全球大众视觉极限和固有思维模式,掀起了无数的狂热与追捧。美国学者在其中看见美洲大陆血腥的殖民史、古老文明的灭绝及21世纪美国在阿富汗与伊拉克的能源掠夺与扩张;中国观众在比照中看见自身生存的无奈;绝望的巴勒斯坦抗议者们则扮成影片中纳美人的形象,不顾一切地冲向以色列占领当局设置的森严铁丝隔离网……一时间,在这个视觉媒体取代阅读的时代,《阿凡达》俨然以新的左派文化代言人的身份跃上娱乐与政治舞台。
如果回到《阿凡达》剧本所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电影本身,我们会发现,作为一个后现代大众文化与好莱坞传统的左倾氛围的杂糅体,《阿凡达》实际上具有对殖民历史特别是美洲殖民历史与同类题材电影的强烈指涉,也存在对各类文化批判理论的显性或隐性的借用,但是否这就是影片的终极意义所在?答案也许是微妙的。
二、指涉与借用
《阿凡达》的剧本于1994年问世,这个年份及之前所连续爆发的几件相隔甚远却又紧密联系的事件,深深地震撼着美洲大地乃至整个世界。一方面,1 992年欧美乃至整个白人世界各处隆重集会,纪念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500周年——在这里,欧洲文明的所谓曙光照亮黑暗,进步战胜落后,文明征服野蛮的“壮举”又一次得到确认。在柏林墙坍塌,苏联解体后,似乎如500年前一样,全球又一次开始成功地被纳入欧美所主导的资本主义体系之中,而历史似乎如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语,走向终结,而人类将永享文明进步的果实。但另一方面,让醉心于文艺复兴动人神话与全球化美妙图景的人们所始料不及的是,在拉丁美洲的知识界与大众社会,庆典却纷纷变成对野蛮西方殖民历史强烈的揭露与谴责——在文明的外衣下对其他未曾被“发现”就已存在数千年的文明的血腥扫荡与摧毁,对金银财富无耻贪婪的掠夺和对族群大规模的残酷奴役与杀戮——在进步话语所叙述的文明史上出现一道深深的裂缝,那些被遮蔽和放逐的文化他者的幽灵,借这一充满反讽的历史时刻,第一次集中而系统地迸发出它们强烈的痛苦与呐喊。于是所有的矛盾在1994年元旦钟声敲响时汇至顶点而猛烈爆发——在墨西哥,这样一个早于被欧洲发现就已存在数千年玛雅文明的国家,这样一个借助1994年元旦《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而渴望成为第三世界跨入第一世界样本的国家中,不甘唯一栖身之地在跨国资本对土地和矿藏资源的掠夺中被吞噬的玛雅原住民萨帕塔解放军(Zapatista National Liberation Army)在一神秘的白人领袖领导下,揭竿而起,在恰帕斯州(Chiaps)发动武装起义,在其《第一丛林宣言》(First Declaration from the Lacandon Jungle)中向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贸易体系发出其脍炙人口的坚决反击:“受够了就是受够了!(Enough is enough!)”。① 而这一持续至今的起义斗争和墨西哥政府在美国支持下对其进行的残酷镇压,迅速通过互联网和蜂拥而至的媒体报导,震惊了整个世界。继它而起的,是席卷整个墨西哥、美洲乃至全球此起彼伏的声援浪潮,其中既包括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萨拉马戈(Jose Saramago)等数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与法国前总统夫人深入丛林的亲临造访,又包括美国著名学者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等重要文章的发表,也包括好莱坞著名左派导演奥利弗·斯通(Oliver Stone)及其摄影组进入原住民营地的拍摄报导……交织笼罩着1994年的是这样一幅喧哗而诡谲的图景:启蒙和现代试图通过历史庆祝与条约化的资本扩张而再次确立自身,不屈的抨击与反抗却在语言之外直接付诸原住民的武力行动。而在同一年稍晚,好莱坞另一左派传奇人物卡梅隆开始了他15年后同样震惊世界的《阿凡达》的潜心构思与写作……
同时诞生在1994年的萨帕塔解放运动与《阿凡达》剧本,似乎在现实和幻想的两个世界里叙述着同一个主题——一个迥异于人类/西方的文明他者,早在“被发现”之前就以独特的形态绵延数千年;而人类/西方的漠视与偏见,将其一律贬为有待启蒙的野蛮人甚至可以直接驱逐的异类,而这也直接导致激烈的对抗和冲突。就具体故事情节而言,跨国公司或政府打着经济开发的口号对原住民丛林社区的摧毁与掠夺和利用高科技手段对起义的残酷镇压,拥有着或曾拥有过神奇文明的原住民们不甘丧失最后的土地,而在一位具有神秘身份的白人领导下选择了奋起反抗而非沉默灭亡,甚至连用原始武器夺取精良枪炮的细节都如出一辙;甚至不难发现,萨帕塔族起义地点恰帕斯州几乎就是影片中蕴含着丰富矿产和独特生态资源的潘多拉星球(Pandora)的原型,而玛雅人因开发造成的种族灭绝的处境恰恰也是纳美人同样的苦难。据关注萨帕塔运动多年的戴锦华教授考证,恰帕斯“是今日世界的无价宝藏之所在”,它所拥有的墨西哥最为丰富、洁净的水资源,其地下沉睡的多种珍稀矿藏,现今世界上储量最为丰富的石油,地球上最后的、也是最为丰富的生物多样生的地位,早就让美国窥测已久;而打通穿越其中的特旺特佩克地峡(Tehuantepec),连接起美国东西部两大工业区及太平洋和大西洋,同时将原住民最后的存身地开发为原材料产地和若干大型加工基地则是美国更为紧迫的需求,早就被列入“中美洲开发计划”;而这一计划一旦投入实施,“除却极少部分的原住民将被改造为合格的现代劳动力,绝大多数的玛雅‘遗民’将丧失他们最后的栖身之地”。②
更令人感兴趣的是,历史和虚构的起义中的主角,都是一位通过对自身族群残暴行径的反思而跨越了种族界限,投身原住民解放运动的白人。两者并非神灵,却均因其独特而神秘的号召力而成为社会学中所谓的“魅力领袖人物”(Charisma),激起民众无限的崇敬,从而顺利地开始最广泛的社会动员。领导着萨帕塔解放运动,且日后成为全球大众传媒英雄的白人副司令马科斯(Subcomandante Marcos)的身份一直是众说纷纭,而他那直至今日都从不摘下面具的佐罗式蒙面形象更是神秘莫测;而《阿凡达》中领导杰克兼有地球人和纳美人的双重身份,由于厌恶人类的恶行而融入纳美人原始部落中,其真实身份直至最后危机时刻方才向纳美人揭开。在玛雅人中,一直有一种离奇但充满顶礼膜拜意味的传说,认为马科斯是古老而神圣的玛雅典籍《波波武经》(The Popol Vuh)中书写过的玛雅先知的现代化身③;在《阿凡达》中,杰克正是凭借一举征服圣物飞龙而最终成为纳美人誓死追随的偶像,被认为具有无上的领导力,是世代相承的传说中具有神的力量能拯救整个星球的“魅影战士”的复活。
诚然,《阿凡达》作为一个发生在外星球的科幻作品,它不可能也无意只简单复述地球的某一个故事,但在影片中,确实充满着对广阔的历史与现实的模仿与暗示。如影片中人类为攫取矿藏,以暴力迫使纳美人离开生息繁衍的家庭树,对他们的强行迁徙,几乎就是19世纪30年代那条噩梦般的美国政府强行迁徙印第安人的“泪水之路”(Trail of Tears)的翻版;而纳美人形象中印第安人的装饰、类似中国清代人的辫子,代替政府成为扩张的先锋和战争的策划者的跨国公司,雇佣军首领类似美国前总统布什那样赤裸裸的“恐怖威胁”、“先发制人”的煽动和动辄对纳美人“异教徒”、“野蛮人”的蔑称,都无不激发观众对地球所发生的事实产生联想。甚至影片中对导致美国军人杰克断腿的委内瑞拉的提及,也让人难免想起美国因石油和政治而在委内瑞拉策动未遂的军事政变。在剧中主人公杰克身上,也不时跳动着因1960年代领导拉丁美洲革命而被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杀害的切·格瓦拉(Che Guevara)的影子——作为一代又一代西方左翼运动的精神偶像,格瓦拉圣徒的形象至今仍强有力地影响着无数文艺作品的创作。同时,它与早期同题材电影也存在着某种渊源,杰克游走在地球人与纳美人之间的双重身份与披上面具后却背叛殖民势力的佐罗有着某种令人感兴趣的相似性;对落后异族的同情与最终的认同与融合,也存在对《与狼共舞》(Dances with Wolves)、《最后一个武士》(The Last Samurai)、《风中情缘》(Colors of the Wind)等早期同题材影片某种程度上的借用。
同时,《阿凡达》一片似乎不光在经典地适应流行于西方的如后殖民、生态主义等种种文化批评理论的检验,它本是几乎就在直接或间接借用或展示此类理论的关键概念。如在剧中反复出现的“Relocation, Removal”(迁徙)、“Barbarian,Inhuman”(野蛮人、非人类)等词语是历史学家用以描述非洲或印第安等殖民地民族悲惨命运的经典术语,而它们所指向的现象,也早已同样激起后殖民理论家的兴趣,常常以此探讨空间物理的迁徙和对被殖民者人格与文化的否定。如何塑造新的权力关系从而影响殖民文化与心态的形成,著名学者法农(Frantz Fanon)早就尖锐地指出:
“通过否认民族真实性,通过由占领势力树立新的法律关系,通过殖民社会将原住民和他们的风俗驱赶至边远角落,通过强行征用,通过系统地奴役,文化灭绝得以成为可能”。④
而《阿凡达》中纳美人所信仰的万物有灵论,具体狩猎场景中反复出现的与坐骑的交流和对所捕杀的猎物的歉意与致敬,对生命的普遍尊重和对伊娃母神的崇拜,地球人关于潘多拉星球是一个互相紧密联系的生物体的发现,几乎就是直接照搬了人类学的实例与生态主义的理论。如著名哲学家阿尔伯特·史怀哲(Albert Schweitzer)曾论述过,自然界每一个有生命的或者具有潜在生命的物体都具有某种神圣的或内在价值,我们因普遍生命存在而存在,只有认识到这一点,人才能在精神上和宇宙沟通。⑤ 人类学学界的一个共识就是,万物有灵论几乎存在于所有原始思维中,在万物有灵观的背景下,原始人天然地拥有众生平等的生命伦理意识。他们对那些被杀的猎物天然地怀有一份愧疚之情,往往要举行简易的仪式向动物表示歉意和忏悔。如人类学之父泰勒(Edward Tylor)在其《原始文化思维》中以丰富的例子揭示:
“北美印第安人像跟有理智的生物一样跟马谈话……当人们要杀死熊的时候,就请它恕罪,甚至尽力赔罪,用和平的烟斗同它一起吸烟……在柬埔寨,人们不会忘记向被他们杀死的动物请求恕罪。北海道的阿依努人杀死熊之后,向它表示敬意和服从”。⑥
而《阿凡达》从对生命的敬畏扩展到对自然母神的崇拜,将自然而非人自身作为人的出发点和归宿,同样有着冲击着今天西方思想界的生态主义的深刻烙印。生态主义理论发展至今天已经以提倡个体的生物中心论上升至着重整体价值的生态中心论。如现代“生态中心论”伦理学创始人莱奥波德(Aldo Leopold)强调,自然不仅仅是供人类享用的资源,而且是价值的中心。生物共同体具有最根本的价值,它应当指导人类的道德情感。⑦ 同样,影片中科学家们对潘多拉星球如同一个有着信息能量循环流动的生物体计算机的描述,也暗合着当今的生态运动由浅层(The Shallow Ecology Movement)走向深层(The Deep Ecology Movement)的一个核心理念:任何有机体都是生物圈网络中的一个点,没有万物之间的联系,有机体不能生存,而在生态系统中的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进行着复杂而有序的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换,构成动态平衡的有机统一体。⑧
具体到影片中,通过将全球诸多尚未被破坏的自然景观的拼接,通过这样一个天人合一的纯净而和谐的纳美世界的虚拟构建,和杰克对着母神伊娃的喃喃私语“地球上再也没有绿色”,我们反观到的是一种对西方文明最核心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解构。而影片中推土机肆意破坏原始森林,怪兽般的轰炸机和大部分人类部队无动于衷地各处纵火、屠杀着无辜的纳美人和悍然摧毁其赖以生存的家庭树,无不表明人类的文明下的愚昧,进步中的残忍。而最终广袤大地深处无数圣兽奔腾而出,一举击溃高科技武装的人类,与其说是影片所描述的神灵动怒,不如说是如同地球上近年一再爆发的洪水、干旱、暴雪、瘟疫等灾害那样,人类的贪婪极大地突破大自然生态平衡的底线而导致她无情的报复,而面对着自然的无情与无限,人类所拥有的科技无论怎样进步都是微不足道的。这也是对狂妄人类试图征服自然的既有历史和西方现代文明内在的天人两分理念的一种极大讽刺。影片中生态主义观可谓昭然若揭。
这些,都似乎表明,《阿凡达》只是基于西方左派艺术对西方自启蒙以降或地理大发现后500年血腥殖民史和物质进步所带来的环境崩溃的某种反思与救赎。它似乎在借助电影的优势,以拼图般的效果,调动当代各类理论与精神资源,浓缩展现贯穿于过去殖民史中无数侵略与反抗的故事的主题,并用另一个人类/西方尚未侵染的原始文化,用它那伊甸园般的壮丽自然风景、纯朴而圣洁的精神世界反衬人类环境的彻底恶化与人性的彻底堕落。但是,正如《阿凡达》英文原版的标题“Avatar”所暗示的那样,它从一开始就同时叙述的,是否还有另一个相反的故事?
三、消解与反讽
如果我们回到影片原本的英文标题“Avatar”,我们会发现,它并非一个像中文音译标题那样没有任何意义的词,相反,“Avatar”一词由梵语“Avatāra”转化过来,本身就有“(印度教大神毗湿奴)从天堂降至人间”这一充满暗示性的意义,而英文常将其译为具有强烈基督教神学色彩的“Incarnation”一词,则强烈地赋予其基督临世、道成肉身以拯救世人的含义。⑨ 因此,影片从一开始也许就试图微妙地表明,这并非一个简单的原住民起义反抗工业文明摧残的故事,而是一尊人类/西方之神从天而降,拯救凡间土著的传奇,在这里,两者的关系并非完全平等;而同时潜伏于影片反抗主题的,仍然是其所竭力要反抗的启蒙与线性进步话语。
在影片中,且不说纳美人头后的那条类似于中国清代人的辫子,其本身经过两百年西方文学中的形象演变,就早已固化为西方特别是美国文化中一个充满侮辱性和歧视的劣等种族的符号;他们身体拖的尾巴,已经清楚地表明影片强烈的达尔文主义的潜意识以及对他们是未进化完全的生物的定位。而纳美人带口音的英语,按照社会分层论的观点,也是现实生活中特别是美国社会中将主流与他者隔开,区分种族、个人身份地位与教育程度高下的主要语言标志。这些都表明,作为一部美国电影,《阿凡达》未能摆脱西方对文化他者旧有偏见的窠臼。随着影片故事的展开,在人类/西方高科技武器悍然进攻下,我们看见的不是一个能掌握并决定自身命运的民族,而是一群被刻画成目光呆滞,手足无措,被任意屠杀而无法自救,只能等待一个救世主的垂顾与拯救的族群。
而这个救世主也确实如约而降,但这一到来的却非完全意义上古老传说中的魅影战士的复活,而是一个白人的转世!而他是千篇一律呆板面孔的纳美族人中唯一一个具有鲜活面貌的人!他虽是如其他魅影战士那样通过征服纳美人心中至高无上的飞龙而获得承认,但他对确立自己魅力人物权威的谋略,他教给纳美人的知识,他组织战争的方式等却已完全是人类/西方化的。影片中值得注意的一个对比场景是,当人类雇佣军的司令官和杰克各自准备战争动员时,他们所用的手段几乎同出一辙,经典地复制了如群体心理学家们所发现的,唯有现代社会政治才出现的一幕——领袖在集会的巨大公共空间,在振臂高呼时,用如“自由,恐怖,捍卫”等极富神秘感染力而意义不确定的词汇,加以排比、反复、强调等排山倒海式的演说修辞,对群众进行心理催眠,而使之爆发出极端的狂热,彻底丧失个体判断力与意志力,融入周围的集体,而成为无情战争机器的一部分。⑩ 而在这一动员中,我们看见的不光是一种人类/西方高于土著的观念与人类/西方之神启蒙并领导土著的新型权力关系的确认,更看见纳美人淳朴天性和万物有灵论等异于人类/西方的文化传统的丧失——他们,不再每杀一个生命都虔诚忏悔与祈祷,而开始慢慢陷入和人类一样物我两分的现代思维,和他们一样,开始毫不留情地进行杀戮!
同时,影片在对科技所造成的生态与种族灾难进行显性的谴责时,也隐性地再塑造了科技难以动摇的统治地位。当镜头一再出现心灵无比纯净的纳美人在人类大规模的高科技进攻中家园被毁,只能哭泣呻吟,四散逃难时,当苏泰等英勇的战士们在枪弹中倒下时,我们看见的是一种含糊地对线性文明观的无奈确认。或者,当纳美人的公主跃入实验车,在杰克即将窒息时用人类的氧气面罩救活他时,一个充满象征性的微妙时刻就此来临——原住民第一次学会使用人类的科技,并在为杰克的地球身体续命的同时抓住了与现代的联系……而这一隐约的对线性文明发展的确认,在影片行将结束时,得以清晰登场。押送地球人残余部队离开潘多拉星球的纳美人手里,不光是他们旧有的弓箭,而出现了人类的枪支!
这是一种抗拒中的悖论,一个所谓“落后”接受“进步”,一个不无反讽色彩的故事——一个古老文明为求生,被迫中断自身进程而向殖民者看齐,而最终丧失了它所要捍卫的文化独特性。当武装殖民者被(暂时)赶走时,文化裂变的进程却已隐约开始。它是否会意味着潘多拉星球在驱赶走人类时,已被推入人类/西方的发展轨道?而在为抵抗而模仿人类/西方的过程中,是否会形成对传统文化的断裂,从而进一步接受“进步”的科技及它的思维模式,甚至复制它的种种灾难?我们对一个虚拟的外星球的将来不得而知。但在地球的历史中,一个让人感慨的悖论正是对西方殖民者的抵抗,即使成功,本身也就意味着向西方学习和告别传统的现代化历程的启动,唯独如此,弱小民族才能在日后图存。这点,在那些曾有漫长独特历史的东方文明古国,在殖民危机尚未触发便已成功转型的日本,在漫长斗争后成功地摆脱殖民或半殖民地地位的印度与中国,都是如此。
或如马克思(Karl Marx)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曾经洞察到的,资本主义的扩张,“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1)
而这一具有反讽色彩的悖论的开启,也为我们思考电影、历史与自身留下了多种可能。正如纳美人所居住的星球的名字所暗喻的,无论如何,潘多拉的盒子已经开启……
注释:
① 戴锦华.副司令马科斯——后现代革命与另类偶像[J].天涯.2006(6).P4.
② 同①,P6-7.
③ 同①,P10.
④ FANON,FRANTZ.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A].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ed.Vincent B.Leitch.London:W.W.Norton Company & Company,2001.P1587.
⑤ SCHWEITZER,ALBERT.The Philosephy of Civilization[M].Florida:University,Press of Florida,1981.P200-223.
⑥ [英]爱德华.秦勒著,连树声译.原始文化[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P382.
⑦ LEOPOLD,ALDO.A Sand County Almanac and Sketches Here and There[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200-223.
⑧ NEASS,ARNE.The shallow and deep,long- range ecology movement.A Summary[J].Inquiry 1973(16).P95-97.
⑨ KRISHNA,FREDA MATCHETT.Lord or Avatar?[M].Surrey:Curzon Press,2001.P4.
⑩ [法]吉斯塔夫.勒庞著,冯克利译.乌合之众[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P12,31,45.
(11) [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P3.
标签:阿凡达论文; 人类文明论文; 殖民扩张论文; 进步主义论文; 人类进步论文; 纳美论文; 武打片论文; 剧情片论文; 科幻片论文; 美国电影论文; 动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