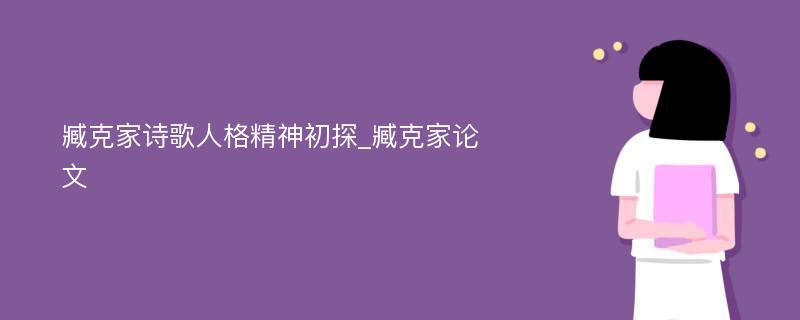
臧克家诗歌的人格精神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格论文,诗歌论文,精神论文,臧克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新诗史上,不少有成就的诗人都在其艺术探索过程中,对新诗的人格精神进行了精心营构。臧克家这位在新诗史上驰骋六十多年的老诗人,更是以其独特的审视领域和艺术追求为新诗人格精神的强化做出了突出贡献。研究臧克家和其他一些有成就的诗人为强化新诗的人格精神所做的努力,对于我们全面把握新诗的主潮和探索未来新诗的发展路向,都是具有重要的诗学意义的。
一、宏观考察:臧克家诗歌的人格基础与人格目标
臧克家走上诗坛的时候,象征派、新月派、《现代》杂志诗人群等的遗风尚未完全消失。这些诗人在新诗艺术上进行过艰难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也应该承认,有些诗人在创作中缺乏对时代、民族的关照,缺乏对现实的历史责任感与使命感。这不能不使新诗一度陷入低谷之中。
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样式,诗歌有其观照世界的独特方式。从历史上看,任何时代的优秀诗歌总与时代的主潮相契合,展示着大多数人的思索与愿望,即所谓“话到沧桑句便工”。在二十年代后期,由于一些诗人钻进“自我”的小天地,对时代、民族关注不够,使新诗出现了过多的颓废、感伤的情调,面对苦难的现实,它无法引导人们为着某种共同的理想而奋斗,无法给人们以人格上的启示与诱导。
臧克家一走上诗坛,便采取了与之不同的人生态度与艺术态度,他对当时的颓废、感伤情调十分不满,他说:“诗做得上了天,我也是反对的,那简直是罪恶!你有闲情歌颂女人,而大多数的人在求死不得;你在歌咏自然,而自然在另一些人饿花了的眼里已有些变样了”。他认为“纵不能用锐敏的眼指示着未来,也应当把眼前的惨状反映在你的诗里。”①他主张诗人应该直面现实,特别是惨淡的现实,而反对“闭下眼睛,囿于自己眼前苟安的小范围”②的那种“象牙塔”式的艺术追求。从一开始,诗人的视野就是极开阔的,关心下层人民特别是他所熟悉的农民的处境和命运,这在当时是颇具特色与个性的,诗集《烙印》出版之后,茅盾便指出:“我对于诗集《烙印》起了‘不敢亵视’之感,我相信在目今青年诗人中,《烙印》的作者也许是最优秀中间的一个了。”③同时,臧克家的诗美追求为中国新诗中的现实主义诗歌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对现实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关照是臧克家诗歌人格精神发展的基础。虽然他在创作初期的诗歌追求还带有一定的矛盾性,但是,由于诗人对下层人民的了解和直观的感受使他对人民的同情大大强于对个人悲哀的关心。他曾说过,诗人应当“把自己的心放在天下痛苦的人心里,以多数人的苦乐为苦乐。把自己投到洪炉里去锻炼,去熔冶。”④这种追求是与诗的艺术潮流相一致的,它不是要诗人放弃自己的艺术个性,而是要通过诗人个人的声音传达更多人的心灵之声。换言之,臧克家主张诗人要以开放的观念去拥抱这个世界,而不能把自己封闭起来,并且,诗人要传达众人的声音,而不能只在个人的小圈子里浅唱低吟。诗是有个性的,但它拒绝个人性,优秀的诗人与诗歌总是与时代进步的潮流结合在一起的。
正因为有这样的生活与心理基础,臧克家十分注重诗人的人格修养。在1935年,他就说过:“伟大的诗人,才能做出伟大的诗篇。”⑤他认为诗人应具有“伟大的灵魂”和“极热的心肠”,“须得抛开个人的一切享受去下地狱的最下层经验人生最深的各种辣味”,“诗人要以天地为家,以世界的人类为兄弟。”⑥这些观念虽然还有些空泛与模糊,但诗人基本的人格追求已形成了,这种追求主要来自诗人的切身体悟,具有自发性,然而也具有真切感与深刻性。当时代的发展呼唤诗人的责任感与使命感的时候,臧克家便把这种自发的体悟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联,把诗歌与时代紧密相联。1937年5月抗战前夕,他就指出,“因为时代是在艰困中,我们需要大的力量。”⑦这种“力量”就是一种人格的力量,就是诗人对民族命运的正面关注。诚如诗人在1947年所说的:“在今日意义上的‘新诗’,语言的近代化、口语化是必需的,而最主要的还是内容方面强烈的时代性--也就是斗争性。”⑧他要求诗人“革除了旧时代诗人孤芳自赏或自怜的那些洁癖和感伤,剪去‘长头发’和自炫的那些装饰,走到老百姓的队伍里去,做一个真正的老百姓。”⑨可以说,臧克家自发的对时代的关注经过时代的洗礼,已发展成为自觉的艺术追求,这一追求成为他终生的艺术目标。
在新的时代,诗人早年所面对的那种忧郁与苦恼早已荡然无存,这个时代与诗人的人生期盼达成了一致。因此,在新的时代里,诗人早年的忧郁与苦闷已变成一种正面的赞颂。这种赞颂仍然是发自内心的,从人格精神上看,先前的忧郁与斗争是在抗争的环境下产生的,而后来的愉悦是在和谐的环境中生发的,这两种不同类型的人格精神在本质上是完全相通的。
因此,可以这样认为,臧克家的诗歌历程实际上就是诗人人格的发展历程,他的诗歌是诗人人格的艺术表现,体现了诗人对民族的深沉之爱,体现了诗人对美好的人生与美好的时代的热切呼唤与赞美。从诗人漫长的创作生涯和丰富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臧克家的诗歌有开阔的视野,在开阔的视野之中,诗人以自己崇高的人格建构了他的诗歌的人格精神,这种人格精神,可以大致地概括为:求真、求善与求美。
早在四十年代,臧克家就谈论过他对诗歌的真、善、美的追求,他认为,“‘诗’,必须是真的,感情不能杂一丝假,‘真’才能感动自己,而后再去感动别人。”在谈及诗的“善”时,他认为“这是从它的本身和它的作用双方面着眼的”,诗必须“有益于人生,有补于生活”,“必须领导着人类挣扎,斗争,前进,一步一步领导着人类向一个伟大的目标前进。”关于诗的“美”,他说:“是指着恰好的表现配合了恰好的内容而融为一体说的。这包括了音节、字句、结构,这包括了诗之所以为诗而从文学其他部门区别开来的一切条件而说的。”⑩
在这里,诗人是就诗的艺术追求而论及诗的真善美的,它是诗人对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的继承与弘扬,也是诗人终生的艺术追求。如果我们把这种追求与诗的人格精神联系起来,可以发现,臧克家诗歌的人格精神与这种追求是密切相关的。求真,就是真实地表达诗人所体悟的一切,也表达诗人真实的人生态度,这体现诗人对人生的真诚;求善,是诗人进行审美评判的基础,这里包括对美的肯定与对丑的否定两种诗美取向,而二者又是一致的,体现了诗人的博爱精神;求美,这里不是从诗的传达方式而言的,指的是诗的人格精神的终极境界,就是对美好人生、优美人性的呼唤与渴求,是一种闪烁的理想光辉,体现诗人的智慧与意志。这几种人格要素的共同组合,便构成了臧克家诗歌的人格主调,也确立了诗人在中国新诗史上的崇高地位。
二、求真:真实与真诚的合曲并奏
臧克家是一位现实主义的诗人,他十分注重诗与现实的联系,强调生活之于诗的重要性。从一开始,他的诗就是对现实的真切体验的艺术升华,真实而深刻地表现了民族与时代的思考与呼唤。从《烙印》开始,臧克家的诗就顺应着时代的主潮,要么揭示现实的苦难,要么解剖个人的心灵及其与现实的关系,要么表达诗人内心的忧乐,全面地展示了他所思考的时代主题。可以说,臧克家的诗是现代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农民艰苦奋斗的精神历史,因此,早在1936年,朱自清就认为臧克家的诗是“有血有肉的以农村为题材的诗”。(11)
臧克家诗歌的真实性既体现在诗人没有回避中国的苦难和艰辛,也体现在他的诗与诗人的人生体验和人生探索紧密相联。他每一个时期的诗歌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中国的现实,没有矫揉与伪饰,同时也体现出诗人在人生观与艺术观上的不断发展与进步。
作为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的文学样式,诗歌真实地表现现实,并不是照相式的,它总是包含着诗人的人生态度与艺术态度,这两种态度是决定诗歌审美流向的关键所在。面对同一种现实,不同的诗人有时会采取不同的态度,比如对于时代的苦难,有些诗人也许会采取幸灾乐祸的讥讽,而与时代精神处于同一领空的诗人则会直面苦难并寻求改变苦难的路径。臧克家属于后者,他的追求与时代的大潮相一致,他认为诗人应当“走到老百姓的队伍里去,做一个真正的老百姓。把生活、感觉、希望,全同他们打成一片。这样,个人的哭笑、欲求,是个人的也是大众的了;个人的声音,是个人的也是大众的了;个人的诗句,是个人的也是大众的了。”(12)他总是以大众之苦乐为自己的苦乐,这样,他在诗中所表现的真实才是真正的真实,诗人也由此而体现出真诚的人格精神。
诗人是时代精神的代言人,但他不是凌驾于时代精神之上的万能的使者,他对时代精神的发现是从对现实的深切体悟中获得的。离开了真诚,诗歌不可能获得具有真理性的真实。臧克家的诗首先表达了他对中国的下层人民特别是农民的认识,他没有因为他们的苦难而失望,而是全心地表达他们的苦难,以求在苦难之中寻找改变苦难的力量,著名的《老哥哥》表达了农民的不幸,《老马》更是新诗史上的名篇:|总得叫大车装个够,|它横竖不说一句话,|背上的压力往肉里扣,|它把头沉重地垂下!|这刻不知道下刻的命,|它有泪只往心里咽,|眼里飘来一道鞭影,|它抬起头望望前面。
短短八行诗,把中国农民的苦难抒写得深刻剔透,诗人的情怀也投入其中。如果诗人没有对农民命运的关注,没有对农民的真诚,是不能写出这样的诗篇的。因此,闻一多认为《烙印》里的诗“没有一首不具有一种极顶真的生活的意义。”(13)我们可以把这句话看成是对臧克家所有诗作包括《烙印》以后的诗作的艺术诠释,诗人不只是面对生活的事实,而是以真诚之心表达了生活的真实,在臧克家的诗中,真实与真诚是两根并立的艺术支柱,支撑着一片具有强大人格力量的艺术天空。
在时代处于苦难的时候,诗人表现时代的苦难;当人们开始觉醒并为消除苦难而奋斗的时候,他全力歌唱这种奋进与抗争的力量;当时代进入光明的时候,他又真诚地赞美光明。臧克家的诗是与时代进步的脉搏在同一境界上跳动的诗,是中国新诗中现实主义诗歌的代表之作。
真诚可以摒弃艺术的伪饰,也可以调整诗人与群体之间的距离,从而使诗与民族、时代达成更和谐的关系。臧克家对苦难的人们怀着同情,他曾说过:“我对一切……都满怀着憎恶,除了劳苦的农民和工人以及为求解放他们而奋斗的战士,我写诗也是想为他们呼喊,把他们的生活撮在有力的笔尖上,叫起读者对这群人的同情心。”(14)这是诗人真诚的表现,因此,当他进入国立青岛大学之后,“窒息苦痛,象被大潮流撒在沙滩上的一条涸辙之鱼。脱离了革命,脱离了群众,觉得个人茕茕孑立,而暗夜如磐!”为什么呢?因为“我的眼光看到的是整个社会,全体人民,我的心思念的是过去轰轰烈烈的革命高潮,今昔对比,悲从中来,心里冒火,眼里流泪。”(15)这仍然体现了诗人的真诚,他渴望与时代、人民打成一片。
因此,诗人总是在表现现实的同时,也敢于剖解自己的内心,力求使自己的人生追求与时代的脉搏合为一体,虽然早期的一些作品如《失眠》、《像砂粒》、《万国公墓》等有一些低沉,但那是环境和诗人当时的人生体验使然。在更多的作品里,诗人对个人人格追求的表现体现了一种开阔、宏大、充满奋进的精神力量。象《生活》:“……在人生的剧幕上,你既是被排定的一个角色,/就应当拼命地来一个痛快,/叫人们的脸色随着你的悲欢涨落,/就连你自己也要忘了这是作戏。”诗人表达了对生活的投入,并且他认为只要“你活着带一点倔强,/尽多苦涩,苦涩中有你独到的真味。”这种乐观、顽强的精神成了诗人在诗歌中的精神主体,也是他的诗歌人格精神的中心。这样的作品还可以列举很多,《自白》、《盘》、《我们是青年》等等都表达了诗人与时代同步前进的心灵之声,长诗《自己的写照》更是全面地抒写了诗人早期的奋斗历程,表达了诗人“再起来”的崇高人格精神:|时代的手,掣动了|我颈上小的圈子,|几年来|平淡的茶饭|涨大了肚皮|却饿瘦了灵魂!|今夜,古城的枕头上|我再也合不上眼,|听四面八方的声音,|呼喊我再起来!
这种深刻的自我解剖正是诗人真诚人格的体现,也由此而形成了诗歌自身的审美人格,一种颇具魅力的诗美精神。
由此可以看出,臧克家是一位真诚的诗人,他以真诚的心去抒唱现实的真实,去呼唤改变现实,由此形成了感应众人的艺术力量。对于诗人与诗歌,真诚的品格都是不可或缺的,缺乏真诚的诗人是没有魅力的诗人;缺乏真诚的诗歌,是没有生命力的诗歌。在他的诗歌生涯中,臧克家都在全力实施着一个“真”字:真实与真诚的合曲并奏。因而他的诗心不衰,诗情不竭,每一个时代都有诗人所歌唱的主题。
三、求善;博爱精神的艺术力量
在中国新诗的人格精神的构成要素中,真诚与博爱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可能是,现代中国长时间处于一种不幸的境地,诗人需要用这两种精神去调整他们与现实的复杂关系,寻找正确的诗美流向,否则,新诗就很难在纷繁复杂的“关系网”之中找到精神上的主潮。
研究新诗中的博爱精神,有两个侧面是界定其内涵的关键。其一,新诗的博爱精神不是单纯从人性的角度去生发的,它或多或少地带有阶级的因素,是对大多数人特别是苦难中人们的博爱;其二,新诗的博爱精神不是那种个人的、本能的爱,而是指对整个民族和进步潮流的爱。因此,我们不能疏离中国新诗的现实去谈抽象的博爱,不能摆脱“我们”去谈关于“我”的爱,而应该结合新诗的生成时代去理解这种特殊的博爱。
臧克家在谈及新诗的发展时说过:“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它就肩负着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在阻碍重重的道路上艰苦地努力地向前走着,它的生命史也就是它的斗争史。在前进的途程中,它战胜了各式各样的颓废主义、形式主义,克服着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情调,一步比一步紧密地结合了历史现实和人民的革命斗争,扩大了自己的领域和影响。”(16)诗人十分看重诗与现实的联系,因此,探讨他的诗歌所体现的博爱精神,我们也必须从这个角度去展开。
臧克家所博爱的对象是民族和时代以及其中的人民,他的诗的博爱精神正是从这里生发出来的,表现为诗歌的主题与诗人博爱对象的一致与统一。可以从几个侧而对此予以剖析。
其一,臧克家诗歌的博爱精神的立足点是对苦难者的同情与怜悯。臧克家的不少诗歌是对苦难者表示同情的,这主要是因为诗人与那些受难者处于同一生活处境,对他们有深刻的爱。他没有象有些诗人那样对处于底层的人民进行讥讽甚至辱骂,而是真切而深刻地揭示他们的苦难。同时,也只有认识到这种苦难处境,人们才可能寻找一条消除苦难的路。因此,臧克家对时代苦难的抒写实际上是为了唤起民众,唤起时代的良知。
在臧克家的诗中,抒写农民苦难的作品最多也最有影响,这是与诗人的人生体验相一致的。他“从小生于穷乡,长于穷乡”、“接触的全是贫穷苦难的农民”。“这一切,为他以后写出反映苦难农民生活和破碎的乡村景色的诗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7)他对农民苦难的抒写是从多侧面展开的,从《烙印》中的“尽力揭破现实社会黑暗的一方面”。(18)刻划“不幸的一群”的形象,到《泥土的歌》“用生命铸造成功的”(19)对泥土的悲哀和对宁静的吟咏,诗人的笔触由现象到本质,由点及面,展示了诗人对农民乃至土地的命运的深刻思考,体现出诗人对受苦大众的同情与博爱情怀。
当然,诗人所关注的还不只是农民的处境与命运,他关注着一切受难的人们,对底层的市民,对普通的工人,甚至对那些无法以职业来划分的人们,诗人都投去了全心的关爱。比如《贩鱼郎》写的是靠借债为本卖鱼糊口的青年人的悲哀,《洋车夫》写的是车夫的屈辱与艰难,《神女》写的是妓女的惨痛经历,《炭鬼》写的是煤矿工人的悲惨生活,等等。可以说,只要诗人所认识到的苦难的阶层,他都给予了关注,由此而以诗的形式描绘了中国大众苦难的众生相,很好地实施了诗人“以多数人的苦乐为苦乐”的艺术追求。
可以设想,如果诗人没有“一个伟大的灵魂”,不“把自己的心放在天下痛苦的人心里”,他是不可能在诗中体现出同情与博爱的人格精神的。由此,我们可以认为,优秀的诗人与诗歌总是与诗人所处的时代和民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几乎找不到完全超越时空的情感,即使是“爱情”这样被认为是诗歌永恒主题的领域,在不同的时代也会显出不同的诗意来,所谓超时空的诗,那只是因为诗人表达了一种在不同时代、不同民族都共同存在的情感。臧克家诗歌的博爱精神正是以对时代、民族的深刻体悟为基本前提的。
其二,臧克家诗歌博爱精神的本质是为苦难者呼吁,为他们探寻消除苦难的路径。在诗歌中回避苦难与冲突是艺术发展所反对的,因为那是虚假伪饰的诗;而只在诗歌中表达苦难与冲突也是优秀诗人所不齿的,因为照相式地“反映”现实对于生命的发展是无益的。现代主义的某些诗作只是把表现“生存状态”作为艺术的最终旨归,在美学上讲,那是一种缺乏生命活力的追求。
每一个时代都有冲突,诗人的正确态度应该是直面现实,而又要以崇高的人格精神引导人们去参与对现实的改变。即使是在和平的时代,臧克家都能从现象之中挖掘现实的本质,寻找人生的真谛,著名的《有的人》就是这类作品,当然,它所针对的是少数人。在民族处于艰难的年代,诗人更能从现实之中探求光明之路。
对下层人民和时代悲苦的揭示,诗人首先是要让人们认识自己的处境,找到造成苦难的根源,同时呼唤人们去改变这种处境。这种意识在臧克家早期的作品中就有比较明显的体现,虽然目标和方式还有些模糊不定,但要求改变现实的愿望却是十分强烈的。
象《歇午工》,“他们要睡--/睡着了,/铺一面大地,/盖一身太阳”。这不只是人的沉睡,也是心的沉睡,而诗的最后几行却饱含深意,把诗引向一个新的境界:|沉睡的铁翅盖上了他们的心,|连个轻梦也不许傍近,|等他们静静地|睡过这困人的正晌,|爬起来,抖一下,|涌一身新的力量。
有人对这首诗大加赞赏,认为“这是一幅生活的画,生活本身的充实,供给了他充实的诗的意象”,“他不只是能作了这生活的轮廓,而他也充分地感到了这生活里含蓄着的生命的力。”(20)这一评价可以引申到对臧克家的大多数诗作的评价之中,在他的诗中,不仅可以感到因同情苦难而造成的内心的忧郁与苦闷,而且可以在忧郁与苦闷中体悟到一种强大的“生命的力”,这种力,正是诗人博爱的人格精神的诗美效应。
抗战爆发后,全民族为抗战而齐心协力,出现了不少英雄人物。诗人臧克家发现了这些英雄人物的启示力量,便融合个人的人生体验创作了不少歌唱抗战的诗篇,以范筑先的事迹为题材的五千行长诗《古树的花朵》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在这首诗中,诗人企图把范筑先塑造成为“一个艺术上的人型”,使他成为一个能“把人的水准提高,使大家去够及它”的“新的英雄”。(21)诗人写道:|生命是脆弱的,|死,并不是难事;|但,谁能死得象他这样,|有声,有响,|有彩光?|谁有他这样|一副肝胆,义气,|更叫人激动?|一家的红血,|化一道长虹,|耀眼放亮的|挂在历史的天空。
虽然写的是一个人的事迹,但诗篇表达了诗人对民族的爱,体现了诗人对民族振兴、民众觉醒的极大关切。无论从艺术表现,还是从人格精神上看,《古树的花朵》都是臧克家诗歌探索的新收获。
当诗人把对苦难的揭示转移到对改变苦难的力量的歌唱的时候,他的诗歌的博爱精神已转化为一种具有“目标”的奋进精神,其感召力与净化功能得到了明显的加强。因此可以说,臧克家诗歌的人格精神的本质是对时代民族的深爱,是对改变苦难的力量的呼唤与赞颂。
其三,臧克家诗歌的博爱的人格精神还体现在诗人对造成苦难的负面因素的尖刻而犀利的揭示与驳斥。任何冲突的现实都是由两种或多种因素构成的,当这种种因素无法调和的时候,富有正义感、使命感的诗人就会对那种阻滞历史进步的力量进行剖解,为进步力量的张扬扫除障碍。在中国新诗史上,除了那些表达时代苦难的诗作涉及到这一主题之外,袁水拍、臧克家等诗人的讽刺诗更是直接地表达了诗人们对各种冲突中的负面因素的审美评判。
在抗战以后,臧克家针对当时的现实写了不少讽刺诗,主要收录在《宝贝儿》、《生命的零度》、《冬天》三部诗集里。作为一位以抒情诗见长的优秀诗人,讽刺诗在艺术上似乎与臧克家的追求不太协调。但是,如果从诗人的人格追求来考察,二者却是一致的。诗人用讽刺诗揭示当时的虚假与丑恶,实际上是在张扬正义与善良,是在为诗人所追求的理想作另一种开拓。与直接抒写苦难者的悲哀的抒情诗相比,讽刺诗更能正面地揭示丑恶的实质,把诗人心中的爱与恨表达得更明了、清晰,与当时时代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因此,臧克家写讽刺诗虽然在他的诗歌生涯中只能算是一个小插曲,但却是不可或缺的插曲,诗人的人生态度与人格理想在讽刺诗中体现得十分明显,从另外一个角度张扬了诗人的博爱精神,也限定了他的博爱对象的范围。
象下面这些诗行:|苦苦打了八年,|刚刚打出了一个希望,|仿佛怕这希望生长,|当头就给它一棒!|大破坏,还嫌破坏得不够彻底?|大离散,还嫌离散得不够悲惨?|枪筒子还在发烧,|你急忙又去开火!|和平,幸福,希望,|什么都完蛋,|人人不要它,它却来了--|内战!| --《枪筒子还在发烧》
与一般的讽刺诗相比,臧克家的讽刺诗具有更含蓄的艺术风格。但是,诗人对当时现实的揭示是深刻的,解剖了假恶丑,也找到了把人民再次导入苦难的根源。作品中含着对制造内战者的仇恨,更包含着对进步力量的深切的爱与赞美。
其四,臧克家的诗歌创作跨越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以1949年共和国的成立为分界线。虽然在1949年以前的不少作品中,诗人已表达了对新生活的热望与喜悦,象1944年4月13日写于重庆的《废园》中的后一节,诗人就以浪漫主义的手法抒写了新时代的宁静与安详,“满院子花,/喷放出青春的香,/绿色到处流动/像活泼的心情,/一群小孩子,个个红光满面,/打闹又欢笑,/生命充溢了这早晨的庭院。”但这毕竟只是一种遐想,当新的时代真正来临的时候,诗人的心境又有了新的变化。
这个时代是与诗人的人生理想相一致的时代,“锦锈河山不再黯淡无色,/天地生出了新的光辉”(《祖国在前进》),因此,诗人的歌喉一改往日的凝重,出现了轻快、愉悦的赞美之声,“心头象有只宛啭的春莺,/按捺不住要歌唱的欲望。”(《凯旋·序句》)在新时代的创作中,我们似乎很难找到过去那种对人格精神的深沉张扬,但是,诗人的心境与时代主潮的一致与和谐正是诗人博爱精神的另一种体现。在这些作品中,诗人是正面地、直接地表达这种博爱精神的,诗人对新时代的极大的热情体现了他的爱的执著与深沉。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臧克家在不同时期,面对不同的现实写出了在风格上有所不同的诗篇,但是,这些表象上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都因为诗篇所包含的人格精神而协调地组合在一起,体现了诗人对时代、民族的一贯的爱,这种爱,以不同的方式渗透在诗人的作品中,展示了优秀诗人在人格追求上的一致与执著。臧克家是一位具有爱心、尊重艺术也尊重现实的诗人。
四、求美:关于终极人格的探寻
这里的“美”,可以理解为对美的艺术的追求,也可以理解为对美的人生、美的现实的思考。从人格精神的角度来看,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后者。
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涉及到臧克家诗歌的人格目标,即是对优美人生的呼唤与渴求。诗人真实地揭示现实,以博爱的精神去感召与唤醒苦难中的人们,主要体现了诗人的道德审美精神和意志力量,但是,如果以人格的三大要素,智慧力量、道德力量、意志力量来作全面考察,我们会发现,前面的分析还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诗人对时代苦难的揭示和对博爱精神的传达能产生巨大的启示力和审美感召力呢?
回答这个问题,就要从诗人在诗篇中表现的人格终极目标入手。
在早期的创作中,臧克家揭示了现实,表达了改变现实的强烈愿望,但是,诗人的人格目标还不十分明确。他虽然相信人们会“捣碎这黑暗的囚牢,/头顶落下一个光天。”(《炭鬼》),也相信沉睡的人们会“爬起来,抖一下,/涌一身新的力量。”(《歇午工》)然而,他还不明确这“光天”与“力量”之所在,因此,那时的诗人在心理上还处于朦胧与矛盾之中,那“天火”是“奇怪的”(《天火》),“变”也是“奇怪的”(《不久有那么一天》)。这种迷蒙的人格目标所产生的人格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是缺乏审美上的净化功能的,因此,在感伤的时候,诗人也唱:“不要记住你还有力量,/更不要提起你心里的那个方向。”(《像粒砂》)
然而,臧克家的优秀之处正在于,他不沉迷于现实的苦难,在他的心中,对美好现实的希望之火从来没有熄灭过。他从两个方面寻找着走向美好人生的路,一是在现实中寻找奋进与抗争的力量,二是寻找造成苦难现实的根源。在长诗《自己的写照》中,诗人反思了自己思想的发展脉络,更开阔地抒写了对时代动力的深刻体悟,真正地找到了创造美好人生的路向。|几多的汗,几多的血,|才开熟了这片片远荒,|四万万人民,|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地面,|这宝贵的家珍|做了多少帝王的私产,|“双十”的红血这才把个民主的名义|写给了天下的人|……|手掣住手,心靠近心,|悲壮的感情|传染了人群,|是时候了,|大家已经站起身来,|不做任谁的奴隶,|要做一个人!
诗人通过对历史、现实的深沉思索,发现了真正的力量,这不是个人的哀怨,而是一个民族伟大的集合。因此,诗人深深地认识到群体力量的强大,在那以后的诗歌中,臧克家展示人格精神是以民族、人群为本位的。这让我们意识到,诗人的博爱与真诚如果不投入到“我们”之中去,就会显得很脆弱。臧克家诗歌中人格精神的魅力以及他对光明未来的执著追求正是以这一原则为基本立足点的。
因此,我们发现,臧克家诗歌中对美好人生的呼唤与探求顺应了人的心理发展逻辑。生活于苦难中的人们,都渴望改变自己的处境,诗人将这种渴望艺术地表达出来,成为引导人们心路历程的审美精神。
我们也发现,臧克家诗歌所表达的人生理想是历史发展潮流的艺术化。诗人站在时代的至高点上,把一个时代的愿望表达在诗篇中,从而使诗篇具有了与时代脉博相契合的人格力量,成为时代发展的精神历史。
这种艺术事实告诉我们,诗人对美的渴求,除了在诗歌本体上的开拓之外,还有对人类进步潮流的把握,如果一个诗人只在个人自我的小天地里吟哦,他的作品只能成为精致的小摆设。优秀的诗人总是把自己的审视目光投入到广阔的人生领域,表达那种属于民族的乃至人类的理想之光,从而形成一种令众多心灵都感到震动的人格力量,这一点,不仅为历史上的优秀诗人所证实,也为臧克家这样的优秀的新诗诗人的创作所证实。
为此,有必要对人们一向谈及的诗的真、善、美做一些新的认识,特别是对诗之美,更应做全面的思考,美的情绪、美的渴望都应该纳入它的范畴。臧克家诗歌的人格探索启示我们,优秀的诗人都是民族与时代的产儿,他们把握时代的主潮,是时代精神的真正代言人。
注释:
①②⑥臧克家:《论新诗》,《文学》第3卷第1期,1934年。
③茅盾:《一个青年诗人的“烙印”》,《文学》第1卷第5期,1933年。
④⑤臧克家:《新诗答问》,《太白》第2卷第1期,1935年。
⑦臧克家:《新诗片语》,《文学》第9卷第2期,1937年。
⑧臧克家:《新诗》,《中学生》1947年6月号,总第188期。
⑨(12)臧克家:《诗人》,《中学生》1947年8月号,总第190期。
⑩臧克家:《诗》,《中学生》1947年2月号,总第184期。
(11)朱自清《新诗的进步》。
(13)闻一多:《烙印·序》。
(14)臧克家:《如此生活》,《文艺座谈》1卷3期,转引自张惠仁《臧克家评传》第62页。
(15)臧克家:《甘苦寸心知》第5页。
(16)臧克家:《“五四”以来新诗发展的一个轮廓》。
(17)张惠仁:《臧克家评传》第11页。
(18)臧克家:《烙印·再版后志》。
(19)臧克家:《十年诗选·序》。
(20)侍桁:《文坛的新人--臧克家》,《现代》第4卷第4期,1934年2月。
(21)臧克家:《古树的花朵·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