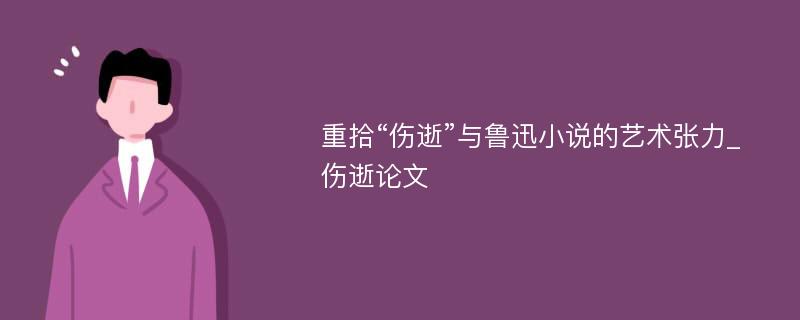
重温《伤逝》——兼论鲁迅小说文本的艺术张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文本论文,艺术论文,小说论文,张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10.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110(2001)增刊-0314-06
一
无论如何鲁迅给我们留下的文字,留下的作品,都是另类的。他抑或是作家的思想家,抑或是作为思想家的文学家,一时难以说清。即使根据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概念中的描述游戏、指令游戏、叙事游戏等等语言游戏规则来归类的话,鲁迅的文本也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种。然而尤其是西方评论界(国内也有),在没有任何参照系统和在现成理论和艺术标准无法识别的情况下,对鲁迅的作品作出了人们大抵预知的、先定性的结论:鲁迅是一位有“杂念”的作家,“艺术之肉每每包不住‘改良社会之骨’……”[1]但是,当人们不是抱着所谓的艺术理念,而是独自走进他的话语世界之时,发现他应该是“天生”的艺术家。他的那种超常运用话语的能力营造出的独一无二,且极具包容量、穿透力的语境、语感,能传达出多重的信息和幽深的思索!
《伤逝》就是鲁迅小说中最让人留连忘返,魂牵梦绕的那种文本。这是鲁迅小说中唯一的爱情小说,描述的是一场亘古未有的、让人心动的爱情。在20年代,那怕是时间已经进入到21世纪的今天来看,这桩爱情也是前卫而现代的。这爱情最现代的标志,就是男女主人公选择了同居。同居,就意味着他们勇敢地蔑视封建礼教、封建道德的存在;同居,就意味着他们的爱情是真正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唯一只需要情感来编织自己的爱巢。正因为如此,鲁迅先生在小说的开篇还是用了一种真诚、深情、诗意的笔调写下了涓生和子君让人艳羡的相识和相恋。然而熟悉这个爱情故事的人都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一个正在发生或将要发生的浪漫至极而又“简单”的爱情故事的开始。一切好像是神奇的寓言,一切又好像是二人世界的现实状态和情感状态的逼真复活。鲁迅先生意味深长地把这个爱情故事的主人公只限制在当事人二者之间展开,没有捕风捉影的第三者,这通常是一般意义上爱情崩溃、婚姻解体的固定模式。这个有着迷人开端的爱情故事,却无可挽回的从涓生和子君的相恋到相疑,相怨到相离,最后以一个始料不及的人间悲剧结束:子君抑郁而死,涓生则在悔恨和辩解中灵魂开始分裂,他今后的新生活将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
每当我们掩卷沉思,都深深感到鲁迅先生实际上并无意于描绘一个毛骨悚然,让人费解的爱情悲剧,也无意于要让读者去纠缠不清谁是这个爱情悲剧的制造者,谁是受害者和受益者,而是让读者在领略了一段扑朔迷离,悲喜交集的二人情感世界的心灵交锋之后,不由得对“爱情”——这个好像从来都充满创造力、亲和力的“圣物”从此有了怀疑,有了警惕,虽然这无论怎么说都有些“鬼气”和“煞风景”。
子君,这是一个具有清醒的现代自救意识,并成功实施了自救行动的新女性代表。她的那句“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无疑我们现在听起来也是时代的强音、生命的呐喊。子君的个性生命意识的觉醒,使她仿佛已经把自己送到了天堂之门。我们的子君在新的社会文化背景的支撑下,有着足够的勇气和力量与凶恶但垂死的封建礼教、封建道德相抗衡。她浩大无边的爱征服了、震憾了涓生,在她的爱情道路上,似乎一切横亘在前的有形和无形的障碍,通通化为乌有,更不要说“半瓶雪花膏和鼻尖的小平面”了。然而鲁迅先生的“火眼金睛”太具穿透力了,他甚至永远走在时间的前面,像个不合适宜的预言者:“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求”。[2]当然,这对于意志薄弱者,对于好大喜功者,对于那些不愿脚踏在结结实实地面上的人来说,都是极其“残酷”的,但遗憾的是鲁迅先生的“先见之明”往往被不幸言中。到此为止,我们很不情愿地发现:涓生和子君伟大而惊世骇俗的爱情,充其量只挣得了与包办婚姻不同的一种婚姻形式罢了(当然这个形式也是很重要的),然而这种孤注一掷的爱情并没有把他们双双领上永远幸福、白头偕老的康庄大道。恰恰相反,这个现代社会看来最富人性、最合理,最无羁绊的爱情进入方式的最终结局,却是千百年来层出不穷、让我们欲哭无泪的爱情悲剧。在这里,能逢凶化吉,超越世俗的爱却变得无力回天,苍白可怜,甚至我们还可以隐隐作痛地读出,子君的死是死于自己浩大无边的爱。爱情究竟怎么啦?为什么无可指责的爱情本身也无法拯救我们自己,这也许就是鲁迅先生在观察、思考了20世纪现代爱情婚姻后给人们提出的关于爱情、婚姻的最高、最后的课题。从这个意义上讲,《伤逝》也成了“五四”以来,迄今为止有关爱情的最本质性的话题描述。然而更具意味的是,人们一直都想在《伤逝》中找到相关的答案,又往往不得而获,而值得关注的却是一段象征意蕴极其浓郁的抒写:
“我们总算度过了极难忍受的冬天,这北京的冬天,就如蜻蜓落在恶作剧的坏孩子的手里一般,被系着细线,尽情玩弄,虐待,虽然幸而没有送掉性命,结果还是躺在地上只争着一个迟早之间。”
这是一个让人“扫兴”,但又永远激发人们思绪处于亢奋、追问状态的抒写。有的研究者也注意到了鲁迅这一段话的精彩,杨义说:“悲剧不能由爱情本身寻到充分的解释,更为本质的解释存在于社会结构之中,于是他象征地写出这个戏虐蜻蜓的‘坏孩子’,以严密的形象说明旧的社会制度是玩弄、虐待,最终毁掉涓生、子君这双天真的“蜻蜓”,从而控诉了旧社会毁灭青春,毁灭爱情,毁灭生活美的罪行”。[3]杨义的分析无不道理,也很深刻,但我总觉得鲁迅文本给我们提供的信息量要大得多,丰厚得多。《伤逝》并不是“娜拉走后怎样”的注脚和简单的主题重复,《伤逝》更不是演讲,不必要简洁、扼要地回答所设计的问题。《伤逝》写在《娜拉走后怎样》的著名演讲一年之后,甚至我以为鲁迅先生是要把“简单”的爱情问题“复杂化”,并希望用一种旷世的描写,尽可能达到逼真的现实效果,同时又包含深邃的哲学反思,人文关怀以及社会解剖。
爱情无疑既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问题,又是一个无法超越各种社会相关因素的综合话题,鲁迅先生作为精神界自觉的战士和一个现实的清醒者来说,最有资格对此言说(当然他在公共场合也说得不少)。但是作为艺术小说的《伤逝》,我们从它全篇开放、随意的结构,到“双重第一人称独白论争性的呈现”[4],从少量的而且无法严格确定的议论,到象征意蕴浓厚的所指,再到男女主人公的行为判定无任何标识等等,可以看出,第一,鲁迅先生无意于要给出什么包医百病的现成答案,也没有什么现代答案可给,他只是发现问题,让人们活得明白一些;第二,鲁迅小说具有巨大的包容量和艺术再生性,《伤逝》会永远引领人们将人世间的爱情纠葛继续说下去,而且会往深处说。《伤逝》是那种不可多得的,将形而上的人生思考和社会解剖融化在逼真的现实生活和精神情状之中的艺术文本,同时从这个“近乎于无事”的爱悲剧中,读出人世间最深层的,最难以战胜的悲哀和不幸。
二
我以为我还有再说的必要,因为这个言说的空间,好像是鲁迅先生在《伤逝》中给我们所有人留下的。来看子君的悲剧。
如前所述,她有良好的接受和感悟新思想的能力,而且敢作敢为,在自己人生的重要关口上,非常勇敢地作出选择,真正地做了一回主人。然而随着爱情悲剧的徐徐展开,我们越来越惊讶地发现:子君全部的勇敢和她无畏强暴的自救,却是把自己从一个旧的束缚中解救出来,再放进了一个新的束缚之中。如果说旧式的包办婚姻、媒说之言,是父母或他人替自己找一个婆家,而子君只不过是自己相中了一个男人,是她可以依托终身的人。当然,面对这种新的困境,子君抑或是浑然不觉,抑或是百分之百的心甘情愿。鲁迅先生以他高度敏锐的感知力,对于所有新的或貌似新的所谓潮流、思想,有一种自觉的怀疑和冷静的观照,他会迅速发现困扰人们的新问题和新倾向。子君的勇敢、子君的自救,确实让现代女性们激动不已,跃跃欲试,但殊不知子君的全副精力、全部身心,只是要想把自己送进一个一劳永逸的幸福城堡,然后做它的看门人。从这里我们似乎才恍然大悟为什么子君前后判若两人;为什么子君主动放弃了一切追求,一心只准备着爱和被爱,为什么在爱没有了着落情况下,顷刻间就像一个输光了赌注的赌徒,面如土色,迅即崩溃,再也找不到当初那个骄傲、勇敢无畏的子君的影子了。子君的悲剧告诉我们,女性的悲哀、女性的弱势,是双重的、深重的。这里有来自社会千百年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对女性的歧视和不公,更有女性自身无法超越和颠覆的长期以来整个社会给她们所规定的角色,因为不管在意识还是潜意识中,女性只能顺应社会意识形态的存在而存在,不然将无法辨认她们自己。子君的全部骄傲和全部悲哀,在于她既有一种自救意识,但是这个自救意识本身,是对“男权”社会结构的依傍。这种符合常理的,但又几乎带着撞大运的爱情心态,使多少楚楚动人的女子,在自己一生所爱的人面前,百思不得其解,甚至抱恨终身。鲁迅先生的高妙就在于他残酷地、无情地把女性们“唯一”在这个社会上所能依傍的理想爱情的神话戳穿了、毁灭了(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先生是真正的女权主义者)。女性和男性的所谓平等,只能是真正的、最后的精神上的完全平等,这是一个前提,也是一个底线。也许美丽的爱情结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是至少我们没有了爱的压力,没有了爱的负担,轻装上阵,共同前行。
子君的爱是博大、炽烈的,她是富有创意的爱情导演。多少年来在我们爱的哲学里,爱是和冷漠相对立的,甚至是和罪恶相对立的,在《伤逝》中我们领略了另一种爱的哲学:子君的爱使他得到了涓生,同时子君的爱又使她彻底失去了涓生,这里的个中滋味,这里爱情哲学的辩证思考,使我们不得不沉思良久。子君在人生的大关口处,煞费苦心,精心酝酿,开始了温馨的生活。同居后,她更是大喜过望,每天以温习旧课度日,这时的子君已不再注视涓生的眼神和内心,她觉得涓生已经永远是她的了。渐渐地子君本质的单薄和虚弱开始显露出来,她一无所有但又很“富裕”,这就是那个感天动地,浩大无边的爱。然而,爱这个玩意儿是不能自足的,它一定要发射出去,还必须能反射回来。于是《伤逝》中涓生“莫明其妙”的变化和不合作,使子君的爱没有了着落,甚至事情越来越恶性循环起来,子君越是无条件地付出自己的爱,涓生越是像躲瘟疫似的逃避着,一种无形的力量把爱情的结打成了死扣。
《伤逝》的发表具今已有70多年了,那个捉弄涓生和子君的“坏孩子”,可能更加“面目全非”,至少,当今女性的经济权、社会地位等已不再是困扰女性现实生活的显性问题,然而子君的悲剧仍然随处可见,这个“坏孩子”似乎有无穷的法力。想一想,其实早在《伤逝》的年代,鲁迅先生已经给我们开启了一条思索女性自身、女性生存状态、女性生存困境的路径,虽然用的是男性作者的眼光,但这恰好是女性本身少有的反观的思路,因而具有一种真正的洞见和无法替代的体验。当今社会越来越走向现代文明和物质进步,女性问题的交锋,往往主要变成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交锋。如果我们可以畅想一下未来,那么男人和女人都应该还原他们本身的角色,卸掉他们的种种面具,善待自己,善待对方。
三
涓生在《伤逝》中的遭遇,耐人寻味,更具哲理。“我没有负着虚伪的重担的勇气,却将真实的重担卸给她。”“我不应该将真实说给了子君,我们相爱过,我应该永远奉献她我的说谎”。“我想到她的死……,我看见我是一个卑怯者,应该被摈于强有力的人们,无论是真实者,虚伪者。然而她却自始自终,还希望我维持较久的生活……”。读着涓生这些撕心裂肺、痛不欲生的忏悔,我们与涓生一样,情感上遭受到强烈的震撼和煎熬,但是我们好像并没有因此而失去理智,也不愿放弃理性的注视,这是鲁迅先生的语感和语境给我们的细微感受。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故事,是天底下最悲哀的爱情故事,也是最难堪的爱情故事,他们面对自己所爱的人,鬼使神差地除了伤害,就是把对方推上绝境,这无论如何是他们抑或也是我们始料不及的。涓生的觉醒,就是子君的死期,这样的描写,这样的设计,有突兀、巧合之嫌。但是鲁迅先生正是拨去了现实中的层层遮敝,将此种人生的大不幸赫然推到我们的面前,让人们少几分苍白、无用的浪漫,多几分做人的责任和理智。涓生的悲剧在于他的所谓觉醒是以子君的毁灭为代价的,这种结果的命定性又使“跨进新生活”的涓生永远在心灵上烙下“原罪”的红字。这是追求的陷井,也是爱情的悖论。的确,爱情就是两个人并肩涉过一条大河,没有充分的准备,没有完全的默契,心灵的相通,是无法到达彼岸的。如果只有一个人上岸,那个人无论如何必须承担“不救自逃”的嫌疑,如果结果是命定的,不可更改的,那么就只能说明他们双方进入这一过程的“程序”错了,涓生和子君都必须退回到原点,重新等待。
鲁迅先生用极致的语言和一种哲理渗透式的描述,表现出一个爱情“幸存者”最大的悲哀,也是最深刻的清醒。然而鲁迅先生一生只作反题,不做正题,并不是“叫人死,而是叫人活”,不是叫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涓生的荒诞和清醒,涓生的悲哀和新生,都具有同等的真实性、严肃性和同等的认识意义,没有必要得出悲观主义的结论。
而青年鲁迅研究者汪辉在论及《伤逝》中的涓生一节时,以其思辨的兴奋,注意到了涓生在这场爱情悲剧中的荒诞处境,但是最后却把涓生爱情、新生的过程纳入了“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的“过客”精神,“是劳而无功却持续不懈的西西佛的人间体现”。汪辉的用意是用涓生的处境和涓生的悲剧再一次验证他在《反抗绝望》一书的宗旨——鲁迅思想的悖论。议论此书的主旨已不是本文的范围,但是有一点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在很多时候,汪辉会情不自禁地将鲁迅思想的悖论推到一种极致,接近一种极端。于是这种悖论就更多地成为了一种非理性的焦灼、死灭、无望的强刺激的身心体验,而渐渐地人们会淡化那悖论性的思想中所包含的理性价值和认知意义,而这种理性价值和认知意义,在于这种所谓悖论的思想,恰恰提供了一种大智大勇,高远缜密,悲喜交集的辩证思维格局。智者的痛苦,是一笔财富,甚或是芸芸众生的福份。
四
每一次重温《伤逝》,除了对男女主人公爱情悲剧命运的重新解读之外,小说文本本身的艺术张力,也在久久地撩拔我们,同时我们感到了鲁迅先生完整的话语系统,以及在这个话语系统的艺术性中,既有对共识规律的谙熟和经典发挥又始终具有极个人化的独特追求。
尽管鲁迅先生自称自己不愿“把小说抬进文苑”,尽管他的小说创作数量较少,以至于有人因此怀疑他文学家的地位,尽管他作品中显而易见的启蒙主义功利性“企图”,有的人因此怀疑他“真可以被称做文学家”,但是,每当我们一对一地和鲁迅的小说对话、交流,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平静下来。读鲁迅小说是一种异样兴奋而又焦灼的体验,同时身内的一切现成的积累仿佛都不够用,或是成为一些空白。文学是什么?小说是什么?鲁迅的生命样式是独一无二的,甚至没有现成可以参照的东西,但是他的伟大、丰厚和峭拔,无人不与认同,包括他的论敌。然而,我们又不能简单用什么主义、什么家给他盖棺定论。他所从事的一切,仿佛在他幼年无拘无束的“杂览”中,以及13岁那年,家庭发生灭顶之灾的突发变故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13岁这个微妙而情绪化的年龄,所看到的一切、所体验到的一切,都永远定格,刻骨铭心,无论岁月的洗刷,阅历的消解都无济于事。从这一刻起,我以为鲁迅的心思至少有两点开始清晰、明确起来:一是,他从此自愿的,带着“皮肉之苦”的创痛,永远把自己放逐在主流上层社会之外了,从而深情地、一厢情愿地把自己划在了全社会最低层的劳苦大众一拨儿。他自己那个高贵的血统连同官府后代的名份倾刻间灰飞烟灭,涅槃后的精灵已是一位“心事浩茫连广宇”、“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独行侠士”。二是,一切皆是变数,一切都须重新做过,一切权威,按部就班,顺理成章,在鲁迅的经历中已经成为反讽、笑谈,剩下的只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如果我们再重温鲁迅先生从文的每个细节,我们不能不为之感动不已。沉默八年之久,鲁迅先生在人们看来不能预知结果的情况下,结束了他“立人”的元思想,开始了具体的“实作”,从此他把全人类、全民族的痛苦一个人扛在肩上,进入了一项亘古未有的(以后也不会再有)、浩繁的精神系统工程。他的选择,不同于当时很多的仁人志士:“医学并非一件紧要的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5]。由此我忽然想到,其实鲁迅先生一经走上这条荆棘丛生、陷阱无数的道路,有一种常使善良人们扼腕的现象会发生:这就是,呼风唤雨、叱咤风云的政治家们要骂他,高雅纯粹,一尘不染的艺术家们要骂他,而一群附着在各式各样权势、利益上的名士、文人更要骂他。我怎么也不明白一个道理:为什么所谓有“杂念”的作家,不论其作品如何,一概被视为先天不足,难成正果。我认为问题的关键,不是先有对文学的规定,才有鲜活、绚烂的文学创作;不是规定只许写什么,不许写什么,而是怎么写,如何写的问题。如果不是用一种偏见来硬套的话,鲁迅先生作为中国少有的天才作家、语言大师是人所共识的。他的文本的“异样”早在其诞生的那天起,一直被人们深深地体识着,不论是他的朋友,还是他的论敌。曹聚仁说:“鲁迅在文艺上的造诣比胡适高,对青年人的影响也比胡适广,但鲁迅的文体,比胡适不容易学”。“上海出过一种《鲁迅》的刊物,结果都不属于鲁迅的风格”[6]。我认为鲁迅作为文学家,特别是小说作家的成功与魅力,恰恰在于他竟然能将文化的因素与文学的因素;历史的因素与文学的因素;政治的因素与文学的因素最大限度地、无懈可击地融合在一起。他独创了一种文体,独创了一种语境,独创了在中国这块荒淫、丑恶、专制、腐朽、灾难充斥的土地上最为“匹配”的文学样式,这是一种直面现实后义无返顾的选择,这是一种良心和才艺的最后抉择。
五
出手不凡、道破天机的《伤逝》发表于1925年,这正值鲁迅先生小说创作进入游刃有余、炉火纯青的阶段。《伤逝》和鲁迅其他的小说比较起来,更能使鲁迅先生全方位的文学才能得以展示:不论是全篇文字、语境的诗意化、情态化;还是对男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本质的准确把握或对二人情感世界亦真亦幻的逼真捕捉和摄取,总之,这一切充分显示了鲁迅先生“基本小说”的创作功力[7]。而所谓“基本小说”的创作往往是评论家衡量作者有无艺术天赋、艺术能力的重要语术,但我认为除了深谙“基本小说”的套路外,《伤逝》中鲁迅小说的艺术张力、鲁迅小说一贯的自身优势——寓言式的发现、哲理在细节间的跃动等,则更具魅力,更令人魂牵梦绕。下面我们举例来具体感受一下这种艺术文本的张力。
首先,《伤逝》独特的话语系统深深地吸引着我们,鲁迅先生用不多见的悲情缱绻、诗意清新的描写,让我们“感兴趣的开始”进入男女爱情主人公的情感世界,那种语境、语感,恰恰是我们熟悉而又陌生的爱情世界的经典设计,那种语境和语感使我们自始自终沉浸在一个逼真的旷世爱情悲剧的体验里,观爱情主人公的沉沦、挣扎,舔我们自己爱情创痛的伤口,思人间不幸的道理……
其次,在谈到《伤逝》的艺术张力时,小说中有一个极具意义的设置是不容忽略的,这就是那条巴儿狗阿随。这只狗的出现,是鲁迅先生很富艺术性、戏剧性的创设,本来养狗、养动物是子君很生活化的行为细节,但鲁迅非常“诡秘”地把自己的“意图”依托在了这只狗上。因为正如《小说修辞学》的作者布斯所说:“杰出的叙述者总是设法找到某种方法,来使这种概述变得有趣”,“用来把它们的倾向伪装成被表现的客体的组成部分”,“其综合效果是让我们感到,他给我们的故事远比他把未加工的题材端出来所能成为的故事更优美、更精制”。鲁迅首先描写了涓生买了几盆花草,希望子君喜欢,但偏偏子君不喜欢花草,不经意中,二人意趣上的差异已是不祥的预兆。然而更糟糕的是子君给狗取名叫阿随,涓生不喜欢这个名字,读者们心领神会也不喜欢这个名字。怪不得涓生那种“只知道捶着个人的衣角,那便虽是战士也难于战斗,只得一同灭亡”的慨叹与日俱增。子君无法排遣虚空,而阿随正是填补他们二人关系的最好的傀儡。涓生、子君、阿随三者构成一种关系,而子君与阿随的关系正好成为涓生和子君关系的折射,子君和阿随的关系赫然成了我们解读这一爱情悲剧的最简捷的路径。这个具有讽刺意味的戏剧化设置包含了子君,一个现代新女性全部的悲哀和虚弱的本质。
还应该提及的就是上文曾经提到过的那个象征性意蕴极其浓郁的总结式议论。从艺术的高度来看,这段文字很有策略性,包容性,更具有一种艺术的张力,这样的抒写避免了回答问题似的把复杂的情形简单化的倾向,同时从主题的复调性、深刻性;从艺术氛围隽永,具象、灵动等来看,都要求小说《伤逝》必须按照其艺术生存的方式去结构语言,打造语言。
如上所述,《伤逝》是证明鲁迅先生在思想价值上远远超越同代人的一部力作,同时《伤逝》作为一部成功的艺术性文本,使鲁迅先生艺术家的天赋展露无遗;使鲁迅作为思想家的作家的优势尽显无遗。艺术上的独具匠心,使深邃、过人的感悟和理性变得声情并茂,刻骨铭心。鲁迅先生是一位善于体验,善于感悟,又善于表达的艺术家,并且他的表达一定是不可重复,无法模仿的,这是因为他找到了既属于他自己,又属于全世界的如“东方的微光、林中的响箭、冬末的萌芽”般的文学载体和话语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