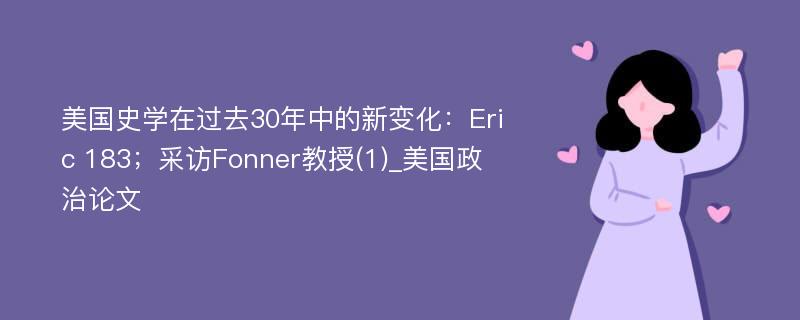
近30年美国史学的新变化——埃里克#183;方纳教授访谈录(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美国论文,新变化论文,访谈录论文,教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埃里克·方纳(Eric Foner)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现任美国历史学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主席。 方纳于1943年生于纽约市,1963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学院,1965年获英国牛津大学学士学位,1969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并被哥大破格聘用。1972—1981年,方纳先后在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院和英国牛津大学任教。1982年, 方纳被母校聘为威廉·皮特美国史讲座教授(WilliamPitt Professor of History),1988年起至今, 担任哥大历史系德威特·克林顿历史讲座教授(De Witt Clinton Professor of History)。方纳的研究领域涵盖19世纪美国史(尤其是内战与重建),美国政治文化史,黑人史和美国激进改革运动。自1970年来,方纳共写作和出版了8部专著,编著了数本论文集、资料集和美国史研究的工具书, 并写作了大量论文。他的每一本专著对美国史领域的研究都有重要影响,相当一部分是美国各大学和研究生历史课程的必读书。在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之前,方纳曾担任美国历史学家组织(Organization ofAmerican Historians)的主席(1993—1994), 成为能在一生中获此两种殊荣的极少数的美国历史学家之一。方纳是英国皇家科学院的通讯院士,他曾在普林斯顿大学、牛津大学、莫斯科大学、耶路撒冷大学等世界著名大学担任过讲座或客座教授。
王希:在过去30年里,美国的美国史研究经历了一场重大的转变。您能不能首先概括一下这场转变的主要特点?
方纳:美国史研究在过去30年里的确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可以说这个变化的过程至今仍在继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便是社会史学(有时也称为新社会史学)的全面崛起,并取代传统的政治和外交史学而成为了美国史研究的中心内容。史学界的这场转变是美国新一代历史学家多年奋斗的结果。新一代历史学家中的许多人经历过60年代社会运动的熏陶,深受那个时代社会改革精神的影响,他们一直主张美国史研究的主体应是普通美国人的经历,而不只是那些政治精英和领袖,这一代人现在已经成为美国史研究的主力军。
社会史学的兴起和发展,不仅丰富了美国史本身的内容,也极大地拓展了美国史的研究范围。社会史学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扩大了在美国历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演员队伍”,换句话说,就是对那些被传统美国史学无视或忽视的美国群体的历史给予了高度重视。非裔美国人(African Americans)便是这些群体中最首要的一个。从1960 年代起到现在,各个历史时期——无论是奴隶制时期、内战或重建时期,还是20世纪——的美国黑人史以及种族关系史、种族主义史等一直是美国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应该说明的是,以社会史学为主导的新美国史学所做的并不是在传统史学的故事中加入有关黑人的内容,而是力图改写传统的美国故事的内容,对传统的历史结论提出挑战。同样是讨论民主、自由或经济机会等问题,但如果历史学家是从黑人的角度出发或将黑人作为这些问题的中心,他们很快发现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和解释比起仅从白人的角度来研究时有很大的出入。
妇女史的兴起也是美国史研究转型的结果之一,而且还把美国历史的“演员队伍”的人数翻了一番。妇女史在刚开始时只在传统史学的内容上增加一些有关妇女的故事,简单地说,就是把妇女的历史代表性地附带在男人的历史上,并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但到后来当妇女史研究引入和使用了“社会性别”(gender)这个概念之后,妇女史就对整个美国史学的研究发生了革命性的影响。现在gender这个概念已经与阶级(class)、种族(race)和政治结构(political structure)其他几个经典概念一起成为历史分析中常用的一个中心概念了。今天历史学家研究美国史,如果不或多或少地将“gender”考虑在内,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妇女史可以说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
其他领域也经历了类似的转变。譬如说,传统的美国劳工史只注重对工会的研究,工会的结构、劳工组织的兴起以及重要的工会领袖如塞缪尔·冈波斯(Samuel Gompers)或约翰·刘易斯(John Lewis)等是劳工史的经典题目。新劳工史则注重研究普通工人群众的历史,不光研究工人们在工作场所的工作经历,也研究他们的日常生活,包括他们的家庭结构、家庭生活、宗教活动以及他们闲暇时间与内容等等。这样,劳工史就不再仅仅是工会史, 而变成了属于工人阶级的人民史( thehistory of working class people )。新劳工史也包括了对黑人和妇女劳工的研究,而这两个群体曾经长期被排除在劳工组织之外,也未受到传统劳工史的重视。事实上,美国历史上仅有三分之一的工人是工会成员,即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工会发展到顶峰时期也不过如此,所以对美国工会历史的研究不能等同于对整个美国工人阶级历史的研究。社会史学的其他一些重要分支一如家庭史、性别史、刑事犯罪史和城市史等一也都产生了相当重要的研究成果,成为了当代史学研究中的显学。
八十年代社会史学主导美国史研究时,一些从事政治史、外交史和思想史研究的人曾一度感到压抑和被动,甚至可以说在史学界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但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社会史学本身也遭遇到了其他新的流派的挑战。所谓“语言学派”就是对社会史学的一种挑战。语言学派的学者主张把研究的主体从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转移到语言自身,他们感兴趣的不是社会现实本身,而是现实经过语言和话语的媒介而被理解和被体验的方式。语言学派的学者注重对交流方式的研究,注重对交流方式随时间推移而产生的变化的研究,他们关心的是交流方式本身如何反映了普通人对日常生活的体验这类问题。语言学派在美国史领域内远未取得它在英语文学领域中那种支配性影响,但它仍成为了历史研究中的一种重要的分析手段。
近来我们注意到文化研究开始对美国史研究产生重要影响。形象(image)、语言(rhetoric)和表述(representations)等取代了真实的生活经验,成为了历史学家研究的对象。研究劳工史的学者现在开始去研究电影、文学作品和大众话语中的那些涉及劳工的形象或语言。妇女史或社会性别史的学者则去研究表现在不同媒介中表现男性或女性的社会性别的形象以及这些形象如何在社会斗争和政治对话中得以反映。最近还有一些学者开始了关于“白色”(whiteness)的研究, 他们研究的重点不是涉及种族关系的法律问题或政治斗争,而是种族的形象问题,即人们是怎样进行种族识别和种族认同的,或者说人们在现实中如何来确定和认同自己是一个白人或非白人的。这些历史学家们认为,“种族”(race)的概念是社会成员和群体进行自我和相互识别和认同的一种通用性概念,可以用来研究包括白人在内的美国社会的所有成员,而不只是用于研究非白人民族或种族。在他们看来,“白人”(white)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带有种族性质的概念(a racial construct),它与“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等概念一样,也是一种用于构成社会认同的概念。
虽然文化研究和语言学派看起来是史学研究的前沿方法,但美国史本身是一个范围非常宽广的领域,实际上各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和解释都在同时使用,直到今天,继续从事总统政治或外交条例研究的也仍然大有人在。我认为,过去30年史学发展的最主要贡献之一就在于,它使美国历史学家比从前更深刻全面地意识到了美国人历史经验的多元化,它使我们比从前更不情愿地仅凭对一些狭隘有限的历史经验的研究就简单匆忙地作出那种对美国史带有高度概括性的结论。
五十年代,史学界的一些书常常冠之以“美国心灵”或“美国性格”的题目出版。这些书的研究对象往往是几个新英格兰地区的文人作者,再加上几个南部绅士,于是就构成了一部描写整个美利坚民族心路历程的著作。今天,因为我们更为真切地认识到了美国人口的多元化,我们因而不大愿意去做这样简单的结论。但也许正因为我们比从前更加小心翼翼,更强调对个别群体的历史经验的研究,我们有可能比从前更容易忽略对整体美国史画面的研究。
我应该补充一句,在某种意义上,史学总是产生它的那个社会和时代的反映,尽管这种反映不一定是直接的。自从1965年新的移民法开始实施以来,美国人口构成出现了极为戏剧性的变化。随着来自拉丁美洲和亚洲的移民大量进入美国,原来那种美利坚种族黑白二元论(bina-ry of black and white)的区分法今天已经过时了。 这种二元论从来就是不准确的,但在19世纪却始终是一种现实而适用的思考种族问题方式。美国人口组成的多元化也导致和带动了对亚裔和拉丁语裔美国人的历史的研究。这种情形一方面说明迄今为止美国历史的“演员队伍”仍在继续扩展,另一方面也说明要作出一个能准确地涵盖所有美国人历史经验的史学结论将面临何等的困难。
王希:您的第一本主要著作在1970年出版,正好处在史学界这场革命性变革的初期,您显然经历了这场史学革命,您如何看待自己在这场变革中的位置?(注:这里指的是埃里克·方纳:《自由土地,自由劳力, 自由人:内战前共和党的意识形态》(Eric Foner,Free Soil,Free Labor,Free Men:The Ideology of the Republican Partybefore the Civil War)纽约,1970年。该书于1995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再版。)
方纳:我开始自己的研究时,可以说还是一个传统的政治史学家。我当时的研究题目是意识形态,但我实际上真正研究的是政党政治和政治领袖。这样的研究直到现在还有人在做。我认为,只要“政治”这个概念不是局限在国会辩论和选举这类狭隘的范围内,政治史的研究仍然十分有用。研究选举活动和过程本身也没有什么不妥,但在政治史的研究中,“政治”这个概念的内涵一定要扩展,“政治”应该包括政治权力在现实生活中的许多领域内运作和运用的内容和方式,“政治”不仅存在于社会生活,也存在于家庭生活中。譬如说,传统的妇女史很重视妇女选举权的研究,这几乎是妇女史的一个经典课题。但新妇女史却使我们认识到妇女对于政治的参与和影响早在她们获得选举权之前开始了,禁酒和废奴团体等自愿性的妇女组织都是妇女对政治施加影响的重要媒介。换句话说,在她们还没有赢得政治程序中那些决定选举结果的位置之前,美国妇女就在公共生活中找到并扮演了影响政治的角色。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 Jurgen Habermas )提出的“公共领域”( public sphere)的概念是一个重要的分析历史的概念, 对于认识和理解政治在社会不同层次上的发生和运作,相当有用。当然也有历史学家继续在做总统传记或传统的政党研究,迈克尔·霍尔特(Michael Holt)去年出版的那本1200页的《美国辉格党的兴起与衰落》大部头就是一个例子。(注:迈可尔·霍尔特:《美国辉格党的兴起与衰落:杰克逊时代的政治与内战的开始》(Michael F.Holt,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American Whig Party:Jacksonian Politics and the Onset of the Civil War)纽约,1999年。)有人认为这本书虽然有价值,但主题和风格都过于陈腐,带有旧史学的遗风。现在继续这样写历史的人是越来越少了。这部书能不能得到史学界的大奖倒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因为它的确代表了一种回归传统史学的趋向。(注:根据美国历史学会的通讯报道,《美国辉格党的兴起与衰落》获得了由葛底斯堡学院的林肯与葛底斯堡研究所主持评选和颁发的 2000 年的林肯史学奖 (
The Lincoln Prize)。这是美国内战史研究领域的一项最主要的专业学术奖,通常只有一部著作获奖,但今年却同时有三部著作获奖,其他两部获奖的著作为:约翰·霍普·富兰克林与洛伦·施文宁格:《逃跑的奴隶:种植业中的反抗者》( John
Hope
Franklin
andLorenSchweninger,Runaway Slaves:Rebels on the Plantation), 牛津大学出版社和艾伦·格尔诺:《林肯:悔过者总统》(Allen C. Guelzo,Abraham Lincoln:Redeemer President)(W.B.Eerdmans),《美国历史学会通讯》(AHA Perspectives)2000年4月号第3页。)我认为,政治史的研究者并不需要抛弃自己的研究计划,但必须吸收和囊括新的研究方法和成果。无论怎么说,历史学家总不能对近年来史学界的变化视若无睹,而一味埋头按照原来的路子进行研究和写作。
王希:美国史研究方面的变化对美国史的教学有什么影响?
方纳:传统的美国史学以从殖民地时期至今美国政治和思想的发展为基础,建立了一套定义清楚、脉络清晰的美国史叙事模式。尽管这种模式对美国史所作的结论并非完全准确,但它却有一种高度的概括综合能力,能清楚地勾画和界定美国发展的脉络,尤其适用于美国通史课的教学。今天的美国史教学可就不那么容易了。如何将美国历史经验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的内容准确地传达给学生,如何帮助他们理解自由和民主等这些概念本身不断被质疑、挑战和重新定义的历史事实,我们目前还没有找到有效和通用的答案,所以美国史的教学要比从前复杂和困难得多。除此之外,档案研究与课堂教学之间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为了弄清美国史上的一个具体问题,你也许要在档案馆里苦苦研究若干年,但你能在通史课上与学生讨论这个问题的时间恐怕不会超过5分钟。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采用叙事模式的问题,即历史是不是一定要用叙事体来写作。 现在有的学者已经把叙事性历史(historicalnarrative)作为一种虚构性的写作(fiction)而彻底抛弃了。在海登·怀特这样的后现代历史学者看来,历史研究和写作说穿了无非也是一种虚构,历史学家的工作无非是在创造发明一种叙事模式,即选取一些过去发生的事,将它们串连起来,再人为地加上一些这些事物本身并不具备的意思,以增强叙事的故事效果。(注:海登·怀特(Hayden V.White)(1928—),后现代派历史学家, 曾先后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圣克鲁斯分校历史系任教,主要著作包括:《大历史: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Metahistory: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Nineteenth-Century Europe)巴尔的摩,1973年, 《形式的内容:叙事体话语与历史代表性》(The Content of the Form:Narrative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巴尔的摩,1987年。 )这种批评有它的可取之处,至少它提醒历史学家在研究和教学时在选择材料和方法时要倍加审慎,不要将那些没有经过明确论证的推论当成事实和真理强加于人。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教历史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创造不同的叙事模式,这就是历史学的本质:表现和叙述因时间的推移而产生的变化。尽管新史学注重对普通美国人历史的研究,但在教学中,历史学家仍然脱离不了讲述杰斐逊、林肯和罗斯福这样的政治人物。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些领袖人物把你描述的美国历史连结起来,使其成为一个连贯的整体。所以,即便是那些反对使用叙事体的人在教历史时也不得不采用这种方式。你总不能象一个社会学家那样来教历史课吧,只是给学生机械地罗列一大堆不带历史概念的事实和数据。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不是历史学家了。所以,历史教学的问题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如我刚才提到的,主要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如何将史学研究的新趋势和新成果贯穿到大学历史教学中去的路子。
王希:有没有什么有效的方法能将传统的叙事性历史与新史学结合起来,使它们成为相辅相成而不是相互排斥的教学和研究方式?
方纳:我在最近出版的新书《美国自由史话》中就进行了这方面的尝试,成功与否,另当别论。(注:埃里克·方纳:《美国自由史话》(Eric Foner,The Story of American Freedom),纽约,1998年。此书的中文版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我想展示的就是历史学家有可能创造出一种既有别于传统的叙事模式、但又具有连贯性的新美国史叙事模式,你也许可以把这种方法称为一种“质疑性叙事体”(a contestednarrative )。 这是一种不确定的、 无预设限制的叙事性历史(anuncertain,open-ended narrative ),它没有一个事先决定的开始、中间和结尾,也并不只是叙述美国历史上的进步和成就,事物的发展总是既有前进,也有倒退,并非只是遵循一条永恒向前的直线。“质疑性叙事”的目的就是要说明,在美国历史上的每一时期内,许多的事物和观念总是处在不断地被人们质疑和辩论的状态之中。我在书中描述了“自由”作为美国社会和历史的中心思想在美国历史上演变的过程,我想展现在美国历史的不同时刻“自由”这个概念是如何引起争议、受到质疑和被重新界定的。在这样的叙事体中,事物的不确定性始终是研究和写作要考虑的重点。这样做可能会使学生也产生一种不确定感,他们甚至可能因此感到有些不适应,但这是解决美国史教学面临的困难的一种尝试。
王希:要解决这个问题恐怕有一定难度,因为教学是一项个人意志和个人取向性都很强的活动,不同的教师对同一个历史问题,不光是教学方法不同,而且很可能对问题本身的理解也不同,在这种情形下,要建立一种通用的教学模式是相当困难的。
方纳:正是如此。在美国,我们没有统一规定的全国性教科书或教学大纲,也没有统一的教学规定,大学里面更是如此。教师也许是最后一批传统的手工匠人(artisans)—因为他们仍然在自己的工作场所继续掌握自己谋生的工具。我想这种情形将在21世纪被改变,传统的大学最终会被集团化或者为网络技术占领或取代。但是,只要有历史教师的存在,教历史的方法就一定会是多种多样的。
王希:近几年来,美国公众舆论就历史问题展开了好几场大辩论,为什么美国公众会突然对美国史的写作和解释如此地关注和投入?
方纳:美国历史在1990年代一度成为公众辩论的焦点,这着实使许多历史学家大吃一惊。一般来说,美国的公众和舆论界并不关心历史学家的研究,但在90年代里,史学界内出现的对美国史的重新解释和对旧史观的修正却变成了热门的政治问题。这些引起争论的问题包括制定和颁布全国性的中小学历史教学标准,在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举办有关美国在日本投掷第一颗原子弹的展览,迪斯尼乐园希望建造一个以美国历史为主题的游乐场的计划,在首都华盛顿举办有关奴隶制的展览,以及修建纪念犹太人被纳粹德国大屠杀的纪念馆等,还有南部邦联的旗帜是否应该继续悬挂的问题等,这些都涉及到美国历史上的敏感问题或者说继续被质疑的问题,因而在公众中引起了激烈而持久的辩论。这些辩论的核心实际上是美国应当怎样书写和纪念自己的历史。就对待历史的态度而言,美国人实际上是一个很矛盾的民族。一方面,美国人—当然这是一种泛指—是一个注重未来的(future-oriented)民族。 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当年曾说过:“我们的过去决定了我们要创造一个崭新的世界。”在潘恩看来,建立美国的真正意义是对过去的抛弃;这个过去就是欧洲大陆,就是旧世界,而美国是一个属于未来的国家。与其他民族国家不同的是,美国的国家认同的不是由那种根基于数百年历史而形成的国土疆界或那种经过数代人的积累而形成的单一的民族(volk)传统来确定的。美国人既不是由一个共同分享的过去、也不是由一个对未来的共同期望连为一体的,因此有些美国人认为历史是无关紧要的。若干年前,在国会调查伊朗门事件的听证会上,当里根总统被问到一年多以前发生的事情时,他回答说:“那已经是古代史了,已经不重要了。”在他看来,发生在一年以前的事就已经是古代史了!
但另一方面美国人又十分重视历史,对历史充满了强烈的兴趣。眼下历史很受大众的欢迎。有线电视网中的“历史频道”属于热门频道,历史书的销路不错(尽管销路好的历史著作并不一定是由专业历史学家写的)参观和游览历史博物馆、历史遗址及类似葛底斯堡这样的国家历史公园的人终年络绎不绝。对许多人来说,历史带给他们一种认同感,一种家庭的认同感和一种民族的团结感。人们不仅看重历史,更看重历史的功能,对历史功能的发挥和运用也很投入。保守派认为历史的功能就是向人民灌输爱国主义思想。前一段时间,曾有人指责历史学家在写作中没有足够地强调国家的目的,没有充分地表现爱国主义思想,没有对美国民族的内在凝聚力给予应有的认可和强调等等。与此同时,其他一些群体对历史又抱有另外的期望。传统的历史研究把黑人排除在外,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黑人权利被剥夺的现实;民权运动将黑人重新纳入美国历史的范畴,也推动了对黑人历史的重新书写。妇女史也是女权主义运动在60年代复兴的结果。对于这些从前受到排斥的群体来说,历史研究是一种使他们原来所处的历史地位合法化的途径,他们希望通过对他们历史地位的重新定位和评价来建立一种新的对美国历史和美国国家的认同。这些不同的诉求显然给历史学家的工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历史学家的工作不应该是为了帮助某一个社会群体做到自我感觉良好,因为我们不是心理学家。无论是对那些在历史上受到过压迫、而迫切要求在历史中寻找国家认同感的群体,还是那些坚持历史的功能就是向人民灌输爱国主义思想的群体,历史学家的工作不应该是简单地去迎合或满足这些群体的愿望,增强他们的自尊心,让他们为自己的过去感到骄傲等等。历史学家的工作应该是把过去发生的故事——包括这种故事本身具有的种种复杂性,以及它所具有的正面和反面的内容一尽可能准确而有力地讲述出来。这是历史学家的责任。
历史研究当然不能回避政治内容,事实上历史学家提出和关心的问题本身就受到他们所处环境的影响。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史学研究被当成一种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其成果也就往往变成一种不可信赖的历史了。如果一个人研究历史的出发点仅仅是为了证明和宣扬某一特定的政治观点,他可能不得不对历史作简单化的处理,甚至有可能曲解的割裂历史。所以,历史学家面临很大的压力,肩负重要的责任。我们的工作就是保证人民能尽可能地获取最好的历史感(sense of history)。有一件事时常令美国历史学家感到苦恼,那就是尽管公众社会对历史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但真正懂得美国历史的人却不多。这一点在一年前克林顿总统遭弹劾的前后表现得尤为突出。当然我并不指望所有的新闻记者或普通群众对弹劾总统的细节都做到了如指掌,很多历史学家也不一定知道美国历史上出现过多少次弹劾,但人们起码应该知道制宪者们当初为什么要建立弹劾的机制,至少要懂得弹劾作为一种法律程序所必须依赖的基本原则等。但真正深入了解这些知识的人实在太少了,这说明我们历史学家还需要更努力地工作。
王希:作为现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您认为美国历史学界在近期将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方纳:我想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是如何使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能在历史学界得享一席之地。如前面提到的,我知道有相当一批历史学家有一种被新史学排除在历史学界以外的感觉,他们觉得自己从事的研究不再受到重视,有的研究甚至被贬为过时的或不重要的,他们的研究领域也不再具有什么重要意义等等。毫无疑问,新史学为历史研究带来了新鲜血液,历史学家不可能总是重复同样的研究,每一个时代都会有自己的方式来研究历史,这一点是无可非议的。但是,新一代人有时会以否定上一代人成果的做法来界定和树立自己,这是需要审慎而行的。随着我自己在开始告别中年,我对老一代历史学家的尊重日益增加。我认为,史学界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必须具有包容性(inclusive )的时候了,所有形式的史学研究都应在史学界受到欢迎。
我们面临的第二个挑战与其说是与历史研究有关,不如说是与历史教学的机制有关。如你所知,我们目前面临一个严重的历史学家的就业问题。因为大学聘用的史学教授的人数远不如过去多,刚刚拿到博士学位的人要想顺利地在大学里谋得一个全职工作远不象从前那样容易。许多人只能屈就去做兼职或临时教授,他们的工资不高,作为教授应享有的权利很少,晋升和转正的希望渺茫,如何使这些历史学家获得起码的有尊严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是一个重要问题。历史是一门重要的基础学科,与其他任何学科相比,它都应该被看成是一门非常中心的学科,我们必须要使社会、政治人物、州议会和大学认识到这一点。当财政出现紧缩和困难时,政府和学校的决策者们往往首先裁减的是历史、文学和艺术这些看起来并不具有任何现实重要性的学科,他们觉得这样做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而且也更有道理。他们认为,把钱花在科学研究、技术培训、电脑培训等课程上显然要比把钱花历史学科上更为明智和更具有说服力,因为科技课程可以为学生毕业后找工作提供直接现实的好处。这些决策者应该懂得,历史也许不一定能帮助学生找到某份特殊的工作,但历史能够培养学生学会如何思考,帮助他们学会在民主社会中扮演一个有思想的公民的角色,学会思考比简单地为找一份工作而学习要重要得多。
王希:历史学界本身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呢?譬如说:新史学会不会面临挑战?
方纳:历史学界已经出现了一些对新史学的批评,这些批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其中一种批评认为,新史学在研究内容的扩展、方法的多元化以及要求对所有社会群体面面俱到的做法,已经导致了美国史研究中的“碎化”(fragmentation)现象和趋势。 持这种批评态度的人认为,目前的史学非但未能产生具有高度概括和综合性的叙事性美国史,反而把美国史研究变成了一种割裂的地方或个别群体的研究。地方和个别研究本身是非常有价值的,但如果只是把它们简单地拼合起来,我们并不能够得到一个完整的美国历史的总体画面。所以,如前面提到的,我们仍然需要探索一种新的方法,一种既能帮助我们重新把握美国历史的整体面貌、但同时又不至于迫使我们放弃新史学所具备的那种对美国史的深刻的洞察力的方法。 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对综合性历史 (synthesis)的重新呼吁是一种倒退的表现, 认为这是要求史学研究回到政治史为中心的时代,我并不这样认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