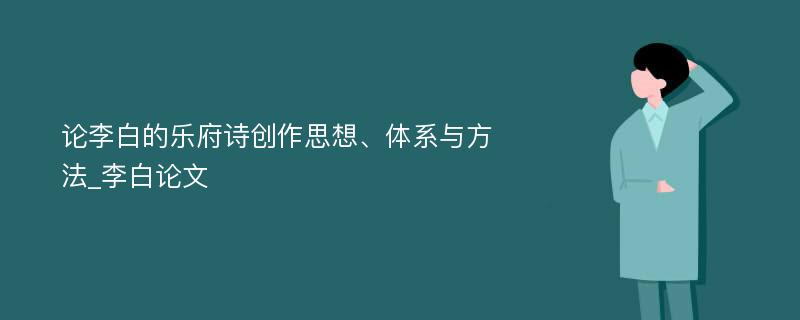
论李白乐府诗的创作思想、体制与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乐府诗论文,李白论文,体制论文,思想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李白的乐府诗创作,是代表了唐诗艺术非凡高度的创造品之一,具有一种奇迹性的特点。对它进行深入的研究,是我们理解唐诗艺术的成因、解开唐诗发展的根本奥秘所必须做的工作。从整体上看,李白乐府诗是他自觉追求以复古为创新的诗学发展道路的实践成果,同时也是他的诗学思想与创作个性达到高度契合所获得的成果。本文打算从上述思考出发,对其乐府诗创作的基本思想、体制与方法做比较系统的论述。同时也由此展示李白乐府诗与汉魏六朝乐府诗复杂、多层的关系,并试图解答李白是如何通过复古的方式达到与诗歌艺术创造规律高度契合的境界的。
一
李白的乐府诗创作,是他复古诗学的重要构成之一。除了《古风》类的写作之外,古乐府写作也是李白终生追求的事业,《唐诗纪事》有这样一个记载:
韦渠牟,韦述之从子也,少警悟,工为诗,李白异之,授以古乐府。权载之叙其文曰:初,君年十一,尝赋《铜雀台》绝句,右拾遗李白见而大骇,因授以古乐府之学。①
由“授以古乐府之学”可见,李白的古乐府写作内部包含着有成熟的诗学系统。从魏晋到盛唐,文人诗创作的复古、拟古作风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在魏晋时代,由于文人创作的五言诗与乐府诗所使用的体制、曲调多来自汉代,并且早期文人诗的写作方法也还不太成熟,所以在创作上比较自然地趋向于摹拟前人,形成了在篇制甚至题材内容上转相沿袭的作风。尤其是在傅玄、张华、陆机等人的写作中,拟古成了重要的方法。此后刘宋甚至齐梁的部分诗人、诗篇,仍采用这种魏晋式的拟古方法。但从齐梁以后,这种拟古方法日益陷入陈陈相因、缺乏新意的困境中。而在另一方面,刘宋以来的诗歌发展以新变为主要趋势,体物、写景、缘情的因素不断增加,声律艺术也开始出现,诗歌开始转入以景与境为主要因素的发展方向,以叙事、言志、比兴为主要特点的汉魏艺术传统开始衰落。但在这种齐梁以降整体趋新的风气中,一部分的诗人和诗歌作品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模拟汉魏诗歌,沿承晋宋旧体。他们可以说是唐代复古诗学的先声②。但这时期的复古诗学,还没有完全明确,一直处于摸索之中。我们看魏徵主编的《隋书·文学传论》,在指示新王朝的文学创作方向时,仍然只提到将“江左之清绮”与“河朔之贞刚”相结合的方法,也就是走融合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的发展道路。这其实是隋代的一些诗人已经初步探讨过的。在文学史观方面,仍属于齐梁文学观的范畴,还没有发现复古方法的重要性。只有到陈子昂提出“汉魏风骨”的概念,复古诗学才真正得以确立。到了李白登上诗坛的时代,则复古诗学已经占了主流的地位。不仅作为唐人复古体制的古风和五、七言古体已经确立,而且源自齐梁的近体诗,在语言与风格方面也受到了复古诗风的影响,形成了声律、风骨与兴象比较圆满结合的作风。
上述魏晋南北朝的拟古、复古创作风气,以及初唐陈子昂以来的复古诗学,共同构成了李白复古诗学的基本渊源。但是李白的复古诗学并非是对上述传统的简单继承,而是对初唐以来复古诗学的一个深化。或者说,在盛唐诗坛绍复汉魏与沿承齐梁两派已经取得比较好的融合、古体与近体两种体裁都得到比较平衡的发展的时候,李白再次提出复古的问题,仍然以齐梁宫掖之风为革新的对象,这对盛唐诗坛无疑是一个突破。而且我们还发现,虽然陈子昂、张九龄等人是唐代复古诗风的开创者,但明确提出“复古”这个概念的,很可能是李白。唐孟棨《本事诗·高逸第三》云:
白才逸气高,与陈拾遗齐名,先后合德,其论诗云:“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与!”故陈李二集律诗殊少。③
又李阳冰《草堂集序》:
卢黄门云:“陈拾遗横制颓波,天下质文翕然一变。”至今朝诗体,尚有梁、陈宫掖之风,至公大变,扫地并尽。
这两条材料,第一条是李白自述其诗学宗旨;第二条是他同时代的卢藏用对他的评价,都着眼于李白的复古诗学,都强调他继陈子昂之后进一步提倡复古,并且以当时诗坛上尚存的齐梁宫掖之风为革除对象。这不能不视为李白全部诗学的出发点。与李白同时,但在诗坛发生影响比他更早一些的王维,他的创作,在体制、题材与风格上,也有不少的创新,但并没有形成像李白这样明确的进一步复古的思想。所以王维的诗风,是对汉魏六朝至初唐的诗风比较自由的取舍与综合。后于李白的杜甫,则是自然地继承当时诗坛上流行的古体、近体及歌行体,将主要精力放在发展这些体制的创作艺术,在表现与再现的强度上突破古人,同时在题材与风格上对诗歌史作出全面的继承与发展,从而取得“集大成”的艺术成就。如果说王维、杜甫与诗歌史及当时的诗坛风气的关系,是顺流而下、因势利导的关系,那么李白与诗歌史及当时诗坛的关系,可以说是一种逆流而上的发展方向。他要彻底扫除齐梁以来因声律、隶事、偶对诸项因素而造成的程式化作风,要完全克服齐梁以来诗歌艺术中因循、递相祖述的惰性,走完全独立的复古与创新之路。表面上看,他在古风、古乐府的创作中采用了当时看来已经比较落后的拟古、代言的写作方法,但他的真正目的并不是简单地复古,而是要通过个人创作,来重新书写李白个人的诗歌史。这无疑是一种富有英雄主义色彩的创造行为。正是因为这样,李白的这种逆流而上、彻底复古同时也重新书写诗歌史的创作道路,只能是他个人的天才行为,不具备可取法性。从为诗歌史确立一种写作范式来看,希望通过自己的创作全面复兴古道从而使齐梁宫掖之风扫地并尽的李白式的复古方法,其实是失败的。因此,我们还可以说,在盛唐诗国中,李白是一个悲剧的英雄。要解释这个悲剧发生的历史与个人的原因,显然是很困难的。
李白的复古诗学,如果寻找它内部的体系,最核心的是古风与古乐府。古风又派生出的一般的五言古诗;其中的一些山水纪游之作,源于陶渊明与大、小谢,也部分地带有复古的色彩。古乐府的系统又派生一般的七言与杂言的歌行体,可以说是乐府体的一个扩大。除此之外,李白日常吟咏情性、流连风物的五律体、五七言绝句等近体诗,也在风格上程度不同地受到上述古体、古乐府体的影响。虽然从李白自身的认识来看,五言尊于七言,古风尊于古乐府。但以他实际的创作成就来说,是七言高于五言,古乐府高于古风。由此可见古乐府在李白的诗歌创作中,实为重要的一部分。而上面所说的李白诗歌创作逆流而上、试图以个人创作重新书写诗歌史的特点,在他的古乐府创作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从李白的《古风》其一我们看到,他的观念中最为崇高的诗体为大雅,其次是《国风》,他的《古风》五十九首,就是试图由汉魏言志比兴的古诗上溯到国风④。风与雅的区别,是在表现的对象上,风是主要通过个人的情事来反映国俗的兴衰,雅则是直接地表现国俗与国政。《毛诗序》对此有很好的阐述:“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大雅焉,有小雅焉。”这样的思想,李白当然很熟悉,他的《古风》五十九首,就是按照这种诗歌思想来写作的,其中有正面地“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的雅的成分,但更多是通过具体的个人的情事来反映古今政治与风俗之兴衰。汉魏六朝的乐府诗,是典型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何休《公羊传解诂》)的里巷歌谣,而经过文人儒者的阐述,其中含有政情与国俗的兴衰,与《国风》的性质正好相近。所以,在李白等唐代诗人的观念中,风雅之后,最重要的诗歌就是汉魏六朝的乐府,尤其是原生的汉乐府与南北朝乐府民歌,其次才是魏晋南北朝的文人诗。这个风雅之后,接以乐府,而以文人拟作乐府为等而次之的排列次序,在元稹的《乐府古题序》中表达得很清楚:
自风雅至于乐流,莫不讽兴当时之事,以贻后代之人。沿袭古题,唱和重复,于文或有短长,于义咸为赘剩。尚不如寓意古题,刺美见事,犹有诗人引古以讽之义焉。⑤
李白之所以大量创作古题乐府,正是由“风雅至于乐流”这样的诗歌史观念出发。乐流成了仅次于风雅的诗歌经典,反映到李白的创作中,则是在写作《古风》五十九首之外,又创作了大量的古题乐府,包括他的模仿歌曲形式的歌行体,也属于乐流范畴。可见其对乐流的重视,亦可见由元稹概括出来的“乐流”这一概念,实是支配着唐代复古诗学的重要思想。而唐人对“乐流”重视,最典型地反映在李白古乐府、歌行,元白新乐府,李贺的歌诗这几宗重要的创作成果上。
要了解“乐流”在唐代诗人那里何以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就要对诗歌史由乐章到徒诗的发展规律有所认识。从诗歌史的发展来看,乐歌是文人徒诗的母体,而“乐”则是诗歌原生的、本质的精神。文人持久的拟乐府创作,正是对这个母体的回顾,并且体现了以“乐”为诗歌的原生精神的艺术思想。这当然也是李白乐府诗创作的基本思想。但除此之外,李白的个性最接近乐诗的精神,也是将其导向大量的乐府创作的主观条件。汉魏六朝乐府诗歌是在充分的音乐文化环境中产生的,与文人诗歌尤其是齐梁以降的文人诗歌相比,体现了更为自由、原始的诗歌创作精神,这一点与李白奔放不羁的个性与非凡的想象力等主观素质正好契合,由此造成了以汉魏六朝乐府诗为母体的李白的古乐府与歌行的写作。所以,在李白的诗学观念中,音乐本体的思想是很突出的。当然,对于一位古代的诗人来说,如果重视风雅颂,重视乐流,最理想的做法,就是为其当代王朝制作各种实际入乐的雅俗乐章,李白是否有这样理想,这一点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他创作过《宫中行乐词》、《清平乐三首》这样的乐章歌词,这说明他与当代乐章的写作并非完全绝缘。但是,这种当代乐章的写作,不可能全部容受李白的创作热情。因为李白的诗歌艺术,本质上还是植根于汉魏六朝以来高度发达的文人徒诗系统之中。与作为歌者的李白相比,作为徒诗作者的李白是更为根本的⑥。这是他采用了拟古乐府的拟乐章创作形式,而不选择当代乐章写作为主要形式的原因。还有一点,唐代的雅颂乐章,并非像李白这样的布衣诗人所能擅作。而作为俗乐的燕乐歌词,从音乐体制来说,则源于南北朝后期开始流行的以娱乐性为主要特点的燕乐,与其相应的诗歌体制正是齐梁艳俗之体,即李白所指斥的“梁陈宫掖之风”。上述两点决定了富有音乐精神、崇尚乐流传统的李白,只能选择汉魏以来的乐府诗为其模拟对象。
除了“乐流”这个重要的概念外,“讽兴”也是李白乐府创作中核心性的概念。据上引元稹《乐府古题序》“自风雅至乐流,莫不讽兴当时之事”可知,讽兴是唐人对古风、古乐府的基本创作精神的概括。在唐代诗人看来,有无讽兴是源于风骚汉魏的古风、古乐府与沿自齐梁的近体诗的基本区别。元稹《叙诗寄乐天》论到他自己的诗歌创作时说:“其中有旨意可观,而词近往古者,为古讽。意亦有可观,而流乐府者,为乐讽。”《毛诗序》概括诗歌创作的精神时说:“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又在论六义之“风”时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唐人的“讽兴”之说,即来自《毛诗序》的这些理论。这些理论当然也是李白古风、古乐府写作基本的指导思想。而后人在论述李白乐府诗时,也强调其讽兴的特点。如胡震亨《李诗通》云:
太白诗宗风骚,薄声律,开口成文,挥翰雾散,似天仙之词。乐府连类引义,尤多讽兴,为近古所未有。⑦
胡氏以“连类引义,尤多讽兴”评李白乐府诗,可谓深中肯綮。其中“连类引义”为方法,“讽兴”则为旨趣。又应泗源《李诗纬》还指出李白的一些写男女之情的作品,也有君臣遇合的政治性寄托在内:
太白愠于群小,乃放还山,而纵酒以浪游,岂得已哉。故于乐府多清怨,盖不敢忘君也。夫怨生于情,而情每于儿女间为切切焉。读勿以其辞害意可矣。⑧
应氏所说的,正是胡氏所说的“连类引义”的一种表现。屈原的《离骚》、《九章》、《九歌》等作品,开创以香草美人喻君子、以男女离合喻君臣之际的传统,其寄托的精神与方法自然也被汉魏晋诗人所继承,李白的古乐府创作,正是对这一传统的发展。汉魏六朝的乐府诗,原本为一种娱乐的艺术,多出于民间里巷歌谣,劳者歌其事,饥者歌其食,又多写男女相爱及其别离的种种情事。李白多依古题古义,所以其乐府也多写儿女之事,有些是仅仅实写男女之情;有的则是有君臣之际、朋友之际遇合仳离之意,人生失意之感的寄托;但 总的看来,都是寄托着李白对人生、社会的感喟,都是具有讽兴宗旨的。乐府自晋宋以下,转为模拟,但陆机、谢灵运等人之作,多重于意,常在旧篇寄托作者的主观感情。鲍照的拟乐府,更是借古题直接地写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矛盾,曲折地表达个人的生活遭遇,抒发个人的情志。但齐梁以下,乐府中赋题咏物之风盛行,远离了汉魏的叙事言志传统:“《落梅》、《芳树》,共体千篇;《陇水》、《巫山》,殊名一意。”⑨李白的乐府诗,与鲍照的渊源关系很深,深受鲍照以古题来写现实生活、抒发个人情志的启发,言志的特点十分突出。所以,他的乐府诗,所采用的基本方法,为汉魏的言志讽兴之体。古今学者在研究李白乐府作品时,也多有指揭:如《梁甫吟》一首,萧士赟评云:“此篇意思转折甚多,盖太白借此以言志也。”唐汝询《唐诗解》卷一二:“此伤不遇时,赋以见志也。”沈寅等《李诗直解》评曰:“此篇太白为《梁甫吟》,屡借古人以言其志也。”《唐宋诗醇》评曰:“此诗当亦遭谗被放后作,与屈平眷眷楚国,同一精诚。”⑩又如《将进酒》,《唐诗解》评云:“此怀才不遇,托于酒而自放也。”《李诗解》亦评云:“此篇虽任放达,而抱才不遇,亦自慰解之词。”(11)应该说,上述言志与抒发怀才不遇之感,是李白好多乐府诗的共同主题。讽喻同样也是李白写作乐府的基本出发点,集中如《乌夜啼》讽君主之荒淫,《上留田》讽风俗之衰薄,《白头吟》、《妾薄命》讽人情之薄幸、男女之仳离。讽喻之外,颂美也是古诗的一种原则,李白乐府诗中,属于颂美的篇章也有不少。如《临江王节士歌》、《司马将军歌》、《东海有勇妇篇》、《秦女休行》,都是以古今烈士、节妇为对象的颂美之作,同样表现了李白个人的人生理想。整体上看,李白乐府诗创作正是上述言志、讽兴为基本的写作原则的一种有宗旨的写作,体现了力求恢复风雅乐流传统的创作理想。
上面我们从复古诗学的基本概念出发,论述了李白乐府诗创作的基本思想,同时也揭示出,在拟古乐府整体衰落的诗坛背景中,李白大量创作古题乐府并且做出巨大的艺术发展的原因。
二
乐府古题以拟古为基本方法,唐人已经对它进行了一些概括。早于李白的卢照邻,在《乐府杂诗序》中就描述过两晋以下以模拟为尚的文人乐府诗的写作情况:
《落梅》、《芳树》,共体千篇;《陇水》、《巫山》,殊名一意。亦犹负日于珍狐之下,沉萤于烛龙之前。辛苦逐影,更似悲狂;罕见凿空,曾未先觉。潘陆颜谢,蹈迷津而不归;任沈江刘,来乱辙而弥远。其有发挥新题,孤飞百代之前,开凿古人,独步九流之上,自我作古,粤在兹乎?(12)
卢照邻是为中山郎余令将贾言忠咏九成宫的新题乐府及许圉师等人的和作汇编成的《乐府杂诗》作序时发表这一番议论的,对晋宋以来拟乐府的写作方法提出了批评,并最早提出新题乐府的写作方法。但是这个时期的新题乐府,其实与隋唐之际的新声乐曲属于同一体系,是带有为新声乐曲提供歌词的性质。其基本的体制,实属齐梁之体。卢照邻指出“共体千篇”、“殊名一意”,正是文人拟乐府所遭遇的困境。正是这一困境,使初唐拟乐府创作趋于衰微,而且出现了像贾言忠这样的尝试用新体作新题乐府的创作现象。但是,用新体作新题乐府,或许能为当代乐章写作创出新路,但拟乐府系统也将因此而结束。李白的乐府诗写作,虽然也有类似于贾言忠等人《乐府杂诗》的写法,如《宫中行乐词十首》、《清平调词》即属此类,从体制上看实为“梁陈宫掖遗风”,李白的复古思想,决定他不可能主要选择这一方向来改革乐府诗风。他所选择的是已经开始被当时诗坛放弃的晋宋齐梁文人拟古乐府的传统,并通过自己的创作激活这一传统。值得注意的是,卢照邻批评历代文人拟乐府因袭前人,作为无谓的文字上的竞争,是“辛苦逐影,更似悲狂”。他说的“罕见凿空,曾未先觉”,是批评历代文人拟乐府缺乏独辟新径的创新思想与方法。其实后者正是李白乐府诗写作的基本方法。所谓“罕见凿空”,即从缘题立意出发,在写作上独辟蹊径,通过对题意的深入挖掘,多层演绎,再加上奇特的构思,以求超越古辞与前人旧作,正是李白古题乐府出奇制胜之法。“凿空”二字,原是司马迁用来形容张骞开辟通往西域的道路,“然骞凿空,诸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苏林曰:“凿,开;空,通也。骞开通西域道。”《索隐》曰:“案:谓西域险厄,本无道路,今凿空而通之也。”(13)卢照邻这里所说的“辛苦逐影,更似悲狂;罕见凿空,曾未先觉”,正是自晋宋至初唐拟乐府诗陷入的困境,正是这种困境使得初唐以来的诗人,逐渐放弃拟乐府的创作,开始转向新题乐府、新歌曲的创作。但是这样做,等于放弃了汉魏以来的乐流传统,所以李白选择的创作道路与时人相反,继续选择古乐府体,但在创作方法上做新的创造。但是,李白的这一创作方法,在唐代并非主流化,尤其是在初唐至盛唐的乐府诗及乐章歌诗的创作流脉中,他是带有反潮流的倾向的。所以,虽然李白古乐府写作取得巨大成就,突破了“共体千篇”的困境,后人甚至赞叹:“太白于乐府歌行,不许唐人分半席。”(14)但是,唐人在评述乐府诗歌的历史时,李白的这种突破似乎没有被充分地注意到,更没有将李白这种高度个性化的“罕见凿空”的拟写方法作为普遍的经验来推广。甚至在古乐府写作方法上实际受到李白影响的元稹,也并没有对李白的创作经验作出充分的肯定。元稹所批评的“沿袭古题,唱和重复,于文或有短长,于义咸为赘剩”的古乐府写作,其中也包括了李白的古乐府写作。尽管接着这句话说的“尚不如寓意古题,刺美见事,犹有诗人引古以讽之义焉”,算是对古乐府写作的部分肯定,而且这里主要还是概括李白的经验;但元白真正肯定的,还是发源于杜甫的“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的写作。只是此时的新题乐府,与初唐的新声乐曲与新题乐府之沿用齐梁体制不同,完全采用古诗、古歌行的体制,并且恢复汉魏写时事的方法,不同于初唐之缘情咏物,并且体兼雅颂。白居易所肯定的也是新题乐府的传统,其《与元九书》论李白时说:“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15)从这里可以看到,唐代文人乐府的两个系统,一为初唐以来的新乐府的传统,一为李白重新激活的古乐府传统,后者显然未受到时人及稍后元白等人的足够重视。
其实,我们说拟古是晋宋齐梁以来古题乐府的基本写作方法,是一个比较笼统的说法。事实上,在文人拟乐府的内部,因为侧重于曲调、旧篇与旧题等不同的倾向,形成各种不同的写作方法。以比较大的视野来分类,有拟调、拟篇与赋题三大类,并且这三种方法也标志着文人乐府的三个发展阶段。汉魏文人的乐府诗,多依旧调制新词,属于拟调之法。这个时期乐府诗多用旧题旧调,受到古辞题材内容的影响,古题对新作的取材范围有一些影响,但基本属于元稹所说的“自风雅至乐流,莫不讽兴当时之事”的一种,拟篇的作法还没有明显出现。至傅玄、陆机的一部分旧题乐府,采用了拟篇的作法,沿流至东晋、刘宋。而此期的五言徒诗中也出现拟古的作风,两者构成晋宋时期拟古诗学的全部。至齐梁时代,诗风由以拟古为主转入以革新为主流。在乐府诗创作方面,为了突破拟篇法的因袭,由赋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的曲名开端,形成缘题立义、专写题面的赋题法。赋题法其实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拟古,但因为毕竟继承了汉魏乐府的旧曲名,而这个曲名对作者的取材与赋写仍然有一种制约的作用,所以广义来说,仍属拟古乐府的范围。李白的乐府诗创作,可以说是对上述魏晋至齐梁各种写作方法的全面继承,并以其特有的“罕见凿空”的非凡想象力与表现力,对前人的写作方法作出了个性极为突出的新发展。
晋宋的拟古诗和拟乐府,好多都是“规范曩篇,调辞务似”(16),在内容与文词上不同程度地模拟旧篇。这种拟篇的方法,在李白的作品也有所表现。太白对自己创作乐府的思想与方法,很少交代。唯有《秦女休行》题下原注:“古词魏朝协律都尉左延年所作,今拟之。”此当为李白自注,也是李白唯一自陈其拟古之法的一条材料。李白的《秦女休》即是典型的拟篇之作:
左延年《秦女休行》:
始出上西门,遥望秦氏庐。秦氏有好女,自名为女休。休年十四五,为宗行报仇。左执白杨刃,右据宛鲁矛。仇家便东南,仆僵秦女休。女休西上山,上山四五里。关吏呵问女休,女休前置词:平生为燕王妇,于今为诏狱囚。平生衣参差,当今无领襦。明知杀人当死,兄言怏怏,弟言无道忧,女休坚词为宗报仇。死不疑!杀我都市中,徼我都巷西。丞卿罗东向坐,女休凄凄曳梏前。两徒夹我持刀,刀五尺余。刀未下,朣胧击鼓赦书下。
李白《秦女休》:
西门秦氏女,秀色如琼花。手挥白杨刃,清昼杀仇家。罗袖洒赤血,英声凌紫霞。直上西山去,关吏相邀遮。婿为燕国王,身被诏狱加。犯刑若履虎,不畏落爪牙。素颈未及断,摧眉伏泥沙。金鸡忽放赦,大辟得宽赊。何惭聂政姊,万古共惊嗟。李白这一首,人物、情节结构全遵原作,可以说是一种改写旧作的方法。左延年的《秦女休行》看似语词参错,但正是用带有说唱故事特点的汉代相和曲的体制,有些模仿《陌上桑》。这是因为其曲调或演艺的方式,与《陌上桑》属于同一类。所以左作富有原生乐府古辞的质朴生动的趣味,场景与动作都很突出,富于戏剧叙事的特点。到了李白这里,则成了一个纯粹的文人叙事诗,人物形象写得更加集中鲜明,叙述结构更加紧凑,并更加注重形容。可见李白虽是模拟旧篇,但以改写为主,并不像陆机《拟古诗》那样“调辞务似”,“神理无殊,支体必合”(17)。
李白的乐府,即使是严格地“规范曩篇”,或者说改写旧篇,也都是采用脱胎换骨之法,自铸伟词,别出窠臼。如《独漉篇》原是晋宋乐府演唱的拂舞歌词,讲为父报仇的故事。李白将其改写成为国报仇,以寄托时事之感。对此萧士赟已经指出:“《独漉篇》即拂舞歌五曲之《独禄篇》也。特《太白集》中禄字作漉字,其间命意造词亦模仿规拟,特古词为父报仇,李白则为国雪耻。”(18)原作叙述情节带有一种迷离的特点,可能与其原为舞词有关系。因其歌词原是与舞蹈及相关布景配合,不同于普通的案头读物。李白的拟作则完全是文士言志之作,但他在“命词造意”上仍然模仿规拟,并且着意再现原作情景迷离、词旨闪烁的特点:
独漉水中泥,水浊不见月。不见月尚可,水深行人没。
越鸟从南来,胡雁亦北度。我欲弯弓向天射,惜其中道失归路。
落叶别树,飘零随风。客无所托,悲与此同。
罗帷舒卷,似有人开,明月直入,无心可猜。
雄剑挂壁,时时龙鸣。不断犀象,锈涩苔生。国耻未雪,何由成名?神鹰梦泽,不顾鸱鸢。为君一击,鹏抟九天。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李白不仅学习旧作的情节与词气,而且对于古乐府“分解”的作法,也有所模拟。可见李白是很重视他的拟作与乐府古辞的血脉关系的。但即使是这样,李白通过白铸伟词,别出窠臼,形成比原作更为奇创的风格。虽然不能说是覆盖旧作,但也获得了与旧篇各具千秋的地位。这一点,是其他唐人的拟古乐府所无法比肩的。我们要知道,李白以一人之力,对垒汉魏以下众多无名与有名氏的古乐府、拟乐府,并且是采用当时看来已经落后了拟篇法,真可谓化腐朽为神奇,其凌轹千秋的雄心,至少在古乐府的创作方面,是冠绝古今的。李白乐府诗也有隐括前人的作品,带有明显改写性质。如《越女词》其四:“东阳素足女,会稽素舸郎。相看月未堕,白地断肝肠。”王琦《李太白全集》:“按谢灵运有《东阳溪中赠答》二诗,其一曰:可怜谁家妇,缘流洗素足。明月在云间,迢迢不可得。其一曰:可怜谁家郎,缘流乘素舸。但问情若何,月就云间堕。此诗自二作点化而出。”(19)这种隐括,也可以说是带有笔墨游戏的性质,体现了李白对乐府民歌娱乐趣味的领会。
从晋宋以降,拟古中出现尊重古意的一派。所谓“古意”,也可以说是一些传统的、经典性的主题。重视古题、古意,也可以说一种拟篇的方法,但是它主要是发挥古意,在具体的情节、情境上则可以做自由的发展。李白的古乐府,有许多都是采用这种方法创作的。如李白《长歌行》、《短歌行》都是沿承古意之作。《长歌行》的本意是歌声之长短,所以汉魏时人所作长歌,并没有特别的立意。古诗《长歌行》有三首,“青青园中葵”一首言人命短暂,当及时努力,实为格言之体;“仙人骑白鹿”一首写游仙;“岩岩山上亭”一首则为游子恋念父母之歌。而魏明帝“静夜不能寐”一首感慨夜中不寐,殷忧丛积,傅玄“利害同根源”一首写报国立功之思。都是各有立意,其立意未见明显的依拟痕迹。但晋宋人陆机的《长歌行》都是写感春物芳菲,人生易逝,是对古辞“青青园中葵”的主题的沿承。于是感慨生命短暂,需要及时努力就成了拟乐府《长歌行》的传统主题。郭茂倩说:“若陆机‘逝矣经天日,悲哉带地川’,复言人运短促,当乘间长歌,与古文合。”(20)后来谢灵运、沈约的《长歌行》,都是拟陆机之作。其基本的结构,是先写时流迁逝之速,后感年时易过,功名难成,或为叹息,或为振作之词,或为及时行乐以消忧。在写法上,陆机只是直接写时流之速,“逝矣经天日,悲哉带地川。寸阴无停晷,尺波徒自旋。年往迅劲矢,时来亮急弦”。谢灵运也是这样写,只不过意象有更易。沈约之作,稍及时物荣衰,“春貌既移红,秋林岂停茜”。李白的《长歌行》正是祖述古辞“青青园中葵”的古意,同时也旁承陆机、谢灵运、沈约诸家的同题作品:
桃李待(21)日开,荣华照当年。东风动百物,草木尽欲言。枯枝无丑叶,涸水吐清泉。大力运天地,羲和无停鞭。功名不早著,竹帛将何宣。(陆《长歌行》:“但恨功名薄,竹帛无所宣。”)桃李务青春,谁能贯白日。富贵与神仙,蹉跎成两失。金石犹销铄,风霜无久质。畏落日月后,强欢歌与酒。秋霜不惜人,倏忽侵蒲柳。
我们可以看到,李白此篇纯用古意,并且体制、结构一仍旧作。在修辞上也是采用陆机开创的用其意而易其语,但是造语奇卓过于前人。李白的《短歌行》与《长歌行》一样,也是用魏晋古意。郭茂倩云:“崔豹《古今注》‘长歌,短歌,言人寿命长短,各有定分,不可妄求’。按《古诗》云‘长歌正激烈’,魏文帝《燕歌行》云‘短歌微吟不能长’,晋傅玄《艳歌行》云‘咄来长歌续短歌’。然则歌声有长短,非言寿命也。”(22)郭氏之说是对的,短歌长歌,原指歌声长短。现存最早的《短歌行》为曹操的“对酒当歌”,实际上是一首酒歌,叙宾主相得以见求贤若渴之意。曹丕《短歌行》为哀悼其父曹操,是因为曹操曾作《短歌行》。傅玄《短歌行》,似写男女从绸缪到仳离的情变之事,大概也是自出其意。但自陆机《短歌行》开始,虽然其体仍用四言,但专取曹操感叹“人生几何”一意,衍为全篇,感叹人生之短暂。此后凡作《短歌行》都是言生命之短暂。如梁代张率《短歌行》,仍然是四言体,写人生苦短,及时行乐之意。可见崔豹所说短歌、长歌言人寿长短,虽不合其原始的意义,但却是符合两晋时期《长歌行》、《短歌行》的立意的。李白《短歌行》也沿承了“言人寿命长短”这一主题:
白日何短短,百年苦易满。苍穹浩茫茫,万劫太极长。麻姑垂两鬓,一半已成霜。天公见玉女,大笑亿千场。吾欲揽六龙,回车挂扶桑。北斗酌美酒,劝龙各一觞。富贵非所愿,为人驻颓光。
此诗所用的是袭其意而易其词的方法。但其感情更为奔放激越,想象力强,意象之奇特生动,远远超过晋宋梁人的旧作。这是李白乐府诗出奇制胜的方法。
李白拟篇乐府的模拟对象,不仅是汉魏旧题,对于南朝的文人乐府,也常有模拟。如《夜坐吟》为拟鲍照同题之作,其命意、造词、体制规仿模拟的特点都很明显。但鲍照是正面地写听歌者的情深意悦,李白则最后一句云:“一语不入意,从君万曲梁尘飞。”写女子因一语失宠,纵有万曲亦不能挽回,其实寄托人生遇合相知之难。但这种对情感进行质疑的笔调,其实也是出于鲍照一些作品。《乌夜啼》是南朝流行的新曲,现存有庾信、萧纲等人的作品,体有五言与七言两种。李白《乌夜啼》:
黄云城边乌欲栖,归飞哑哑枝上啼。机中织锦秦川女,碧纱如烟隔窗语。停梭怅然忆远人,独宿空房泪如雨。
胡震亨注:“《乌夜啼》,宋临川王义庆妓妾所作。庾信《乌夜啼》云:‘御史府中何处宿,洛阳城头那得栖。弹琴蜀郡卓家女,织锦秦川窦氏妻。讵不自惊长泪落,到头啼乌恒自啼。’白诗似本此。”(23)按胡氏说李白此诗用庾信诗意是有道理的。但在写法上,庾信是典型的齐梁赋题法,重在赋乌啼二字,其具体写法,先是形容事物,然后以用丽典。最后两句,稍有情节。李白则以乌啼为背景,专取丽典,塑造织锦女这个人物,加以叙事化的形容。在艺术上是用汉魏的叙事来取代齐梁的赋题。李白《乌栖曲》也改造齐梁赋题为汉魏叙事:
姑苏台上乌栖时,吴王宫里醉西施。吴歌楚舞欢未毕,青山犹衔半边日。银箭金壶漏水多,起看秋月坠江波,东方渐高奈乐何!
胡震亨注:“梁人辞云:‘芳树归飞聚俦匹,犹有残光半山日。金壶夜水岂能多,莫持奢用比悬河。’又徐陵云:‘绣帐罗帏隐灯烛。一夜千年犹不足。唯憎无赖汝南鸡,天河未落犹争啼。’皆白诗所本也。”(24)按李白这首诗的处理方法与《乌夜啼》首相近,用徐陵之作以男女欢会嫌夜短的主题,但创造性地将其与吴王沉溺西施女色相联系,将徐作一般性地写男女之欢悦改变为吴王宫中耽乐之事,由此使这个本是齐梁艳体的题目,改变成有讽刺意义的作品。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李白的古乐府,在模拟南北朝旧篇时,常常用汉魏叙事之法,并且将原本只是一个赋写事物的题目,改造成具有讽喻寄托之意的新作。这也是李白对乐府旧作的一种发展。李白的《白头吟》、《妾薄命》、《怨歌行》、《秦女卷衣》,皆为模拟旧篇,写女子宠衰爱歇,以寓人生失意之感,或君臣遇合之艰。从思想传统来讲,是继承屈骚的以男女之事寓君臣遇合的传统。
三
齐梁是诗歌革新的时代。这一革新的结果是复杂的,一方面通过体制与写作方法的革新,走出晋宋以来模拟汉魏的困境,使诗学由主要通过经典学习的方式来演生,改变为主要通过一种可遵依的体制来演生,并且初步确立法度的意识。这对诗学无疑是一个解放。但在另一方面,这一革新又是抛弃汉魏传统,并且解构汉魏以来以比兴言志为核心的诗歌审美理想为代价的。通过这次革新,诗歌艺术得到了普及,但汉魏诗歌那种原生的诗性精神也被淡释了。而初盛唐的复古派诗人,所作就是将被解构的汉魏诗歌审美理想重新恢复,将被淡释的诗性精神再度凝聚。但是,这种复古行为,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属于天才的个体行为,只有通过天才的创造力,才能神话般地恢复原生的诗性精神,并且跃入更为成熟的创造。李白的复古实践就是体现了这种精神。在乐府方面,李白正是通过复活业已过时的拟古法,将淡释了的诗性精神重新凝聚,并且创造出全新的乐府歌行风格。但是,在创作方法上,李白并非简单地恢复晋宋的拟古法,而是作出创造性的发展。这一创造性发展的渊源,其实来源于李白对齐梁文人拟乐府诗赋题法的继承。
本来魏晋以来的乐府写作,就有一定的缘题的倾向。到了齐梁时代,沈约、谢朓等人开创了赋曲名的写作方法,经过梁代宫体诗人的发展,成为乐府写作的主要方法。这一方法的确立,使拟乐府创作由重视旧篇、旧事、旧词转化为单纯重视旧题。将古题、旧曲名从原生的乐府古辞中单提出来,呼应齐梁时期重题、咏物的风气,形成了一种赋题法。就诗歌创作方法来讲,实是一次意义深远的革新行为。它的影响不仅局限在乐府方面,而且是影响整个诗学的。它使诗歌创作从以无题为主,走向以有题为主。题由此而成为诗歌创作最重要的因素。但是,仅就乐府诗系统的发展来说,这种赋题法的使用是有利有弊的。如它多采用齐梁声律体来赋古题,使乐府诗在体裁上失去了独立性。而在题材上,由于过于重题,使原本以叙事为主的乐府诗,退化为一种缺乏兴寄精神的单纯的咏物诗。所谓“《落梅》、《芳树》,共体千篇;《陇水》、《巫山》,殊名一意”,就是当时人对这种写作方法的弊端的体会。而吴兢的《乐府古题要解》的写作,主要动机即来自对齐梁以来乐府写作多失旧题之意不满。而这正是赋题法流行之后出现的情况(25)。
李白拟乐府的写作方法,如果我们采取由近向远回溯的方式观察,可以发现,除了晋宋的拟调法与拟篇法外,齐梁赋题法也是他乐府诗创作的重要起点。他早年所作的《宫中行乐词八首》,正是沿承齐梁乐章的风格与体制的。只是诗人非凡的创造力,使其摆脱单纯绮靡的作风,创造出齐梁诗人所缺乏的生动的艺术形象。在旧题乐府方面,他的一部分作品,仍是使用初唐流行的以近体赋曲名的作法:
紫骝行且嘶,双翻碧玉蹄。临流不肯渡,似惜锦障泥。白雪关山远,黄云海树迷。挥鞭万里去,安得念春闺。(《紫骝马》)
垂杨拂绿水,摇曳东风年。花明玉关雪,叶暖金窗烟。美人结长恨,相对心凄然。攀条折春色,远寄龙庭前。(《折杨柳》)
白玉谁家郎,回车渡天津。看花东陌上,惊动洛阳人。(《洛阳道》)
从军玉门道,逐虏金微山。笛奏梅花曲,刀开明月环。鼓声鸣海上,兵气摧云间。愿斩单于首,长驱静铁关。(《从军行》其一)
百战沙场碎铁衣,城南已合数重围。突营射杀呼延将,独领残兵千骑归。(《从军行》其二)
塞虏乘秋下,天兵出汉家。将军分虎竹,战士卧龙沙。边月随弓影,胡霜拂剑花。玉关殊未入,少妇莫长嗟。(《塞下曲》其五)
烽火动沙漠,连照甘泉云。汉皇按剑起,还召李将军。兵气天上合,鼓声陇底闻。横行负勇气,一战静妖氛。(《塞下曲》其六)
齐梁赋题乐府,多咏物之体,内容多写征夫思妇之事,从上面的这些诗可以看到,李白对这个传统的沿承是很明显的。如《紫骝马》一题,今存李白之前的有梁简文、梁元帝、陈后主、李燮、徐陵、张正见、陈暄、祖孙登、独孤嗣宗、江总、卢照邻之作。李白之后,有李益、秦韬玉之作。大体或是咏马而兼及骑士,或咏骑士以见马,但多与思妇、艳妇相连,或征夫而及思妇,或游冶而及艳妇。李白的《紫骝马》,正是继承齐梁这一传统,但突出骑士壮侠之气,并以“挥鞭万里去,安得念春闺”作结。全篇为咏紫骝马,但征夫形象自在其中,最后又逗出思妇这一形象。其他《折杨柳》、《洛阳道》、《从军行》、《塞下曲》数首也是一样,基本上采用赋题之法,但由于他对汉魏诗歌生动地叙事、塑造人物形象的写作方法很熟悉,所以能超越齐梁式的平面咏物、堆垛词藻的写法,转入人物形象的塑造,在效果上高于齐梁体。这说明李白是在采用齐梁拟乐府体制与方法的基础上作出了艺术上的新发展。
齐梁赋题,多束缚于题面,至初唐犹然。李白乐府诗多由齐梁赋题法入手,但突破了束缚题面的作法。比如《战城南》,梁代吴均“躞蹀青骊马,往战城南畿”一首,陈张正见“蓟北驰胡马,城南接短兵”一首,唐卢照邻“将军出紫塞,冒顿在乌贪。笳喧雁门北,阵翼龙城南”一首,非但用声律新体拟古辞,而且严格地按“战城南”三字赋写。李白之作,既不规范汉篇,又能突破狭窄的赋题方法。他取原作反战的主题,写成一个更具有典型意义的反战诗。其中“野战格斗死,败马号鸣向天悲。乌鸢啄人肠,衔飞上挂枯树枝”是对《战城南》语意的创造性改变,也是李白乐府诗取得与汉魏六朝原作联系的一个方式。《将进酒》也是这样,梁陈人所作,束缚在题面,李白的《将进酒》,采用赋题之法,但纵横开合,把《将进酒》之题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在这些地方,我们可以看出李白是将晋宋的拟篇法与齐梁的赋题法相结合,即重视古意与古乐府体制的再现,又吸收了齐梁善于赋题的作法。这方面的作品也可以举出一些,如《有所思》为铙歌曲一种,有汉古辞存在。但齐梁诗人多用赋题之法,并且不用汉古调的体制。李白的《有所思》,在写作方法上仍然用齐梁赋题,但是在体制上取杂言歌行,在立意上则兼取张衡《四愁诗》,恢复汉词的体制:
我思仙人,乃在碧海之东隅。海寒多天风,白波连山倒蓬壶,长鲸喷涌不可涉,抚心茫茫泪如珠。西来青鸟东飞去,愿寄一书谢麻姑。
铙歌《有所思》写一情变故事,齐梁人用赋题法作《有所思》则专就题面发挥。李白将之改成游仙之词,也可以说对古意的一个发展。《君马黄》一题也是这样,古辞言君马臣马相对之意,其实是主宾相得之意。梁陈人用赋题法,写成咏马之词,如陈代蔡君知一首:“君马出西极,臣马出东方。足策浮云影,珂连明月光。水冻恒伤骨,蹄寒为践霜。踌躇嗟伏枥,空想欲从良。”张正见两首也是这样。不但失去了古意,并且在体制上弃原词杂言之体,改用齐梁五言八句的声律体。李白《君马黄》放弃梁陈近体,恢复古辞的体制:
君马黄,我马白。马色虽不同,人心本无隔。共作游冶盘,双行洛阳陌。长剑既照曜,高冠何赩赫。各有千金裘,俱为五侯客。猛虎落陷阱,壮夫时屈厄。相知在急难,独好亦何益。
李白部分作品采用赋题的方法,但恢复古辞的立意,在体制上也恢复汉词的杂言体制。变齐梁无寄托之咏物为有寄托之体。另外,与齐梁呆板的赋题不同,李白之赋题常常是窥入题意,深入形容。如《野田黄雀行》:
游莫逐炎洲翠,栖莫近吴宫燕。吴宫火起焚巢窠,炎洲逐翠遭网罗。萧条两翅蓬蒿下,纵有鹰鹯奈尔何!
此诗实为野田黄雀自幸之语,是就“野田黄雀”这个题意来赋写的。不但刻板咏物,而且全用反衬之法。黄雀自语不逐炎洲翠游玩,不近吴宫燕栖息。是因为宫燕易被焚巢,洲翠易遭网罗。而今我深栖野田中蓬蒿之下,可以藏身远害,纵有鹰鹯奈若何!此实亦赋题法,而巧妙如此。又如《北上行》原出于曹操《苦寒行》,因诗首句为“北上太行山”,故李白拟作篇名取《北上行》,其全诗自“北上何所苦,北上缘太行”始,至“叹此北上苦,停骖为之伤。何日王道平,开颜睹天光”,实是借此旧题写自身北上目睹安史反情的惊险情节。所以这一首诗中,综合运用发挥古意、赋题与以古题寓今事三种方法,可见李白对传统拟乐府方法的创造性发展。
“依题立义”的方法,也是李白对赋题法的一种发展。王琦对《幽州胡马客歌》一首做解题时指出这种方法:
《乐府诗集》:梁鼓角横吹曲有《幽州马客吟》,即此也。胡震亨曰:梁鼓角横吹本词言剿儿苦贫,又言男女燕游。太白则依题立义,叙边塞逐虏之事。(26)
乐府诗歌,汉代古辞都是讽兴当时之事,主题思想包含在具体的事件叙述中。建安三曹之作,也仍然是以事为主的,但多寄托主观的思想感情。其后嵇康、陆机、谢灵运、鲍照等人,无不以言志寄托为拟乐府的基本方法,它是晋宋拟乐府重义与齐梁乐府重题的结合,逐渐形成文人拟乐府重义的传统。到了齐梁之作,辞与物突出,事与义则沉晦不彰。李白的“依题立义”,正是晋宋重义传统与齐梁重辞传统的重新结合,是对赋题法的有效发展。我们看王琦所举的《幽州胡马客歌》一篇:
幽州胡马客,绿眼虎皮冠。笑拂两支剑,万人不可干。弯弓若转月,白雁落云端。双双掉鞭行,游猎向楼兰。出门不顾后,报国死何难。天骄五单于,狼戾好凶残。牛马散北海,割鲜若虎餐。虽居燕支山,不道朔雪寒。妇女马上笑,颜如赪玉盘。翻飞射鸟兽,花月醉雕鞍。旄头四光芒,争战若蜂攒。白刃洒赤血,流沙为之丹。名将古谁是?疲兵良可叹。何时天狼灭,父子得安闲。《幽州马客吟》的原作,是写剿儿之事,原为马客的歌谣。李白抛开原来的事义,专就“幽州胡马”一题着眼,将其塑造成一个壮侠之士边塞逐虏、沙场报国的形象。这种“依题立义”的写作方法,正是李白得以摆脱单纯的模拟旧篇与刻板的赋写题面的局限,在思想感情的抒发与艺术形象的塑造上开拓出一个极为自由的空间。拟汉古辞的《公无渡河》一篇,也是典型的“依题立义”之法:
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波滔天,尧咨嗟。大禹理百川,儿啼不窥家。杀湍堙洪水,九州始蚕麻。其害乃去,茫然风沙。披发之叟狂而痴,清晨径流欲奚为?旁人不惜妻止之,公无渡河苦渡之。虎可搏,河难冯,公果溺死流海湄。有长鲸白齿若雪山,公乎公乎挂罥于其间,箜篌所悲竟不还。
古辞《公无渡河》是写一个狂夫渡河,其妻欲止而不及,最后坠河而死的单纯的悲哀故事,因为其声情之悲而动人。李白则一方面发挥赋题之长,先专就“河”字演绎,极写黄河风波之险,自古已然。最后写狂夫不知利害,强欲渡河,坠河而死。作者究竟寄托何事,我们不得而知。但其对人生和世事有所象征,是可以肯定的。
拟乐府的创作,无论晋宋拟篇还是齐梁赋题,其重要的动机就在于诗艺的较量。元稹说前人写作古乐府“唱和重复”,“于文或有短长,于义咸为赘剩”,这的确击中了拟乐府的要害。在旧篇存在的情况下,模拟写作即是对原作的尊重与模仿,同时也是对原作的挑战。在文人诗修辞艺术不断发展的情况下,文人作者觉得自己能够对修辞质朴的原生乐府歌诗有所超越。而当拟作的行为出现后,不同拟作之间自然形成一种竞赛的行为,拟乐府的历史也就成了一个跨越时空的古今诗人的艺术竞赛。元稹所说的“于文或有短长”,的确是拟乐府创作得以存在的理由,也是支撑拟乐府诗歌发展的基本动力。在这自魏晋至三唐的众多竞赛者中,李白无疑是最强有实力的。而李白本人,也可以说是最富于这种竞赛意识的。赋题法在体现同题竞赛这一点上显得更加的突出,虽然前人陈陈相因的赋题,陷入“《落梅》芳树,共体千篇”的困境,但李白复活了汉魏诗歌原生的自由创造的精神,在赋写题意上达到后人无以复加的程度。尤其是他的《公无渡河》、《远别离》、《蜀道难》、《将进酒》、《天马歌》、《长相思》等作品,真正可说是“罕见凿空”,是对齐梁赋题法空前绝后的新发展。殷璠赞叹:“至于《蜀道难》等篇,可谓奇之又奇。然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也。”(27)李白能取得这种成功的原因,除了复活骚的体调之外,对赋题法的创造性发展也是一个因素。我们不妨以《蜀道难》为例。郭茂倩引《乐府解题》云:“《蜀道难》备言铜梁玉垒之险。”(28)可见是一个主题性很明确的题目。《蜀道难》古辞已佚,其原来的内容不得而知。李白之前,现存《蜀道难》拟篇如萧纲、刘孝威、阴铿、张文琮诸人之作,都是以竭力形容蜀道之难行为能事。其中刘孝威、张文琮所作最为出色,刘作云:“玉垒高无极,铜梁不可攀。双流逆巇道,九坂涩阳关。邓侯束马去,王生敛辔还。惧身充叱驭,奉玉若犹悭。”张作云:“梁山镇地险,积石阻云端。深谷下寥廓,层岩上郁盘。飞梁架绝岭,栈道接危峦。揽辔独长息,方知斯路难。”(29)这两首诗都是典型的赋题之作,使用隶事、形容的手法,将《蜀道难》这个主题比较成功地表现出来了,但将它们与李白《蜀道难》相比,其对主题的挖掘可以说还停留在很浅表的程度。李白之作,采用带有骚体风格的杂言歌行,极尽曲折描写、唱叹引情之能事。诗一开始,“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以一种惊呼式的感叹来破题。其后“蚕丛及鱼凫”,想象遥远的古代蜀地与外界隔绝的情况,传说中的帝王增添了蜀地的神秘感,为下面正式写蜀道之难作了很好的铺垫。其后“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两句横空而出,写蜀道之前更有蜀道,其惊险更百倍于后来“天梯、石栈相勾连”之蜀道也。下面“地崩山摧壮士死”极写蜀道开凿之艰难奇异,实非寻常人力所成。蜀道开凿神话的引入,又是一层铺垫。此下是以“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这样的夸张方法作进一步形容。有了上面几层铺垫后,才是人物的出现。这也是李白赋题的特点。李白的乐府赋题,总要塑造比较鲜明的人物形象与生动的行动场景,不同于齐梁的平面赋写。在大段的蜀道之行艰险情状的描写后,方才曲终奏雅,在出奇的形容之后,说出作者形容蜀道之难的真正意图,在于讽喻朝廷:“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这是李白写作的思想归宿。他虽然在文辞上与古人竞赛,但真正的目的是要恢复诗歌的讽喻精神。从上面的分析可见,李白这首诗,是典型的李白式的赋题法,诗中三次出现“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主题得到尽情的宣叙。我们分析他的其他带有赋题特点的作品,也都是这样以“罕见凿空”来出奇制胜。
李白乐府诗重在赋题的特点,还表现在他的一些乐府诗,选择了一些见载于古代文献但失去了原有歌诗的乐曲名,如见于《汉书·艺文志》的《中山孺子妾歌》、《临江王节士歌》,出于《隋书·音乐志》“梁三朝设乐歌词”中的《夷则格上白鸠拂舞辞》、《设辟邪伎鼓吹雉子斑辞》,这些冷僻并且失去古辞与本事记载的旧曲名,正是对作者赋题能力的考验。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李白写作乐府诗“因难以见巧”的特点。而这种搜寻佚辞旧曲名的作法,正是齐梁诗人开创的。
本文尝试对李白乐府的创作思想、体制与方法做上述系统的分析。在初盛唐之际诗坛复汉魏之风与承齐梁之体两者已经达到相对的平衡,玄宗朝揄扬风雅,诗界已臻文质彬彬之盛的情况下,李白以其天才的伟力与超越时流的诗歌审美理想,再次提倡复古。并且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从当时已经陷于困境的拟乐府创作入手,采用表面看来已经落后的拟古方法,试图全面恢复风雅汉魏的艺术精神。这不能不说是盛唐诗国中最为雄伟壮观的一次远征。从李白在乐府诗及一般的歌行体方面创造出的非凡成就来看,我们不能不承认,李白那种全面复古、也全面地覆盖诗歌史的意图,可以说已经成功。之所以能达到这样的成就,一方面当然是因为李白个人的天才,另一方面是因为陈子昂、李白他们的复古思想,是一种深刻的、植根于崇高的审美理想之上的复古思想,所以能够激发巨大的活力。尽管李白的拟乐府、古风等复古诗学的实践,是一种天才的个人行为,在方法上不具有普遍性。但是其创造的诗歌境界,作为古典诗歌艺术所达到的最高维度之一,对后来的诗歌史的影响是深远的。其次,即以李白所复活的拟调、拟篇,及其作出巨大发展的齐梁赋题等方法而言,对此后的古乐府系统的写作,也是有直接的影响的。就唐代而言,李贺的歌行写作,在体制、方法与精神上就深受李白的影响,可以说是李白之后,唐代歌诗创作的又一奇葩。我们也可以说,正是由于李白复古诗学实践的卓越成果的取得,有力地启示了中唐韩孟、元白两派的复古诗学。从这个意义上说,李白可以说是唐代复古诗学、甚至唐宋复古诗学的核心。至于其具体的创作方法,尽管我们说过,李白的拟古法是天才的个性化行为,但是他所激活的拟篇法,一直为后来的元、明、清数代诗人所效仿。总之,关于李白乐府诗创作的这些问题,都还有深入探讨的必要。
注释:
①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三五《年谱》,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611页。
②参见钱志熙《论齐梁陈隋时期诗坛的古今分流现象》一文中的相关论述,《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③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页。
④参看钱志熙《论李白古风五十九首的整体性》一文有关论述,《文学遗产》2010年第1期。
⑤《元稹集》卷二三,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54页。
⑥乐章和徒诗的分际,参看钱志熙《歌谣、乐章、徒诗——论诗歌史的三大分野》一文中的有关论述,《中山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⑦⑧转引自詹锳《李白诗文系年·李白乐府集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65页。
⑨卢照邻《乐府杂诗序》,《卢照邻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4页。
⑩以上各条俱见《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第333—336页。
(11)以上两条俱见《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第365页。
(12)卢照邻《乐府杂诗序》。
(13)司马迁著、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点校本,第3169页。
(14)王夫之《唐诗评选》卷一,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20页。
(15)《白居易集》卷四五《与元九书》,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61页。
(16)郝立权《陆士衡诗注·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页。
(17)《陆士衡诗注·自序》。
(18)转引自《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第501页。
(19)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二五,第1195页。
(20)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三○,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42页。
(21)待: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三○(第445页)作“得”。
(22)按郑樵已有此说。见《通志·乐略》。
(23)转引自《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第337页。
(24)转引自《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第343页。
(25)参看钱志熙《齐梁拟乐府诗赋题法初探——兼论乐府诗写作方法之流变》,《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
(26)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四,第268页。
(27)《河岳英灵集》,《唐人选唐诗(十种)》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53页。
(28)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四○,第590页。
(29)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四○,第591页。
标签:李白论文; 文学论文; 长歌行论文; 古风论文; 毛诗序论文; 汉乐府论文; 秦女休行论文; 齐梁论文; 诗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