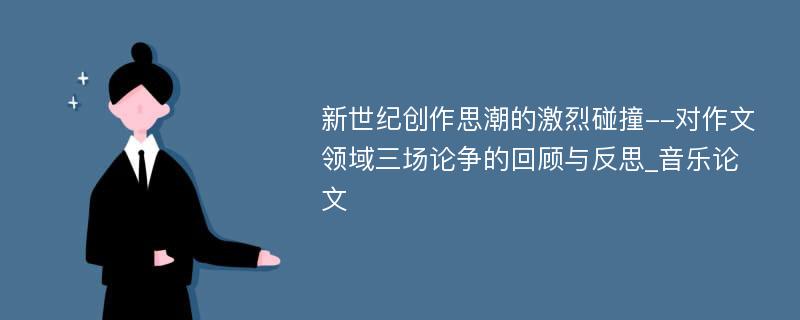
新世纪创作思潮的激情碰撞——对作曲界三场论辩的回顾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世纪论文,思潮论文,三场论文,激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谭卞之争”
打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国乐坛围绕“新潮音乐”的争论一直持续不断。这一争 论大致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
第一阶段——在整个80年代,除了少数文献依然沿袭实用本本主义的惯性思维、对“ 新潮音乐”进行政治追问之外,这一争论基本上集中在音乐观念和作曲技法层面,参与 论战的以作曲家和理论家居多,如发生在苏夏和郑英烈之间的争论;当时最活跃的“新 潮”作曲家也纷纷发表言论而宣示他们的艺术主张。
第二阶段——到了80—90年代之交,由于宏观语境之变,一直处于隐忍状态待机而动 的实用本本主义思潮强势回流,关于“新潮音乐”的争论已经蜕变为一面倒的批判,其 弹着点几乎不约而同地集中到了政治层面上,把它当作“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严重泛 滥以及“颠覆反颠覆、演变反演变、渗透反渗透”的主要领域和主要表现来加以否定, 参与批判的主要是中国音协某些领导人以及一部分作曲家和理论家。
第三阶段——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实用本本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由于其基于阶级斗 争哲学和冷战思维的政治批判已因宏观语境之变而失去了话语空间,关于“新潮音乐” 的争论重新回到音乐艺术层面上来,参与论战的多是“新潮”作曲家、理论家和批评家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首推发生在指挥家、批评家卞祖善与作曲家谭盾之间的争论,即 所谓“谭卞之争”。
从80年代初开始,谭盾一直是“新潮音乐”中风头最劲的代表人物。后移居美国,孜 孜不倦地致力于先锋派音乐的探索。其人聪明绝顶,作品花样翻新,也是中国作曲家中 最善自我推销者,在欧美被当作中国先锋派音乐的主要代表,影响很大。2001年,他的 电影《卧虎藏龙》配乐获奥斯卡金像奖,使之在世界乐坛上声名大振。同年,他的《永 恒的水》和《卧虎藏龙》两场个人音乐会在京演出,在听众和同行中均引起不同反响。 对此持批评态度最烈者,就是卞祖善。
卞祖善早年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是我国第二代指挥家之一,长期担任中央芭蕾舞团 交响乐队指挥,也曾指挥过一些现代派作品。其人在音乐界以音乐修养深厚、听觉特别 敏锐著称;同时以批评家身份活跃于乐坛,文风以直言不讳见长。卞氏对谭盾作品的批 评,非自今日始。早在1995年,卞氏便公开撰文将谭盾对于现代作曲技法的种种探索和 实验比喻为“皇帝的新衣”,认为其作品是“比小脚、女人的裹脚布及尿壶更不屑一顾 的货色”(注:卞祖善《关于“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及其他》,《人民音乐》1995年 第12期。)。由于文章发表在学术刊物上,在圈外人中影响不大。
2001年10月27日,北京电视台《国际双行线》栏目将谭卞二人约到一起(据谭盾本人讲 ,事先他并不知道有此安排),就谭盾音乐会的评价问题进行现场对话和访谈。卞当时 即对谭盾提出直言不讳的批评,认为谭盾是在“玩音乐”。对此毫无心理准备的谭盾当 即表示:“卞老师跟我的音乐是完全没有任何共同语言的,不在一个水平上,是完全不 可能去沟通”,当场拂袖而去,访谈就此不欢而散。该节目向全国播出后,成为轰动文 艺界和社会各界的一大新闻事件。
最早对此做出反应的是首都新闻界。北京电视台与《现代传媒》邀请了部分专家学家 就此交换意见。11月1日,《北京晚报》的《现代音乐——两位音乐家执著的追求和探 讨》一文对此事作了披露。一周后,即11月8日,谭盾之父在《天府早报》上发表了对 卞祖善批评的反批评——为了某个艺术问题的争鸣而父子为辩,这在中国乐坛上甚为鲜 见。
音乐界的反应虽然稍慢一些,但显然更具专业性和学术性。2002年初,《音乐周报》 辟出专栏,就这一问题展开讨论;此后,《人民音乐》《音乐研究》《黄钟》《音乐探 索》等多家学术刊物均发表作曲家、音乐学家的文章和评论,使得这场争鸣向纵深发展 。
李扬在《音乐周报》上发表《“水乐”余波》(注:李扬《水乐余波》,《音乐周报》 2002年1月18日、25日连载。)一文,批评卞祖善“将自己的观念、观点强加于人”,对 谭盾表示声援。作为这场讨论的主将,卞祖善在《人民音乐》发表题为“向谭盾及其鼓 吹者挑战”的文章,对自己多年来关于谭盾的批评进行系统回顾,并对谭盾及其支持者 提出措词强硬的批评(注:卞祖善《向谭盾及其鼓吹者挑战》,《人民音乐》2002年第3 期。)。
2002年在“上海现代音乐研讨会”上,“谭卞之争”成了一个热门话题;而卞祖善在 探讨会上继续抨击极端先锋音乐的言论也受到部分与会者的当场反驳,会议气氛十分激 烈而活跃,难怪后来有人记叙当时情景时描绘道:“场内弥漫着‘和平年代’久违了的 火药味儿”(注:《现代音乐谁来听》,《音乐周报》2002年4月12日。)。回京后,卞 祖善将他的发言整理成文,以《我与谭盾的鼓吹者针锋相对》为题在《音乐爱好者》上 公开发表,该文的核心仍是他多年来一直坚持的观点,即:“大多数的现代音乐作品是 被忘却的后备军”(注:卞祖善《我与谭盾的鼓吹者针锋相对》,《音乐爱好者》2002 年第5期。)。
作曲家金湘也发表文章参与论战,他把卞祖善称为“古典音乐的卫道士”,把谭盾称 为“现代音乐的急先锋”,而现代音乐则是一旦从瓶子放出便再也回不去了的“魔鬼” 。他认为“卞、谭之争”的实质是“延续于世界乐坛多年的两种音乐观之争在中国大地 上的继续”(注:金湘《魔鬼还能回到瓶里去吗?》,《音乐周报》2002年4月26日、5月 3日连载。)。
卞祖善针锋相对地指出,约翰·凯奇和谭盾的部分音乐乃是真正的魔鬼,而他自己则 要做打鬼的“钟馗”(注:卞祖善《从钟馗捉鬼谈起——答金湘先生》,《人民音乐》2 002年第6期。)。
音乐学家梁茂春把卞祖善对谭盾的批评形容为“墙外开花墙内骂”,总体上不赞同卞 祖善的立场,并针对卞氏对谭盾的批评,在文章中为谭盾的作品《十九个操》辩护(注 :梁茂春《墙外开花墙内骂》,《音乐周报》2002年6月7日。)。
此后,中央音乐学院两名博士生分别从“谭卞之争”谈论了自己对现代音乐的看法(注 :吴春福《从媒体关于现代音乐之争论所引发的思考》,《音乐研究》2002年第3期; 项筱刚《谭盾音乐与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的发展出路——由“谭卞之争”所想到的》,《 黄钟》2003年第1期。)。
最后,卞祖善在《音乐探索》上撰文对自己批评谭盾作品的缘由及各方主要分歧进行 回顾,提出“最可靠的检验标准是时间和听众”的观点(注:卞祖善《最可靠的检验标 准是时间和听众》,《音乐探索》2003年第4期。)。
纵观这场争论,不妨提出如下看法:
1.我国作曲家关于现代音乐的探索已有20余年的历史,从早期之激情萌动到今日之冷 静反思,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已渐趋成熟。由于中国的“新潮音乐”从其滥觞 阶段就开始不断遭受各种质疑和批判,因此,许多音乐家从保护艺术探索、创新精神不 受压制和打击的角度,为其生存和发展摇旗呐喊,而对其发展中实际存在的许多问题和 弊端并未真正从艺术和学术两方面进行深究,甚至对某些问题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护 短”现象。例如人们对约翰·凯奇的偶然音乐观念和手法赞扬过多,却忽视了它的“非 乐”倾向及其对音乐艺术的颠覆性后果。音乐界对谭盾作品的态度也大致如此。从这个 意义上说,梁茂春断言“墙外开花墙内骂”,无论从墙内还是墙外都是不准确的。因为 ,在欧洲,谭盾作品所遭受的批评并不比卞祖善温和。在国内,除了一些人在特定阶段 的政治批判之外,专业界对谭盾的赞扬之声远远超出批评,有些赞扬是过分的溢美之词 ,违背了音乐艺术的起码美质,像卞祖善这类直率、尖锐、专业化程度很高的批评更是 凤毛麟角。
2.人们应该注意到,卞祖善并不一般地、笼而统之地反对现代派音乐,而是针对那些 抱着猎奇心理“玩音乐”的所谓“极端先锋派”音乐。例如他对勋伯格《华沙幸存者》 的充分肯定并以指挥家身份积极参与现代音乐作品的演出实践就是明证。因此,金湘判 定卞氏是“古典音乐的卫道士”并不公平。同时,人们也应该注意到,卞氏的批评是针 对谭盾某些作品的,并不一般地否定谭盾的音乐。具体到谭盾的《水乐》以及《十九个 操》之类,其中到底有多少值得肯定的艺术价值,不仅卞氏可以批评,其他人同样有权 提出批评和反批评。
3.这一争论表明,生活在当今多元化时代的中国作曲家和理论家,其艺术观念、理论 识见、美学胸怀还存在许多重要缺陷,于是养成一个习惯:某些作曲家、某些作品是批 评不得的;这些作曲家本人也把批评家看成是吹喇叭、抬轿子的角色,只能说好不能说 坏,只能赞扬不能批评。在当代世界乐坛,巴赫可以批评,柴可夫斯基可以批评,为什 么谭盾就不能批评?卞祖善的批评之所以可贵,就在于不趋炎附势,不敷衍苟且,不人 云亦云,敢于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至于卞氏批评中的许多是非曲折,同样必须经受别 人的批评。但他关于“皇帝的新衣”的警告,是应该引起国内乐坛重视的时候了。
4.作曲家是专业音乐史的第一推动力。为此,音乐创作中对于新观念、新风格、新技 法、新音响的追求,永远要小心翼翼地加以保护。否则,音乐艺术的发展就会停滞。正 是在这个意义上,包括谭盾在内的我国“新潮”作曲家勇于探索的精神及作品受到同行 们的热情肯定是必要的、当之无愧的。但是人们也不应忘记,既然是探索,就允许走弯 路。音乐的创新与探索,如果离开了音乐作为一门艺术的美的本质,如果已经到了对这 种美的本质进行整体性颠覆的程度,把音乐的艺术音响混同于生活音响和自然音响,甚 至发展到取消声音、自然也就从根本上取消了音乐的地步,如果不在发掘音乐美上殚精 竭虑而是解构这种美上花样释新,这样的“创新”还值得今天的中国音乐家无保留地加 以肯定么?因此,对谭盾提出批评和忠告,是抱有不同观念的批评家的责任。正如谭盾 可以不同意这种批评,完全有权在自己择定的创作道路上继续前行一样,都是多元代时 代的题中应有之义。
关于“第五代作曲家”的论战
所谓“第五代作曲家”,指的是“文革”后进入高等专业音乐院校作曲系的作曲家, 其中多数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崛起的“新潮”作曲家,其代表人物有谭盾、瞿小松、郭 文景、陈其钢、叶小纲、何训田、许舒亚、陈怡等人,后来均成为中国乐坛上叱咤风云 的人物。其中多数人如谭盾、瞿小松、许舒亚、陈怡等从80年代后期起长期移居欧美, 叶小纲出国数年后又返回中央音乐学院任教,郭文景、何训田则一直留在国内从事教学 和创作。
其实,由“第五代作曲家”及其作品所引起的纯然学术性争议,在“后新时期”就已 发生过多起。其中影响较大者有二:其一发生在90年代中期,有人撰文,对哈尔滨歌剧 院创作演出、徐坚强作曲的歌剧《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中运用较多近现代技法表示 不满,另一些人对此文的看法提出不同意见,从而引起争论。其二发生在90年代末,有 听众对叶小纲的作品音响怪异、晦涩难解提出批评,叶小纲本人撰文反驳,认为批评者 听不懂是耳朵有问题,应把视唱练耳学好了再来批评别人。
世纪之交关于“第五代作曲家”的论战,发生在王西麟和郭文景之间。王、郭两位都 是当代中国乐坛的著名作曲家。按照习惯的“分代法”,王西麟应在第三代作曲家之列 。
论战起因于郭文景2003年在国内首演的两部室内歌剧《夜宴》和《狂人日记》。
不久,王西麟在《人民音乐》上发表《由<夜宴><狂人日记>到对“第五代”作曲家的 反思》(注:王西麟《由<夜宴><狂人日记>到对“第五代”作曲家的反思》,《人民音 乐》2004年第1期。)一文,对郭文景的《夜宴》和《狂人日记》、陈其钢的《蝶恋花》 等作品提出措词激烈的批评,进而对“第五代作曲家”近年来的创作状态及其理论批评 表示不满。王文最后向“第五代作曲家”提出如下忠告:
我希望第五代作曲家们首先要打破对自身的虚伪恭维的庸俗空气的包围;千万不要把 外国人的巨奖和人的评论相对立;千万不要变成“昔日穷学生,今日新巨头,跻身进朱 门,不见冻死骨”;千万不要变成“技术大师,思想侏儒”;千万不要把孱弱、苍白、 贫乏、冰冷、卑贱拿来自我欣赏无限陶醉;千万不要以为自己会天然地不受权势和商业 的污染而无须不断补充自己的人文资源;千万不要自封或被封为至高无上的“大师”、 “权威”。一个对别人的命运、对大环境的命运毫不关心而只关心自己的艺术的人,只 能是一个自私的人,而绝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对人类有深深的悲悯情怀的艺术家而受到 历史和民众的“感激的记忆”。
郭文景本人奋起撰文,对王文进行反驳(注:郭文景《谈几点艺术常识,析两种批评手 法》,《人民音乐》2004年第4期。)。他首先指出,创作选题问题“实在是一个关乎艺 术生死的严重话题”,并以沈从文的遭遇为例,说明写什么和怎样写是作曲家的自由, 艺术评论不能指责作曲家可以写A或不能写B;在谈及艺术评论与大批判的区别时,郭文 景意味深长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王西麟先生是旧时代的受害者之一,他对旧时代深恶痛绝,我认识他的十多年间,他 一天也没停止过对旧时代的抨击。可惜,他情绪化的怒吼不绝,便理性的思辨太少。… …看清你所憎恶的东西在自己身上的潜在影响,是非常不容易的。做到这一点,除了理 性的批判精神之外,特别需要自省和抛弃“伤兵”情绪。
这场关于“第五代作曲家”的论战,在王西麟、郭文景之间进行了一个回合之后再无 下文。但论战双方所阐述的立场和理念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
不该否认,撇开王西麟个人性格中的明显弱点及其文章中充溢着的情绪化成份和过激 言词不谈,其文章的主要立论的确包含某种值得肯定的东西,即当代中国作曲家对时代 精神的把握与感悟、对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深刻关怀,以不断补充自身的人文资源, 从而使自己的音乐创作更为充盈而厚实。如果我们仅仅因为王西麟及其文章中的某些弱 点而否认这些合理内核,显然是有失公允的。
不可否认的是,郭文景的反驳同样也存在着某种情绪化的东西。但文章的主旨是在捍 卫作曲家在创作题材选择上的充分自由,这一立论任何人也无法摇撼。他指出王西麟本 人及其文章所存在的问题,也一针见血,举凡熟悉王西麟的音乐家都有大体类似的看法 ,但像郭文景在公开文章中如此直言不讳,却是前所未有的。
争论的焦点首先不在于,作曲家可以写什么或不能写什么。在这个问题上苛求作曲家 是毫无意义的。关键是怎样写和写得怎样。在这个问题上,王西麟文章的毛病是在立论 时没有抓住这个关键,具体表述时又失于偏颇。表现在他对《夜宴》《狂人日记》《蝶 恋花》及《大红灯笼高高挂》等作品的批评,由于受“伤兵”情绪支配,其审视的切入 点太过单一,评价尺度偏于严苛,缺乏同行间理应具备的宽厚心态。
争论的焦点也不在于作曲家对于名利的态度。因为作曲家也是社会人,不能要求作曲 家根本无视金钱和荣誉,特别在当代社会,以自己的作品获得相应的经济利益和社会荣 誉更是无可指责。在名利面前安贫乐道、清心寡欲,一心专注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探索, 固然是一种高风亮节,但艺术成就与经济状况、社会地位成反比,让今天的艺术家再过 曹雪芹晚年那种“举家食粥酒常赊”的日子,或如舒伯特那样用一首经典艺术歌曲仅能 换取一块面包,却未必是健康社会的健康现象。
问题的实质是,像郭文景、谭盾、何训田这样的“第五代作曲家”,作为“崛起的一 群”和思考的一代、探索的一代、“离经叛道”的一代,当初是以强烈的忧患意识、批 判意识登上中国乐坛并赢得多数同行的尊敬、支持和赞誉的,他们在80年代的作品,在 许多方面代表着中国知识分子对祖国、对历史、对中西哲学和文化传统及其当代现实的 思考深度和创造成果。时至今日,在“第五代作曲家”中,究竟有多少人还在保持当初 那种批判意识和勇不可当的锐气,究竟还有多少人能够有意识地主动承担起自己肩负的 历史责任呢?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不是“要我”如何如何,而是“我要”如何如何的 问题,也就是说,在当今时代条件下,“第五代作曲家”将何以处之?如何自处?这完全 取决于各人的自我定位和历史选择。再说,音乐创作无禁区,大千世界林林总总,什么 都可以写,然而一旦它们成为音乐创作的对象,就要把它们按照音乐艺术的规律组织进 一个有序发展的音乐结构和音乐形式之中,给以艺术化的表现;如果“创作自由”和“ 题材选择自由”到连这一点也不管不顾的程度,这样的音乐创作无论是出于表达的“真 诚”还是出于别的动机,都是令人怀疑的。
关于“中华乐派”的争鸣
新时期以来一直活跃在中国乐坛上的作曲家金湘,早在1988年就提出“中华乐派”的 命题,后来,他在多种场合不断重申这一命题。进入新世纪之后,理论家赵宋光公开致 信金湘,首次强力鼓吹“新世纪中华乐派”的主张,并以金湘的创作实践为例,指认金 湘是“20世纪中华乐派的嫡亲传人”(注:赵宋光《举起中华乐派的大旗——致金湘》 ,《人民音乐》2003年第3期。)。
5个月之后,赵宋光、金湘、乔建中、谢嘉幸在《人民音乐》发表《“新世纪中华乐派 ”四人谈》(注:赵宋光、金湘、乔建中、谢嘉幸《“新世纪中华乐派”四人谈》,《 人民音乐》2003年第8期。)一文,大张旗鼓地亮出“新世纪中华乐派”的旗帜,并从哲 学基础、美学特征、传统渊源、技术构成等4个方面论述了“新世纪中华乐派”形成的 条件。
此文公开发表一个月之后,即2003年9月26日,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主持召开“ ‘新世纪中华乐派’大家谈”座谈会。据主办者称,这个座谈会是一次统一认识的工作 会议。与会者除首倡“新世纪中华乐派”口号的4人之外,还有作曲家唐建平、杨青, 琵琶演奏家刘德海,声乐教育家石惟正,音乐美学家韩钟恩,《人民音乐》代表等。绝 大多数与会者对“新世纪中华乐派”的提出表示支持,并从哲学、工艺学以及20世纪中 国音乐发展历史与当代现实等角度论证了这一口号提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也有部分与 会者对此提出了各自的忧虑和不同意见。会议重申,“新世纪中华乐派”不是一个组织 、不是一个机构,而是一种思潮、一种态势,要把这个口号在音乐界喊响。座谈会还计 划召开“新世纪中华乐派”演讲会和音乐会,所有中国音乐家都应当朝中国音乐复兴的 方向努力。(注:李岩《“新世纪中华乐派”大家谈》,《天籁》2003年第4期。)
老一辈作曲家朱践耳率先致信金湘,对“中华乐派”的主张表示“衷心拥护”,认为 “新世纪中华乐派”的建立是“一个百年大计的雄心壮志”。同时也提出“先经营,后 挂牌”的建议,主张“先实践,干实事”,“在若干年的成果积累的基础上,再树起这 块‘乐派’的招牌,才是可靠的‘水到渠成’”;认为“中华乐派”表现在创作上“是 一个极大的、极开放的大乐派,而不是一个狭隘的模式”,因此,“需要的是百花齐放 ,各人有各人的创作个性、创造力和想象力……并不强求一律,也欢迎有其它乐派的出 现”。(注:朱践耳《致金湘》,《人民音乐》2004年第1期。)
海外华人作曲家储望华与“新世纪中华乐派”的提法持有不同的立场,用储望华自己 的话说,是“唱反调”(注:储望华《读<“新世纪中华乐派”四人谈>之杂感》,《人 民音乐》2004年第2期。)。储文坦言“四人谈”是“迄今为止中国音乐史上最具雄心挑 战的一份宣言书”,但读之有似曾相识之感,“使我又想起了充满豪言壮语的火红年代
”;作者表示不大习惯“四人谈”作者“对自己的见解、看法提得这么高,某些文风及 语气也欠妥”。此文以苏联作曲家萧斯塔科维奇、普罗科菲耶夫、卡巴列夫斯基、哈恰 图良及中国作曲家贺绿汀、丁善德的创作道路为例,说明历史环境和时代条件造就了作 曲家,是时势造英雄而非英雄造时势。“四人谈”提出20世纪中国新音乐的成就是“按 西方人的眼光,依照西方文化的标准而获得的”,“应该摸索一条如何‘走出西方’的 路子”,“老跟在西方后面没有出路”等结论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二十世纪有志 于发展中国音乐文化的志士仁人(包括‘四人谈’作者)前赴后继,学习吸收中国本土音 乐文化,并使其不断传承发扬光大,继承借鉴外来技法,为的是开创中国音乐之路,业 绩伟大。可歌可泣!”随后储望华对于所谓“西方眼光”和“欧洲中心主义作祟”的理 论,阐明了如下的立场:
我压根儿就不认同,无法接受。以我之见。这是自设樊笼,自我限定,自我制约并制 约他人,也是自我否定,因而违背历史唯物主义。
他所憧憬的“百花争艳”理想境界是:
各就各位、各司其职、各行其道、各有所创,大家心往多处想,劲往多处使,这便是 一个百花争艳的局面。
受音乐创作界的启发,关于“新世纪中华乐派”的讨论不久出现了向表演艺术领域拓 展的初步迹象(注:尹兆旭《对“中华声乐学派”的期望与探讨》,《人民音乐》2004 年第8期。)。
关于“新世纪中华乐派”的论战,迄今为止尚未有更多音乐家介入。我认为,这一口 号的提出有其积极意义,一概否定有失公允。实际上,从20世纪初的曾志忞、萧友梅、 刘天华等人提出“中国新音乐”的概念起,直到共产党人的“新音乐运动”,再到50— 60年代的民族化探索和“三化”口号,中国音乐家对于“中华乐派”的追求孜孜不倦, 绵延持续了一个世纪之久,尽管其中经历了太多的沟沟坎坎,但成就举世公认,并在总 的方向上与“文化独特性和多样性”的世界趋势相一致。时至今日,“新世纪中华乐派 ”的提出也是出于同样一个良好的愿望。鉴于我们过去在处理中西文化关系时的确存在 若干失误,因此这一口号的提出也使得当今之中国作曲家能够在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更清醒地处理中西关系,更自觉地确立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地位。
不过,在强调创作个性化和多元化的今天,这一口号的提出失去了过去时代所具有的 普适性和某种强制性,所以口号的提出者才再三声明它“不是一个组织、不是一个机构 ,而是一种思潮、一种态势”。尽管如此,由于赵宋光等人在文章具体语词的表述中存 在着许多失当之处,给人以过分张扬、欲强加于人的印象。而且这一口号以所谓“欧洲 文化中心论”为其立论根据,把“西方眼光”、“西方标准”当作建立“新世纪中华乐 派”的对立面,这就使得“新世纪中华乐派”的理论基础发生偏斜;他们提出的“走出 西方”口号,更是指出了一个错误的发展方向,既不符合20世纪中国新音乐的全部历史 ,也与被赵宋光称之为“20世纪中华乐派的嫡亲传人”的金湘本人的创作实践相背离。 因此,所谓“走出西方”,作为金湘本人及其同道的创作信条亦无不可;但若将它作为 新世纪中华乐派的整体性主张,即便算不得国粹主义、保守主义在当代的新变种,在很 大程度上也只能是乌托邦式的空想。
鉴于这一论争涉及20世纪中国音乐道路的评价以及对其在对世纪发展路向的战略定位 ,问题本身极为严肃且具有无可回避的性质,也一定会有更多音乐家参与其中。随着论 战的深入展开,相信其最终结局无非是:“新世纪中华乐派”一定会有人热烈响应并身 体力行之,也有人反对而各行其是,更有人不予理会而我行我素,各自按照自己择定的 艺术理想探索前进;而走进21世纪的中国音乐,也绝不会是某一个口号、某一种风格、 某一类美学规范的一统天下,必然呈现出一派百花争艳的春天景象。
标签:音乐论文; 谭盾论文; 郭文景论文; 艺术论文; 艺术批评论文; 艺术音乐论文; 夜宴论文; 作曲家论文; 狂人日记论文; 古典音乐论文; 王西麟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