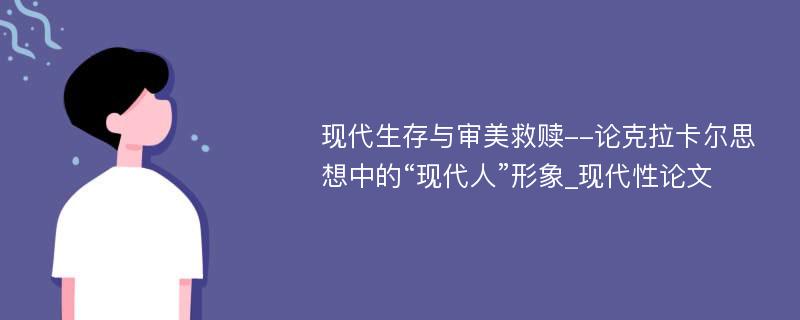
现代性生存与审美救赎——论克拉考尔思想中的“现代人”形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现代人论文,形象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3)04-0123-07
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是德国著名批评家、文化社会学家和电影理论家,目前国内外对于克拉考尔现代性思想的研究总体上处于缺失状态,极少数提及克拉考尔现代性思想的著作或论文也只是蜻蜓点水、语焉不详。克拉考尔在流行文学、音乐、都市生活等方面所表达的现代性审美观念,具有现实穿透力,尤其是他对都市“现代人”的精神状态、生存空间和审美救赎展开了深入而独到的分析,他对“现代人”生存境遇的深深忧虑以及对如何摆脱这种困境所做出的思考,对于我们当下的现实生存仍然具有启示意义。
一、流动的现代性:“现代人”的生存之隅
克拉考尔对“现代人”形象的分析是在文化分析的基础上展开的,克拉考尔对审美现代性的观察都是围绕着高雅文化的边缘区域,并且最终落脚在那些通俗文化媒介上:电影院、街道、体育、轻歌剧、时事讽刺剧、广告、马戏表演等等。克拉考尔文本的鲜明特色,就在于他试图从纷杂的文化碎片中解析出社会的流动现代性特征。
克拉考尔将“现代人”的文化悲剧归结为现代科技的发展,认为科学技术所带来的物质文明导致客观文化与主观文化的悲剧性分离,现代文明正日趋物化,正如布朗所言:“克拉考尔指出了西方精神文明的退化和衰败……主要原因是科学发展的结果。”[1](P64)对克拉考尔来说,现代科技的发展直接促成了大机器的引进。机器作业在实现大批量生产的同时,也抑制了劳动个体创造力和自主性的实现。“每个人在传送带前各司其职。他们履行着部分职能,却无从掌握生产过程的全貌。”[2](P78)
如果说文化悲剧是克拉考尔对于“现代人”生存语境宏观层面的思考,那么现代性都市空间则是“现代人”生存语境微观层面的思考。克拉考尔曾言:“空间意象是社会的梦。无论哪里,只要一切空间意象的象形文字得到破解,那里社会现实的基础就会呈现出来。”[3](P142)他的目的正在于通过分析空间意象,来揭示“现代人”身处其间却不自知的现实。对克拉考尔来说,空间意象的范本就是现代都市。现代都市是一座有着无穷奥秘的迷宫,在那里有被遗忘、被掩盖的现代性痕迹,这些痕迹以碎片的形式存在着,只有通过搜寻与整合,才能重现原貌。因此,他孜孜不倦地搜寻着城市生活中偶然生成的都市碎片,以期揭示出它们隐藏的意义。克拉考尔并不想描述社会梦境的表层现象,而是想揭示梦境背后的现实:一个被整个社会所掩盖,也被建构了社会空间的主体所掩盖的现实。为了揭示这种现实,克拉考尔以巴黎和柏林这两座都市迷宫为例展开了深入分析。他认为巴黎是有着历史感的城市,它“额头铭刻着岁月的痕迹。记忆从它房屋的气孔里面疯长出来,雨水常年洗刷着玛德莱娜纪念碑,使它洁白如雪。岁月的苍白是这所城市的主色调。然而,在白色面纱之下,一切受到人们的呵护,并且像第一天那样清新”[3](P183)。与之相比,柏林的街道是非历史的时间错置,弥漫着无以言状的不安,它的街道的时间是一种空洞的、没有历史性的时间,它的走马灯似的店铺及其他企业的无根状态,磨灭着人们对它们的记忆。在克拉考尔眼里,柏林是一座将现代性展现得淋漓尽致的都市迷宫:它的转瞬即逝性令人应接不暇,带给人狂热兴奋的同时也抽离了历史与记忆;它的即兴创作式的印象掩盖了稳固持久的感觉,没有任何事物可以长久存留;它的变动性使街边建筑处于一种无根状态。也就是说,一股求新求异的狂潮席卷柏林的街头,很少有其他城市像柏林那样迅速地摆脱刚刚发生的事物,在迅猛的变迁中冲刷着历史的记忆。柏林的都市生活给人们带来一种即时变迁的兴奋感,似乎当下永远处于消逝的一个点上,片刻也不停留。
都市生存的意义也曾是齐美尔和本雅明所关注的问题。齐美尔认为都市体验的心理基础是强烈的紧张感,而货币则是导致这种紧张生活的罪魁祸首。本雅明则对都市生活中弥漫的恐惧展开批判性的反思,“害怕、厌恶和恐惧是大城市的大众在那些最早观察它的人心中引起的感觉……在这种来往的车辆行人中穿行,把个体卷入了一系列惊恐与碰撞中。在危险的穿越中,神经紧张的刺激急速地接二连三地通过体内,就像电池里的能量”[4](P232)。本雅明认为,现代生活就像一场击剑比赛,人们永远处于出击与防范的紧张之中。与他们相类似,克拉考尔在柏林的街头意象中感受到弥漫其间的恐惧感。“封闭的建筑空间和不断流逝的混乱人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唤起一种莫名的恐惧……四面袭来的无名力量将行人推入其间,使人们深陷于赤裸裸的恐惧。”[2](39)可见现代都市在克拉考尔眼中就像一座迷宫,在飞速转换中掀起眩晕和骚动,如柏林的街道就弥漫着一种无可名状的不安情绪,给人留下“恐怖惊慌”的印象:汽车飞速驶过,乘客冷漠地向车外张望,面无表情地看着一闪而过的人行道、商店和涌动的人群,等等。眼前永远是陌生的面孔,每个人都不知去向何方。柏林的存在不像一条直线,而是一系列的点;它每天都是新的,就像是报纸,一旦过期了,就被丢在一边。“现代人”正是在这种从一个主题到另一个主题转变的生存中体验着兴奋和恐慌,也由此导致了现代人生存的不确定性和流动性。
除了在公共生活的都市街道,克拉考尔还在公共生活的内室发掘出了现代性的痕迹,只不过在他看来,这些现代性痕迹被虚假的意识形态所遮蔽,生活于其间的人们往往浑然不觉,甚至还沉浸于统治阶级精心编制的幻影之中。比如职业介绍所,它既包含了克拉考尔的空间社会学成分,也融入了对意识形态的批评,同时还是一条本雅明意义上的“拱廊街”。空间在这里被视为一种社会建构:每个社会阶层都有一个与之相联系的空间。空荡荡的职业介绍所内摆着少得可怜的家具,墙上却贴着“失业者!爱惜和维护公共财物”之类的警示语。克拉考尔对此别有深意地问道:“总共有多少值钱的东西值得动用如此夸张的辞藻呢?几张破旧不堪的桌椅板凳,既无须假借公共财产的名义,也没必要维护,甚至用不着特别的爱惜。社会由此保存和维护了财产;它甚至在完全没必要加以防护的地方,都设置了语言的战壕和壁垒。它可能是无意中这样做的,大概一些受其约制的人也几乎没有留意这一举动。但那恰好是语言的妙处;它下达不是指令的指令,而且把壁垒构筑到了无意识当中。”[3](P195-196)无论是对失业统计的各种评价,还是相关的议会辩论,都没有提供任何有真正意义的信息,它们都被意识形态所渗透,并在一种或另一种意义上,是被扭曲了的实在。与职业介绍所相类似,在大型百货商店,克拉考尔也意识到意识形态在空间意象中的遮蔽作用。表面看来,商店职员和顾客共享着美妙的购物环境:徜徉在宽敞明亮的商场里,似乎人人都是“上层人士”。实际上,灯火通明的环境不仅激发着顾客的购物欲望,同时也起着一种通常为人们所忽视的作用:职员们在这里工作,往往会忘掉生活在阴暗狭小的公寓内的苦闷,陷入一种梦幻的陶醉之中。对此,克拉考尔辛辣地指出:“灯光所遮蔽的要远远多于它所照亮的。甚至可以说,如今照遍城市大街小巷的灯光,甚至还起着增加黑暗的作用。”[5](P90)大型百货商店所提供的奢华环境,使工薪大众感觉自己融入了上流社会,事实上这种幻影只不过让他们安心地停留于既定位置罢了。
对克拉考尔来说,都市空间就如同一座迷宫,它那带有迷幻色彩的瞬息万变,使人们狂热兴奋、紧张不安;而它所隐藏的现代性奥秘,使“现代人”迷倒于“美梦”之中而不能自拔。当然,克拉考尔的目的也不止于对现实的记录,而在于探求背后隐含的意义。他穿梭于都市迷宫,毫不留情地掀起虚假意识的遮羞布,袒露真实的生活本身,他以敏锐的眼光和独到的批判意识,从表层现象中挖掘出深意,从现实中看到非现实性,在都市迷宫中寻找着现代性的痕迹。
二、意义的虚无:“现代人”的精神之维
都市空间所带来的骚动不安与虚幻梦魇,猛烈地冲击着“现代人”的生存状态,给“现代人”的生存带来了全新的心性体验。然而,这种新的变化,在克拉考尔看来是充满悲剧性的,即膨胀的理性使“现代人”的感性萎缩,理智取代情感成为行为准则,利润至上的信条切断了维系情感的纽带,“现代人”成为孤独的个体,并最终导致“现代人”生存意义的虚空。为了说明这一点,克拉考尔通过碎片式的呈现方式,对“现代人”的精神生存之维展开了独到而深入的分析。
克拉考尔从大众装饰的分析入手,揭示了现代社会的理性特色:“大众装饰彻头彻尾是‘理性’的,由几个平面和圆圈组合而成。它正是占据支配地位的经济体系孜孜以求的那种‘对理智的审美性反思’:既然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原则不是从自然中单独演化出来,它必然会破坏对它来说是手段或是阻力点的自然机体。当可计算性成为必须时,人的共同体和个性消失了;只有作为大众中的一颗微小粒子,人才可以顺利地爬上图表的顶部,也才可以伺候机器。”[2](P78)克拉考尔以当时颇为流行的集体女性歌舞表演为例,揭示出在那些精确的人体动作背后的现代性规划对身体的严密训练:女性表演的大腿展露就像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人的手工动作一样准确无误。“她们排成起伏的蛇阵,她们正热情地演示着传送带的美德;当她们随着快速的节拍跺脚起舞,那声音听起来像是做事、做事;当她们以数学般的精确,高高地踢起双腿,她们正欢快地颂扬理性化的进程;并且,当她们毫不中断其程式,一直重复同样动作的时候,人们可以想见一个摩托车长龙连续不断地开出工厂的场面,而且相信对繁荣的祝愿永无完结。”[3](P199-200)在他看来,大众装饰流露出一种程式化、理性化的激情,而它们对应的正是资本主义的生产链条。每个人都在流水线上从事着局部工作,却无从了解生产的全貌。跟体育场上的阵型一样,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也是按照理性原则设计的。而资产阶级政府则是这种理性崇拜的始作俑者,他们宣称“理性化适应于科技和系统组织所提供的各种方法,它推动经济增长,在减少成本的同时,促进商品的批量生产”[5](P43)。可见,在克拉考尔看来,现代社会是一个崇尚理性的社会,无论是大众装饰还是歌舞表演,都流露出一种程式化、理性化的激情,它们往往是资本主义生产链条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现代人”则受困于这样一个无法实现人类个体性潜力的系统,人性在理性至上的现代社会被忽视,已不再扮演重要角色,而这种理智最终导致了大众的同一,导致“现代人”感性的缺失。
无疑,克拉考尔对资本主义理性是持批判态度的。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的理性并非理性本身,而是一种昏暗不明的理性……这是一种不包含人类自身的理性……资本主义的核心缺陷在于,它不是理性化过了头,而是理性化得太不够”[2](P81)。在克拉考尔眼中,资本主义的理性并不是真正的理性。真正的理性应该建基于人性,能够丰富和发展人的本质。韦伯曾把理性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种,前者是一种强调手段而不追问目的的理性,它成为奴役人的工具,最终使人们丧失自主性和能动性;后者则是一种强调价值与意义的理性,它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马尔库塞则认为,真正的理性应该是人性中一种超越现实的批判意识,如今却成为一种固定的模式禁锢了现代人的生活。①克拉考尔与韦伯和马尔库塞一样,对资本主义理性心怀忧虑,不过,他更多的是从大众装饰、侦探小说、白领雇员这些世俗的人与事着眼,在对其观察调研中展开对资本主义理性的批判。在他的分析中,资本主义所倡导的理智并不是理性本身,而是一种枯燥的理性,一种不包含人类自身的理性,它平均化了性质各异的事物,使世间万物在人们眼中沦为毫无特色的单一存在。置身于资本主义理性社会,“现代人”失去了丰盈的感性、独立的思考和鲜活的创造力,转而麻木地接受一切,从而导致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冷漠。
可以说,酒店大厅里的人们正是克拉考尔笔下彼此疏离的“现代人”精神生存的生动注脚。与小城镇中的亲切互动相比,大都市中的人际交往就像浮萍聚散,人们由于一种共同的利益而暂时联系在一起。在这种短暂的表面的交往中,没有人愿意敞开心扉,流露出真实性情。而“现代人”正是这样一群彼此疏离的陌生人。克拉考尔甚至悲观地认为,在现代性语境下,个体的感受和价值再难与社会融为一体。“现代人”在其情感深处是孤立无援的,“人类主体,原本是遍布世界的形式之舞的一个组成部分,如今却沦为仅是心智活动的能动者,孤零零地面对无边无际的现实世界……(他)被放逐到时空俱滞、冷寂无垠的荒原之中”[3](P158)。“现代人”渴望融入日常生活的世界,却又处于游离的边缘,他们在彼此疏离的同时,也体尝着深深的孤独感。
此外,在克拉考尔看来,社会的瞬息万变使得无止境的追逐成为都市现代人心灵深处的一种信念。“这种信条把生命阐释成从一种新事物再到另一种的永恒的追逐和紧迫性,同时,它把任何永久的和不变的东西都从生活中剔除并禁止它们发生作用;这种信条,把运动而不是该运动的目标摆在观察的中心位置。”[3](P149)克拉考尔深刻地感受到了现代社会的瞬息万变,当下的一瞬间本身,永远不会一直停留在现在,它总是处于消逝中的一点上。这就导致了大都市生活中对新异的无止境追求和时间意识的永久性转变。没有目标的永恒追逐,使现代生活与真实存在相抽离,人们转而投向娱乐寻找刺激,最终换来的只是人生意义的虚空。在这里,克拉考尔表达了他对于世界意义失落的忧郁。“当简洁的信仰愈来愈被当作束缚所用的教条,被当作令人懊恼的理性的桎梏而被加以保存的时候,被意义粘合在一起的宇宙解体了,世界自身分裂为存在着的事物的多样性和面对着这种多样性的主体。……主体被弹射到空洞时空展现的冷漠的无限性之中,发现自己面对着已被剥去了一切意义的物质。”[6](P87)在他看来,世界已不再作为一个整体存在,它的流动性取代了意义的整体性。现代个体,不管是商人、学者、医生、律师或知识分子,都只是在孤寂中消磨时光,他们每天为工作奔走,却在喧嚣之中忘记内心深处的呼唤。“现代人”被困在一个无法实现个性潜力的系统当中,“只是强大的、没有灵魂的、依靠无数相互啮合的小轮子来运转的机器上的一个齿轮。奋斗的目标从内心关注的视域中消失了”[3](P148)。生存最终成为没有目的地的徒劳,人们永远在旅途中辛苦追赶,却终究无法找到归宿。没有目标与方向,找不到意义与目的,“现代人”面临着空洞与虚无。
在克拉考尔的分析中,“现代人”是孤独的个体,他们发现自己游离于大众之外,他们在疏离日常的芸芸众生的同时,也承受着如此强烈的孤独感。对于失去信仰和情感慰藉的“现代人”而言,生活的奔忙成了没有意义的徒劳。娱乐消遣成为应对无聊的工具,它们所唤起的却只是对麻木神经的刺激,没有生命的痕迹。对“现代人”的这种精神生存之维,克拉考尔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批判性介入,并在此基础上对“现代人”的生存救赎展开了剖析。
三、碎片中的审美:“现代人”的救赎之途
在现代性问题史上,最早对“碎片”进行审美阐释的是齐美尔。齐美尔对于现代性的思考,不是从宏观的概念体系出发,而是凭借对生活的细微感觉来捕捉稍纵即逝的瞬间和碎片,进而挖掘生活中的审美意蕴。受齐美尔的启发,克拉考尔也选择从“碎片”着手展开对于现代人救赎的思考。对他来说,从“碎片”出发,可以把握现实世界、发现生活的真意,从而为“现代人”的生存救赎提供有效的途径。
克拉考尔认为,只有追寻日常生活的直接具体的现实,才能揭示现实领域的内在结构。于他而言,碎片可以串起历史的脉络,展现被掩盖的社会生活的原貌。在他看来,对于一个时代的解读应当针对不起眼的社会表象,而不是时代自身的评判。因为后者并不能为社会的全貌提供可信的证据,而关于表层的阐述则借由其无意识性,直达事物最基础的本质结构。“对于事物的了解有赖于其关于表层的阐释。每个时代的表象与其内在本质往往是相辅相成的。”[2](P75)克拉考尔认为,从概念出发的思考实际上脱离了现实本身,人们不可能借此抓住现实。因此,他的分析总是着眼于日常生活中实实在在的片段,认为通过碎片来揭示社会的真相,捕捉瞬间中隐藏的审美内蕴,是现代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激情之所在。
弗里斯比曾评价克拉考尔早期的著述“表现了一个不变的主题,即作为一个总体的世界的破碎性:在一个意义尽失的世界中,仅剩下个体,面对着不再具有任何更高意义或价值的日常存在的碎片”[3](P246-247)。而本雅明也曾这样描述克拉考尔,“一个黎明时分的拾荒者,用棍子串起片断的言语和零星的对话,把它们扔进手推车中。他郁闷而又固执,略带醉意,但从不会无动于衷地,任由这些被舍弃的碎片——人道,灵性,深挚,其中的一种或另一种,随清晨的微风飘走”[3](P142-143)。事实上也正如本雅明所描述的那样,克拉考尔穿梭于都市(主要是柏林和巴黎)的迷宫中,领悟那些显现了现代性奥秘的现实碎片。他往往从无关宏旨的表面碎片入手,采用了一种自下而上的视角,通过拾起现实碎片来呈现“现代人”在社会生活中特有的心性体验。可见,在克拉考尔眼里,这些碎片是现代性已经逝去的历史的部分,而且,这些碎片能够被再次利用,通过拼接组装,给人们提供一个新的可以理解的脉络。碎片看似毫不起眼,却是把握现实世界的起点,它们蕴含着人性的光芒,串联起历史的纽带,饱含着生活的深意。借由这些反映着真实生活的碎片,被物欲吞噬的感性有了复苏的希望,被切断的历史有了串接的可能,而日益抽离于现实本身的人们也有望贴近真实。在他看来,通过将现代碎片与现实总体相连,日常生活得以向审美状态敞开,而这对于感性缺失、情感疏离、意义虚空的“现代人”而言,无疑具有救赎意义。
关注现代生活的碎片,使克拉考尔具有一种自下而上的视角:紧紧扣住直接体验到的现实,从世俗中发现生活的本真。克拉考尔对世俗中所蕴含的意义给予了深切的关注,在他看来,“通向真理的道路就在世俗当中”[2](P201)。他以直接体验到的活生生的现实为出发点,围绕着高雅文化的边缘区域,去挖掘常常被忽视的世俗:比如白领职员、大众装饰、庸俗艺术等。在克拉考尔看来,白领职员是现实的模型,是展示最新德国的马赛克,只有以这一典型作为切入点,才能更充分地揭示真正的现实。②这是一次“也许比电影中的非洲之旅更具冒险性的历险。因为,我们在研究白领职员的同时,也将触及都市生活的内核。尤其在当代的柏林,一个明显拥有白领文化的城市。……只有在柏林,这样一个并不强调籍贯和故乡的地方……白领职员的现实才能得以理解”[5](P32)。诚然,白领职员数目的激增,是现代化大都市的一个突出现象。每天,成百上千的白领职员挤满街道成为柏林这类大都市的一道奇观。但是,他们的生活状况却不为人所知。大部分知识分子认为白领职员太过普通而对他们缺少兴趣,至于白领职员自己,更是最少关注自身境遇的人。笔者以为,在克拉考尔的分析中,白领职员是研究现代人生存状态的具体对象,是都市意象研究的切入点,同时也是对文化层面上的娱乐主题研究有着重大意义的群体。围绕白领职员所做的分析,构成了他的研究重心。在他看来,针对白领职员这一“未知之地”的研究,能够使人们意识到自身的真实境遇,从而引发批判反思的意识。这对抽离于现实、几于麻木的现代人而言,正是认识自我、回归本真的关键所在。
克拉考尔坚信:“人必须在世俗中直面神学,两者间的裂隙和鸿沟,正表明那里是真理沉没的地方。”[3](P165)克拉考尔对日常世界的分析表明,即便在一个丧失了较高意义的世界里,这个“较高领域”被从原有的位置移开后,现如今就寄居在那些表面看来非常琐碎的事物当中,即隐身于日常世界的表面现象之中。这些在世人眼中看似意义甚微的世俗表象,在克拉考尔眼中却是现代人通往本真的入口。克拉考尔倾向于对世俗表象的凝视与剖析,继而挖掘出背后隐藏的真实,而且,他对世俗人事的关注,也表明他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群众自我救赎的能动性,而这也正是他对现代人最终实现审美救赎所寄予的希望。
然而,克拉考尔从碎片出发,于日常世俗着眼,最终旨在复原现代人的理想生存状态。他认为,“现代人”陷入思想的虚空,成为对现实漠不关心的孤独之人,而只有与事物直接沟通,亲近现实世界,才能走出抽象化的危险。在他看来,这一任务应该由提升我们生活经验的艺术来完成,而电影正是一门能将现实完整呈现出来的艺术。在克拉考尔眼中,“现代人”不再有共同的信仰,科学的发达导致人们“把现实现象数学化”,把事物的具体的物质内容化为抽象的认识,而看电影的意义则在于使“现代人”体验物质现实,把注意力从内心世界转移到生活的外部现象上来。③
在《电影的本性》一书中,克拉考尔从电影的基本构成元素的各个角度展开了关于电影本性的辩论,全书的中心即在于其副标题——“物质现实的复原”。克拉考尔认为,“电影按其本质来说是照相的一次外延,因而也跟照相手段一样,跟我们的周围世界有一种显而易见的近亲性”[7](P3)。摄影机能够帮助人们真正“看见”现实世界,而借助于电影这种“客观记录”的工具,可以疗救我们的“抽象”和“物质的匮乏症”。可以说,克拉考尔抛开了传统的艺术观念,而用物质现实复原来概括他的电影观。在他看来,电影的本质是照相的外延。照相具有其他艺术手段少有的独特的“揭示”功能:它能抓住瞬息即逝的自然形态或人的面部表情,使人们在看照片时总能发现某些意外的,但因囿于习以为常的概念而在生活中未能看见的新的东西。正因为照相具有这种记录和揭示的功能,因而它与物质现实有着天生的“近亲性”,并且具有不同于其他艺术的特殊魅力:在记录真实、揭示意外中体现其美感。而电影存在于包围它的世界环境里,它衍生现实,也必须回归现实。当影片记录和揭示物质现实时,它才成为名副其实的影片,而通过这样一种方式,电影才能把人们从异化的内心世界带回到物质的现实中来,从而实现“现代人”生存的自我救赎。
在克拉考尔推崇写实主义美学的背后,隐伏着对现代人生存困境的救赎思考。他对电影本性的探讨已经远远超越了电影问题本身,把电影置于诸如对待世界的观念、人类生存方式等更为深广的背景中。他强调电影长镜头理论,目的在于扭转科学技术所导致的抽象性思维,使人们亲近曾经视而不见的世界。因为只有还原事物的盎然生机,“现代人”才能从抽象化倾向中解脱出来,而对于具体事物的感知与体认,才是治愈现代人心灵萎缩的良药。他认为,“为求认识‘具体的事实’,就必须既置身其外而又深入其内;为求表现出它的具体性,就必须通过类似欣赏和制作艺术品时所使用的方法去认识事实”[7](P401)。因此,克拉考尔是在提倡以一种艺术的方式来实现审美救赎。在他看来,电影正是这样一门艺术,它以审美的方式来帮助现代人实现经验的具体化。
在这里,克拉考尔的思路与齐美尔的“距离”式审美救赎有着相似之处。在齐美尔看来,艺术也能通过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来彰显自身的审美特性。这种与现实的疏远所带来的张力赋予艺术独特的魅力,从而帮助现代人以一种审美立场来品味生活,超越现实的平庸与陈旧,获得对生活的诗意发现,最终实现审美救赎。当克拉考尔在论述电影通过“陌生”的方式使人们重新认识习见的事物时,也正是试图以一种与日常遮蔽拉开距离的方式,使人们恢复对本真的体认。但是,与齐美尔强调通过“距离”来实现对日常生活的批判与审美超越不同,克拉考尔更强调电影与现实的亲近性。他认为,电影“不仅是用手指尖来触摸现实,而且要抓住它,和它握手”[7](P402)。电影应当引导人们深入物质生活,潜到现实的最下层,去挖掘世界的内在奥秘。电影以一种自下而上的方式,带领人们认识物质世界,探索生活的真意,向自然敞开怀抱,进而实现诗意的栖居。可以说,作为一名富有社会责任感和对现代性投入严肃思考的理论家,克拉考尔旨在倡导一种审美立场,呼唤一种复原物质现实的艺术方式,来帮助现代人走出生存困境,最终实现审美救赎。
注释:
①具体参考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中的相关论述。
②参考The Salaried Masses:Duty and Distraction in Weimar Germany的相关论述。
③参见克拉考尔《电影的本性》。如前文所言,流动的现代性使人们身处的世界充满了碎片,在这种语境下,人们的心灵也倾向于吸收生活的短暂瞬间。在他看来,电影能捕捉稍纵即逝的生活片段,帮助人们真正“看见”现实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