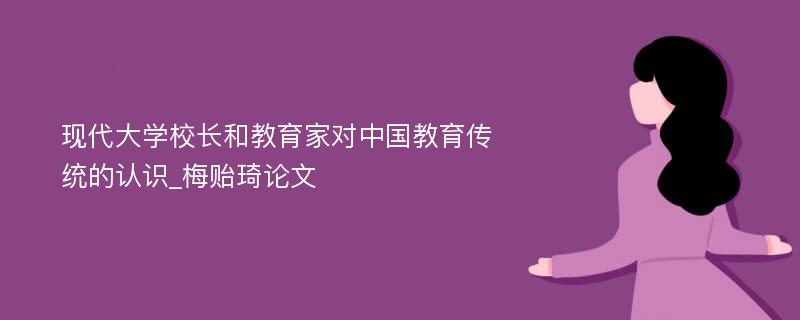
近代大学校长和教育家对中国教育传统的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育家论文,中国教育论文,近代论文,大学校长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19(2006)04—0023—07
晚清以来,废科举、兴学堂,中国现代大学得以形成和发展。大学是西方文明的产物,中国历史上有类似的高等教育机构(如大学、国子监、书院),但并未有现代意义上以“大学自治、学术自由”为核心价值观念的大学。故中国现代大学的形成与发展是学习、借鉴、模仿西方大学的结果。但是,中国现代大学并不是简单地移植西方大学,而是中国教育传统与西方现代大学制度对话、抗争、融合,并因此而形成的新式中国大学教育。
近代大学的校长和教育家,如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竺可桢、胡适、潘光旦等,认识到中国教育传统不能挽救中国教育,不可能引导中国教育走向现代化,因为中国教育传统并不能适应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是,中国教育传统是民族精神的一部分,已渗透到教育的灵魂中,并且有其固有的长处,并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现代大学发展,故完全切断这个传统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明智的。
一、继承中国传统教育精神是近代大学发展的重要方面
中国近代教育的形成与发展,诚如梅贻琦所言:“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故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就制度而言,中国教育史固不见有形式相似之组织,就精神而言,则文明人类之经验大致相同,而事有可通者”。① 中国近代教育是学习西方的结果,与中国古代的高等教育并无本质的联系与历史的继续。我国古代的高等教育机构,最早是公元前124年即汉武帝元朔五年设立的太学,后在隋以后改为国子监,实为古代最高官方学府。宋代以后兴起的书院也类似于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强调自由研讨、教与学相结合、不同学派相互交流等。蔡元培指出:“吾国历史上本有一种大学,通称太学,最早谓之上痒,谓之辟雍,最后谓之国子监。其用意与今之大学相类;有学生、有教官、有学科、有积分之法、有入学资格、有学位,其组织颇似今之大学。然最近时期,所谓国子监者,早已有名无实。故吾国今日之大学,乃直取欧洲大学之制而模仿之,并不自古之太学演化而成也。”②
我国近代高等教育,并不是古代高等教育机构的延续和发展,但大学的精神却与中国古代教育传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大学理念、人才培养、学校管理等无不渗透着中国传统教育精神。我国近代大学校长和教育家也深刻认识到传统教育精神的意义和价值,以及如何运用这种精神塑造大学。他们一直探讨如何将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和西方大学制度结合在一起。1921年,蔡元培在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演讲时,便强调应把传统的孔墨精神与英之人格教育、德法之专深教育、美之服务社会结合起来,方才是理想中的大学教育。梅贻琦的《大学一解》就是用中国传统精神诠释现代大学之内涵,认同《大学》开篇之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但总体而言,我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学习和引进西方教育体制较为成功,继承和弘扬传统教育精神则明显不足。
二、大学要“取为天下先”、“以天下为己任”
中国传统教育精神一以贯之的就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士的精神。从春秋战国时的“士不可弘毅,任重而道远”,到宋代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再到明清之际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汉代太学的学生运动到宋代的太学生上书,直至明代东林书院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中国古代教育都表现出强烈的“入世”精神与“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
这种精神和情怀使得中国大学不同于西方的“象牙塔”。特别是中国近代大学诞生于民族危亡、国衰民弱之际,导致中国大学精神的发育和大学制度的形成有着与西方国家很不相同的情境和路径。蔡元培提出“学术独立”,但也强调学术报国。他直言:“昔范仲淹为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果然有志竟成。现在的学生又安可不以国家为己任!”他将学生“精研学理”等一切长进都归到“对于社会国家和人类做最有价值的贡献”这样一个目的上。③ 马寅初在北京大学29周年纪念会上提出北京大学之精神即“牺牲主义也”,“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之私利,勇敢直前,以达其至高之鹄的”,“欲使人民养成国家观念,牺牲个人而尽力于公,此北大之使命,并即吾人之使命也”。④ 我国大学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参与意识,与古老的“太学”传统息息相关。历史上北京大学学生自认继承太学传统,以天下兴亡为己任,这种信念之确立,早在五四运动前就有所体现。所谓太学传统,主要是其“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参与意识。1903年拒俄运动中,北大学生集会抗议,表示要象古代太学生一样,“伏阙上书”。外敌入侵、国难当头的局势无疑强化了对大学和大学生社会责任的需求,这与儒家知识分子“士”的理想相当吻合。当年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的意见极具代表性。他认为“大学教育的目的,绝不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生之类”,而主要是培养“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气,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这种人才需要具备五种基本条件:肯牺牲自己,努力为国,以天下为己任;清醒而富有理性的精神;深思熟虑,不肯盲从的品质;明辨是非,而不恂厉害的气概;健全的体格。⑤
竺可桢为学校确定了求是和牺牲的精神,认为“民族自由重于个人自由”,“民族没有自由,个人合理的自由也失去保障”,⑥ 提倡浙大学生尤应刻苦砥砺,不要辜负大学神圣的使命。在1938年6月26日浙江大学第十一届毕业典礼上他号召全体毕业生要以天下为己任,“每个人也应该以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不能灭亡与不可灭亡之民族为职志”,“望各位就事,不求地位之高,不谋报酬之厚,不惮地方的运动和困苦,凡是吾人分内所应该做的事就应该去做”。⑦ 张伯苓在《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中指出南开是为实现教育救国之目的而设立的,其目的是“培养救国建国人才,以雪国耻,以图自强”,阐述了“允公允能”的办学方针,惟“公”故能化私、化教,爱护团体,有为公牺牲之精神;惟“能”故能去愚,去弱,团结合作,有为公服务之能力。“允公允能”的“目的在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众之公德,与夫服务社会之能力”。⑧ 作为清华大学、中央大学的校长,罗家伦特别强调大学为国家服务的功能。1929年,他提出一所国立大学的存在应尽两种义务:“对于人类知识的总量有所贡献;能够适应民族的需要,求民族的生存”。1941年,他提出目前中国的大学应该有三种任务:“第一是要为国家民族培养继起人才;第二,要为人类增加知识总量;第三,要能把握住时代精神和需要”。⑨ 在1932年任中央大学校长的就职演说中,罗家伦提出中央大学的使命就是为中国“创造有机体的民族文化”,其具体含义“第一,大学必须具有复兴中华民族的共同意识……第二,必须使各部分文化在这个共同意识之下,成为相互协调的……精神一贯、步骤整齐,以趋于民族文化之建立的共同目标”。“民族文化乃民族精神的表现,而民族文化之寄托,当然以国立大学为最重要。”⑩
三、注重人格培养,陶冶品学才德皆健全的人才
儒家的教育目的是培养“士”,而“士”的标准是“君子”或“君子儒”。“德者,才之帅也。才者,德之资也。”德才兼备,方是君子。儒家把道德教育居于首位,但同时也未忽视知识教育的作用。孔子说:“好仁不如好学,其蔽也愚”,“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未知,焉得仁”。董仲舒说:“仁而不智,则爱而不别也;智而不仁,则智而不为也。”这就是儒家传统的德智统一观,德育要通过智育来进行,智育要为德育服务,德育与智育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孔子还提出君子应有“智、仁、勇”三方面的修养:“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即仁德之人不忧虑,智慧之人不迷惑,勇敢之人不惧怕。此外,孔子还注意美育陶冶,提出人的修养“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提出君子应“文质彬彬”,追求“尽善尽美”。由此可见,孔子提出了使受教育者在仁(德)、知(智)、勇(体)、美(乐)等方面全面修养、和谐发展的目标。
在近代中国文化崩解,新的社会文化教育精神尚待建立之时,我国近代大学校长和教育家们一个共同追求,是继承儒家文化中培养君子、士的人格理想,使之与现代知识分子的养成相衔接。梅贻琦将大学之道概述为“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他系统地提出了通才教育的理念,强调“通才为本,专识为末”,大学教育“通专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也,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已,亦所以自通于人也,信如此论,则通论为本,而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11) 他认为“工科教育于适度的技术化之外,要取得充分的社会化与人文化,是工业化问题中最核心的一个问题。”(12) 朱光潜在《文学院》中明言教育目的“不仅在训练一技之长, 而尤在培养宏正通达之士;不仅在传播知识技能,而尤在陶冶品学才识具备之完人与培养健全之士风”。(13)
中国近代教育家往往把培养健全人格之人才与士的自觉性相联系。潘光旦在反思教育的缺点时写道:“教育没有能使受教育的人做一个‘人’,做一个‘士’”。而“士”的首要命题是做人,故《大学》的结论是:“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以修身为本”。对儒家来说,修身具有普遍价值,而且得到墨、道两派的认同,《老子》有“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之说,墨子、管子、荀子都著有《修身》篇。“志”是在做人上的最高体现,是“士”的重要标准。中国历代学者几乎无不强调立志。1924年10月张伯苓在阐述南开训练之方针时道:“其一曰,志大而正”,把“志”放在首位。潘光旦认为实践上的教育,须有两个步骤,首先是立志,其次是要学会忠恕一贯的道理。(14) 唐文治致力于将文化传统融于现代教育中,他提出“欲成第一等”,学问、事业、人才,首先砥砺“第一等品行”,要做大智、大仁、大勇之人。(15) 唐文治认为对大学生应“以道德端其模范,以规律束其身心”,使其“蔚为通才”;大学的功能,“其大要在造就专门人才,尤以学成致用,振兴全国实业为主,并极意注重中文,以保国粹”。(16) 在办学中强调道德育人,德才统一,知行合一;主张文理兼通,两文并重,既重数学、物理、外语,又重中文学习,使学生由“文理兼通”而达“体用兼并”。他为交通大学撰写的《工程馆记》集中表达了洋务运动以来主流的教育理念:“维余平生之志愿,在造就中国之奇才异能,冀与欧美各国颉颃争胜……吾愿诸生勤究物之质,更培养性之灵,庶几体用兼有,以捍外侮而致太平矣”。(17) 近代教育家郑晓沧在阐述大学教育的两种理想时说,英国大学的理想是培养绅士,德国大学的理想是培养学者,综上两种理想就是中国古代的“士君子”,“士”重学问之修养,“君子”重人格之修养。但郑晓沧又指出,中国向来重人本主义,故向来“士”之涵义,除学识外,亦必注重人格之培养。并且“士”不宜以专究某科学术之故,而摒弃其他一切,要注重全面发展。(18)
四、学术与政治:既要保持学术独立,又要参与政治,以学术回报社会
中国古代学人具有强烈的入世倾向。孔子言:“仕而忧则学,学而优则仕。”尽管对这句话的解释历来存在分歧,但其基本含义是主张把官职与学习紧密联系起来,有官职的人应该是受过教育并继续学习的人,受过教育的人应该得到一定的官职。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治国安民的贤能之士。这种传统导致我国学术与政治紧密联系,正如陈独秀所言:“中国学术不发达之最大原因,莫如学者自身不知学术独立之神圣”。(19)
近代中国大学校长和教育家坚守学术独立,反对政治干涉学术。1912年,蔡元培任中国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亲自制定的《大学令》确立了大学“教授高深学术”之宗旨,作了“学”与“术”的分离,确定了大学设评议会,各科设教授会的所谓“教授治校”的制度。1917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奠定了北京大学兼容并蓄、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精神,“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则,循思想自由之原则,兼容并包”,从而确立了大学的基本准则和文化精神。从那时起,学术独立、学术自由的思想日渐彰显,成为中国大学占主流地位的理念。1929年,陈寅恪为王国维纪念碑撰写的铭文表达了这种心声:“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20) 并认为,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不能研究学术。但学术独立,并不等于逃避政治,视政治为畏途,视政治为污浊。贺麟撰《学术与政治》一文指出,求学术的独立自由可,求学术和政治脱节就不可,学术和政治不但须彼此独立自由,还须彼此分工合作。真正的学术独立自由,应当“磨而不潾,涅而不淄”,象孔子、孟子、顾炎武、王夫之等人,他们的学术维系政治命脉与民族兴衰。贺麟还批判了轻蔑政治的文人习气,认为这不可作为保持学术独立自由的护身符。并提出,“这种脱离政治轻蔑政治以求学术自由独立的传统风气,在学术上是不健康的风气,在政治上,也不易走上近代民主政治的道路”。(21) 1945年“七七”纪念日,昆明各大学师生举行了一次座谈会,3000多人出席。纪念会中最引人关注的问题是学人是否应有政治兴趣。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认为学人应脱离政界、商界。潘光旦却明确主张学人论政,并认为“学人论政是中国文化的一大传统”,(22) 并引用了顾炎武的话:“有体国经野之心,而后可以登山临水,有济世安民之志,而后可以考古论今”,说明一个人研究学术要有政治的志向与抱负。
真正的学者,既要追求学术独立,又不能以此为借口脱离政治,要担负起学统道德的责任,以学术指导政治,用学术回报社会。他们喜欢引用顾炎武的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来说明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学人要用学统维系民族的命脉。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合大学在民族危亡之际,就“自觉承担起民族精神象征的重任,以刚毅、坚韧、持久的努力,沉潜于文化(学术与文学)的继承和创造,维系民族文化的血脉,保持民族文化创造的活力”,成为抗战时期“精神坚守与文化抵抗的堡垒”。(23) 抗战时期,涌现出一批国学大师,包括梁漱溟、熊十力、陈寅恪、冯友兰、贺麟、钱穆等人,以学问号召爱国救亡,对于鼓动中国人民的抗日士气起了很大作用,此为治学者忧国心切的象征。他们都有留学背景,提出新儒学、新心学等。他们都是与民族和时代密切相关的。
五、大学教师既是经师,又是人师,要以自身的人格与道德影响和教育学生
中国古人对教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要求教师把“有言之教”和“无言之教”结合起来,“言教”在于说理,以提高学生的认识,“不言教”在于示范,实际指导学生的活动。在处理两者关系方面,孔子强调的是身教,教师要以自己合乎规范的道德行为为学生做出榜样。这样,教师才能在学生心目中树立威信,教师的榜样才能发挥作用。西汉杨雄提出,“师者,人之模范也”。韩愈的《师说》将教师定义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并提出“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也”。
西学东渐,新式学校兴起,整个大学教育都是按照西方人的思路办学,其特征是注重知识的传授,而不太注重人格的培养。钱穆有一段话讲得很精彩:“西方人重其师所授之学,而其师则为一分门知识之专家。中国则重其师所传之道,而其师则应为一具有德性之通才”。梅贻琦认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里的“大师”不仅因其学识渊博,而且因其是学生的道德楷模,是经师与人师的统一。在《大学一解》中梅贻琦进一步用“小鱼和大鱼”的关系比喻了师生关系。“古者学子从师受业,谓之从游。孟子曰:‘游人圣人之门者难为言’,间尝思之,游之时义大矣哉。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反观今日师生之关系,其一奏技与看客之关系耳,去从游之义不繤运哉!”“大鱼前导,小鱼尾随”的“从游”之喻形象地表明了中国古代师生耳濡目染、传之业、授之道的师生之谊。梅贻琦接着批评了当时大学教育的弊端,一是教师只注重知识传授,而忽视对学生的人格陶冶,“今日大学教育所能措童者仅为人格之三方面之一,为教师者能于一己所专长之特科知识,有充分之准备,为明晰之讲授,作尽心与负责之考课,即已为良善之教师”。二是教师只注重自身知识之积累,而忽视道德之修养,“为教师者……其曰以孜孜者,专科知识之累积而已,新学说与新实验之传习而已,基于持志养气之通,待人按物之方,固来尝一日讲求也”。三是师生关系仅限于课堂教学,而缺少相互交流,“今日学校环境之内,教师与学生大率自成部落,各自其生活之习惯与时尚,舍教室中讲授之时间而外,几乎不相谋面,军兴以还,此风尤甚,即有少数教师,其持养操守足为学生表率而无愧者,亦犹之椟中之玉,斗底之灯,其光辉不达于外,而学子即有切心于观摩取益者,亦无从问径”。大学教师既要善于教学,“古之善教人者,《论语》谓之善诱,《学记》谓之善喻”,又要善于育人,“古人所谓身教,所谓以善先人之教,所指者大抵即为此两方面之品格教育,而与知识之传授不相干也”。(24)
六、书院制的理想和现实
20世纪初,伴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实行了一千多年的书院教育制度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新式学堂一统天下。晚清思想家中,最早对废书院改学堂表示不满的,首推章太炎。他在不少场合为传统的书院制度作辩护,并将其作为批评新式学堂的主要理论武器;与此同时,选择独立讲学的姿态,拒绝进入现代大学体制。章太炎把教育和学术复兴的希望寄托于同人自由组合的学会,而非政府控制的学校之上。因为聚众讲学的明德之士,其长处在于思考之独特,作述之精深;任职学校的官学之师其职责在文化的普及,学术之遍布。学校发展赖于实事求是的精神和自由探索的勇气,以及摆脱朝廷一时一地之“用”。(25)
不仅旧日巨儒关注书院制度,就连致力于以欧洲大学为模式改造北京大学的蔡元培也提出把书院之长与西方大学之长相结合。他在《湖南自修大学的介绍与说明》中讲到:“书院旧制,荡焉无存。大学规程,虽有研究所之目,而各地讲授学术之所,多及专门学校而止。即有大学,亦仅为毕业之准备;至于极深研几之业,未遑及也。”“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其诸可以为各省新设大学之模范者与?”梁启超也建议采书院之长于新式学堂中,在新式学堂中实行自由讲座制。他批评近世学校教育,一是“各科皆悬一程准,课其中程不中程”;二是“其学业制相授受,若以市道交也”。至于自由讲座制的具体实施,则有如下规划:“此种组织,参与前代讲学之遗竟而变通之。使学校教师学生三者之间,皆为人的关系,而非物的关系……如此则教育不至为‘机械化’,不至为‘庸俗化’。社会上真面目之人才,或可以养成也”。蔡元培认为“学校确有不及书院之点”。胡适更是感叹:“把一千多年来的书院制度完全推翻,而以形式一律的学堂代替教育……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了。”(26)
湖南自修大学与古代书院的传统在某些方面非常类似。毛泽东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说:“回看书院,形式上的坏处虽然也有,但上面所举学校的坏处(指师生间没有感情,用一种划一的机械的教授去残戮人性,钟点过多,课程过繁,就会不能用他们的心思为自动自发的研究)则都没有。一来是师生的感情等。二来,没有教授管理,但为精神往来,自由研究。三来,课程简而研究同。可以优游瑕喻,玩索有得。”(27) 1925年,留美归来的陈衡哲、任鸿隽夫妇联合发表《一个改良大学的建议》,特别标举中国的书院精神,希望将其与欧美大学制度相结合。“我们以为当参合中国书院的精神和西方导师的制度,成立一种新的学校组织。中国书院的组织,是以人为中心的,往往一个士师以讲学所谊相号召,就有四方学者翕然成风,不但学问上有相当的研究,就是风气上也有无形的转移,如朱文公的白鹿洞、胡安定的湖州,都是一例。但是书院的组织太简单了,现在的时代,不但没有一个人可以通遍众学,满足几百千人的希望,而现在求学的方法,也没有一人而贯注几百人的可能。要补救这个缺点,我们可以兼采西方的导师制。就是一个书院以少数教者及少数学者为主体;这个书院的先生,都有旧时山长的资格,学问品行都为学生所敬服,而这些先生也对于学校(生)的求学、品行两方面,直接负其指导陶冶的责任。”(28)
近代大学研究院的设置,即是将书院精神引进现代大学体制,使当时探讨的协调东西方教育理念的思路,在办学实践中得到了真正落实。1924年,清华校长曹云祥向胡适请教如何创办研究院,“胡氏略仿昔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为研究院绘一蓝图”。1925年3月6日,清华学校校务会议通过的《研究院章程》明确说,要把中国传统的书院制度与英国的大学制度结合在一起,如第六章“研究方法”第一则称:“本院略仿旧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度:研究方法,注重个人修养,教授任指导,其分组不以学科,而以教授个人为主,其他学员与教授关系异常密切,而学员在其短时期中,于国学根底及治学方法,均能确有收获”。(29)
国外人士把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合大学的办学模式,看成是西方大学与中国书院结合的产物。美国学者约翰依斯拉尔在论述西南联大的书中生动地描述了西南联合大学从知识的纯自由主义理念即强调学术自由,到它与中国现实相结合的转变,即西方大学的学术自由与中国书院的智力自由的结合,然后又与中国当时战争的现实相结合的历程,认为“与战前很有地位的大学相比,西南联合大学更像是传统的书院”。(30) 许美德亦指出:“西南联合大学在最困难的形势和环境下进行运转,其重要而突出的学术地位说明了美国与德国的学术传统与中国传统书院的多元价值观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有机的结合。”(31) 在他们看来,正是中国书院传统与欧美现代学术价值观的结合造就了战争困苦环境中的西南联合大学。
在中华民族悠久的文明发展历程中,中国呈现出一种与欧美截然不同的教育价值体系。中国教育传统无论从形式还是从内涵上说,都与欧洲国家有着重大的差别。而传统是历史中发展出来的一个价值系统,它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全部历史积淀,是一种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和延续,是一种活着的民族精神的生命体。借鉴、模仿西方大学而又扎根于教育传统的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注定不同于西方大学。正是认识到这一点,中国近代大学校长和教育家才一方面学习西方,另一方面又强调继承中国教育传统。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近代以来面临的特殊境遇使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教育发展呈现出“反传统”的激烈色彩。近代中国在转化教育传统上,认识虽有一些,但做出的实绩并不多。在21世纪的今天,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留给我们的使命之一,就是把中国教育传统这一历史前提和资源,转化为今天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源头活水。对中国教育传统的认识、扬弃与转化,是中国教育现代化未尽的一个历史任务。
收稿日期:2006—06—09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儒家文化影响下的高等教育”项目。
注释:
① 梅贻琦.大学一解[J].清华学报,1941,(1).
② 蔡元培.大学教育[A].教育大辞书(上册)[C].北京:商务印书馆,1930.
③ 蔡元培.怎样才配作一个现代学生[A].蔡元培全集(第6卷)[C].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559—565.
④ 马寅初.北大之精神[A].马寅初演讲集(第4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⑤ 转引自杨东平.浅议中国近现代大学的教育目标[J].高等教育研究,2000,(6):33—36.
⑥ 竺可桢.大学教育的主要方针[J].国立浙江大学校刊,1936,(248).
⑦ 竺可桢.求实精神与牺牲精神[A].浙江大学西迁纪实[C].
⑧ 张伯苓.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A].南开四十年纪念校庆特刊[C].1944.
⑨ 同上.
⑩ 同上.
(11) 梅贻琦.大学一解[J].清华学报,1941,(1).
(12) 梅贻琦.工业教育与工业人才[A].自由之路[C].北京:商务印书馆,1946.
(13) 朱光潜.文学院[A].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最近实况附录“升学指导专号”[C].北京:商务印书馆,1941.
(14) 潘光旦.国难与教育忏悔[A].观察社.教学罪言[C].1948.
(15) 唐文治.上海交通大学第十三届毕业典礼训辞[A].唐文治教育文选[C].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95.
(16) 刘露茜,毛桐荪.唐文治教育改造[M].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95.19.242.
(17) 同上.
(18) 郑晓沧.大学教育的两种理想[J].浙大月刊,1936,(26—27).
(19) 陈独秀.随感录:学术独立[J].新青年,1918,(1).
(20) 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A].陈寅恪的最后20年[C].北京:三联书店,1995.
(21) 贺麟.学术与政治[J].当代评论,1941,(16).
(22) 潘光旦.说学人论政[A].自由之路[C].北京:商务印书馆,1946.
(23) 姚丹.西南联大历史活动中的文学活动[M].云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24) 梅贻琦.大学一解[J].清华学报,1941,(1).
(25) 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6) 胡适.书院制史略[A].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史料[C].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27) 转引自章柳泉.中国书院史话:宋元明清书院的演变及其内容[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
(28) 陈衡哲,任鸿隽.一个改良大学教育的提议[J].现代评论,1925,(39).
(29) 研究院章程[J].清华周刊,1925,(360).
(30) 许美德.中国学术传统的特点与价值[A].许美德.东西方文化交流与高等教育[C].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31) 同上.
标签:梅贻琦论文; 大学论文; 大学教育论文; 西南联大论文; 中国教育论文; 国学论文; 蔡元培论文; 中国大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