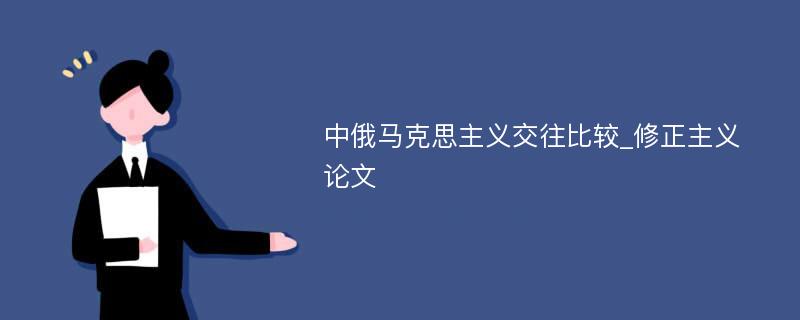
中俄马克思主义传播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中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中国的传播,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俄国、中国的国情不同,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中国的传播也具有不同的特点。透过这些特点,我们试图找到今天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中国不同命运的原因,使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自觉地不断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论创新。
一、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早期传播及其特点
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普列汉诺夫是这一运动的先驱,经过普列汉诺夫、列宁等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努力,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得到广泛传播,并与俄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成立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
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具有以下特点:
(一)把传播马克思主义与批判地继承俄国唯物主义思想传统紧密结合起来
在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和东正教的斗争中,俄国形成了唯物主义思想传统,产生了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杰出的俄国唯物主义思想家。他们不仅受到俄国先进分子的尊重,而且也受到马克思的高度评价。因此俄国唯物主义思想传统成为俄国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桥梁。普列汉诺夫、列宁等人正是在批判地继承俄国唯物主义思想传统的同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如普列汉诺夫评价赫尔岑的名言说:“黑格尔哲学是革命的代数学,它不同寻常地使人得到解放,并彻底打破基督教的世界,打破过时的传说世界。”“这说得非常好,非常鲜明。”[1](P708-709)但是“赫尔岑没有预感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立是他那个时代最重要的理论成就之一”[1](P790)。与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波罗留波夫相比,“别林斯基在许多方面是他们的先驱”[1](P789-790)。在1890~1892年,普列汉诺夫连续发表四篇论文,正确、全面地评价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哲学、历史、经济、政治和社会主义思想。他指出:“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位唯物主义者。”[1](P542)但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社会主义问题也像对其他历史发展的一般问题一样,是从唯心主义观点来考察的”[1](P122)。他还批判了自由民粹派竭力把自己伪装成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继承者的罪恶行径,指斥他们是“主观主义者大吹大擂,自称是六十年代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人,实际上他们继承的仅仅是这个时代的世界观的缺点”[1](P79)。他还结合欧洲思想发展史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文明的产物,从历史与现实、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角度,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和丰富的革命内容。列宁比普列汉诺夫大大前进了一步。他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不但批判地吸收了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唯物主义思想,而且批判地吸收了其反对沙皇制度和解放农民的民主革命思想,把这一思想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俄国特色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相统一理论,为十月革命胜利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二)把传播马克思主义与批判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结合起来
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传播正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巴黎公社的失败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统治政策的调整,使主张“议会斗争”的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尘嚣日上,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传播也受到修正主义的冲击。针对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歪曲,普列汉诺夫首先批判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哲学口号“回到康德去”,指出伯恩施坦背叛唯物主义而号召“回到康德去”,完全不是哲学家的普遍错误,而是他同资产阶级同流合污的自然的、必然的和鲜明的表现。其次,通过对“布丁之味在吃”和工业发展的实践的论述,普列汉诺夫证明了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对康德的“不可知论”做了最好的反驳。“他们(修正主义者)把它(唯物史观)解释得完全脱离了唯物主义的立场而回到唯心主义,或者更正确些说,回到折中主义”[2](P388),并企图使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离开哲学唯物主义,用新康德主义和马赫主义来代替唯物主义。列宁对修正主义进行了全面、彻底的批判。在《怎么办》等著作中,列宁不仅批判修正主义的哲学基础,而且批判修正主义反对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反动实质,不仅批判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而且批判了修正主义在俄国的变种——“合法马克思主义”,保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三)总起来说,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存在着较严重的脱离实际的倾向
首先,普列汉诺夫作为俄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优秀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他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时,脱离了俄国革命实践。这是因为他长期侨居国外,这不能不使他脱离俄国的工人运动,他不可能亲自到工人中间去宣传、鼓动和指导,不能及时全面地总结工人运动的经验教训。尽管他与俄国国内的马克思主义小组保持着联系,但是他的古怪粗暴的性格,使他较少接触到来自国内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从而更加远离俄国革命的实践。其次,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侧重理论阐述,其理论著作存在着严重的学究气、书呆子气,表现为过多的逻辑论证和理论对比,显得比较抽象,缺乏通俗性和形象性。如普列汉诺夫在批判继承俄国的唯物主义思想的优秀成果时,“几乎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人类的‘理论’活动上,因此智力的发展在他眼里就成了历史运动的最深刻的原因”[3](P539)。再次,俄国沙皇专制制度,特别是严格的书刊检查制度,不仅使大量反映俄国革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文章无法登载,而且使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者被逮捕、流放或杀害,列宁、斯大林、捷尔任斯基等人多次被捕和流放,他们只能以极端秘密的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接触俄国的工人运动,这是造成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存在着较严重的脱离实际倾向的重要原因。后来随着列宁等一批职业革命家的成熟,这一状况逐渐得以改变。
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特点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始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特别是五四运动爆发之后,传播马克思主义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在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者的努力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工人运动相结合,成立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其在俄国的传播,不仅面临国情的不同,而且处于不同的时代。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具有以下特点:
(一)传播马克思主义与宣传和介绍十月革命的经验和意义紧密联系在一起
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正是巴黎公社失败后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低潮;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处于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新时代;因此,十月革命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推进剂。“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9](P1471)。如果说在十月革命前,中国的先进分子曾认为“社会主义,理想甚高,学派亦甚复杂,惟是说之兴,中国似可缓于欧洲”[5](P170)。经过十月革命,中国人民认识到中俄社会历史条件相近,既然俄国能实行社会主义,中国“谋社会主义的实行,也是一定可以在短时期内成功”。“物质文明不高,不足阻社会主义之进行”[6](P142)。人们觉得要救中国惟有采用“俄国式的革命”。1920年12月1日,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复信中,表示“深切赞同”蔡和森的主张,即走俄国人的道路,组织共产党,经过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改造中国社会的目的。1921年1月1日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的新年大会上,毛泽东提出“主用俄式,我极赞成”;“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达到)预计效果的,故宜采用”[7](P2-3)。中国的先进分子在介绍和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的同时,广泛传播了马克思主义。
(二)宣传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中心内容
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也是十月革命的基本经验。传播马克思主义和“走俄国人的路”,就必须宣传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但是,中国的反动军阀把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视为“过激主义”,借以严禁马克思主义传播。即使当时一些主张社会改造的政治派别也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如:胡适主张“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认为“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没有用处的”。不去研究些问题,高谈社会主义“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8](P312-316)。研究系的梁启超、张东荪也认为中国不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其总原因在于无劳动阶级”[9],反对在中国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从否认强权政治出发,尤其集中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提出:“我们不承认资本家的强权,我们不承认政治家的强权,我们一样的不承认劳动者的强权。”[10]他们污蔑苏俄无产阶级专政是“压制个人的表征”。咒骂布尔什维克是“独裁、专制”,叫嚷“应早早废止劳农政府”[10]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上述非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三次论战,从对中国社会进行根本改造的实际出发,结合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论证了必须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社会的旗帜,以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反动政权和帝国主义压迫,建立劳动人民的政权。如1920年9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8卷第1号上发表《谈政治》一文,以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及胡适等人的观点和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深刻阐明了唯物史观关于阶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思想;李达也在1920年12月和1921年6月先后写出了《马克思还原》、《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等文章;蔡和森在1920年7月主张马克思主义的激烈革命,主张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立即组织共产党,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1920年12月1日和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回信中,赞成蔡和森的“走俄国人的路”主张,并进一步指出:“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11](P15)“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的看法都只认为理论上说的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11](P8)施存统的《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工读互助团”的实验与教训》、《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应用》等文,不但对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进行辨证分析,而且提出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主张。
(三)传播速度较快(与俄国相比),但理论成果不足
首先,从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开始传播,到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成立,历时20年(1883~1903)。而这一过程在中国仅4年(1918~1921)。其原因在于,一方面,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对旧思想、旧文化、旧秩序的冲击,打开了中国当时思想界的闸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提供了优越的条件(与19世纪80年代后的俄国相比)。马克思主义就是随着当时各种新思潮一起在中国广泛传播的,特别是五四运动后,传播马克思主义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更是极大地加快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强烈的实践性,十月革命的实践榜样,再加上中国先进分子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新思想的论战、实践验证,大大缩短了马克思主义被接受的过程(注:这种环境和做法在俄国是没有的,在俄国马克思主义只能以秘密的、隐蔽的方式来传播)。据不完全统计,五四运动后的一年间,全国新出版的期刊猛增到四百余种,新成立的社团发展到三百多个。其中不少期刊和社团以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研究马克思主义为其主要宗旨[12](P6)。不仅如此,在短短的两三年里,中国的许多先进分子还对当时最时髦、最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想进行实验,结果表明无论是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还是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还是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都是“理论上说的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决心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践。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在论战、实验和交流中,深化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认识,不断纠正自己的错误。如:蔡和森到法国勤工俭学,一到法国就“猛看、猛译”马克思主义著作,在1920年7月提出中国要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激烈革命,主张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立即组织共产党,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并与国内的毛泽东通信交流,1920年12月1日和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回信中,完全赞成蔡和森的“走俄国人的路”主张。其次,与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巨著相比,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理论成果不足。一方面,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后,比较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译本仅四、五本,其余多为节译的片段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介绍。另一方面,建党前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存在着简单化、片面化的理解,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建党以前几乎没有提及,直到1923年后,瞿秋白、李达才介绍辩证唯物主义的内容。如:李达的《现代社会学》、《社会哲学概论》等阐述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著作写于二十年代以后。因此,中国共产党建党理论准备不足,这是我党在幼年时期屡犯错误的原因之一。
三、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中国传播的经验和教训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中国传播各有优势和不足,形成了各自的经验和教训。
第一,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早期传播历时近二十年(1883~1903),在这近二十年里,以普列汉诺夫、列宁为代表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从本体论、认识论、逻辑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多个角度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对马克思主义从哲学到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和发展,远远超过中国无产阶级政党成立前后的理论准备。如仅《共产党宣言》就先后被翻译过三次(加上1869年巴枯宁的译本);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等人写下了诸如《唯物主义史论丛》、《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怎么办》等著作,为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革命做了充实的理论准备,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俄国革命经过14年(1903-1917)取得了胜利。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时间较短,中国共产党建党理论准备不足,因此,在建党后相当长一个时期里,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内容了解不深,不善于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路线、方针、政策;而是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或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的经验,先后出现过三次“左”倾错误和两次右倾错误。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才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第二,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早期传播存在的脱离实际的倾向,不但表现在普列汉诺夫身上,而且对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运用产生影响。正如列宁指出:“普列汉诺夫由于只看到唯心主义历史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理论差别,而忽略了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的政治实践的和阶级的差别”[13](P611)。“所以普列汉诺夫虽然坚持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但是他不能将唯物史观与唯物辩证法有机结合起来,他看不到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历史作用,把广大农民也抛到一边,却对自由资产阶级参加俄国革命抱有极大的幻想,在十月革命前后成了一个机会主义者。”“普列汉诺夫的理论著作——主要是对民粹派分子和机会主义者的批评——仍然为全俄社会民主党员的牢固收获……可是作为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社会民主党的政治领袖来说,作为策略家来说,普列汉诺夫就不值一评了。他在这方面表现这样一种机会主义。这种机会主义给予俄国社会民主党员——工人的损害,要比伯恩施坦的机会主义给予德国人的损害多出百倍以上。”[13](P225)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运用过程中,除了列宁、斯大林等人能够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俄国的国情相结合外,斯大林以后的苏联领导人都无法做到这一点,不能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论创新,他们要么固守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和苏联僵化的政治、经济体制,要么在政治上全盘抛弃马克思主义和否定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企图以“政治上的自由化、人道化”、“经济上的私有化”和“思想文化上的多元化”来“发展”马克思主义,最终丢掉了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极为沉痛的教训。
第三,马克思主义的强烈的实践性和中国先进分子的炽热的“救亡图存”的爱国情感,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一开始传播就不是被当作一种只是在书斋中进行学术讨论的纯粹的理论,而是被当作一种有鲜明的实践特色和功效的救国良方,来指导当时中国“社会根本改造”的实践。正如陈独秀在《学说与装饰品》一文中指出:“学说之所以可贵,不过为他能够救济一社会、一时代的弊害昭著的思想或制度。”“一种学说有没有输入我们社会的价值,应该看我们的社会有没有用它来救济弊害的需要。”[14](P25)尽管在早期传播中理论成果不多,但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方面毫不动摇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老祖宗不能丢”(邓小平);另一方向,不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不照抄别国的道路和模式,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坚持实事求是,善于在实践中不断学习,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努力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不断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论创新,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标签:修正主义论文;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无产阶级政党论文; 俄国革命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中俄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