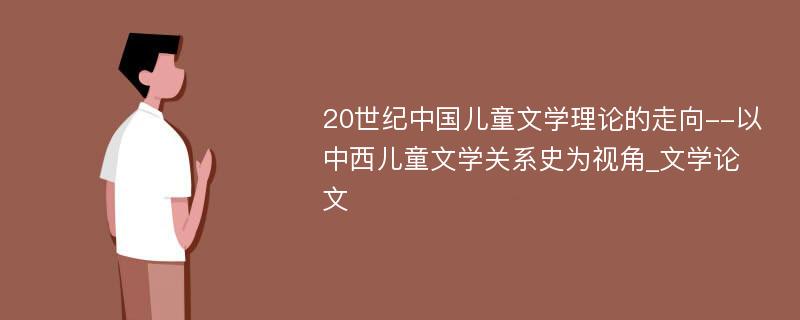
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理论走向——中西方儿童文学关系史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理论论文,中西方论文,儿童文学论文,中国论文,二十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从中西方儿童文学关系史的视点,从一个侧面描述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走向——它在发生期的性质,后来曲折发展的因由以及理论的现实需求与未来发展战略。
一、历史回顾:“别求新声于异邦”
中国儿童文学发轫于何时,学术界对此有以下三种观点:一种观点是外国“移植说”,即认为中国儿童文学萌蘖于外国童话的移植。持这种观点的人大都将孙毓修编译的“童话”丛书(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起始年1908年〔1〕作为中国儿童文学诞生的标志。另一种观点认为, 中国儿童文学是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产生的,叶圣陶的《稻草人》(1923年)是中国的第一部儿童文学作品集。上述两种观点都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儿童文学。第三种观点则与此相反,认为中国古代虽无“儿童文学”之词,但儿童文学却是“古已有之”,而且源远流长。
对中国儿童文学的诞生期的划分之所以会出现如此众说纷纭,根本原因在于研究者对儿童文学的本质以及中国社会在儿童文学方面的特殊境遇持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
儿童文学的产生是以儿童的发现为前提的。因此,儿童文学只能产生于建立起尊重儿童人格和诸项权力的新型儿童观的近代社会。这一结论已经成为儿童文学理论中的公认原理。如果依据这一原理来分期,中国儿童文学古已有之的看法便失去了立足的根基。当然,人们有理由挖掘神话、传说、志怪、传奇等中国古代文学样式中的儿童文学的某些要素,但是,归根结底,只能把它们看作是儿童文学的史前现象。
依据上述原理,中国儿童文学产生于晚清这一观点也似乎令人生疑,因为迄止晚清,中国社会并没有形成近代意义的儿童观。但是,探究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必须将中国近代社会的特殊性质置于视野之中。中国的近代化是在西方近代化的猛烈冲击之下开始的,在这个意义层面上,中国的近代化不是能动的而是受动的。中国近代化的这种受动性,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以及后来的发展具有根本性的影响。尽管晚清社会因没有建立近代意义的儿童观而并不能产生自给自足的儿童文学作品,但是,自鸦片战争特别是进入二十世纪之后,西方儿童文学、儿童读物的大量翻译介绍,却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催生出儿童文学的稚嫩萌芽。正是由于移植西方儿童文学作品,晚清儿童文学才呈现出一片氤氲气象。
所谓“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如果把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看作是一个过程的话,晚清无疑是中国儿童文学的胎动期。这个时期的儿童文学还没有获得主体性。到了五四时代,反对封建传统的新型儿童观的确立和白话文的提倡,打破了阻碍儿童文学成长的两大桎梏,中国儿童文学终于获得了主体性并走向近代化。
如上所述,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不具备西方儿童文学的能动性和常规性,它的发生过程脱逸出了先有创作,后有理论这一文学发生、发展的一般规律,而是表现出先有西方(包括日本)儿童文学的翻译和受西方影响的儿童文学理论,后有中国自己的儿童文学创作这样一种特异的文学史面貌。
中国儿童文学在西方文化、西方儿童文学的催生下产生这一历史事件,充分证明了中国儿童文学在诞生之初的受动性格。正是这种受动性格给得风气之先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以蓬勃的生机,使其出手不凡、震聋发聩。
在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发生期,呼唤“人的文学”的周作人做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从目前可见的史料来看,周作人于1920年10月25日在北京孔德学校所作的讲演《儿童的文学》(发表于《新青年》第8卷第4号)是中国最早立于哲学的基点,系统、全面、深入地推出自己完整的儿童文学观的一篇理论文字。在这篇论文中,周作人不仅承继《人的文学》中对封建儿童观的批判,而且更进一步正面阐述了他的儿童观:“以前的人对于儿童多不能正当理解,不是将他当作缩小的成人,拿‘圣经贤传’尽量的灌下去,便将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说小孩懂得甚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近来才知道儿童在生理心理上,虽然和大人有点不同,但他仍是完全的个人,有他自己的内外两面的生活。儿童期的二十岁年的生活,一面固然是成人生活的预备,但一面也自有独立的意义与价值;因为全生活只是一个生长,我们不能指定那一截的时期,是真正的生活。我以为顺应自然的生活各期,——生长,成熟,老死,都是真正的生活。”基于这种近代的进步的儿童观,并具体运用儿童学的方法,周作人对少年期前半的各年龄段的儿童文学,从体裁分类上进行了清晰而不乏精到的阐述。《儿童的文学》所提出的儿童文学观,如果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周作人后来在《儿童的书》一文中所强调的——“儿童的文学只是儿童本位的,此外更没有什么标准。”正是由于把儿童文学规定为儿童本位的文学,周作人才敏锐地洞察到儿童文学的两种偏颇:“在儿童文学上有两种方向不同的错误:一是太教育的,即偏于教训;一是太艺术的,即偏于玄美:教育家的主张多属于前者,诗人多属于后者。其实两者都不对,因为他们不承认儿童的世界。”〔2 〕周作人指出:“中国现在的倾向自然多属于前派,因为诗人还不曾着手干这件事业。向来中国教育重在所谓经济,后来又中了实用主义的毒,对儿童讲一句话,眨一眨眼,都非含有意义不可,到了现在这种势力依然存在,有许多人还把儿童故事当作法句譬喻看待。”〔3 〕周作人所批评的实用主义观念不仅是当时的流弊,而且在其后漫长的历史时期,一直限制着中国儿童文学的长足发展。
周作人这样的儿童观和儿童文学观,为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奠定了坚实的近代性基础。在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期,象周作人这样深刻而全面地洞察儿童文学本质的,还别无他人。比如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的鲁迅,虽然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文章中表现了与周作人十分相似的儿童观,但是,在鲁迅那里,对儿童问题的论述,主要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封建主题的扩展和深化,而并没有直接走向儿童文学,因此,鲁迅与周作人在儿童问题方面是处于不同的维度。在批判封建思想和文化上,鲁迅有着周作人所无法替代的深刻,而在儿童文学理论的奠基上,周作人则当仁不让地拔了头筹。再如就童话问题与周作人进行过数回合深入讨论的赵景深,虽然其研究的范围也比较广泛,但在接受西方学术观点时,对中国的民族性问题思考不足,有着脱离实际之嫌。此外,象郑振铎、郭沫若、茅盾等人的儿童文学主张虽各有特色和优长,但在总体的儿童观和儿童文学观上,仍然无法与周作人比肩而立。
周作人走向儿童文学理论,当然是出自他同情、关怀弱小者的心性,在他的儿童文学论中,表现出比任何人都来得强烈的对人生的追求和信念。周作人的儿童文学理论是其强烈的主体性的结晶。但是,另一个事实是,他的令人难以超越、起点甚高的儿童观、儿童文学观,是他个人的素质与西方(包括日本)思想、学术的影响相融合的产物。简略而言,他在民国初年开始的童话研究是从泰勒、弗莱泽,特别是安德路·朗那里习得神话学、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童话的研究,也于是有了门路”。〔4〕周作人自称:“对于儿童学的有些兴趣这问题, 差不多可以说是从人类学连续下来的”。〔5 〕而他的儿童学理论也同样受启示于西方和日本学者的研究著述。他在回忆录中说:“我在东京时,得到高岛平三郎编的《歌咏儿童的文学》及所著《儿童研究》,才对于这方面感到兴趣,其时儿童学在日本也刚开始发展。斯丹来贺尔(Stanley Hall)博士在西洋为斯学之祖师,所以后来参考的书多是英文的,塞莱(Sully)的《幼儿时期之研究》虽已经是古旧的书, 我却很是珍重,至今还时常想起。”〔6〕
可以说,至20年代末,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疆域成了以周作人为代表的“儿童本位”论的一统天下。虽然进入三十年代,苏联儿童文学创作及其理论的影响渐次加强,但是,“儿童本位”论仍作为系统化的理论在学界传播,1947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辞海》就写道:儿童文学乃“以儿童为本位而组织之文学也。”正如任何理论都是一种选择,因而任何理论都有不足和缺憾一样,五四时期接受西方理论产生的“儿童本位”论也并非无懈可击,但是,作为儿童文学基本理论,它具有系统性、科学性是不容怀疑的。还有一点必须称道的是,由于“儿童本位”论是在以周作人为代表的学贯古今中西的一流学者勉力借鉴西方理论构筑而成,因此,在当时与西方的学术发展进程保持着大体同步的状态。
二、借鉴的困境:理论与创作间的错位
五四时期接受西方影响而产生的“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理论漂亮地拉开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大幕。从先有理论后有创作的中国儿童文学的特殊历史逻辑来看,“儿童本位”论理应发挥其对创作的指导功能。然而历史事实却令人失望:在中国这块封建思想文化板结的土地上,在中国这块遭受外国帝国主义蹂躏的土地上,“儿童本位”论难以结出饱满的果实。
我认为,历来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研究忽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文学史现象,这就是为中国儿童文学奠基的“儿童本位”理论与后来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创作之间出现的重大错位。
叶圣陶的《稻草人》作为中国的第一部创作童话集,沈从文的《阿丽思中国游记》(1928年)作为中国的第一部长篇童话,都象征性地说明中国儿童文学创作一开始便与先行的理论之间存在着裂痕。郑振铎在《〈稻草人〉序》中曾说:“圣陶最初动手写作童话在我编辑《儿童世界》的时候。那时,他还梦想一个美丽的童话的人生,一个儿童的天真的国土。……然而,渐渐地,他的著作情调不自觉地改变了方向。……在成人的灰色云雾里,想重现儿童的天真,写儿童的超越一切的心理,几乎是个不可能的企图。圣陶发生的疑惑,也是自然的结果。我们试看他后来的作品,虽然,他依旧想用同样的笔调写近于儿童的文字,而同时却不自禁地融化了许多‘成人的悲哀’在里面。”〔7 〕叶圣陶本人似乎也意识到自己的童话渐渐出现离开儿童的倾向。他在1922年1月 14日写给郑振铎的信上就说“今又呈一童话,不识嫌其太不近于‘童’否?”〔8 〕而赵景深则这样评价童话集《稻草人》:“我以为叶绍钧君的《稻草人》前半或尚可给儿童看,而后半却只能给成人看。”〔9 〕至于沈从文的《阿丽思中国游记》,作者在《后序》中自述:“我先是很随便的把这题目捉来。因为我想写点类乎《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的东西,给我的小妹看,……谁知写到第四章,回头来翻翻看,我已把这一只善良和气的有教养的兔子变成了一种中国式的人物了(或者应说是有中国绅士倾向的兔子了)。同时我把阿丽思也写错了,对于前一种书一点不相关连……我把到中国来的约翰·傩喜先生写成了一种并不能逗小孩发笑的人物,而阿丽思小姐的天真,在我笔下也失去不少。……我不能把深一点的社会沉痛情形,融化到一种纯天真滑稽里。”〔10〕这段自述将沈从文创作《阿丽思中国游记》的经过说得十分清楚。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沈从文的作品所描写的阿丽思和兔子约翰·傩喜在中国的游历,展开了五光十色的社会世相,全书贯串着强烈的对中国文化负面和社会黑暗面的讽刺性批判,它的语言和内容都不是少年儿童所能理解的。”〔11〕
“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理论与紧随其后出现的儿童文学创作之间的错位,因由来自蕴含着西方式儿童文学精神的“儿童本位”理论这颗种子,与当时中国的社会土壤、历史气候的互不适应。其实,叶圣陶这样的“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儿童文学作家又何尝不想创作“顺应自然,助长发达,使各期之儿童得保其自然之本相”〔12〕的儿童文学作品,但是,从现实生活中获得的体验,迫使他不得不由“想重现儿童的天真”转向抒写“成人的悲哀”。文学是时代妈妈的儿子,当时的中国只能产生而且也需要产生这种性质的作品。儿童文学的生成和发展需要精神自由、经济发达、社会(国家)稳定的多方条件。在没有这些条件的情况下,创造这些条件便成了儿童文学生存、发展的首要前提。这些条件的创造当然要依靠成人社会。叶圣陶、谢冰心、张天翼等中国进步的和革命的儿童文学作家正是肩负着改造黑暗腐朽的旧社会,创造光明健康的新社会的历史责任来为儿童创作的。这种有着浓厚成人倾向的儿童文学虽然无奈地牺牲了许多对儿童文学而言十分珍贵的“儿童性”的内容和表现,但是,它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和揭露,它对合理平等的未来社会的期待和呼唤,既是“救救孩子”的切实工作,也是为更加理想的儿童文学得以出现所做的必要准备。
当然,“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理论没能在创作园地扎下根须,并不能证明这一理论就是非科学、非合理的。它的悲剧命运起因于它的生不逢时的超前性。在现实社会的矛盾斗争中,特别是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践踏的民族危亡关头,“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理论很快失去了原来的影响力。中国儿童文学也改变了学习西方的姿态转而借鉴苏联的社会主义儿童文学理论。
三、现实思考:借鉴取向的再度选择
儿童文学是最具世界性的一种文学。中国儿童文学在五四时期因对西方的学习和借鉴而露出自身的现代化端倪,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历史给予的恩惠。遗憾的是好景不长,外来的政治、军事侵略,阻绝了西方优秀文化输入的通道,而战后两大阵营的对峙局面,也逼迫中国不得不对西方文化抱封闭的心态。虽然五十年代曾有过对前苏联儿童文学的情有独钟,然而很快两国失和,对前苏联的学习和借鉴也成了昙花一现。历史肤浅、先天贫血的中国儿童文学就是在这种封闭的状态中,迟滞了走向现代化的步伐。
时光流至70年代末。改革开放打开国门,中国文学豁然看到“外面的世界真精彩”。在短短的十几年间,西方文学百年的各种思潮、流派便都在中国文坛轮番登场并施加影响。虽然壁垒与误读始终存在,但总以观之,中国(成人)文学已经与西方文学相互打通。
在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上,新时期是可以引为自豪的年代。纵观历史,中国儿童文学的创作和理论都曾出现过两个高峰。创作方面,第一个高峰是50年代,第二个高峰是新时期;理论研究方面,第一个高峰是五四时代,第二个高峰则又是新时期。新时期儿童文学在创作和理论上的梅开二度,昭示着中国儿童文学已经迎来了发展的最佳时期。即是说,五四时期,以周作人为代表的蕴含着西方精神的“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当时特定的土壤上,尚无法催开同根的创作花朵,而50年代“教育儿童的文学”创作也难以引发本体意义的儿童文学理论研究,只有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儿童文学才开始摆脱理论与创作相互错位的尴尬处境。
新时期儿童文学理论的开展是立于对五、六十年代儿童文学传统理论的反思和超越基点之上的。新时期伊始,儿童文学理论工作者就敏感地识破“教育工具论”是偏离儿童文学本体的畸形理论,进而提出了“儿童文学是文学”〔13〕的命题。虽然这一命题本来是应在儿童文学理论之前解决的问题,但是对于面对忽视文学属性的传统理论的新时期中国儿童文学来说,却是最不得绕过,最需要首先解决的重要理论环节。随着研究的深入,儿童文学理论进入了五、六十年代传统理论的盲区——儿童观研究。“儿童观——儿童文学的原点”这一命题〔14〕与“儿童文学是文学”一起成为新时期儿童文学的两大理论生长点。这两个命题从文学性与儿童性两个决定性方向为新时期儿童文学理论的起飞提供了推动力。
耐人寻味的是,新时期出现的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驼峰与五四时期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它们都与西方(包括日本)的影响有密切关联。但是,比较而言,新时期儿童文学理论对西方学术文化的吸收、借鉴,缺少五四时期的清醒意识与全方位感。这种历史的退化也许暗示出新时期儿童文学理论研究队伍素质的下降与知识结构的不合理欠缺,而这些问题从根本而言,主要是社会的而非个人的责任。
新时期儿童文学研究对西方理论的成功借鉴主要集中于儿童哲学与儿童心理学领域。卢梭的“重返自然”的儿童哲学思想,英国浪漫派诗人的儿童观,杜威的儿童中心主义教育哲学,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马斯洛的人本主义心理学等西方理论,经常伴随着有条件的批评而成为新时期儿童文学理论的立论依据。这些西方理论虽然有的已经历史悠久,但是,它们对中国儿童文学在儿童观问题思考方面的启蒙却具有崭新的意义。当然,也曾出现过“儿童的审美能力处于低水平”,儿童“还处在一种前审美的阶段”之类以成人为本位来否定或轻视儿童的少数理论话语,不过,从整体上看,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界的儿童观水准依然取得了极大提高,而与此相伴随的是,儿童文学观也大大前进了一步。
然而,与五四时期以周作人为代表的学者们对西方儿童哲学和儿童文学理论的全方位借鉴相比,新时期显然在借鉴西方儿童文学理论方面远不如人意。据我的统计,至今为止,翻译介绍的外国儿童文学研究书籍仅有日本学者上笙一郎的《儿童文学引论》、日本儿童文学学会编著的《世界儿童文学概论》,另有一本《俄苏作家论儿童文学》则是由中国译者编辑的论文集。这种窘况与新时期成人文学对西方理论的翻译介绍相比,难免令人流汗。中国儿童文学研究队伍基本处于只能依靠翻译来了解西方理论的状况,有机会接触并有能力阅读消化西方理论原著的研究者不过寥寥数人。由于借鉴途径的闭塞,新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常常是自说自话。
有的研究者企图通过借鉴来提高儿童文学理论的水准,但是,面向西方儿童文学理论的道路不通,只得另寻出路,转向西方成人文学理论。毫无疑问,西方成人文学理论中适合儿童文学的部分应该大力引进,(事实上,有的研究者在接受美学理论启发下进行的儿童文学读者论研究便比较成功。)但是,离开儿童文学的主体立场,而投靠西方成人文学理论,却时时会落入陷井。比如某些理论话语就曾在追求诗化、哲理、象征以及淡化性格等方面出现过迷误。而偏离儿童文学本体,在价值观上的最大借鉴错位出现于对故事(情节)的价值评判上面。80年代中期发出的淡化故事(情节)的局部理论呼声,至90年代初期,在个别研究者那里已经恶化成对故事(情节)价值的根本否定。众所周知,19世纪末至20世纪五十年代,西方文坛上掀起了影响广泛的现代主义思潮。以反传统为大旗的现代主义作家中,否定故事的不乏其人。然而,西方儿童文学创作和理论不为成人文学这种风潮所动,坚持并发扬了自己的故事传统。故事之于儿童文学具有本体意义。简而言之,故事是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思维方式,同时又是儿童读者的阅读思维方式。如果抽去故事,儿童文学作品便会颓然倒地,而儿童读者的眼前也将是一片黑暗。把现代主义文学否定故事(情节)的主张当作整个成人文学的金科玉律尚不足取,让其君临具有独自价值系统的儿童文学理论之上,更是一种理论上的颠覆和背叛。
新时期儿童文学理论面临着借鉴取向的再度选择。矫正已经出现的借鉴取向的错位,明确面向西方儿童文学理论的借鉴意识,尽快行动起来,通过准确选择,翻译出版西方儿童文学理论的经典著作,以此打通向西方儿童文学理论借鉴之路,是目前中国儿童文学理论面临的实际而重大课题之一。
四、未来设计:搭乘三驾马车
西方是世界儿童文学的发祥地,它的儿童文学历史悠久、传统深厚、水准很高。西方儿童文学的传播,促进了全球性的儿童文学发展。从中西方儿童文学的关系史而言,对西方儿童文学的每一次吸收、借鉴都或是催生了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或是提升了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具体观点的借鉴固然需要,不过研究方法的借鉴却尤为重要,尤为根本。我认为西方儿童文学理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路数。
1.以儿童哲学和儿童心理学为理论根基
儿童哲学和儿童心理学的理论价值在于为儿童文学解决儿童观的问题。儿童观是儿童文学的原点,有什么样的儿童观就有什么性质的儿童文学。如果考察西方儿童文学的历史,我们会清晰地看到儿童观的演变呈这样的趋势:传统基督教的原罪观—→英国哲学家、教育思想家约翰·洛克的“白板”说—→法国思想家卢梭“重返自然”的儿童观—→英国浪漫派诗人的“儿童是成人之父”的儿童观—→现代儿童观。儿童观的生成及其变化,总是在制约着儿童文学的性质,决定着儿童文学的发展方向。整个一部西方儿童文学史,就是在儿童观的操纵下发生着演变。
不能不承认,在儿童哲学和儿童心理学研究方面,西方一直走在世界的前面。正是越来越趋近儿童心灵堂奥的儿童观为儿童文学提供了科学的、坚实的理论根基。我们翻开在西方被誉为儿童文学研究者必读之名著的法国文学史家、比较文学学者波尔·阿扎尔的《书·儿童·成人》(1923年),不仅为博识多才的作者所具有的法国式睿智而折服,而且更为其洞悉儿童心灵,深解儿童生活本质的儿童观后面所蕴含的博大人格而感动。波尔·阿扎尔的具有丰富人格力量的儿童观生发出《书·儿童·成人》一书的生命气蕴。1981年由剑桥大学出版局出版的尼克拉斯·塔卡的《儿童与书籍》则通过心理学和文学这两个研究途径探究了儿童与儿童文学的关系。儿童文学研究与一般文学研究相比,有着更为显著的跨学科性质。活跃于儿童文学研究领域的塔卡,正是由于同时身为心理学学者,才以这部划时期的力作展示了儿童文学研究的新方法。就我所阅读过的西方儿童文学论著而言,除了上述两部著作,象与阿扎尔的《书·儿童·成人》一起被誉为西方儿童文学理论著作之双璧的利利安·史密斯的《儿童文学论》(1953年)、贝蒂娜·修丽曼的《儿童书籍的世界——三百年的历史》(1959年),都是基于科学而稳固的儿童观之上的满蕴着对儿童文学的真知灼见的研究著作。
2.以丰富的感性体验为先行
理论研究必须建立在通过阅读作品而获得的感性体验之上,从这个角度讲,由于儿童文学创作匮乏而导致感性体验贫弱的国度,在理论研究方面身患先天贫血症。五四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恰恰因为采取“拿来主义”,获得了对西方儿童文学的感性体验,才使理论立于较高的起点。感性体验的准确与丰富与否,很大程度地决定了儿童文学理论的水准高低。可以说西方发达的儿童文学创作,为其儿童文学理论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西方儿童文学理论尤为珍视对儿童文学名著的感性体验,其许多著作字里行间流溢着对名著的信赖之意。由于对感性体验的重视和感性体验的溢满而流的丰富状态,西方儿童文学理论便多有富于感性、诗情的随笔型著作,波尔·阿扎尔的《书·儿童·成人》便堪称这类研究的典范之作。在我的阅读感受里,有时恰恰是这种感性化的理论文字,更能一语道破儿童文学本质的天机,令人心悦诚服。
3.以切实的儿童读书状况为参照
在成人文学理论领域,研究者只须将自己的阅读感受升华为理论便可以了,但是,儿童文学的理论批评的形成过程则是另一番情形。儿童文学的本位读者是儿童,然而,儿童文学研究者却是成人,两者间的年龄和心理落差很容易使儿童欣赏的文学与成人研究者欣赏的文学并不完全契合。因此,儿童文学理论研究一方面要求研究者具有保持儿童心性和早年阅读体验这一素质,另一方面则要求研究者充分了解和把握儿童对儿童文学的现实需求样相,对儿童喜欢什么样的书,讨厌什么样的书心中有数,因为对于一部作品即使成人研究者给予再高的评价,但只要儿童读者不感兴趣,那么它作为儿童文学作品的价值便值得怀疑。可以说,是成人研究者的价值评判受制约于儿童读者的阅读态度。
西方儿童文学理论十分重视儿童读书的状况,并以此为参照,调整自己的理论判断准绳。在西方(包括日本)的理论著述中,我们常可以看到研究者对儿童读书现状所作的细致调查,在这些调查结果的基础上所形成的结论或理论主张几乎没有与儿童读者的根本需求发生龃龉之虞。西方完备的儿童图书馆各项服务,程序化的儿童图书出版与发行,都为儿童文学研究者提供了各种关于儿童读书状况的切实数据。日本学者鸟越信编著的《儿童自己选择的儿童图书》〔15〕一书,便是以在儿童读者中阅读流传25年以上作为选择作品篇目的尺度。这种以切实的儿童读书状况为参照的研究方法,避免了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的主观臆测,因而理论的客观性、正确性有了保障。
我把上述以儿童哲学、儿童心理学为根基,以感性体验为先行,以儿童读书状况为参照这三种研究方法比喻为拉着西方儿童文学理论这辆马车稳健飞奔的三匹骏马。我认为,中国儿童文学研究对西方理论的借鉴首先应该是对这种研究方法的借鉴。搭乘上这辆三驾马车,未来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将驰往光明而广阔的前路。
中国儿童文学研究对西方儿童文学理论的吸收和借鉴既已经积淀为一段历史,也正在形成新的现实要求。必须认识到,作为人文科学的文学理论的吸收和借鉴决不同于自然科学技术的引进,即中国儿童文学研究吸收和借鉴西方儿童文学理论,必须是保持自身主体性的一种能动行为,而绝不是盲目追求西方化。儿童文学是既具有广泛的世界性,也沾染民族特色的一种文学。虽然与五四时代相比,借鉴、移植的社会土壤条件有了极大改善,但是全盘西化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上,都是“东施效颦”之举。结论只能是,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发展必须借助于对西方儿童文学理论的吸收和借鉴,但是这种吸收和借鉴的根本目的在于提升自身的水准,形成自身的特色并进而实现对自身局限的超越。
注释:
〔1〕我国学术界普遍认为“童话”丛书的出版起于1909年, 但据日本学者新村彻对原始出版物所作的调查,应为1908年。参见拙文《“童话”词源考》,载《东北师大学报》1994年第2期。
〔2〕〔3〕周作人:《儿童的书》,见王泉根编《周作人与儿童文学》第53页,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1985年8月。
〔4〕〔5〕〔6〕周作人:《苦茶——周作人回想录》,第533、 539页,敦煌文艺出版社,1995年4月第2次印刷本。
〔7〕〔8〕见郑尔康、盛巽昌编:《郑振铎和儿童文学》,第34页,少年儿童出版社,1990年11月。
〔9〕赵景深:《研究童话的途径》, 见王泉根评选:《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第385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8月。
〔10〕〔11〕金燕玉:《中国童话史》,第271页,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1992年7月。
〔12〕周作人:《童话略论》,见王泉根编《周作人与儿童文学》第76页,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1985年8月。
〔13〕参见周晓:《儿童文学札记二题》,载《文艺报》1980年第6期;曹文轩:《儿童文学观念的更新》,载《儿童文学研究》第24辑。
〔14〕参见拙文:《儿童观——儿童文学的原点》(载1988年11月12日《文艺报》和《论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儿童观》(《东北师大学报》1988年第4期)。
〔15〕(日文版)创元社,1990年9月20日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