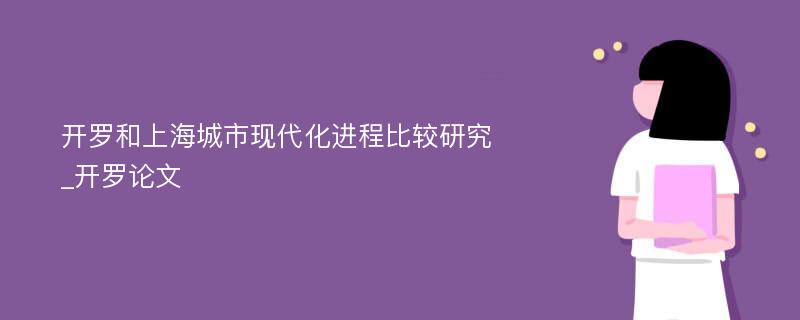
开罗、上海城市现代化进程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开罗论文,上海论文,现代化进程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2;C9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873(2003)05-0052-04
作为世界文明古国的中国和埃及,其城市历史源远流长,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其城市发展水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随着1798年法国侵入埃及和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埃及与中国的历史开始由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过渡,其城市在西方文明的撞击下开始接受新文明的洗礼。
一
自969年后,开罗一直是埃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法蒂玛王朝时期成为世界商业中心,1046—1049年访问埃及的波斯旅行家纳赛·库斯特说:“我无法估计它的财富,我从未在任何别的地方看到像这里这样的繁荣。”(注:《剑桥非洲史》(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第1卷第3册,1988年,第16页。)阿尤比王朝时期,开罗成为穆斯林世界经济中心和中世纪亚非欧三大洲的大都会。据赵如适《诸蕃志》记载,开罗“市肆喧哗、金银绫绵之类种种萃聚、工匠技术咸精其能。”(注:沈福伟:《中国与非洲——中非关系二千年》,中华书局,1990年,第250页。)马木路克时期,开罗规模“比巴黎大6倍”,(注:何芳川主编:《非洲通史·古代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17页。)“拥有35个主要市场和2万个商店”。(注:Malia Ruthen,Cairo Time—Life Book,B.V,1980,P.43.)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形容开罗“地区辽阔、物产丰饶、商旅辐辏、房舍栉比、而且极其富丽。”(注:沈福伟:《中国与非洲——中非关系二千年》,第248页。)
上海地踞长江口,内联腹地,外通四洋五海。早在唐天宝年间就开海贸易。元至元14年(1277)设立市舶司时,已是“蕃商云集”,“有市舶、有榷场、有酒肆、有军隘、儒孰、佛官、似馆。”(注:刘惠吾:《上海近代史》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1页。)清嘉庆年间,上海“闽广辽沈之货,鳞萃羽集,远及西洋暹罗之舟岁亦间至,地大物博,号称烦剧,诚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也。”(注:嘉庆朝《上海县志·序》。)
两地经济虽然繁荣,但开罗在1798年被拿破仑征服之前,上海在1840年开埠之前,其经济模式仍属传统的商业和手工业。市民以职业划分,往往集中在同一地段,如开罗有皮匠胡同、木匠胡同、裁缝胡同……,上海有豆市街、花衣街、咸瓜街……。各行业都有行会,其职责是解决内部纠纷,规定产品价格和劳动报酬等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开罗和上海的大小商人都有相当程度的增长。但在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中,他们的力量还很弱小。埃及和中国被纳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后,外商纷至沓来。在与外商贸易的过程中,一些资本主义的商业经营方式、经营手段、会计核算、雇佣制度等等纷纷引进。开罗“从事各行各业的行东,为行事方便,必须领取执照”,(注:穆罕默德·艾尼斯:《埃及近代简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33页。)“对所有私人财产进行登记,……根据登记的财产调整应缴捐税的数额。”(注:艾周昌:《非洲通史·近代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35页。)上海钱庄开始介入国际金融业务,到1895年前后,“南北二市每日银票往来何止千百万数”。(注:唐振常:《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41页。)不仅如此,上海钱庄还介入了有价证券交易及金银、期货等投机买卖。这些措施不仅使开罗和上海原有的地方性小规模的家庭商店、商行,转变为有较大规模的在大范围内运营的大商行、大公司,拥有了数十万、数百万资本的新式商人集团,而且使这些城市率先出现了若干个新兴的商业类别和商业行业。1849年开罗第一家西式旅馆——撒费尔德旅馆(Shepheard Hotel)建成并开放,希腊式、德国式啤酒店出现;大量面包店、西服店、咖啡屋等在上海租界经营。这些新兴的商业行业具有现代化的性质,把开罗和上海纳入现代商业网络之中。
新兴的商业贸易的发展带来了众多先进的生产技术,开罗和上海出现了交通运输、保险、通讯、现代工业、城市市政建设等新兴经济部门,从而使开罗和上海作为本国中心市场的作用突出。开罗成为埃及乃至中东地区的商贸中心,城市人口大幅增长,相当于埃及其他城市人口的总和,其人口从18世纪末的30万上升为1947年的200万。(注:Mattei Dogan John D Kasarda,The Metropolis Era Mega-cities,Volume2,P.236.)从1853年起,上海取代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同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300多个港口有经济联系和贸易往来,其直接对外贸易额占中国外贸总值的一半以上。人口从1880年的100余万上升为1949年的500万。(注:唐振常:《上海史》,前言第9页。)
西方的城市建筑风格和理念改变了开罗和上海的面貌,促进城市建设和功能向现代化发展。
首先,形成了新的市中心和商业街区。开罗的市容变化最早开始于拿破仑占领时期,拿破仑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强令加宽街道,拆除把各个市区隔开的胡同大门,拆毁一切有碍的民房和寺院。”(注:穆罕默德·艾尼斯:《埃及近代简史》,第32、33页。)开罗新的市中心和商业街区的形成则发生在伊斯梅尔在位期间(1863—1879),他不仅在艾兹拜基耶区和老开罗之间新建了两条林荫大道——克鲁贝特大街和穆罕默德·阿里大街,而且在开罗城的西边兴建了一个与旧开罗风格迥异的城市。新开罗仿效巴黎,按照笔直、布局、景观三原则而建。如在新的市中心建立大广场,市内修建笔直的大街和环行路等。为了加快新城市的发展,伊斯梅尔决定为那些能在18个月内修建一幢价值在3万法郎以上豪宅的人免税,这样就奠定了新区为富人居住区的格调。纵横交错的街道、绿草如茵的广场、鳞次栉比的宅区、富丽堂皇的宫苑出现在尼罗河东岸。各种各样的商业公司林立在街道两旁。10年间,新开罗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欧式建筑群。英国驻埃及总督克罗默(1883—1907年在职)对新开罗进一步扩建和实行欧化,出现了一大批法国、意大利等国式样的公园和建筑物,如著名的花园城(Garder City)、劳代岛(Roda Island)、伊斯梅利亚——陶非克依区(Ismailiya—Tawfikiyy)、金字塔区等等,开罗的城市范围急速膨胀。
上海自租界开辟后,工部局和公董局以西方城市的标准在租界内筑路,使街道一改传统城区局促狭窄的格式。到1865年租界内已有通衢大道13条。租界与旧县城的市容形成鲜明的对比,“租界马路四通,城内外道途狭隘;租界异常清洁,车不扬尘居之者几以为乐土,城内虽有清道局,然城河之水,秽气触鼻,僻静之区,坑厕接踵,较之租界,几有天壤之别。”(注:唐振常:《上海史》,第10页。)上海租界的面积1915年比1848年扩大了12倍。在上海租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城市,数十年间成为中国最大的城市,拥有中国建筑质量最好的高层大楼和最繁华的商业大街。外滩一带的欧式建筑群,南京路、四川北路等繁华大街初具规模。以“小洋楼”为代表的欧式风格与旧城厢的传统风格形成鲜明反差。
其次,改变了城市布局。随着新市中心在新开罗区和上海租界的形成,改变了中世纪开罗以法蒂玛王宫和爱资哈尔清真寺为中心,旧上海以官府衙门为中心的城市布局。外国商品和资本的大量输入,新型交通工具的引进,不仅进一步淡化了开罗和上海的“城”的功能,增加了“市”的功能,而且市区的面积大幅向外扩大。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开罗,向西、北、南三方发展,特别是北部坎米堡得区(Cmbodia)的开发成功,新的工业区和居住区在此形成。19世纪下半叶的上海向西沿着苏州河、向东沿着黄浦江延伸,逐渐形成沪东杨树浦、沪西曹家渡、浦东陆家嘴等工业区。开罗出现了“一个城市两个开罗”的结构,上海则形成“三家两方”(华界、公共租界、法租界;中国一方、外国一方)的格局。
第三,殖民者把开罗和上海视为他们进出口的总枢纽。一方面将大量廉价的工业品运进埃及和中国,通过开罗和上海等城市分销到其它城市和农村,占领当地市场。如上海进口的商品,只有20%在上海本地消费,其余的80%转销到内地;内地进口、出口货物,通过五大中介城市与上海发生联系,完成交易过程。(注:戴安钢:《港口城市腹地——上海与长江流域经济关系的历史考察》第5章,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另一方面对埃及和中国的原料进行疯狂掠夺,控制其原料市场,把越来越多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推向商品化。如1832年长维棉的种植,使19世纪中期埃及的出口产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25万亩棉地。(注:Malise Rathen,Cairo Time-Life Books,B.V,P.107.)与此同时,城市经济结构发生变化,手工业家庭作坊在资本主义商品的冲击下衰落,“这几年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开罗市场上充斥着欧洲商品,过去我们在街头经常看到的埃及本国货已经绝迹。”(注:穆罕默德·艾尼斯:《埃及近现代简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76页。)这样的情况同样也发生在上海,据记载,“松、太利在棉花梭布,较稻田倍蓰;虽(捐税)横暴,尚可支持。近日洋布大行,价才当梭布三分之一。吾村专以纺织为业,近闻已无纱可纺,松太布市,削减大半。”(注:刘惠吾:《上海近代史》(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85页。)
二
西方文明的传播在推动东方城市实现现代化的同时,也为它们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首先,外国人控制了开罗、上海的政治、经济大权,享有相对独立的行政权、司法权、开发权、征税权等等。同时,本国工人和外国工人从事同样工种的劳动,但得到的报酬却低得多。
其次,阻碍了埃及、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由于列强通过战争和不平等条约把开罗、上海纳入资本主义的体系之中,使其从一开始就处于边缘与依附地位。开罗、上海的民族资本企业除了面对国内传统势力的压制外,还要遭遇外国资本这个劲敌,不仅享受不到低税率等优惠条件,反而承担各种负担,结果使民族企业生产成本高,产品销路不畅,无力与外国商品竞争。如开罗现代企业大多规模小、资金少、技术力量薄弱且多集中在棉花加工、轧糖等部门。据统计,1945年埃及共有企业12,902千家,其中无雇佣劳动者的企业占51.2%。(注:高尔东诺夫:《埃及》,三联书店,1956年,第154页。)上海众多的民族企业也发展困难,就造船业而言,1868年中英修约谈判时,允许英商船厂所需的一切机器、物料进口免税;1881年,又与德国签订了德商船厂修船免税新章,从此各国“一切未能预言而实用修船各物”进口关税一律免除,(注: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57年,第310、394页。)遂使一大批华商造船厂纷纷破产。发昌、均昌造船厂曾辉煌一时,但由于得不到清政府保护,1900年发昌被迫以4万元廉价转让给耶松船厂,成为后者的一个车间。(注:《申报》1899年7月11日,转引自《学术月刊》,1965年第12期,第66页。)均昌机器厂被迫转产,改为经营小量纺织机件修配业务,才得以苟存(注:《上海之机制工业》,中华书局,1933年,第34页。)。
第二,加重了开罗、上海城市空间的不合理分布。20世纪初,在英国政府的鼓励下对开罗的开发达到顶点,外国公司纷纷到开罗寻找开发空间,城市出现了自流发展的印记,克罗默虽然制定了一套《总计划书》,但从未对土地开发利用实施过控制,结果供水、排水、电力系统等缺乏统一规划,拆建缺乏宏观控制,往往因一个小小疏漏,造成全区瘫痪。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在市政建设上各自为政,虽然在各自的辖区内对道路宽窄、桥梁建造等有一定规划,但作为一个整体,城市是局部有序,全局无序。如相邻交界的供水管道互不沟通,各区的水质、水压、水价五花八门;各区电压不一,或220伏,或110伏等等。这就为上海的改造和进一步的发展造成了严重障碍。大量外地贫困人口的涌进,又形成了大量贫民窟和临时棚户,使城市布局的不合理现象进一步加重。
三
埃及和中国的城市现代化展现了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发展特点。
第一,开罗和上海城市现代化的进程被打上了殖民地性质的烙印。开罗和上海的经济命脉始终操纵在外国殖民者手中,其经济以“外向型”经济为主,表现在经营倾向上,外资的半数以上用于进出口和与其相关的运输、银行等事业,工矿企业的投资却很少。同时开罗和上海的城市现代化的程度和进度也受到外资的制约。如伊斯梅尔时期由于得到了外国大量贷款,使开罗的改建工作顺利进行,仅用了10年的时间就在尼罗河畔建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同样,上海在短短的时间内取代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与外国资本主义的投资紧密相连。据统计,到抗日战争前,除东三省外,外国资本主义对华进出口贸易和商业总额的81.2%,银行投资的79.2%,均集中在上海。这些投资迅速转化为垄断开罗和上海的经济力量,并以此控制埃及和中国的经济命脉。
第二,开罗和上海的城市现代化的过程是畸形发展的过程。开罗、上海的城市现代化是以商贸为主,是外部力量作用的结果。帝国主义在商业掠夺和开办大批现代企业的基础上,通过开罗、上海等大城市把埃及、中国的广大城镇与乡村卷入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从自然经济形态中分离出来的大量劳动力,形成了一股庞大的失业大军,造成了开罗、上海城市人口过剩的畸形结构。
第三,开罗和上海的现代化是被动的、突进的,是在其国民缺乏现代化意识的背景下开始的。无论是开罗、上海的官僚贵族还是平民百姓,对西方文明都经历了由拒绝到接受的过程。开罗的两次起义为其冲突的表现,而随后大批埃及官僚、贵族、富商等建立西式别墅,创办新式学校、医院、着西装、看歌剧、说英语等则为接受的表征。在上海当电灯在租界内出现时,“其初,国人闻者,以为奇事,一时谣诼纷传,谓为将遭雷殛,人心汹汹,不可抑置”。(注:唐振常:《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53页。)随着时间的推移,电灯在上海市民的心中从惊恐的怪物变成了令人羡慕的夜明珠,时人称为“赛月亮”,于是争而仿效,最终电灯普及,成为上海市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必需品。以上这些过程,可视为反映市民文化心理状态现代化过程的缩影。
第四,开罗、上海现代化的过程具有外发性和殖民性的特点。由于这些大城市现代化进程与农村脱节,因而它们的发展状况并不能反映两国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它既不能把埃及、中国的农业从封建的落后状态中解脱出来,也不可能在经济、文化等方面与西方的城市展开公平的竞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