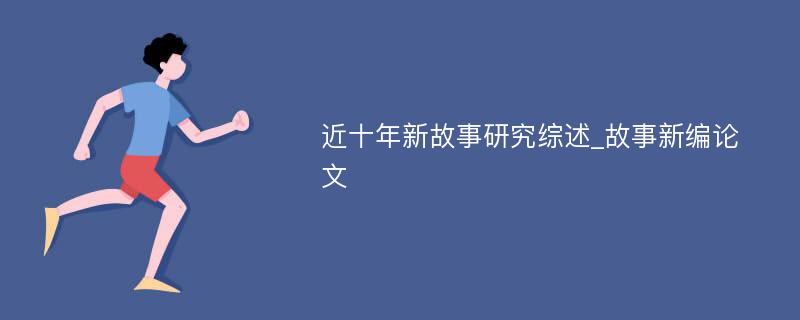
近十年《故事新编》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编论文,近十年论文,故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共时性的角度上考察,近十年来的《故事新编》研究相对于《呐喊》、《彷徨》的研究可以明显地见出滞后性、歧义性与非系统性的缺失与局限。[1]但在历时性的角度上,近十年的《故事新编》研究也不断有深化和发展,取得一大批重大研究成果。1993年吴颖和吴二持的《重评几十年来〈故事新编〉论争双方的主要论点》[2]对五十多年来的《故事新编》研究作了系统地历史回顾,显示出研究者对以往研究自觉地总结,也代表了研究界一种总体的自觉倾向。而进入新世纪以后,又以郑家建的《被照亮的世界—〈故事新编〉诗学研究》[3]、姜振昌的《〈故事新编〉与中国新历史小说》[4]、陈方竞的《对〈故事新编〉研究历史及发展的再认识》[5]为标志,显示《故事新编》的研究在新世纪走向新的高峰。在这些新时期《故事新编》研究历史上的标志性成果所划分的区间内,对种种特色各异的成果的检点与梳理,能够在总体上显现出以往研究的特点,并启示着未来研究的发展趋向。
第一个五年:在整合中深化发展
在新世纪《故事新编》研究高峰迭起之前,1995——2000年之间的第一个五年(本文在论述中也对这个时间段以前所出现的成果有所涉及),《故事新编》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众多研究者在一个分散的扇形平面上对各自研究方向的不断探索以及对所取得成果的整合。众所周知,鲁迅小说创作最大的特征在于“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6],而《故事新编》无疑在这两个方面进行了更为卓越而大胆的探索。研究者也首先在这两个领域中进行《故事新编》的解读和把握。
一、许多研究者试图从总体意蕴上对《故事新编》进行解读与把握。薛毅在《论〈故事新编〉的寓言性》[7]中发现,整个《故事新编》其实是写出了文明的“缘起”、“以致衰亡”的寓言。这是处于文明末世时代的鲁迅重新审视文明缘起时代的特点,从“缘起”中看到“衰亡”的必然,其文本的叙述着重指向了文明的末日和精神的解体与颓败:神和超人英雄消亡,“脊梁”们困顿不堪,没有意义或意义最终异化,哲人们没有任何救世或自救的能力,剩下的是“女娲氏之肠”的小东西们……《故事新编》都结束在小东西们的喧闹和卑琐行为上,理想精神的解体与小东西们鱼活伶俐,如鱼得水相连接。徐麟的《无治主义·油滑·杂文——鲁迅研究札记》[8]认为,《故事新编》中的“油滑”非常真切地表明了鲁迅在与历史的关系中,最后所站取的位置和态度,而这也正是他在杂文中,面对现实所站取的位置和态度。这就是鲁迅式的“无治主义”态度。这种由于正面价值的无法实现和意义的丧失而产生的生命虚无感正是鲁迅“无治主义”的根源。鲁迅以消解自身的方式,实现了中国现代启蒙主义最有深度也最艰难,最琐碎也最伟大的推进——向日常话语批判的推进。钱理群的《〈故事新编〉解说》[9]在对作品进行细读的基础上,以其艺术感觉的精微也别具特色。他认为:一、鲁迅对中国传统中的神话英雄与圣贤人物进行了重新审视,将他们还原于常人的本相,揭示了他们真实的矛盾与痛苦,对“神圣之物(人)”的这种反思(还原),显示了鲁迅思想的彻底;二、《故事新编》是鲁迅在小说艺术上的新探索,是他突破《呐喊》、《彷徨》小说模式的自觉尝试,但同时这种实验性也决定了其在艺术上的某些不成熟性;三、《故事新编》在总体风格上是在鲁迅固有的悲凉之中显示出从未有过的从容与洒脱,这表明鲁迅在思想与艺术上都达到了超越的境界。汪跃华的《试论〈故事新编〉人物的喜剧性》[10]在《故事新编》喜剧艺术风格体现出悲剧意蕴这一点上与钱理群持有相近似的观点,认为《故事新编》作为鲁迅后期创作心理的反映,承袭着《呐喊》、《彷徨》时期以来一贯的忧愤深广和对现实的强烈批判精神。《故事新编》中各类人物在鲁迅特有的否定式思维方式下,其喜剧性风格带上了复杂而深潜的悲剧色彩,体现了鲁迅在塑造人物上的主观个性化把握。秦弓在《〈故事新编〉解读》[11]中认为:《故事新编》描写古代题材,一则着眼于历史精神的澄清,二则旨在刻画“中国的脊梁”。在创作方法上,鲁迅以其深厚的造诣与创新的精神,继承并发展了中国古代喜剧传统,于历史小说中时有古今错杂的神来之笔,体式、语调、风格也呈现出多种风姿。
从对古老文化的批判与扬弃的角度解读《故事新编》,也是把握其深层内蕴的重要切入点。倪玉联的《对古老文化思想的深刻反思——〈故事新编〉本体意义新探》[12]发现,人类摇篮时期的文化思想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演变成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这种精神以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和墨家思想为其主要组成部分,《故事新编》主要是鲁迅对这几种思想的选择和超越。高远东在《鲁迅与墨子的思想联系》[13]中认为,《故事新编》在鲁迅以往人所熟知的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之“吃人”的定性和立论中,崛起了一种作为其批判“国民劣根性”主题之正题的所谓“中国的脊梁”的墨家英雄。鲁迅精神上接近墨子,对墨家思想意义的理解是在其一向关注的“立人”和“立国”的逻辑范围内进行的;对墨家价值的肯定,是在其对儒家和道家思想人物的批判中对照性地确立的。钱振纲在《对儒、道、墨三家“显学”的扬弃——从文化角度解读鲁迅后期五篇历史小说》[14]中认为鲁迅以现代知识分子的眼光,弃儒、道而扬墨,以反传统的态度重估了传统文化的观点也与高远东的观点有共通之处。另外,高旭东和聂廷生的《鲁迅与墨子》[15]也较具代表性。
从鲁迅这一创作主体的心理流动和人生体验的角度来挖掘《故事新编》的深层意蕴也是研究者关注的重要方面。皇甫积庆在《历时创作中的变异与持恒——〈故事新编〉创作心理解读》[16]中发现,在《故事新编》这一跨时漫长的分阶段创作中,一方面,由于三个完全不同时空的创作,《故事新编》有明显的阶段性变异;另一方面,由于主体创作时一定程度的心理注意,《故事新编》同时又有着持恒、同一的特点,这种既变异又持恒的特点,表现在鲁迅在创作《故事新编》的三个不同时间段内所体现出的创作心理的各个方面,其中包括创作欲求、创作心境、审美趣味及风格等等。例如,鲁迅在《故事新编》中的创作欲求,由于三个阶段的文化及生存环境的变化,出现了文化诠释——文化解脱——文化批判的变异,但纵观这八篇作品,这种变异的心理欲求后面又有不变的一面,即对身边人生、周围环境黑暗面的迅速反响与抗争,以及鲁迅对创作力的自我开拓和实现。李怡的《鲁迅人生体验中的〈故事新编〉》[17]根据传统研究中对《故事新编》的三段式分组方式(即《补天》、《铸剑》、《奔月》与《非攻》、《理水》以及《采薇》、《出关》、《起死》各为一组),认为这其实正显示了鲁迅不同人生体验的积淀过程,具体表现为:走向主观——返回“现实”——重写“元典”的积淀过程。并且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对鲁迅的三个阶段的创作心境进行解读后发现,鲁迅的创作心境中本我(情绪)、自我(感情)、超我(理智)形成一种自我肯定与自我否定相矛盾的循环往复的心理流向。但这样循环不已的矛盾不会导致内在的分裂,而是强化着作品内部的张力,强化着这种悲喜剧相交织的复杂的人生体验,这就是作品的成功之处。
二、对《故事新编》艺术形式的探索也是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吴秀明在《论〈故事新编〉在历史文学类型学上的开拓意义》[18]中认为,鲁迅在作品中不拘一格地借鉴传统和现代的一切艺术手法,并将它们熔于一炉,造成了一种异于传统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新类型,打破传统经典范式古今界限森然有序的艺术观念,创造了古今杂陈、幻实相映,并有意夸大了“反差”的新形态,让历史和现实都展现在同一个理想的时间、同一个理想的平面上,从而实现了对传统的历史文学类型作了富有意味的丰富和超越。黄佳岩的《迥然相异的形态:论〈故事新编〉独特艺术风格及文体界定》[19]认为,作品将象征主义艺术方法、杂文艺术方法、喜剧艺术方法等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鲁迅特有的动态艺术思维方法。因此,《故事新编》是一部新型历史小说。另外,王立英的《论〈故事新编〉的艺术形态》[20]、段建昆的《〈故事新编〉独创风格简论》[21]也是努力探索《故事新编》艺术特色的成果。
将《故事新编》的整体风格判定为表现主义是这一时期的引人注目的成果,主要以严家炎的《鲁迅与表现主义:兼论〈故事新编〉的艺术特征》[22]和徐言行的《论〈故事新编〉的表现主义风格》[23]为代表。严家炎认为,《故事新编》的主要艺术特征,如在“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中引进某些现代内容和现代细节,以古和今的强烈反差造成滑稽和“间离”效果;部分作品所显示出的情节内容的荒诞性;以及借古代的故事将作者特定的情感、心境、意趣加以外化和折射都显示出与表现主义的吻合。徐言行则认为,《故事新编》中的鲁迅针砭时弊,坚持文明批判的寓言化的思维呈现方式和主题,以及艺术方法上的间离效果、怪诞形象与情境、陌生化抽象化等等都显示出与表现主义的共通。《故事新编》的风格可以说是在表面玩世不恭的“油滑”中渗透着内在的焦虑与愤激,并寄寓着对现实冷峻的洞见。因此,这部小说的近乎后现代式的游戏笔调中其实埋藏着深刻的现代性情节——对理想的执著和对理性价值的确认。这也正是表现主义作家在反叛传统时所谨守的立场。
鲁迅深受古典文学的浸染,在艺术方法上也多有取法。彭波的《从〈理水〉看鲁迅对〈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的继承与发展》[24]即是这一时期有益的尝试。经过详尽而贴切的比较,作者认为,无论在“秉持公心,指摘时弊”的讽刺内容的思想性和真实性方面、“无一贬词,情伪毕露”的讽刺态度的主观性与客观性方面、以及“戚而能谐,婉而多讽”的讽刺艺术风格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方面,都可以看到鲁迅天才地继承和发展了《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使自己成为吴敬梓之后的又一位讽刺文学大师。
三、将鲁迅及《故事新编》同其他作家与作品进行比较,也是研究者深入理解鲁迅及《故事新编》的重要视角。钱理群的《鲁迅小说的“复仇”主题——从〈孤独者〉到〈铸剑〉》[25]以及周海波的《英雄的无奈和无奈的英雄——关于〈奔月〉与〈铸剑〉的重新解读》[26]侧重于鲁迅作品内部的比较。钱理群认为,鲁迅对复仇与死亡进行了独特的思考:虽然其感情上无疑是倾心于复仇的,但鲁迅仍然以他犀利的怀疑的眼光,将复仇面对无物之阵必然的失败、无效、无意义展示给人们看。周海波从一个体味着挫折与失败的文化英雄的角度观照鲁迅《故事新编》写作的创作思想和人生哲学思想,认为“鲁迅站立于远离现代文明的‘乡村中国’的土地上,以悲悯的目光注视着人生,并感受了人生的无常。他试图寻找中国现代的精神界之战士,却看到了无奈中的英雄和英雄的无奈。”
鲁迅与施蛰存、郭沫若的历史小说的比较也较引人注目。王骏骥的《论鲁迅、郭沫若历史小说的文化底蕴》[27]、毛晓平的《〈故事新编〉与〈将军底头〉:鲁迅与施蛰存的历史小说比较》[28]、何希凡的《现代文化创造者忧思和豪兴的重奏:鲁迅〈补天〉和郭沫若〈女神之再生〉的情感内涵比较》[29]是此一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文章。这些文章在对鲁迅和《故事新编》与其比较对象的具体比较中肯定了鲁迅与其对应作家的共同之处,但更侧重两者之间的差异,从而显示出《故事新编》的深层的意蕴。例如,王骏骥认为,在鲁迅和郭沫若看来,传统文化和现实生活确实是可以贯通的,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但是鲁迅对历史的态度是严厉的,表现了深刻的批判性,郭沫若的态度要显得自然温和。因此,鲁迅与郭沫若在出于现实需要对传统文化的重塑和改造中,鲁迅强调尊重历史要服从于改造现实,郭沫若对历史与传统文化则是继承多于批判的。毛晓平认为,鲁迅、施蛰存的历史小说的共同特色是体现于历史小说中的现代意识,但鲁迅侧重的是对现实社会、文化的批判,施蛰存侧重的是现代心理分析等艺术技巧的探索与展示。何希凡认为,《补天》和《女神之再生》题材相同,外在风貌相似,但情感内涵和终极旨趣迥异。主要表现在:1、作品表现实际不同;2、表现实际的不同反映出两位作家有着不同的创作关怀;3、以上两方面不同深层次蕴含着两位作家不同的人生经历和社会文化感受。两位作家反映在创作中的不同精神特征和文化心态也正是整个中国处于新旧文化交替期的两类现代知识分子的典型精神特征和文化心态。
《故事新编》与外国文学的比较以葛涛的《有意味的形式——论〈故事新编〉与〈神曲·天堂篇〉》[30]为代表。作者认为,《故事新编》与《神曲·天堂篇》两部作品的结构都是“有意味的形式”。并且在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的基础上,发现鲁迅投身文艺运动是以“打倒吃人的礼教”为旗帜的,鲁迅毕生坚持这一原则,始终保持这一本色,所以在晚年没有像但丁、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理那样陷入宗教的神秘情绪中。鲁迅用“油滑”手法穿透“三皇五帝的厚厚的旧尘”,但仍没有从痛苦中“分娩出宁静的愉悦”,所以未能获得精神上的“再生”,从而走到“天国”去。苦难深重的人间成为鲁迅最终的立足之点。
四、对《故事新编》单篇作品的解读也显现出异彩纷呈的特点。日本研究者丸尾常喜的《复仇与埋葬——关于鲁迅的〈铸剑〉》[31]从三个方面对《铸剑》进行了富有新意的解读:1、认为《铸剑》是在血与火的时代背景下催生而成的“复仇的文学”。2、从鲁迅精神史的角度入手,认为黑衣人与眉间尺的故事结晶于鲁迅的同归于尽的思想与许广平这位“同行者”的支持。3、通过对作品中出现的歌谣的分析认为,《铸剑》这一复仇剧实际上是“分裂”与“团圆”的故事。姚新勇的《鲁迅〈铸剑〉新探》[32]借助于佛洛伊德的有关视觉经验的心理分析学说,契入文本深层的无意识空间,发现正是无意识欲望的结构功能性机制生成并推动了文本的表层情节,构成了它的内在“逻辑”。眉间尺的为父报仇的心理也是一种典型的前俄底浦斯状态下的“混乱的、施虐的、进攻的和自我专注的”儿童心态。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他就不是为报仇而报仇,而是通过为父报仇而寻找自己的父,自己的精神之父。正是这种本我的利比多的驱动,形成《铸剑》文本的弑父与寻父双重母题的奇异结合。秦林芳的《奔月:中间物意识的历史寓言》[33]认为,当时鲁迅处在特定的“回忆”心境中,所以采用了历史题材,从而使《奔月》成了一个历史寓言。为了寄寓这种深刻的人生意识,鲁迅首先在《奔月》中对后羿的神话做了双重颠覆:即颠覆了神话的体裁,也颠覆了人物的性格。在鲁迅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奔月》最早以小说的方式展示了中间物意识,并且隐示了鲁迅未来思想发展方向。余志平、吕浩的《〈补天〉新论》[34]发现,《补天》无论从内容还是从艺术形式上都服从于通过“人神对立”表达人类异化这一总体构想。人对神的否定和消解实际上也就是人对人的根本价值的消解。女娲的悲剧也表现了鲁迅对英雄即“造物者”的悲剧命运的思考。《补天》反映了五四退潮以后,鲁迅感到的苦闷和压抑,甚至悲观与绝望,也更深切地反映出鲁迅体验到的人性的恶劣与“创造”的艰难。鲁迅一方面坚持韧的战斗,一方面又常被虚无所笼罩。《补天》正是这一方面的艺术体现。
第二个五年:向系统化体系化发展
进入新千年以后,《故事新编》的研究在前一阶段研究的基础上,明显的呈现出系统化的特点。并且开创出了许多学术创新点,不仅深化了《故事新编》的内部研究,也由此生发出以郑家建为代表的《故事新编》诗学研究和以姜振昌为代表的《故事新编》与新历史主义小说的比较等一批重要成果。这些成果不但在学科的理论探索方面取得较大突破,并且在对鲁迅《故事新编》创作风格的继承与发展这一点上也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郑家建的专著《被照亮的世界——〈故事新编〉诗学研究》借助于茵加登的对文学作品的分析理论和巴赫金的诗学理论对《故事新编》进行了富有创见的解读。1、作者认为,《故事新编》的语言形式最重要的特征为“戏拟”:一方面,它对所依据的旧文本(故事)的语言形式或当时现实生活中的某些语言形式进行虚拟(新编)。另一方面,在虚拟的过程中,他又渗透着鲁迅独特的荒诞的感受和分析意味。2、在创作思维层面,作者将《故事新编》的创作思维概括为“隐喻”。借助于闻一多的阐释,把关注的重心定位于“隐”与“喻”的双向互逆的关系状态分析方面。正是“隐喻”的创作思维及其内在张力,使得《故事新编》具有了诸多的独特艺术特征。3、通过对作品文本的考察,郑家建认为,如果用“历史小说”、“讽刺小说”的名称来概括《故事新编》的文体特征,会有捉襟见肘之感。因此,作者借助“四大奇书”等传统小说的命名方式,把《故事新编》的文体特征称为“奇书文体”。4、在《故事新编》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关系方面,作者认为值得重视的有以下几点:《故事新编》“叙事智慧”的“想象力”与中国古代神话、庄子之间的渊源关系;《故事新编》对中国古代小说和史传的叙事智慧的吸收;把“油滑”置入中国民间诙谐文化里加以关照等。5、在探讨《故事新编》与现代艺术技巧的关系时,郑家建侧重的是《故事新编》与现代电影蒙太奇、《故事新编》与现代美术等方面的联系。6、在细读基础上完成了“诗学”与《故事新编》的“内涵”释读之后,郑家建将重点放在了二者关系分析的“文化层面”——即“文化诗学”的探究。并且通过对中外“知觉形式”的比较,尤其是对“中国知觉”形式的形成过程、文化意义及演变走向的细致分析,从而有效而迅速地把《故事新编》“诗学研究”挪移到了对中国现代小说整体的文化诗学理论建构的范畴上来。
郑家建的研究得到了研究界的充分的关注,在多家刊物转载以外,许多研究者也提出了具体的意见与建议。严家炎认为:郑家建的文学研究工作永远不脱离审美直觉力、感悟力。正因为这样,《被照亮的世界——〈故事新编〉诗学研究》也就可能成为将《故事新编》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水平的标志。关于这本著作的不足,严家炎谈到:“我以为是在论述鲁迅边缘性思维的第六章。经过前五章对作品深入的论析,最后自然需要理论性的概括和抽象;但这种概括和抽象又不宜与前面的具体论析脱节,不宜离得过远,跃得过快。它需要一个中间环节,那就是对《故事新编》现代主义创作方法的探索。”[35]席扬认为:“他对中国现代小说进入诗学研究所必需的类型划分,尽管有明显的差强人意的地方,但其思路无疑是确当的。瞩目于他在这条路径上的不断前探,我们应当有大的期待。”[36]
二、新时期所出现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在形式和内容上与《故事新编》的高度相似性明显地标示出其对《故事新编》传统的承传。这一课题也引起了许多的研究者的瞩目,其中以姜振昌的《〈故事新编〉与中国新历史小说》最具代表性。姜振昌发现,正是“杂文”意识的渗透和介入,使《故事新编》的作意和文体,在整体上富于杂文意识,可称之为“杂文体的历史小说”。鲁迅以一种近乎“游戏”式的姿态,按照“自我”心理结构的轨迹,让最纯粹的历史生活与最不可思议的现实幻境在直叙与反讽、写实与夸张、认真与调侃、严肃与诙谐中融为一体,使作品散发着强烈的社会讽刺锋芒。其艺术内涵因“杂交”优势而显得丰富、深邃,并迥异于一切文学体裁类型。而新历史主义小说,以乱语讲史,俗眼看世,以调侃、戏说和玩世不恭的态度随意臧否人物,嬉笑怒骂皆成为小说整体艺术风貌,无疑比《故事新编》更加杂文化。但是,“新历史主义”小说过分放纵的虚构很可能是偏执和过极的探索,它们虽然在强调文本及叙事主体的作用方面提供了不少生动的范例,但却始终没有把握住观念与历史、文本与存在之间的关系,大都滑入了叙事游戏的空间,变成商业规则和大众消遣的“历史妄想症”的俘获物,最终消解的还是“历史主义”本身。
姜振昌以其对《故事新编》精神内核精确和深刻地分析,显现出鲁迅与新历史主义表面的契合与深层的分裂,表明《故事新编》提供的艺术经验具有典范性和恒久的生命力。并且姜振昌努力开拓的这个课题也成为近期《故事新编》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吴秀明、尹凡在《“故事新编”模式历史小说在当下的复活与发展》[37]中认为,20世纪90年代《故事新编》模式的历史小说在“新历史主义”的影响与催发下,奇迹般地出现了某种复活。在这种“新故事新编”作品中,形成了一个由夸张、怪诞、反讽、错置构成的文本空间,在一种抽象反常的状态下,历史与现实变成了一种“共时”的结构性存在;在这种结构性存在中,对历史和现实的观照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深度。而这,恰恰是古往今来一般的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作品所无法企及的。但是,“新故事新编”模式的历史小说创作优长赫然若揭,局限也显而易见。与鲁迅的写作相比,他们没有回忆可供咀嚼,没有包袱前来重压,人物被符码化了;作者的审美情感是冷静而低沉的,缺乏拥抱生活的热望,更多的是颓废、反讽和揶揄;此外,情节破碎,缺少宏大的历史感和对历史抗争的意识,导致了一些小说看似悲剧而又缺少悲剧的崇高美,看似反传统却最终遁入价值虚无主义的空虚。秦方奇的《〈故事新编〉与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叙事方式》[38]认为,《故事新编》所创造的跨越时空,杂陈古今的独特的历史叙事模式与“新历史主义”小说古今杂糅杂陈、寓庄于谐的历史叙事之间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契合。鲁迅和新历史主义小说家用反讽、戏仿、虚构荒诞情节等叙事策略,完成了对占统治地位的一切宏大叙事、既定权威的“解构”。
三、在郑家建所提倡的诗学研究以外,陈方竞在他的《对〈故事新编〉研究历史及发展的再认识》中主张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视角。陈方竞充分肯定了90年代着眼于《故事新编》的独创性而形成的人类学与民族学视角的研究,认为《故事新编》研究的发展趋向在于:从游离于鲁迅创作研究体系之外到进入而得到发展,再从这一研究体系中剥离出来,确立切合自身特点的研究基础与框架而获得深化。
新世纪对《故事新编》的研究,也有众多的成果是沿袭了前一阶段的研究方法与视角,深化推演而来的。但其超越之处在于大多数都在文本的解读与理论的阐释方面获得新意。
在对《故事新编》意蕴的挖掘方面,日本学者片山智行的《〈故事新编〉论》[39]较具特色,作者以细密而精微的解读,将各篇的意蕴在条分缕析中显现出来,结论多有独到之处。总结全篇,作者认为:鲁迅在《故事新编》中力图相当普遍地来观照中国的现实。“故事”在这种情况下发挥了有效的触媒作用,他歌颂了自古就有的改造世界的“实行”者,同时也对人的只是搬弄“名”的“虚妄”进行了批判。其中,他以历史上一直贯穿着的“实”(“行”)和“虚妄”(“名”、“马马虎虎”)这一对立的本原形态,再次提出了成为中国革命前提的“国民性”改造问题。江胜清的《论〈故事新编〉的荒诞感》[40]认为,导致《故事新编》研究众说纷纭、争论不休的根本原因在于作者对荒诞感自觉不自觉的追求。这种荒诞感主要是由小说题材本身的荒诞性和古今杂糅手法的运用形成的。这种追求,不仅创造了一个历史与现实交织、古人与今人同台、真实与虚幻相生的艺术境界,拓宽了小说的意蕴;而且产生一种强烈陌生化的艺术效果;同时还大大增强了小说的战斗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故事新编》整体上的完美和谐。刘延红的《历史的穿透力与感受力——论〈故事新编〉的文化批判和生命体验》[41]认为,鲁迅创作《故事新编》正是他的对历史的深刻认识和对生命的独特体验的外化,从而显示出其建立在独特生命体验基础上批判传统文化的深度和力度。从启蒙的理性层面对文化传统进行批判,从生命的非理性层面对人的生存的体验,使《故事新编》具有一种空前的历史深度和文化深度。
相对于《故事新编》意蕴的挖掘,对其艺术形式方面的探索是更有成绩的一个方面。鲍国华的《论〈故事新编〉的消解性叙述》[42]发现,《故事新编》标志着鲁迅在《呐喊》、《彷徨》之后新的艺术探索,他的关注点由现实转向历史与现实之间,寻求一种处理历史与现实关系的叙述方式。《故事新编》中消解性叙述的建立正是这一探索的结果。这一叙述方式消解了文本的历史性,也形成了对鲁迅过去小说创作范式意义的突破,体现出独特的美学价值。毛庆的《日常与悖论—〈故事新编〉中的时间意象》[43]认为,《故事新编》在整体和具体篇章的时间运用上分别采取了时代的延续、古今杂糅和季节、静止物等多种意象的方法,揭示出文本背后隐藏的虚无和荒诞性。孙刚的《文化寓言:〈故事新编〉文类研究》[44]认为,《故事新编》的叙事中包含三种异质文本:历史、现实和自传性文本。了解了它们间的辨证关系,就能解决一直争论的有关《故事新编》的“文类”的问题。这三种文本统一于文化的意义作用域,而叙事的类型(文类)—立义机制—则为“寓言”。《故事新编》以“寓言”的方式呈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世界。张雪莲的《反讽的意义——〈故事新编〉的现代性再评价》[45]认为,鲁迅是运用了反讽手法来敷陈历史。从而将历史、现实与个人的主观态度结合在一起,表现自己对历史和现实的态度。《故事新编》的表层意义在于颠覆历史显文本,深层意义便在于通过对历史显文本的颠覆,解构中国传统文化,解构人心中的历史,解构“由于岁月的迁移以及语言和习俗的变化,流传到我们的原来的事实真相已被虚伪的传说遮掩起来了”的历史。
用新的理论方法来观照《故事新编》的整体艺术风格也给研究带入了新的气象。廖久明的《〈故事新编〉的后现代主义特征》[46]认为,《故事新编》是将现实成分嵌入历史题材的后现代主义边缘文本。生活于极端贫穷落后的中国的鲁迅,写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故事新编》之所以具有后现代特征,其根源在于:(一)鲁迅与后现代主义者具有相似的历史观;(二)他们处于大致相同的生存困境中;(三)从共时的、艺术倾向的角度说,中国古代小说与后现代主义文本存在着相通的地方。这种大胆的尝试虽然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但许多研究者也相继提出了质疑。王亚娟在《游戏不等于后现代主义——与廖久明商榷》[47]中认为,鲁迅与后现代主义作家同是用“游戏”的方式对待文本,但二者所希望达到的目的和产生这种文本特征的原因却不同,其“游戏”并不必然是后现代主义的文本特征,因此中国学者在将西方思潮中的理论概念、论点、命题移植到中国文学的评论话语中时,必须慎重。刘岩的《共时的角度:鲁迅与后现代主义——兼与廖久明商榷》[48]认为从共时的角度来看,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边缘生存策略,鲁迅一方面重视中国民间边缘文本对正统宏大叙事的消解,并有所借鉴,另一方面却拒绝认同其代表的后现代主义生存策略,这决定了《故事新编》的文本“类似点”无缘成为后现代主义“特征”。作者更从历史体验和重估“叛逆性”传统两个方面,探讨了鲁迅与后现代主义者在生存策略上的分歧,试图为当下问题语境提供一个有价值的参照。针对前一时期严家炎与徐言行关于《故事新编》体现的表现主义特征的论述,高旭东、贾蕾在《鲁迅是表现主义者吗》[49]中也提出了不同意见。他们认为,虽然徐行言、程金诚对鲁迅前期进行了表现主义的解读,严家炎也认同《故事新编》是表现主义作品。然而不能将鲁迅描绘成一个表现主义者。鲁迅前期受到过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现实主义、存在主义等的影响,也间接地受到表现主义的影响。夸大其中任何一种主义用来指代鲁迅,都不合理。鲁迅二十年代后期介绍表现主义时,已在摆脱包括表现主义在内的现代主义的影响,所以不能将主要是后期创作《故事新编》都说成表现主义作品。
《故事新编》的比较研究仍然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戴清的《历史、时代、叙事——〈故事新编〉与〈豕蹄〉之比较》[50]认为,这两部历史小说集在创作时间与创作动机上存在着相似之处,选择历史作为对现实批判的切入角度表现了两位巨匠共同的文化选择;讽刺手法是这两本历史小说集共同的、基本的特征,尽管个别作品如《出关》与《柱下史入关》叙事话语、叙事视角、时序、“陌生化”效果的营造、人物语言表达方式等方面也存在着差异。林方瑜的《放逐之子的复仇之剑——从〈铸剑〉和〈鲜血梅花〉看两代先锋作家的艺术品格与主体精神》[51]发现,鲁迅和余华是两代颇具“先锋性”的历史小说家的代表,其主体精神及文化心态尽管各不相同,但对传统侠文化的“现代性”追求,却有相当的一致性。另外,陈方竞等的《〈故事新编〉文本构成的两重性及其意义——兼与茅盾、郭沫若的历史小说相比较》[52]、廖久明的《鲁迅〈故事新编〉与郭沫若的历史小说比较——对历史的不同态度》[53]也在鲁迅与其同时代作家的比较研究中较具特色。
标签:故事新编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文学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鲁迅论文; 叙事手法论文; 铸剑论文; 补天论文; 呐喊论文; 彷徨论文; 历史小说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