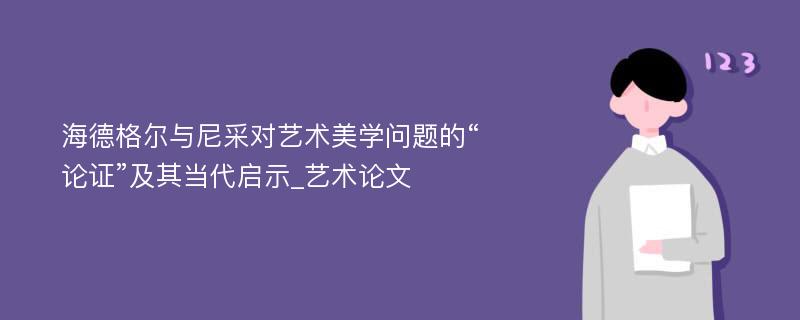
海德格尔与尼采在艺术审美问题上的“争辩”及其当代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德格尔论文,尼采论文,启示论文,当代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1936年起,海德格尔在追问存在的途中注意到了尼采在西方思想传统中的特殊地位;此后到1942年,他先后举行了六个以尼采为专题的讲座。最后有一个讲座因故未能举行,然后又写了四篇同一主题的论文。所有这些讲稿和论文,经过海德格尔本人整理后收入《尼采》(1961)一书,这方面的内容构成了海德格尔后期思想道路的一个重大课题,也是他对现代美学和艺术进行反思的一个焦点。
海德格尔把自己对尼采的阐发称为“争辩”。那么,海德格尔通过与尼采的“争辩”,赢获了哪些思想内容?把握了现代艺术审美的哪些重要问题?对我们今天又会带来什么启示呢?限于篇幅,本文只简要地勾勒出最主要的方面。
一、虚无主义:从“心理学”到“历史学”
海德格尔的时代,和尼采时代一样,延续着黑格尔所谓的“艺术的终结”。但这个终结表现在艺术对其根本存在的背离上,只是“表明艺术已经失去了它的趋向绝对者的力量,失去了它的绝对力量”(注:海德格尔:《尼采》上卷,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92页。),而不是其外在形态的彻底消失,所以并非就此再无艺术作品或艺术家出现。相反,艺术在现代社会的体制下,一方面继续为自己争取生存空间,另方面又在适应市场经济和产业化、世俗化的过程中发生着畸变。其趋势之一,即演变为令人喜欢和讨人喜爱的东西的审美表达,从而作为“享乐艺术”而在大众快感享受的领域里泛滥。
面对现代艺术的这种境况,海德格尔和尼采一样,都竭力要恢复和维护艺术的绝对力量,赋予它自我救赎和拯救西方文化精神的崇高使命。当然,两人的做法不同。尼采通过《悲剧的诞生》,既以希腊悲剧为参照系表达了对流行的“享乐艺术”的不满,又寄希望于当时瓦格纳以创新的歌剧而付诸实现的“总体艺术”。这意味着尼采期待以重塑古典传统的方式,用一种现代艺术形态克服另一种现代艺术形态。而当瓦格纳的歌剧在尼采心目中变得只剩下感情泛滥和激情体验,“总体艺术”的意义和本质不再是诗歌的原创性和语言作品的被赋形的真理,反而只注重表演上的舞台效果和煽情渲染时,尼采就把他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全部的现代艺术,仅以渗透了酒神精神的古典悲剧艺术为唯一的典范了。
由此导致了尼采在艺术问题上的个性化立场,这一立场不能简单断言为二元悖立,毋宁说是一种区别对待的分析。我们看到,他既尖刻地挖苦实际生活中流行的意大利歌剧,又大力推崇艺术的超越作用。他说过:“艺术是反对一切要否定生命的意志的唯一优越对抗力量,艺术是反基督的、反佛教的、尤其是反虚无主义的。”又说:“我们的宗教、道德和哲学乃是人类的颓废形式。——反运动:艺术。”(注:尼采:《强力意志》,第853、794节,第491、532节。“强力意志”(Der Wille zur Macht)国内译名不统一,或作“权力意志”。作为尼采遗著,其编辑出版除其胞妹外,还有多人经手,因而版本复杂,内容也不尽一致。为便于核对原文,笔者引文标明的是小节序号,所据德文版本是克罗纳出版社1930年起推出的《尼采全集》12卷本。中译文参考了周国平《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三联书店,1986年)和张念东、凌素心《权力意志》(商务印书馆,1996年),并有所校订。下同。) 同样,他既批评瓦格纳诉诸感官的音乐导致美学沦为一门“应用生理学”,又极力鼓吹感性的力量,并把感性推向身体性。他主张,“对身体的信仰比对心灵的信仰更为基本”,认为“根本点”是“从身体出发,并且把身体用作指导线索”,因为“身体是更为丰富、丰富得多的现象,它可以得到更为清晰的观察”,要求“确定对身体的信仰,胜过对精神的信仰”。(注:尼采:《强力意志》,第853、794节,第491、532节。“强力意志”(Der Wille zur Macht)国内译名不统一,或作“权力意志”。作为尼采遗著,其编辑出版除其胞妹外,还有多人经手,因而版本复杂,内容也不尽一致。为便于核对原文,笔者引文标明的是小节序号,所据德文版本是克罗纳出版社1930年起推出的《尼采全集》12卷本。中译文参考了周国平《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三联书店,1986年)和张念东、凌素心《权力意志》(商务印书馆,1996年),并有所校订。下同。)
尼采所有关于艺术的积极功能的论述,都需要从这个分析的角度去理解。他在肯定艺术的超越性时,有一个隐含的前提,那必须是符合他的古典理想、充溢着生命力的理想化艺术。然而,尼采所推崇的酒神精神和生命力,又如何同瓦格纳的感情泛滥和激情体验划清界线呢?尼采虽花费了不少力气反对瓦格纳,但恰恰在这一点上讲得不清楚。按照托马斯·曼的见证,正是在尼采(而不是别人)的影响下,审美主义变成了“一场灾难”,他参与其中的“审美时代”也沦为了“可怕的历史”。(注:托马斯·曼:《从我们的体验看尼采哲学》,载刘小枫等编译:《人类困境中的审美精神》,东方出版中心1994年版,第341页。) 这样的结果,对艺术审美和美学当然是加倍灾难性的,似乎是再也找不到任何出路了;对由存在的追问之路而转向艺术与诗之思的海德格尔同样是严重障碍:艺术审美还能给人带来什么有益的东西吗?还有可能像他所期待的,提供一个本真绽亮的开启吗?
从这个角度看,海德格尔同尼采的“争辩”,实质是在觉察到尼采的理论困境后,在肯定其基本方向的基础上,重新来为艺术审美奠定意义与价值。
海德格尔同意尼采对“总体艺术”的评价,看到了他为恢复艺术和绝对的内在联系所做的努力,以及这一意图的最终失败。他指出,这一综合性的“总体艺术”,“所要求的是作为音乐的艺术的支配地位,因而是纯粹感情状态的支配地位……其目的在于印象、效果、想产生作用和激动人心”。于是它向绝对者的回归,实际成了“向纯粹感情的完全消融”(注:《尼采》上卷,第93、95页。)。这样一种事与愿违的情况,实际也是从现代美学诞生起,就鲜明地镌刻其上的情感主义或感性主义的必然结果。其特征即将审美简单地赞同于感性、感情或感官,并在审美的名义下抬高甚或夸大它们的地位。海德格尔说过,以更纯粹的审美方式作用于人的感官的音乐竟能获得这种优先地位,根源在于“那种不断增长的对于艺术整体的美学基本态度;这就是根据单纯的感情状态对艺术整体的理解和评价,以及不断增长的对感情状态本身的粗俗化”(注:《尼采》上卷,第96页。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海德格尔觉察到,尼采本人最终也没逃脱现代美学的困境。他虽反对瓦格纳,但并未脱离感性主义的美学立场,既要令艺术承担起虚无主义的“反运动”的使命,又完全依靠心理学方法来把握虚无主义的本质。海德格尔发现,在《强力意志》一则题为“宇宙学价值的沦落”的笔记中,尼采把导致虚无主义的“登场”归之于“心理状态”,并具体区分为三种形式:一是因寻求一切事件的“意义”的受挫和对人生“目的”的沮丧;二是因发现“整体性”、“系统化”及“组织化”的占最高支配地位和统治形式的“统一性”的不存在而导致的“神性”的失落;三是对超感性的“真理”或“真实世界”(“上帝”即是其化身)的怀疑。事物“登场”涉及的“本源”其实关系到其本质,所以不能不加以辨正。
在对虚无主义作了包括词源学在内的充分研究后(《尼采》一书有专章讨论“西欧虚无主义”),海德格尔指出,尼采以心理学方法加以诊断的西方社会普遍的虚无主义心绪,实质是个历史的过程。他说:“我们不难认识到,上述虚无主义的三种形式保持着一种相互的内在联系,一道构成一种独特的运动,即历史。”(注:海德格尔:《尼采》下卷,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706—707页,着重号原有。) 所谓虚无主义“心理状态”的三种形式,恰好构成一个完整的历史进程:第一种,寻找事件的“意义”的受挫和对人的生成“目的”的失望,属于虚无主义成为可能的基本条件;第二种,发现“整体性”、“系统化”、“组织化”或“统一性”及“神性”的不存在,是虚无主义变为现实的开始;第三种,对超感性的“真理”或“真实世界”的怀疑,则是虚无主义必然的本质完成。这三个历史环节,又正好对应着西方哲学思想或形而上学的实际历史阶段。溯源而上,最后一种形式,相对于生成中的“虚假的”世界的“真实世界”的设定,对应的是柏拉图的形而上学及其后果;第二形式,相对应的是巴门尼德的“存在为一”的学说,此即是对存在者整体的一种“统一性”或抽象“神性”的设定;更早的第一形式,形成虚无主义的可能性的基本条件,暂时难以找到明确的对应者,不过能够肯定,那位于更原初的阶段。
很明显,海德格尔把尼采的心理学方法和视角,转换成历史学(广义)的了。一般而言,尼采并不赞成历史方法,涉及历史学时,也是从消解的角度谈的,毋宁说,他主张的是谱系学,即探究“来源”(Herkunft)和“出现”(Entstehung)的“效应史”(wirkliche Historie)。(注:参见福柯:《尼采·谱系学·历史学》,中译文载汪民安、陈永国编:《尼采的幽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对导致虚无主义登场的“心理状态”的三种形式的分析,本身就是谱系学方法的运用。但海德格尔追问存在的“返回步伐”及其开端之思,决定了他不同于尼采的历史学视域。这一视域,不仅仅把虚无主义的问题带出了主体心理情绪的范围,也进入了形而上学的历史起程。
海德格尔进而指出,虚无主义展开的历史过程,恰好是柏拉图主义奠定基础的形而上学日益统辖西方思想的历史。他说:“虚无主义、更原始更本质性地被经验和被把握的虚无主义,就会是那种形而上学的历史,这种历史驶向一种形而上学基本立场,而在这种形而上学基本立场中,虚无的本质不但不可能得到理解,而且不再可以被把握了。”而虚无主义的登场或出现,也从这一点重新获得了更加深刻的说明:“这个已经展开的关于虚无之本质的问题的悬缺,乃是西方形而上学必然沦于虚无主义的原因……这样,虚无主义或许就意味着:根本不思虚无的本质。”(注:《尼采》下卷,第692、699、699页。)
在海德格尔看来,尼采尽管声称反对虚无主义,却未真正思及其本质,仍然是一位表达正在发生的形而上学历史过程的虚无主义者。虚无,来自对存在者的否定和否决(包括对最高价值和生命体的否定和否决),是纯粹的思想产物,是抽象之物中最抽象的东西。虚无不存在,因而存在者不可能沉沦于虚无中,一切也不可能就此消解于虚无中。因此,“虚无主义”看来只是个幻觉。然而,如此的印象,恰好是未能把握住虚无主义的本质的结果。虚无主义的本质在于,正是在虚无主义的名义下,回避了对虚无问题的认真思考。人们用习惯已久的“非此即彼”的模式想问题,鉴于虚无绝不可能是存在者,就站在和存在者与存在对立的立场上,把它当成完全的空无所有。所以在历史中展示的虚无主义的完成,正好隐蔽了构成它本身的本质。由此也掩盖了“上帝已死”的真相和原因,掩盖了长久以来对生命体采取蔑弃态度的缘由。尼采的思想没有超出这一水平,所以他注意到了虚无主义的现象,却未能揭示其真正根源。
实际上,尼采谈论虚无主义的角度,所体现的乃是现代主体论的形而上学特征。按照更合乎学院正统的说法,形上性质的“宇宙学”和形下性质的“心理学”本来分属两个领域。但在尼采那里,所追问的“心理之物”(即生命体)受“强力意志”规定:“只要‘强力意志’构成一切存在者的基本特征,而关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的真理被叫做形而上学,那么,尼采的‘心理学’就完全与形而上学同义。”(注:《尼采》下卷,第692、699、699页。) 与此同时,正是在现代主体论中,“人成为存在者的尺度和中心”;“人是一切存在者的基础,以现代说法,就是一切对象化和可表象性的基础,即subiectum [一般主体]”。(注:《尼采》下卷,第692、699、699页。)虽然尼采一再反对为现代形而上学奠定基础的笛卡儿哲学,但并不反对后者把人设定为一般主体,而只是反对这方面做得还不够彻底和极致,他的“超人学说”就是由此提出的。
正因为这样,在克服虚无主义的途径上,海德格尔改变了尼采的方向。尼采主张用高扬生命力的艺术,来填补最高价值的虚空,重新为人生设定“目的”和注入“意义”,通过艺术来“组织”与“统一”起支配一切事件的最高统治形式,用审美的“身体性”来取代“神性”的位置,并把艺术审美世界当成唯一的“真实世界”,当成超越生活世界的最高“真理”。这是不难推导出来的逻辑结果,也是现代审美主义后来走上的路径。而对海德格尔而言,对虚无主义的克服或“反运动”,首先将是克服柏拉图主义形而上学的历史性转折,这也是拯救现代审美主义困境的一种可能性。
二、审美状态:身心统一和超越主客体二分
尼采把高扬生命力的重大使命托付给理想中的艺术。他说:“艺术,除了艺术别无它物!它是使生命成为可能的伟大手段,是求生的伟大诱因,是生命的伟大兴奋剂。”(注:《强力意志》,第853节。)关于艺术乃“生命的伟大兴奋剂”的说法,尼采在不同场合多次地提到过。他甚至留下了一份题为“艺术生理学”、包括十七个要点的笔记,尽管几乎看不到每点之间的嵌合可能或结构上的轮廓,但不同片断实际讨论的是同一件事,即作为对艺术的追问的美学。这种把艺术移交给“生理学”的做法,如同把虚无主义当作“心理状态”,对尼采而言是顺理成章的,体现了针对西方理性主义传统而发的感性主义倾向。在尼采那里,“生理学”和“心理学”一样,也是种形而上学,甚至可说是二位一体。
海德格尔后期也对艺术(包括诗)寄予厚望,艺术作品成为存在的召唤者和暂栖地,他同样在现代社会的体制下坚持艺术的自主性与自律性。但他不赞成“把艺术贬低到胃液作用的水平”,那丝毫无助于艺术对虚无主义的“反运动”,更不可能使艺术重新设定为绝对,保证艺术替历史性的此在筹划和建立尺度,为本真的敞亮提供开启。基于此,他突出了尼采的一个重要概念——“强力意志”,将一种更高的规定性和更本质性的联系带入艺术审美中。
海德格尔阐发说:“这种把艺术规定为生命的兴奋剂的做法无非是说:艺术乃是强力意志的一个形态。因为‘兴奋剂’是驱动者、提高者、自我超越者;它是强力的增加,因而是地地道道的强力,这就是说,它就是强力意志。”(注:《尼采》上卷,第82、104、105、104、108页。)他认为,“艺术是强力意志的形态”构成了尼采关于艺术的“总命题”,其他提法均服从于这一总命题。“强力意志”还和“虚无主义”、“重估一切价值”、“相同者的永恒循环”、“超人”共同构成了尼采形而上学的五大主标题。
与此同时,只要把艺术视为强力意志的最突出形态,也就能从“艺术生理学”看似相互抵触的众多规定中发现从艺术本身要素中得出来的统一性。这个统一性,海德格尔解释为“身—心统一体”:“从整体看来,这恰恰就是那个未被撕碎的、也撕不碎的身—心统一体,就是被设定为审美状态之领域的生命体,即:人类活生生的‘自然’”。(注:《尼采》上卷,第82、104、105、104、108页。)值得注意的是,海德格尔在这里强调了身与心的不可割裂的统一,并据此把尼采的“心理学”和“生理学”整合到了一块:“被看作纯粹心灵上的感情状态,应当归结于与相应的身体状态”;“首先要揭示出在人的身体—心灵自然(即人的活生生的自然)的本质中的那些状态”。(注:《尼采》上卷,第82、104、105、104、108页。)
无疑,不管尼采把自己的美学思考命名为“艺术生理学”或别的什么,其实仍和现代美学以人的感情状态来经验和规定艺术的主张一脉相承,只不过把保留着思辩性质、同理性相对的感性引向了更具体可感、由“心理—生理”合成的身体性。这也是尼采往往不说“审美状态”,而说“艺术家的”或“非艺术家的”状态的缘故。原因在于,前者仍可以是一种理性抽象,作为理论概念来讨论,甚至像叔本华那样,解释为“无欲静观”的“审美态度”——恰恰就在这样的规定中,“审美状态”中的审美因素被蒸馏干净了。
正是针对上述情况,尼采强调艺术家的状态是“陶醉”。他说:“艺术家不应该如其所是地观看什么,而应当观看得更丰富、更质朴、更强烈;为此,艺术家的生命就必须具有一种青春和春天,一种惯常的陶醉。”(注:《尼采》上卷,第82、104、105、104、108页。) 然而海德格尔坚持从身心一体观来看待艺术家的审美状态。他从尼采后期写的《偶像的黄昏》而不是早期的《悲剧的诞生》来阐释“陶醉”,所说的“陶醉”不再等于酒神祭式的狂欢与迷醉,而是在更广泛意义上身体性和情感性互相包容一体的此在。至于《悲剧的诞生》所涉及的酒神和日神的对立(这一对立的设置其实也属尼采区别对待的分析态度的表现),他以不是新提法(文化史家布克哈特和诗人荷尔德林都早有同样说法)而淡化了,并视为尼采未予克服、有待导出新问题的一种模糊性。
《偶像的黄昏》说:“陶醉的本质要素是力的提高感和丰富感”,海德格尔则申明,情感性和身体性都是此在的一种基本方式。“我们并非‘拥有’一个身体,而毋宁说,我们身体性地‘存在’。这样一种存在的本质包含着作为自我感受的感情。感情自始就把身体扣留和吸摄入我们的此在中了。”(注:《强力意志》,第800节。)不能说我们先“生活着”,然后装备着一个身体,这个身体另外还表现出情感。相反,生命、身体、情感,说的都是一回事。在这里,不能让身体事先被曲解为一个单纯的自然物体,也不能让感情事先被曲解为这个单纯的自然物体的派生物或附加物。他说:“在把陶醉说明为感情状态时,我们曾多次专门强调,我们不可把这种状态看作‘在’身体‘之中’或‘在’心灵‘之中’的一个现成之物,而是要把它看作一种对存在者整体的肉身性的、有心情的对待方式,一种本身规定着心情的对待方式。”(注:《尼采》上卷,第116、124、124、135页。)
尼采把美规定为产生快感的东西,但海德格尔指出,关键取决于对快感和产生快感者本身的概念理解。尼采说:“坚固、强大、结实的东西,它博大有力,安然静息,庇护着它的力量——它‘产生快感’,这也就是说,它与人们对自己的看法相吻合。”(注:《强力意志》,第852、803、852节。着重号原有。)海德格尔据此认为,这意味着“美是那个规定着我们以及我们的行为和能力的东西”;“因为通过美,我们最高地占有了我们的本质,这就是说,我们超越了我们自己”。(注:《尼采》上卷,第116、124、124、135页。)这样一种本质能力的丰富性中的超越自身的提升,就发生在陶醉中。他得出结论:
美是在陶醉中展开出来的。美本身是那个把我们置入陶醉感之中的东西。
从这种对美之本质的揭示出发,对陶醉、对基本审美状态的特性刻画就获得了一种更高的清晰性。……陶醉的情调乃是最高的和最适度的规定性意义上的一种心情。(注:《尼采》上卷,第116、124、124、135页。)
作为基本审美状态的陶醉,不再是片面地来自酒神的迷醉狂热(这是尼采给一般人留下的印象),甚至也不像瓦格纳歌剧中的激情恣肆。所谓生命的快感,或尼采所说的“生物学的快感”,实质成了心身同一的最高级和最适度的心情体验。不仅如此,陶醉还和美处在密不可分的关联中:陶醉既是美得以展开的前提,而美本身又是激发陶醉感的本原。这里所谓的美,当然不是什么外在的东西,而是我们在审美现象中据以判断其为美的那个“是”。
海德格尔的“陶醉”观,包含着更彻底地清除形而上学的主体性理论的筹划在内,他要让尼采从残存的形而上学思维模式中进一步脱身出来。他说得十分清楚:“作为感情状态的陶醉恰恰冲破了主体的主体性。由于拥有一种对美的感情,主体就超越了自身,也就是说,它不再是主观的,不再是一个主体了。另一方面,美不是一种单纯表象活动的现成对象。作为一种调音作用,美贯通并且调谐着人之状态。美突破那个被设置在远处、自为地站立着的‘客体’的范围,并且把后者带入与‘主体’的本质性的和原始性的归属状态之中。美不再是客观的,不再是一个客体。审美状态既不是某种主观的东西,也不是某种客观的东西。‘陶醉’和‘美’这两个美学基本词语具有相同的含义范围,指示着整个审美状态,以及在审美状态中开启自身并且贯通自身的东西。”(注:《尼采》上卷,第116、124、124、135页。)
三、艺术形式与“强力意志”
在艺术审美的领域,审美状态还必须有借以实现自己的基本方式——审美行为或审美活动,即艺术家的创作和艺术作品的接受。对尼采来说,它们无非是生命力的实行,因此强力意志一以贯之地发挥着本质的作用。这首先表现在艺术家的美的创造或更确切说美的“驯服”作用中。他说:“对艺术家来说,‘美’之所以是某种外在于任何等级秩序的东西,是因为在美中各种对立被驯服了,这乃是强力的最高标志,也就是超出对立之物的强力的最高标志”。(注:《强力意志》,第852、803、852节。着重号原有。)同样进行审美判断的活动也和“强力”密切相关:“是否以及在何处着手进行‘美的’判断,这是(一个个体或者一个民族的)力的问题。”(注:《强力意志》,第852、803、852节。着重号原有。)
但在海德格尔看来,审美行为中强力意志的作用有特定内涵,既非简单的“身—心”过程,也不是审美对象中各种对立因素的一律敉平。简要地说,它是对审美过程中照面之物的主要特征的“夸张”或突现,即通常所说的“理想化”。它涉及审美对象(注意这里的“审美对象”是现象学意义上的而不是对象化的)一系列特征(Gezüge)和结构(Gefüge),涉及艺术创作的赋形或格式化(Gestalt),实即一般美学所讨论的形式问题。
尼采只是简单地谈到艺术家只有在知道“形式生成”的情况下才能给予事物以价值,虽然他同样明白形式的重要性,但仍滞留在二元框架里,从与内容相对的角度,来讨论形式问题。而对海德格尔而言,形式从来就是存在者的到场或显现:“它是具有包围作用的界限和边界,它把某个存在者带入和置入它所是的东西之中,使得这个存在者站立于自身,此即形态。如此这般站立者乃是存在者自行显示而成的东西,即它的外观,通过这个外观并且在这个外观中,存在者走出来,表现出来,敞开自身,自我闪烁,并进入纯粹的闪现中。”(注:《尼采》上卷,第130、142、147页。)其结果,也就排除了把创作理解为主观行为、把形式理解为客观规律的传统思维模式——我们已不止一次提到过,海德格尔对这样一种对象化的二元论的主体性模式从来就是置疑的。
艺术形态的强力意志在审美行为中,不仅体现于审美对象的赋形,体现于这一赋形过程中对主要特征的夸张,还表现在对形式规律和创作法则的尊重和强调,它有力量和自信担当起这样的法则和尺度,在它们的限度之内进行自由的创造。“艺术状态是这样一些状态,它们本身服从尺度和法则的最高命令,把自身纳入超出它们的意志之中;当这种状态意愿超越自身,超出它们所是的东西,并且在这种主宰中维护自己时,它们才是它们本质上所是的东西。”“艺术不仅要受规则支配,必须遵守法则,而且更应该说,艺术本身就是立法,艺术只有作为这样一种立法才真正是艺术。不可穷尽的和有待创作的东西就是法则。”他特别强调,“那种把风格消融于单纯的感情奔腾中的艺术,从根本上误解了人们在发现法则时的不安;在艺术中,唯当法则为达到公开的作用而浸淫于形态之自由中时,这种法则的发现才能成为现实的”(注:《尼采》上卷,第130、142、147页。)一旦艺术的形式法则得到实现,艺术也就实现了其伟大的风格。
这一伟大风格,尼采也称为“古典风格”。但千万不能用流俗的眼光看待之,将其混同于文学史和艺术史上的古典主义,毋宁说,它是一种属于艺术的“古典性”。具体讲,就体现于被称为“伟大时代”的古希腊的艺术。对古希腊艺术的崇尚,在德国思想史和艺术哲学中由来已久,已成为一种文化传统,我们并不陌生,从赫尔德、歌德、席勒、温克尔曼到黑格尔,莫不如此,关键的区别只在于对古希腊艺术精神的领会。在尼采看来,希腊艺术的古典精神,或古典性,是平衡身体性的最好调节。作为现代审美文化的开拓者和缔造者,尼采面对的不仅是理性主义的长期统治和由此而来的虚无主义,也面对着审美主义或审美性本身的问题,他亲眼目睹感性的片面膨胀同样无济于事,并可能走向反面,瓦格纳的音乐艺术就是实例,因而他把古典性规定为对生命体的丰富生成的征服。他说,“最高的强力感集中在古典类型中”。(注:《强力意志》,第799节。)结果,安宁构成了强大灵魂的基础,古典风格也体现为宁静、简化、凝缩和集中,这恰是强力意志的展现。不了解尼采思想上述的两难处境,是不会理解强力意志何以又同古典性联系在一起的。
海德格尔在这一点上认同尼采的观点,照他的讲法,“古典性乃是一种从馈赠者和肯定者的丰富性而来的对存在的要求”(注:《尼采》上卷,第130、142、147页。)。他不允许希腊艺术的古典精神遭受以后的古典主义或人本主义的曲解。他指出,所谓古典性或伟大风格,是把生命的原始冲突及一种胜利的必然性根源突现出来,而绝非古典主义意义上的单纯、静穆、理性、完善。他还进而引申说,应该从此在的基本结构去理解古典的东西,说到底,那属于一种本初的自由、超越混沌中的极端对立的自由,也即对由原始的古朴性和原始的法则性的对立,而导致的对束缚性的自由把握和自由支配。“凡在对这种束缚的自由支配成为事件的自我构成的法则的地方,就有伟大的风格;凡有伟大风格的地方,具有纯粹的本质丰富性的艺术才是现实的。”(注:《尼采》上卷,第141、142、142页。)打个形象的比方,即既非不拘形相的癫狂,也非枷锁镣铐的囚禁,而是合着节拍的舞蹈或张弛有律的飞行。
海德格尔认为,正是审美形式或法则,在让伟大艺术得以实现的同时,也使尼采的“艺术生理学”或生理学美学发生了重大的倒转。在此过程中,艺术的本质要素,超越了原先所归结的“生理学的东西”。身体性被超越了,陶醉也被超越了,审美状态服从于自身形成的伟大风格的法则。“审美状态本身只有作为伟大的风格才真正是一种审美状态。所以,这种美学就在它自身范围内超越了自己。”(注:《尼采》上卷,第141、142、142页。)连关于艺术是生命最大“兴奋剂”的说法,都有了新的诠释:“‘兴奋剂’的意思是:把人们带入伟大风格的命令领域之中的东西。”(注:《尼采》上卷,第141、142、142页。)
通过海德格尔的“争辩”,尼采对叔本华艺术是“生命的入静”一说的颠倒,不再单纯是用刺激品来替代镇定物,从而变成了走向伟大的存在体验。当然,从动摇和颠覆西方理性主义的长期统治看,尼采的“艺术生理学”不失其积极的意义。但他继续将感情和理性、身体和精神割裂开来,把两者置于非此即彼的对立中,并在这种语境里确认感性的合法身份和重要价值,又难免导致新的局限性。关键恰恰在于,确认感性的真实度和重要性,不等于倒向另一极端,毫无保留地全盘加以肯定,和彻底排除同它相对的东西。接下来必须要走的一步,是从颠倒上升到转换。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形而上学之完成试图从形而上学本身出发,首先通过简单的颠倒来克服‘真实的’世界与‘虚假的’世界之间的区分。当然,这种颠倒不是一种单纯的机械的倒转,使得最低级的东西(即感性领域)达到最高级的东西(即超感性领域)的地位——这样做,两者连同它们的地位就还没有丝毫变化。这种颠倒是对最低级的感性领域的转换,把它转换到强力意志意义上的‘生命’中去。而超感性领域作为持存保障,就被转换入强力意志的本质结构之中。”(注:《尼采》下卷,第653页。)既不能像原先那样无视感性,也不是掉过头来只要感性而蔑弃超感性,相反感性或超感性,都须经过转换而进入更为本质性的结构之中。
尼采曾宣布他的信条是:“艺术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来的形而上活动。”(注:《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周国平译,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2页。)现在海德格尔已经将“生命”从生物学的身体变成了存在论的此在,“生命的形而上运动”也转换成了此在对存在的开启或澄明。现代的艺术和美学尽管因审美主义的困境在尼采同时及后来的“审美时代”曾再度陷入窘态,但此刻又从存在论哲学的高度重新获取了合法性。
四、启示:当年的“争辩”和当下的争论
海德格尔与尼采的“争辩”不仅仅是现代美学史上的一个事件,而且继续葆有当代的意义。今天重提这桩公案,正是有鉴于我们自己的语境。处在现代转型过程中的中国,随着市场经济而激发的物欲高涨,形形色色的“享乐艺术”正在逐渐形成的中产阶级人群里风行。有人认同这一趋势,从西方的消费文化研究者那里搬来了“日常生活审美化”(aestheticization of everyday life )加以表征和提倡,从而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但争论的双方都对何谓审美、何谓艺术等等重要前提及其内涵和外延不作任何分析与界定,唯一自明和公认的东西只是审美即感性。当年的“争辩”至少能够告诉当下的争论者,当审美告别了静观与思辩后,在感性问题(以及身体性)上已经历过哪些曲折与拓展。面对有关的历史内容和深刻反思,相信那些声称“审美当是人生之艺、人生之情、人生之趣、人生之福”的煽情词句,立即就会暴露出自己的浅薄和空乏。同样,人们也不必再为既不能将美学与生活和人生隔离开来、又不可无条件地接受时尚化的“审美”而感到进退两难,因为我们懂得了,美学和生活的联系就建立于审美方式上,而这一审美方式需要并必须作出规定。
事实再次证明,中国美学界患上了“哲学贫血症”。在争论中,大家着眼于从量的角度弄清所谓的“审美化”到底“化”到了什么程度,想证明问题的提出有无合理根性,却未曾想到过,按此逻辑,中国因有上亿人失学或是文盲,那么是否高等数学、天体物理学等高深科学都应该废弃?也有人从学科范围出发,议论文艺美学的边界要不要扩大到把文化也囊括进来,却不清楚,美学的理论取向从“自上而下”转为“自下而上”后,它的发展方向应当是艺术哲学,而不是心理学、生理学、人类学或文化学。后者也应加以研究和探讨,却不能取代美学或艺术哲学的存在。在艺术审美的诸多问题得到哲学高度上的充分反思之前,我敢断言,无法期待当下的这场争论会得出什么有效的结论。
海德格尔与尼采的“争辩”也启示我们,如果当下的争论打算从美学的审美范畴汲取理论的力量,那么决不限于康德。相反,后康德的美学或许更值得关注。当然,无论尼采或海德格尔,都只是美学史上的一个片断。但我们特别地提到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美学观,乃是因为迄今为止,仍有人将存在论美学与生存美学乃至生态美学混为一谈(注:关于这个问题,请参见拙著:《西方存在美学问题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尤其第十三章“存在还是生存:中国当代美学向何处去”。),所以很有必要一正视听,以免其本质的内涵继续受到遮蔽。
标签:艺术论文; 形而上学论文; 尼采论文; 海德格尔论文; 理性与感性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悲剧的诞生论文; 文化论文; 历史虚无主义论文; 生命本质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存在主义论文; 哲学家论文; 现象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