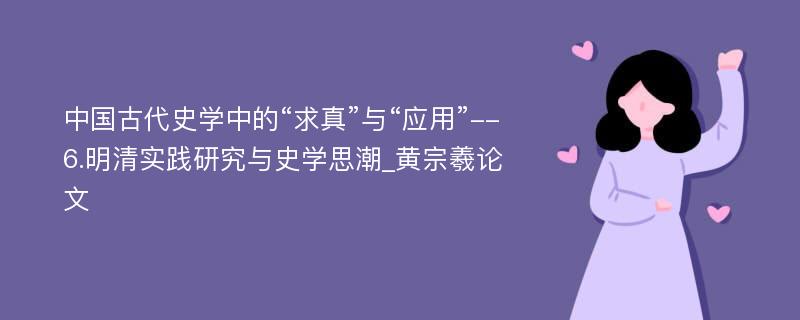
中国古代史学的“求真”与“致用”——6.实学思潮与明清之际的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实学论文,思潮论文,明清论文,中国古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明清之际是中国历史上“天崩地解”的大动荡时代。这一时期,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结构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在学术上,学者们立场鲜明地举起经世致用的旗帜,力反明末的空疏学风,在求真和致用方面达到了高度统一。
一、实学思潮的兴起
明末清初经世致用的史学宗旨与实学思潮的兴起有密切的关系,可以说它是实学思潮在史学的具体表现。“实学”一词产生很早,至少在南宋郑樵的著作中就出现了。郑氏在《通志·图谱略》中对“义理之学”和“辞章之学”都提出了批评,认为“二者殊途而同归,是皆从事于语言之末而非为实学也”。在《昆虫草本略》序中,又云:“学者皆操穷理尽性之说,而以虚无为宗,至于实学,则置而不问”。但作为一个思潮,实学思潮则形成于明末清初。
首先,实学思潮是空疏学风的反动。明朝,陆王心学占据主导地位。王学走向极端即流于空谈性理,理学禅学化。“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是他们治学的鲜明写照。物极必反,一种学风在其初期往往具有它的合理性和生命力,但发展到极致,必然弊端丛生。王学发展到后来,就是如此,所以它日益引起一部分有社会责任感的学者的不满。明代万历中期以后,以顾宪成、高攀龙等人为代表的“东林党”,既是一个政治团体,也有学术团体的特点,在知识界颇具影响。东林党人不贵空谈,而贵实行,主张革新朝政,以济世救民。此后在江浙一带又产生复社,且向其他省份发展。复社成员“接武东林”,关心政治,致力于学风、文风的改良,匡正王学末流。
其次,实学思潮是明朝社会危机的社会现实在思想文化界的反映。明朝中后期,社会危机加深,学者在治学的同时,对社会表现了沉重的忧虑。著名史学家无论是否受到王学之影响,均有博通经史、通今达变的学术倾向。如郑晓、王世贞、李贽、焦竑等人,都是如此。他们学识渊博,提出“六经皆史”,重视史学的经世功能,对明末学术多有影响。茅元仪的《武备志》、陈子龙等人编辑的《皇明经世文编》、陈仁锡的《皇明世法录》、王圻的《续文献通考》等著作都是这种学术旨趣的继承和发展。
第三,明朝最后三四十年,“西学东渐”,西方文明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影响,开始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对实学思潮的发展起了一定的催进作用。如利玛窦、汤若望、艾雅略等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学者李之藻、徐光启等联系密切,相互学习。他们在宣讲耶酥教的同时,也传播了西方的科学技术。他们不务空谈,讲求实际,主张要“实心、实行、实学”。西方科学知识和务实学风,赢得了中国一些高层知识分子的信任和推崇,丰富了实学的内涵。
第四,明朝的灭亡,更刺激了明朝遗民士大夫“黜虚崇实”的学术取向。他们认为,王学和空疏学风是导致明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于是坚决地与专用心于内、尚虚的王学决裂,使实学思潮发展到鼎盛的阶段。如顾炎武说:“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有余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谈,王介甫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之良知是也”。(《日知录》卷18,《朱子晚年定论》)“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日知录》卷7,《夫子之言性与天道》)顾炎武对明末空疏学风批评得最严厉,他的著作出现“实学”的次数也比较多,而且由于他身体力行地实践他所倡导的学风,所以其学术影响亦更加深远。
“实”与“虚”是相对而言的。“虚”含有唯心的意味,“实”则含有唯物的义蕴。“实”主要指实事、实物、实象、实证、实行、实践以及实事求是的学问态度。黜虚崇实可以说是明清之交的学术主流,当时最具学术话语权。对于实学,各家有所侧重,有修养履践之实学,有国计民生之实学,有通经致用之实学,有博通古今、明体达用之实学,有研究各种切用于世如农田、水利、河渠、盐政、赋税、漕运、边防等之实学,也有资测之学(自然科学)的实学。这些实学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哲学层面的,即以经学济理学之穷、通经致用的实学;二是史学、政论、文学等层面的,学以经世的目的也非常明确;三是有关经济、地理、边防以及科技等方面的具体学问。此三个层面相互联系,具有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倡导做学问要有益于社会,“文须有益于天下”。明清之际的中国史学,是实学思潮下的史学,是实学的组成部分。
二、社会批判与历史盛衰论
明清之交和清朝建立初期,实学思潮发展到新的阶段。在抗清失败之后,一些学问博洽之士痛定思痛,从经学、历史学以及自身的亲身经历中探讨明朝灭亡的原因,进而研究社会历史盛衰之理。当时出现了一批经史兼通的学术大师,其中以在清末被称作“三大思想家”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最有代表性。他们所作出的社会批判和关于历史盛衰的观点,反映了时代的要求,最能体现那个时代历史学的精神。史学的求真与致用,在他们的著作中充分展示出来。
首先,他们都能够从哲理上论述历史的盛衰变化,指出社会历史变革的必然性,主张要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而进行变革。如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已日》:“《革》:已日乃孚,《六二》已日乃革之,朱子发读为戊己之己。天地之化,过中则变,日中则昃,月盈则食。故《易》之所贵者中,十干则戊己为中,至于己则过中而将变之时矣,故受之以庚。庚者更也。天下之事,过中而将变之时,然后革而人信之矣”。就是说,任何事物都是变化的,在“将变之时”主动变革,则“人信之矣”,就能够赢得人心,取得信任。《通乎昼夜之道而知》云:“通乎昼夜之道而知,则终日乾乾,与时偕行,而有以尽乎《易》之用矣”。就是说,变化是一种自然属性,就像白天黑夜交替一样。人只有掌握变化的规律才能获得智慧。奋发努力而又与时俱进,按照事物变化的规律办事,才是遵循了《易》的原则。顾炎武这里在指出变的同时,还强调了“时”。《艮其限》提出“物来而顺应”,反对执一不化;《垂衣裳而天下治》提出“通变宜民之论”。黄宗羲对《周易》深有研究,著有《易学象数论》。他也训解了《革》卦,说:“器弊改铸之之为革。天下亦大器也,理乐制度,人心风俗,一切变衰,圣人起而革之,使就我范围以成器。后世以力取天下,仍袭亡国之政,恶乎革?”(《易学象数论》卷3,《原象》)他非常注重从变化的角度认识历史上的得失存亡,说:“消长得失,治乱存亡,生乎天下之动,极乎天下之变”。(《易学象数论》卷6,《胡仲子翰衡运论》)王夫之关于《周易》的研究著作有《周易内传》、《周易内传发例》、《周易外传》、《周易大象解》、《周易稗疏》、《周易考异》等,他从《周易》中汲取思想营养,深刻论述了势、理、时、因、革等问题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主张社会变革要顺势乘时,“更新而趋时”。
其次,他们对封建专制政体的弊端进行了揭露,并通过反思历史,提出了一些具有民主色彩的社会变革主张。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对专制的帝王作了激烈的抨击,说:“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明夷待访录》,《原君》)顾炎武也有类似的思想,他的批判比较含蓄,但却不乏理性。他从考据的角度对君臣关系作了新的解释,从而表达出他的民主启蒙思想,突出地反映在《日知录》的《饭糗茹草》、《周室班爵禄》等条中。王夫之也坚决地反对帝王专制,说“虽帝王不能不下邱民以守位。”(《读通鉴论》卷2)“独夫者,有天下而国必亡,身必戮”。(《读通鉴论》卷15)
对于君臣关系,黄宗羲说:“缘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认为:“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明夷待访录》,《原臣》)也就是说,君臣都是因管理国家而设立的,他们有共同的职责,就是为民谋利,“臣之与君,名异而实同”。臣与君,是一种同事的关系,“吾无天下之责,则吾在君为路人”,“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明夷待访录》,《原臣》)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有《称臣下为父母》、《人臣称人君》、《人臣称万岁》等条,很明显是在有意淡化神圣不可侵犯的君权,为建立新型的较为平等的君臣关系寻找历史根据。王夫之主张君主和官吏各负其责,相互制约。“天子之令不行于郡,州牧刺史之令不行于县,郡守之令不行于民”,反对君主对地方“越数累而遥系之”。(《读通鉴论》卷16)顾、黄、王关于君臣关系的议论,可以说涉及到了改革封建政治制度的问题。
在议政方面,黄宗羲提出了“学校”的职能,说“学校,所以养士也。然古之圣王,其意不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义始备”。即学校还具有议政、参政的职能。认为皇帝也要受学校的约束,推举当世大儒为大学祭酒,“祭酒南面讲学,天子亦就弟子之列。政有缺失,祭酒直言无讳”。(《明夷待访录》,《学校》)这里的学校,颇类似于西方的议会。黄宗羲的这些思想,的确是破天荒的。他没有接触西学,他是在批判中国封建专制制度,总结历史的基础上得出的。而明朝皇帝的高度集权所造成的政治黑暗、宦官专政,更使他有切肤之痛,是他能够较为深刻地认识到专制危害的直接原因。与黄宗羲相类,顾炎武提出了“清议”思想,他说:“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然则政教风俗,苟非尽善,即许庶人议矣”。(《日知录》卷13,《清议》)顾氏认为人心风俗关乎社会盛衰,而清议对维持良好的社会风俗具有重要的意义,故清议与国家治乱也息息相连。顾氏也注意到了学校的作用,说“设乡校、存清议于州里,以佐刑罚之穷”。(《日知录》卷13,《清议》)
黄、顾、王在当时能提出上述主张,不愧是中国近代思想的先觉者,无怪至200多年后的清末,维新派宣传变法,还从他们的著作中寻找思想武器。
第三,他们都高扬史学经世的旗帜,理直气壮地肯定史学的社会价值。顾炎武说:“夫史书之作,鉴往所以训今。”(《亭林文集》卷6,《答徐甥公肃书》)“不学古而欲稽天,岂非不耕而求获乎?”(《日知录》卷2,《其稽我古人之德》)黄宗羲提出“国可灭,史不可灭”,他一生致力于搜集明代文献,在于保存故国历史,在于这些文献“可以补前史之缺略,胜国人品,前朝遗事,以及天官历数之家,皆可考正”。(《南雷文定四集》徐秉义序,见《黄宗羲全集》第1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王夫之对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极为称赞,说它“非知治乱而已也,所以为力行求治之资也”。(《读通鉴论》卷末,《叙论四》)他著《读通鉴论》、《宋论》,继承司马光史以资鉴的为学宗旨,认为“所贵乎史者,述往事以为来者师也。”(《读通鉴论》卷6)他将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思想提高到新的水平,并贯彻于他的史论中,在许多地方,辨正和纠正了司马光的某些僵化的史论观点。
要之,以顾、黄、王为代表的明清之际的史学,密切关注社会现实,通过研经著史,探讨历史兴衰之理。他们批判封建专制,主张社会变革,目的都是为了社会进步,“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体现出崇高的学术境界。
三、求真致用的学风及其影响
明清之际的学术大家,在经世致用的宗旨下,富有求真的学术态度。他们治学严谨,心胸开阔,所表现出的优良学风和优秀的学术品德,很值得后人继承和发扬光大。
顾炎武把治学比作“采铜于山”。《日知录》可谓是他采铜于山的杰作。这部著作,在他生前只刻了八卷本,以后不断增益,反复修改。在给弟子潘耒的信中,他说:“著述之家,最不利乎以未定之书传之于人……《日知录》再待十年,如不及年,则以临终绝笔为定”。(《亭林文集》卷4,《与潘次耕书》)他撰《音学五书》,用了三十余年,所过山川亭鄣,无日不以自随,“凡五易其稿而手书者三矣”。他探究学问,不存门户之见,说:“自结发以来,奉为师友者,盖不乏人,而未敢存门户方隅之见也”。(《亭林文集》卷3,《复陈蔼公书》)黄宗羲也认为,学要有宗旨,但不可有门户。他编撰《明儒学案》,能够公平地对待各家学术,对各家学术的价值均予以承认和肯定。
他们重“器识”,胸怀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如顾炎武说:“‘夫子归与归与’,未尝一日忘天下也。故君子之学,死而后已。”(《亭林文集》卷4,《与人书六》)“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亭林文集》卷4,《与人书二十五》)他们力戒作空虚无用之文,“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同上,《与人书》)
顾氏反对做学问讲求名利,说:“古人求没世之名,今人求当世之名。吾自幼及老见所以求当世之名者,无非为利也。名之所在则利归之,故求之惟恐不及也。苟不求利亦何慕名!”(《日知录》卷7,《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他引用孔子的话,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他所以不坐讲堂,不收门徒,就是为了反对明朝正德以来以讲学为名,师徒相互标榜,甚至党同伐异的不良习气。
他们坚持学术民主,主张学术平等。顾炎武对明初政府控制经学,搞四书五经大全,使经说归于一提出批评,说:“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十族诛而臣节变。洪武永乐之间,亦世道升降之一会矣”。(《日知录》卷18,《书传会选》)黄宗羲也说:“盖道非一家之私,圣贤之血路,散殊于百家,求之愈艰,则得之愈真。虽其得之有至有不至,要不可谓无与于道者也”。(《清溪钱先生墓志铭》,见《黄宗羲全集》第10册)
他们都主张做学问要独立思考,要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风格。如黄宗羲认为,“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者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明儒学案发凡》,见《黄宗羲全集》第7册)顾炎武批评写文章模仿古人之病:“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模仿。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极致,况遗其神理而得其皮毛乎?”(《日知录》卷19,《文人模仿之病》)他对朋友诗文之点评,也是强调要有自己的特色:“君诗之病,在于有杜;君文之病,在于有韩、欧。有此蹊径于胸中,便终身不脱依傍二字,断不能登峰造极”。(《亭林文集》卷4,《与人书十七》)
对以顾、黄、王为代表的明清之际史学的特点,如果以简单的话来概括,我想用顾炎武反复强调的“博学于文”、“行己有耻”比较恰当。这两个词反映了明清之际史学的博大气象和史学关心现实、史学家情系民族气节的基本特征。“博学于文”和“行己有耻”在他们看来是有机统一、不可分割的。在清初高压的文化政策之下,他们以这两点作为自己的治史原则和行为准则,的确难能可贵。康熙中叶以后的史学家,特别是乾嘉史家,也很佩服这一时期的史学,甚至在经史小学等方面做得更加精细,有了很多推进,但却不能将二者统一起来,特别是在后一方面,已缺少了先前的生机。他们更多地承继了这些史学大家的技术性的东西,在治学宗旨方面没有这几位大家的气魄。明清之际的史学,之所以受到后人的推崇,求真的学术业绩是一个方面,但最根本的还是他们经世致用的为学精神。他们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和社会改良的要求,虽然没有像他们期待的那样为当政者所采纳,甚至不如他们的学问在历史上影响之大,但他们表现的社会责任感和济世救民的学术精神却是永恒的。
标签:黄宗羲论文; 顾炎武论文; 儒家论文; 易学象数论论文; 明夷待访录论文; 明清论文; 读通鉴论论文; 社会思潮论文; 国学论文; 日知录论文; 经世致用论文; 明末清初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