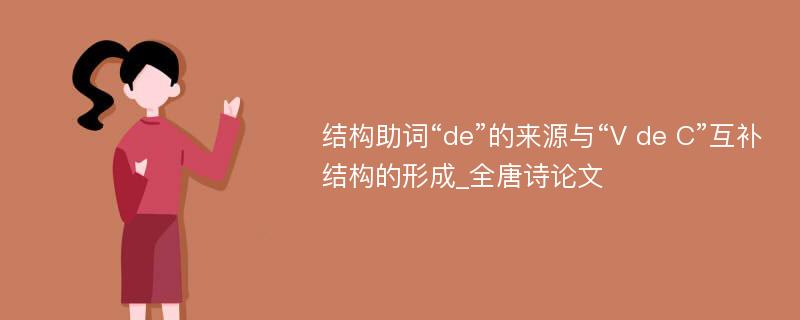
结构助词“得”的来源与“V得C”述补结构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论文,助词论文,来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代汉语中“V得”除了可带体词性成分构成“V得O”、“VO 不得”等格式之外,还可带谓词性成分,构成“V得C”、“V得OC ”等格式。
这种带“得”的述补结构何时产生?形成的机制以及“得”的来源、性质是怎样的?这是本文将要讨论的问题。
一 前人对带“得”的述补结构产生时间及“得”来源的看法
1.1带“得”的述补结构最早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较有代表性的意见有两种,一种意见认为南北朝时期便已产生(潘允中1980,岳俊发1984),所举例证为《世说新语》中下面的例子:
(1)平子饶力,争(挣)得脱,逾窗而走。 (《世说新语·规箴》)另一种意见认为唐代始产生(王力1958,杨建国1959,杨平1990,蒋绍愚1994,吴福祥2000)。
对于第一种看法,杨平(1990)、蒋绍愚(1994)都曾提出反驳意见,认为南北朝时期尚未产生出带“得”的述补结构,(注:针对例(1)《世说新语·规箴》中的这句话,杨平(1990)作了很好的分析, 她指出:我们认为这里的“争(挣)得脱”还不宜看作述补结构。“挣得脱”可以理解为“挣而得脱”,与“遇赦得还”(世说新语·贤媛)类似,可看作连谓结构。照此理解,上句或可断为“平子饶力争,得脱,逾墙而走。”因为唐以前目前大家能举出的带“得”的述补结构的例子只此一例。任何一种语法现象都不会是孤立的,如果早在五世纪的刘宋时期带“得”的述补结构就已经出现了,而在后来的几百年里又销声匿迹,一个例子也看不到,这是不大可能的。我们不能仅根据一个孤证就把一种语法现象的产生年代提前几百年,何况这个例子还可以有别的分析方法(56-57页)。李平(1987)则倾向于将例(1 )断句为:“平子饶力,争,得脱,逾墙而走。”也是将它视为连动结构。)我们认为他们的意见是成立的,唐代才真正出现了带“得”的述补结构。
1.2对于带“得”的述补结构中“得”的来源,也有不同的看法。
杨建国(1959)认为结构助词“得”是直接由“V得O”式中“获得”义的“得”发展而来的,他说:“如果对上述动补式谓语的宾语有所补叙时,即说明宾语因动词所使成的一种变化或状态时,我们探求的结构助词‘得’就出现了。”祝敏彻(1960)、岳俊发(1984)等认为状态补语结构的“得”是从表完成的“动词+得”结构的“得”虚化来的,可能补语结构的“得”是从表可能的“动词+得”结构的“得”虚化来的。岳俊发说:“结构助词‘得’正是直接由这种表完成的‘得’字虚化来的。因为情态补语总是表示动作完成以后所造成的一种具有描写性质的情态,所以就有可能在上面这种表完成的‘得’字之后,补述上一种描写性质的成分。这样就产生了一种崭新的‘动-得-动/形/主谓’的格式。在这种格式中,‘得’字失去了动词的性质和功能,成为连接动词和补语的成分,从而虚化成结构助词,产生了情态补语‘得’字句。”王力(1958)则认为二者来源相同,都是“由原来的‘获得’意义转化为‘达成’,由‘达成’的意义更进一步的虚化,而成为动词的词尾。”杨平(1990)、蒋绍愚(1994)和吴福祥(2000)持同样的看法。杨平说:“当‘动词+得’后面不是体词性的宾语而是谓词性成分的补语时,就产生了带‘得’的述补结构。”吴福祥说:“上面例子中的‘V得’,如果后接谓词性成分,那么整个结构就变成了述补结构,同时,‘得’也就逐渐演变成用作补语标记的结构助词。我们认为述补结构‘V得C’就是这样形成的。”
上述几种看法的一个共同点是,都试图从“获得”或“完成”义“得”的虚化来解释“V得C”、“V得OC”述补式的产生。 这些解释是有道理的,“V得”中的“得”由“获得”义引申而有“达成、 达到”义,表示动作行为的完成、实现,进而在“V得VP ”结构中引申而表示行为动作达到什么结果,“得”进一步虚化而为连接两个谓词性成分的结构助词,“V得VP”变为“V得C”述补结构也是合乎逻辑的。但是,“V得C”是否仅有这一种来源呢?
下面我们尝试从另外的角度对带“得”的述补结构的形成及结构助词“得”的来源提出另一种可能的解释。
二“得”的“使令”义用法
2.1魏晋六朝时期,“得”有与使令词如“使、令、 教(交)”等相通的用法和功能。如:
(2)天即雷电霹雳,终不能得坏。(《法显传》)
(3)自挽草木,平治处所,使得净洁。(同上)
(4)有人入者辄捉,种种治罪,莫使得出。(同上)例(3)、(4)“使得”同义连用,均表使令、致使义。又如:
(5)是谓边城初业成就,外寇不能得坏。 (姚秦·竺佛念译《出曜经》卷八652页下,《大正藏》No.212)
(6)彼仙人捉一澡瓶,语城神言:“先动此瓶,然后掷我。 ”尽其神力,不能得动,惭愧归伏。
(元魏·吉迦夜共昙曜译《杂宝藏经》卷七481页下,《大正藏》No.203)试比较:
(7)诸人各各尽其神力,不能使动。(同上,卷七483页上)
(8)尔时魔王闻是语已,欲去死尸,虽尽神力,不能使去。 (后秦·鸠摩罗什译《大庄严论经》卷九307页下,《大正藏》No.201)
(9)尽其神力,不能令却。 (元魏·慧觉等译《贤愚经》卷十三443页中,《大正藏》No.202)例(6)“不能得动”与例(7 )“不能使动”义同,与例(8)、例(9)“不能使去”、“不能令却”句式同,“得”具有“使、令”义,似不能再视作能性助动词,“不能得动”不宜看作“能”与“得”同义连用。再如:
(10)洗浴毕,身体羸瘠,不能自出,天神来下,为按树枝,得攀出池。(刘宋·求那跋陀罗译《过去现在因果经》卷三639页中, 《大正藏》No.189)比较:
(11)树神即便按此树枝,令佛攀出。(同上,卷四648页下)又如:
(12)汝当然一大镬,七日七夜,使令极沸,莫得断绝。(元魏·吉迦夜共昙曜译《杂宝藏经》卷七484页下,《大正藏》No.203)上例为祈使句,前言“使令极沸”,后说“莫得断绝”,“得”同样表示的是“使令、教令”义。唐代,“得”的这种用法仍有用例,如(例16、17、20、22、23引自江蓝生、曹广顺1997):
(13)将老忧贫窭,筋力岂能及。征途及侵星,得使诸病入。(《全唐诗·杜甫·早发射洪县南途中作》)“得使”犹“致使”,“得”、“使”同义连用,义同。
(14)之罘南山来,文字得我惊。(又《韩愈·招杨之罘》)
(15)归来经一宿,世虑稍复生。赖闻瑶华唱,再得尘襟清。(又《白居易·答元八宗简同游曲江后明日见赠》)
(16)能共牡丹争几许,得人嫌处只缘多。(又《陈标·蜀葵》)
(17)苏五奴妻张少娘,善歌舞,有邀迓者,五奴辄随之。前人欲得其速醉,多劝酒。五奴曰:“但多与我钱,吃锤子亦醉,不烦酒也。”(崔令钦《教坊记》)
(18)信禅师从外入城,劝诱道俗,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其时遂得狂寇退散,井泉泛溢,其城获全。(《神会和尚禅话录·南阳和尚问答杂徵义》)
(19)六载苦行,四智周圆,破九百万之魔军,成八十庄严之好相。遂得天上天下,惟佛独尊,三界之中,竟无有比。(《敦煌变文集·破魔变文》)
(20)忽忆父兄枉被诛,即得五内心肠烂。(又《伍子胥变文》)
(21)姜女自雹哭黄天,只恨贤夫亡太早。妇人决列(烈)感山河,大哭即得长城倒。(又《孟姜女变文》)
唐五代时期的熟语“得人怜”、“得人憎”意为“使人怜”、“使人憎”,“得”亦为“使、令”义。如:
(22)玄宗问黄幡绰:“是勿儿得人怜?”对曰:“自家儿得人怜。”(《因话录》卷四)
(23)悔嫁风流婿,风流无准凭。攀花折柳得人憎,夜夜归来沉醉,千声唤不应。(《敦煌曲子词集·南歌子》)
上引诸例,“得”不仅在诗歌中出现,散文中亦见,说明其使用较为普遍。
“得”具有“致使”义的另一证据是,唐五代时期在诗歌、变文和禅宗语录等文献中有不少“致得、直得、感得”后接谓词性成分的用例。如:
(24)致得仙禽无去意,花间舞罢洞中栖。(《全唐诗·姚合·崔少卿鹤》)
(25)李陵闻诮,直得身皮骨解。(《敦煌变文集·苏武李陵执别词》)
(26)治国四年,感得景龙应瑞,赤雀咸(衔)书,芝草并生,嘉和(禾)合秀。(《敦煌变文集·伍子胥变文》)
(27)太杀拽人鼻孔,直得脱去。(《祖堂集》卷十四)试比较:
(28)三界众生多爱痴,致令烦恼镇相随。(《敦煌变文集·左街僧录大师押座文》)
“致得、直得、感得”意义相近,均为“致使、致令”的意思。(注:参见蒋礼鸿(1988 )《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第四次增订本)427页。)据杨平(1990)调查,《敦煌变文集》中“感得”36例、“致得”2例、“直得”6例,《祖堂集》“感得”1例、“直得”28例。 宋代文献中仍有用例,如:
(29)细追思,恨从前容易,致得恩爱成烦恼。(《全宋词·柳永·法曲第二》)
(30)衲僧家智游象外,妙入环中,犹是家常茶饭,无端被释迦老子以无丝线系却脚跟,直得东西南北去路无从。(《虚堂和尚语录》卷二)
(31)法师七人,焚香望鸡足山祷告,齐声动哭。此日感得唐朝皇帝、一国士民,咸思三藏,人人发哀,天地陡黑,人面不分。(《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入竺国度海之处第十五》)
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卷一“教(二)”条:“教,犹得也。”举有唐人罗隐诗例:
(32)祗合当年伴君死,免交憔悴望西陵。(罗隐《铜雀台》)
2.2“得”与“使、令、 教(交)”这种“致使”意义上的相通相近,使得它们在句法功能上也有平行的表现。“使、令、教(交)”六朝以后的一个重要功能是用于两个谓词性成分之间,起使令标记的作用,表示其前面的动作行为致使(导致)出现某种结果或达到某种目的。如:
(33)菩萨为然大智慧灯,汝今云何欲吹令灭?(刘宋·求那跋陀罗译《过去现在因果经》卷三641页上,《大正藏》No.189)
(34)然后细剉,令如枣栗,曝使极干。(《齐民要术·造神麴并酒第六十四》)
(35)仁者若称大种姓,嫌我境狭不肯停,我共诸臣及百官,当更吞并令宽广。(隋·阇那崛多译《佛本行集经》卷二十三760页下, 《大正藏》No.190)
(36)愁应暮雨留教住,春被残莺唤遣归。(《全唐诗·白居易·闲居春尽》)
(37)孤云虽是无心物,借便吹教到帝乡。(又《崔涯·咏春风》)
(38)谁把金刀为删掠,放教明月入窗来。(又《成文干·柳枝词九首之五》)
(39)还似花间见,双双对对飞,无端和泪拭燕脂,惹教双翅垂。(《花间集·张泌·胡蝶儿》)
这些用于两个谓词性成分之间的“使、令、教”等,为“得”进入相同的格式提供了合适的句法位置。因此,唐代有些“得”最初可能是以“致使”义动词的身份进入这一格式的,它所起的作用也和“使、令、教(交)”等相近,作使令标记。试比较下面两例:
(40)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全唐诗·王昌龄·闺怨》)
(41)早知落处随疏雨,悔得开时顺暖风。(又《孟宾于·句》)
唐代文献中有时“得”与“教(交)”可在上下文诗句中形成互文,如:
(42)诗名占得风流在,酒兴催教运祚亡。(《全唐诗·徐振·雷塘》)
(43)地脉尚能缩得短,人年岂不展教长。(又《吕岩·七言》)
(44)人间医药实难量,先且寻求要好方。奉佛永交增福利,献僧长得灭灾殃。(《敦煌变文集·妙法莲华经讲经文》)
不过,“得”与“使、令、教(交)”等虽然都可用于相同的句法位置上,表达大致相同的语法意义,但彼此仍有一些不同之处,表现在:1)“使、令、 教(交)”等通常用来表达主使者(施事)通过实施某一动作行为,有意要致使某一特定的结果出现或达成某一特定目的,比较强调结果或目的是施事有意志的动作行为导致或造成的,主使者(施事)对动作的结果有较高的操控力。“得”则一般用于表达某种动作行为自然(或必然)导致某一结果状态的场合,着重于某种结果的出现是某种动作行为发生后必然会产生的自然结果状态。2)出现在“使、令、教(交)”等前面的动词一般为及物的动作动词,较少不及物动词;出现在“得”前的动词则既可以是及物的动作动词,也可以是不及物的状态动词。考虑到上面这两方面差别,我们可以将“使、令、教(交)”等看作是强式使令标记,“得”为弱式使令标记。前者侧重于主观使令,后者侧重于客观致使。
三“得”的虚化与述补结构“V得C”的产生
3.1“得”既为弱式使令标记动词, 其语法功能就有进一步虚化的可能和趋势。“得”特定的句法位置(处于两个谓词性成分之间)使得它只能朝起连接两个谓词性成分的结构助词方向虚化。使令标记词“得”虚化为结构助词后,原为连动结构的“V得VP ”也就演变为述补结构的“V得C”。
“得”这种语法性质的转变并没有明显的形式标志可以判定,其原因在于,“得”前的动词与后面的谓词性成分之间的因果语义关系并没有因“得”语法性质的转变而发生变化。因此,早期文献出现的“V 得VP”格式中的“得”哪些仍是使令标记动词,哪些已虚化为结构助词并不容易明确判定,两可的情形很多,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这些结构格式的语义理解。比如:
(45)一一口衔食,养得成毛衣。到大啁啾解游颺,各自东西南北飞。(《全唐诗·王维·黄雀痴》)
(46)九江三月杜鹃来,一声催得一枝开。(又《白居易·山石榴寄元九》)
上举两例中的“得”理解为使令标记词或结构助词似乎都可以,并不太影响我们对“得”前后两个谓词性成分语义关系的理解。这说明,“得”即便已虚化为结构助词,但仍多多少少保留着一些较实的致使语义,二者的界限难以判然划清。
3.2我们上面尝试提出了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思路, 试图从相关语法格式的相互影响以及“得”自身语法功能和语法意义的转变入手,对“V得C”述补结构的形成做出比较自然合理的解释。因此,我们倾向于认为,“V得C”结构很可能有两个来源,一是直接源于“达到、达成”义“得”的虚化;二是源于“致使”义“得”的进一步虚化。虽然二者从本质上讲又都来自“获得”义的“得”,但在形成“V得C”述补结构的过程中,二者所起的作用还是有所不同的。
由于“致使”义的“得”和“达到”义的“得”在“V得VP ”结构中的语法位置和语法意义,促使它进一步虚化,合二为一,最终成为一个语法词——结构助词。“V得VP”也因而演变为述补结构“V得C”。
从早期“V得C”的用例还可以大致看到一些它们的来源情况,下面我们就不同来源的“V得C”分别举几个例子:
A.“得”来源于“达到,到”义
(47)别来老大苦修道,炼得离心成死灰。(《全唐诗·白居易·晚春欲携酒寻沈四著作先以六韵寄之》)
(48)啼得血流无用处,不如缄口过残春。(《全唐诗·杜荀鹤·子规》)
(49)始从怀妊至婴孩,长得身躯六尺才(长)。(《敦煌变文集·父母恩重经讲经文》)
(50)遂骂燕子:“你甚顽嚣,些些小事,何得纷纭,直欲危他性命,作得如许不仁。两个都无所识,宜吾不与同群。”(《敦煌变文集·燕子赋》)
(51)若体会不尽,则转他一切事不去;若体会得妙,则转他一切事向背,后为僮仆著。(《祖堂集·卷八》)
B.“得”来源于“致使”义
(52)芳情香思知多少,恼得山僧悔出家。(《全唐诗·白居易·题灵隐寺》)
(53)空令骨肉情,哭得白日昏。(《全唐诗·孟郊·悼吴兴汤衡评事》)
对上举各例“V得C”来源的区划只是大致的推测,并非绝对的认定。事实上,两种不同来源的“V得C”在语言发展过程中,由于“得”语法化程度的加深,其最初的来源越来越难以判定也是很正常的。
四 余论
4.1 这里我们需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得”的“致使”义用法是如何产生的?在回答之前,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同为“获得、获取”义的“取”在六朝时期的一种新用法。
“取”在六朝时期也有与“得”相同的“致使”义用法,在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一书中这种用法很常见。如:
(54)凡非时之要,水沤一月,或火逼取干,虫皆不生。(《齐民要术·伐木》)
(55)半熟,更以油五升洒之,即下,用热食。若不即食,重蒸取气出。(又《素食》)
下面三个例子句式相同,分别用了“使”、“令”和“取”:
(56)生布绞取浓汁,涂盘上或盆中,盛暑,日曝使干,渐以手摩挲,取为末。(《齐民要术·种枣》)
(57)窖麦法:必须日曝令干,及熟,埋之。(又《大小麦》)
(58)啮看豆黄色黑极熟,乃下,日曝取干。(又《作酱法》)“取”、“令”、“使”还可以同义连用,其意义不变,如:
(59)昼曝,夜内汁中,取令干,以余汁密藏之。(《齐民要术·种木瓜》)
(60)其和麴之时,面向杀地和之,令使绝强。(又《造神麴并酒》)
其他文献中“取”用如“使、令”义的如:
(61)丘巨源,兰陵兰陵人也。少举丹阳郡孝廉,为宋孝武所知,大明五年,敕助徐爰撰国史。帝崩,江夏王义恭取掌书记。明帝即位,使参诏诰,引在左右。(《南史·丘巨源传》)此例“取”与“使”互文,义亦同。
(62)名位未高,如为勋贵所逼,隐忍方便,速报取了,勿使烦重,感辱祖父。(《颜氏家训·风操》)唐代仍有用例,如:
(63)椒房,殿名,皇后所居也。以椒和泥涂壁,取其温而芳也。(《汉书·车千秋传》颜师古注)
4.2“得”与“取”均有“致使”义用法,表明作为“获得、 获取”义的“得”、“取”具有相同的引申途径。因此,本小节开头提出的问题可以改为:为什么“获得”义动词可以引申出“致使”义用法?
我们认为,“得”、“取”是在由“获得”义引申为“达成,达到”义之后,进一步引申出“致使”义的。“得”单用表“到达,达到”义的例子如:
(64)午辞空灵岭,夕得花石戍。(《全唐诗·杜甫·宿花石戍》)
“取”单用表“达到”义的例子如:
(65)医方之事,取妙极难,不劝汝曹以自命也。(《颜氏家训·杂艺》)
达到某种结果跟致使某种结果产生或出现,就结果而言是一样的,因此,“得”、“取”由“达到、达成”引申为“致使”义是有其逻辑基础的。
在“V得VP”结构中,如果强调以某种手段或方式V,致使达到或实现某种结果VP的话,“得”的“致使”义就更突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