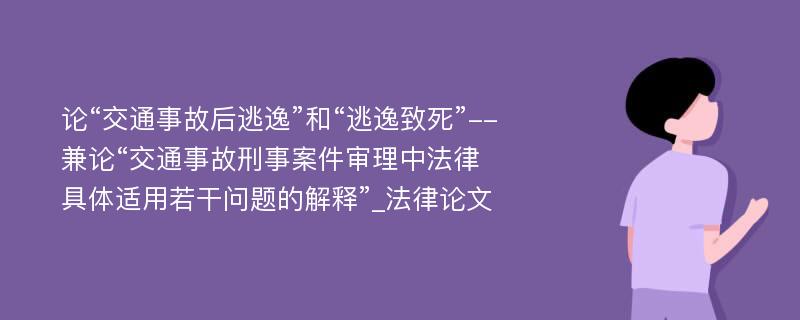
论“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和“因逃逸致人死亡”——兼评《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若干规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刑事案件论文,若干规定论文,致人论文,关于审理论文,法律若干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逃逸”行为的分析与评价
刑法第133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个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如果理解其中的“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和“因逃逸致人死亡”规定,理论和实践中存在比较大的分歧看法。理论界根据立法的表述方式,将上述规定的内容视为交通肇事罪的处刑情节,而在2000年11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中,对其中附条件的“逃逸”行为解释为构成交通肇事罪的条件之一。当然,无论理论上、实践中对刑法规定的“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因逃逸致人死亡”是如何理解的,首先涉及的是“逃逸”,“致人死亡”只是“逃逸”行为的后果而已。因此,对“逃逸”行为的分析,既是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情节的理解,也是对“因逃逸致人死亡”这一结果认识的前提。
对于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行为,学者的表述基本一致。如有学者认为,“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造成了重大交通事故,为逃避法律追究而不依法报警、保护现场、等候处理等,私自逃离现场的行为。”(注:鲍遂献、雷东生:《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9页。)或者“是指不依法报警、保护现场、等候处理而私自逃跑。”(注:陈明华主编:《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21页。不过,笔者认为上述的表述使用“私自”一语有词不达意之感,因为就违法的逃跑行为而言,并不存在被允许而“逃跑”,何需以是否“私自”来界定。)还有学者认为“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造成的重大交通事故的发生,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行为”。(注:胡康生、李福成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释义》,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52页;朗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解释》,群众出版社1997年版,第150页。)更有学者详细地分析了“逃逸”的主客观特征,认为“所谓逃逸,即为躲避不利于自己的环境或事物而离开。”主观上是“逃避抢救义务以及其后逃避责任追究是逃逸者的两个根本动机。”“逃逸行为客观表现为逃脱、躲避,在实践中主要表现即是自现场逃离。”同时还认为,刑法第133条的规定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依法处理道路交通肇事案件的通知》有关规定相比,“逃逸情节本身已经构成一独立的量刑情节而在司法运作中发生作用,不再依附于或者必须与先行的交通肇事行为所造成的人员死亡或者公私财产直接损失相结合,即能发挥其量刑价值。”(注:林维:《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研究》,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判解》,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49、251、253、249页。)
上述观点的共同出发点显然都在于事故发生后,行为人依法负有国务院《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于1997年9月22日颁布。)第7条规定的“发生交通事故的车辆必须立即停车,当事人必须保护现场,抢救伤者和财产(必须移动时应当标明位置),并迅速报告公安机关或者执勤交通警察,听候处理”的义务。既然负有该种义务,不承担该义务的逃跑的行为只能是故意的行为。所以,认识的共同点都在于认为“逃逸”行为是故意而为之。区别在于,前几种观点都将交通事故界定在“重大”上,并且“逃逸”行为必须与重大的交通事故相联系才具有刑法上的意义,而后一种观点对此的看法,似即使先行的交通肇事行为造成的后果无论达到“重大”与否的程度,“逃逸”行为本身也可以是论罪处罚考虑的依据。
《解释》第3条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是指……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但是,同时要求“行为人具有本解释第2条第1款规定和第2款第1至5项规定的情形之一”,即第1款规定的,“死亡1人或者重伤3人以上,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死亡3人以上,负事故同等责任的;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在30万元以上的。”但该条第2款规定:“交通肇事致1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其中第6项规定:(注:该款1至5项的规定依次为:“酒后、吸食毒品后驾驶机动车辆的;无驾驶资格驾驶机动车辆的;明知是安全装置不全或者安全机件失灵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明知是无牌证或者已报废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严重超载驾驶的”。)“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可以看出,这里“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显然同时是对《解释》第3条规定的“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的进一步解释,并且这一层解释的意思中,已将该内容转变为行为人构成犯罪的条件之一。
笔者认为,《解释》对此规定的精神是值得研究的。首先,从《解释》自身的内容看,虽然在关于“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的解释中并没有明确指出交通“事故”的程度,但是从其第2条第1款对“事故”的一般解释内容分析,很明显并非是指一般的交通事故,而是指“重大”的交通事故,即如果仅从后果而言是已经能够构成犯罪的交通事故。笔者认为,从法理上说,如果前行为造成的事故本身并尚未达到“重大”程度,那么,发生事故后的“逃逸”行为本身就不具有作为量刑情节的意义。道理很简单,“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既然造成“事故”的行为不构成交通肇事罪,当然“逃逸”行为也就失去了由刑法予以评价的前提。在现行刑法第133条的规定中,“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只是构成犯罪后在决定刑罚时的量刑情节,但在《解释》中第3条第2款的规定中是将“交通肇事致1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作为构成犯罪的条件,很明显是将立法作为量刑情节的规定,提升为构成犯罪的条件。这不仅仅只是属于越权解释的问题,而且直接造成与刑法第133条规定两者的相冲突和矛盾。
其次,“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从法律设置事故发生后行为人负有义务的角度说,“逃逸”,是指在发生交通事故后,行为人没有履行法律所规定的,对于受害人或受毁损的财物未做必要的救治或者处理的义务,未按法律规定向公安机关报告,而逃离现场,使交通事故所引起的刑事、民事、行政责任无法确定和追究的行为。无论因何种原因而“逃逸”,行为的目的就在于推卸和逃脱责任。毫无疑问,“逃逸”行为不可能是由“过失”而实施,只能是一种“故意”而为的行为。但是,问题在于对“逃逸”行为本身能否视为具有犯罪性的行为?在《解释》的上述规定中很明显是有将该种情况予以犯罪化趋势的。这在一些学者的论述中,同样已具有将“逃逸”行为本身予以犯罪化认识的倾向,(注:林维:《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研究》,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判解》,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49页。)并且是将“逃逸”视为是一种不作为行为。如认为,“法律加重处罚肇事后逃逸行为,并非处罚逃逸行为本身的作为,而是处罚其逃逸行为所导致的抢救义务的缺失及逃避责任认定这一不作为行为,正是本质上是不作为而非作为的逃逸行为,表征着逃逸行为的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正是如此,我们认为逃逸行为本质上是不作为。”(注:林维:《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研究》,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判解》,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50页。)这一认识也成为比较多的学者在分析“因逃逸致人死亡”时依据的前提。如认为,“是行为人发现被害人受伤后,为逃避法律责任,弃之不顾,驾车逃跑,导致被害人死亡。这一阶段,行为人主观上又形成新的罪过,客观上又有新的行为和危害结果。”(注:张兆松:《论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的定罪问题》,载《人民检察》1999年第5期。)
笔者对“逃逸”行为本身表现出一定的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逃逸”行为本质上是不履行法律、法规规定的义务等,不持有不同认识,但是,对“逃逸”行为这种在客观上由作为方式而实施的不作为行为,虽由刑法规定为量刑情节,却被《解释》规定为犯罪成立条件之一的根据,笔者认为有必要作进一步探讨。
在刑法理论上,本质上的不履行作为义务的不作为,既可以表现为“什么都没有做”,也可以表现为“逃避应做的”。“逃逸”行为应属于后一情况。但是,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看“逃逸”行为,也表现出“做了不应当做的”的行为特性。换言之,是“做了”而不是“什么都没有做”。那么,刑法将“逃逸”行为量刑情节化的根据究竟是因为“做了不应当做的”还是“什么都没有做”?笔者认为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理由在于,仅仅以“什么都没有做”予以量刑情节化的根据不充分就在于:如果以此作为加重刑事责任的根据,则在现场既没有实施“逃逸”行为,也“什么都没有做”的不作为行为,是不是同样有理由作为量刑应当考虑的情节呢?换句话,无论其不作为行为是否造成被害人死亡的结果,如果没有实施逃逸行为,则法律没有必要将该种不作为行为予以量刑情节化。正是社会有理由期待行为人积极履行法定义务,而行为人“做了不应当做”的“逃逸”行为,立法者才将该种行为予以量刑情节化。这是恰当的。
但是,在肇事后果尚不严重,例如仅造成一人重伤,如果不附加《解释》的各种情况,显然仅此尚不能够认为行为本身已经完全符合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在此前提下,单纯是不作为的“逃逸”行为能否认为就具有应当予以犯罪化评价的价值或者说根据?笔者认为应当是否定的。理由在于,该种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尚未达到必须予以独立评价的意义。根据刑法理论,不作为的行为构成犯罪就其成立条件而言,可分为纯(真)正不作为与不纯(真)正不作为,而不纯(真)正不作为的犯罪性,在于发生法律要求的严重结果。“逃逸”行为就其行为性看,显然不能视为纯(真)正不作为行为,所以,“逃逸”行为作为不纯(真)正不作为行为,在没有发生严重后果(例如被害人死亡结果时),其不作为行为非刑法意义上的不作为,不具有犯罪性而应当受刑法评价,其具有犯罪性而受刑法评价的基本条件在于发生被害人死亡的结果。而《解释》将先行行为的交通肇事致人重伤后,实施了“逃逸”行为的,作为构成犯罪的条件之一,理由是不充分的。原因在于这里的重伤就是先行肇事行为的结果,其“逃逸”行为只是造成对责任划分和追究的困难,其危害性尚不足以达到必须予以犯罪化的程度,否则就必须否定刑法第133条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作为量刑情节的立法规定本身。根据我国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现行刑法中,除了特定的少数脱逃行为(如脱逃罪)外,尚没有对实施犯罪行为,或者违法行为后的逃跑行为单独予以论罪的规定。就交通肇事后逃跑行为而言,如果对此有必要而且必须予以犯罪化评价,可以说实施刑法规定的任何犯罪后而“逃逸”的行为,都有予以犯罪化的必要。所以,“逃逸”行为脱离已经构成交通肇事罪造成重大事故的前行为,这种不作为的“逃逸”行为本身不具有应当独立予以评价的性质,“逃逸”也就丧失作为量刑情节的意义。或许会有人说,这并不是对单纯“逃逸”行为评价为构成犯罪的条件,而正是将“致一人重伤”与“逃逸”行为相结合而评价为构成犯罪条件的。如果是这种主张,这恰恰又犯了对同一事实“不得重复评价”的错误。详言之,正因为重伤系肇事行为造成非逃逸行为,所以,将逃逸作为条件附加于重伤一人,重伤一人的事实实际上被重复使用于评价,这是违背法的基本理论的。如果说该“逃逸”行为造成被害人的死亡,作为下一层次的量刑情节,危害性的根据的主要方面是被害人“死亡”的结果,而并非仅仅只要有“逃逸”行为就应当具有被评价为量刑情节的条件。因此,《解释》将该种单纯的“不作为”行为视为具有犯罪性的规定,没有充足的理论根据。
由此,笔者认为,交通肇事的后果尚未达到“重大”程度,“逃逸”行为本身不具独立由刑法予以评价的价值,更不应当成为犯罪成立的条件之一。
二、“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分析与评价
“因逃逸致人死亡”的理解,理论上的争议则比较大。归纳起来,大体上有二方面的问题,三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个方面是对“因逃逸致人死亡”情节的概念界定,有如下认识:
(1)认为,“所谓‘因逃逸致人死亡’是指,交通运输肇事致人伤害,如果抢救及时,不会引起死亡,由于行为人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延误了抢救时机,引起死亡的情况。”(注:余剑主编:《危害公共安全罪》(新刑法适用案例指导丛书),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09页。)或者,“‘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是指在出现交通事故后,被害人受伤严重但并未死亡,如果抢救及时可以挽救生命,但由于行为人不采取积极救护措施,逃离事故现场,致使受害人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而死亡的行为。”(注:胡康生、李福成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释义》,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52页。)很显然,上述认识仅仅是就造成残废的客观现象而言,并不涉及行为人主观的认识问题。(2)主张“‘因逃逸致人死亡’,是指行为人发生重大事故后,置受伤人于不顾,致使其未得到及时救助而死亡”。(注:陈明华主编:《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22页。)这里的“置受伤人于不顾”,显然不能排除具有故意所为的性质。
第二个方面是针对“因逃逸致人死亡的”的理解和范围,主要有以下观点:
(1)主张该种情况下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属于故意犯罪,如认为,这一规定“只适用于由交通肇事罪转化成的故意犯罪”。(注:侯国云、白岫云:《新刑法疑难问题解析与适用》,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年版,第349页。)还有学者认为属于故意但仍然构成交通肇事罪,如“肇事后逃逸,不能排除肇事人对被害人的死亡结果持放任态度,但这是肇事后的结果行为,主观上是为了逃避法律责任,因此应定交通肇事罪。”(注:魏克家、欧阳涛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罪名适用指南》,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2页。)只有在“行为人发生重大事故,为逃避责任,故意将致伤人员移弃荒野造成死亡的,应按刑法关于杀人罪的规定定罪处罚。”(注:苏惠渔主编:《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55页。)
(2)认为,刑法第133条的规定只适用于行为人交通肇事后逃跑因过失致人死亡的情况,不包括因故意(包括间接故意或直接故意)致人死亡的情况。(注:参见黄祥青:《浅析刑法中的交通肇事罪》,载《政治与法律》1998年第4期。)更有学者指出,“‘因逃逸致人死亡’,应限于过失致人死亡的,即事实上发生了两次交通运输事故;已经发生交通事故后,行为人在逃逸过程中又发生交通事故,显然刑法将同种数罪规定了一个法定刑。如果在逃逸过程中对致人死亡持故意,则成立另一个独立的犯罪,不能适用上述规定以一罪论处,而应实行数罪并罚。”(注:参见张明楷:《刑法学》(下册),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586页。)换言之,“因逃逸致人死亡”是指第二次交通运输事故中致被害人死亡。也即“在交通肇事案件中,行为人的罪过心理态度常有发生转化的情况,即由过失转化为故意犯罪,常见现象如:肇事以后在行人较多的马路上逃逸,对撞死撞伤其他行人采取放任的罪过态度,结果在逃逸中造成新的伤亡后果。”(注:黄祥青:《浅析刑法中的交通肇事罪》,载《政治与法律》1998年第4期。)这一观点也得到其他学者的支持,如认为,“刑法第133条所规定的‘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含义是指交通违章肇事后,行为人明知被害人重伤,但弃之不顾驾车逃跑,致使被害人得不到及时抢救而死亡,或者在违章肇事后,为避免罪责,驾车逃窜,又第二次交通肇事致人死亡,应该分别作为交通肇事罪的结果加重犯和交通肇事罪的同种数罪定性处罚,对于逃逸过程中又介入故意的加害行为致使被害人死亡的则成立故意杀人罪,排除在刑法第133条规定的‘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含义之外。”(注:李晓龙、李立众:《试析交通肇事罪中的“因逃逸致人死亡”》,载《法学》1999年第8期。)
(3)对“交通肇事致人重伤后逃逸使被害人未得到及时救护而死亡的行为性质的认定”提出看法,并对如下观点:“被害人的重伤系由行为人所造成,行为人见危不救而置人于死地,这是一种故意的行为,具有放任的间接故意,因此,对逃跑的行为应单独定罪”的观点进行商榷而认为:“前述逃跑等思想状态是发生于肇事之后,是为逃避法律责任,属于罪后表现,所以不能以其犯罪后的态度而改变其前行为的罪过形式。其罪后逃跑行为不宜单独定罪,引起被害人不能抢救而死亡,可作为从重情节考虑。”(注:陈兴良主编:《刑法全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73页。)更有学者提出,“因逃逸致人死亡’的,逃逸行为是交通肇事行为的自然延伸,因而构成交通肇事罪的结果加重犯。(注:参见张波:《“交通肇事‘逃逸’”的定性分析》,载《中国刑事法杂志》,1999年第5期。)有其他学者进一步补充论述为,该种情形中行为人的行为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行为人的行为致人重伤已经符合交通肇事罪的基本构成要件;二是由于逃逸行为出现被害人因得不到及时救助而死亡的加重结果,逃逸行为与加重结果之间存在无前者即无后者的因果关系,是发生了基本构成以外的基于间接故意的加重结果,因而成立交通肇事罪的结果加重犯。(注:参见于改之:《不作为犯罪中“先行行为”的本质及其产生作为义务的条件——兼论刑法第133条“因逃逸致人死亡”的立法意蕴》,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0年第5期。)
《解释》第5条规定:“‘因逃逸致人死亡’,是指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情形。”从《解释》的规定而言,是对交通肇事后实施的“因逃逸”行为“致人死亡”的客观属性而言,并没有涉及行为人主观罪过形式问题。从“逃逸”行为的实施而言,无论行为人出于何种动机,“逃逸”行为是主动或被动,都属于故意脱离现场的行为,而不可能由“过失”构成。而且,表明仅仅属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行为不具有另行定罪的根据,只能作为交通肇事罪的量刑情节之一。由此区别于假意抢救而故意遗弃被害人,客观上同样表现为“逃逸”而致使被害人死亡、重伤的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根据就在于:必须符合《解释》第6条规定的,“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将被害人带离事故现场后隐藏或者遗弃,致使被害人无法得到救助而死亡或者严重残疾的”的情况。该规定,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理论界对发生交通肇事后,假意抢救而故意遗弃被害人,由于抢救失时而造成被害人的重伤、死亡行为定性的争论。
从《解释》的规定看,“因逃逸致人死亡”,只是涉及行为人“逃逸”行为的直接后果,而并不涉及其主观罪过的形式和内容。然而,应如何理解“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心理态度是“过失”还是包括“故意”?(注:参见胡康生、李福成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释义》,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52页;陈明华主编:《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22页;张明楷:《刑法学》(下册),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586页。)笔者认为,在前述学者的有关论述中,有将“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心理态度只限定在“间接故意”或者“过失”的范围的观点,笔者认为这并不符合司法实践中的复杂情况,对“因逃逸致人死亡”的罪过,不应作简单的理解,应当既有故意也有过失。(注:对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主观心理态度因为对于致人伤害是“明知”的,所以,不可能在“逃逸”情况下对死亡结果发生是“疏忽大意”的。)具体说,“希望”或者“放任”死亡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都可能存在。但上述结论建立在下述两点的基础上:其一,在逃逸过程中没有发生新的事故致人死亡;其二,没有实施假意抢救而故意遗弃被害人的行为。
首先,这里的无论是“过于自信”或者“希望”、“放任”死亡结果发生,并不是行为人在交通肇事行为之前或者在事故发生当时对结果的犯罪心理态度,而是事故发生后行为人“逃逸”行为时的心理态度,如果行为人没有上述两种情况存在,那么,这种“逃逸”而对被害人死亡结果发生的“过于自信”或者“希望”、“放任”的心理态度并不具有被独立评价的意义。其次,司法实践中,行为人在突发的事故面前,恐惧、胆怯、不知所措或者惊慌失措的情况是常见的,无论出于何种动机而从现场逃离,对于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可能性,行为人不是不可认识的。如果行为人根本没有发觉已经发生交通事故,即使是“应当预见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其脱离现场的行为也不符合“逃逸”。既如此,因何将因逃逸致人死亡”限制在只能由“间接故意”或“过失”(过于自信)的范围?其次,如果行为人既没有在逃逸过程中发生新的事故致人死亡,也没有实施假意抢救而故意遗弃被害人的行为,如前所述,在我国现行刑法中,除了特定的少数脱逃行为(如脱逃罪)外,尚没有对于逃跑行为单独论罪的规定。就交通肇事后的逃跑行为而言,主观上逃跑故意根本谈不到是一种犯罪的心理状态。如果因“过于自信”或者“希望”、“放任”被害人死亡即要作为构成新的犯罪予以评价,是不是有以主观论罪之嫌呢?由此,无论将行为人“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心理态度限制在“间接故意”或者“过失”心理状态,都是不够准确的。笔者认为,在立法对“因逃逸致人死亡”作为交通肇事罪的情节规定的情况下,这种心理态度无论属于故意还是过失,都不影响应属于交通肇事情节的意义。
因“逃逸”的客观情况也不一样,所以有必要对“因逃逸致人死亡”条件作如下分析:(1)行为人的逃逸行为必须发生在交通肇后,而且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已经认识到发生交通事故撞伤了人。只有在此基础上,行为人脱离现场的行为才谈得上是逃逸,如果证据证明确实不知道撞了人而继续前行的不能认定为逃逸。(2)被害人的死亡与行为人的逃逸行为之间必须存在着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即被害人的死亡必须是由于肇事者“为逃避法律追究”,不抢救被害人的逃逸行为造成的。如行为人交通肇事当场致被害人死亡后或发生死亡结果已不可逆转而逃逸的,因死亡与行为人的逃逸无因果关系,不属于“因逃逸致人死亡”;如因认识错误而认为已经死亡,但被害人确因行为人逃逸,挽救失时而死亡的,则不影响认定。(3)被害人死亡必须是由于逃逸行为造成的,其中并未介入其他行为,包括肇事者自己的行为和他人的行为,如果由于介入其他他人的行为,或者肇事者自己的行为,切断了重伤与发生死亡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发展,即使发生死亡结果,也不符合该规定。
至于是造成何人“死亡结果”,从学者的观点看,有认为是属于第二次造成重大交通事故而致人死亡,即是指造成其他人的死亡。笔者认为该种认识有些牵强。从《解释》第5条规定,“‘因逃逸致人死亡’,是指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规定看,显然这里的“因逃逸致人死亡”,非指“逃逸”行为再次发生“事故”而造成其他人死亡。
三、对《解释》有关规定的分析与评价
1.《解释》第2条规定:“交通肇事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其“情形”的第3项规定:“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在30万元以上的。”
根据刑法关于交通肇事罪的规定,因第133条规定交通肇事“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即符合构成要件,换言之,“或者”表明即使只造成财产的重大损失,同样构成犯罪,而这里的财产损失,是指直接造成的财产损失。《解释》第2条第3项也规定财产损失只限于“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从我国目前理论解释看,也是如此,如“在计算财物的危害后果时,只能计算直接损失,即因交通事故而损失的交通工具或其他财物的价值,或其修复的折价费用,而不能将间接损失也计算在内。”(注:陈兴良主编:《刑法全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71页。)而“无能力赔偿”又是一种什么概念呢?当然是指客观上不具有赔偿能力。而无能力赔偿的数额虽然不可能大于所造成的直接损失的数额,但是,完全可以等同于所造成的直接损失的数额。如果数额比较大而行为人倾家荡产赔偿了部分但仍然有30万元以上的损失无能力再赔偿;如果行为人有万贯家财,即使因肇事所造成的直接损失再大也毫不再乎,那么,这无疑传递给公众“有钱就能买刑”的观念。彭真早在5届人大2次会议关于刑法第7个法律草案的说明中就指出:“对于违法犯罪的人……都应当依法制裁。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不允许言行不符,不允许有任何超越法律之外或者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上述规定显然是与我们倡导的法治价值观、与刑法第4条“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的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相悖。因此,笔者认为,这一规定是不符合社会的法治精神,应当取消。
2.《解释》第5条第2款规定:“交通肇事后,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指使肇事人逃逸,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
共犯,也即共同犯罪人,在刑法中有广狭之分,狭义的共犯是指教唆犯、从犯(帮助犯);广义的还包括共同实行犯(正犯)。(注:参见马克昌、杨春洗、吕继贵主编:《刑法学全书》,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52页。)在我国现行刑法中,共同犯罪只限于共同故意犯罪,刑法第25条第2款规定:“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基于“共同过失犯罪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不承认它是不切合实际的,也是不明智的。”(注:侯国云:《过失犯罪论》,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版,第194页。)所以,上述规定虽然明显地与现行刑法的规定不符,实属越权解释,但是它的积极意义是应当肯定的。如果因为刑法没有规定而否定共同过失犯罪现象不恰当的原因就在于,这种社会现象并不是以法律是否规定而决定其客观存在与否。正因为如此,笔者对共同过失犯罪持肯定看法。(注:参见拙著:《犯罪过失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章第1节。)
不过,问题在于上述规定的过失共犯的行为,是在交通肇事后“指使”肇事人逃逸,而非共同的交通肇事行为,所以,只能认为《解释》规定的是指狭义共犯中的教唆或者帮助行为。理论上虽然对是否存在过失共犯肯定与否定观点都有,而且过失共犯的范围也有争论,但是,如果持肯定的观点,那么,从过失成立须具备违反注意义务为核心而言,共同过失是否也应当如此考虑呢?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过失共犯的行为是否可以包括教唆犯、帮助犯,是值得研究的。从以往我国刑法立法文献看,对于过失共犯曾经有过规定,但限于过失正犯的范围,如1928年《中华民国刑法》第47条曾规定:“二人以上于过失犯有共同过失者,皆为过失正犯。”理论上对过失持肯定态度的,也多认为限于在正犯范围内成立过失共同犯罪,如“在过失犯,行为之意思非不可共同,且过失并非无意识,虽认识犯罪事实,而不容认其发生时亦有可能。因此,在认识之限度内,意思之共同,亦有可能,即可采认过失之共同正犯。”(注:[台]郭君勋:《案例刑法总论》,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88年版,第495页。)再如,日本学者福田平教授就认为,既然存在着所谓违反客观注意义务的危险的实行行为,而在对此具有共同的意思并对该事实能够认识的情况下,是能够肯定过失共同正犯的存在。(注:参见[日]西田典之:《过失的共犯》载《法学教室》,有斐阁(日文版)1992年第2期。)
结合《解释》的规定具体分析,实施“教唆”或者“帮助”的行为人,无论出于何种动机、目的,主观上是故意的,即明知在事故发生后,肇事者应当实施救护,但故意教唆或者帮助肇事者脱离现场;客观上实施了教唆或者帮助行为,并且,正是因为其教唆或者帮助行为,使肇事者逃逸而造成被害人因抢救失时而死亡。其教唆或者帮助行为与肇事者的逃逸,以及被害人的死亡结果发生,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如从具有“共同罪过”的范围看,是“逃逸”的“共同故意”,而非“肇事”的共同过失;如从“共同行为”的范围看,是“逃逸”的“共同行为”,而非“肇事”的共同行为。即上述“共同犯罪”的犯罪限于“逃逸”的共同犯罪。这就产生一个问题,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在我国刑法中并没有独立的罪名和法定刑,何以认为成立共犯?更何况《解释》规定的是“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这就更使人不解。即使我们说交通肇事罪的共同犯罪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也只能认为行为人都负有防止违法结果发生的共同注意义务;行为人都具有违反共同注意义务的共同行为,导致违法结果的发生。行为的共同性就在于各个行为人都不仅自己没有履行注意义务,防止结果的发生,也没有履行使共同行为的其他人防止结果的发生的注意义务,主观的共同性就在于行为人对违反共同的注意义务具有共同过失。正是由于各行为人共同的作为或不作为,导致了违法结果的发生。换言之,交通肇事罪的“共同犯罪”应当发生于交通肇事行为实施的过程中,而不可能在交通事故已经发生之后,以主观上的“教唆、帮助故意”,客观上的“教唆、帮助行为”与交通事故已经发生之后的肇事者的““逃逸”行为,成立共同犯罪。理由如前所述很简单,在我国现行法中,并不具有对单纯“逃逸”行为明文规定的犯罪,更何况怎能够以事后的教唆或者帮助行为与前行为共同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共同犯罪”。
笔者认为,《解释》的这一规定,不仅从逻辑上说十分混乱,而且也是违背了刑法有关共同犯罪的基本理论,是不应当给以肯定的。
标签:法律论文; 交通肇事逃逸论文; 交通论文; 量刑情节论文; 逃避心理论文; 交通肇事罪论文; 刑法理论论文; 不作为犯罪论文; 法制论文; 刑事案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