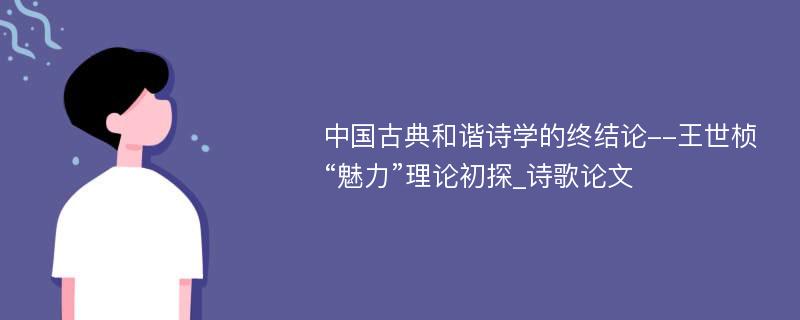
中国古典和谐诗学的终结理论——王士禛“神韵”说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学论文,神韵论文,中国古典论文,和谐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围绕王士禛“神韵”说的特征、审美趣味及其在中国诗论史上的意义展开论述,试图尽可能清晰地阐明渔洋“神韵”说的理论内涵,在论证王士禛对中国古代诗论的建树的基础上,剥去“神韵”说笼罩着的恍忽迷离的面纱,展示其对中国古代诗论的贡献。
主持清初诗坛数十年,且又被称作“一代正宗”的王士禛,论诗标举“神韵”,并因此在中国诗歌思想史上产生深刻影响。钱钟书先生《谈艺录》引郑朝宗先生说云:“‘渔洋提倡神韵,未可厚非。神韵乃诗中最高境界’。余亦谓然。”可知“神韵”说对诗歌理论发展的重要意义已渐引起注意。但何以人们又常非议“神韵”呢?这就涉及与“神韵”有关的一些理论问题。为了进一步认识“神韵”说在中国古典诗论发展过程中的意义,本文试图从历史和逻辑统一的角度出发,对王士禛的“神韵”说作些初步探讨。
一
“神韵”说的产生,当然与渔洋(王士禛号)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在清初的顺治、康熙两朝,从仕途上说,王士禛确实是一帆风顺的。他先后为官四十五年,累官至刑部尚书,且多次得到皇帝的垂青。康熙曾谕曰:“山东人偏执好胜者多,唯王士禛否,其作诗甚佳。”并屡赐书画,专为他写了“带经堂”、“信古斋”两匾额。因此,从袁枚开始,就不断有人认为,王士禛的“神韵”诗,不过是一种为清初皇帝装点升平的“盆景诗”而已,其所提倡的“神韵”说,也只是一种粉饰太平的诗论。
能否这样理解“神韵”说?我们不妨换个角度来看看,新城王氏一族,世为明代显官。王士禛的祖父王象晋,在明代官历二品,位居浙江右布政使。明亡后,以遗老身份隐居,自号明农隐士。其父王与敕亦因能诗文曾被举荐入朝。当明末清军犯山东时,王氏家族中就有过在一日之中数十人死于清军兵刃之下的记录。明亡时王士禛大约已十一岁,切肤的家国之痛,不致一点印象也没有。从王士禛早期的诗歌来看,经常地体现出这一点。如其《明神宗御书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全诗不加任何掩饰,大胆热烈地为明政权唱颂歌,表现自己对明政权的向往和景慕。再以其早期所写的《秋柳》四章为例。此诗向来被认为是王氏诗歌中极富“神韵”的代表作。其一曰:“秋来何处最销魂?残照西风白下门。他日差池春燕影,只今憔悴晚烟痕。愁生陌上黄骢曲,梦远江南乌夜村。莫听临风三弄笛,玉关哀怨总难论。”诗中所寓情感虽朦胧隐约,但在今昔对比中怀念南明,感伤朝代更替这一点,却殆无疑义。执着的故国之思,哀婉的沧桑之痛构成了《秋柳》诗的主题。联想当日的政治特点及王士禛家世,其对明清鼎革怀有这样的感情,原也无足为奇。也正由于《秋柳》诗的这一特点,无怪此诗一出,即产生极大反响,短短的时间里,“和者不减数百家”,由是亦奠定了王士禛的诗风,成就了他的诗名。所以,我觉得对王士禛所以提倡“神韵”,我们不妨作如下认识:即由于他从事创作始于清初,当日的政治特点不允许他公然和明确地表现家国之痛与帮国之思。但在另一方面,深沉的家国之痛又促使他不能不表现。因此,他只好借在对景物的描绘中,若明若暗,扑朔迷离地表现出内心的哀伤和失落,并因此形成其诗歌“清远”的“神韵”特征。其《香祖笔记》中曾有这样一段话:“释氏言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古言羚羊无些子气味,虎豹再寻他不着。九渊潜龙,千仞翔风乎?此是前言注脚,不独喻诗,亦可为士君子居身涉世之法。”我以为即透露出王士禛在清初企求全身避世,隐于朝廷的心曲。这一点,也许正成为渔洋倡导“神韵”的契机。
明清的鼎革,促成王士禛对“神韵”的倡导。然而,严格地说,“神韵”作为一种诗歌美学思想,又绝非王士禛首倡。清翁方纲认为:“诗人以神韵为心得之秘,此义非自渔洋始言也,是乃自古诗家要妙处,古人不言而渔洋始明著之也。”[①]早在六朝时期,我国画论中就已出现过“神韵”这一名称。南齐谢赫在《古画品录》中即谓:“神韵气力,不逮前贤;精微谨细,有过往哲。”如果说在谢赫的说明中,“神韵”与“气力”对应并举,还偏重于指艺术形象的神态、神情的话,宋元以后的南宗画派在讲“神韵”时更侧重于“韵味”,即强调绘画应有含蓄深远,意余笔外的超妙意蕴。如苏轼论书,讲究“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②]王世禛论画,推崇“妙契自然”的“逸品”[③]均是例证。以“韵”论诗,一般认为以北宋范温为最早。范温论“韵”曰:“有余意之谓韵”。“于简易闲淡之中,而有深远无穷之味。”[④]按范温所说的“韵”的意思,我们可以将论诗主“韵”的主张一直向前追溯到钟嵘。当然,钟嵘是用“兴”来说明“韵”的:“言已尽而意有余,兴也。”[⑤]从王士禛自己的眼光看,他明确表示:“余于古人论诗,最喜钟嵘(诗品),严羽(诗话),徐祯卿(谈艺录)。”[⑥]何以如此?即因钟嵘在《诗品序》中要求诗歌“言已尽而意有余”。严羽《沧浪诗话》中指出诗歌应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玲珑透彻,不可凑泊。”“徐禛卿《谈艺录》论诗重情致神韵,都与王士禛的主张颇有相通之处。
所以,论诗标举“神韵”,体现出前人传统在王士禛身上的承传。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我们还应看到,由于时代的差异,渔洋在谈到“神韵”时,又对前人传统有所发展。这种发展,主要体现于渔洋自称的诗歌“须以清远为尚”[⑦]这一点上。这也就是说,渔洋所谓的“神韵”,既不是如钟嵘所说的源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杨蛾入宠,再盼倾国”[⑧]的“言有尽而意无穷”,也不同于严羽所说的由“诗之法有五:体制、格力、气象、兴趣、音节。诗之品有九:高、古、深、远、长、雄浑、飘逸、悲壮、凄婉”[⑨]而形成的“入神”。而是须源于诗人对自然景物的深切感受,源于审美观照中由物我契合而形成的静穆和悠远。王士禛曾自述其赋《秋柳》诗的情状云:“一日会饮水面亭,亭下杨柳千余株,披拂水际,叶始微黄,乍染秋色,若有摇荡之态。予怅然有感,赋诗四章。”[⑩]这里清楚点明《秋柳》的写作,是由于诗人对景物静观默契的深刻体会。明湖秋柳的一片哀色,逗动诗人的审美情趣,使诗人沉缅其中而至物我两忘。猛然间,他忽然感受到这一片哀色中蕴含的深情与意趣,于是,诗人遂以此为契机,委婉深沉地感慨人生盛衰的无常,悲叹美好景物的飘零。诗歌因此显得自然隽永,淡泊清远。王士禛在《鬲津草堂集序》中进一步指出:“昔司空表圣作(诗品)凡二十四”,其中“冲淡”、“自然”、“清奇”、“是三者品之最上。”所以如此,从审美主体角度说,是三者体现出淡泊宽阔,超凡绝俗的胸襟;从审美客体的角度说,是三者又反映出不随流俗、孤高静穆的品质。王士禛有鉴于此,恰正是他遗民心态的真实写照。
应该说,为王士禛所标举的“神韵”说,确实抓住了中国古典诗歌美学的一个关键问题。中国古典美学从庄子开始,一直十分重视和强调审美中的主客两忘,心与道契的境界,并认此为审美之极致。“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11)在这种境界中,主客双方冥然一体,不可凑泊,无迹可求,已经初步接触到审美的特征。降及魏晋,玄学兴起,士人为全身远祸,倜傥放荡,潜心玄谈。由于以玄理月旦人物风气的盛行,人们重视玄学情调在形象中神形合一的风姿神貌,并将此称之为“韵”。《晋书·庚凯传》:“雅有远韵”。《郄鉴传》:“乐彦辅道韵平淡,体识冲粹。”《宋书·王敬传》:“敬弘神韵冲简。”《谢方明传》:“自然有雅韵。”等等,均足证此。而此所谓玄学情调,又主要指的是人物的闲淡、清远,通达、放旷等个性特征而言,所以时人称“韵”时,又常“雅韵”、“道韵”、“清韵”、“远韵”、“玄韵”连称。这也就说明,当时所谓“韵”,其实就是指形相中表达反映出来的闲淡、清远、通达、放旷之美。
盛唐王孟山水诗歌和南宋文人画的出现,标志着“神韵说”由月旦人物转诸于艺术创造。在这种艺术创造中,强调艺术家以高洁虚旷的胸怀,在与山水景物的审美观照中静观自得,并因此形成艺术作品中意境园融平淡含蓄,冲和通达的美感特征。苏轼评王维诗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闻一多论孟浩然诗“淡得几乎看不见人”,正指这种特征而言。由于这种美感特征体现了古典美学对和谐宁静的重视,所以在此后的中国诗论、画论,不断地展开了对这种美感特征和审美趣味的探讨。然而,由于种种局限,这种探讨总是沿着创作论的角度展开。例如,司空图《诗品》中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本来讲的是审美观照中的静观自得,乃“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之意,但在孙闻奎的解释中,却成了“纯用烘托,无一字道著正事,即‘不着一字’,非无字也。”(12)再如,讲究“言有尽而意无穷,”(13)“画有尽而意无穷”(14)本来也是古典美学很重要的一个内容,但在沈祥龙的解释中,却是“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其妙不外寄言而已”(15)。固然诗人静观自得的审美感受最终总是需要借助诗歌文字来表达,但无论如何,将物我相契的审美观照归结于某种修辞手法,实在不能说是理解了中国古典美学重视和谐肃穆宁静的内涵。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士禛以“清远”为核心的“神韵”说体现出它的精随所在。
渔洋所谓“不着一字”、“无迹可求”,云云即是说对于富有“神韵”的艺术作品,绝不能拘泥于外在的手法和形似特点去理解它,而应立足于作品的整体去感受与把握它的风神韵味。作品的风神韵味固难以言述,但通过对整体的审美观照,人们又可能确切地以体会及之。本此,对于艺术作品,渔洋极力推崇“逸品”。他所说的“逸品”,其实就是难以从表面形式上坐实其妙处所在,只能从心灵的审美感受中去把握其淡逸绝尘的意趣的作品。如郭忠恕曾“画天外数峰,略有笔墨,意在笔墨之外,”王士禛马上心领神会,赞曰:“得诗文三味。司空表圣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者也。”(17)又如相传王维曾画《雪里芭蕉图》,致招后人非议。渔洋对此颇不以为然,认为“古人诗画只取兴会神到。”(18)超越客观色相的粘滞,强调从审美感受中去领会艺术作品,正是“神韵”说的基本特征。也因此,对于作家的审美观照,渔洋借助禅宗参禅的体会,主张“禅悟”、“禅悦”。他说:“冯开之先生梦正(快雪堂集),颇得禅悦山水之趣,予少时极喜之。”(19)禅宗参禅,讲究的是一悟之后,万法俱空,只留下对真如本性的一缕淡淡的回味。这恰正与王士禛“神韵”说反对粘皮滞骨的看法颇有相通之处。要之,不拘于尺尺寸寸,强调通过对作品整体的审美感受,去领略那清远的味外之味,是王士禛“神韵”论的特点,也是他的高明之处。在王士禛之前的陆时雍,虽也论及“韵”在艺术作品中的生气贯注作用,他说:诗歌“有韵则生,无韵则死;有韵则雅,无韵则俗;有韵则响,无韵则沉;有韵则远,无韵则局。”本也不失为一种颇有见树的见解。但他接着又说:“物色在于点染,意态在于转折,情事在于犹夷,风致在于绰约,语气在于吞吐,体势在于游行。此韵之所由生也。”(20)可见其论“韵”仍局限于在表现手法上,未能就艺术作品作整体的审美把握。这也就是陆时雍虽也论“韵”,但却未能形成广泛影响的原因所在。
王士禛自学诗伊始,其兄士禄便教他王孟家数,加上他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造就了他冲和淡远的审美趣味和论诗“独以神韵为宗”的趋向。从中国古典美学的发展历程看,他既继承了自唐皎然、司空图,宋梅尧臣、苏轼、严羽等人强调诗歌的美感特征的诗论遗产,又有所发展侧重。在集古典“神韵”论的大成的同时,又体现了以和谐为特征的古典诗歌美学的终结。
二
王士禛以“神韵”论诗,并不意味着他对具体的创作论的漠视。相反,为提倡“神韵”,他结合自己的创作体会,对诗歌的创作论也作了许多颇有见地的论述,丰富了古典诗歌的创作论。
在对诗歌创作所作的论述中,为渔洋所最重视的,就是诗歌应有诗人的性情这一点。王士禛曾向人解释,他所以特别欣赏司空图《诗品》中“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原因在于:“此性情之说也。”(21)“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与“性情”二者有什么联系?原来在渔洋的认识中,诗歌无疑当然是性情的表现。但是,在富于“神韵”的诗歌中,这种表现却不能淋漓痛快,而应“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蕴籍含蓄,意在言外。”(22)
渔洋曾举李白《夜泊牛渚怀古》及孟浩然《晚泊浔阳望炉峰》两诗为例,说明富于“神韵”的诗歌的表现特点应是“色相俱空,正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画家所谓逸品也。”(23)不妨看看孟浩然的《晚泊浔阳》。这首诗看上去似写庐山,实则处处言情,表现诗人对曾在庐山住过的名僧慧远的仰慕及由此仰慕而导致的对超然物外的向往。正因诗人有此性情,故而诗人虽乍见庐山,但眼前所见景物都蕴含让人回味不尽的深长韵味。如诗歌的结尾“东林精舍近,日暮但闻钟”二句,诗人着意表现自己对慧远的怀念,但这怀念完全融入眼前所见的东林精舍故址与耳畔所闻的梵寺钟声,表现得一点痕迹不露,读者只能自己去领悟,去体味那悠然高远的言外之意。于此正见出“神韵”从这个意义上看,王士禛将“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解释为“性情之说”,颇有道理。它揭示了诗歌创作中有限与无限,理性与感性统一的义蕴。它要求诗人的创作不能直抒其情,而应以形写神,也要求读者的欣赏不拘滞于诗歌所描绘的有限形象,而应通过形象去领略清远含蓄的诗人性情。王士禛反复说明诗人创作应“词简味长,不可明白说尽”,“蕴籍含蓄,意在言外,”即是此意。
自来以“神韵”论诗者,都十分重视灵感的作用。司空图说:“情性所至,妙不自寻,遇之自天,冷然希音”,“真予不夺,强得易贫”。王夫之说:“以神理相取,在远近之间,才着手便煞,一放手又飘忽去,如物在人亡无见期捉煞了也。”(24)就这一问题来说,王士禛也不例外,他也十分重视艺术创作中“兴会神到”,“天然不可凑泊”的灵感。其《师友传诗录》曾这样论及灵感:“当其触物兴怀,情来神会,机括跃如,如兔起鹘落,稍纵即逝矣。有先一刻、后一刻不能之妙。”吴调公先生在谈到王士禛的“神韵”说时,曾指出:“王渔洋的神韵说虽说有其理论渊源,……而从他的创作构思说,首先得力于对‘眼前景’的深刻领会。”此论点出渔洋灵感论的独到之处。渔洋论灵感重在“触物兴怀,情来神会”,即突出了“眼前景”的触发特征,强调源于眼前景物的主体灵感情感产生的契机作用。如其七绝《寄陈伯玑金陵》云:“东风作意吹杨柳,绿到芜城第几桥?欲折一枝寄相忆,隔江残笛雨潇潇。”此诗之作,即因诗人偶然见到东风吹柳,猛然想起与陈伯玑分手之杨州桥头,又因之回忆起与陈的交往,遂忍不住起了“欲折一枝寄相忆”的念头,无奈此时风雨潇潇,诗人与陈之间相隔着一条大江。远处传来的残笛更衬得这种怀人之情如泣如诉。从全诗看,诗人抒发的情感都源自东风吹柳这一眼前之景的触发,由此“兴会”,诗人感受到杨柳的神韵,“绿到芜城”、“欲折一枝”、“雨潇潇”等皆从此生发,因此,全诗显得“天然入妙”,(25)“天然不可凑泊。”
强调由眼前景物形成诗人创作的兴会,看上去似乎创作机缘只在偶然之间,而无须诗人的苦学深思。其实不然。诗人要真切感受景物的神韵,离开日常大量的生活积累,无异于幻想。所以,尽管论诗强调“兴会神到”,但王士禛并不因此否认诗人生活积累的重要。他平生爱竹,为感受竹的神韵,他自谓:“予尝游吴、越、秦、蜀、楚、粤、韩、魏之墟,经行逾万里,所至遇人家竹圃,必造而观之。或见于山石荦确,川溪旷淼之间,未尝不停骖辍棹,徘徊移晷然后去。”(26)即说明广泛接触自然,使胸有成竹,然后方能体味其神韵。进而,在《师友诗传续录》中,他又指出:“诗歌创作“苦思自不可少。”在《渔洋文》中,他具体说明学诗途径道:“本之风雅以导其源,溯之楚骚,汉魏乐府以达其流,博之九经、三史、诸子、以穷其变,此根柢也。根柢源于学问,兴会发以性情。于斯二者兼之,又干之以风骨,润以丹青,谐以金石,故能衔华佩实,大放厥词,自成一家。”可见王士禛虽强调灵感的作用,但他并没有过分地夸大这种作用。作为创作之阶,他还是实实在在地要求从阅历、苦思、学养三方面入手。因此,他所谓的“兴会神到”原也并非飘渺虚无的空中楼阁。
渔洋“兴会神到”的艺术创作论还有另外一方面的内涵,这就是要求艺术形象应具“传神”的特征。王士禛在《花草蒙拾》中曾引程村说:“咏物不取形而取神,不用事而用意,二语可谓简尽。”讲究艺术形象的“传神”、“神似”,本来是中国古代艺术理论的传统。传晋顾恺之为人造像,于颊上益三毫,而形象愈见生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苏轼曾对此传统加以总结道:“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这里的问题是:怎样才能使艺术形象产生传神的特征?按一般的认识,传神、神似,是艺术家对生活形象进行万取一收式的典型概括的结果,但渔洋却将之归结为由诗人的“兴会”所致。渔洋这一认识是否是唯心的?我以为不能这样看。就艺术表现而言,形象的传神之处,总是诗人心灵与客观形象的契合处。诗人凭借其阅历、学养,再因“兴会”而唤起对景物山水的某一点的强烈感受,这正是形象“传神”的基础。陆时雍《诗镜总论》谓:“精神聚而色泽生,非雕琢之所能为也。精神道宝,闪闪著地,文之至也。”王夫之《姜斋诗话》云:“含情而能达,会景而生心,体物而得神,则自有灵通之句,参化工之妙。”都指出了这一点。如王士禛的《再过露筋祠》一诗,写诗人经过一农女为守节不入民宅借宿,结果被蚊叮露筋而死,后人为之所立之祠而产生的感受。诗歌的最后一句“门外野风开白莲”,向来被认为是王士禛写荷花而传其神的名句。单就此句来看,诗句并未具体刻划荷花,为何被视为能传荷花之神?这就须从全诗出发来考虑了。在此诗中,诗人先以白描对眼前所见景物以淡淡数语略作勾勒:“翠羽明珰尚俨然,湖云祠树碧于烟。”表现出一幅残月初坠时露筋祠景物的清淡风貌。在这背景的衬托中,诗人来到露筋祠。偶然的门外一瞥,他看到野风吹拂中的白莲。顿时产生兴会,溶情于物,对自然景物的赞美,对守节农女歌颂,种种情感猛地全部溶入这一片洁白的莲花之中,白莲也因此成为诗人此时种种情感的象征而传达出其内蕴的风神韵味,启人绵绵不尽的思绪,给人悠长无绝的回味。这就是这句诗虽未刻划白莲形态,但却得白莲神韵风致的关键所在。以渔洋诗歌中向被人称传神的句子。如“半江红树卖鲈鱼”、“绿杨城郭是扬州”等,大皆如此。宋张戒《岁寒堂诗话》曾评曹植“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说:“本以言妇人清夜愁思之切,非为咏月”,但正以此诗本为言情之故,这二句于无意之中遂成咏月佳句,“后人虽极工巧,终莫能及”,也说明中国古典诗歌美学“传神”论的特征。但渔洋以“兴会”来说明情感融贯的特点,较张戒尤见精确。
由渔洋论诗的这一立场出发,在论及艺术形象时,他自然否定诗人的创造为生活真实所局限,而要求诗人表现出超越生活真实的艺术真实,以臻传神之妙。其《香祖笔记》论画说:“郭忠恕画天外数峰,略有笔墨,然而使人见而心服者,在笔墨之外也。”《池北偶谈》论诗说:“世谓王右丞画雪中芭蕉,其诗亦然。如‘九江枫树几回青,一片扬州五湖白’,下连用兰陵镇,富春郭、石头城诸地名,皆寥远不相属。大抵古人诗画,只取兴会神到,若刻舟缘木求之,失其旨矣。”均可见出他的这一主张。他的诗歌在描绘自然景物时,也常因表现出自己感受中的真实,显得神趣盎然。如其《南海集》中的诗句:“长松吹细雨,水石共潇潇”(《招隐桥》),“朝来雷雨过,白日下飞龙(《青玉峡》)。”等等,都具这一特色。艺术家创造的艺术真实,虽然有时并不完全吻合生活中的真实,但它作为诗人感受的真实,比起生活真实来,往往显得更真实,更深刻,更传神。“若刻舟缘木求之,失其旨矣”,渔洋此见,不为无理。
提倡诗人表现感受中的艺术真实,并不意味诗人可以置生活真实于不顾。相反,它要求诗人更多地接触了解生活真实,从而感受自然景物的精神所在。中国古代以神韵论诗者,大都重视诗人对自然的感受,渔洋又岂能例外?王士禛自称有“山水之癖”,观其一生,不论在什么地方,总忘不了寻幽揽胜。其《东渚诗序》称:“远观六季、三唐作者,篇什之美,大约得江山之助与田园之趣者,什者六七。”王士禛的诗歌也大致如此。山水自然,给渔洋的神韵诗提供了丰富的题材与表现对象,渔洋也从山水自然中开拓出清远淡泊的神韵。二者的交相融贯,使得王士禛的“神韵”说具有较扎实的基础,不致流于空阔飘渺。试看王士禛的诗歌:“江干多是钓人居,柳陌菱塘一带疏。好是日斜风定后,半江红树卖鲈鱼(《真州绝句之四》)”“振衣清音亭,松柏鸣骚屑。坐对大峨峰,云销露残雪(《清音亭》)”。都以恬淡疏阔的笔触,表现出静穆悠长的韵味。诗人的性情融化在景物之中,景物因之带有清远的神趣。这类实践着王士禛“神韵”说的佳作,体现着中国古典诗歌创作艺术的丰富和发展。
三
当然,无庸讳言,“神韵”说也存在本质上的缺陷。
清初,尤其是在康熙时期,固然社会经济有所发展,人民生活相对稳定,但从整个封建社会的发展历程来看,应该说只是一个百足之虫临终前的回光返照时期。在这样一个社会主客矛盾空前激化的时期,“神韵”说不但没有认识这种尖锐的矛盾,反而在艺术创作中鼓吹清远淡泊,以求回避与逃脱现实,这是王士禛作为封建士大夫思想上软弱性的体现。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就这一点来说,王士禛的“神韵”说比起明代出现的李贽,公安派的文学观来,表现出了懦怯的退步。因此,尽管王士禛也许在主观上并没有想为清初的统治者粉饰现实,涂抹太平,但在客观上,其“神韵”说却能起到这种作用。王士禛及其“神韵”说受到清初统治者的欢迎,实非偶然。也因此,尽管王士禛及其“神韵”说在清初诗坛能独领风骚数十年,但当袁枚“性灵”说出现之后,其诗坛祭酒的地位就不得不让出了。
由回避社会矛盾这一点出发,王士禛自然排斥那些表现和反映社会矛盾的文艺作品。他借杨亿之口斥杜甫为“村夫子”,用司空图说贬元、白为“都市豪估”,就体现这一立场。前人多据此认为王士禛只认平淡清远之为诗美,而不知沈著痛快亦为诗歌之一种境界。其实不然。因渔洋倡导“神韵”,目的就在于回避社会矛盾与斗争,而慷慨激昂的沈着痛快,恰导源于诗人由社会生活而得之深切体会,认此为诗美,岂不有违渔洋标举“神韵”之初衷?所以翁方纲《神韵论》中说:“有于实际见神韵者,亦有于虚处见神韵者,有于高古浑朴见神韵者,亦有于情致见神韵者,”这种“无所不该”之神韵,正是对渔洋所说的“神韵”的一种弥补。
尽管王士禛“神韵”说存在这一根本缺陷,但它全面总结了我国古典和谐诗歌美学的美感特征与创作经验,不仅在古代诗歌思想发展史上有其意义,而且在今天,也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之处。所以,我们又怎能在倒洗澡水的同时连婴儿一起泼掉呢?
注释:
①翁方纲:《神韵论》下
②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
③王世贞:《艺苑言》
④范温:《潜溪诗眼》
⑤钟嵘:《诗品序》
⑥王士禛:《渔洋诗话》
⑦王士禛:《池北偶谈》
⑧钟嵘:《诗品序》
⑨严羽:《沧浪诗话》
⑩王士禛:《菜根堂诗集序》
(11)庄子:《齐物论》
(12)孙联奎:《诗品臆说》
(13)袁中道:《淡成集序》
(14)方薰:《山静居画论》
(15)沈祥龙:《论词随笔》
(16)王士禛:《分甘馀话》
(17)王士禛:《香祖笔记》
(18)王士禛:《池北偶谈》
(19)王士禛:《居易录》
(20)陆时雍:《诗镜总论》
(21)王士禛:《香祖笔记》
(22)王士禛:《蚕尾续文》
(23)王士:《分甘余话》
(24)王夫之:《姜斋诗话》
(25)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
(26)王士禛:《苍雪轩诗集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