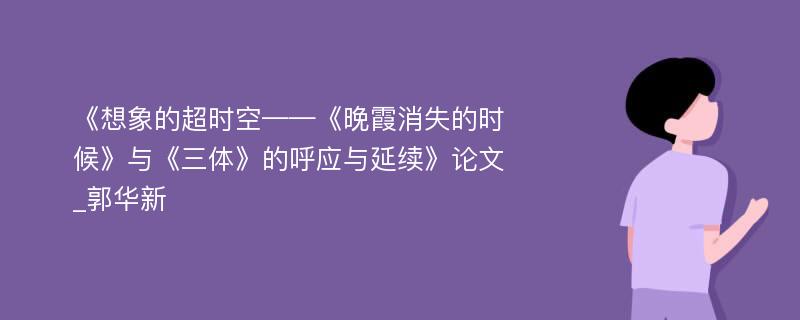
摘要:由礼平在80年代创作的《晚霞消失的时候》与新世纪科幻小说名著《三体》产生了若有似乎的联系,二者都是借对文革往事的伤痛叙述来展望未来。虽然二者在叙述角度和叙述时代背景上凸显差异性,但都殊途同归地对新时代的诞生做出遥想。本文将从分析二者中皆出现的忏悔意象,形成对时代背景的再解构和再解读,同时强调“想象”对塑造新时代与人类共同体在“未来”叙事中的重要性,将个体反思建立在历史的庞大废墟之上,以带给当下崭新的启示。
关键词:忏悔;想象;时空
《晚霞消失的时候》(以下简称《晚霞》)是以男主人公李淮平的视角来叙述他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当时的李淮平是一名普通在读的中学生,父亲是参与过“国共内战”的将领,政治背景可谓根正苗红。在时代大背景的召唤之下,他成为了红卫兵小将当中的一员,飞扬跋扈,坚决信奉“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抄了国名党招安将领楚轩吾的家,也带给南珊一段难以磨灭的伤痛回忆。
毋庸置疑的是,作为主体经历者的李淮平,将“文化大革命”在自我认知中定义为一场充满疯癫的政治运动,而时过经年,他仍然对自己曾参与其中感到忏悔不已。从他在参与抄家的过程中,“我身上的军装,我臂上的袖章,我所处的位置和身份,以及这大举查抄的严厉场面,都使我获得才不久的那种冲天的,然而虚伪的正义感和使命感迅速地复活起来。”其中消极修辞的使用可以看出李淮平当时就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带来巨大的伤害,然而无论是个人的虚荣感也好,还是对红卫兵信条的盲目追求也好,种种原因驱使着他最终完成了抄家。而时光如梭,他在顺应知识分子“上山下乡”政策乘坐火车时又碰到了南珊一家人,这时他抱有的态度依然是忏悔。“激烈的思想斗争和感情上的悔恨使我真想遽不及防地走到他们面前,庄严地道个歉,然后马上走掉。”甚至在十二年后与南珊重逢,他的态度仍旧是“从那天以后,我的心再没有一天平静过,真的,没有一天!⋯⋯”。李淮平对国家历史以及个人经验的态度符合80年代的“伤痕叙事”文学主流,诉说着十年浩劫带给国家和个体的伤痛。正如福柯在其《疯癫与文明》一书中谈到“激情是疯癫发生的基础,疯癫的可能性也就隐含在激情现象之中”。一代中国人随着历史的车轮义无反顾地投身共产主义革命,而在这压倒性的激情面前,理性不再是疯狂的对立他者,而是与政治正确划上了对等符号。而经历过文革的作家们往往在回溯时,也不能理解自己当时做出的选择,因而将其解读为异化和疯癫,随即产生忏悔和反省的情绪。然而,文革的产生是建立在历史合理性之上的,其中背后形成的发展长河特定阶段的客观存在条件和必然性依据不容忽视。如果《晚霞》就此停留在李淮平对时代驱使的个人行为而感到忏悔,小说就沦为一部典型“伤痕小说”,而《晚霞》的可贵就在于,小说最后借南珊之口发出了对历史的反思与对文明的呼唤。南珊回答是:“真想不到,你把那些微不足道的事情看得那么沉重。……毕竟,你是抛弃了自己的一切在为理想而奋斗,虽然它并不正确”;南珊认为“并不需要任何的抱歉和悔恨的表示”。南珊的话语突破了文革中造成伤害者与被伤害者的立场对立藩篱,而是争求处于历史漩涡中,每一个个体存在的合理性。如果说《晚霞》以李淮平在少年时代与南珊会面谈论诗歌文学为序幕,逐步展开了人性被摧残和践踏的“启蒙叙事”的话,南珊的话就完成了二次对李淮平的启蒙,同时完成了对新历史主体的建构。
而在《三体》中,天文物理学家叶文洁的父亲叶哲泰被严厉批斗,红卫兵们放肆地殴打他,而母亲也在批斗中亲自站出来指认了父亲,叶文洁自己也惨遭迫害。在这一篇名为《疯狂年代》的章节中,最初就为读者们展现了一幅政治意识形态凌驾于一切伦理道德之上的混乱画面。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叶文洁的身份特殊:她是右派之女,同时也是文革中地位极其低下的知识分子,与《晚霞》中的南珊属于同一阶级。而本要在大兴安岭劳改的她因为出色的天体物理学知识储备被选入“红岸工程”,从此改变了命运。
经历过文革的叶文洁,在《无人忏悔》这一章节中又再次与打死父亲的红卫兵见面。而三个红卫兵面容枯槁,甚至有人在百日大武斗中失去了双臂,而有人已经淹死,她们都成了历史废墟的见证者,身上承载着一部分的时代残骸。“你们不该忏悔吗?”那谁对我们忏悔呢?”这一段叶文洁与红卫兵的谈话无形中与《晚霞》的情节产生角色转换上的呼应:由伤害者李淮平向受伤害者南珊发出的忏悔请求遭到南珊的拒绝;而《三体》中,确是由受伤害者叶文洁期待的忏悔与道歉遭到了伤害者红卫兵们的拒绝。而这次与红卫兵见面恰恰是叶文洁在阅读了《寂静的春天》后,对人类文明彻底失望,已经向更高阶的三体文明发出了介入请求。
不管是伤害者的一方(红卫兵们),还是受害者的一方(南珊),他们都拒绝了忏悔,其原因大致为其中一名红卫兵所说的:“听到了吗?是历史!是历史了!现在是新时期了,谁还会记得我们,拿咱们当回事儿?大家很快就会忘干净的!”忏悔来源于对历史的唤醒,是一种不断对过往进行追究和反思的机制,是拉近过往与当下的手段之一。而如果人们对历史已经逐渐遗忘,忏悔便无存在之合理性,且不论忏悔者有无诉说之意愿,当世已无聆听之对象。“忏悔”在《三体》与《晚霞》叙述主体中的刻意缺失,恰恰说明了两位作者都在着力塑造历史与新时代的断裂感和被遗忘感。旧的阶级主义已经被解构,新的人类共同体正在产生。“与过去激烈的断裂”带给人们对崭新时代的渴望;在《晚霞》中,是人类的谅解和携手带来新文明;在《三体》中,是由对抗三体文明入侵而催生出的新文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提到:“知觉到自己深深植根在一个世俗的、连续性的经验——这样的知觉,引发了对“认同”的叙述的需要。” 但如果一旦对某一时代的认同感不再是必须的,“遗忘”自然就起了效用;无论是《晚霞》还是《三体》,都选择遗忘伤痛,然后将信心放在了更远的未来。
综其所述,《晚霞》与《三体》都是通过设置历史情境来讲述历史,通过个体经验,由“小历史事件”着手去讲述“大历史时空”。两部小说达成了“去政治化”的历史写作风格,着重于个人体验发出对十年浩劫的控诉。“文革”作为《三体》中一个重要的情节推进事件,《晚霞》中也是以这一场历史事件为叙述轴心,虽然占了颇大篇幅,但小说的核心仍在发出对未来的展望。在这点上,《三体》可看做是《晚霞》的延续,完整地展现了想象中的未来时空,甚至这未来不再仅仅关乎于中国,而是与整个宇宙密切相连。罗辑在《三体》II中参透的宇宙黑暗森林法则,实际上也是在隐射当今国际政治下下大国博弈、弱肉强食的社会现实。外部高智慧生命对地球的入侵正似地球内部大国对小国的压迫和社会主流力量对弱势群体的压迫。虽然和平与安定是世界的普遍渴求,但人类自身依然动乱不休。《三体》和《晚霞》都通过逆向思考权力斗争下历史的颠簸无定,突出与反思国家事件,而着眼全人类的命运。
参考文献
[1]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 =Imagined communities 吴叡人译.[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2]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刘北成 杨远婴译.[M].三联书店,2016.
[3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4]吴叡人.思想记忆与认同——为《想象的共同体》翻译之序[N]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5]洪子诚.读作品记:《晚霞消失的时候》[N].中华读书报,2016-03-30(013).
论文作者:郭华新
论文发表刊物:《知识-力量》2019年8月29期
论文发表时间:2019/6/10
标签:红卫兵论文; 晚霞论文; 历史论文; 文革论文; 共同体论文; 政治论文; 上海人民出版社论文; 《知识-力量》2019年8月29期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