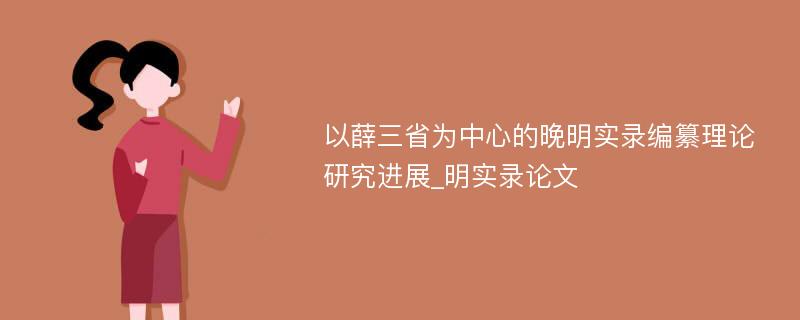
晚明实录编纂理论的进步——以薛三省《实录条例》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录论文,条例论文,理论论文,中心论文,薛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实录是由国家出面组织编纂的政府编年史,一般一帝一史。实录的编纂,自梁朝至清,有近1500年的历史。20世纪以来,学术界出了不少成果,推动了实录体的研究(注:有关研究成果概况,详见钱茂伟:《实录体起源、发展与特点》(《史学史研究》2004年第2期)及谢贵安:《明实录研究·引言》(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明实录》是研究历代实录“最早且最完整的标本”(注:谢贵安:《明实录研究》,第90页。)。80年代中期,华中师大等单位组织编纂了大规模的《明实录类纂》,这可以看作是《明实录》史料价值的应用开发。《明实录》从编纂以后,一直只有抄本,没有正式出版的定本。台湾地区的学术界将《明实录》制成电子版本上网,这是一件有意义之事。对《明实录》编纂的研究,目前以武汉大学谢贵安教授为权威。谢贵安参与了《明实录类纂》工作,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写成博士论文《明实录研究》。此书1995年收入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的“大陆博士文库”。《明实录研究》无疑是吴晗《记明实录》之后最为权威的研究《明实录》的专著。谢贵安精通《明实录》本体资料,《明实录研究》充分展示了这方面的特点(注:谢贵安教授正在进行“中国实录体史学研究”,200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通过《明实录》本体资料,确实解决了不少问题,这是此书的一大贡献。
近二十多年来,笔者一直关注明代史学的整体系统研究。《明实录》既是明代官方史学的代表,同时也直接制约着当时的民间国史修纂活动,自然是我十分关注的对象。初步的研究成果,见于《明代史学的历程》(注:收入“东方历史学术文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出版。)。历史研究要重视扩充新史料,解决新问题。明人上千部文集,无疑是搜寻新史料的宝库。最近,笔者在重新阅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明人文集时,从《明神宗实录》副总裁薛三省的《薛文介公文集》中找到了完整的《实录条例》。对照台湾地区影印本《明神宗实录》,正缺凡例。这篇条例,不同于吴晗《记明实录》所收《明宣宗实录·修纂凡例》,也不同于谢贵安《明实录研究》所收《明太宗实录·修纂凡例》,理论水平更高,自然也更值得研究。
本文拟以薛三省《实录条例》为主,再结合其他相关几篇资料,对晚明的实录编纂思想、规则,作更为深入的考察。
一、薛三省与《神宗实录》的编纂
《明实录》的修纂,是明朝官修史书的主要项目。明代惯例,老皇帝死,新皇帝立刻要修实录。天启元年(1621年),神宗、光宗先后逝世,熹宗继位,允辅臣之请,纂修祖宗实录。三月,下令组建班子,修《神宗实录》。张惟贤监修,叶向高、朱国祚等七人为总裁,顾秉谦等十二人为副总裁。
《神宗实录》纂修难度较大,“朝家故事,湮废者多”(注:周宗建:《周忠毅公奏议》卷一,转自吴晗《记明实录》。又略见《熹宗实录》卷八,天启元年三月己酉。)。有鉴于此,这年三月,御史周宗建在汇总朝野诸臣意见基础上,上了《请修实录疏》。该奏议主要提出了七点设想:
(一)主张分地采访,“臣请于中行仪部中,择其博雅端详者,分地而往,务令幽遐之壤,孝子贞女,逸士高流,悉讨其实,纳之囊中。而又问询故老,核之名家,悉录其书,以备闻见”。
(二)立专官,“方今承明著作之庭,虽称济济多才,而学有专门,事难兼习。如星历、乐律、河渠三项,非藉讲求,终难虚课”。
(三)求野之宜公,主张乘修史之机,统一传闻之讹。“请悉收其书,明为订辨,务令野之所信,合于朝之所征,墓谀无灵,齐谐息影。”
(四)查邸牍,主张仿《武宗实录》例,将万历朝留中之奏疏,宣付史馆,“使感时慨论者既得尽见,而任情附会者毋得轻淆,以正今日之公是公非,达皇祖之不闻不见”。
(五)入传人物不论官品。“臣谓史以褒贬人伦,岂论显晦?若令一遵官级,将高门跖、桥亦书,寒退者夷、鳅并屈,以此垂后,何益劝惩?则请大僚而下,倘有奇节特行,不妨并为序次。间有大谗大秽,亦复著其情形,蕙葹并列,衮鉞平悬”。
(六)编次有期,主张照万历初年修实录例,严立程限,不准史臣“乞私差而图自便”。
(七)总裁专职化,“今请略仿万历初年,责令总裁分年专任,示以划一”(注:周宗建:《周忠毅公奏议》卷一,转自吴晗《记明实录》。又略见《熹宗实录》卷八,天启元年三月己酉。)。
周宗建的奏议,得到了熹宗的重视。
据董其昌记载,天启初年,“礼部奉诏,移文海内,求岩穴佚才、有所纂述、可为实录用者。所司以闻于时,附丽而起者甚众。两都九卿之署,各自修志。志成,其秉笔者,各予官郡倅,或中书舍人。”(注:董其昌:《容台文集》卷八《沈高士公路墓志铭》。)这说明三个问题:其一是修实录开始之时,例向全国征求修史人才。其二是南北各衙门各自修衙门志。其三,修志也是升官资本。各部门志纂修者,都得到了不少职务。
天启二年八月,吏部推荐《光宗实录》纂修董其昌为《神宗实录》纂修,等到《光宗实录》成稿,前往南京采辑邸报、奏疏。十月,董其昌到南京。在南京方面官员支持下,抄得留中邸报、奏疏,装为三百本。“但据原本对录,以备史官取材征实,无所点窜,随蒙钦命”(注:董其昌:《荐李维桢修史疏》,见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三十二《翰林院》,转引自谢贵安《明实录研究》,第71页。)。这部书,有的称为《万历事实录纂要》。这正和薛三省的《移阁列实录条例揭帖》“凡奏疏留中而编纂所不及收者,近南都所抄录进在内阁者,亦已略备”记录相吻合。董其昌认为自己“有删繁举要之义”,觉得“兹四十八年之留中之疏,有事因疏而传,言不以人而废”,于是,复采留中之疏,切于“国本、藩封、人才、风俗、河渠、食货、吏治、边防,议论精凿、可为后事师者,别为选择,仿史赞之例,每篇系以笔断……共四十卷,目录一卷,别表进呈”。这就是传世的《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四十卷。董其昌回北京时间,各书不详。据实录记载,在天启四年四月(注:《熹宗实录》卷四十一,天启四年四月己丑,转引自《明实录类纂·文教卷》,第647页。又见董其昌:《容台文集》卷五《进神庙留中奏疏汇要表》,今有铅印本。)。
由于时局动荡、政治腐败,《神宗实录》修撰进程很慢。天启三年四月,熹宗下令吏部,要求翰林院请假、告病官员前来供职。薛三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我们视线的。由于现存《明神宗实录》没有修纂官,故纂修人员名单也成了难题。谢贵安的《明实录研究》经过深入研究,初步整理出《明神宗实录》总裁、纂修名单,这是一大贡献。唯因材料缺乏,故而仍有探讨之余地。譬如,副总裁薛三省,就不见于谢贵安所列《明神宗实录》的35位副总裁名单,仅见于纂修名单。
薛三省(1558—1634年),字鲁叔,别字天谷,浙江镇海(今属宁波市)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后守母丧,万历四十年复原官,后升左春坊春赞善、右谕德。万历四十七年,升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读。以兄三才卒,辞职回家。天启元年,即家起少詹事,兼原官。天启三年,升礼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协理詹事府。薛三省上疏辞,皇帝不允。天启四年夏,始赴任。“寻充经筵讲官,兼神宗实录副总裁,署翰林院事”(注:民国《镇海县志》卷二十四《薛三省传》。又见光绪《镇海县志》卷二十二。)。光绪《镇海县志》的薛三省传,据《神宗实录》另一副总裁李康先所撰《行状》及《明史稿》而成,当是可信的。此外,薛三省本人也提到了,如天启五年三月作的《催实录文册疏》“臣顷者叨掌院事,为诸史臣领袖,盖不胜陨越。草疏欲上,而适解院事,意谓可相忘于言;更念忝副总裁,倘实录或有未光,臣亦无所逃责”(注:薛三省:《薛文介公文集》卷三《催实录文册疏》。)。
地方志大体介绍了薛三省在史局中的情况:
“史局开已数岁,日费不赀,而业未及半。三省为条议,裁滥员冗费数千金。复手创实录总例,曰帝赞、臣传、提纲、事论、摘要、存疑,条凡六。实录分例曰大书、重书、特书、常书、数书、别书、最书、参书、备书、权书、直书、约书、原书、及书、不书、略书、凡书、附书,凡十有八。兼咨内阁检丝纶簿,其不及注起居与南都抄录所进,与疏留中而副在阁者,发史局折衷。又咨各部寺院监,据款查辑,送馆参订,以备六曹编纂之漏”(注:民国《镇海县志》卷二十四《薛三省传》。又见光绪《镇海县志》卷二十二。)。
关于薛三省兼翰林院事时间,方志仅称天启四年夏上升,“寻”署翰林院事,精确时间不详。成于天启五年的《催实录文册疏》有“昨秋,臣叨掌院事,更列款目,复行催趱”,则可以肯定,薛三省是天启四年秋兼任院事的。薛三省为翰林院院事,“为诸史臣领袖”,于是,具体负责实录条例的修订,作《实录总例》、《实录分例》、《移阁列实录条例揭帖》、《再论实录条例》四篇文章。
《明神宗实录》的编纂进程十分缓慢,到了天启五年,“迄今犹复如前,寂然不应也”。为此,天启皇帝对史馆成员的低工作效率提出了批评,天启五年正月,上谕“朕惟:史官无他业,专纂修为事。皇祖实录开馆至今已经五载,而未告成,虚靡廪禄,各官职守何在?以后俱著入馆编摩,不许私寓逍遥宴饮,亦不得给假乞差,以致出入无常,稽误大典。仍限按月送馆,其修成实录,一年两次进呈,务在早完。特谕。”(注:《熹宗实录》卷十五,天启五年正月癸酉。)这年三月,时已经升礼部左侍郎、不再兼翰林院事的薛三省,实在看不过去,考虑到“条例原发自臣,何敢终默然不竟初议”,“是用不嫌越俎,理牍上陈”(《催实录文册疏》),要求皇帝再次催促各衙门编纂文册。这年九月,薛三省升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侍讲经筵。十二月,因与魏忠贤不合,辞职回家,从此离开了实录编纂工作。而《神宗实录》编修工作,直到熹宗去世仍遥遥无期。崇祯元年(1628年),继续修《神宗实录》。在崇祯的督促下,修史进程加快。崇祯要求起用薛三省为南京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协理詹理府,兼《熹宗实录》副总裁。薛三省以病辞而不赴。崇祯三年十月,《神宗实录》进呈。至此,前后花了10年时间。薛三省等受到嘉奖,皇帝再次要求薛三省赴任,但薛三省再次推辞了;崇祯七年,第三次要求起任,诏令到宁波,而薛三省已卒月余,年七十七,赠太子太保,谥文介(注:民国《镇海县志》卷二十四《薛三省传》。又见光绪《镇海县志》卷二十二,乃据李康先所撰《行状》及《明史稿》而成。)。
与宋朝相比,明朝政府不太重视官修。明朝政府只对修《实录》还勉强重视,修正史不感兴趣,重修旧史更不感兴趣。如何看待这种官修的弱化现象?一般总将之归结为官修的腐败。我的看法相反,官修的弱化,是正常的事,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因为,政府毕竟是政府,有更多的行政工作要做;修史,说到底是学者事业,让政府投入那么多的精力来做这种事,是不现实的;过多依赖官修,对政府寄予很高的期望值,是一种错误的史学理念。政府有事实记载之责,档案保管之责;中国传统的左右史理念,应该从记载的角度来理解。至于修史,应该交由学者去做,政府不必代庖。把修实录当作国家大事来做,每次修实录要牵涉那么多现任朝廷高层领导,也只有中国才有的事。史官参与修史工作,有其长处,如了解朝廷情况,政治把关比较好。但也有其短处,官员大多是一些功利思想很重的人,他们不可能静下来修史。官场中的推诿、扯皮毛病,在修史工作中时有表现。政府只负责基础性的编年国史,放弃纪传体国史编纂大权,由学者负责综合性社会史写作,形成自然的社会分工,也许是一个进步。
二、广采故实,汇编文册
薛三省重视实录的资料搜集,重视实录的书法。天启四年作的《移阁列实录条例揭帖》,主旨有二,“广采故实,谨酌凡例,以便纂修”。
决定一部实录编纂质量高低的要素:一是材料,一是书法,一是史官。史料的丰裕程度,直接决定实录的编纂。“窃照国家之正史,取裁于累朝之实录,而实录之典故,又取衷于每年之纂注。起居注与六曹编纂,即实录之底草,实录又正史之成案也。故必实录慎而后正史当,纂注详而后实录备。若弗备,则无从加慎也。”(注:薛三省:《薛文介公文集》卷三《移阁列实录条例揭帖》。)这是从理论上说明,纂注是实录之“底草”,实录是正史的“成案”。
明神宗一朝的历史记录,问题较多。“我神宗皇帝临御多年,而晚年政事则不无少弛。夫政弛则官守易懈,而史氏之纂注,遂成率略。况年久则故迹故湮,虽朝章之要务,亦多遗忘。”(注:薛三省:《薛文介公文集》卷三《移阁列实录条例揭帖》。)万历朝有起居注,但十分简略。万历朝起居注官,主要的工作是编纂《六曹章奏》。“神宗时,阁臣始议开史局,以东西十馆密迩朝堂,纪述为便,乃以东馆近上四所,令史臣分直其中,一起居,二吏户,三礼兵,四刑工,日轮日讲官一员,专记起居,兼录圣谕、诏敕、册文。其《六曹章奏》,则选史官中年深而文学素优者六人分纂。因定常朝御门,日记注”(注:《钦定历代职官表》卷二十四。)。从《明实录类纂·文教卷》来看,从万历四年正月以编修沈渊、黄凤翔为起居注馆的编纂章奏官开始,一直到万历四十六年为止,中间隔几年换一批纂修官,一直没有中断过《六曹章奏》的编纂工作。《六曹章奏》是六部上奏的奏疏,问题是仅有奏疏目录还是抄录了全文?从“凡奏疏留中而编纂所不及收者”来推断,《六曹章奏》应该抄录的是全文,且是经过皇帝批文、下发的奏章。所谓“留中”,就是未经皇帝批文、自然也没有收入《六曹章奏》的奏疏。“二十余年之静摄,公车之言率归高阁;其所下六垣者,不啻十中之一”(注:周宗建:《周忠毅公奏议》卷一。),说明《六曹章奏》内容不全。《万历起居注》记录工作也基本保持了,但内容较为简单,已经失去了第一手记录的真义。“圣明之举明,半销于禁庭之秘;起居之职徒悬,风影之传失实。”“史局条章,因循且久;阁中之私记,仅托诸于执事之人”(注:周宗建:《周忠毅公奏议》卷一。)。内阁有《丝纶簿》,即条进稿底,“今起居注所不及注者,内阁《丝纶簿》则所具载”,这似乎是说,《丝纶簿》可以弥补起居注记录之不足。虽然政府有《六曹章奏》、《万历起居注》、《丝纶簿》,但要编纂出高质量的《神宗实录》,仅有这些是不够的,“自非今日先为广询博采,未免他日遂至挂一漏万,非所称一朝实录也”(注:薛三省:《薛文介公文集》卷三《移阁列实录条例揭帖》。)。
搜集材料之法,无非是“送进来”与“走出去”。官修模式,决定了史官搜集资料之法,必定要别人“送进来”,而不会自己“走出去”搜集资料。实录编纂,核心是解决政府各部门的文册编纂。纂修实录,主要依据现存的文册撰写;文册的编辑,直接影响了实录的编纂进程。薛三省也不例外,要求各级政府部门组织编纂各部部门志。“本院深惟,编纂虽有疏漏,六曹职掌,藏在副案,必不以年远而或至湮没。相应随诸曹所掌,移咨各部寺,分别款项,督令司官,逐年纂辑要略,类成一册,以移本院呈阁,随年分发副总裁官,转发各纂修官。即彼此先后互参,共为商略,亦一便也。其先经催取天下司府县册籍,以备纂修者,今当大计,政可携带前来。相应移咨原行衙门,及今行文督促定限,大计前完。其不完者,所当以怠缓示戒,仍刻期为限者也”(注:薛三省:《薛文介公文集》卷三《移阁列实录条例揭帖》。)。
要别人送进来,就会受制于外界配合程度。按理,编文册是修明政府历次修实录的惯例。“窃照累朝纂修实录,皆移文在京各衙门修辑事件文册,送馆参订,以备六曹编纂之所未备,此成例也。盖纂修实录,虽稗官、野史、邑志、家乘,皆所兼访,以备采择,岂以各衙门公牍而可或遗?”但因为实录编纂不涉及各部门利益,所以各部门积极性不高。“盖各衙门直视纂修为史局之事,不关其职掌,故了不经意若此。”《神宗实录》文册的编纂,就遇到这样的难题。天启三年前后,翰林院臣钱象坤、周如磐已经移文,要求各部门提供文册。结果两年过了,文册编纂仍无动静。于是薛三省再上《催实录文册疏》,基本精神也是催各部门提供史料汇编,“各衙门文册关系实录,且往可以补毁册、后可以务会典”。要求各衙门“专委属官,刻日分造,解送史官,以便纂修”。针对各衙门事不关己心态,薛三省动了一些脑筋,从文册编纂有利于会典编纂角度来相催促各衙门。对政府各部门来说,修会典与修实录不同。会典涉及各部门利益,自然积极。“实录与会典相关,会典又与诸司故实相关。会典不修者已四十余年,此必修之书也。修则各衙门必详备故实,先为草创,而后主者讨论润色,萃为成书。此时各衙门欲藉口于无存,恐无是法也。且会典所载,必证诸实录。今日实录所不收,他日会典将何所凭据!即今日实录所收,与他日各衙门故实稍有异同,会典又安所折衷!故今日文册,虽为实录,亦所以为会典。各衙门政非为史局代笔,实自为会典属草也。”汇编文册是苦差事,但又是一举三得之好事。“虑从败楮中翻阅精详,从冗牍中芟取要领,不无不费心目,诚人情所苦,然了一事而三事皆办,则暂劳者,乃所以永逸,又何烦之惮而不亟为纂辑也?”薛三省尤其强调各部门派专人负责文册汇编工作。“顾欲纂辑不可无专责……臣念各部院府寺皆多属官,其无属官者,掌印外,亦多备员堂印官,皆得推择。若皆如臣部选新进有才学者,专领其事,文册完日,即与咨递迁转,而吏部则少录其劳,有敏于事而竣者,虽一月亦准一年之资。如此,则既急向进而惜日,又冀累资而趋时,庶任事者人皆竞劝,文册可刻日立就。文册就而纂修有所取裁,实录亦可以刻期早完。不然,诸臣虽日进馆,而故实不备,终不免于阁笔”。
编纂实录,是政府行为,史馆完全是一种行政化的编纂机构,政府部门色彩十分浓。从薛三省奏疏可以看出,当时史馆修史,用的是上班制,史官每天进出史馆,纂修实录。由于纂修者都是官员,不会像学者一样,自己找材料,必须由政府各部门提供资料,才能顺利纂修。资料的来源:一是纂注,一是各衙门文册。实录的本质是政府史,所以更重视衙门之事。衙门文册汇编进度与质量,直接关系到实录的纂修进度与质量。而在官僚体制下,强调各尽其守。修史是史官职责范围之事,不是衙门职责之事,各衙门自然不肯积极配合。在以行政为中心的时代,一切工作,都是靠“红头文件”来办。皇帝与史馆总裁屡次催促,但效果并不明显,反映出当时官僚体制太僵化、以致政府文件失灵、指挥不动。
三、参用史法,谨酌凡例
凡例是集体纂修的基础。大千世界大得不得了,社会人物多得不得了,要记录的历史信息浩如烟海,人类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全部将之记录下来,所以人类的历史记录,总是一种有选择的记录。既然历史记录是一种有选择的记录,那么记录内容轻重缓急比例的确定就成了问题。选择是一种人为的主体选择,选择总是受一定的标准制约的,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选择标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标准。为了让人们明白自己的选择标准与思想,史家们总要制作一定的凡例,形成一套成文化的修史规则,这就是书法。对于集体修史来说,凡例是最为重要的。凡例是修史机构统一修史人员的行动指南,没有一定的凡例,就不可能形成风格统一的史著。薛三省自然也有这种认识水平:“至于纂修凡例,更为史官第一要义。此义不立,则编摩无法,详略任意,或当详而反略,或可略而反详,或详而致冗,或略而致疏,他日将过勤大总裁之修润,亦安取纂修者草创之为也?”(注:薛三省:《薛文介公文集》卷三《移阁列实录条例揭帖》。)凡例不当,选择不当,影响上面口味,自然是头等大事。
明代历朝修实录,都有一定的凡例,如经常提到的《明太宗实录·修纂凡例》、《明宣宗实录·修纂凡例》。今本《神宗实录》前面没有凡例,不知何故?不过,明代的实录编纂规则比较成熟,想来与前面的凡例相差不会太大。除此凡例之外,《神宗实录》的编纂还有副总裁薛三省提出的一套实录“书法”理论。
薛三省的实录书法理论,是建立在实录即史著基础之上的。薛氏认为,实录是史著,所以,应讲究史法。“实录既为史底,其比事属词,务当模仿史体。若起凡创例,更当参用史法,使事核文典,录成而无少纰缪。及今不失述而之旨,更词严指正,义具而有所折衷,将来可备作者之资,庶一朝之文献足征,而千古之笔削不爽。此副总裁者皆所留心,而本院谬与其任,更为悚惕者也。是用仰成大指,略取史汉之法,并寻《纲目》之义,拟为《凡例》数款,具列于后。伏俟裁定施行,须至揭帖者。”(注:薛三省:《薛文介公文集》卷三《移阁列实录条例揭帖》。)从薛三省话来推断,《神宗实录》编纂班子开工四年,虽有修史凡例,但显然没有“书法”理论。
薛三省拟定的条例,分《实录总例》、《实录分例》两部分,没有一个总标题。从“拟为《凡例》数款”来看,似乎称《凡例》。但《移阁列实录条例揭帖》、《再论实录条例》则称“实录条例”。为便于与政府实录凡例有所区别,还是将薛三省凡例称为《实录条例》为妥。
1.首次总结出实录编纂的总体书法
薛三省的《实录总例》凡5款,文字不多,全文录于下:
帝赞,颂语也。大指在称功德,总举临御之大体规模,而略其细过小疵。万一圣德或有亏损,如日月之食而不可讳者,亦微词寓意焉。及后妃赞,亦略仿此。
臣传,小传也。主于定人品,少或数言,多亦不过数十百言。评目务当其人,毋过誉,毋曲讳,亦毋苛,毋褒采虚声,毋刺捕疑影,以失人之生平。其履历先后,具于录中,不必复叙。若有异绩,则直云在何官时。其为某科甲,则不可略也。
提纲,揭大纲也。每遇大事,以大义裁之,提于其首,后详其事之始末,与议事之异同。若案牍之有朱语,则大意自明也。
事论,断国事也。凡事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论,而论于事始,或淆于是非,论于事后,又易掩于成败。自非究极其端末而熟察其事情,则一时之臆断,未必足千古之定案。如使剿取异同之说,又无贵论矣。
摘要,采其大要也。如条议实可以施行者,章疏实有稗益者于中,则饰其要而芟其繁。然亦有不必可行而议论必不可不存者,亦复删削载之,不没其大指(注:薛三省:《薛文介公文集》卷三。)。
关于实录总例,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据文集,总例只有五条。但地方志称总例有六条,多“存疑”一条。“存疑”见于《再论实录条例》第一条,或许是后来补上的。“存疑,非《春秋》阙疑之谓也,盖万历间事亦多变矣。如初年则有怀刃入宫门者,真王大臣乎?真谋逆乎?真某以刃授之,欲阴行其毒乎?末年又有从狱中上书告变者,真王日乾乎?真宫戚咒诅乎?即如持挺入东宫者,真谋太子乎?真有主谋乎?然又俱无从辩其非也。盖四十余年之事,亦不止于此,故特拟此例,欲存所疑,以传信于后也。”
第二,《实录总例》可以明了实录体特点。谢贵安教授讲到实录体例,称“《明实录》并非简单的编年体史书……是一部融进了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典章制度体等多种体裁风格的史著”(注:谢贵安:《明实录研究》,第90—91页。)。这个观点大体是对的,但须进一步完善。这五条原则,实际上揭示了实录体的特点。从这篇总例来看,一部实录的写作,要注意帝赞、臣传、提纲、事论、摘要五个基本方面。每一个方面的编纂、写作、评价,都有明确的要求。显然,君臣是主角,皇帝与大臣有简传,写作分寸的掌握十分要紧。实录体例有点类纲目体。奏疏摘要。大事有结论。
2.规范实录编纂具体“书法”
《实录分例》16款,又补2款,共18款。这篇分例篇幅较大,每一条都有详细的要求。
大书,“谓国之大事”;颂书,“谓经政足配帝王,宝训足当典谟”;特书,“谓重其事而书也”;常书,“谓寻常制度沿习者也”;类书,“谓事体相同而先后繁复不胜书者”;别书,“谓同事而分别以书”;撮书,“谓撮其大凡以书也”;参书,“谓参互并书,以见情实也”;备书,“谓国家有故典而不行,特借此书以备此制也”;权书,“谓衡量其事而书之,以寓微意也”;直书,“谓事本显直截以书,当否自见也”;初书,“谓事所创见,或有更旧为新者也”;原书,“谓本其事之所由而书也”;及书,“谓因此而及彼者也”;略书,“谓举其大略而书之也”;不书,“谓非所当书,与不足书者也”;凡书,“谓国家之典礼,所循习常行者,因此举此典礼乃有此仪注”;附书,“谓大事内之支事,本非所书,则因此而附见也”(注:薛三省:《薛文介公文集》卷三。)。
《再论实录条例》16款,可以算是补充性文字,即对实录总例与分例书法有异议或不明确内容,再次予以说明。由于内容较为琐碎,且是针对前面内部的某些条例展开讨论的,所以,不再予以抄录。
关于这个凡例,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这是一套历史书写理论。明代历朝实录编纂,都有凡例,如《明太宗实录·修纂凡例》、《明宣宗实录·修纂凡例》,特点是平列了五十多条。《神宗实录》开馆时,应该也有这个凡例,且是按常规凡例编纂的。薛三省的《实录条例》是开馆四年后提出的,完全按逻辑方式加以提炼,不同于常规凡例。常规凡例至多圈定了实录书写的边界,至于如何写,写到什么程度,并没有交代清楚。而薛三省的《实录条例》则进一步规定了实录书写的轻重缓急配置格式:文本仿佛是一种镜框,一个镜头,同时可摄进的历史内容有限,必须加以比例配置;文本的总篇幅,决定了历史记录内容的篇幅;历史内容的选择与历史内容的比例配置,两者功能不同,都是历史记录不可少的要素。
第二,薛三省的《实录条例》理论水平高于常规凡例。中国的实录编纂,到16世纪初期,有了近1000年的历史,理论化程度并不高。像明朝的常规凡例,也停留于就事论事阶段,严格说来,没有理论可言。一个学科理论思维的成熟标志,无疑是术语或概念的提出。《实录条例》才可以算是真正的历史书写理论。薛三省在研究历朝实录凡例基础上,对书法进行了形式上的归纳,提炼出了一系列的术语,形成了一套历史书写理论。《实录条例》高明之处,在于术语的提出,且有规范性文字解释。《实录条例》所谓18种书法,此前没有人提出过。如此细化,正是理论进步的表现。尤其有规范性文字解释。众所周知,传统中国学人,逻辑思维落后,擅长于譬喻,短于概念界定。《实录条例》于每一种书法术语,都有明确的概念解释,且有详细的事例加以说明,这就相当不容易了。
第三,薛三省的《实录条例》操作性更强了。从这个条例来看,实录书写方法,到了明朝已经相当成熟,完全格式化。把历朝实录编纂中积累起来的经验文字化、法则化,这是一大贡献。术语或概念是实践经验的理论化。有了详细文字规定,才有可操作性。操作性强,是历史书写理论的基本要求。这些书法格式,也有助于后人正确解读实录记录的深刻内涵。不了解实录书写成规,自然也无法透彻理解实录内容。
第四,薛三省的《实录条例》在当时有一定影响。方志有“议不尽行”一语,不知此话是针对文册编纂而言,还是针对实录条例而言。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条例在当时是有影响的,且有助于后人阅读理解实录书写成规。《实录条例》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薛氏在历朝实录编纂经验基础上提炼出来的。它是实录书写理论的总结,自然有助于后人理解实录的书法理论。
第五,薛三省的《实录条例》反映出晚明史学理论化程度的提高。讲究史法,是这个条例的特色所在。这恐怕是晚明叙事史学复兴的产物。明代前期史学,基本为理学化史学控制。唯一没有理学化的内容,就是正史、实录编纂。嘉靖以后,晚明史学开始走出理学化史学,走向叙事化史学之路。在这个过程中,史、汉提供了理论与实践模式(注:详见拙作:《明代史学的历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14—216页。)。薛氏条例显然吸收了史、汉记录格式理论,这是产生薛氏条例的学术基础。同时,在形式上,显然也模仿了朱子《纲目凡例》。详细罗列修史凡例,正是《纲目》的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