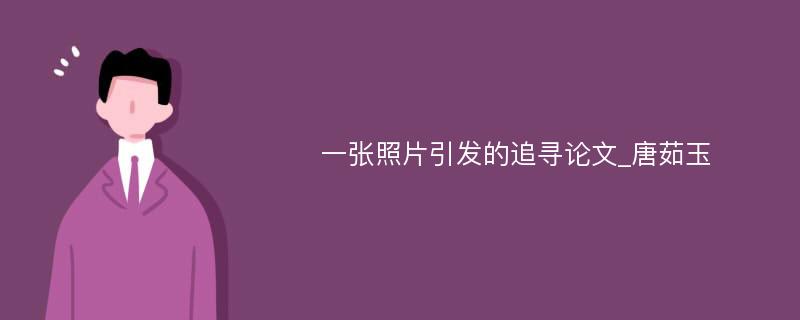
——读《顾颉刚日记》及其他
唐茹玉
瞿秋白纪念馆 江苏 常州 213003
史料是认识历史真实最重要的依据,所谓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史料挖掘得越充分越彻底,今人对历史的了解方能越接近历史真实。阅读人物自述、日记等史料,对于了解历史人物之间的交集和关联,明辨历史的真相,还原人物本真,自感大有裨益。
发现一帧秋白“新照”
2014年,偶读《郑振铎传》,作者在描写1923年10月10日,上海一品香酒家郑振铎婚礼时,配有当时所摄婚礼照片一帧,是新婚夫妇郑振铎、高君箴、瞿秋白、一位男士、两位伴娘和两名小花童的合影,都身着盛装,甚是隆重热闹。
这帧照片之所以引起笔者注意,原因有二:一是因为它是瞿秋白生平影像资料档案中未被发现过,又多了一个真实的瞿秋白形象,增加了一份感性的认识;二是这帧照片拍摄的时刻隐含着一个动人故事。郑振铎婚礼前一天,发现母亲没有印章,按照当时“文明结婚”的仪式,结婚证书上必须盖上主婚人、介绍人、新娘新郎及双方父母的印章。郑振铎知道秋白篆刻技艺精湛,马上请人送信给秋白,请他赶刻一章。瞿秋白请送信人带回一张“秋白篆刻润格”便条,每刻一字都明码标价,如需急用,价格翻倍。郑振铎以为瞿秋白繁忙无暇,借故推脱。于是转求沈雁冰连夜赶刻救急。第二天一早,瞿秋白派人送给郑振铎一个红纸包,上书“贺仪五十元”,让郑振铎大为惊诧:“秋白何必送这样重的礼呢!”旁边的沈雁冰打开红包一看,原来是秋白刻的三枚印章,一枚是郑振铎母亲的,另外两枚是一对新人的,边款还刻有“长”“乐”各一字,按照秋白的润格,恰好是五十元。这份“重礼”,出人意料,顿时引得大家一阵欢笑。及至婚礼,瞿秋白发表一番诙谐幽默的讲话,又让宾朋捧腹不已,为婚礼增添不少喜庆气氛。多年之后,郑振铎等多位好友回忆秋白时,对这一桩雅事仍描绘得有声有色,如临其境,足见秋白的高才与风采。
“秋白表弟”是谁
对于瞿秋白的粉丝来说,但凡关于瞿秋白的,哪怕是一句话,一个字,都是极为珍视的,并总带有探究一番的兴趣。细看这张照片,问题来了:瞿秋白身旁站着的那位年青男子,是否为当日的婚礼司仪顾颉刚?带着这个问号,笔者购得洋洋六百万字的《顾颉刚日记》 [1],以期寻找到顾的有关记录。
身为历史学家,顾颉刚每日记录起居、读书、写作、公务、家事、会友、聚餐等等,精细至极,用词简炼,而在有所思处也会洋洋洒洒尽情抒发。对于郑振铎的婚礼,顾当天日记提及一句:
“与履安(顾妻——笔者注)到振铎处看新房,与履安到一品香贺振铎、君箴结婚。……予为司仪人。”
求日记不得,笔者又搜集数本有关顾颉刚的传记、自述,将瞿秋白身旁的男子比对顾颉刚摄于1924年的相片(《顾颉刚自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1月出版),脸型和五官都不像,可以断定瞿秋白身边的不是顾颉刚。
在阅读《顾颉刚日记》过程中,又有新的发现,令笔者眼前一亮。1923年顾颉刚日记共提到“写秋白信”10封:
9月17日,“姑母来,为秋白表弟欲移居事。”
9月22日,“秋白来谈”,“与秋白、伯祥到新开松鹤楼吃饭。”
11月29日,“与秋白同室。”
11月30日,“为秋白集孟姜女故事史料”……
顾颉刚有个“秋白表弟”,此“秋白”是否“瞿秋白”,却是闻所未闻。
复从日记开篇逐年翻阅,1924年上半年,顾颉刚日记录“写秋白信”又5封。1924年11月4日的秋白来信,令笔者欣喜万分,几乎要认定这就是瞿秋白了——
“秋白来信,以喜期在迩,嘱寄喜联。予实不能书联,下笔恐怖,笔力既弱,又大小不均,勉作十字,曰‘乔木莺萝茑,蒹葭倚玉枝’。”
1924年11月,正是瞿秋白与杨之华结婚之期,但为何瞿杨都未说起此联,难道二人此次结合特意低调?顾颉刚日记未有对“秋白”其他事项的记录,无以证实“秋白”究竟为何人。此时,只有继续追踪下去:1925年“写秋白信”3封,1927年8月30日“到鲁弟处,并晤秋白”。循着见面时间的线索,查《瞿秋白年谱详编》:(瞿秋白于)“1927年九月底返沪。”[2]顾、瞿见面时间对不上。此时刚开过八七会议,在白色恐怖之中,瞿秋白担负党的领导重任,似乎不大容易访亲会友。直到1929年4月11日顾颉刚记下“秋白表弟自沪来”,得以确定此“秋白表弟”不是“瞿秋白”,此时瞿秋白远在莫斯科,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不能“自沪来”。一桩追寻化为泡影,欣喜落空,而转念一想,也极合情理,若瞿秋白是顾颉刚表弟,为何所有人都未提及呢。
那么,问题又来了,这个“秋白”是谁呢?这个背影好像不曾转身,而越发教人想要一探其庐山真面目。只恨日记中寥寥数语,语焉不详。笔者同时翻阅《顾颉刚评传》《顾颉刚自传》《顾颉刚自述》等,全然无涉“秋白”。一天深夜,忽然想到“秋白”与顾颉刚曾共同商讨过“孟姜女史料”一事,试着搜索百度,终于在一篇研究论文中找到答案:
“同年冬(1923年——笔者注),《上海文学》周年向他约稿,顾氏因预备北行而无暇动笔,只好把收集的材料交给表弟吴秋白(立模),写成《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一文,发表于《星海》上。”[3]
真相大白,释然。
追寻获得最有力的启发
二十多天的查阅,虽无更多有关瞿秋白的信息,却让笔者走近了一位史学大师。余英时作《顾颉刚日记》序言以“未尽的才情”为题,道出顾颉刚一生之才情皆有其憾:建国后其史学、民俗学方面的奇才,“硬生生”的由“海洋”被逼成“一条溪流”,再无超越《古史辨》之作;其挚爱谭慕愚女士,从1924年在颐和园望见她第一眼起,到最后的日子,终其一生魂牵梦萦,从未结合,也从未放弃。这些让笔者对这位严肃的大师产生更多的亲近感。读他的日记,好像听着他絮絮言谈每日行止、思索与苦闷,也凸显着他身上的独特魅力——“真”,这是顾颉刚为人之本,用情之根,傲骨之核。
顾颉刚给予笔者最有力的启发:
“如果我们要求真知,我们便不能不离开了人生的约束而前进,所以在应用上虽是该作有用与无用的区别,但在学问上则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的结果,而不是着手做学问的目的。”“我敢于大胆作无用的研究,不为一般人的势利观念所笼罩。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4]
顾颉刚做学问,只求真实而不计眼前功利,“所以特别爱好学问,只因学问中有真实的美感,可以生出我的丰富的兴味之故。”[5] “我们若要有伟大精美的创造,必须任着作者随了自己的嗜欲和兴会而发展,愈不求实效愈可得着料想不到的实效。”[6]顾先生说的有道理,做学问如果先定功利成见,以之裁剪史料,削足适履,势必曲解史实,写成伪史,遗害甚大。
其巨著《古史辨》震动当年中国学术界,是受胡适“典范”启示的产物。顾晚年因人所共知的原因,推说自己在学问上更崇拜王国维而不是胡适;1926年后即与胡适疏远了。依余英时所论,顾早年受章太炎影响,却数年不谙门径。直到1917年听胡适讲中国哲学史,耳目一新,才有豁然贯通之感。又读胡适考证井田制度和《水浒传》的著作,掌握了治史的方法,才有《古史辨》的发轫。至于王国维,恰恰与胡适南辕北辙。1925年秋,王国维在清华讲授《古史新证》,正是针对《古史辨》而发。顾把王的造诣悬为将来努力的榜样,也是真话,但与《古史辨》无关。顾氏一生的学术工作,《古史辨》是他在胡适影响之下,其创造力发挥得最为淋漓尽致的时期。顾氏自谓:“《古史辨》中诸文,皆为余卅岁左右所作,才气横溢,一身是胆,今不如矣!”(1944.9.22日记)胡适亦颇贤之。余英时认为,“盖棺定论,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学术史上,顾先生的大名只能系属在胡适而不是王国维的谱系之下,是个不易撼动的结论。”[7]
活跃于学、政、商界的史学领袖
别人多称顾为“纯粹学者”,实则顾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曾与傅斯年、罗家伦等创办《新潮》,希望以新意识启蒙民间大众,后来有意“唤起第二次新文化运动”;研究民族史、边疆史,以激发民族意识,抵抗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的侵略。培养不少后起之秀,追随者日益增多。他以学术研究为根基,坚持普及文化知识于广大民众。1930年代后,创办通俗社(1933年)、主持边疆语文编译会、主编《文史杂志》(1941年),合办中国图书公司(1943年),无一不与他自己的学术文化事业密切相关。为了事业,他辗转活跃于学、政和商界,自信确已成为史学界的领袖人物。
有人说他是“学阀”,顾则希望以自己的学术建树与育才聚才之势,独树一帜,成为学界领袖,以推动史学的进步。傅斯年与顾颉刚,同为胡适门下两大弟子,却因个人性格、学术构想和抱负的不同,互争雄长,形同“学敌”终至分道扬镳。1940年代,顾之投入国民党的文化运动,也是为与傅争锋。尽管交恶,傅对顾的《古史辨》仍十分心折和珍惜。余英时对于这一场胡适门墙之内的纠纷评论说:“他们两人的友谊破裂虽不免令人惋惜,但分途发展的结果是中国现代史学呈现出一种多姿多彩的面貌,则是必须加以肯定的。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学术界存在着多元互竞的空间,这是一个无可否认的客观事实。”[8]
顾先生在学术与政治上都堪称活动家。中学时代,为实现“无政府、无家庭、无金钱”的境界,他曾加入社会党。生在内忧外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激起现代社会意识与民族救亡情怀,余英时说:“这是他的事业心的‘原动力’。”为了争取办刊办社经费,他于1936年加入国民党,并与之合作,发起“民众运动”。1941年7月13日,在教育部长陈立夫陪同下,到重庆黄山官邸谒见蒋介石谈经学,陈布雷在座。但他很快便发现自己不能适应“党文化”。在抗战大局下,他对蒋介石领导抗战,废除英、美等国不平等条约,使中国跻入“四强”之列,抱有敬意,承命撰写《九鼎铭辞》歌颂蒋氏是很自然的事(1943年)。“献九鼎”在解放后却成为顾的一条罪状,他在1950年所作《顾颉刚自传》中执意要“说个清楚。……当时国、共合作尚未决裂,共产党尚喊‘拥护蒋委员长’的口号,而废除不平等条约也未始不是共产党该庆幸的事,这鼎铭就使是我做也并不在今天犯罪。”[9]
顾氏的国家民族意识强烈,在日本投降后中苏同盟条签订,令他深为忧惧,认为苏联是继日本后侵略中国的可怕力量,斥条约为“帝国主义的复兴”(顾日记,1945年末条),是“认贼作父”(顾日记,1945年8月末条)。傅斯年公开支持中苏条约,说外蒙在历史上不是中国本土的一部分,顾斥之为“御用学者”“无耻也!”(日记,同上条)。对中共颇多非议,预感到“中国的巨变”势必接踵而至,他的“事业”也将天翻地覆,不知所终。
晚年的坎坷与梦幻
1949年鼎革之前,顾本拟携妻儿去国民党治下的广州,因亲友拖累未成。对苏联认识如故,对中共外交、内政亦有不少微词。1954年由上海到北京,被召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遂有对中共“感激知遇的心理”[10]。然而,当他把《顾颉刚工作计划》交给历史所党的领导人尹达,两个月后取回时,尹竟未看,而对顾以往几十年的工作,只评为“大而无当”。尹达对顾“一若征服者对被征服者”(1955.3.17日记),训斥顾说:“你是在上海等待蒋介石反攻大陆的,现在看我们的政权巩固了,你才肯来了。”[11]人生的新阶段,顾未感到兴奋,而只感到痛苦。他自比吴梅村在清初身降而心不降的无奈,以“文化遗民”自居。
政治环境如此,家庭环境更糟糕。顾妻张静秋原是国民党员,她与其兄雁秋有意竞选“国大代表”。前政权垮台,又欲携兄全家同去广州,依附国民党。镇反中,雁秋被捕,判刑12年。从此,静秋生活在极度恐惧中。为求得生存空间,静秋逼迫顾颉刚“进步”,以争取党的信任。顾被聘为全国政协委员,而未进入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行列,又遭静秋埋怨。顾为表现“进步”,在1958年的“交心运动”中有上乘表演,在民主促进会中交心570条,名列前茅。随后,又作歌颂韶山、颂毛公等诗。1963年12月26日,全家吃面祝贺毛七十大寿(1964年至1968年,每年毛生辰,顾都在日记上以朱笔书“毛主席生辰”)。然而,“文革”到来,把他的“进步”梦打得七零八落。家中人各自求活命,顾成为“文革”打击的“反动学术”,也成为家中妻儿求生的唯一障碍物,随时以捶打相加。
1966年9月11日,顾记下家庭斗争会的场面:
“静秋与潮、洪、湲三儿与予斗,静秋打予至五次。……
家中人与予斗……以我为‘反动学术权威’故,四儿皆不得为红卫兵,以是皆恨我,我每出一言,必受其驳,孤立之状可想……诸儿皆不与说话……在饭桌上,常瞋目斥余……”
1967年3月8日,又记:
“彼闻此言大怒,斥我不信群众,即要到‘文革’小组检举。予急谢失言,彼乃打骂不休。噫,以我之年与病,一死何足惜,但想不到竟死于静秋之手耳。”
顾日记中,记梦甚多。且多权威人士入梦,早年的如王国维、梁启超,当代的韶山冲与毛泽东。1967年6月8日,竟梦“毛主席来我家,温语良久,同出散步。”然而,幻境无常,在尹达高擎“史学革命”大旗的历史所不断遭批斗和张静秋为保命而打骂交至的恶境中,一切希望皆成泡影。所幸,他没有像王国维、老舍那样自杀,在“文革”噩梦中尚有主持《二十四史》标点工作之令下达,得以活到1980年,以脑溢血辞世。算是“善终”吧。
俱往矣,大师已远去,他的求真良知、深厚学问,钟情文化,心系世运,以其生命践信的情怀依然给予我们力量,他的学术成就惠及当今而远未过时。研读历史人物,翻阅历史档案,就是在温情与敬意中汲取,从和合与扬弃中把握,于沉潜与深思中领悟,抒写今天,创造未来。
参考文献
论文作者:唐茹玉
论文发表刊物:《文化研究》2016年4月
论文发表时间:2016/8/27
标签:胡适论文; 秋白论文; 瞿秋白论文; 日记论文; 中国论文; 笔者论文; 表弟论文; 《文化研究》2016年4月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