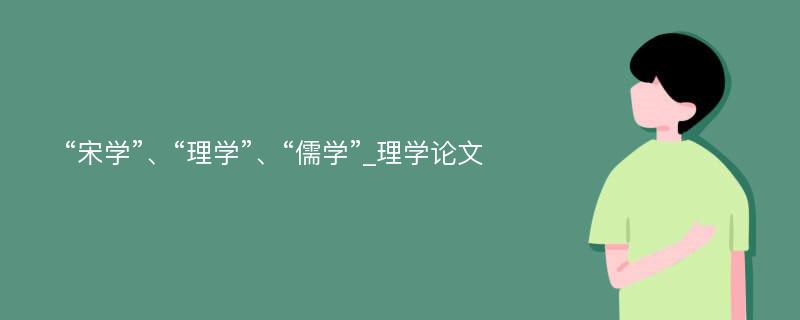
“宋学”、“理学”与“理学化经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学论文,经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宋学”形成的历史原因及其学术走向
清代乾嘉时期的学者从治学方法上将汉代以后的经学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汉学”,一类是“宋学”。汉学偏重训诂考证,宋学偏重义理诠释。但是,“宋学”概念并不意味有宋一朝的学术。北宋庆历以前的80年间,经学的主要成就是邢昺所主持修纂的《论语注疏》、《尔雅注疏》、《孝经注疏》等经书,这可以说是唐代孔颖达《五经正义》,贾公彦《仪礼注疏》、《周礼注疏》,杨士勋《春秋谷梁传注疏》,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义疏体经注的延续。它是汉唐经学的绪余,是“唐学”,而不是“宋学”。
“宋学”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我们以为应该从北宋庆历时期算起。北宋庆历以后,“学统四起”,义理之学勃兴,经学从此走上开新之路。这时,义理之学的概念是广义的,王安石、王雱父子所代表的“新学”,苏轼、苏辙兄弟所代表的“蜀学”,程颢、程颐兄弟所代表的“洛学”,张载、张戬兄弟所代表的“关学”,等等,都属于义理之学。因此,这些学派也都可以视为“宋学”。在这个意义上,“宋学”概念与“义理之学”概念可以说是等值的。
学者中常有人将“理学”概念与“宋学”概念相混淆。其实,“理学”可以说是“宋学”中的大宗,并不是“宋学”的全部。也就是说,“宋学”的概念较“理学”的概念外延要宽。“宋学”的下限一直延续到晚清。
“宋学”与“汉学”的治学方法有很大的不同,并且很难相互认同。这里,首先就有这样一个问题:以训诂之学为特点的“汉学”是如何转变到以义理之学为特点的“宋学”的?或者说,“宋学”形成的历史原因是什么?我们认为有如下几点。
1.经学发展的内在逻辑
任何一种学术,从其发展的历史过程看,都可以展现出一条内在的发展脉络和逻辑,如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先有汉晋儒者的笺注阶段:笺注以“简当无浮义”为原则。但由于此种注经形式并非字字皆加注,后人读经仍不能通晓经旨,于是进入南北朝隋唐儒者的义疏阶段:义疏以“详正无剩义”为原则,对经注作尽量详细明正的串讲和疏解。唐代孔颖达领衔修纂的《五经正义》作为官修经典,是对南北朝以来义疏之学的统一。此书一出,古来其他说经之书渐渐废而不传,可谓“一花独放百花摧”。儒家经学从此进入了一个“大一统的时代”,但同时也是一个思想僵化、扼杀生机的时代。经学要延续发展,必须从整体上经历一次创造性诠释的大转变,于是而有北宋庆历时期义理化经学的兴起。
2.宋代士人的担当精神
汉唐时期的学术,有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的说法。虽然孔颖达所主持修纂的《五经正义》以及后来续修的诸经正义成为当时钦定的科举考试内容,但官修经典统一思想的用意本身即在扼杀学术的自由发展。而与此同时,佛教中的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的兴盛,则标志着中国化的佛教在学术思想界已经有了压倒性的地位,以致许多儒家士大夫因歆羡佛教的精致哲学而皈依佛门。但与此同时,发展儒学以适应当代社会生活需要的呼声也日益高涨,这反映在宋初便是书院在民间社会的蓬勃兴起。
而儒学要复兴,首先应该起衰振靡的就是经学。北宋初,古文家柳开对于汉唐经师“不明理道”深感不满,因而一直抱有重新注解儒家五经、复兴儒学的宏愿,他常说:“吾他日终悉别为注解矣。”(《河东集》第2卷《补亡先生传》)孙复亦曾致函范仲淹,希望他上言天子,“广诏天下鸿儒硕老,置于太学”,重新注解儒家六经。(《孙明复小集·寄范天章书二》)重注儒家经典,这正是有宋一代儒者的宏愿与梦想。
3.宋儒所面对的时代课题
在我们看来,社会发展所形成的“时代课题”也是促使宋学形成的重要原因,甚至是根本性的原因。那么,宋代儒者面临哪些历史和现实的课题呢?根据我们的分析,主要有如下几项。
(1)五代时期的篡弑屡起、君臣之伦崩解所造成的历史阴影,使得宋世经学家刻意修复与强化君臣伦理。唐末五代,儒家三纲五常之道废绝不行,儒学完全失去了它维持世道人心的功能。如程颐指出:“唐有天下,如贞观、开元间,虽号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风。三纲不正,无父子、君臣、夫妇,其原始于太宗也。故其后世子弟,皆不可使。玄宗才使肃宗,便篡。肃宗才使永王麟,便反。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镇不宾,权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乱。”(《二程集》第1册,第236页)五代时期,武臣司政,篡弑屡起,欧阳修指出:“前日五代之乱,可谓极矣。五十三年之间,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国被弑者八,长者不过十余岁,甚者三、四岁而亡。”(《欧阳修全集》,第413页)
(2)北宋时期,辽与西夏强邻压境;南宋时期,宋与金南北对峙。两宋之世岁输缯币给西夏、辽、金,并且内部支出费用庞大,以致财政拮据,这使得宋世经学家刻意强调夷夏之大防,使得一些有为的政治家着意从经典中寻求富国强兵之方。如清儒颜元指出:“宋岁输辽、夏银一百二十五万五千两,其他庆吊、聘问、赂遗近幸又倍是,宋何以为国?买以金钱,求其容我为君,宋何以为君?又臣子所不可一日安者也。而宋欲举兵,则兵不足;欲足兵,饷又不足。荆公为此(按:指王安石变法),其得已哉!”(《颜元集》下册,第779页)
(3)在文化思想上,唐、五代以来佛教的兴盛恰与儒学的衰落成正比,许多士大夫到佛教那里去寻求心灵的安顿,这种情势促使儒家中的“豪杰之士”发愿创立儒家的安身立命之学。
对以上这些历史症结,宋朝的大臣们曾提出过许多具体的因应方案,我们且不去说它。学者为解决上述“时代课题”,怎样以注经解经的方式阐发儒家的思想原则,并从而引导学术发展的历史走向,这是我们所要探讨的。
首先我们来看,要解决上述“时代课题”,传统儒学有哪些文化思想的资源。对于“君臣纲常”与“夷夏之防”的问题,儒家经典《春秋》是一种很好的资源。而宋代的春秋学,从孙复、刘敞到胡安国都着力阐扬这两个问题。后世学者往往批评他们的春秋学深文周纳,有如苛法,而这正是宋代春秋学的特点。当时的经学家刻意强化“君臣纲常”与“夷夏之防”,乃是时代和现实课题的要求所致。孙复、刘敞是庆历时期的学者,那时理学尚未形成,胡安国虽然与二程多名弟子交游,且自称“私淑二程”,但严格说来,他与二程一系并无师承关系,他的春秋学继承孙复思想为多。二程与朱熹都不专擅春秋学,因此,从一种思想发展脉络说,宋代孙复、刘敞、胡安国的春秋学自成一种系统,只是因为后世理学家大多认同他们的学术思想,自然也将他们的春秋学纳入到理学的思想体系之中。
对于如何通过理财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儒家经典《周礼》似乎是一种较好的资源。熙宁变法,王安石以“先王之道”为号召,颁《诗》、《书》、《周礼》三经新义,此三经中言“先王”之语为多。王安石建立了作为官学的新学系络,这一新学系络在熙宁变法之后仍在学术思想界占据统治地位近60年。王安石新学的教训是:作为人文经典,本以解决人的价值观问题为其所长,而以解决现实的具体问题为其所短;宋代的财税政策改革牵涉到现实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以及许多复杂的操作技术,故如果不从现实实际出发考虑问题,而寄希望于经典文本的权威,这不仅可能无补于政策的制订与实施,反而可能损害经典的权威。而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不仅使政治改革至此止步,国势越发不振,也使荆公新学成为一种僵化的教条和既得利益者的护身符,因此,至南宋以后其学遂绝。而此后的学术将循着理学的路数发展。
对于士大夫及广大民众寻求安身立命之道的精神诉求,儒家经典《周易》和“四书”则是一种较好的资源。北宋中期以后的儒家学者立志要恢复和重建对儒家道德的信仰。从理论上说,当时所能采取的方式只有两种:一是将儒学转化成一种宗教神学,这条路在西汉时今文经学家们曾经尝试走过,没有走通;二是建构“道德”的形上学理论,找出具有终极关怀意义的超越理念,作为信仰的对象。
由此,周敦颐、二程、张载等人利用《周易》和“四书”的学术思想资源,建构了一种历史上称为“道学”或“理学”的学术思想体系。从表面上看,这是一种心性哲学的理论体系;而从更深层次看,则是一种理性化的道德信仰体系。但这种思想体系只有贯通在经典诠释之中,成为儒家经学的指导思想和灵魂,才能最终实现其理论的价值。因为传统教育是经典教育:一种流行的经典诠释著作,就意味着是一部社会通用的教科书。从这个意义说,儒家经学的发展至周敦颐、张载、二程兄弟的时代,开始进入了理学化的诠释阶段。宋代儒者大约经历了近200年几代人的努力,使儒学各经有了许多不同于唐及宋初官修儒家经典注疏的新的优秀注本。其中尤以二程、朱熹及其后学的经注最为著名。
二、“理学”在“宋学”中的大宗地位
北宋时期,以二程为中坚的“理学”曾长期与王安石所代表的“新学”相对峙,至南宋以后,“理学”逐渐在学术界占据支配地位,并成为“宋学”的大宗。“理学”何以成为“宋学”的大宗?在我们看来,理学相对于佛老的虚无主义与王安石的功利主义而言,采取了一种“中道”的路线,因为无论是佛老的虚无主义,还是王安石的功利主义,都在挑战正统儒家的“道德至上”原则。而理学家给自己提出的历史任务,就是要左手打倒佛、老“异端”的虚无主义,右手打倒王安石“新学”的功利主义,以重建儒家的道德信仰。
然而这一历史课题颇不轻松:一方面,当时佛、老之学的理论形态是一种“心性之学”或“性理之学”,而要战胜佛、老之学,就要建立足以与之抗衡的儒家心性之学或性理之学。另一方面,王安石变法的失败被归结为“学术不正”和“心术不正”。道学(理学)人物并不是一概反对功利,但他们认为,统治者的一切政治作为都应以“正心”、“诚意”为本;不以“正心”、“诚意”为本,而去求所谓“功利”,那就是“舍本逐末”。因此,无论从回应佛学挑战而言,或从反对功利之学而言,道学(理学)的开创者都感受到创立儒家心性本体论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正因为道学(理学)是因应佛老之学与荆公新学而起,所以,道学(理学)又同佛老之学与荆公新学有某种割不断的联系,甚至学术思想精神也有某些相似之处,这就引起后世学者的误解,而导致学术源流混淆不清的情况。为此,我们在这里有必要厘清以下两个问题:第一,道学(理学)的兴起与佛、老之学的关系;第二,道学(理学)的兴起与荆公新学的关系。弄清了这两个问题,我们便会看清理学的“中道”路线及其在宋学中的位置。
1.道学(理学)的兴起与佛、老之学的关系
在谈这个题目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传统儒学对待佛、老之学的态度。
佛教于汉代传入中国,其始势力较弱,并没有引起儒家学者太多的关注;待其慢慢兴盛起来,佛教文化与儒家文化便长期处在一种冲突与互补的矛盾当中。佛教有关轮回果报、天堂地狱之类的教义,对于一般民众而言,有劝善诫恶的作用,有助于教化。但佛教的兴盛也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比如大量兴建寺庙,耗费了无数人力物力;天下僧众日增,不仕不农,不工不商,成为社会的寄生者;佛教徒无君臣之道,绝父子之亲,严重扰乱了中土的政教秩序。这些因素促使一些儒者起而辟佛。韩愈是“辟佛”的健将,他提出要强令僧人还俗,焚毁佛典,改寺院为民居。这种主张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付诸实践并不能奏效,历史上三次重大的灭佛事件——所谓“三武灭佛”最后都失败了,正如北宋欧阳修《本论》所说:“佛法为中国患千余岁,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尝去矣而复大集,攻之暂破而愈坚,扑之未灭而愈炽,遂至于无可奈何。”(《欧阳修全集》,第122页)
佛教、道教作为与儒学长期并行的思想流派,本有其合理的因素与优长之处,儒学对之加以吸收消化,为我所用,并无不当,但当时儒者对此讳莫如深。我们以韩愈为例,韩愈在其所作《原道》中引《大学》之文,然后说:“古之所谓正心而诚其意者,将以有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第17页)他区分儒家与老、佛之道的不同在于:儒家是“正心而诚其意者,将以有为也”,佛、老之道是“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实际上韩愈在这里已经默认和预设了儒家和佛、老二教在“正心”或“治心”这件事上有相同点。
“道学”或“理学”从理论形态说,属于心性之学。道学家明确把“正心”或“治心”作为学问的根本。就此而论,道学家与佛教禅宗站在了相同的起点上。正统道学家如二程、朱熹等人创立儒家心性之学,其儒家的原则和观点是很鲜明的,其“辟佛”的立场也是坚定的。但是,对于佛教教理中关于人性的一些有价值的论述,道学家们也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并加以吸收。如程颐所作《明道先生行状》言及程颢曾“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二程集》第2册,第638页)。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言及张载曾“访诸释、老之书累年,尽究其说,知无所得,反而求之六经”(《张载集》,第381页)。他们特别于程颢、张载的学术历程中着此一笔,似乎意在告诉学者:张、程始求诸老、释之道而无所得,返求于六经之后而知大道之要。事实上,恰恰因为张、程曾“尽究”佛老之说的底蕴,所以在对儒学作创造性的理论转化时才能左右逢源。对此,南宋学者叶适曾有深刻的认识:“本朝承平时,禅说尤炽,儒释共驾,异端会同,其间豪杰之士有欲修明吾说以胜之者,而周、张、二程出焉,自谓出入于老、佛甚久,已而曰:‘吾道固有之矣。’……及其启教后学,于子思、孟子新说奇论皆特发明之,大抵欲抑浮屠之锋锐,而示吾所有之道若此。”(《习学记言序目》下册,第740页)问题在于,道学家们明明是吸收了佛学,却不愿坦白承认,反而用“吾道固有之”的说法加以掩饰,因而被佛教信徒指控为偷窃。如金朝李纯甫说:“宋伊川诸儒,虽号深明性理,发扬六经圣人心学,然皆窃吾佛书者也。”(刘祁《归潜志》第9卷)朱熹也有“伊川偷佛说为己用”之说:“近看《石林过庭录》,载上蔡(谢良佐)说伊川参某僧,后有得,遂反之,偷其说来做己使,是为洛学。某也尝疑如石林之说固不足信,却不知上蔡也恁地说,是怎生的?……但当初佛学只是说,无存养底工夫,至唐六祖始教人存养工夫。当初学者亦只是说,不曾就身上做工夫,至伊川方教人就身上做工夫。所以谓伊川偷佛说为己使。”(《朱子语类》第8册,第3040页)石林是叶梦得的号,《宋元学案》谓叶梦得曾助蔡京定元祐党籍,因此他攻击程颐“偷佛说为己用”之事未必可信,但朱熹的分析却颇值得重视。在二程之前,唐代禅宗六祖惠能已先倡导“主敬”工夫,如惠能说:“常行于敬,自修身是功,自修心是德。”(《坛经》,第65页)陈淳《北溪字义》说:“敬一字,从前经书说处尽多,只把做闲慢说过,到二程方拈出来,就学者做工夫处说,见得这道理尤紧切,所关最大。”(参见姜广辉,第325页)上引朱熹之言正说此事,他似乎认为程颐所倡导的“主敬”工夫并不是自家首先从经书中“拈”出来的,而是受启发于六祖惠能的“主敬”修养工夫。
在我们看来,二程洛学之所以能开此后数百年道学(理学)之风,而有别于传统儒学,正在于他们一面辟佛、老,一面又借鉴了佛、老之学,尤其是佛、老之学的“本体”与“工夫”的理论架构,开创了儒学的心性哲学的学术思想体系。
2.道学(理学)的兴起与荆公新学的关系
一般的学术思想史著作很少谈到王安石曾是“义理之学”强有力的倡导者,以及他对于道学(理学)兴起的前导作用。陈植锷先生所著《北宋文化史述论》指出,宋代之有所谓“义理之学”、“道德性命之学”等说法,推其原始,大都与王安石有关系。如南宋赵彦卫说:“王荆公《新经》、《说文》(按:指《三经新义》与《字说》),推明义理之学。”(《云麓漫钞》第8卷)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后志》卷二“《王氏杂说》十卷”条中引北宋蔡卞《王安石传》之言曰:“自先王泽竭,国异家殊,由汉迄唐,源流浸深。宋兴,文物盛矣,然不知道德性命之理。安石奋乎百世之下,追尧、舜、三代,通乎昼夜阴阳所不能测而入乎神。初著《杂说》数万言,世谓其言与孟轲相上下。于是天下之士始原道德之意,窥性命之端。”(转引自陈植锷,第225页)《靖康要录》卷五载钦宗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四月二十三日臣僚上言略云:“熙宁间王安石执政,改更祖宗之法,附会经典,号为新政……以至为士者非性命之说不谈,非老庄之书不读。”(同上,第226页)根据上述资料,陈植锷先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以“性命之说”或“性命之理”作为宋学讲求义理的内容,乃王学、洛学之所同。南北宋之交,王学和洛学,水火不容地斗争了100多年,直至理宗(公元1225年即位)时代以程朱之学的胜利而告终。自那以后,王学被排除在性理之学以外,而后者长期以来成了程朱之学的代名词。通过上述两家说法的比较,给王学也给宋学正了名。作为宋学内部的两个最大派别,王安石新学和二程洛学在“穷性命之理”或者说“窥性命之端”一点上,原来是一致的。(同上)
陈植锷先生发现王安石新学的前导作用,以及与程朱理学的联系,这是一个贡献,可补现代一般学术思想史研究之缺失。但他进一步的推论,却有混淆王安石新学与二程洛学之嫌。他认为,王安石新学和二程洛学在“穷性命之理”或者说“窥性命之端”一点上,原来是一致的。我们认为,对于王安石的“义理之学”或“道德性命之学”的内容及其水准,尚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儒家的“道德性命之学”虽然自宋代才兴盛起来,但早在《中庸》和《孟子》中已有过深入的探讨,此后讨论此问题的代有其人。王安石作《虔州学记》说:“余闻之也,先王所谓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王文公文集》第34卷,第401页)宋世“道德性命之学”的说法当从此语化出。由于王安石在当时的巨大影响力,我们相信,他的这一说法推动了“性命之理”的深入研究和讨论。
但从《王文公文集》来看,王安石本人探讨“性命之理”的文字并不多,并且在理论形态方面对前人也没有较大的突破。陈植锷先生关于王学与洛学在“性命之说”方面“原来是一致的”这一结论,是从旁人的评论中推论出来的;评论者大多是道学(理学)的局外人,他们把当时的学术风气皆归于王安石的影响,而没有看到这其中更有二程等道学人物的学术影响。如果我们更广泛地参考其他人的评论,那么当时及后世批评王安石新学为功利之学的声音要大得多,而“穷性命之理”或“窥性命之端”则更多的是与二程等道学人物联系起来。
持平而言,王安石变法对于科举制度的改革,可以说是儒家“义理之学”的初步胜利,它实现了儒者对于治学方向的调整与转变。作为一种“义理之学”,王安石新学较早注意到了“道德性命之学”的理论价值,但其学术的重心和焦点并不是“道德性命之学”的问题,而是当时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改革问题,它的现实政治目的性是很明确的。历史上将王安石新学界定为“功利之学”,应该说是恰当的。而正是在这一点上,王安石新学与稍后兴起的“道学”有明显的区别。二程所代表的“道学”,正如程颐《颜子所好何学论》所说:“凡学之道,正其心,养其性而已”(转引自陈植锷,第224页),其学问的侧重点是反观内省的心性之学;而王安石新学,则如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所说:“今世之所宜学者,天下国家之用也”,其学问的侧重点是经世致用的功利之学。两家之学的差别是很大的。
因此,对于王安石新学与后起的“道学”的关系,我们既要承认前者倡导“义理之学”的前导作用,同时也要看到两家之学的重要差别。后世学术史家不把王安石置于“道学”或“理学”的系谱中并无不妥。
这里再顺便讨论一下“义理之学”与“性理之学”的概念内涵及二者之间的关系。陈植锷先生将义理之学与性理之学当作宋学的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并将北宋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定为宋学从义理之学转向性理之学的重要标志,理由是:程颢、程颐兄弟15、6岁时即有求道之志,经过10年的摸索,方“知尽性知命”之理;嘉祐;占二年正是程颢26岁登进士第之年,也是程颐初入太学发表《颜子所好何学论》之年,在这篇文章中程颐明确提出了上引思想:“凡学之道,正其心,养其性而已。”
在我们看来,义理之学是从经学的视角来说的,是相对于汉唐经师的训诂之学而言的。大体来说,宋明儒者的经学著作都可以说是义理之学,并不以嘉祐二年为下限;而性理之学是从理学的视角来说的,凡以“性理”二字冠书名的如《性理字义》、《性理群书》、《性理大全书》之类,皆是指理学一类书。与义理之学相比较,性理之学较为晚起,但性理之学的概念出现后并没有取代义理之学,而是长期共存而各有所指的。
三、“理学化经学”的解释学特点
宋明时期的思想资料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经学家的经注类著作,一类是理学家的语录类著作。从经学史角度而言,只有经注类著作称得上“经学”,而语录类著作只能名之为“理学”或“道学”,而称不上“经学”。但在宋明儒者中,许多人既是理学家,又是经学家,一身而二任。如程颐、朱熹等人既有重要的语录类著作,又有重要的经注类著作;不仅经注类著作中有经学思想,语录类著作中也有经学思想,而且许多有思想闪光的经学观点恰恰是在语录类的著作中,因而他们的语录之书与经注之书不是能截然分开的。即使如此,我们这里关于“理学”的讨论,仍与一般的“理学”讨论有所不同,即我们不是侧重于“理气心性”的哲学思辨,而是侧重于理学家对儒家经典的理解与解释,我们称之为“理学化的经学”。这里我们所要探讨的是:理学化经学的解释学特点是什么?
我们以为,理学化经学的解释学特点至少有如下几点。
1.注重解决安身立命的时代焦虑
从根本上说,儒家经学的功用主要在于解决制度的焦虑和生命的焦虑。制度的焦虑和生命的焦虑是人类的两大焦虑。人类是以群居形态生活于一定的环境中的,其环境的好坏直接关系人们的生活品质,而环境的好坏主要决定于其社会制度是否合理,以及如何制定一个适应共同体文化传统的社会制度,实现长治久安,这是制度的焦虑。汉唐经学重名物制度,所体现的正是一种制度的焦虑。汉唐儒者致力于国家的礼制建设,五经自然成为礼制建设的大经大法,而随着唐代《开元礼》的修定,标志着君主专制国家的礼制已臻于完备。
随着佛教的盛行,很多人成了佛教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信奉者。这便使人们由制度的焦虑转向生命的焦虑。当时人们普遍在思考:人作为个体而言,其生命是短暂的,那么该怎样安身立命?如何把握永恒?若从宗教信仰方面考虑,人死之后灵魂会在哪里?灵魂能否得到安宁 ?若从意义信仰方面考虑,生命不能白白流淌,生命如何才有意义?这些问题都是生命的焦虑。宋代中期以后,儒者重视性命道德之学,所体现的也是这种生命的焦虑。
佛教“以山河大地为幻妄”,以为众生皆处在六道轮回① 之中;世人接受了这样的理论,便会这样理解世界的存在与人的生命存在。②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之所谓“存在”其实乃是一种“解释”。因此要清除佛教世界观与人生观对人们的影响,改变人们的生命状态,就需要一种有说服力的对“存在”的新解释,这就需要借助传统的儒家经典。然而汉唐经师对传统儒家经典的解释完全不能胜任这样的工作,这个工作由宋代的大儒们承担了起来。而宋儒首先要做的,就是重新发掘和认识儒家经典中的思想资源,并赋予这些思想资源以新的意义。因而对经典的诠释,归根结底乃是对人的生命实存的诠释。而宋儒中的不同流派从不同侧面对儒家经典的阐释,实际上都是在对世界存在与人的生命存在作一种儒家式的哲学阐释,以消除佛教世界观与人生观对社会的影响。
宋代儒者同传统儒者一样有深沉的忧患意识,但因为时代变迁,其忧患意识又有不同的表现。首先是忧患纲常被破坏:纲常被破坏会直接导致社会分裂,内战无已,民不聊生。唐末五代之乱,便是前车之鉴。宋代经学家强调“尊王”,其意盖出于此。其次是忧患社会生活的宗教化路向,反对将人类命运寄托于虚妄的鬼神,宋明理学家反对佛、道二教,其意盖出于此。第三是忧患人们单纯追逐物欲,如同动物,因而倡导有觉悟、能反省的精神境界,宋明理学家提出的“体认天理”、“致良知”等等,其意盖出于此。
总而言之,儒学毕竟与佛教不同:它是入世的,而不是出世的;它是此岸的,而不是彼岸的。儒者必须在现实的人伦日用生活中来解决其安身立命的问题。
2.先识义理,方始看得经
儒学原典中有许多概念和命题,宋儒往往将它们作为开放讨论的话题,从中阐发哲学的意蕴,用以建构新的思想理论,而其中权威的见解又被回输、吸收到新的经典注疏中。程颢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我们知道,一个哲学思想家虽然可能著作等身,但他一生的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可能就是他“体贴”出来的一两个概念或命题,并由这一两个概念或命题阐发出一套哲学体系来。“天理”概念涵盖性很大,可以用来整合儒学的其他许多形上学的概念,所以“天理”这一核心概念的发明,使儒学从此进入了一个理论思维大发展的时期。理学家建构“天理”论的思想体系,就是要人们用“天理”论的观点来看待自然、社会和人生。但根据古代社会人们的思维方式,一种思想观念只有贯通在经典解释之中,才能最终发挥其理论指导的价值。程颐说:“古之学者,先由经以识义理。……后之学者,却先须识义理,方始看得经。”(《二程集》第1册,第164页)对程颐此语,我们可以做这样的解读:后世学者只有首先成为一个理学家,才能成为一个经学家。理学家特别看重以理学思想对儒家经典作重新注释,这一方面是为了增强儒家经典解释世界、主导社会的理论力度,另一方面也是要通过传统的经典教育的形式传播他们的理学思想,因而宋明时期许多注经的著作中渗透了理学思想,而理学家的讲学内容也大多不离经学的主题。因此,理学与经学的关系变成了一种相互交叉的关系。在中国古代官定的注经著作中,经典与传注有这样一种关系:经典固然具有神圣的尊崇地位,传注亦因为钦定而具有准经典的地位。而且经文往往因传注而有其新的解释向度。在宋以后的经学中儒者已不甚关心经文的逐字解释,而更关心其中包含的哲学范畴和义理,像“理一分殊”这类命题,儒家十三经中本无其语,但当它被作为注文堂而皇之地写进注经著作中,而此一注经著作又被立为官学之后,这一命题实际上已经成了经典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3.争立“道统”——使解释体系成为信仰对象
从经典诠释的历史来看,有两大类解释:一类是陈陈相因的解释,所谓“集解”、“通释”之类的经典解释著作,虽然其中一些内容也不乏新意,但最多不过是前人注疏之学的集成;另一类是推陈出新的经典解释著作,如程颐、朱熹等著名理学家的解经之作,都具有解释体系整体改观的特征。这些新的解释之作所以能耸动人心,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它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但从另一侧面而言,它自身也必须具备成为信仰对象的“资格”,即要人们相信只有他们自己才是圣人之道的真正继承者,最典型的是儒者所发明的“道统论”,按照理学家的说法,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圣人相传之道,至孟子后千载不传,直至宋代周敦颐、二程、朱熹始接续“道统”。这种“道统论”具有“判教”的意味,它起初被作为“伪学”加以禁绝,后来则得到官方肯定,成为人们信奉的对象。因此,研究新的解释体系出现的原因,以及何以有的解释体系成为人们的信仰对象,而其他解释体系却未能成为人们的信仰对象,这是研究儒家经典解释学应予以特别关注的。
注释:
① 佛教所谓“六道轮回”,指地狱、饿鬼、畜牲、阿修罗、人间、天堂。
② 人们唯恐自作恶业,堕入地狱、饿鬼轮回道中,因而整日内心惶惧;这虽然有劝人为善的功效,但作为一种生命状态却是很低级的。
标签:理学论文; 宋朝论文; 王安石论文; 儒家论文; 经学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读书论文; 五经正义论文; 国学论文; 佛教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