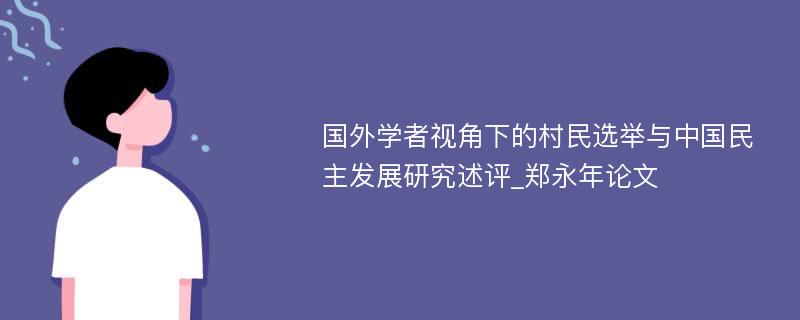
国外学者视野中的村民选举与中国民主发展: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中国论文,村民论文,视野论文,民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每逢村委会换届选举的季节,列队等候投票的中国农民形象就会在国外的大众传媒上刊登出来,正在行使民主权利的农民,似乎成了中国民主化的象征。以村民直接选举与自治为核心内容的中国农村政治改革与发展,成了近10多年来国外学者持续关注的学术焦点。由他们撰写的学术论文发表在国际知名的学术刊物上面,由此逐渐形成了这样的印象:比城市落后的中国乡村,仿佛成了民主的发祥地,被边缘化的农民似乎成了民主的“先锋队”。吴国光曾经提问到,作为中国民主化失败的一个例外,基层民主为什么在农村?为什么是农民?综观国外的中国农村政治研究,始终隐含这样一个主题,即中国的民主化有没有可能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有所突破?或者说,20世纪80年代初,农民以包产到户揭开了中国经济改革序幕,然后促使中国逐渐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么,20世纪90年以来的农民直接选举,会不会导致中国政治的根本转型?本文述评国外学者对这些问题的学术研究。
国外有关中国农村政治的研究成果,主要发表在The China Quarterly,The China
Journal,Modern China,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等有关中国研究的专门学刊上面。政治学的综合性学刊如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World Politics,Journal of Democracy以及Asian Survey等也经常发表这类研究文章。在国际学术会议、学术论文集中发表的相关论文也占有相当数量。在研究当代中国农村基层民主与治理等问题的学者当中,国际知名的主要有欧博文(Kevin O'Brien)、李连江(Lianjiang Li)、白思鼎(Thomas P.Bernstein)、戴慕珍(Jean Oi)、柯丹青(Daniel Kelliher)、史天健(Shi Tianjian)、墨宁(Melanie Manion)、罗伦丝(Susan Lawrence)、郑永年、何包钢等。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后,这些学者大多获得了与国内学者进行合作研究的机会,由他们组织的课题组可以在中国的许多省份选择实地调查地点,通过选举观察或访谈等形式开展他们感兴趣的学术研究。
综合起来,这些国外学者所关注的问题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选举与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二是村民选举的政治效应问题;三是村民选举与公民权利意识或民主文化的关系问题。综合这些前沿性研究所能给我们的启发,是这些研究究竟涉及了哪些关键性问题,并采取了什么样的理论框架和分析的概念。至于他们的分析结论,可以采取波普的证伪主义来检验。
一、村民选举与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
以村民选举为动力的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究竟同村庄的社会经济发展有什么关系?学者们对这个问题的假设性回答主要有:
1.农村民主选举更容易在集体经济比较发达的农村获得成功。例如,欧博文认为拥有效益良好的集体企业的富裕村庄提倡村民自治比较容易,因为集体经营得法、村民从中受益的农村,村干部靠经济业绩赢得了村民的钦佩,不怕选不上,而且选举能够加强他们的权力合法性(O'Brien,1994)。何包钢和郎友兴根据他们在浙江农村的调查,发现经济发达的村要比经济落后的村的村民选举竞争激烈。一方面,村干部职位报酬有吸引力;另一方面,竞选人之间的攀比拉票,使竞选者和投票者都活跃起来。而且经济条件好,不仅使村委会选举更加顺利,而且更便于开展日常工作。他们得出了一个很有启发的结论:经济发展对村民选举的影响属于“强相关”因素,而民主是否促进经济发展属于“弱相关”因素(何包钢、郎友兴,2002)。这就摆脱了民主选举与经济发展的简单对应的关系。笔者近期参与的一项对广东基层民主建设实践的研究(李江涛、郭正林、王金洪、李大华、童晓频,2002),揭示出发达农村的村委会选举,竞争更激励、拉票方式也更多样化,结论似乎支持第一个假设。
2.农村民主制度往往在经济落后的村庄首先建立并发展起来。例如,罗伦丝根据其在河北农村观察发现,以农业为主比较贫穷的村庄通过村民选举而产生的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成了迅速改变村集体经营面貌的动力。由此,她认为不是经济发展而是制度创新促进了政治发展(Lawrence,1994)。邱越伦的分析也支持这种观点,他认为经济落后的地区会更加认真地实行民主选举,以促进经济发展并巩固贫困农村的政权基础(Choate,1997)。与这个观点相一致的论点认为:集体经济发达的农村,民主改革反而难以推行,村民选举面临重重阻力。例如,戴慕珍根据他在江苏和广东的实地观察,发现经济发达村庄的实际权力如财权一般都掌握在村支书手中,村民选举和自治制度并没有提供任何保障村支书权力的制度措施。因此,处于这个职位的人就有可能利用现有的权力资源来控制村委会选举,降低政治风险(Oi 1996)。在后续研究中,她和罗斯高认为,相对封闭的农业村比相对开放的工业村更适合民主的村民自治,村委会有可能成为村庄的决策中心(Jean Oi & Rozelle,2000)。
3.民主发展同经济水平是曲线相关,不是简单的反比或正比的关系。坚持这个论点的学者有爱泼斯坦(Amy Epstein)和史天健等。爱泼斯坦认为,能够为村民带来物质福利的村民选举,会激发农民参加投票选举的热情,民主发展同经济水平呈曲线相关。史天健以实证研究的方式部分地验证了这个假设(Epstein,1996)。史天健在49个县和85个市抽取的551个村委会(包括部分居委会)进行问卷调查3287人,他的分析发现当经济发展处于起步阶段时,村民选举有可能是半竞争性的;中等发达的村庄,更有推行自由公平选举的动力。而处于贫困或富裕状态的农村,要么认为选举不能当饭吃,要么出现经济能人垄断权力的“老板政治”(Shi Tianjian,1999),使民主选举大打折扣。
分别来看,上述论证都是根据实地观察或实证研究得出的可靠结论,都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然而,如果让我们把上述假设及其论证综合起来看,分歧就一目了然了。经济发展同民主选举、村民自治究竟有什么关系?郑永年的回答是没有多大的关系。他认为导致中国各地农村民主发展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这些原因中,最关键的因素是国家在基层民主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而地方自治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级地方政府的愿意,而与地方经济发展没有多大的关系(郑永年,1998)。笔者根据在广东26个村1852张问卷调查分析发现,农民的个人收入水平同其参与选举的动机基本不相关,同村民对集体分红的关注程度有明显的关系,而同个人政治面貌和经历呈显著相关(郭正林,2003)。
二、村民选举的政治效应
村民选举的政治影响或政治效应是多重的。对于乡村基层政权来说,这种影响具有直接广泛性。对上层或中国的宏观政治来说,这种影响具有持久和战略性。然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人们都难以预测农村直接选举的政治后果,由此导致了决策高层的意见分歧以及基层民主步伐的摇摆不定。
具体地,就农村基层来说,村民选举的政治效应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对农村党支部权力地位的影响,是加强还是削弱?二是选举是否真正能够使当选的村委会干部更愿意听取村民群众的意见,维护村民群众的利益?三是选举是否会削弱乡镇政府对村级组织的政治控制?四是村民选举会不会导致国家的政策难以在农村贯彻执行?从宏观政治方面来看,村民选举是有助于加强执政党的合法性还是与事无补?农村实行的这种直接选举制度能否像中共元老彭真所乐观设想的那样,会从自下而上地延伸到各层政权组织?这些都是学者们所关心并加以认真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由于问题的复杂性、变化性,许多问题还没有得到多少深入的研究,相应的理论假设还处于待经验验证的阶段,而且意见明显分歧。
“党的领导”始终是中国民主发展绕不开的政治因素。那么,对于执政党的农村基层组织来说,村民选举是加强其权力地位、巩固其传统权威、改善其组织结构,还是恰恰相反?戴慕珍和罗丝高则认为,无论选举与否,实权仍然由掌握了企业经营权、村集体财务分配权的村党支部书记控制。而在经济落后的农业村,由于村党支部书记毫无建树,村民选举正好为乡镇领导撤换这些无能的村支书提供机会,这使村委会有可能成为村庄的权力中心(Oi & Rozelle,2000)。欧博文的结论基本上同戴慕珍和罗丝高的一致。他发现,在很多地区,党支部的影响都超过村委会,村委会在村的政治活动中没有最终发言权(O’Brien,2001)。
何包钢和郎友兴在浙江的实地研究发现,村民选举对党支部的控权地位影响不大,但党支部在农村权力结构中的绝对优势开始变成相对优势。他们还发现,农村能人或企业老板对党支部书记的权力产生了冲击,他们不再满足经济上的成功,而试图谋求政治地位,出现了“老板书记”(何包钢,郎友兴,2002)。笔者的研究发现,“两选联动”或“两票制”的制度安排,可以从根本上化解村委会与党支部的权力冲突和矛盾。这种制度的前置性条件是,村级组织任何决策人都必须接受村民的任何一种有效形式的直接选举(郭正林,2001)。
不少学者看到,中国农村民主的有力推动者或热心倡导者恰恰是中共一些元老级领导(O'Brien & Li Lianjiang,2000;郑永年,1998)。欧博文和李连江认为,邓小平、彭真、薄一波、赵紫阳以及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都是民主的热心推动者(O'Brien & Li
Lianjiang,2000)。从党的正统理论来解释,基层民主就是走“群众路线”,是实现党的政治任务的手段。令一些学者矛盾的是,作为民主推动者的角色又在其他许多方面成为中国民主化的阻碍(郑永年,1998;吴国光,1998)。这种角色矛盾对遭遇村民选举的农村党支部建设具有深刻的影响。瑞典隆德大学的沈迈克甚至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下一步,共产党最急迫的任务是获得一种新的合法性(Michael Schoenhals,1999)。那么,农村党支部合法性更新的方式能否为这种政治任务的实现提供有益的经验?正面回答这个问题的学者不多,研究有待深化。
一些学者认为,不是村民选举削弱了党支部的政治影响,而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长期积累起来的问题在直接、公开和竞争性的村民选举过程中集中暴露出来了。笔者和白思鼎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分析到,村民选举在挑战农村党支部的传统权威。如果农村党支部书记及其他成员逃避选举,那无疑是主动放弃政治领导地位。无疑,村民选举把党支部权力的合法性问题提了出来,这种政治合法性问题能否在村民选举中解决,关键取决于执政党自身如何进行制度化调整(郭正林,2001)。李连江、白纲等对山西河曲县农村党支部选举的“两票制”改革研究表明,两票制之所以能够加强党支部的权力地位,在于两票制把决定党支部书记及其他成员人选的权利都交到了普通村民的手中(Li
Lianjiang,1999;白纲,2001)。中共十六大积极倡导党内民主制度建设,莫不与执政地位的合法性刷新有关。而被官方称之为“两推一选”的两票制,已经被许多省、市作为加强党建的先进经验而加以推广。
村民选举出来的村委会,会不会自然成为村民利益的代言人?这并不是一个没有争议的问题。李连江的研究表明,自由公正的选举有助于加强选举与当选村干部之间的积极接触。村民更愿意同当选的村干部联合起来抵制土政策,而村干部要想连选连任就得维护村民的利益。因此,村民选举有助于提升村委会在村民群众心目中的权威地位(Li
Lianjiang,2001)。墨宁把这种接触称之为选举连接,并认为中国乡村的选举连接是一种革命。在理论上,它扭转了列宁主义关于领导与群众的关系;在实践上,他改变了农村基层领导与普通村民的关系。笔者的案例研究结论支持李连江和墨宁的观点(郭正林,2001)。戴慕珍和罗丝高通过多元分析表明,村民选举对村委会的支持情况应当考虑村庄经济结构类型。对于工业化和集体经济程度高的农村,村民和村干部的选举参与热情都不高,村民选举对村庄权力结构的影响很少,党支部书记仍然控制权力资源。而在那些外出务工人数不多且以土地收成为主的农业村,村委会有可能成为实际决策中心,这类农村的竞选热情很高,村民选举有可能提升村委会的权力地位,因为村民的土地利益同选举结果利害攸关。她们还发现,农村私营企业主的参选兴趣显著,村庄个体户的数量同竞选呈高度相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党支部对私营企业主采取关门主义的态度,那么党支部就不能从村民选举中捞取好处。在那些外出务工多的村庄,外出的村民很难回村参加村委会选举,他们的利益同村庄联系得越来越少,因此无论党支部还是村委会都难以从缺乏竞选性的选举中获得政治利益(Oi & Rozelle,1999)。而徐勇认为目前的村干部具有双重角色,他们既要扮演国家在农村的代理人角色,又是村里的当家人,必须扮演村民利益的代言人才能站得住脚(徐勇,1998)。实际上,传统的保甲角色也具有显著的两重性质。
实行村民选举后,国家政权特别是乡镇政权机关同村级组织的关系也是一个热点问题。不少学者对中央为什么推行村民选举、村民自治的农村政治改革十分关注。他们提出,受列宁主义支配的中国共产党高层,为什么要摈弃便于政治控制的人民公社体制而接受和推行自下而上的民主选举和村民自治制度。学者的研究发现,村民自治制度是解决“包产到户”后的农村所普遍面临的组织(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瘫痪、治安恶化、干群关系紧张等政治危机的好办法,由此解决农村社会最紧要的秩序和稳定问题(郑永年,1998;王旭,1998;欧博文、李连江,1998;O'Brien & Li Lianjiang,2001)。欧博文甚至认为,实行村民自治的目的是通过赋予农民一定的民主权利换取他们对国家政策的服从(O'Brien,1994)。而郑永年认为,乡村民主的发展并不一定是中共唯一的选择,乡村新制度也并非一定要基于选举之上。在很大程度上,选举制度的产生是和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民主”意识和追求分不开的(郑永年,1998)。而且,基层民主所期待的政治收益也不少:重新组织农民、监督基层干部、遏止专横行为、缓解干群矛盾等等。
近期的乡镇与村级组织的关系状态似乎说明村民自治实践并没有实现原来的民主预期。农民还是一盘散沙,民主选举很难把分散的农民吸引到投票站来集中投票,基层腐败与干群关系紧张等问题也都没有解决。特别是乡镇政府与村委会的关系摇摆不定,要么走向乡镇“一竿子插到底”的老办法,要么村庄成了谁也不管的“化外之地”。吴国光曾问到,直接选举为什么首先在农村?为什么是农民而不是城市居民?他的回答是,因为农村是中国政治制度的边缘地带,农民也不是“领导阶级”。尽管农民人口众多,但包产到户后的农民分散化了,不再是严密组织起来的单位中人(吴国光,1998)。那么,这种发生在制度边缘的农村民主会不会延伸到制度中心?
然而,1998年以后出现的四川省步云乡的乡镇长直选以及部分省份试图将“两票制”推广到乡镇长选举的政治改革,似乎让学者们看到了这种影响的可能。彭真的一段名言被许多学者不断引用。彭真说:“把一个村的事情管好了,逐渐就会管好一个乡的事情;把一个乡的事情管好了,逐渐就会管好一个县的事情,逐步锻炼,提高参政议政能力。”这表明了学者的一种期待,就中国的民主从农村基层做起,然后从乡到县逐级向上发展。学者们大多认为,没有地方党委领导人的坚定支持和高层政治领导的默许,在中国搞乡镇长直选的试验是不可想象的(李凡、寿慧生、彭宗超、肖立辉,2000;Li
Lianjiang,2002;黄卫平、邹树彬,2003)。李凡认为,相对地方政府较少束缚于意识形态,中央政府虽然受到意识形态的干扰,在制度改革上较为保守,但也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基层政府民主化的必要性和意义。他发现,在乡镇长选举的改革过程中,中央政府的作用一直都存在,只是形式上非常隐蔽。他指出,深圳大鹏镇、山西卓里镇的乡镇长选举改革,都得到了中央有关部门的支持甚至参与指导(李凡等,1999)。李连江发现,村民选举使那些有进取心的地方领导不再满足扮演一个地方官僚的角色,而是乐意扮演一个促进政治改革的地方政治家,尽管在推动乡镇长直接选举的改革过程会冒政治风险,但他们认为历史终究会站在改革派这一边的(Li Lianjiang,2002)。
三、村民选举与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
这个问题直接涉及农民在村民选举、村民自治中的民主权利意识的激活与伸张。“激活”是农民对其应有公民权利的认知及自我强化;“伸张”就是通过制度化或非制度化的途径并采取有效的行动来捍卫自己的经济利益和民主权利。对这个问题的学术研究,最有国际影响的就是李连江和欧博文的系列成果。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李连江根据他在江西T县20个村的调查,分析了自由、公正的村民选举是否赋予了农民的民主权利观念。他发现,自由公正的选举的导人,激活了农民的公民权利意识,农民在选举中不再投那些扭曲中央政策的村干部的票,说服和动员其他村民罢免不负责任的干部,要求选举出来的村干部抵制乡镇那些违背中央政策的“土政策”。也就是说,村民选举提高了村民的政治效能感,农村开始把政治参与理解为权利本身,并为捍卫这种权利而采取行动(Li Lianjiang,2003)。欧博文和李连江对农民捍卫权利的行动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们最早提出了“依政策抗争”这个关键观念,区分了“顺民”、“钉子户”、“刁民”这些类型。“钉子户”、“刁民”其实是地方官员们对不服管的农民的蔑称,正是这些不服管的、敢于反抗的农民,在上访告状时,根据法律法规、党的政策甚至政治口号来抵制土政策,捍卫自己的经济利益(O'Brien & Li Lianjiang,1996)。在后续的研究中,他们用“依法抗争”这个概念,强调了农民上访告状不再局限在经济利益要求,而是进一步要求依法保障他们的选举与被选举权、监督权和罢免权等政治权利(李连江、欧博文,1997)。2001年在香港召开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欧博文这样说到:“到目前为止,村民提出的呼吁是要求进入地方的政治,村民们很少要求更广泛的结社、表达以及未经许可的参与的公民和政治权利。他们很少怀疑现存法律和政策的合法性,更不用说怀疑高层负责任的领导颁布法律和政策的权利。”因此,中国的农民最好被看成是处于臣民和公民之间的位置上(欧博文,2001)。而陈佩华(Syvia Chan)似乎走得更远,她认为村民自治也许能够成为中国公民社会的生长点。
对欧博文和李连江所提出的“依政策抗争”或“依法抗争”概念,郑永年批评这个论点过于消极地看待农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所谓“消极”就是“对抗”,没有看到“合作”的一面。他认为,不能根据西方的民主价值来看待和要求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事实上,没有自上而下的动力,中国不可能发展出地方民主来(郑永年,1998)。帕斯特和谭青山似乎支持郑的观点。他们在一篇谈论中国村民选举意义的文章中说到,在原则上村民选举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实质性支持,江泽民多次强调要扩大基层民主,保证农民的民主权利,李鹏也称赞新颁布的《村委会组织法》是直接维护农民利益的好法律。但十分有趣的是,他们的结论却是选举是保证中国稳定的最有效的手段,因为选举为农民提供宣泄不满情绪的机会,而没有这样的宣泄机制就有可能演变出暴力革命(Pastor &Tan Qingshan,2000)。一些学者却更多看到,村民选举激活了村庄里的派性斗争、宗 族竞争甚至村庄恶棍势力的争斗(何清莲,1998;贺雪峰,2001;陈涛,2001;肖唐镖, 2001)。
柯丹青批评分歧中的国内学者有一个共同的价值取向,就是工具主义地看待村民选举,他们在罗列村民选举好处的时候,往往是选出的村委会办了多少企业、修了多长的路、少了多少村民纠纷、增加了多少农民收入,如此等等。而没有视村民选举、村民自治是农村居民的公民权利。戴慕珍和罗丝高的研究似乎表明,村民选举并没有激发起村民多少的公民权利的意义,更不用说主动地伸张他们的民主权利。她们发现了什么呢?富裕的工业化农村,农民仍然指望着有本事的村支书为他们赚更多的钱;那些贫困的村庄,农民都跑出去自己谋生,没有什么政治兴趣。结论是,至少是短期内,农民在推动选举方面的兴趣将会衰退(Oi & Rozelle,2000)。
综合来看,村民选举对农民公民意识的激活与伸张的影响的问题,学者们的学术分歧也很明显。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分歧呢?笔者认为,一是各自分析的资料来源不同,基本上都是基于地方性数据及个案材料而不是全国性数据而进行的可比较研究。而且事实上,中国各地村民选举的质量和结果差异很大,在缺乏全国性的数据资料为分析基础的情况下,要得出共识性的结论几乎是不可能的。二是分析的切入点或理论视野不同。例如,欧博文和李连江的分析切入点,主要是上访告状中的农民如何利用政策和法律同扭曲政策或不守法的地方官僚作斗争,采取这种行动的农民本身就比一般的农民有更强的权利意识。戴慕珍和罗斯高的理论视野在政治经济学,她们从土地产权、工业化程度、收入来源、村庄的开放程度(外出务工的多寡)等来分析村民选举对农村权力结构的影响。郑永年从国家制度建设的宏观视野来分析村民选举这个微观的层面,当然就会注意到中国民主道路要走中国自己的路,也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这种民主的价值取向当然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理论预设。
国外学者对中国村民选举及其政治经济效应的分析结果,显然存在分歧。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利用在中国农村的经验观察来检验他们的政治理论模型,并对中国的民主未来进行预测性的分析。从政治学分析的眼光来看,这些研究的潜在疑问是,从农村基层做起的直接选举,对中国非农村地区的民主化究竟会带来什么影响?显然,期望农村的选举、农民的自治会自动走进城市或“升格”为乡直选、县直选等等,那是再幼稚不过的想法了。学者们的研究所能带来的启发是,无论穷地方、富地方,让公民来投票选举都是能够办到的事情。广大农村实行的民主化改革不仅证明了这一点,而且显示了民主制度建设本身也在塑造民主的人。
标签:郑永年论文; 村民自治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农村改革论文; 领导理论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地方领导论文; 李连江论文; 农民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