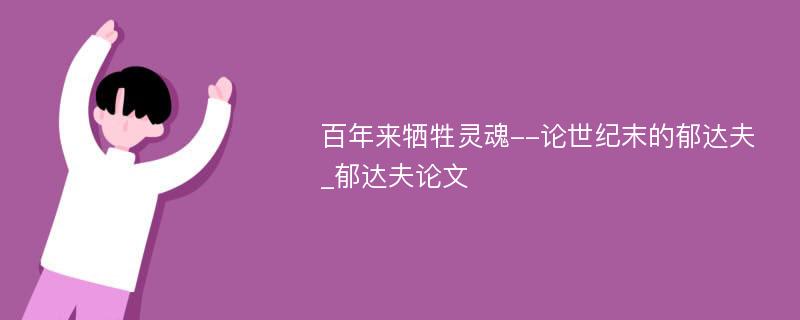
百年祭魂——世纪末论郁达夫,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末论文,达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纪末论郁达夫,似乎预示着一种特有的冥契——语境和论题的和谐化一,虽然这中间相隔了整整一个世纪。“世纪末”与郁达夫那种近乎如影随形的关系,使我们感受和阅读二十世纪末的时候没办法忘记他。世纪末的种种文化现象表明,百年前诞生的这个世纪苦魂正重新回到我们的时代,也许时至今日我们才可能真正理解郁达夫——他的个性、他的作品和他对于历史的意义。
“罗网”:郁达夫现象论
中国人最初关于“世纪末”的概念和知识大概是从郁达夫那里得来的。中国人直观地认识和理解“世纪末”的性格和内涵,估计仍然是从郁达夫身上获得的。这的确是文学史上耐人寻味的一种现象。我相信叶灵凤下面这段话许多现代作家都会有同感:
我年轻时候,是爱好过王尔德的作品的,也爱好过英国“世纪末”那一批作家的作品的。这可说全是受了郁达夫先生的影响。那时大部分的文艺青年都难摆脱这一重罗网。[①]
“罗网”一词并非言重而是恰如其分。想想《沉沦》最初发表时引起的巨大轰动,想想洛阳纸贵般对郁达夫作品的顶礼膜拜,想想那位私淑郁达夫而不知所终的王以仁,郁达夫及其回声就会变得清晰可辨。施蛰存曾说:“在早期的新文学运动中,创造社给我的影响,大于文学研究会。”[②]这一感受是很有代表性的。郁达夫、郭沫若、田汉及其创造社代表了中国世纪初“青年文化”最初的震动。这是一段生机勃勃的历史,“五四”大潮催生出的这个“青年团体”,构成了一个真正的思想与艺术的实验场,在此之中,他们通过交流与冲突、聚集和分化的方式进行着最先锋式的精神活动。郁达夫及其同人用最自由的观点,最富个性的冲撞,甚至最丰富的混乱、嫉妒、狂热、最尖刻的批评、嘲笑和辱骂构成了一个有时无法忍受但又永远具有刺激性的、奇怪地混杂着的气氛。一重罗网撒向社会的各个角落罩住了许多青年人的心。“郁达夫现象”当数其中最具个案意义的例子了。
把“世纪末”和郁达夫联系起来的似乎是他自己授人以柄所致。其实郁达夫从未以此为辱,反倒常以此为荣。创造社的一群青年作家在中国文坛的所作所为能够比得上英国世纪末文艺运动中的“《黄面志》团体”,当然是郁达夫们所求之不得的事。这也很可能是郁达夫撰文介绍《黄面志》及其作家的初衷。十九世纪末的英国,是一个充满了苦闷和颓废的社会。1894年创刊的《黄面志》及其同人作家是在这种倾向上反映得最敏锐的一个文艺团体。这个团体中的主要成员美术编辑比亚兹莱(AubreyBeardsley)、诗人道森(ErnestDoweson)、西蒙斯(ArthurSymons)等与小说戏剧家王尔德共同构成一个规模不小的世纪末文艺思潮。西方“世纪末”文艺思潮在世纪初的中国文坛一度相当盛行,这是许多五四文学活动的当事人都曾提及过的。人们比较熟悉的是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所说的“世纪末果汁”。对此鲁迅提到四个人的名字:尼采、波德莱尔、王尔德和安德列夫。鲁迅当然是要而言之,事实上英国的《黄面志》及其周围的作家也是这种“世纪末果汁”的重要组成部分。叶灵凤说:
《黄面志》那一批作家的作品,以及比亚斯莱的画,对中国早期的新文艺运动也曾发生过一点影响。因为首先将《黄面志》介绍给中国文艺爱好者的是郁达夫先生,接着田汉先生,张闻天先生不仅介绍比亚斯莱的画,还翻译了王尔德的作品。后来鲁迅先生也编印过一册比亚斯莱画选,列为《朝花艺苑》丛刊之一。[③]
郁达夫介绍《黄面志》时,事实上这个刊物在英国停刊已久,有关诸人都已经去世,“世纪末”早已成为过去,新世纪也开始了四分之一。郁达夫不过是当作英国近代文艺活动的一个面貌来介绍的。“他的介绍被接受了,而且发生了影响。可是,却使他自己从此被后人称为流浪颓废作家。这真是当时满怀愤世疾俗的年轻的达夫先生所意料不到的。”[④]其实大可不必为郁达夫的这种遭遇叫屈。同样是一种颓废时代的产物,把郁达夫与世纪末作家比附,既不牵强附会,也无贬损之嫌,倒是能说出一种历史的真实和文化的契合。
在《〈黄面志〉及其他》一文中,郁达夫丝毫没有隐晦他对这批世纪末作家的喜爱之情。他说:“ErnestDowson的诗文,是我近年来在无聊的时候,在孤冷忧郁的时候的最好伴侣。[⑤]”郁达夫是怀着同情和敬仰来介绍道森的,在他看来《黄面志》的一群天才诗人里,“作最优美的抒情诗,尝最悲痛的人生苦,具有世纪末的种种性格,为失恋的结果,把他本来是柔弱的身体天天放弃在洒精和女色中间,作慢性的自杀的,是薄命的诗人ErnestDowson[⑥]。”这是段相当煽情的文字,没有刻骨铭心的触动是说不出来的。类似饱含感情的叙述,文章中随处可见,这样声情并茂的文章深刻打动并影响了一代青年文学者当是可以想见的。其时,郁达夫的《沉沦》正一纸风行,俨然文学青年中的偶像。于是,郁达夫心目中的所爱,被文学青年爱屋及乌地传播开去,形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世纪末文学热”,即如诗人道森,就出现了不少译介者,王统照、傅东华就曾因错译和误译道森的诗颇受文坛指责。施蛰存后来也回忆过,戴望舒和杜衡“合译英国颓废诗人陶孙的诗集,这是受了郁达夫的影响,因为郁达夫在《创造季刊》上介绍过陶孙。”[⑦]至于插画家比亚兹莱的追随者就更多了。田汉译王尔德的《莎乐美》,依据的是英国原版书,中华书局出版时又几乎原样设计,里面附有比亚兹莱的全套插图,此前田汉编辑《南国周刊》版头和里面的插画,用的也都是比亚兹莱的作品,性学博士张竞生编的一本畅销书《性史》也是选用比亚兹莱的插画《月亮里的女人》作封面。至于深受郁达夫影响的叶灵凤就干脆以“中国的比亚斯莱”自居,他当时给《洪水》半月刊和《创造》月刊所画的封面和版头装饰画,几乎全部袭用比亚兹莱风格,为此颇受鲁迅的嘲讽。而象邵洵美、冯至等一些青年诗人对世纪末作家的热情爱好更是与郁达夫的影响分不开。足见其“罗网”之重,覆盖面之大。
鼓动起这么大的风气,拥有如此多的追随者,世纪末文学在中国的正宗传人并无出郁达夫之右者。文化氛围的滋养是一回事,真正从骨子里悟透其神韵则是另一回事。这就涉及到从个性气质到志趣爱好多方面的因缘合和,郁达夫天生的某种“世纪末性格”是其接近西方世纪末文学最直接的亲和力。而从郁达夫小说所折射出来的他本人的精神流程看,西方世纪末文学确实给予他很大的心理慰藉力量。《银灰色的死》是一篇以道森为原型,描写“世纪末性格”的小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篇处女作奠定了郁达夫以后一系列“自叙传”小说的总基调,象征着他沉郁伤痛的心灵觅到的一种得以安栖的主题框架。难怪有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把郁达夫的小说当作诗看,则不啻就是他自己所介绍的珰生和黄面志的一群人物。”[⑧]郁达夫头上戴过许多名号的帽子:浪漫派中的感伤者、唯美派中的颓废者、现实派中的零余者、现代派中的叛逆者……当然还不应忘了“士大夫中的没落者”。如此多的特征杂糅在他一个人身上委实是一种奇异的现象。郁达夫罕见的西学素养,使他能够驾轻就熟地吸纳任何一种合口味的营养。在看似矛盾的充分杂取中,其实有着郁达夫式的逻辑。看看下面两段话:
法国也许会灭亡,拉丁民族的文明、言语和世界,也许会同归于尽,可是,卢骚的著作,直要到了世界末日,……才能放尽它的光辉。[⑨]
文艺季刊TheYellowBook,与那一群少年天才的命运一样,到了1897年,出了第十三期就绝命了,然而他们的余光,怕要照到英国国民绝灭的时候,才能湮没呢![⑩]
虔诚的颂扬出自同一种句式,涉及的却是相隔一个世纪、两个国度的文学现象。他说对屠格涅夫有“一种特别的偏嗜”,“因为我的开始读小说,开始想写小说,受的完全是这一位相貌柔和,眼睛有点忧郁,络腮胡长得满口的北国巨人的影响。”[11]又说:“在日本现代的小说家中,我所最崇拜的是佐藤春夫……我每想学到他的地步,但是终于画虎不成。”[12]郁达夫特有的极端的语汇让人没有回旋的余地,可语出真诚,说的又是绝对的心里话。这种奇异的杂糅恐怕也是一种值得玩味的“郁达夫现象”。
关于郁达夫的文学性格,郑伯奇下面这段评判人们耳熟能详:
郁达夫给人的印象是“颓废派”,其实不过是浪漫主义涂上了“世纪末”的色彩罢了。他仍然有一颗强烈的罗曼谛克的心,他在重压下的呻吟之中寄寓着反抗。[13]
在郑伯奇看来,“创造社的倾向虽然包含了世纪末的种种流派的夹杂物,但,它的浪漫主义始终富于反抗的精神和破坏的情绪。”[14]郑伯奇着眼于郁达夫及创造社文学的社会进步意义,当然旨在寻求为其辩护的理由,毕竟围绕郁达夫的毁誉褒贬实在重雾难破。冷静地剥离包裹在郁达夫身上的“百衲衣”看来需要极高的智慧,仅仅限于拨乱反正的学术评价并不能说明问题。悟性颇强的许子东在他那篇才情逼人的文章中得出的结论,是许多欲从比较文学入手的研究者很难绕过去的。他指出,私小说形式只是郁达夫文学性格的外衣,卢梭精神是他的灵魂,王尔德、施托姆的色调是他的肤色神态,而屠格涅夫的“零余者”与他血肉相连。在私小说这种郁达夫偏爱的艺术格式里“灌注了浪漫派的精神、感伤主义情调及世纪末色彩,还有‘零余者’性格的社会内容(以及……中国“士大夫”气度等等)”[15]复杂的艺术倾向。这似乎是个令人费解的“郁达夫现象”,其实作为一位诞生于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中的卓越作家,郁达夫的矛盾和丰富是其必然。就其古诗词的典雅营造而言,郁达夫是个古典主义的追随者,就其小说、日记的直抒胸臆和情迷似火的意境而言,他是个浪漫主义的中国传人,就其表现手法的综合与现代悲剧意识的表露而言,他堪称中国现代主义的先驱者,而就其作品中寓含的叛逆反抗和无情的剖析而言,又分明不乏现实主义成分。既然哪一派都不是,那么,他就不专属于哪一派。既然哪一项帽子都不完全合适,那么索性让他光着头更来得舒服。脱光了束缚金身的百衲衣,露出的才是一个真真切切的肉体,他呼吸流贯宇宙的文化氧气,汲取生于大自然的果实营养,流淌在体内的仍然是一个中国作家的血,仍然是一个喜穿长袍,身材瘦削颀长,文弱却不乏侠气的中国文人而已。
“颓废”:郁达夫气质论
“颓废”是郁达夫文本中最醒目的精神特征。围绕这一精神特征的指责、非议和理解、辩护构成了五四文学史颇为生动的文化现象。这也是人们把“世纪末”和郁达夫联系起来的一个重要因子。现在人们已经能够从诸如时代、民族和社会等背景因素来理解“颓废”产生的精神土壤,能够从气质、性格、经历等主观因素来理解“颓废”滋生的精神基因,甚至从世纪末文艺思潮的东移来探讨这一文化传播和接受现象。也就是说关于郁达夫的“颓废”倾向的历史评价和审美定位已经不成问题,没有必要再去过多饶舌。现在需要探讨的是:“颓废”作为一种精神因素,在现代知识分子的心理转型历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颓废”作为一种美学因素,在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过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这种独特的“郁达夫气质”在世纪之交的今天对我们有何启示。
我这里说的“气质”并不是指性格、脾气之类个人内在的素质,而是指一种精神和生活的方式,一种价值范畴和审美特性。从这个意义上讲,“郁达夫气质”对于中国传统心理模式不啻是一场整体转换的革命。如果说,《狂人日记》作为新世纪的第一篇白话小说,标志着言语方式和历史观念的一次变革,那么,《沉沦》作为新文学的第一部白话小说集,则标志着自我观照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次蜕变。这不仅是一场艰深而富于创新的文学冲击运动,而且也是一场在崭新、独特的精神状态下的创造活动,不仅是对民众习俗和偏好进行挑战的文学创作,而且也是对心灵中神秘的内在实体进行锻造的思想实验。
我们是沉沦在,
悲苦的地狱之中的受难者,
我们不得不拖了十字架,
在共同的运命底下,
向永远的灭亡前进![16]
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苦行之旅。借用瓦雷里的话说“苦行意味着通过艰辛乃至痛苦的途径力求创立、构造自己,以达到精神的最高境界。”[17]郁达夫一再承认他的创作冲动正是这样一种精神的苦行,他称自己是“一个永远的旅人(Aneternalpilgrim)”,是一个屡遭放逐的迁客,“碰壁,碰壁,再碰壁,刚从流放地点遇赦回来的一位旅客,却永远地踏入了一个并无铁窗的故国的囚牢,……愁来无路,拿起笔来写写,只好写些愤世疾邪,怨天骂地的牢骚,放几句破坏一切、打倒一切的狂呓。越是这样,越是找不到出路。越找不到出路,越想破坏,越想反抗。”[18]从鲁迅“铁屋中的呐喊”到郁达夫“无铁窗囚牢里的狂呓”,这是一种使人走向空寂境界的崇高的痛苦,它作用于他们整个精神境界,刺激它,穿透它,使之陷于变幻无常的波动之中而又抚慰它,粉粹它,向它慷慨地献出诧异、抚爱、启示和风暴,并主宰他们的生命、颤动和思想。不同的是,鲁迅选择了启蒙主义,郁达夫则选择了“颓废主义”,但都同时踏上了走向祭坛的精神苦行之旅,目标所指都是两个字:拯救。
“颓废主义”本来是西方一部分作家的一种挑战性的自称,是对世纪末社会危机状态下的惶恐不安的感受力,本质上是这批作家对内心世界和人类处境的某种哲学表露,带有很强的浪漫反叛色彩。颓废主义在中国的诞生也是与世纪之交社会转型期间整个时代的危机相联系的,西方颓废主义思潮中那种“忧郁的末日感”很容易勾起中国作家的敏感反应。郁达夫坦言:“……颓废堕落也没有法子……有时候还不能完全把知觉感情等稍为高尚一点的感觉杀死,于是突然之间,就同癫痫病者发作一样,亦有一种很深沉很悲痛的孤寂之感袭上身来。”[19]周作人是郁达夫“颓废主义”的第一位知音,这位五四时期以理性和平和见长的理论家对“颓废”深刻意义一直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曾这样看待波德莱尔:
他的貌似的颓废,实在只是猛烈的求生意志的表现,与东方式的泥醉的消遣生活,绝不相同。所谓现代人的悲哀,便是这猛烈的求生意志与现在的不如意的生活的挣扎。这挣扎的表现可以为种种改造的主义,在文艺上可以为弗罗倍尔的艺术主义,陀思妥也夫斯奇的人道主义,也就可以为波德莱耳的颓废的“恶魔主义”了。[20]
五四时期“颓废”(Decadente)被译为“颓加荡”,是当时报章诗文中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概念。田汉对波德莱尔的介绍、张闻天对王尔德的介绍和郁达夫对《黄面志》的介绍,都旨在澄清人们对世纪末颓废主义思想的误解。基本上与周作人的理解相一致。正是从“颓废”的现代性意义出发,周作人才对郁达夫给予充分的呵护,并把《南迁》的主人公的没落与《沉沦》主人公的忧郁病综括为“青年的现代的苦闷”。[21]后来的颓废诗人李金发也是得遇周作人的引荐才走上文坛。这说明提倡“人的文学”的周作人已经充分认识到颓废主义对中国文化和文学的有益冲击,并把它视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生成的重要契机。中国传统中也不乏“颓废”的因子。魏晋南北朝就是一个颇受后人追慕流风遗韵的颓废时代,那倒并不是一个文人自寻解放的时代,只是迫于时局动荡,好多人觉得过去苦心孤诣学来的规矩方圆,到时全无用场,不如放浪形骸自求真趣。在周作人看来那只是“东方式的泥醉的消遣生活”,与波德莱尔表露的“现代苦闷”不可同日而语,用鲁迅的话讲就是“活人的颓唐”与“死人的颓唐”之间的本质区别。
作为西方世纪末社会的一种特有的精神现象,“颓废”情绪的滋生是一种普遍的精神病症,根据诺尔道(MaxNordau)所著《变质论》(Degenation)的诊断,其表现为:
世纪末的病症,是带有传统道德破坏性的疯狂病疾,这些世纪末的人的肉体上的就有着显著的不具者的特征。因而神经衰弱,意志力毫无,易动喜怒,惯作悲哀,好矫奇而立异,耽淫乐而无休。追求强烈的刺激的结果,弄得精神成了异状,先以自我狂为起点,结果就变成色情狂,拜物狂,神秘狂;到头来若非入修道院去趋向于极端的禁欲,便因身心疲颓到了极点而自杀。[22]
诺尔道认为,这种现象“尤其在文明烂熟的都会里为最普遍,因而由都会里产生出来的近代文学,便一例地染上了这一种色彩,这就是世纪末的文学思潮。”[23]这种颓废主义的文学思潮在郁达夫看来是一种人类文明进程的必然产物,在他应邀为《文学百题》撰写的《怎样叫做世纪末文学思潮》一文中,就对诺尔道的上述只知攻击不知“体察”的观点不以为然。他认为“这一种世纪末的精神与物质上的现象,是人类进步不停止一天,在这世上也决不会绝迹的。”[24]精神萎顿、心理倦颓、行为悲观,进而追求享乐和刺激,都是人类在追求个性解放、民主自由过程中的自然现象。而颓废主义作为一种“文化危机”的产物,本质上是文学内部的一种带积极性的“叛逆力量”。对这种美学颓废派,郁达夫还将其列为“文艺赏鉴上之偏爱价值”的第一种加以研究。实际上也是用他人酒杯浇胸中之块垒。五四文学家中自称“颓废派”者不在少数,而且许多人也并不讳言自觉追慕这种潮流。世纪末的“朽水腐城”浸染了一代青年作家,其意义应作如是观:五四作家凭借生命体验和现代生活感悟,凭借摄取来的异域营养——“世纪末果汁”所触发的思维方式和审美态度,努力挖掘现代生活所寓涵的现代性本质,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把握住了现代人生的某种内在特征,以鲜活的现代化风采和色彩斑斓的艺术品格构成了五四新文学的现代性空间。这应该说是五四作家对世纪末果汁所作的一种有选择的吸收和创造性的升华。就郁达夫而言,如果说其文学中思想深度和文化蕴含的拓展,得益于此种外来养分当不为过吧。从郁达夫到李金发,五四批评界对其作品中源自世纪末的异国情调一直持批评态度,认为“在另一意义上,这却形成颓废(不是道德上)的趋势”。[25]但当时资深批评家刘西渭的下列看法仍然值得我们重视,他说:“实际上,一切走向精美的力量都藏着颓废的因子。”[26]把颓废放在美学意义上加以理解,这也是郁达夫为自己辩护所持一个重要证据。所以黎锦明才有理由说:“阿志巴绥夫的颓废是社会的,鲍特莱尔是哲学的,达夫的颓废我承认是真文学的。”[27]郁达夫多次借用王尔德的话来表述自己的唯美主义观点,而从作品的实践来看,郁达夫的现代性不在艺术形式而主要体现为一种文学气质。虽然这种气质本身不乏中国没落知识分子对“颓唐的情调”特有的嗜好,但郁达夫已经能够用“颓废美”这一“近代语”来感悟这种古典意境了。[28]“郁达夫气质”中更多的不是中国的“士大夫气”,而是杂糅着“北欧气质”、俄罗斯的忧郁和日本的颓废美,从卢梭、华兹华斯、屠格涅夫、佐滕春夫那里,郁达夫拈出了一种传统中国人比较陌生的“新感性”。这种“新感性”意味着对传统道德和文化的否定,意味着一种世纪观和人生观的现代生成,意味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新的存在方式的选择。“颓废”只不过是以一种反常、颠覆的姿态出现的一种精神自卫而已。在更深层次上,它意味着一种新的审美道德对压抑性的理性律令的反抗。意味着一种新的精神实体从中国固有的士人传统中分离出来。“郁达夫气质”的革命性意义即在于它以崭新的感受方式来触及自我的存在,作为一种解放了的新感性中的审美力量,虽然以变态形式来表现某种人为的、个人性的经验,但却从根本上激化了中国传统士人心理的裂变,激化了社会精神基础的震动,进而也激化了艺术中的审美力量,促使艺术的价值和功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二十世纪中国颇具“文化地震学”意义的一次革命,首先表现为一种语言结构的变革,“一场革命从本质上看即是谋求另一种社会条件和社会关系,这一革命的程度也许可以通过另一种语言的发展显示出来,这就是说,与统治的连续体的决裂必须同时是与统治者的词汇的决裂。”[29]而语言结构的变革——白话文战胜文言文,又必须依赖于感知方式和感知结构的普遍更新,无论是鲁迅文本中的“狂人姿态”,还是李金发诗中的“异国情调”,都与“郁达夫气质”一样共同构成了五四新感性革命由语言到意识的连续冲击。从这个意义上讲,郁达夫不是一个“颓废”作家,而是一个“颓废时代”的作家。“颓废”的实质是对道德主义传统的大张挞伐,是对废弛社会中自我灵魂的激情透视。把“颓废”作为“郁达夫气质”的主要表现显然并无亵渎之意,而是着眼于一种更深刻的精神否定和审美叛逆,着眼于这种陌生的气质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惯常“寻道坐佛”逃避心理的革命性意义。时至二十世纪末,我们从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中仍然可以看到知识分子身上的某些“郁达夫气质”。醒世预言也好,反社会反文化也好,其精神气质中的“颓废”因素,似乎仍然预示着一种世纪之交价值转换的特殊意义。由此看来,世纪末论郁达夫就不仅仅是一种历史还原了。
“色欲”:郁达夫主题论
在五四小说史上,郁达夫似乎一直被视作一位“扁平式人物”。郁达夫的小说情节单纯,主题重复,技巧也不复杂,很多小说可以看成是同一标题下的反复叙述,对于草创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来说,这一点并不奇怪。郁达夫的小说意义在于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典型的历史文本,这种历史文本与政治风云的变幻无关,它作用于人的内心世界和精神史,其文化意义也在于此。因此,对郁达夫的评论,我一直遵循着整体阅读整体评论的原则,着眼于郁达夫小说的独特个性、自身的张力、自己的面貌和特定的氛围,着眼于其作品反映人生的透明度、说服力和启示性。
从“色欲”入手探讨郁达夫小说的主题,并不想单纯地为其辩护。郁达夫有着中外小说家共有通病:脱开自身经验的性幻想,未能免俗的“窥视”心理,甚至通过艺术渲泄某种阴暗心理。作为人类普通存在的心灵暗角,作家这种勇敢的剖露反倒是一种勇气。色欲成为主题在《沉沦》发表以后就已经奠定了。值得注意的是,五四文学家的“处女作”是一种具有丰富信息量的文化现象,甚至许多作家都在那个时期写下了一生作品的大标题。分解和归总这些信息量对理解现代文学的缘起至关重要。《沉沦》之与郁达夫更是如此。《沉沦》的开篇语是值得玩味的,“他近来觉得孤冷得可怜。”这种语境的揭示已经划定了整个文本的特质:探索自我形式的意义。这是一位与世隔绝状态下的青年人,随着秋凉反而愈加心理郁热的他一直处在半梦幻的状态:
在这清和的早秋的世界里,在这澄清透明的以太(Ether)中,他的身体觉得同陶醉似的酥软起来。他好象是睡在慈母怀里的样子。他好象是梦到了桃花源里的样子。他好象是在南欧的海岸,躺在情人膝上,在那里贪午睡的样子。
这是一种典型的浪漫主义境界,陶渊明和华兹华斯和谐地呼唤着“回到自然”。郁达夫意不在此,这只是一种象征,主人公回到自然的过程非但没能找到避难所,反而使他更深切地感觉到自己的“身体”。他的“忧郁症”由此而来,看看他的自诩:“孤高傲世的贤人”,“超然独立的隐者”,一种“孤独”的情愫也就无可回避,这是一种“稠人广众之中的孤独”。它缘于内心深处,并非仅限于浅意识中觉察的异族人中间的不相容感。对于“他”而言,其实真正的孤独来自“身体”,真正的恐惧也来自“身体”,他怨这怨那,恐怕都只是外在的原因,内心的“槁木”、“死灰”状态反衬的是肉体的压抑。这对“感受性非常强烈的他的性情”不啻是一种颇具毁灭性的洪流。作家强调这是“从始祖传来的苦闷”,并使主人公联想到那些十字架下的清教徒。目的很明显,郁达夫是在探讨“人的自然本性的苏醒”,剖析主人公内心汹涌着的情欲流构成了整篇小说的主题。“主题是关系到人对世界的独特态度的最重要因素。诗人的主题范围,是他对生活将他抛入其内的诸具体情景的典型反映的一览表。”[30]色欲主题的确立,意味着郁达夫人生观念和价值观念的文学确认。它以审美的方式昭示了郁达夫对人生和世界之意义所持的态度。郁达夫总结“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算‘个人’的发现。”[31]即是从这个意义出发的。把“色欲”主题与特定的历史阶段中的中心问题以及文化运动结合起来分析,可以断定,“色欲”成了五四小说扩张自我、表现自我的主要形式。关于郁达夫对性的主导作用与两性关系所持的态度,一直是郁达夫研究的一个学术关键。以“反封建”或“个人解放”一言蔽之,往往会把问题简单化,且并不足以说明郁达夫的个性。郁达夫对“色欲”的表现,应该说,是卢梭给了他勇气,佐藤春夫借给他技巧,但他最终没能从劳伦斯那里分得杯羹,非不能也,实不适时也。色欲成为问题,就中西的文化传统和现实语境而言何止相差万里!当西方世界呼唤人性的自然复归的时候,中国才刚刚发现有个“自我”。郁达夫小说表现的就是一种人们最初发现自己的肉体、欲望以及灵肉分裂状态时的那份内心的颤栗。
不知为什么,“触摸自己”一直是我阅读郁达夫小说时最形象的一种直观把握。从《银灰色的死》到《沉沦》,从《胃病》《怀乡病者》到《空虚》、《迷羊》,郁达夫始终没能离开“身体关注”这一视角。他的意识流、情绪流始终围绕一具瘦弱的躯体在回漩。种种糟透了的内心状态——厌恶、孤冷、死寂;糟透了的身体状况——肺病、瘦弱、垂死;糟透了的生活方式——酗酒、手淫、邪思,构成了小说世界的整体氛围。而且没法形成一种昂扬的生命活力,反而往往使人陷入不健康的欲望泥淖。郁达夫采取的是自我殉身的手法,把个人的经验放到了解剖台上进行想像性的主诉和分解,针对的正是新旧社会转型期人们普遍存在的苦闷和渴望。钱杏村说,性的苦闷,在当时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是青年们同具着这样的事件,而没有勇气很痛快的表现出来的实生活的一部分,达夫是赤裸裸的整个的不隐晦的表现出来了。”[32]五四运动的“个人”发现,本质上是一种青年的发见,青春期的苏醒,象征着中国现代人特定阶段的“梦遗”和“初潮”般的心理转折期。色欲小说主题的盛行,是作为青年文化诞生的标志汇入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过程的。郁达夫一系列的小说可以看作是“世纪病”患者的主诉病历,控告着几千年传统对“我”的摧残:
我想以一己的力量,来拼命的攻击这三千年来的恶势力。我想牺牲了我一己的安乐荣利,来大声疾呼这中国民族腐劣的遗传。我想以一枝铁笔来挽回那堕落到再无可堕落的人心。[33]
类似的语言我们可以从许多五四作家的文集里找到。象周作人一样,郁达夫也在徘徊“究竟还是上北京去作流氓去呢,还是到故乡家里去作隐士”?[34]“隐士好听”,“飘流有趣”都抵不上“流氓过瘾”,其实,就是这一股“流氓气”才最终启开了中国现代化的序幕。苦行最终的着眼点是拯救,唯其如此,才愈显得悲壮。形销骨毁的“质夫们”还是以疲弱之躯扛起了历史的重任,他们的情欲流又何尝不是一种感悟生命真谛后的冲撞潮汐呢!
按弗洛伊德的观点,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性压抑的历史。在《“文明的”性道德与现代人的不安》,《文明及其不满》等论著中,弗洛伊德指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许多消极现象,例如充满“病态行为”和“丑陋的、讨嫌的、暗示人生黑面的东西”,许多人经常处于恐惧、不安或神经质状态,到处表现出“文化和社会的贫困”或“现代文化变迁中的种种危机”,主要根源,就在于性的因素。弗氏这里说的“性”因素不能作单纯的理解,它指的是一种人类普遍的欲望和本能,或是对自由的渴望,或是对自然的倾慕。五四时期的“性解放”是人的解放的组成部分,是思想革命的一块前沿阵地。“性的启蒙”旨在撕开封建道学的对人的自然本性的封杀。在五四启蒙者眼里,“中国独特的假道学”,恰恰是一个戴着古衣冠的淫逸本体”,[35]所以“中国性道德的整饬”就是要刺破这一虚伪的本体,寻求理性的光辉和人性的解放。马尔库斯有言:“性和社会功用之间的根本对立本身反映了快乐原则和现实原则之间的冲突……在一个异化的世界上,爱欲的解放必将成为一种致命的破坏力量,必将全盘否定支配着压抑性现实的原则。”[36]五四时期的“性启蒙”作用于人的生活观念和生存方式的变革,在文化转型过程中影响深远。由郁达夫肇始的五四色欲小说即是一种具有解放意义的经验方式。用周作人评论《沉沦》的话讲,就是“它的价值在于非意识的展览自己,艺术地写出升华的色情,这也就是真挚与普遍的所在。”[37]从垂死的文明形式到新的有活力的形式的重要变化的动力就在于这种个人的“离经叛道”。将自我从社会束缚中解放出来,设想一切人与人的关系(个人的、家庭的、社会的),以“自然的方式”存在,这是五四时期郁达夫们的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理想追求。色欲小说只不过是这种“自然的方式”的微缩景观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郁达夫小说的色欲主题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男权话语”,性幻想、窥视、臆病、苦闷的自述,都是男性视角下的产物,虽然他也试图从女性角度去探测女人的命运,但运用的意识和话语仍摆脱不开浓重的男性特征,如《她是一个弱女子》基本上是一个男性眼中的“女性神话”。郁达夫身上遗留的中国古代传统中“娼优仕子”的血脉,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色欲小说主题的深刻性,与五四时期颇带“女权主义”运动色彩的“妇女解放”潮流不无矛盾和牴牾之处。“忏余独白”与“娜拉言说”毕竟不是一回事,其对自我本质的理解存在相当的差异。如果把自我的本质分为三个方面:一是自然的产物;二是人的意志和人所创造的社会结构的产物;三是自我选择的产物。那么“忏余独白”选择认同的是第一点,对个人对社会都不抱任何责任感。“娜拉言说”则倾向于第三点,注重自我的选择。二者之间的共同点仅在于对第二点的某种不无矛盾的认同。郁达夫的《迷羊》和鲁迅的《伤逝》探讨的正是这种“性差异”下的个人矛盾。两部小说叙述的都是挣脱社会和家庭束缚后的一对男女面对“两个自我”时的生存困境。《迷羊》中感到激情过后的平淡和无聊的是谢月英,她无法忍受“我”的强烈地占有欲而悄然出走。《伤逝》中这一角色换成了涓生,他感到的是个人的独立和生存的威胁来自于日渐生活化庸俗化的子君。月英和涓生同样亲手埋葬了自我选择的“小家庭”。一个女性,一个男性,可因果却是同样的:男女独立意识的不谐和,最终伤害了草创期的家庭。这实在是五四“人的文学”提出的不容回避的严肃命题。这说明色欲也好,婚姻也好,如果不是建立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之上,也就很难形成一股推动社会发展的良性动力。
相对于“五四”,郁达夫是历史的创造者,相对于二十世纪,郁达夫仅仅是一种“精神氛围”的开创者。文学家是人类经验的体悟者和忍受者,当价值转换的世纪末再次来到我们面前时,郁达夫这一忧郁柔情、令人肃然起敬的悲剧形象将身披历史纪元点的烨烨电光,巍然矗立在我们后来人、我们的子孙眼前。英灵不远,魂兮归来!是为达夫先生百年祭。
注释:
①叶灵凤:《郁达夫先生的〈黄面志〉和比亚斯莱》,收入《读书随笔》一集,三联书店1988年版。
②施蛰存:《我的第一本书》,收入《沙上的脚迹》,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72页。
③叶灵凤:《比亚斯莱、王尔德与〈黄面志〉》,收入《读书随笔》一集。
⑤ ⑥ ⑩郁达夫:《集中于〈黄面志〉(TheYellowBook)的人物》,收入《郁达夫文集》第五卷,三联书店香港分店、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
⑦施蛰存:《最后一个老朋友——冯雪峰》,收入《沙土的脚迹》,第125页。郁达夫文《TheYollowBook及其他》载《创造周报》1923年23日、30日,第20、21号。
⑧邹啸(赵景深):《〈郁达夫论〉序》,北新书局版。
⑨郁达夫:《卢骚传》,《郁达夫文集》第六卷。
[11]郁达夫:《屠格涅夫的〈罗亭〉问世以前》,《郁达夫文集》第六卷。
[12] [34]《海上通信》,《郁达夫文集》第三卷。
[13] [14]郑伯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
[15]许子东:《郁达夫新论》(增订版)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31页。
[16]《〈茑萝集〉献纳之辞》,《郁达夫文集》第七卷。
[17][法]保尔·瓦雷里:《象征主义的存在》,译文见金丝燕《文学接受与文化过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61页。
[18]《忏余独白》,《郁达夫文集》第七卷。
[19]《马蜂的毒刺》,《郁达夫文集》第三卷。
[20]周作人:《三个文学家的纪念》,《晨报副刊》,1921年11月14日。
[22] [23] [24]《怎样叫做世纪末文学思潮?》,《郁达夫文集》第六卷。
[25] [26]刘西渭:《咀华集》第100页,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
[27]锦明:《达夫的三个时期》,1927年9月5日《一般》第三卷第一期。
[28]参阅《苏州烟雨记》,《郁达夫文集》第三卷。
[29]马尔库塞《新感性》,译文见《人类困境中的审美精神》,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30]《比较文学研究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26页。
[31]《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郁达夫文集》第六卷。
[32]钱杏村:《〈达夫代表作〉后序》,上海春野书店1928年版。
[33]《奇零集·公开状答日本山口君》。
[35]周作人:《关于假道学》。
[36]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67页。
[37]仲密(周作人):《〈沉沦〉》,1922年3月26日《晨报副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