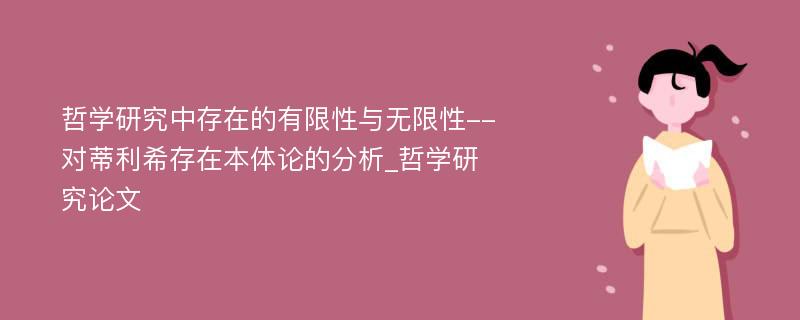
哲学研究 生存的有限和无限——析蒂利希的生存本体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体论论文,哲学论文,析蒂利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的生存是存在和非存在、无限和有限的统一。虽然在现实中,受到非存在限制的存在——有限性是人类生存的普遍命运,但是,人在有限的生存中追求无限的意义,在克服非存在的斗争中展示存在的勇气。这个无限不是量上的规定,而是悖论性的、否定性的和超越性的规定。广义的宗教肯定了人类生存的勇气和价值,它与传统的宗教信仰有着根本的区别。蒂利希的思想是生存主义和基督教相结合的重要成就,但存在着抽象性和模糊性的缺陷。
从巴门尼德提出“存在和非存在”的哲学命题,到莎士比亚笔下哈姆雷特说出“存在还是不存在,这是个问题”的经典名句,存在问题曾经引发多少思想家的睿智思索。当代西方人本主义的一个共同论题就是人的存在和非存在以及它们的关系问题。著名的德裔美国思想家保罗·蒂利希从哲学和神学相结合的角度对这个问题作了富有启示性的回答。
蒂利希认为,哲学本体论研究的就是存在问题。存在是由“非存在的惊骇”所产生的。在人类历史上,人们曾用神话的语言、宇宙生成论的语言和哲学的语言来说明存在和非存在的问题。不过,这些说明都不完善。对于这个问题,只能用哲学和神学相结合的隐喻性和悖论式的语言才能表达和说明。存在和非存在都是表明终极意义的范畴。对于有关它们的提问,我们的回答既是否定的又是肯定的。“作为否定的回答,存在不可定义。因为每一个有定义的存在都只是一种设定;作为肯定的回答,存在是依赖于它的概念加以说明的。但是,只能在一种隐喻的方式中,概念才能揭示它。”[1]语言是用来描述存在物的。 对于存在和非存在,我们只能用象征的方式谈论它们。“我们所要说明的关于存在自身的每一个事物,存在的根据和深渊,必须是象征性的。它来自所有的有限实在中的素材,是对有限的素材作无限的超越性的象征作用。”[2]“隐喻性的语言能成为真实的语言。 它能揭示在这个语言中显示的和隐藏的东西。”[3]在蒂利希看来, 存在自身的隐喻性象征就是上帝。对于作为存在自身的上帝的隐喻性表达还有神秘、深层和深渊等。非存在则用幽暗、晦冥等来喻指。
悖论是指用自相矛盾、似非而是的语言来说明某些至为深刻的真理和现象。蒂利希说:“悖论就是与建立在普通人的经验总体之上的意见——包括感性的和理性的意见——相对立的见解。”[4] 人们一旦提到存在和非存在的关系问题,就必须意识到,他们已经接触到一个神秘的深层所在。这就要求使用悖论的语言。这种悖论语言的表达就是:非存在是存在的否定,是存在力量的阻力。但是,非存在不是存在的异己者,非存在依赖于它要否定的存在而存在。
蒂利希指出,哲学本体论概念要表达,“生存的存在之力量,以及本质的存在与生存的存在之间的区别。”[5] 人的生存参与和分有了存在的力量。人的本质存在,是本真的理想性存在,是人应该所是的东西,是人的潜在的无限可能性。不过,这个本质存在只是人们考虑人类完善性时所作的逻辑性预设,只是一个停留在预测阶段的抽象肯定性。它必须经过历史的否定才能进入具体的现实生存。人的生存实在就是本质存在进入历史和时间中的现实生活。 “生存”一词的拉丁文“exisistō”的原意是“起来、突出、变为。”那么,生存从哪里站起来?又要突出和变为什么?蒂利希的回答是,生存就是人类从与本质相对立的现实中站起来,生存突出的是潜在性和现实性的分裂。一旦人的存在从抽象的潜在进入到时间中的具体现实,人的生存有限性就随之出现。有限性是人的生存的普遍命运。
有限性表现的是人类生存中的非存在。蒂利希说:“受到非存在限制的存在,是有限性。”[6]从时间上说, 非存在表明人的生存有一个开始和终点的限制。非存在显现为存在之“尚未”和存在之“不再”。从空间上看,时间通过与空间的结合造成人的生存。人活着,就意味着有一个生存空间。这首先意味着拥有一个物理位置,诸如躯体、家庭、土地和城市等,它还意味着一种社会空间,诸如职业、影响范围等。但是,人的生存空间是有限的。没有任何人占有着确定地属于他自己的空间。他不仅必须面对自己由于只是一个“世上的过客”而丧失这种那种空间的事实,而且最终还必须面对丧失自己已经拥有或可能拥有的每一种空间的事实。有限性,就意味着不拥有任何确定的空间。“不拥有任何确定的和终极的空间,就意味着最终的不安全。有限,就意味着不安全。”[7]尽管每一个存在物都参与和分有非存在,但是, 有限性是在人的层次上被体验到的。每个人的生活进程都带来双重意义。它既是存在力量的增长,又是存在力量的减少。在人的生活中,有限性对人的精神状况也同样具有决定意义。意识中的有限性就是焦虑。焦虑是有限的自我对自己是有限性存在的自我意识。焦虑是永远存在的,它能在任何时候显示出来;焦虑的对象是虚无,因此无法克服。蒂利希认为,对于焦虑的发现,是二十世纪生存哲学、深层心理学、神经医学和艺术联合努力的成就。焦虑是一种本体性的存在。“作为一种本体的性质,焦虑是同有限性一样无所不在的。焦虑独立于任何可能造成焦虑的特定对象,它只依赖于非存在的威胁。”[8]从蒂利希的上述论说中, 我们仿佛已经体验到《圣经·传道书》所云:“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的思绪。
人们要认识自己的有限,要超越有限的生存,就必须借助于无限:“要体验到自己的有限性,人就必须从一种潜在的无限性的观察点来看自己。要意识到对于死亡的趋近,人就必须越过自己那作为整体的有限存在向外展望;必须以某种方式超越于自己的有限存在之外。他还必须能够想像无限性。”[9]人们在感怀和悲叹人生的短促和有限时, 实际上已经意识到了永恒和无限的存在。人们寻找和设定了一个又一个永恒和无限的理念,采用各种精神和物质的方式把有限的自身和无限的存在联系起来。蒂利希认为,在当代社会中,人的有限生存和无限存在的联系方式主要有三种:狂妄的方式,绝望的方式和参与的方式。狂妄的方式是指人们为了摆脱有限生存的焦虑和困境,就把自己及其活动领域当作无限存在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自工业社会以来,人们认为,以理性为核心的人类力量是无限的。他们开始以某个人、某个民族为中心来建立终极的典范。或者宣称某人的思想是人类精神的绝对体系;或者宣称某个民族是世界历史进步的最终代表。在蒂利希看来,狂妄的人,不过是将自己禁锢在有限实在中而不自知的井底之蛙,是满足于平均化的生产和消费制度而不思考生存意义的人。绝望的方式是指人们面对有限的生命,日益焦虑以至丧失生存信念而采取得过且过态度的生活方式。在每个人的生活过程中,非存在都是一个“尚未有”的幽暗和“不复存在”的晦冥,不知何时何处以何种方式降临。非存在带着无法穿透的黑暗,使人产生畏惧。面对这个不可避免的、日益迫近的虚无,人们不禁要问:既然一切都将归于毁灭,人类生活的意义何在?蒂利希说:“我们用‘无意义’一词来表示非存在对精神上的自我肯定所构成的绝对威胁。”[10]人们对无意义的焦虑是对丧失了生存意义源泉的焦虑,是对丧失了最终牵挂之物的焦虑。如果人的生存在无意义感占居优势地位,人们便会感到自己的生命落进了无比黑暗的深渊。于是,我们看到,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采取得过且过的生活态度的人在生命中体验到了一种“无法承受的轻”(米兰·昆德拉)。人类是否也如小溪的流水,只能依地势高下而随波逐流?人类是否也象深秋的落叶,只能随风飘零,才能得到超脱的无限?蒂利希主张,面对非存在的威胁,人类要有存在的勇气!存在的勇气就是不顾非存在的威胁而对生存进行的自我肯定。参与的方式就是以存在的勇气来抵抗非存在的威胁的自我肯定方式,是人通过对自身的肯定参与到存在自身的无限肯定中去的方式。人们不但要不怕非存在的威胁,而且要把非存在看成是开启存在的钥匙。因为只有人的有限生存才能告诉人们,人的生存是唯一的,无比珍贵的。只有显示了非存在的有限性才能使人的存在脱离遮蔽状态,迫使人们拿出存在的勇气来!同时,人们要意识到自我的生存自身中蕴含的存在力量,要在有限的生存中表现存在自身的无限性。在参与的方式中,蒂利希提到了和人的生存密切相关的两个本体论范畴,这就是存在自身和无限。
存在的勇气源于存在自身。“存在自身指的是一切事物中的内在力量,抵抗非存在的力量。”[11]存在自身并不是一个实体性的存在,而是超乎于有限性和无限性之上的东西。但是,在有限者要超越出自身的冲动中,存在自身向有限的存在物显现自身。人类生存的自我肯定就来源于存在自身的力量。人们参与存在自身的形成就是人们克服非存在威胁的永恒斗争,是人们肯定自身存在价值的无限追求。
蒂利希是在有限和无限的关系中提出无限问题的。他说,人优越于其他一切存在物的地方不仅在于人有自我意识,而且还在于,在知识和外部力量的限制的一切方面,人都能加以克服和超越:“他能用一切事物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他仅仅受自身有限性的限制。但是,这些限制也在无限地缩小。没有人能够说人类力量的最终限制在哪里。在人类与宇宙的遭遇中,人能超越任何可以想像的限制。”[12]无限是一个指引性的概念,它能够指引人们的思维去想像无限,去体验人自身不受限制的潜在可能,去实现追求的无限。无限不是一个量上的规定。它既不是与人的现实生存无关的量上的延续,也不是在有限的领域内通过比较而产生的最大。无限是一个悖论性的、开放性的和超越性的规定。
首先,无限表现为有限和无限的悖论性的统一。每个人的现实生活都是受有限的时间制约的,但存在的勇气能够使人克服时间的有限而达到无限的境界。为此,蒂利希提出了一个深刻的悖论:永恒的现在。他认为,存在的奥秘在于时间,而人的生存时间的奥秘就在于我们拥有现在。现在是转瞬即逝的,又是永恒常驻的。永恒高于一切流变的时间,同时,永恒又在现在中驻足。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悖论。但它揭示了人生的真谛:人是在生存的现在中创造永恒的意义和价值的。而且,人类生存的现在能够包容过去和未来的时间。无限就表现在时间的现在的包容性之中。所以,“现在之谜是所有时间之谜中最深邃难解之谜。 ”[13]“仅仅由于我们在现在中预期了未来,我们因此便拥有了未来;仅仅由于我们在现在中追忆了过去,我们便拥有了过去。”[14]只有通过对生存的现在加以自我肯定,无穷无尽的过去和未来才是人们自己的,人们也由此获得了存在的无限。
其次,无限表现为人类对于世界的开放性。无限是人类前进和发展的一种要求。人类的思维和实践,可以在宇宙的任何一个方面超越种种限制而无止境地向前行进。虽然有限性就是人类生存的命运,但是,任何有限的东西都不能使他止步。因此,人类无限制地进入已经发现和尚未发现的世界领域,人类完完全全地被引向开放之中。事实上,人在提出问题和实践追求方面都保持开放。这种超越有限的开放性甚至成为人类生存的一个条件。如果某些人,某些民族没有这么一个开放的特点,他们就会落后,就会被别的人、别的民族视为颟顸愚笨的动物。因为人总是对新的事物和新鲜的体验保持开放。只有动物才是固守在一些有限的经验和既定的本能上。
再次,无限表现为有限的自我否定和自我超越。生存时间的有限是对每一个人类个体的生命的否定。而每个人的存在的勇气是对有限生存时间的超越和否定:“无限(作为不受限制的自我超越)的潜在的在场,乃是有限性中的否定因素的否定。这是对非存在的否定。”[15]人的生存中具有生命力和意向性的两极结构。生命力是指那种使每一个有生命的存在物得以生存的力量。意向性是指人的生命力总是同有意义的结构相关联的性质。意向性使人的生命活跃于普遍的理想观念之中。生命力和意向性的两极关系表明,人的生存既有保持他原有形式的倾向,同时又有超越既定形式的要求。而且,“人的生命力是与人的意向性相对照而存活的,并受到意向性的制约。”[16]人的生存是静止和运动、保守和变化、同一和差异的统一。人永远不会满足于自身有限发展的任何一种形式。譬如,人的使命的无限性,不断推动他面向未来的无限性。未来既充满希望,也充满危险。存在是一种冒险。人类生存的无限意义就表现在这种希望和危险并存的永恒超越之中。
人生的有限和无限的关系问题,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哲学课题。我们认为,对于人生的思考,离不开有限和无限的辩证关系。我们要用有限来揭示无限:有限不是走向虚无,而要在自身的否定和超越中构成无限;我们要用无限来规定有限:无限不是有限的吞没,而是有限参与和分有的存在力量。这是一个颇有辩证法意味的人生思考方式。在这种互相联系、互相规定的辩证方式中,人的生存的有限和无限,都获得了具体深刻的内涵。
作为一个生存主义的神学家,蒂利希十分强调哲学的理性思考和宗教的终极关怀的统一。在他看来,单单以人为中心来思考生存问题就会走向迷误。因为人关于自身的知识始终是扭曲了的人的生存的一部分。人的迷误首先表现在人对自我的偶像崇拜。其次也表现在当代人迷恋于物质生活的享受,忽视人的心理和精神的需要,结果造成人以非理性的态度来处理自己的生命和生存,导致当代人和自然、社会的疏远。蒂利希认为,宗教信仰是人类在精神上认识和掌握自己存在的重要方式:“信仰是被存在本身的力量所攫住时的存在状态。存在的勇气是一种信仰的表现,而‘信仰’的意蕴必须通过存在的勇气才能得到理解。”[17]当然,蒂利希所说的宗教不是指传统的狭义的基督教信仰。那个宗教信仰只是关于上帝的崇拜仪式,它已经不再符合当代的思想潮流。当代人或者用科学技术、或者用荒谬的僵死教义使传统的宗教信仰趋于窒息。当代的广义的宗教信仰展示了人类精神生活的深层和基础。它赋予人的生存以存在的勇气和终极关怀的意义。在蒂利希看来,宗教信仰就是一种把存在自身当作体验内容的精神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是人们在有限的生存中追求无限存在的表现。这里,我们从人生的有限和无限的关系上来分析传统宗教信仰和蒂利希所讲的现代宗教信仰的几个根本区别。第一,传统宗教信仰把上帝看成是“最高最完善的存在”,这个存在是现实的,居住在人类不能企及的彼岸世界。蒂利希认为,并不存在一个叫做上帝的存在:“肯定有上帝和否定有上帝一样,都是无神论。”[18]上帝不过是一个隐喻性的象征。上帝一词就是人类用以表达终极关怀的精神存在。人对上帝的信仰,无非是通过上帝来表现的对于自身存在意义的无限追求。第二,传统宗教把信仰和理性认识分离开来,主张信仰的神秘性,把信仰看成是“未见之事的证据。”蒂利希则认为,人的信仰与理性认识是统一的。信仰中必然包含着认识论的怀疑因素。信仰不是对上帝的盲目崇拜,而是人们思考自己的罪和拯救的结果,是上帝对人的终极关怀。第三,传统宗教信仰是人对超自然力量的依赖感和畏惧感的产物。信仰的目的是让卑弱的自我得到全能力量的佑护。这种信仰表现的只是人对自身生存有限性的焦虑和绝望。蒂利希则说:“信仰包含着一种偶然因素并且要求一种冒险。”[19]信仰的表现就是存在的勇气。这种信仰接受了“不顾”,即不顾数不清的否定之物,不顾非存在的威胁。从信仰的“不顾”中产生出了勇气的“不顾”。信仰是从存在上接受某种超越普通体验的东西,从参与和分有存在的力量上获得了自我肯定的勇气。总之,在蒂利希的生存本体论中,信仰作为存在的勇气和终极关怀,把人的生存的有限和无限统一起来了。
在当代西方社会,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改善了,人的精神却在平均化的生产和消费制度下日渐萎蘼,加之社会生活的动荡不安,世界好象真的走到了基督教所说的世界末日一样。于是,一大批西方思想家力图从心理学、历史学、人类学和宗教学中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蒂利希以终极关怀的警示和存在的勇气的呐喊,在当代西方社会中引起了极大的响应和共鸣。西方思想界对蒂利希的思想成就评价很高。利文斯顿在《现代基督教思想》一书中指出:“蒂利希对于我们的精神状态的分析,以及他为基督所作的辩护,仍然不仅在思想上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而且获得了广泛的响应,产生了广泛的影响。”[20]但是,蒂利希对存在和非存在的分析,似乎仍然是不够清晰的。他对人生意义的阐释,似乎也仅仅停留在不可定义的象征语言中。在我们看来,存在和非存在作为西方哲学传统习惯使用的哲学术语,无非是指人和自然、社会的最一般性质。它们的存在并不神秘。人类可以通过物质和精神的实践活动来发现并加以利用。人类存在的勇气也来自人类改造自然和社会的不懈实践以及在实践中建立起来的人生信念。人类正是在无限的物质生产劳动和精神创造的实践活动中,不断超越自身知识、力量和生存中的有限性,获得人自身和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的。这也是人类生存的无限意义之所在。
注释:
[1][2][3][12]Paul Tillich:Love,Power,and Justic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0,PP.39、109、38、78.
[4]Paul Tillich:Systematic Theology,Volume Ⅱ.1957.p.92.
[5][6][7][8][9][15][16]引自刘小枫主编《20 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中卷,上海三联1991年版,第820、850、858、853、 851 、852、839页。
[10][17]保罗·蒂利希:《存在的勇气》,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3、15页。
[11][18]Paul Tillich:Systematic Theology,Volume Ⅰ,1951.Pp.236、237.
[13][14]引自刘小枫主编《20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下卷,上海三联1991年版,第1834页。
[19]保罗·蒂利希:《文化神学》,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 第33页。
[ 20] 利文斯顿:《现代基督教思想》, 下卷,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2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