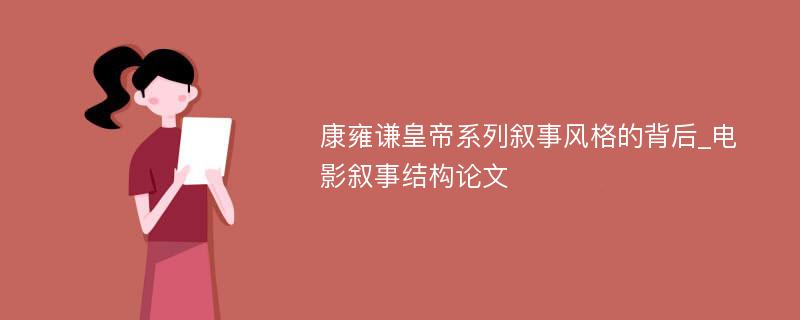
在康—雍—乾帝王系列的叙事方式后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帝王论文,方式论文,系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写中国历史的小说,要让人感到确实像中国历史,有一个历史小说的美学参照,这就是按照古代白话小说的叙事方式。古代白话小说叙事学是古人在古代观念基础上,用完全与古代世界观相符合的叙事方式来叙述故事。今人写历史与古人不同之处在于,一方面,他是在现代世界观的基础上用一种现代的观念去写过去的历史,只有据有这种现代观念,他的历史才能为现代人所接受,另一方面,他用现代观念去写的又是过去的历史,为了让现代人相信他写的是过去,他必须再现历史的原样。而这历史的原样,首先是一种外在形式的原样。所谓的外在形式,一是被叙述对象(人物和事件)的原样,二是叙述方式的原样。对于小说来说,叙述方式的原样更为重要,是叙述方式让人感到这是古代。历史小说所需要的这种艺术形式感觉使得古代白话小说叙事法则具有了重要的影响和意义,从而也成为历史小说在对古代叙事模式的有意识模仿的运用中呈现的相同之处成为其主要的美学特色。另一方面历史小说所产生的现代语境必然使其产生对古代叙事模式的有意和无意的违反,这种违反使之与古代叙事模式拉开了距离,呈现了与古代的不同。比较这相同与不同在各类历史小说中的构成,正好呈现出这些小说的美学特色之一。
二
在古今中外的叙事学理论中,与分析古代白话和今天历史小说相关的主要范畴有:叙述者、叙事次序、叙事距离。从这三个范畴基本上可以对康—雍—乾系列的叙事方式及其所蕴含的内容有一个呈现。
叙述者不是小说之外的作者,而是小说之中叙述故事的人,在对叙述者的不同角度的分类中,具有哲学和文化意义的划分是将之分为三类:大于人物的叙述者,等于人物的叙述者,小于人物的叙述者。这里的“大于”“等于”“小于”突出的是一个哲学认识论和文化真理论的问题,叙述者对自己所叙述的人物知道多少。(1)叙述者大于人物,这类叙述者不但熟悉人物的心理,还知道人物自己也意识不到的内心的无意识想法。它不但知道一人的从外表到内心的全部事情,同时还洞悉作品中所有人物的各自的想法,能叙述一系列不可能被作品中人物所感知的事件。这样的叙述者犹如全能的上帝,不但当下的境况,就是过去的历史和未来的前景全在它的视野之中。古典作品一般都是这种上帝似的全知叙述者。(2)叙述者等于人物,人物知道多少,叙述者就知道多少。人物看见什么,想了什么,感到什么,叙述者就只能讲些什么。人物在,叙述就进行,人物死,叙述就完结。叙述者等于人物又可以分为三类:A.叙述者由一人担任,故事始终是在一个人的视角中进行。加谬《局外人》、卡夫卡《诉讼》都是例子。B.叙述者由几个人物分别担任,如福楼拜《包法利夫人》,叙述先是在查理的视角中进行,然后又在爱玛的视角中进行,最后又转到查理。C.叙述者仍由几个人物分别担任,但几个人物都讲的是同一个故事,同一个故事在不同人物的视角中出现,从而同一个故事被讲得各不相同,构成了多重内聚焦视角。如勃朗宁的叙事诗《指环与书》凶手、受害者、起诉人、被告,轮流诉说各自眼中的案情。叙述者等于人物,特别是在经过享利·詹姆斯的系统运用之后,成为现代小说的基本叙述原则。(3)叙述者小于人物,叙述者知道的比人物实际的情况少。它只叙述人物的外貌、行为、言谈,不进入人物的意识,也不对人物的所作所为做合理的解释和热心的探索。它好像只记录目之所见,耳之所闻,而不去思量和体会人物的心之所想,也不想去追问世界和事件的规律、逻辑、运转机制。达希尔·哈梅特的侦探小说,海明威的《杀人者》等都属此类。
从文学史来看,古典小说的叙述者大于人物,现代派和后现代小说的叙述者等于或小于人物。古典与现代的这一艺术形式上的区分,从文化内容上找原因,在于古典小说对绝对真理的信仰,对小说家应该而且能够从真理的角度把握自己所讲的故事有充分的信心,现代派小说采用叙述者等于或小于人物,表现的正是现代派和后现代派小说家对这种信仰和信心的失去。康—雍—乾帝王系列在形式上是古典白话小说,从而与古典白话小说一样,是叙述者大于人物,在这一质的相同上,康—雍—乾系列又与古典白话小说有所不同,作者生长在古代的文化环境中,对叙述者的全知充满了信心,这体现在说话者的突出,明清小说中的说话者不但常常在小说的开头和结尾亮相,而且在进行之中也常常插进来,对故事、人物、情节进行评论、解释,甚至对读者进行教训,特别是当人物具有复杂性和情节具有多义性的时候,说话人的插入所扮演的全知角色就更明显,他总是拿着正统观念的腔调,通过议论、提醒、说教,控制着整个故事的演进,把整个叙事引向与正统观念相符合的意义之中。在话语形式上,也可以看到,一方面有“话说……”、“却说……”、“表说……”、“但见……”等等句型,显示着故事叙述是在全知叙述者的控制之下,故事不但由叙述者讲出来,而且在讲叙之前所讲之事就已经成竹在胸了。另一方面在故事进行的关键时刻,有“命该如此”、“难逃此劫”、“合当有事”等等规律性词句表明故事再复杂、再离奇、再偶然,又总是在叙事者的内心把握之中。而在康—雍—乾系列里,叙述者仍然是全知的,但“话说……”为引导的首句没有了,叙述者仍然操控着故事的进展,但“命该如此”类的规律之词没有了。从而虽然叙述者在观念内容上仍然有全知型的胸有成竹,但并不在艺术形式上强调自己的心中有数。康—雍—乾系列在全知叙述者上的这种不同于古典白话小说的特点,要由讲叙故事的时代来说明,古代小说用全知叙述者,有着整个文化的全面支持,是一种最主流和最普遍的艺术形式,现代历史小说用全知叙述者,只是诸多艺术形式的一种,没有了普遍的真理性,而且这种方式又处在与其他方式共生的艺术氛围之中,受到了无形的影响。康—雍—乾系列与古典小说在艺术形式上的这种不同又使我们进一步地深考全知叙述者本身的内涵,全知至少可以包含三个层面:一是微观艺术层面,对故事情节和细节的全知;二是中观艺术层面,对故事整体和人物整体的全知;三是宏观文化层面,对故事、人物、情节所蕴含的文化意义的全知。古典小说的全知由于有整个文化的全面支持,因此是完全拥有三个方面的全知,现代历史小说不但没有现代文化的全面支持,而且还处在古今观念多方面的矛盾冲突之中,从而在运用“全知”的时候,在微观艺术层面受到了现代小说形式的巨大影响而不自觉地改变了自己(上面说的“话说……”句型和“命该如此”词型的消失就是这种微观改变的一种表征)。在中观艺术层面,因为要从现代的观念去理解和组织古代的形象和故事而改变了自己(这里康—雍—乾系列里的主要形象多方面地偏离了古代的形象塑造逻辑和故事演进逻辑,对此,后面将要详论),这里只指出一点:就作者用自己时代的观念把握自己的叙述对象来说,是全知的,但就如何从另一个更高的观念来把握自己时代的观念来说,又是不全知的,正因为这种全知中的不全知,给康—雍—乾系列的全知叙述者带来了特点,在艺术形式的全知中让人感到一种对内容意义的若有若无的迷茫。这关联到宏观文化层面。康—雍—乾系列把握住了三大帝历史行为一生,也把握住了三大帝生平的复杂性,但三大帝包含着复杂性的生平伟业的文化意义何在?作者是不清楚的,这种包含着复杂性的生平伟业与古代天道规律的内在关联何在?与现代历史规律的内在关联何在,作者也是不清楚的,因此,康—雍—乾系列中的全知只有了一个现代小说意义上和现代逻辑意义上的把握自己的人物——故事——情节的全知,它既不深入为一种内在逻辑,如在古典白话小说中由数的规律和宿命规律所体现的那样(这两种方式前已有所提及,后面还要详论),也没有外显为一种语言形式,像前面所举的“却说……”句式和“合当有事”的词型那样。又正因如此,康—雍—乾系列在“全知叙述者”上有自己的独特的地位,对此的进一步分析,会被卷进有关整个系列的形象体系的巨大方阵中去而离开本节的主题。暂且打住,回到叙事学的正道上来。
三
叙述者强调的是哲学认识论,叙述者知道多少真理,叙述次序突出的是艺术形式论,故事以怎样一种结构呈现出来。叙述次序主要是所叙述的故事的编年顺序(被叙述故事自身的自然时间,即故事发生的先后次序)与话语出现的顺序(叙述故事采用的艺术时间,即叙述故事的先后次序)之间的对比关系。故事时间是单一的,只有一个。叙述时间则是多样的,随叙事模式的不同而不同。话语时间与故事时间一致,表现为叙事上的顺叙,即按故事时间从头到尾叙述故事,话语时间与故事时间不一致,就有了杂叙、倒叙、插叙。一般说来,古典小说多是顺叙,现代小说和后现代小说多为杂叙。在顺叙中,有多种形式,希腊的史诗和悲剧,喜欢从故事中间的一个关键时刻开始,再回过头去讲以前的事,西方近代作品,也有不少从故事的结尾开始,然后再从头讲起,这些看起来的倒叙,但只有一个倒叙的边框,主体部分还是顺叙。而杂叙则是把整个故事的情节全部打散,叙述不停地在现在、过去、未来中来回跳跃。在顺叙中我们很容易地就看清了故事的演进和演进的逻辑,在杂叙中则一下子看不清故事的演进,弄不明故事的逻辑。古典故事多是顺叙,因为在古典文化中,现实和历史的种种故事与文化思想观念之间有一种明确的对应关系,而在现代文化和后现代文化里,二者的对应关系不是明晰的,而是隐晦、曲折的,甚至根本没有对应关系。中国古典白话小说,少有西方那样加了一个倒叙、插叙边框的顺叙,基本上是从头至尾娓娓道来的顺叙。它尽量少用插叙和倒叙,如果出现插叙和倒叙,也是以顺叙的形式出现的,一是在总的顺叙中以人物解释性说话讲出,一是在总的顺叙中以叙述者来交代,这两方面运用插叙和倒叙,都不是为插叙倒叙而插叙而倒叙,而是由文学叙述本身的时间单一性和被叙述对象的空间多样性所决定,因此从艺术方法上看,虽然也可以说有倒叙和插叙,但在整体的阅读中几乎感觉不到倒叙和插叙,而只是一个与现实或历史行进同步的顺叙。康—雍—乾系列模仿古典白话,也是从头至尾的顺叙,从康熙登基开始,到乾隆退位结束,一桩桩一件件娓娓道来。
四
在中国古典白话小说传统中,作为叙事方式的顺叙,一般包含几个重要方面:一是历史总体叙事用顺叙,二是具体事件叙事上的顺叙,三是话语句式上的顺叙。正是从这三个视角,可以作为我们观看康—雍—乾系列在古今之变中所处的一个位置。
先看第一点。历史总体叙事的顺叙,意味着小说的开始要把所叙之事纳入到一个由文化观念所定义所制约的时空之中,故事是在这样一个文化所决定的时空、以文化所理解的方式开始的。你看《三国演义》第一回前三段。第一段:“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于是依照规律由周末讲到汉末,桓帝、灵帝,朝政日非,不祥屡现,十常侍狼狈为奸。第二段写张角三人黄巾起义,第三段写刘备、关羽、张飞。叙述由规律而历史,由远古而现在,由正面(朝廷)之衰乱引出反面黄巾,由反面的黄巾又引出新的正面:刘、关、张。再看《水浒传》的开头,先讲仁宗皇帝时为瘟疫令洪太尉往龙虎山请张真人,不料洪太尉大意误走妖魔,作为宿命引子,然后,由仁宗而哲宗而真宗,引出高俅,进而徽宗登位,高俅入宠,逼走王进,启动了水浒的现实逻辑。叙述仍然是由历史而现在,有因有果,把故事摆在文化的观念体系之中。又看《西游记》怎么开头。第一段“盖天地之数……”讲一番宇宙构成理论,第二段“感盘古开辟,三皇治世,五帝定伦,世界之间,遂分为四大部洲……”讲一番结合中国历史与佛教理论的历史地理,然后聚焦在东胜神敖来国花果山,山上有仙石,石化为猴,这就是孙悟空。叙述有理论、有历史、有方位,从大到小。在白话小说中,从大到小,从古至今,由理论而现实是一个固定的总体叙事套路。长篇小说是如此,短篇小说也是如此,《三言》《二拍》中,总是在讲一个正故事之前先讲一个小故事,形成一个理论家所说的葫芦形结构,这个小故事的功能,就是要宣告世界的道理都是一样,同类的故事都被统一的世理所制约。这些小故事在功能上,类似于《三国演义》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和《西游记》里的“天地之数”之类。在康—雍—乾系列中,已经没有这样一个历史总体叙事原则。
《康熙大帝》第一卷开头:“顺治十八年正月,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刚过完年,一群一群的叫花子像从地下冒出来似的又开始沿街乞讨。北京城哈德门以西的店铺屋檐下,破庙里挤满了这些人……”这里从历史时间到自然季节到具体人群到具体地点空间,呈出的只是一个历史的具体场景,没有历史的内在规律在其中,看不到宇宙大化的节奏。
《雍正大帝》第一卷开头:“游三吴不可缺扬州,冶扬州不可无虹桥……桥北有个庙……逢到会期,早早的就有城里的商家赶来,错三落五搭起席棚……喧嚣连天……这是康熙四十六年的春天。二月刚过,扬州地气温暖,虹桥两岸已是春花姹紫嫣红,芳草新绿如茵,一个驾着双拐的残疾人出了桥南的‘培鑫客栈’慢慢的踱着……他叫邬思道。”这算是有了由大而小的叙套,但更像一个现在的电影镜头的远、近、摇,仍然感受不到历史律动和宇宙韵节。
《乾隆大帝》第一卷开头:“眼下过了立秋,可天气丝毫没有见凉的意思。接连几场大雨都是旋下旋停……德州府衙坐落在城北运河岸边……靠码头东边申家店里,店老板和三四个伙计袒胸露腹地坐在门里面吃茶打扇摆龙门阵。”这里连由大到小的套路也没有了,只呈出一个具体的场景。
以上三例,第一第二尚有由大到小的艺术形式遗痕,第三连这些遗痕也不见了。不从与古典白话小说的对比,而从第三的视角去重看第一第二,便可感到现代的历史小说是按照现代小说的普遍法则:由小到大,即从一具体开始,逐渐扩大开去。这一具体可以是场景,也可以是人物,还可以是行动。为了进一步感受这一古今之异,不妨看看另两部现AI写作的历史小说。
《曾国藩》第一部开头。首先是一个点:“湘乡县第一号乡绅家,正在大办丧事。”然后,由点扩大,对这个点进行以空间为主体的叙述:“这人家姓曾,住在县城以南一百三十里外的荷叶塘都。荷叶塘位于湘乡、衡阳、衡山三县交界之地……”由大而细,用三大自然段写曾家的自然环境,曾家内外办丧事的情况,最后才落实到人物上“灵堂东边的一间厢房里,有一个六十二三岁、满头白发的老者,面无表情地颓坐在雕花太师椅上,这便是曾府的老太爷,名麟书,号竹亭。”然后才加进时间的叙述,从清初的曾家祖上到清末的曾老太爷。虽然可以感到古典白话小说的手法,但叙述主体上,受到了电影镜头叙述的影响,以具体为主,在话语形式上感受不到历史规律和宇宙规律。
再来看自认为在形式上模仿古典白话小说的《射雕英雄传》的开头:“钱塘江浩浩江水,日日夜夜无穷无休的从临安牛家村边绕过,东流入海。”这形式上有点古韵,但内容上了无古意,只是具体地点的空间标志。接着到了“江畔一排数十株乌柏树,叶子似火烧般红,正是八月天时”。具体的带着自然时间特点的空间景色描写之后,进入了正题:一群男男女女大人小孩正在听一个老者说书。讲了好几个自然段,还不知道这些人这块地是在什么历史年代。
从以上两部现AI写作史小说可知,无论运用了什么古典白话小说的元素让人感到一点古意,但在主体上是现代的从具体的“小”开始,历史总体叙述消失了。最深的根源在于古代的历史观和宇宙观已经被现代的历史观和宇宙观代替了。经历了对西方近代型历史观和苏联型历史观的接受信奉而又开始对之有所怀疑的20世纪末期,历史观和宇宙观正处在清楚与模糊之间,无论怎么开头,都没有了历史总体叙述。
五
再讲第二点,具体事件叙事上的顺叙。古典白话小说,不但在一个大的事件的叙述上用顺叙,怎么开始,怎么发展,怎么了结,从头讲到尾,而故事的进展在表层故事上,有一种中国古代的线的美感逻辑,在深层内涵上,蕴含着古代宇宙的内在规律。表层故事的线的美感,在《西游记》中很清楚,首先是石猴孙悟空的故事,从出生到大闹天宫到被镇五行山,接着是唐僧的故事,从父母罹难,到复仇,为了唐僧取经,插进唐王故事,唐僧西行,收救孙悟空,开始了一个个取经故事。这种线的逻辑在《水浒传》,先是几世之前洪太尉误走妖魔,后是几世之后高太尉逼走王进,开始了史进的故事,由史进引出鲁智深的故事,梁山好汉按线型一个个或一组组登场。但在表层故事的下面,有一种深层的宇宙逻辑,它表现为多种方面,这里仅从数的规律上讲。前面讲过古典章回小说在整体都为一个完满的数,100,120,72等等,这是与历史总体叙述相关。而与具体事件关联的,则是叙述具体事件中的“数”。美国汉学家浦安迪研究出:《西游记》《金瓶梅》明显的是每十回形成一个单元。1~9回,10~19回,20~29回……就是说1~9回讲一个大故事,10~19回讲另一个大故事。大故事如此,小故事也是如此,《西游记》里有孙悟空三借芭蕉扇,《水浒传》里有宋公明三打祝家庄,事件皆到“三”而完成。《红楼梦》中刘姥姥三进荣国府,成了贾府由盛而衰的时间征兆。只是不但故事的表面进展符合人情物理,而且在深层方面又契合于文化的宇宙模式、历史宿命、伦理规律,具体叙事才有了丰厚的内容和无穷的意蕴。
康—雍—乾系列有一种宏伟的历史结构,这种宏伟表现为复杂结构,以《雍正大帝》第二卷“雕弓天狼”为例,写雍正登位后在多方面的斗争中走向胜利。该卷从领兵的十四子被带回京开始(以十四子大闹灵堂开始雍正登位的第一场斗争),以带兵的年羹尧被赐自尽结束(以最危险的对手被雍正消灭标志雍正已经大局稳定)。整卷中包含了多方面的冲突,有雍正与旧的政敌、也是前面一卷中与雍正争位的主要对手八爷和十四爷党的斗争;有雍正与原来的坚定支持者老部下但在新的形势中变成对手的隆科多(倒向八爷党)和年羹尧(具有新的野心)的斗争;有雍正的儿子弘时与弘历为争夺接班人而进行的斗争。在这三种大势力的斗争中,有官场的普遍腐败,有外敌的巨大威胁,这两种因素与前面讲的三种斗争纠缠在一起,在这五大方面的纠葛之中,雍正时代新人孙嘉淦、杨名时、田文镜、李卫、李绂、刘墨林等,一一出场,展开得波澜壮阔。但是在“雕弓天狼”中,这种宏伟和复杂化为具体叙事的时候虽然仍然是用顺叙,但不是以“线”的方式呈现,而是更兼顾各方的同时性,线成了历史总体的顺叙之线,而具体为各方的时候,经常出现相互插入。具体叙事的顺叙成了一个带有西方几何型的方块,也像电视片中的同时性互插。全卷一共50回,前20回中,至少有20段以上的故事,在数量这样多的故事中,只有四个故事算得上具有线的意味:一是第1~3回,十四爷回京,二是杨名时发现科考舞弊,三是田文镜斗诺敏,四是刘墨林的故事。在这四个故事中,严格地说,第一个故事即十四爷的故事只是整卷故事的引子,故事性不强,后三个故事中,完整而呈线型的只有田文镜的故事,杨名时的故事是断的,在第六回开始被其他事切断,在第十三回才出现高潮,结案在第十五回,则用的是虚笔。刘墨林的故事是四个故事中最具有故事性的,从第十七回到第二十回,用的笔墨最多,形象面也最丰富,但一方面在讲刘墨林的故事时,插进了田文镜的故事,另一方面,刘墨林故事中最具有故事性的是他与苏舜卿的爱情,这个故事却是断断续续,从第十七回第十八回后,到第二十九回重出,第三十七回又重出,被其他事插入后,第三十九回苏舜卿死亡。一个整故事分成了四段。我们看到康—雍—乾系列中,顺叙还是顺叙,但具体的方式已经变化了,而且最主要的是古典小说中深层意蕴没有了,呈现出的只有现实中的斗争。
六
最后讲第三点,话语句式上的顺叙。这里主要指的是直接引语。在古典小说中,直接引语都是说话人摆在前面,用一个“道”引出直接引语,如,某某说道“……”,某某笑道“……”,某某哭道“……”,等等。这是一种与顺叙最相一致的形式。西方小说进入中国产生影响以后,用现代汉语写作的小说里的直接引语有了变化:一是把说话人放在前面,形成某某说“……”;二是把说话人放在中间,形成“……”某某说“……”;三是把说话人放在后面,形成“……”某某说;四是只有直接引语,省略了“某某说”,形成“……”。到现代派小说大量进入中国产生重要影响之后,1980年代的中国先锋小说里,直接引语又产生了新的变化:不但可以省略直接引语的说话人,还可以省略直接引话的引号,进而可以省略一切标点符号。受西方古典小说影响的现代汉语小说与中国古典小说不同的三种直接引语形式,虽然在文字顺序上与顺叙的主调不一致,但从西方文化几何美的观点看,并没有改变顺叙的基调,而从一个情景的立体性上细分先后顺序。在具体情境中,一个人说话,我们先看人后听声音,构成说话人在直接引语前的句式;先听见声音,后看人,形成说话人在直接引语后的句式;先听见声音,再看人,继续听说话,形成说话人在直接引语之中的句式;只注意听声音,不注意人,形成省略说话人的句子形式。因此,这三种直接引语的出现是在世界小说总体的顺叙基调里,中国古典的线之美的顺叙与西方古典的块之美的顺叙在现代中国的融合,而受西方现代派影响的中国先锋小说,其直接引语的新变化(省略引号和不要标点等等)是与其总体叙事的往来古今、打散时空相一致的。现代历史小说,由于以顺叙为叙事的主调,没有现代派的省略引号和省略标点符号等情况,却可以承继现代汉语的三种区别于中国古典小说的句式。但只要一运用这三种形式,就意味着在顺叙总基调上的意境变异。这样以古典小说为原点来对照现代历史小说,可以看出现代历史小说在历史观念和美学观念上的变异。还以我们前面一再举的三部小说作比较。金庸《射雕英雄传》全是说话人在前,用“道”引出直接引语,呈出严格的仿古形式,也符合金庸本人自道承继古典的主旨。唐浩明的《曾国藩》则运用了现代汉语小说中直接引语的所有方式:有说话人在前,有说话人在中,有说话人在后,也有省略说话人的。在《曾国藩》第一章“二”中,共有直接引语25次,其中说话人在前14次,说话人在中3次,说话人在后6次,省略说话人2次。在第一卷第五章“四”中,直接引语共77次,其中说话人在前49次,说话人在中4次,说话人在后9次,省略说话人15次。对直接引语的多方面使用正与他在章节标题和叙述对象的时代性相契合。在四种直接引语形式中,说话人在前是中国古典标准句式,因此,说话人在前的句式总是比其他三种句式的总和还多(注:当出现例外时,总有原因,如《曾国藩》第三卷第一章“一”中,慈禧回忆自己在圆明园初遇咸丰皇帝一段,共有直接引语11次,说话人在前的只1次,省略说话人的有4次,说话人在后的有6次,后者最多正与回忆本身的倒叙相契合。)。表明了中国古典小说顺叙原则的影响,也说明了历史小说的历史感与说话人在前这种句式的美学联系。在直接引语的四种形式中,说话人在后最具有句式上倒叙的意味。康—雍—乾系列运用了四种形式,最多的是说话人在前,其次是说话人在中,也有省略说话人的,但最少的是说话人在后。列表如下:
篇名总数说话人在前说话人在中说话人在后省略说话人
《康》第二卷1回 4722 17 5 3
《雍》第二卷10回6937 21 0 11
《乾》第四卷17回7741 19 2 15
说话人在前占了主导地位,表明了总体顺叙对句式上的巨大影响,其他三种句式的出现,表明了总的顺叙基调又有了向西方顺叙的新质。
七
现在讲距离,距离是指故事内容与读者的距离,在现实中,一个对象离我们太远,就看不清楚它的具体面目,离我们太近,则看不清楚与对象有密切关联的背景,在小说中也是这样,让故事内容与读者处于一种什么样的距离,包含了小说的总体趣旨,故事内容是多种层面的统一,距离也体现在故事内容的多个层面上。
从叙述者方面来说,小于人物的叙述者,在对具体形象的叙述上距离最近,但具体与整体的关系距离最远。正如我们在现实中观看随缘碰上的陌生人,看见其外在体貌言行,近在眼前,因为是第一次看,特别引起注意,从外在感受上的最近;但由于看不见性格的完整和内在心灵,又感到模糊迷茫,好像很远。等于人物的叙述者,在具体形象的叙述上,距离很近,宛如我们在现实中碰上的朋友,我们不但观看到他的外貌言行,也知道一些他的人格个性和内在心灵,我们的感受焦点不仅停留在他的身上,而且也同时游目在他此时外貌之外的与他个性和心灵相通的某些时空里,因为熟悉,我们可以知其前,推其后,因此比小于人物的叙述者远一点。大于人物的叙述者,我们不但知道人物自己知道的东西,还知道人物不知道的东西,这样就是在具体地叙述人物的时候,也是从一个更高更全面的视点去叙述的,因此距离最远。
小于人物和等于人物的叙述者之所以让人感到距离较近,因为这两种叙述者都采取了呈现的叙述方式,这种方式让我们直接看到对象,大于人物的叙述者之所以让人感到距离较远,在于这种叙述者一般在呈现对象的同时也呈现了呈现者。前者让我们感到我们是直接在观看对象,后者让我们感到有一个人在为我们呈现对象。看两段二月河的句子:
《雍正皇帝》第三卷“恨水东逝”第一回第一自然段的开头:“深秋,凄风苦雨中,一队络车在泥泞的黄土驿道上艰难地行驶。”就是只有呈现。
该回的第二自然段的开头:“络车最后连的是马陵峪总兵范时绎。这是一个四十五六岁的中年汉子,四方白净脸,平平的两道一字宇眉像是用毛笔画出来的,只眉梢稍稍向上挑一点,透着冷峻的傲岸。”
前一段是距离较远才看得清楚的全景,距离较远,后一段是一个从近景转特写的句子,距离很近。但前一段只呈现叙述对象,在叙事学的意义上,距离较近,后一段在呈现对象的同时又通过“这是”呈现了呈现者,在叙事学的意义上距离较远,当我们感到是通过一个人的指示,才看到一个近景特写时,我们就觉得这一近景特写离我们很远。从这两个例子中可以知道,康—雍—乾系列在近距离地叙述对象的时候,用了出现呈示者方式(“这是”)也使距离显得远,在只呈示对象的时候又采用了整体叙述方式中的全知视角(“深秋,凄风苦雨中”)也使距离显得远。
在人物描写中,直接呈示内心独白,距离最近;通过“他想……”间接呈示内心世界,距离远一点;少用心理描写,直接写人物的外貌、言语、行动,就更远一点。康—雍—乾系列与中国古典小说一样,很少有心理描写,基本上没有内心独白,主要是事件的发展和演进,人物的行动和语言,因此距离较远。下面是《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三部著作第一回中有关心理描写的情况:
篇名自然段数 心想(有内容)处
心想(无内容)处内心独白
《康》第一回56 2
4 0
《雍》第一回52 4
2 0
《乾》第一回40 2
0 0
从上表可见,心理描写很少,无内心独白,主要为两类:一是提及心想,又说出想了什么;二是提及心想,但没有说想了什么,不过这没有说,不是不知道想了什么,而且想了什么已经很清楚,勿需写出。
在人物语言中,省略说话人,距离最近;说话人在话语之中和说话人在话语之后,距离稍远;说话人在前,距离最远。从上面的表中,可以见到康—雍—乾系列中,说话人在前的次数占了一半以上。
通过以上叙述者、叙述方式、人物描写、说话句式的考察,可见康—雍—乾系列在叙述者上采用大于人物的叙述者,在叙述方式上,采用了整体视角和带有呈示者的叙述,在人物描写上,多用外貌、行动、言语,在说话方式上多用说话人在前的句式,都是与叙述对象拉开一定距离的方式,呈现出一种对历史的方式,这就是冷静的态度、哲学的静观、理智的沉思。康—雍—乾系列在叙事学的三要素上用全知叙述者、从头到尾的顺叙、冷静的远距离这样的艺术形式,展示了什么?述说了什么?又寓意了什么呢?
标签:电影叙事结构论文; 直接引语论文; 小说论文; 叙事手法论文; 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历史规律论文; 西游记论文; 读书论文; 曾国藩论文; 历史小说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