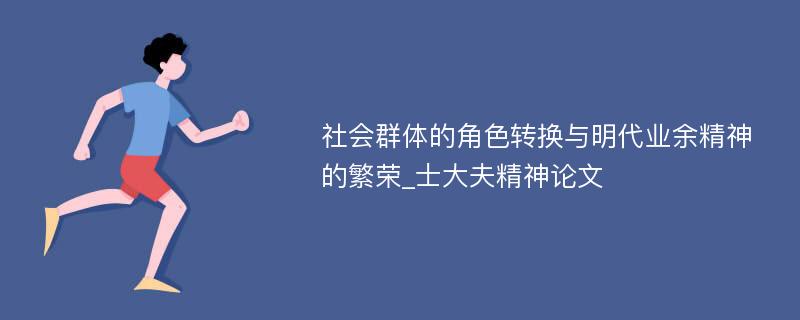
不务本业:明代社会群体之角色转换与业余精神之勃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群体论文,明代论文,角色论文,精神论文,务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14)05-0127-10 一、引论:从“世事十反”说起 若以文字训诂为视阈,所谓的“业”,原本为上古无文字之时,刻木如巨齿之状,藉此记录每日所行之事数。每当一事完毕,则去除一刻;所有事情完毕,则尽去其刻,称为“修业”。变更所业之事,则重新如前加刻巨齿。凡有大事,则大刻,称为“大业”;凡有多事,则多刻,称为“广业”;士、农、工、商所业不同,称为“常业”;农民改业成为读书人,则改刻,称为“易业”。基于“业”字训诂之义,有学者进而加以引申,得出重业之论,即古人一生无不有所业之事,每日无不处于修业的状态,通过身修事理,藉此避免怠惰荒宁。反之,若是“无业”,则会流于昏昏荡荡,偷安惰行而死。[1] 在传统中国的等级制度下,民安其业或者说四民各有定业,既是知识阶层的理想追求,又是历朝统治者确立大统之后付诸社会控制实践的基本国策。正如六朝时人颜之推所云,人生在世,需要各具本业,诸如农民之“计量耕稼”,商贾之“讨论货贿”,工匠之“致精器用”,伎艺之人之“沈思法术”,武夫之“惯习弓马”,文士之“讲议经书”[2],都是他们应尽的本等职业。先秦时期管子确立士、农、工、商四民等级,使之成为不再游移杂处的“石民”,其目的就是为了避免“言吪”、“事乱”的杂处之弊。其后的儒家学者,倡导士人安处闲燕之地,农民辛勤耕作于田野,工匠服务劳作于官府,商人奔走于市井,通过旦暮从事于各自的本等之业,不再见异思迁,藉此以安民心,以定民志,最终达到天下大治。[3] 就传统中国的职业观而言,显然具有以下两大特点:一则“有事必有业”,“人各有业”,肯定各类职业存在的可能性乃至必要性。换言之,职业固然有贵贱之分,然均可藉此“营生”。一旦具备维持家庭生计的内在推动力,即使所从事的是“淘圊”之类的职业,亦能达臻“鼻忘其臭”的境界。[4]“学业”、“农业”诸称,以及农民有畎亩之事,工匠有器用之事,商贾有市肆车牛之事,已经足以证明“未有为其事而无其业”这一基本准则。[5]一旦废业游手,就会流于不肖。随之而来者,则是在传统史料中,“不事本业”、“不务本业”之说,通常与“游手好闲”之“光棍”并称,亦即将“不事本业”者归于无赖游民一类,藉此形成一种“各业其业”、“各事其事”的理想境界。[6]换言之,人若不列入四民之中,则称“闲民”[7]。无论士、农、工、商,吃一日饭,做一日事,都是世间良民。若是游手嬉闲,浪度岁月,就会沦为匪僻之流。[8]二则职业各有等差,甚至有贵贱之别,择术不可不慎。在士、农、工、商四种职业中,士为四民之首。按照传统的观念,除了“耕读”二事,其他无一可为,诸如:商贾近利,容易坏人心术;工技为人所役使,近于贱业;医卜之类,又下工商一等;此外各业,则更为低贱。[9]传统观念所谓的快乐,仅仅愿意肯定“读书乐”、“田家乐”两种,力图宣扬只有务本业之人方可其境常安。[10] 时至明代,职业分化渐趋明朗化。以苏州一带为例,农业获利最少且又辛劳,只有“愚懦之民”尚以农耕为业;奇技工匠能获二倍之利,且又兼辛劳,惟有“雕巧之民”仍以此为业;商贾可获三倍之利,且又轻松安逸,于是“心计之民”纷纷以此为业;贩盐可获五倍之利,且又无辛劳,更使“豪猾之民”以此为业。[11]与此相应,即使作为四民之首的士人,其职业亦日趋变化:一方面,由于汉、宋两代儒家学者的误导,使士人专攻章句之学,再加之科举的引导,士人更是汲汲于帖括八股。其结果则使自古以来士人通过礼、乐、射、御、书、数等业借以谋道之术,荡然无存,而儒家士人转而不得不借助农圃、风鉴、医、卜之术谋生。[12]另一方面,那些世代簪缨的世家子弟,既不读书,又无一业自给,只是终日嬉笑,坐食山空,最后沦为游惰之民,甚至身为臧获皂隶,为盗为娼。[13]这无疑是明代社会流动加剧的背景下的职业分化。 朱元璋建立大明帝国以后,通过一系列社会控制措施的实行,四民等级秩序得以重建。自明代中期以后,随着社会流动的加速,出现了“世事十反”的特殊现象。何谓“世事十反”?根据明末人冯梦龙的概括,主要表现为以下十种表象:达官不忧天下,草莽之士忧之;文官多喜谈兵,武官却不肯厮杀;有才学人不说文章,无学之人偏喜说文;富人不肯使钱,贫人却肯使钱;僧道茹荤,平人却多吃素;闾阎会饮大多通文,秀才却反显粗卤;有司官多裁抑豪强,乡宦却又把持郡县;官愈尊则愈言欲退休,官愈不达则愈自述宦迹。[14]由此可见,所谓“世事十反”,既是十种反常的社会现象,又是明代社会群体角色转换乃至业余精神勃盛的典型征候。 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时代风尚,其结果则造成时人纷纷追求业余爱好,无不以此作为一种时髦。这更是一种不务本业的特殊现象。细究之,又可分为以下两类:一是地方官员任意役使很多职业人士,令其整日在衙门中伺候,使他们无暇从事自己的本业,尤以阴阳生、医生、塾师为甚。①这可称之为被动的不务本业。二是很多职业人士,由于受到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不再坚守自己的本业,而是更喜欢从事与本业无关的事务:诸如虽不擅长书法,笔砚却讲求精到;虽不以医为业,家中却多存有经验之方;虽不工于弈棋,书斋案头却必备楸枰。[15]这可称之为主动的不务本业。两种现象结合在一起,不仅造成了明代社会群体角色转换的频繁,更使业余精神达臻勃盛。 二、“缙绅余技”:士大夫之业余精神 明代中期以后,士大夫的社会角色转换颇为频繁,业余精神更趋勃盛。究其社会史的原因,显然与士之失职甚或游士层的形成有关。自古以来,学者栖息有所,出游有方,游学属于不得已之举。遐方僻郡的士人,前往中原求学,或游于京师,其目的大者在于成就自己的学问,小者则为成就名声。一至明代,士穷失职,伏处闾巷,不仅难以获取生计,更难成就名声,于是不得不奔走四方。等到倦游而归,却又大多无半亩一丘之地可以营造草堂,安置书籍,藉此徜徉忘老。士人出游,盖有其因。明代士人不仅好游,而且出游无方。这就是说,明代士人大多好游,有得则忻,无得则戚,甚且因老困而无所归趋,由此形成一种“游病”[16]。所谓士人的“游病”,就是士人出游,不再追求学问,仅是为了成就自己的声名。在这些出游的士人群体中,其中卑卑曳裾之人固可无论,即使那些所谓的高尚之士,亦不过是“挟一策一卷,往而师一先生,谒当世大人数辈,投刺名下士数辈,归而索赠言十数通,评文满纸”,希望藉此在众人之前大加炫耀,宣称“某吾师也”,“某吾友也”[17]。可见,自明代中期以后,在士、农、工、商四民之中,无不习染“游惰之习”,其中又以士人为甚:“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而已;群居终日,言不及义而已。”[18]究其为害,甚至更甚于“游民”[19]。 按照六朝人颜之推的说法,儒家士人原本应该秉持一种“素业”,亦即“清素之业”。而事实上,早在六朝,士大夫已有不务本业之习,此即所谓“耻涉农商,差务工伎,射则不能穿札,笔则才记姓名,饱食醉酒,忽忽无事,以此销日,以此终年”。其结果则“及有吉凶大事,议论得失,懵然张口,如坐云雾;公私宴集,谈古赋诗,塞默低头,欠伸而已”[20]。在明代的士大夫群体中,这种现象得以再现,且较之六朝士大夫更甚。借用晚明名僧袾宏的说法,就是出现了一种“儒昧当务”现象。举例来说,如孔子号称儒之宗主,理当被青衿之士朝夕礼拜而加以供养;然明代的士人舍弃孔子不拜,却去侍奉文昌帝君,且极尽恭敬之能事。《六经》、《论语》、《孟子》,理当为士人朝夕信受而加以奉持;然明代士人舍弃这些不读,却去奉持《准提咒》,且竭其虔诚之能事。如此不分“当务”之事,其目的均在于藉此求取富贵。[21] 揆诸明代士大夫之角色转换乃至业余精神,大抵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论之:一为文人尚武之风的形成;二为业余精神之勃盛。 (一)文人尚武之风 从仕途的角度而言,对明代的文、武关系大体可以概括如下:明初文武合一,甚或重武轻文;明代中期以后,文武异途,甚或重文轻武。自正德、嘉靖以后,出现了一种“儒将”的说法。“将”而又“儒”,并非是“文武全才”的典型,而是武将抛弃自己的习武本业,去附和文士的习气。与此相应,巡抚、巡按也以文字的优劣作为荐扬武将的标准,兵部也据此作为任用的尺度。而晚明文、武关系的实际演进过程,却是文人尚武精神的形成,进而投笔从戎。这一风气由丘濬开其端,倡导“文武一途”,继之者有唐顺之、赵本学、郑若曾、陈第、茅元仪、曹飞、陆世仪等,从而形成一股文人“尚武”与“重兵”的风尚。 传统文人大多胸怀大志,然一旦科场失意或干谒不成,就只好投身边塞戎幕,以为晋身之阶。明代的文人也不例外。如嘉靖年间,倖臣胡宗宪、赵文华辈,开府浙江。时世宗方喜祥瑞,争以表疏称贺博宠,词人纷纷入幕,诸如胡宗宪幕府之徐渭、沈明臣、赵得松、朱察卿。[22]文、武失其本色,是晚明的基本特点。对文人来说,时势动荡,正是他们大显身手的时机,于是纷纷“抵掌而谭孙吴,恨不得一当单于,以暴其能于天下”[23]。如以文士著称一时的赵时春,却“喜骑射谈兵,日以边备不修为恨”,其志向则“专在攘夷狄复祖宗之疆宇,遗后世以长治久安”[24]。更有一些文人,效班超投笔故事,毅然弃去文章之事,以武胄起家,成为将军。如何南吉,死后被茅坤称为“谁言将家子,耻做一文儒”[25]。至于陈第,更是投笔从戎的著名文人与学者,其例在此不赘。尽管明代文士娴习骑射,其目的或许是为了达到“立致边都”[26],起到躐等而用的效果,却不能不说是明代士大夫业余精神勃盛的一大佐证。 (二)业余精神 明人沈德符以“缙绅余技”概括士大夫业余精神之勃盛。所谓“缙绅余技”,大抵是指士大夫安享太平之乐,纷纷将他们的聪明才智“寄之剩技”,即各自有业余爱好,甚至达到专精的境界。如吴国伦擅长击鼓,技艺高超,甚至到了渊渊有金石声的境界;苏州一带的士大夫大多留意声律,太仓人张新、吴江人沈璟、无锡人吴澄时,无不工于度曲,每次广坐命技,即使老优名倡,亦多皇遽失措,真可谓不减江东公瑾;至于京城,驸马王昺、锦衣卫指挥张懋忠等,亦是擅长蹴鞠,堪称精绝。[27] 尽管儒家学说不乏“游于艺”之说,然其终极追求还是在于修齐治平之术。即使闲暇时所习之“艺”,明代学者仍将其定出轻重之分,即所谓的“学文胜学诗,学诗胜学书,学书胜学图画”。这就是说,诸如学文、学诗、学书、学图画之类的技艺,可以起到垂名法后之效。下此一等,则为弹琴、弈棋,尚不失为清士之举。除此之外,则均可归于“末技”[28]。 仔细考察明代士大夫的业余精神,大抵集中于精于书画、文具、器械诸方面,甚至不乏精于卜筮、禄命之学的例子。 清人钱泳曾有言:“大约明之士大夫,不以直声廷杖,则以书画名家,此亦一时习气也。”[29]抛开“直声廷杖”不言,所谓的“以书画名家”,显已一语道破了明代士大夫业余精神之勃盛。钱氏之论的依据,显然是指如文徵明、祝枝山、董其昌、吴宽、李贞伯、陆子传、王雅宜、张东海、娄孟坚、陈鲁南、王百谷、周公瑕之流,无不以善书著称一时,且成为当时案头的珍玩。事实确乎如此。明代苏州善于书画的名流,如文彭、王宠,都是精通画学,显然是受到了唐寅、文徵明等人的传习熏染。此外,如刘基之精于山水,酷似李营邱;岳正之精于蒲桃,几同温日观;王直亦工绘事,尤非后生所及。[30] 士大夫之精于文具制作,则可以沈炼、周岐凤两人为例加以说明。史称沈炼因得罪权臣严嵩,系狱长达18年。在狱期间,读书之暇,傍攻匠艺,不用斧锯,仅以片铁日夕磨琢。沈炼曾以尺许香楠为材料,雕琢文具,制成三个大匣、七个小匣、二个壁锁,又用棕竹数片,制成扇子一把。其制作之精好,巧匠亦叹为弗如。此外,沈炼还以粥炼土,经过数年之久,制为两只铜鼓,可以声闻里许,品质远胜暹罗铜鼓。又周岐凤,不但能诗,而且深具巧思,“文房器用、裳衣冠屦悉自制,良工莫及”[31]。 至于士大夫深具巧思,精于器械制作,则以黄子复、严寅为典型。史称黄子复,擅长巧思,所制木偶,靠机关运作,无异生人。他曾用木头制作一个美女,手捧茶橐,可以自行移步供客。客人举瓯啜茗,即站立以侍,茶瓯返于橐,即转过其身,仍内向而入。又制作一个小木偶,在席间以木偶传觞。其行止一视觞之举否,周旋向背,不借人力。此外,他还用木头制成一犬,上面蒙上真皮,犬口可以自行开合。在牙端攒聚小针,可以衔人衣裔,挂齿不脱,与真犬一般无异。[32]严寅在正德、嘉靖年间曾为府学生员,后因哄闹提学御史,被褫夺生员科名。史称其字法米帖,粗能写诗及画兰竹,收藏古法书名画颇多。严寅又精于制作,所制藤床、藤椅,均以藤制成,不加寸木。他还制作了枣根香几,天然为之,不加凿削,最称奇品。此外,他又精于煮茶,所用茶具,无不佳妙。[33] 星相、堪舆,均可归于术数之学,非儒家倡导的正学。反观明代的士大夫,却对这些术数之学,“人人能讲,日日去讲”[34]。朱升、万祺的例子,已经足证此说不诬。史载朱升博综群书,即使是数学、卜筮,亦“靡不精究”[35]。史称万祺少时曾遇到异人,曾传给他《禄命法》一书。经过钻研,万祺精通其学,“以卜公卿贵人,多奇中”[36]。 何以明代士大夫业余精神如此旺盛?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名士风流之风的影响。至于名士风流,明人何良俊曾以王西园为例,加以定义性的阐释。王西园曾为岁贡生出身,任太顺训导,被何氏许为“最有胜韵”。那么,他的“风流”乃至“胜韵”包括哪些?何良俊进而阐述道:其一,王氏“善书画”,“每一入城,好事者争趋之,其舟次常满”。其二,“喜歌曲”,“曾教妆戏者数人,名丹桂者亦有声”。其三,“其室中畜侍姬三四人”,以供“笔砚图书”[37]。由此可见,业余精神大抵已经成为名士风流的精髓。 三、“经文纬武”:武将之业余精神 自弘治、正德以后,一些武将开始沉浸于翰墨之事,且以习文为雅事。武之好文,成为一时风尚。究其所由,明代学者唐枢有下面一番剖析: 国初以将对敌,举动自由,以渐而制于群珰之出镇,乃设巡抚以制群珰,又渐而制于巡抚之总督。重臣握兵权,籍巡按以为纠参,又以渐而制于巡按之翻异。随在掣肘,不得不文,以为自御之计。且文臣轻辱鄙陵,动以不识字为诮。及其荐剡,则右文而后武,又不得不文,以为自立之途。于是天下靡然,莫知其自为武,岂安不忘危之道哉![38] 武将好文,盖有其因。明人徐学谟云:“武人而耽翰墨,即阶阃帅。”[39]此说可作前论的补充。 明代武将耽于翰墨,专力于业余精神,大抵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论之:一为武将擅长诗文,甚至不乏精通词曲之例;二为武将喜与文人交往,且聘幕成风。 (一)武将耽于文艺 武人能诗,自古以来,不乏其例,尤以晚明成为一时风气。明代武将能诗者,有沐昂、俞大猷、郭登、李言恭、万表、陈第等,其诗“皆见英雄本色,有文士所不能道者”[40],并非只能写“明月赤团团”一类俗句。尤其是戚继光,因深得文坛名人汪道昆、王世贞的称道,俨然以风雅自命,幕客郭造卿辈,尊之为“元敬词宗先生”,几与缙绅分庭抗礼。又萧如薰,亦以翰墨自命,山人辈纷纷投入幕中,尊称其为“季馨词宗先生”[41]。其他如杜弢武,亦甚好文,建曲馆,以“经文纬武”镌其斋,作有《餐霞外编》。[42]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根据清朝人刘廷玑的记录,明朝武将能诗之人,分别有:定襄伯郭登,著有《联珠集》,其代表作有《湳牙山》、《普安道中》、《入缅取贼早发金沙江》、《军回》、《寄泾州守李宏》、《梅子》、《塔顶》诸篇;参将汤胤勣,其代表作有《题壁》一诗;戚继光著有《止止堂集》,其代表作有《登石门驿新城眺望》、《盘山绝顶》、《度梅岭》诸诗;俞大猷著有《正气堂集》,其代表作有《挽薛养呆》一诗;万表著有《玩鹿亭稿》,其代表作有《悯黎吟》、《山亭纳凉》、《宫女叹》、《和徐东滨》诸篇;参将余承恩著有《鹤池集》,其代表作有《感兴》、《答草池约泛蓉溪》、《放舟行》、《望忠州》诸篇;都督张通著有《游西林庵》一诗;京营都督周于德,著有《平乌剌江》一诗;指挥张元凯,著有《伐檀集》,其代表作有《春日游西苑》、《西苑宫词》诸篇;千户李元昭,著有《岣嵝山房集》,其代表作有《送周虚岩归吴》一诗;参将黄桥栋有《听秀上人弹琴》一诗;右都督张如兰,著有《功狗集》,其代表作有《吴门夜泊》一诗;参将狄从夏有《月夜同刘天山作》一诗;守备袁应黻有《郑司马入塞歌》;百户奚汝嘉有《旅怀》一诗;百户陈鹤著有《海樵集》,其代表作有《夜坐见白发寄别朱仲开、张瓯江》、《高邮赠龚山人》、《泊京口望金山寺》、《题杨法部容闲阁》、《写山水》、《题画赠姜明府》、《送张伯淳还关中》、《送王谏北山》、《吹笛怀友》;游击将军陈第著有《寄心集》,其代表作有《岁暮客居呈焦弱侯》、《邵武舟次》、《禹碑行》、《山中蚤秋》、《江心寺除夜》、《闽关旅夜》、《维扬谒文信公祠》、《过蓟州》、《追怀宜黄大司马谭公》、《元夕宿泉州洛阳桥》、《送戚都护》、《塞外烧荒行》诸篇;临淮侯李言恭著有《青莲阁》、《贝叶斋》、《游燕》诸集,其代表作有《花朝》、《赋得匡庐山》、《送仲弟南还兼怀老亲》、《李佥宪招饮黄鹤楼》、《显灵宫》诸篇。[43] 明代武将不仅精于诗歌创作,而且对文章的创作理论亦别具一番见解。如千户姚福,曾对《六经》而下历代文章名家,一一作了自己的评述。他认为,左丘明所作《春秋》,堪称后世文章的鼻祖;司马迁的《史记》,力量超过《左传》,可谓汉代“文中之雄”;韩愈深醇正大,可称唐代“文中之王”;欧阳修渊永和平,可称宋代“文中之宗”。此外,诸如班固之详瞻,柳宗元之精核,曾巩之竣洁,王安石之简淡,苏轼之痛快,均可谓文中名家。[44]如此评论,不乏精到之见。 更有甚者,明代一些武将,尚精通词曲。陈铎堪称典型一例。史称陈铎虽为“金带指挥”,却以词曲驰名,平日随身带着牙板,能随时“高歌一曲”[45]。尽管此举被当时的魏国公贬斥为卑陋行径,但至少说明在当时的武将群体中,确乎不乏“不与朝廷做事”、只是热衷于业余爱好的风尚。 (二)武将聘幕之风 明代很多能文的武将,大多喜欢与文人交往。如戚继光与当时著名的文人王世贞、汪道昆、李攀龙均有交往,甚至雅歌相和,篇章交映,体现出一种“质有文武”的特点。②此外,戚继光在蓟镇时,凡是招待前来阅兵的官员,亦极尽招待曲奉之能事。根据钟羽正的揭示,戚继光一次招待阅兵官员,多用奇花排列,共花费了200多两银子。而那些参与阅兵的官员亦大多不加自爱,喜欢带上很多伶人游客,人数多达数十人,日夕酣歌,流连光景,登高览胜,伐鼓飞觞。[46] 与此同时,明代武将聘幕也蔚然成风。显然,这是晚明武将尚文风气影响所致。此外,武将幕中又多山人幕客。史称隆庆以后,“款市既成,烽燧少警,辇下视镇帅为外府。山人杂流,乞朝士尺牍往者,无不餍所欲”[47]。尤其是万历中叶以后,边镇专阃将帅以能诗名者很多,戚继光、萧如熏、杜文焕即其中之佼佼者。戚继光尤好延文士,倾赀结纳,取自军饷。③萧如熏亦能诗,士趋之若鹜,宾座常满。 山人杂流多投奔边帅幕中,武将亦多以聘幕为荣,以便与文臣往还。[48]陈第、颜钧为著名的王门学者,均曾入俞大猷幕,成为参谋、军师。[49]至明季,武将多聘记室、幕客。当东平侯刘泽清开府淮阴时,贾开宗“掌其军书记”[50]。即使如卫所指挥,解粮进京,也要寻一个“通文理,管得帐”的幕宾。[51]聘幕宾专为记账,这与请钱谷师爷基本相同。 四、“释中名士”:佛僧之业余精神 按照常理说来,僧人的本分是在寺院念经、礼佛,体现出一种禅静的境界。令人称奇的是,在业余精神日趋兴盛的明代,僧人却不再安分守己,跼蹐于寺庙一隅,而是纷纷外出,与士大夫相交,反而显得忙忙碌碌。晚明南京有“十忙”之说,都是各行各业的名人,显得十分忙碌,分别为:祝石林写字忙,何雪渔图书忙,魏考叔画画忙,王尧卿代作忙,雪浪出家忙,马湘兰老妓忙,孟小儿行医忙,顾春桥合香忙,陆成叔讨债忙,程彦之无事忙。[52]其中雪浪和尚“出家忙”一说,大抵已经道出晚明僧人之山人化倾向,争相竞逐“诗僧”的名头,随之出现了“释中名士”一称。 明代僧人业余精神的勃盛,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为僧务“外学”;二为僧务“杂术”。 (一)僧务“外学” 业有专攻,这无疑是众所周知的道理,更是职业精神的反映。然值得注意的是,在晚明僧人群体中,流行一股“僧务外学”之风。正如当时的名僧袾宏所言,僧人“不读佛经而读儒书,读儒书犹未为不可,又至于读《老》、《庄》,稍明敏者,又从而注释之,又从而学诗、学文、学字、学尺牍”[53]。这同样可以称之为“事外而忘内”,如当时南京寺庙中的僧人,“往往好通文雅,而鄙戒律为寻常”[54]。可见,僧人不再以学习内典为荣,而是与文人士大夫交往,学习儒家经典,并赋诗习文。 至于僧务“外学”的具体表现,则可从下面三个方面加以考察: 一为僧人走出禅房,与士大夫相交成风。这种事例,不胜枚举。明人盛时泰所著《牛首山志》载,嘉靖初年,“顾司寇、陈侍讲,致政家居,数来牛山。于是祝禧寺僧福全、崇明寺僧寄芜每随之。……陈侍讲有云:‘相随一童子,作伴两山僧。’”[55]又载:“内江赵大洲先生,自谪所起为南铨,深嗜禅理,多所访问。是时,嘉州毛起元善、宝应朱曰藩子价、嘉陆光祖、仁和王子卿原寀、华亭何良傅叔毗、南海黎民表惟敬,先后俱在郎署,而云谷老禅住摄山团瓢,号曰古佛庵。时入城,则群公各迎于家,或与同游牛山,清谈雅论,杂以诗句。”[56]又苏州竹堂寺僧人福懋,文墨标雅,诗画兼工,“吴之名公巨卿,皆折节与交,而郡使一方之尊,亦礼遇之,缁衣莫不啧啧称羡”[57]。再如公安派文人袁宏道,喜与不知其名、不识面貌之怪僧交游。而当时的僧人冷云,过柳浪时,“出茂才张君时艺若干求评”[58]。僧人交游,于此可见一斑。 到了万历年间,在士大夫中形成了一股狂禅习气,而在佛僧中也崭露一批名僧,诸如紫柏、憨山、达观、雪浪、莲池几位大师,士僧相交,更成一时佳话。④尤堪注意者,士大夫不仅与僧人相交,而且与僧人结成诸如“放生社”、“澹社”一类的团体。⑤一至明季,又出来一位名僧三峰大师。三峰性高旷,不关心寺院事务,喜欢留心笔墨之间,阄题拈韵,与同里薛敷政辈相倡和。为此,“宰官居士,皈依遍天下,其最醉心法乳者,文文肃、姚文毅、周忠介、蔡忠襄、金太史声、熊黄门开元、刘孝廉道贞,而孝廉犹称入室”[59]。 二是僧人近儒,学习诗文,导致“诗僧”辈出。早在明代初期,就有一些僧人善于词翰,与士人交往密切。如福严寺僧至讷、无言,擅长词翰,所交皆一代名人,如赵松雪、冯海粟、柯丹丘、郑尚左、陈众仲、钱惟善等。至讷、无言的诗卷真迹藏在孙叔英家,而无言的诗卷则留存于寺中。[60]又如福严寺老僧景燮,“颇能诗”,景燮瘦削,有寒士气;淀山僧人宗潮,丰厚而凝重。二僧均为一时乡里所推,有“潮外而燮内”之称[61]。 至晚明,僧人习诗之风更盛。钟惺著有《秣陵桃叶歌》36首,堪称金陵风土信史,其中有诗句云:“衲子称诗也不妨,西方亦自有词场。开函首检新题额,春日邀同某部郎。”[62]显已道出“衲子称诗”的实情。至于莲池大师与憨山大师二人,更是堪称典型之例。两位大师均为佛教界的耆宿,诗文并传于世,尤其是憨山,其诗清娟要渺,学士大夫“多颂美之”[63]。明人冯梦祯曾说:“和尚作诗,正如秀才家唱曲。”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和尚作诗,虽然说不是一件过恶之事,但终究失去了他们的本分。 三是僧人追袭缙绅,争学书画。对此,晚明名僧袾宏已是一语道破:“末法僧有习书、习诗、习尺牍语。而是三者,皆士大夫所有事,士大夫舍之不习而习禅。僧顾攻其所舍,而于己分上一大事因缘置之度外,何颠倒乃尔!”[64]袾宏之论,并非空穴来风,而是道出了当时僧人群体的风气。如杭州僧人笑鲁,曾任学士桥侧笑隐庵的住持,此庵又名法喜院。据笑鲁自述,他与董其昌、陈继儒等人交游,故其书法,能做到不落时蹊。此外,他还朝夕往来于学士桥畔,眺望湖山,意有所得,就赋小诗。笑鲁的徒弟彬远、奕是,亦均以能诗著称。尤其是彬远,别字秋蟾,所赋之诗颇为超纵,大有青莲、长吉风味。[65]相同的批评亦见诸汪道昆之论。他说:“当世苾蒭,倍无学而趋义学,藉令诗如灵一、齐己,书如智果、怀素,绘事如臣然,何益哉!舍己田而芸人之田,病也。”[66]此外,汪道昆在《长歌送无学归摄山》诗中亦云:“近者袈裟袭缙绅,翻从点画斗心神。江东竞学祝希哲,白下争传徐子仁。”[67]细绎袾宏、道昆两人之意,足见晚明僧人习学书画,已是蔚然成风。无论是士大夫之习禅,还是僧人之习书法,均属“舍己田而芸人之田”。这种职业颠倒现象的出现,大抵已经说明在晚明的僧人与士大夫之间,角色互换已成一时风尚。 (二)僧务“杂术” 与僧务“外学”相应者,则是明代僧人专务“杂术”之风。所谓僧务“杂术”,就是僧人不再秉持在寺院念经修行的清净之风,而是多务“杂术”,学习诸如看相、地理一类的江湖杂学。 当然,所谓的杂术,根据晚明名僧袾宏的揭示,其间亦不一:有做地理师者,做卜筮师者,做风鉴师者,做医药师者,做女科医药师者,做符水炉火烧炼师者。[68]尤其是僧人行医,更是成为一时风气。 为示明晰,不妨引用诸多例子加以说明。就地理师来说,明代僧人不但讲究风水,无论是寺庙建筑乃至丧葬之塔,大多重视风水的选择,而且一些僧人,开始担当起风水师一类的职责。如僧人集庆,精通郭璞所传地理之术。明帝陵献陵之建,集庆曾预效劳。[69]就卜筮师来说,明代很多著名的方术,如卜筮之技,无不来自僧人的传授。如号称能“召风雨、役使鬼神”的吉道人,就是在福建时,遇到了一位“神僧”,传给他“神通秘术”[70];又徽州人汪龙,“受数学于异僧,著奇验”[71]。就风鉴师来说,僧人精通此术,亦不乏其例。如释清上人,凭借精湛的看相技艺游历并居住在京城,甚至“相名满天下”[72];又南京高座寺僧人道清,亦“善风鉴,往往有奇中”[73]。就医药师来说,明代僧人行医亦成一时风气。如僧人止庵,“以接骨治创为业,其效至神,擅名一方”[74];又苏州大云庵的住持僧人,亦“攻岐黄,就医者舟楫弥洲渚”[75]。就烧炼师来说,明代很多僧人热衷于黄白之术。如苏州有一位老僧,为了兴造佛殿,每天诵读《法华经》七卷、念佛号万声,“祈丹事早成”,即使屡被诓骗,亦不退悔;[76]又有一位朱和尚,“负干汞之术,资以自给”[77]。 五、“粉黛山人”:妇女之业余精神 按照儒家传统的观念,自从混沌初分以后,自然是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尽管造化无私,却也是阴阳分位,亦即阳动阴静,阳施阴受,阳外阴内。正是基于这样一套阴阳理论,儒家文化已经将男女之职各自作了区分:男子主四方之事,女子主一室之事。主四方之事的男子,顶冠束带,所以称之为“丈夫”。他们出将入相,无所不为,全要博古通今,达权知变。主一室之事的女子,三绺梳头,两截穿衣。一日之计,只不过饔餐井臼;终身之计,则不过是生男育女。一些仕宦家族中的闺女,其家长虽然也让她们读书识字,但不过是教她们识些姓名,记些账目。她们毋须应科举,更不必求取名誉,所以,诗文一类的雅事,与她们全不相干。 然究之晚明妇女史的实际演变之态,却与传统儒家的观念多有相左之处。一方面,正如明人吕坤所云,晚明时代,“内职不讲”,已成一种普遍现象,“市井贫贱妇人百事不为,群集讲话,衣饰是尚,口腹为欲”[78]。另一方面,当时的一些妇女已是不务女红,只好诗书。闺房之中,“都无针线箱”,但有“图书箧”。这确实是晚明妇女业余精神勃盛的典型征候。 (一)谈禅好道 在晚明的士大夫阶层中,已经形成一股禅悦之风,其影响及于他们家庭中的很多妇女。 如明末人张履祥说:“近世,士大夫多师事沙门,江南为甚,至帅其妻子妇女,以称弟子于和尚之门。兵饥以来,物力大诎,民不堪生,而修建寺宇,斋僧聚讲,殆无虚日。民间效之,都邑若狂。”[79]又崇祯年间,有一僧人,名金台,善于惑众。在杭州皋亭建禅院,“自尚书、状元,率其命妇女子皈依之”[80]。 在这股士大夫家族女子谈禅好道之风中,涌现出了两位较具代表性的人物,即梅国桢之女澹然,以及王世贞的仲女昙阳子。 在与李贽交往并深得其欣赏的妇女学佛之人中,最著名者当数澹然。此外,尚有善因与明因。澹然,为梅国桢之女,被李贽称为“澹然师”。其人有才色,嫠居之后,结庵事佛,颇于宗门有悟入处。[81]这位梅澹然,深得李贽器重,甚至称她是“出世丈夫,虽是女身,然男子未易及之”[82]。澹然出家为尼的行为,并不为其父梅国桢所禁。澹然戒律甚严,对佛法颇有心得,甚至“父子书牍往来,颇有问难”[83]。 李贽在给周友山的书信中有言:“此间澹然固奇,善因、明因等又奇,真出世丈夫也。男女混杂之揭,将谁欺,欺天乎?即此可知人生之苦矣。”[84]可见,除了澹然、善因之外,当时跟随李贽学佛的妇女,还有一位明因。 上面所提到的几位妇女,均为晚明妇女好禅的典型例子。而在晚明名噪一时的昙阳子,不仅谈禅念佛,而且好道。她曾手书《阴符经》赠给一位姓徐的学使,而且还手书《心经》,赠与王世贞。梅鼎祚称其所书“鸟迹龙文,若出造化,其原反终始,必归轨于正经”[85]。在她得道“化去”之时,更是引得当时诸如沈懋学、屠隆、冯梦祯、瞿汝稷将近数百名士前来顶礼膜拜,并且自称“弟子”,甚至出现“以父师女”之事。⑥在当时轰动一时。 (二)风流好文 明末清初人李渔的记载已经证实,当时的妇女中确实出现了一些专攻“男技”之人,反不屑女红,“鄙织纴为贱役,视针线如仇雠,甚至三寸弓鞋不屑自制,亦倩老妪贫女为捉刀人者”[86]。传统女子原本应以女红为正业,而晚明的妇女反而迎合时尚,专门去习以文字翰墨为主的“男技”,这就不是简单的“借巧藏拙”,而是当时妇女业余精神勃盛的最好体现。晚明妇女之诗文风流,大多与家庭环境有关,而且出现家族化的倾向。如杭州黄氏家族中的顾若璞,是黄汝亨的儿媳。早年夫亡,但人有绮才。所著有《涌月轩稿》行世,其中包括替自己舅姑所撰写的墓志铭及为丈夫所写的行状,号称文章“详赡”。她的孙女埈儿,生而端丽,能作诗歌小令。其中《宫词》一首云:“长信宫中侍宴来,玉颜偏映夜光杯。银筝弹罢霓裳曲,又报西宫侍女催。”又《咏雪》一首云:“霏霏玉屑点窗纱,碎碎琼柯响翠华。乍可庭前吟柳絮,不知何处认梅花。”[87]清警殊甚。宁波屠氏家族亦多出能文之女。如屠瑶瑟,字湘灵,著名文人屠隆之女,士人黄振古之妻。沈天孙,字七襄,沈典之女,屠隆的儿媳妇。此二女少皆明慧,读书能诗。七襄嫁入屠家之后,湘灵“时时归宁,相与征事书,分题授简,纸墨横飞,朱丹狼籍”。当时屠隆的夫人亦谙篇章,每有讽咏,就与她们一起商订。为此,屠隆诗云:“封胡与遏末,妇总爱篇章。但有图书箧,都无针线箱。”又云:“姑妇欢相得,西园结伴行。分题花共咏,夺锦句先成。”[88]这确乎可称一家之盛事,亦一时之美谈。 明代妇女能诗之人,代不乏人。尤其是到了晚明,小品文渐趋流行,山人更是到处可见,妇女亦渐为这种风气所染,于是,晚明女子所作小札,多有小品气象。最好的例子是杭城妓王琐,娴诗歌、尺牍,其所作尺牍,致妍韵冷,置诸晚明文人小品之林,毫不逊色。⑦明季,常熟有柳如是,云间有王修微,钱塘有李因,皆以“唱随风雅闻于天下”[89],鼎足而三。又据钞本《明事杂咏》云:“山人一派起嘉隆,末造红裙慕此风,黄伴柳姬吴伴顾,宛然百谷与眉公。”注云:“黄媛介常在绛云楼伴河东君,吴岩子常与横波夫人游,所谓女山人也。较之山人,尤风流可传。”[90]上面所谓的“河东君”,指钱谦益之妾柳如是,而“横波夫人”则指龚鼎孳之妾顾媚。可见,当时的女山人、女清客者流,或以书画,或以诗词,均非幸致。妇女对文学的主动参与,必然导致妇女文学的发达,这可以从晚明大量的女子诗歌总集中得到证明。明人纂辑女子诗总集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嘉靖时期,至万历、天启时期达到极盛,流传至今者有《诗女史》、《淑秀总集》、《彤管遗编》、《名媛玑囊》、《秦淮四美人诗四集》、《青楼韵语》、《古今名媛汇诗》、《古今青楼集选》、《花镜隽声》、《古今女诗选》、《闲情女肆》、《女中七才子兰咳集》、《名媛诗归》。⑧ 六、余论:职业精神之沦丧与业余精神之勃盛 明代各色社会群体不务本业,转而将精力更多地投入业余爱好之中,无疑又与时代风尚桴鼓相应。晚明时期,名士之风甚盛。社会各色群体,无不转换角色,藉此追求“有致”的名士风范。何谓有致?明末人陈继儒作了如下解释:“名妓翻经,老僧酿酒,将军翔文章之府,书生践戎马之场,虽乏本色,故自有致。”[91]又云:“武士无刀兵气,书生无寒酸气,女郎无脂粉气,山人无烟霞气,僧家无香火气。换出一番世界,便为世上不可少之人。”⑨可见,所谓的有致,就是不再追求本色、安于本业,而是一种矫情,甚至是故作标致,藉此“换出一番世界”。 明代各色人物群体不务本业现象的出现,固然以社会流动之加速乃至职业分化为社会史背景,然若细究之,仅仅是角色本体与所业之事的分离而已。换言之,所谓不务本业,既非改业、易业,更非无业浪游,而是一种角色转换。进而言之,无论是文人尚武乃至专注于“余技”,武将耽于文艺,还是僧人专务“外学”、“杂术”,妇女内职不修,甚至工匠修治文艺及“儒匠”的出现⑩,无不都是职业精神沦丧、业余精神勃盛的典型反映。 美国学者列文森将明代视为文人业余精神最昌盛的时代,而明代文化也是“最典型的文人业余文化”。至于业余精神,其实就是基于一定经济基础或稳定生活之上的消闲精神。[92]这种文人业余精神的勃盛,显然得力于社会群体角色的转换。在这一角色转换过程中,文人士大夫始终占据中心的位置。在明代的传播媒介体乃至大众评价体系中,文人士大夫在专精文艺之余,可以将闲暇时间专注于其他技艺,且受到社会舆论的正面评判。至于其他社会群体之好文,诸如:生员言诗,藉此掩饰其训诂之陋;武人拈韵,藉此文饰其剑槊之粗;甚而托钵之僧、倚市之女之类,亦雅附于声诗,藉此自别于不韵无文之俗髠、凡妓。究其原因,则是因为经生士子因为依靠本业不足以致身,只得遁于诗坛,凭借诗才贩卖于王公大人之门;武弁起于行间,力单援寡,只得依附词坛,不但藉此可以博取雅歌之誉,亦可拓展他们的交游网络,达到“连其奥援,身名俱泰,金多而取大位”的目的。至于吟僧、诗妓,他们从事于诗歌创作,目的亦无非是藉此“仰衣钵于冠盖,来门前之车马”[93]。由此不难发现,上述所有不务本业且力图跻身诗人行列之人,其目的无非是通过模仿士大夫之生活乃至角色转换,藉此提高自己的社会声誉。 就其本质而言,明代社会群体之角色转换乃至业余精神之勃盛,显是一种社会异动,亦即在广泛的社会流动背景下所产生的职业兴趣转移。按照原始儒家的根本宗旨,虽以“志于道”为终极归趋,然在求道的过程中,尚不乏“游于艺”的精神。在随后的儒学流变中,“道”已被视为根本,而“艺”则被归入末技而不再受到知识人的重视,重道轻艺之说根深蒂固。就此而论,若是将明代知识人业余精神高涨这种社会异动,置诸儒家精神文化史的内在变迁历程加以观察,则又属对原始儒家“游于艺”精神的理性回归。 这种风气一旦形成,且蔚为大潮,势必导致士商相混、僧俗相混现象的出现,进而对士、农、工、商等级秩序形成冲击,甚或妇女向“女丈夫”人格转变。(11)与此同时,文人好武,多纸上谈兵而已,不切实际;而武士习文,亦非本色当行。对内忧外患的晚明时代来说,这种文恬武嬉,绝非是一件幸事,却是当时职业精神沦丧或业余精神勃盛的实录。 注释: ①如明代史料记载:“阴阳、医生、教读等,尝见各处府司视为在官之人,一概差用,不使专务本业,是岂祖宗设立之美意!或今后阴阳生轮流日守日晷时牌,夜收更漏,医生亦轮流日守惠民药局,教读分教各里童生,使各专务本业。”即其典型例证。参见不著撰者:《居官格言》下篇《阴阳医生教读》,载《官箴书集成》第2册,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第80页。 ②著名文人李攀龙称戚继光,“唯公建大旗鼓,扫清海上,大小百战,无不奇捷,遂壮皇朝之气,而遥制江、广,使诸偏裨得贾余勇,填荡潢池,功不且半天下乎!”云云。对戚氏武功多有称颂。参见李攀龙:《李攀龙集》卷28《报戚都督》,济南:齐鲁书社,1993年,第616页。 ③如史载戚继光以方元沂为重客。方氏死后,“戚方镇莅南海,殓之正堂。发引之日,柩从中门出,服朋友服,步送之葬所”。参见姚旅:《露书》卷11《人篇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68页。 ④关于紫柏、憨山、达观、雪浪、莲池事迹,参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7《紫柏祸本》、《憨山之谴》、《雪浪被逐》、《禅林诸名宿》各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下册,第690-693页。 ⑤如冯梦祯,“以时与僧莲池、邵重生、虞淳熙兄弟、朱大复诸公结放生社,人以为无愧太白傅苏长公云。”万历三十九年(1611),吴之鲸与佛石禅师、胡木仲、卓去病“共订澹社,为无言清坐之会”,参加者尚有一些“有韵衲子”,主持其事者仍为冯梦祯。吴之鲸:《澹社序》,载吴之鲸:《武林梵志》卷3《城外南山分脉·理安禅寺》,收入王国平主编:《西湖文献集成》第22册,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年,第69-71页。 ⑥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3《假昙阳》、《黄取吾兵部》,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593-595页。按:昙阳子是王世贞之女。 ⑦王琐致程静致小笺云:“昨日下雨,今日又下雨。老天闷人,足下斋头攻书。曾知下雨,必知闷人。知闷人,不妨过来走走。”又曰:“连日冷冷,足下独居冷不?无事过我冷斋,说几句冷话,万勿以我为冷人也。”寥寥数笔,小品之性已具。说见郑仲夔:《耳新》卷5《谐艳》,载《明史资料丛刊》第3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96页。 ⑧详细阐述可参见陈正宏、朱邦薇:《明诗总集编刊史略——明代篇(下)》,载朱立元、裴高主编:《中西学术(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24-129页。 ⑨陈继儒:《小窗幽记》卷9《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25页。按:此说亦见于吴从先:《小窗自纪》,载于诸伟奇、敖堃主编:《清言小品菁华》,深圳:海天出版社,2013年,第323页。 ⑩明代工匠业余精神之勃盛,乃至“儒匠”之广泛出现,当另撰一文予以探讨,在此不赘。 (11)如谢肇淛称妇女写诗好名,堪称“女丈夫”。钱谦益亦称女山人王微与黄皆令,一则近于“侠”,一则近于“僧”。分见谢肇淛:《五杂俎》卷8《人部四》,上海:上海店出版社,2001年,第144页;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33《士女黄皆令集序》,载于钱谦益:《钱牧斋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9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