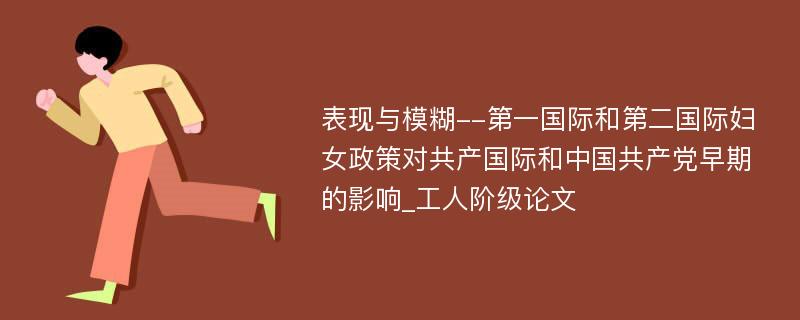
彰显与隐约——第一、第二国际的妇女政策对共产国际及早期中共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产国际论文,中共论文,妇女论文,政策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彰显与隐约:“已然”历史与构建历史中的非妇女与妇女
回顾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诞生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很容易想起毛泽东的那句名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送来之后如何巩固与生根发芽,则需要送方与接收方的双向努力。这些努力绝非一声炮响那般干脆和立竿见影,而是需要机制化与持续化。在俄共与早期中共的交往中,最彰显的机制莫过于共产国际:中共成立、国共合作、北伐战争、城市暴动、领导人的更迭,乃至被时人、后人批评且让中共付出巨大代价的李立三路线、王明路线等无不与俄共、共产国际密切相关。但细细考察之后,却可以发现,俄共经由共产国际对早期中共产生的影响固然涉及方方面面,但却并非处处都影响彰显,中共早期妇女政策就是一例。在粗线条的历史教科书里,我们几乎看不到共产国际对中共妇女政策的直接指导,即使是在众多学者的细致考察中也难得一见这方面的内容,所以共产国际对中共早期妇女政策的影响迷散在了一片隐约之中。所以,在考察中共早期这段历史时,我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历史(如共产国际对中共非妇女政策和妇女政策的指导上)和对历史的考察(众多学者关于共产国际对中共非妇女政策和妇女政策之影响的分析),即“已然”的历史和构建的历史之间为什么会有雷同的彰显与隐约?
带着这个问题,我查阅了我所能找到的资料,发现学者对共产国际在中共早期妇女政策的影响上为什么言语缺乏似乎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即资料匮乏。在中国大陆,关于共产主义运动的教科书、论文在数量上木算很少,但原始资料相当匮乏。所以,当我发现了一本厚厚的《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的书,而且目录里也的确有多处“妇女”和“女工”字样时,我非常高兴。但当我迫不及待地查看内容时,却吃惊而又遗憾地发现,“妇女”、“女工”等字样后面一般都有一个“(略)”。这是明白标出了“略”的历史文本,而更多的却是没有标出“略”但妇女却杳然不见的文本。
除资料的匮乏外,构建的历史中缺乏妇女当然还有一个根本的原因,那就是缺乏性别视角。所以,在厚厚的一本关于共产主义国际运动的教科书、著作中,只列出一两节来谈妇女的现象司空见惯,似乎在其他章节中的人都是没有性别或没有女人的。
构建的历史表现出如此模样,那么,这是否与“已然”的历史有关呢?根据我就三次共产国际运动的考察发现,的确如此,而且“已然”的历史中彰显与隐约对照分明。
但是,尽管在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国际对早期中共的指导中,妇女的身影与声音隐隐约约,但并非无迹可寻。而且,也正是这对比鲜明的彰显与隐约激励我去探寻,为什么妇女会若有若无?在处于被有意无意忽略的处境中,共产主义妇女们又是如何努力摆脱被隐去的命运?她们这些先驱者的努力又给我们后人留下了哪些宝贵财产与经验?
二、第一国际中的彰显与隐约之争
在第一国际成立后第二年(1865年)的伦敦代表大会上,代表团们讨论了一个问题:女工是否也可以理解为工人。当时的法国代表团认为,社会准则应该是男人工作和研究社会问题,女人照顾孩子和美化工人的住宅。而且据共产国际1922年的妇女工作会议的代表赫尔塔·施图尔姆说,这种思想在几十年后的法国和意大利仍然非常盛行[1](P945)。由于得不到资料,所以不知道当时的第一国际是如何处理这一争论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即使是在直接由马克思亲自领导参与的第一国际内,这种传统的性别分工仍然生存了下来。
其实在性别分工上,马克思本人的观点相当激进。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1.“分工和私有制是两个同义语,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2](P36)。2.“分工的萌芽和原始形态在家庭中已经出现,在那里妻子和孩子是丈夫的奴隶”[2](P36)。3.“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发的,那末人本身的活动对人说来就成为一种异己的、与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驱使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2](P36)。那如何摆脱这种分工呢?他接着指出,“只有交往和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这样普遍的程度,以致私有制和分工变成了它们的桎梏的时候,分工才会消灭”[2](P43)。那什么时候才能达到这样的程度呢?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所以从这些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出:(1)马克思的确发现了分工的关键作用,包括分工对妇女地位的作用。(2)但分工如何具体地造成妇女的从属地位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论述重点,这一工作主要是由1960年代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进行的。(3)马克思为消灭分工开出的药方是共产主义社会,但在争取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途径——无产阶级革命是否会继承并发展传统的性别分工,马克思没有足够的警惕和论述,这使人们产生一种印象:似乎只要完成了无产阶级革命,传统的、对女性不利的社会分工就会自动烟消云散,而且无产阶级只需克服前阶级社会陈腐的性别观念即可,无产阶级自身不会发展新的对女性不利的性别观念。联系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对无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革命中的性别观念与制度缺乏自省的传统在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的实践中一直若隐若现。
这种自省的缺乏在恩格斯身上也可发现。以性别分工为例,他一方面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妇女是家庭的奴隶。另一方面他又积极地维护这种性别分工。如他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写道:“妻子挣钱养活全家,丈夫却坐在家里看孩子,打扫屋子,做饭……这种实际上的阉割在工人中激起什么样的正义的愤怒,……那是不难想象的。”[2](P12)在引用了一封反映一个失业已三年的男工被迫在家里专搞家务的信后,恩格斯写道,“还能够想象出一件比这封信里所描写的更荒谬更不近情理的事情吗?”[2](P13)这是“使男人不成其为男人、女人不成其为女人,……最可耻地侮辱两性和两性都具有的人类尊严的情况”[2](P13)。
列宁在性别分工上的传统积淀也很明显。一方面,他强烈贬低性别分工所造成的妇女专职的家务劳动,认为“妇女仍是家庭奴隶,因为琐碎的家庭事务压迫她们,窒息她们,使她们愚钝卑贱,把她们缠在做饭管小孩的事情上;极端非生活性的、琐碎的、劳神的、使人愚钝的、折磨人的工作消耗着她们的精力”[2](P289)。另一方面,他又巩固着传统的性别分工。在1918年起草的《关于苏维埃机关管理工作的规定草案》中,他说,为“最大限度地节省人力”,要“尽量用女子代替男子,并把能够调到军队、军事部门去的或做其他工作(不是文牍工作,而是执行工作和实际工作)的男子列一名单。”[2](P281)在这里,他贯彻了传统的性别分工:文牍工作是适合女子的,而执行工作和实际工作是适合男子的。将文牍工作与实际工作对立的分法,也表明列宁认为文牍工作不是实际工作。恩格斯和列宁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杰出继承者,他们对性别分工的看法尚难以摆脱传统的束缚,那么在第一国际中出现上述的论调也就不足为奇了。而且,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这种观点的提出也反映了海迪·哈特曼所说的资本主义与男权制联姻时双方的冲突与协调。在人类历史上,资本主义第一次大规模地将妇女卷入工厂劳动中,剧烈地破坏了传统的家庭制度与性别分工,并引起了家务无人照管、“男人不成其为男人,女人不成其为女人”和“道德堕落”[3](P473)。因此在当时,要求妇女回家,尤其是禁止已婚妇女在工厂里做工的呼声很高。所以第一国际的代表会讨论女工是否也被理解为工人的问题,并维护传统的性别分工。
是否争取妇女的普选权在国际共运中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如1865年1月31日,马克思在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提出,要争取国内所有男性成年居民的普选权,对妇女普选权则悬置不提[3](P836)。尽管这是为争取更多的(男)工人而采取的策略,但为什么妇女普选权被回避,这值得深思。而且同样的策略,在第二国际中就被斥为是机会主义,对这种策略的断然否定还受到了列宁的高度赞扬[4](P74)。
在考察共产主义国际运动的过程中,让我非常感兴趣的一点是:在当代,如果可以武断地将女权主义的策略或思路概括为争取将性别从阶级中独立出来的话;那么,在第一和第二国际中,共产主义妇女们却热切地努力将性别纳入阶级。而且,在几十年间,尤其是第一国际的男工人们、男共产主义者们还非常不愿意接纳妇女,并且拒绝妇女成为他们力量的一部分,也不肯将无产阶级妇女置于自己的领导之下!
尽管第一国际中的绝大多数男人们都拒绝接纳妇女,但马克思毕竟比这些男人们看得远。所以,虽然1866年通过的第一国际章程与条例(马克思制定)中并没有提及如何领导妇女,但巴黎公社中妇女们的英勇斗争使马克思看到了妇女的力量,于是在1871年修改第一国际的章程和组织条例时,他在组织条例中加了一条,“建议在工人阶级当中成立妇女支部”[3](P483)。由此开始,在工人阶级开始渐渐有了专门的妇女支部,并且被第二国际和共产国际继承了下来。这一传统对妇女运动作用复杂,一方面它将无产阶级妇女的运动置于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严密领导之下;另一方面,也为无产阶级妇女运动的开展提供了论坛和发动的机构,当然议题的设定和运动的开展都必须在党的允许范围之内。由此,工人阶级队伍中的妇女支部有效地预防和阻止了妇女运动的分离倾向。另外,这一条文中的“建议”二字也大有深意。这表明当时在工人阶级中成立妇女支部还不是一项硬性要求,而是可以选择的,这反映出第一国际中的工人阶级在是否要将无产阶级妇女运动纳入男性无产阶级运动时的犹豫和分歧。马克思、恩格斯、倍倍尔和列宁都是看到无产阶级妇女巨大力量的理论家,但他们个人的努力并不能完全改变男性共产主义者们对无产阶级妇女的轻视和忽视。也正因为如此,改变妇女在共产主义国际运动中的隐约处境的主导力量是女共产主义者们自己,是一代代的“她们”通过不懈的和艰难的努力才使共产主义国际运动中的妇女们由隐约到半彰显的。
在我们今天看来,妇女在第一国际中显然处于隐约地位,但即使是觉察到妇女巨大力量的马克思却也对妇女们在第一国际中的地位表示满意。在1868年12月12日的一封信中,他写道:“妇女对于国际是无可报怨的,因为它选了一位妇女罗夫人担任总委员会委员。”[3](P571)但实际上,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的成员是每次大会重选,所以罗夫人的委员似乎没当太久,因为在以后的总委员会联名签署的决议中并没有发现她的名字。而且在第一国际的资料中,我们几乎听不到罗夫人的声音。
有趣的是,尽管无产阶级妇女们在第一国际中处于隐约的地位,但资产阶级妇女们却被大大地彰显了。如在1872年,第一国际开除了第十二支部。这一支部是谁领导的呢?用当时第一国际中的男人们的话讲,是由美国的两个“百万富翁,两个鼓吹妇女解放,尤其是自由恋爱的”[3](P107)两姊妹维多利亚·伍德赫尔和田纳西·克拉夫林在1870年组织的。根据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的决议,开除的理由如下:(1)第十二支部任意解释第一国际的决议、章程与组织条例。如第十二支部将第一国际的目标解释为,“通过夺取政权解放男女工人。这首先包括:男女的政治平等和社会自由”[3](P107)。这显然与第一国际的目标——使劳动者在经济上获得解放——不同;(2)第一国际要求,国际支部的成员应三分之二以上是工人阶级,而第十二支部却是由“形形色色的由资产阶级骗子手、自由恋爱的拥护者……”[3](P108)等人组成的;(3)第十二支部实行与第一国际共同目标不同的特殊任务,如呼吁和平、提倡禁酒、争取妇女投票权、参与总统选举等,用恩格斯的话说,就是“什么事情都要管”[3](P111)。并且,第十二支部的革命次序也明显异于第一国际的革命次序,因为第十二支部认为,“在对劳资关系进行任何总改变以前,应该先在全世界推行妇女的公民平等权”[3](P108)。既然第十二支部与第一国际的目标、策略等是如此不同,那么它被第一国际清理出局也就不出意料。这次对资产阶级女权主义的清理所产生的示范效应,再加上马克思主义中强烈的阶级意识,使之与资产阶级女权主义作斗争成为国际共运屡屡大力彰显的热点之一。
三、第二国际中的彰显与隐约之争
在妇女的彰显与隐约上,比起第一国际来,第二国际显然发生了令妇女高兴的转变。如在第二国际的两大主要议题——劳动保护与普选权上,妇女的利益都得到了考虑,并分别在1891年的布鲁塞尔大会、1893年的苏黎世大会、1904年和1907年的阿姆斯特丹大会上,通过了关于保护女工、妇女选举权的条文和决议[5](P108,109)。第二国际的成立与第一国际的解散相距不过十几年,为什么会在妇女的彰显与隐约上发生如此明显的断裂?由于缺乏资料,我对这一问题仍不得而知。但这一转变毕竟令人高兴。
当然,发生这种转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也是显而易见的。即妇女共产主义者们自身的巨大努力。尽管我对为什么1891年的布鲁塞尔大会和1893年的苏黎世大会提出的关于妇女的议题仍一无所知,但1904年与1907年的阿姆斯特丹大会显然受到了成立于第二国际内部的国际妇女社会党人代表会议的影响与压力。下面,简单介绍一下第二国际中的妇女共产主义者们为改变妇女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巨大沉默和隐然不见而做出的尝试与推动。
国际妇女社会党人代表会议由德国女代表克拉拉·蔡特金等倡导成立,共召开了三次代表大会。第一届国际妇女社会党人代表会议于1907年8月召开。德国代表指出,在普鲁士、巴伐利亚和德国其他地区都禁止妇女从事政治活动,党的妇女工作委员会被解散了,因此建立了委托人制度,由委托人在妇女中进行社会主义宣传[6](P546)。遗憾的是所查文献没有说明是谁解散了妇女工作委员会,谁建立了委托人制度,委托人如何选派。根据相关内容,似乎是普鲁士等当局不允许妇女参与政治运动,但党的内部好象也不愿意建立妇女工作委员会。因为在十五年后的共产国际第二十四次会议(1922年)上,蔡特金指出,有些国家的共产党仍没有建立专门的妇女工作机构或建立后又解散,如波兰至今仍拒绝建立专门的妇女工作机构,英国也一再推迟建立类似的专门机构[1](P929)。俄国也没有独立的妇女工作机构,而是在党内指定专人,负责领导女工。俄国代表说:“在共产党的任何一个工厂支部中,都有一个同志——女工组织委员,受委托做妇女政治思想工作。”[1](P958)上述内容表明代表们在如何领导女工上产生的争执:是党内的妇女党员们自己组织起来建立专门的妇女工作机构,去领导女工,还是不建立专门的妇女工作机构,而委托专人(此人不一定是妇女,俄国代表就是用“他”来指代女工组织委员)去领导女工?而事实上,组织专门的妇女工作部门对无产阶级政党更有利。但如果这样的话,那就等于承认了无产阶级妇女的巨大力量,也就会将无产阶级妇女由在共产主义国际运动中的隐约地位提拔为彰显地位。共产主义国际运动的百年历史表明,这是男共产主义者们不大愿意看到的。
妇女普选权是第一届妇女代表会议的另一争论中心。蔡特金指出,1902年在比利时,1905年在奥地利,1906年在瑞典,各国的社会党只要求男子享有普选权。在该届妇女会议上,英国代表(费边社和独立党人)又提出给妇女有限的选举权。当这个提议案遭到以德国蔡特金为首的大多数代表的反对后,奥地利代表提出“关于展开争取妇女普选权的斗争时机和有效方法问题,应由各个国家的党自己决定”[6](P548),这实际上是迂回地拖延给妇女普选权,也被大多数代表识破并拒绝。德国另一位代表齐茨则折衷了一下,提出“妇女选举权不应被看做是妇女在法律上的要求,而应被看做是社会民主党人的要求,不过也不应把它当作党的整个政治斗争的关键问题”[6](P549)。最后,大会在妇女选举权问题上采取了原则性的阶级观点,认为妇女选举权问题是工人阶级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6](P550)。这种“原则性的阶级观点”的利弊在于:一方面,它为妇女争取普选权取得了合法性,但另一方面,在“工人阶级”以男性工人为主体和代表的前提和事实未得到充分认识和警醒之前,这种原则性的阶级观点有将妇女消融于(男)工人之中的危险。
第二届国际妇女社会党人代表会议召开于1910年8月。主要内容如下:(1)大会指出,尽管各国的女工运动正在蓬勃发展,但在工会中女工的比例仍大大低于男工。(2)在妇女选举权上,英国代表再次要求给予妇女有限的选举权,遭到了各国代表的一致反对。(3)德国代表提交且大会通过的提案规定了女工如何争取选举权。a.女工必须利用她们已经争取到的权利,如地方自治机关的选举权等;b.建议各国妇女社会党人按照同各社会党和各工会达成的协议,每年庆祝妇女节,以争取妇女的选举权。[6](P552)这些实际上是妇女大会发展出的斗争策略,既针对阶级敌人,也针对男性,还针对阶级内部的组织。
应该指出的是,继承第一国际彰显资产阶级女权运动的传统,国际妇女社会党人代表会议从初次集会始,几乎历次都谴责资产阶级女权运动。在1896年的会议上,代表们谴责了资产阶级的男女平等运动,认为它是违反女工利益的,如女权运动者们反对制定妇女劳动保护法[6](P545)。第一届妇女会议通过的决议案也指出,无产阶级妇女不应与资产阶级妇女联合进行争取普选权的斗争,而应与社会党紧密团结在一起。英国费边社代表们和奥地利代表们提出的应由每个组织自己决定斗争策略的建议遭受否决,也是因为大多数代表认为这是试图与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合作找借口[6](P548)。在第二届妇女会议俄国代表作的报告还说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彼得堡女工严厉批判了资产阶级主张的男女平等运动等[6](P551)。
第三届国际妇女社会党人代表会议于1915年3月召开。在这次大会上,由于一战的爆发,战争与和平成为大会的争论焦点,没有进行专门的妇女议题。我认为,这次会议体现了妇女与国家、民族、阶级、战争等的不可分割。但也说明,无论是男性社会党人(如列宁等人对这次大会的评论),还是妇女社会党人本身,在确定革命的优先次序时,都将妇女运动置于次要地位。如果进一步深思的话,可以看出,这种迄今为止仍盛行不衰的排列重要性的做法,实际上反映出方法论和认识论上的缺陷。因为,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生活是网络状的,无数条经与纬将人们编织在了一个无法抽离和机械割裂开来的多重、多向、流动和立体网络之中。所以,指望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再追求妇女的解放是不可能实现的路线。因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自动带来妇女的解放是不可能的,无产阶级在革命期间,不可能脱离开性别观念和性别制度,因此,如果没有足够警醒的话,无产阶级革命不但不会自动带来妇女的解放,而且相反,对妇女压迫、歧视和不利的观念、实践和制度还会在无产阶级革命期间复制、收编、衍生和创造出来。但这样的思路不但束缚了男性共产主义运动者们,而且也束缚了克拉拉·蔡特金等杰出的女共产主义运动者们。所以,她们努力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彰显妇女的同时,自己就已设定了一个框架:即以往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过分模糊妇女是不对的,所以要彰显妇女,但彰显妇女必须有分寸,不能超越以男性为主体的阶级和共产主义国际运动。所以,她们的这种彰显只能是隐约之中的彰显。
四、第一、第二国际对共产国际及中共早期妇女政策的影响
从上文对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分析来看,就妇女而言,这两次共产主义国际运动解决了如下几个问题。(1)女工是不是工人阶级;(2)要不要将妇女斗争纳入到阶级斗争之中;(3)要不要给妇女普选权;(4)女权主义运动与无产阶级妇女运动的区别在哪里。其实就其实质来看,这四个问题均是阶级与性别的关系。按照当代妇女研究学者和活动家的理解,是希望将妇女从阶级大一统中策略性地独立开来,即阶级之外和之内有性别。但考察第一、第二国际,令人深思地发现,那时的妇女共产主义者们似乎是竭力想掩盖自身的性别色彩,希望能跻身于阶级这个大一统中,即性别之外和之内有阶级。
另外,第一和第二国际留给共产国际的宝贵遗产是:劳动妇女是无产阶级中的一部分;无产阶级妇女运动是无产阶级运动中的一部分,无产阶级要领导女工农妇们一起推翻统治阶级;妇女应该得到与男人一样的普选权;八小时工作制是包括所有女工在内的一切劳动阶级应享有的待遇等。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起,上述这些要求就几乎没有什么争议地成为全党和妇女解放运动的目标。但通过考察第一、第二国际的妇女共产主义者们的经历,我们这些后人和受益者才意识到:这些目标和原则都不是自然而然就有的,而是经过这些妇女先辈们用半个世纪的斗争赢得的,是她们苦心构建的结果。
共产国际继承了这些遗产,而且通过下列几种方式将这些前人成果和共产国际的意图贯彻到了中共的早期妇女政策中。1.直接以会议决议等形式要求落实。2.通过远东局、妇女书记处等机构下达指令。3.通过东方大学、中山大学等培养中共人员,影响中共的妇女政策。由于篇幅所限,这些具体影响不在本文展开论述。但中国共产党的妇女工作的特点之一却非常值得大家思考。对照党早期四次妇女工作决议案与1922年11月27日举行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议题,似乎表明,在妇女运动方面,共产国际领导下的其他各国支部普遍没有中共做得好,而且,通过全国妇联编的《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19-1949,共分四册)和《晋察冀北岳区妇女抗日斗争史料》、《江西苏区妇女运动史料选编》等地方性史料,我惊叹地发现,党在妇女运动上有着细致的政策指导和卓有成效的成果,但令人不解的是,从1920年代的后期起,只要一提妇女工作,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党总是先自我检讨或强调指出:(1)不能在妇女运动上犯取消主义,即认为妇女工作是“党的附属工作”,从而忽视或取消妇女运动;(2)也不能搞妇女主义,即“不站在整个工作中去认识妇运的倾向”。这种提起妇女工作就作批评和检讨的模式一直持续到整个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所以,我对此现象的疑问是,为什么在实际工作中,党已经很彰显妇女工作,但却总是检讨自己将妇女隐约起来了呢?是否因为其总担心犯了妇女主义的大忌,而觉得自己总在压制妇女运动呢?在这种表相和实际的彰显和隐约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总之,从1864年第一国际成立到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的55年间,遍布着妇女及其议题的彰显与隐约之争:从第一国际中妇女的沉默与缺席,到第二国际中妇女努力争取妇女议题的彰显,历经两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才争取到的妇女彰显到共产国际时,在列宁、蔡特金等人的努力下,终于成为制度,阶级化、政党化、组织化和制度化使妇女不能再被轻易地从无产阶级革命中抹去。但这种历经多年获得的相对彰显却又伴随着妇女在无产阶级革命中时断时续的隐约命运。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运中的“后发”优势,使党从一开始就制定妇女决议案、建立妇女部,为妇女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中争得了一席之地,但党对于“妇女主义”和“取消主义”的担心和提防,使得中国无产阶级妇女在彰显与隐约之间不时徘徊。
标签:工人阶级论文;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论文; 共产主义社会论文; 第二国际论文;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无产阶级政党论文; 第三国际论文; 共产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