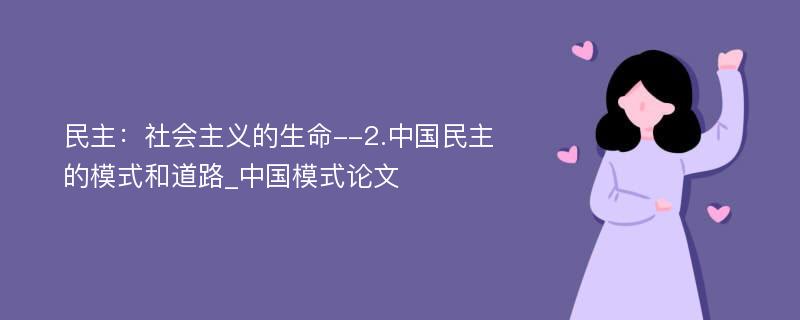
民主:社会主义的生命——2.中国式民主的模式和道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主论文,道路论文,模式论文,生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七大报告以前所未有的频率提到“民主”,以前所未有的具体论述勾画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前景和蓝图,这说明,民主政治已成为执政党和中国人民坚定不移追求的目标。从党内理论工作者、媒体和社会各界的反映看,对民主的追求和建设,已成为理解和落实十七大精神的重点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参考、借鉴古今中外的民主理论与实践,对未来中国民主的形式、类型、特征作一些探讨和设想,是必要和有益的。当然,这是一个大题目,不是一个人或一些人在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下面只是一些粗浅的断想,旨在抛砖引玉。
民主模式需要鉴别和选择
“民主”一词起源于古希腊语,基本含义是“由人民来统治”。在古希腊,一个人只要有公民资格,就可以在选任官员、制定政策和司法判决等方面直接发挥作用——虽然当时有公民资格的人还很少,如不包括妇女、奴隶等等。而在近代,则发展出“代议制”民主,即公民虽然是国家的主人,但并不直接管理国家、决定国家的法律和政策,而是选任官员来代表他们的利益、表达他们的观点,间接地实施统治。当然,严格来说,公民选任的还不是行政或司法官员,而是具有立法权的民意代表,再由他们任命官员。
直接民主制和代议制是民主模式最基本的分野,也被有些人视为古代民主和近现代民主的分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高度复杂化,人民直接管理国家越来越不现实,直接民主让位于代议制民主看来已成定论。“主权在民”不像以前那样表现为公众集会和议事,而是通过民选代表的中介来实现,20世纪中期之后,代议制在西方确立并为其他国家接受。当然,代议制的含义不仅限于间接和中介,普选权,言论、出版、结社自由,选举中的自由平等竞争等等,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与代议制在形式上是相同的类型,但我们曾长期在意识形态上否定间接民主而肯定直接民主,这大概是教条主义在作怪。马克思、恩格斯考虑理想的民主模式时明显受古代民主模式的影响,他们在《法兰西内战》中提倡巴黎公社模式,这是一种人民直接参与政治从事国家管理的制度。不论我们实际上是怎么干的,我们总是习惯于以巴黎公社为理想和楷模,明显的一例,是著名的《十六条》(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第九条关于权力机构的组织形式就规定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办。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到中国的,也是被神化了的苏维埃制度,是一种工农兵直接参加国家管理的模式。这种实际做法与意识形态指导之间的矛盾,造成了思想上的混乱,妨碍我们探讨恰当的民主模式。
在肯定间接民主模式或代议制的同时应该指出,这只是在全国范围内就总体情况而言,在基层,直接的选举、罢免、讨论、管理等是不可避免的和有益的。民主意味着很多领域内的广泛参与,而不仅仅是每过一段时间去投票选出议员或代表。另外,就非常重大的问题(比如国家的合并、分离、入盟)举行全民公决,也表明了国家的统治权属于人民。
民主的理论和实践在现代政治中不断受到挑战和得到发展,上面提到的关于民主的主流观点在20世纪受到各种批评,形成了一些新的理论。新理论、新模式传到中国,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有人看到既有的民主观念受到如此大的挑战和如此深刻的批判,产生了动摇,感到我们自己的政治文化传统中反民主的说法也很有道理;有人以为最新的东西就是最好的,想用西方最时髦的理论解决中国多年来难以解决的老问题。这样一来,我们在探讨中国民主的道路和模式时,就既有许多理论可以参考借鉴,也有许多问题需要仔细鉴别和澄清。现在仅以两种关于民主的新理论为例来说明我们应该怎样在各种民主模式中进行鉴别与选择。
约瑟夫·熊彼特提出“竞争性精英主义”民主理论,反对以下这种长期占主流地位的民主观:“民主方法就是为实现共同福利作出政治决定的制度安排,其方式是使人民通过选举选出一些人,让他们集合在一起来执行它的意志,决定重大问题。”熊彼特将此称为古典民主学说,他说,所谓人民的共同意志、共同福利、共同目标并不存在,不过是宗教或功利主义的虚假信念,古典学说只是在小而原始的社会才比较适合,在现代,不过是政客用来竞选和讨好选民的口号。他的主张是应该把古典学说中的两个因素颠倒过来:原来是说,首先是人民有自己明确而合理的主张,然后选出代表以保证实现这些主张,即目标第一,选代表第二;而倒过来的说法是,选举第一,目标或政策第二,人民的任务就是产生政府。一般认为,民主必须与选举相关,选民选出体现自己利益的代表,熊彼特对此说法鄙夷不屑,他说:“选民的选举不是出于选民的主动,而是被塑造出来的,对选民的塑造是民主过程的本质部分。”
笔者认为,虽然熊彼特的观点概括了现代工业社会中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的某些事实,但从根本上说并不正确。它解释不了这样一个事实:选民根据候选人的政纲与自己政治信念的吻合程度决定投票。笔者还认为,熊彼特的立场实际上包含了较强的批判意味,与他之前对现代代议制民主的批判是一脉相承的。对熊彼特的理论应该仔细研究和持小心警戒的态度,因为他主张“民主政治并不意味着也不能意味着人民真正的统治……民主政治就是政治家的统治”。我们不能像熊彼特那样,以为社会主义民主就是所谓的“精英统治”。
审议民主不能取代主流民主模式
上世纪80年代起,“审议民主”(或译为“协商民主”)理论在欧美流行。有人主张中国的民主应该采纳这个模式。
他们认为,传统的多数决定模式虽然具有程序上合理合法、能得出明确结果的优点,但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多数人很可能并不是出于理性或深思熟虑,而只是出于偏见或既得利益,投票仅是人数多寡的简单对决。但人们是有理性和公共精神的,很可能在理性的沟通、讨论后改变自己的观点,多数与少数的比例会发生变化,多数表决制没有为人们理性协商和在更深刻的认识基础上决策留有余地。
审议民主在得到一些人大力支持的同时,也受到各方面的批评。比如,有人说,过分强调理性和普遍利益是有缺点的,在现实社会中,有人比其他人更有能力和手段以理性的姿态发言,审议民主实际上有利于话语权更大的人群;还有人说,审议民主追求普遍和共同的利益,容易压制、消除特殊的视角和利益,特别是少数或弱势群体的利益。
笔者认为,传统的、主流的民主模式确实不是尽善尽美的,它需要审议民主的某些有益成分加以补充和改进,但不能被它取代。传统的民主模式的缺点被夸大了,因为投票前后的讨论和争论始终存在,并不是没有沟通和协商;另外,从操作的意义上说,什么事都不能议而不决,最后还是要靠投票来决策。也许,最好把协商民主理解为对传统民主模式的锦上添花。在民主建设的起步阶段应该把握、强调基本的、核心的内容,不能好高骛远、舍本逐末。
想起孙中山提出的“训政”
在作了以上分析之后,自然会产生的问题是:我们应该选取什么样的民主理论和模式呢?我们当然应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主,这是最正确的回答,也是最一般的回答。
笔者以为,任何现成的、主要来自西方的民主理论、民主模式都只能起参考借鉴作用,不能直接应用于中国,因为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进行民主建设的历史条件与西方很不相同。当然,人类社会进步也有一些大致相同的、带规律性的东西,而且,实现民主也有一些必不可少的要求。把我们就要建设的民主称为“宪政民主”是可取的。
首先,“宪政民主”满足了赋予“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具体内涵的要求,也表明我们建设的民主在大方向和基本价值方面与人类政治文明公认的成果是一致的。同时,还说明这种一致只是在总的原则和精神上的一致,我们并不想教条、片面地照搬某一种特定理论、模式,或某一国的特殊经验。
“宪政民主”还表明,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与法治不可分离的、受法治制约和保障的民主。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对我们来说,民主建设与法治建设可以说是二而一、一而二的事。在宪政民主的架构下,任何党派、团体、个人的活动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每个公民有平等的政治和法律权利乃系宪政民主的应有之义,比如十七大报告提出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就可以根据宪政民主的理念来说明。
“宪政民主”还包含这样的意思:虽然有投票和尊重多数的原则,但并不单纯照多数意见办,除了有保护少数的机制,还有一些公认的甚至是先验的原则,哪怕有多数人主张也不得实行。这样,就可以免除“多数人的暴政”。“宪政民主”还要求建立违宪审查机制,这对于中国的法治建设有很大意义:现实中我们的一些法律法规要么过时,要么就是为部门利益、特殊利益集团张目,违反了宪法精神。
要实现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应从哪里入手呢?有人认为可以从党内民主开始,有人认为基层的民主选举最重要。其实,十七大报告有全面阐述,方方面面都是应该付诸实施的,关键是要有所突破,不能只说不做。最要紧的是正确把握稳妥和积极之间的关系。近年来的事实说明,民主建设有些缓慢,政治体制改革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有所滞后,重要原因就是重视不够,稳妥有余而积极不足。
不想推进民主建设,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理由,什么文化传统、国情不适合,民众素质不够,搞民主不利于安定团结等等,不一而足。种种顾虑、种种托词,比当年孙中山提出“训政”落后多了。以前,我们对“训政”极尽挖苦嘲讽之能事,但不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上看,训政的归宿都是宪政。坦率地说,我们今天可能还是需要训政,只不过,第一,自从孙中山提出“军政—训政—宪政”三部曲以来已过去大半个世纪,训政不应漫无止境,训政和宪政之间的距离应大大缩短;第二,训政不是官训民,而是民众的自我训练。我想,与其像以前那样说中国已经有了最充分的民主,还不如老老实实承认我们正在搞训政,这种训政的意思是点滴积累、循序渐进、不断成熟,是以民众为主体。
人类社会都进入21世纪了,中国人的民主梦想,快实现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