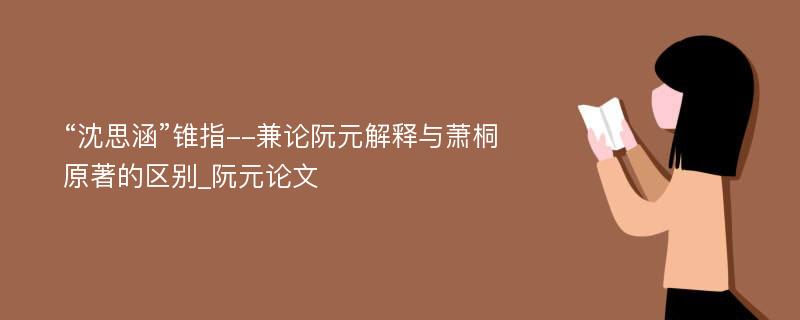
“沉思翰藻”锥指——兼论阮元释义同萧统原序之区别,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释义论文,沉思论文,区别论文,兼论阮元论文,锥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6-0766(2011)01-0070-07
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文学总集之一,《昭明文选》前《序》所提出的“沉思翰藻”一说历来是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焦点。《选序》“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见解,经过清代学者阮元的着意阐释和表彰,其意义由《文选》的选文标准上升至选文通则乃至魏晋文学的学科分类标准。这一观点为后来诸多学者所祖述,《文选》以“沉思翰藻”简别三部、树立文学封域的观点在中国学术史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截至目前,虽然关于《选序》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诸多实绩,但是以笔者愚见,在以下三个方面仍然有继续探讨的空间和必要性。
其一,考察魏晋六朝文学理论的建设和《文选》之前各重要的“总集”的编撰,无一例外都遵循分体论文的原则。“沉思翰藻”作为《文选》的编选标准当是针对部分文体而言的,换言之,其应当具有明确的适用范围,而并非如阮元《文言说》所说,是《文选》诸体适用的选文通则。
其二,关于“沉思翰藻”的含义,学界目前众说纷纭,迄无定论。之所以会出现这么多的歧论,笔者窃以为,主要是因为对“沉思翰藻”的阐释原则尚不完善,因此还有补充的必要。
其三,通过对阮元文论的细致研读,笔者发现以“沉思翰藻”为魏晋文学界说的观点,不过是阮元等清代选学家为了与桐城古文争夺文章正统而提出的权宜之说,与《选序》本义不符。但是阮元的著作历来又被认为是研究《选序》的重要参考资料,那么我们在探讨阮元文论与《选序》的相通性的同时,对阮元“沉思翰藻”说同萧统原《序》的歧义应当具有更为充分的警醒和觉察。
以下,本文就此三方面的问题作出论述。
一、“沉思翰藻”作为选文标准的适用范围
东京以降,文体转繁。西汉刘歆作《诗赋略》不过录“歌诗”、“杂赋”二体,及臻东汉,箴、铭、诔、颂、赞诸体勃兴。刘咸炘《〈文选序〉说》从目录学的角度论述两汉文体演变之历史曰:“《七略》渐变而为四部,刘氏《诗赋》一略,王氏《七志》更为‘文翰’,阮氏《七录》又改‘翰’为‘集’,而‘文集’之名成。盖诗赋之体流变为颂、赞、箴、铭、设词、连珠,而其风势推用于一切告语之文,必称‘翰’而后可该,而集之为称自隋以前固专指篇翰之出于诗教者也。”[1]文章依据其体裁的差异而有不同的创作要求。因此,判断文章良莠的第一标准是得体与否。《文镜秘府论·论体》尝论之曰:“至如称博雅,则颂、论为其标;语清典,则铭、赞居其极;陈绮艳,则诗、赋表其华;叙宏壮,则诏、檄振其响;论要约,则表、启擅其能;言切至,则箴、诔得其实。凡斯六事,文章之同义焉。……故词人之作也,先看文之大体,随而用心。遵其所宜,防其所失,故能辞成炼覈,动合规矩。而近代作者,好尚互舛,苟见一涂,守而不易,至令摛章缀翰,罕有兼善。岂才思之不足,抑由体制之未该也。”[2]
文体差异的日益显著促使与之相适应的文学理论必须针对不同的文体特点作出分体研究。自三国曹丕的《典论·论文》以迄南齐刘勰的《文心雕龙》,各家文论基本上都采用了分体论文的方式。顾农《〈文选〉的三重背景说》一文指出:“关于文体分类的问题,曹丕在《典论·论文》中首先提出了所谓四科八目,讲的比较概括;到陆机《文赋》便分作十种,原先被排在最末的诗赋被提到了前列,各体的规范讲得较为细致。到挚虞,更联系所选之文来畅论文体问题,并注意在历史的变迁中分析有关文体的初原状态、古今之变与假借名义似是而非等复杂情形。”[3]文体样式的渐趋繁盛和文章著作的日益增多,催生了杂纂诸体的文学总集。《隋书·经籍志》曰:“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摘孔翠,芟翦繁芜,自诗赋以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之《流别》。”[4]
文章的创作及其评价标准既然依文体不同而有所区别,那么作为杂纂诸体的总集势必不可能以一个整齐划一的标准来权衡其编选的各体文章。诞生于《昭明文选》之前的一部重要的文学总集即东晋李充编纂的《翰林论》使用的就是分体编选的标准。《翰林论》全书久佚,今辑其论文之说,略见分体编选之法:“论贵于允理,不求支离。若嵇康之论,成文美矣。”“表宜以远大为本,不以华藻为先。若曹子建之表,可谓成文矣”[5]2678,2674。“或曰:‘如斯何可谓之文?’答曰:‘孔文举之书,陆士衡之议,斯可谓成文矣。”[6]李充的分体编选之法值得我们注意的有以下两点:其一,各体文章成文与否不使用统一的评判标准即没有选文通则,因而各文体的代表作家和作品有明显差异;其二,成文或者不成文是文章优劣的评判标准,而非如清人阮元所谓是文学与非文学的评价判准。
《昭明文选》并未效仿《翰林论》,对各体文章的编选标准详加论述。其主要编撰者萧统为后人留下的“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一段论述,引发了后世对《文选》编选之法的无限猜测和争议。然而,只要我们细致地在现存文献中钩深索隐,仍然可以找到《文选》分体论文的蛛丝马迹。作为《昭明文选》编撰者之一的刘孝绰,在《昭明太子集序》中说:“窃以属文之体,鲜能周备。长卿徒善,既累为迟;少孺虽疾,俳优而已。子源淫靡,若女工之蠹;子云侈靡,异诗人之则。孔璋词赋,曹祖劝其修今;伯喈答赠,挚虞知其颇古。孟坚之颂,尚有似赞之讥;士衡之碑,犹闻类赋之贬。深乎文者,兼而善之,能使典而不野,远而不放,丽而不淫,约而不俭,独善众美,斯文在斯。”[7]245刘《序》所言,分明是分体论文之说。而此《序》既为萧统文集所作,可想萧统亦必对分体论文有所会心。由此我们可以推论《昭明文选》的编纂应当不会在前人分体论文的原则之外另立新规。故而以“沉思翰藻”将《昭明文选》选文标准一元化的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事实上,俞绍初、曹道衡诸先生业已指出“沉思翰藻”说是针对《昭明文选》中的两类文体即“史论”和“史述赞”①而提出的②。因此,“沉思翰藻”作为《文选》的选文标准,它的适用范围就具有了明确的界定即是“史论”的编选标准,而非《文选》的选文通则。
二、“沉思翰藻”释义
《文选序》“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一说的确切含义,历来解说多有不同。朱自清先生主张“事”、“义”一体,皆训“事典”,“翰藻”训作“比类”,“沉思翰藻”即“善于用事,善于用比”之义也[8]。王利器先生认为“萧统之所谓‘事’,即刘(勰)、颜(之推)之所谓‘事义’;其所谓‘义’,则刘、颜之所谓‘辞藻’也”[9]。蔡钟翔先生认为萧统所谓“事”指“事类,也就是后人所说的典故”,“义”与“事”对举,属于内容。至于“翰藻”也即是辞采,指形式[10]。赵树功先生援引魏晋玄学之说,以为“义归乎翰藻”之“义”是“玄学所关涉的经典和对这些经典要旨的领会与清谈的一个总称”[11]。
综观前贤时彦阐释“沉思翰藻”的方法,主要是蒐集大量含有“事”、“义”之说的魏晋六朝文献,通过分析比对,总结出六朝文献使用“事”、“义”的语例,并据此解释《选序》“沉思翰藻”之说。然而笔者认为,欲阐明《选序》“沉思翰藻”的含义,仅有吻合“事”、“义”语例的惟一原则是不够的。尚须同时遵循以下两个阐释原则,方能做到释义圆足:
其一,诚如俞绍初先生所言,“事”、“义”之说夺胎于《孟子》之文,原典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檮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也。’”(《孟子·离娄下》)因此,阐释《选序》之“沉思翰藻”,必须首先阐明原典中“事”、“义”的含义,厘清“事”、“义”之说的渊源所自,在正本清源的前提下,方能逐次梳理出后世文献中“事”、“义”语义流变的轨迹。
其二,如笔者上文所言,“沉思翰藻”说的适用范围是《文选》所收录的史论。因此,在阐释“沉思翰藻”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考虑到六朝史论文体的发展历程以及由此带来的时人文学观念的变化。
以下,笔者试对“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说作出重新解释,以与前贤时彦相商榷。
按原典之义,孟子认为:一部杰出的历史著作应当包括两部分的内容即“事”和“义”。“事”指的是历史文献所记录的史实,即“齐桓晋文”之类是也。“义”指的是史家对纷繁复杂的历史事实作出的深刻观察和准确评价。孔子之“春秋大义”,《汉书·艺文志》所谓“有所褒贬,不可书见”者也,故曰“窃取”。一部史书如果仅有对历史事件的复述,而表达不出深刻的历史见解,孟子认为这样徒有其表的历史叙述就是“其文则史”。“其文则史”之“史”,当与“文胜质则史”(《论语·雍也》)之“史”同义。王衡《四书驳义》曰:“史乃祝史之史,知其文而不知其文之实,《郊特牲》所谓‘失其义,陈其数,祝史之事也’。”[12]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事”、“义”二者至少具有以下两点不同:
其一,“事”作为对历史事件的复述,是文本明示的内容,换言之是“表面文章”。相对而言,“义”是史家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叙述,以“春秋书法”的形式暗示的内容,读者尚须经过钩深索隐的阐释方能有所会心。换言之,“义”指的是历史文本的“言外之意”。
孔子所开创的这种通过历史故事的讲述来隐晦地表达思想观念的方法,为后世学子们继承和发展,演化为文学创作中事典的使用。《文心雕龙·事类》曰:“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昔文王繇《易》,剖判爻位,《既济》九三,远引高宗之伐;《明夷》六五,近书箕子之贞:斯略举人事以征义者也。”[13]472刘勰所谓“据事以类义”者,就是通过讲故事来表达思想。如《易》爻辞通过讲述“高宗之伐”、“箕子之贞”等故事来表达中国古人朴素的哲学观念,即其例也。
笔者在此要特别指出的是,今所见六朝文章“事义”连用的语例——除《颜氏家训·文章》“事义为皮肤”外——皆指“义”而不指“事”。换言之,“事义”宜看作偏正结构的合成词,释作“事之义”。如《抱朴子外篇·喻蔽》:“数千万言,虽有不艳之辞,事义高远,足相掩也。”[14]以及《文心雕龙·附会》:“夫才量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13]519前者之所谓“辞”,指的是文章的表面形式,而高远的“事义”是文章的深刻内涵;后者以“事义”、“辞采”分属“骨髓”、“肌肤”,一为内蕴,一为外露,可见“事义”所指亦即是“义”。
阐明“事”、“义”语例之后,我们进一步分析萧统文章中“事”、“义”的使用情况,可知其同样与笔者上述分析相吻合。如《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发函申纸,阅览无辍。虽事涉无有,义异拟伦,而清新卓尔,殊为佳作。”[7]155萧统所谓“事涉无有”,指的是文章虚构的人物事件荒诞无稽,“事”即虚构之故事。“义异拟伦”指的是萧统通过分析,发现这些故事的虚构不符合“拟人必于其伦”(《礼记·曲礼》)的文化传统,“义”指的是与传统文化不侔的思想观念。
其二,“事”、“义”的区别还表现在两者对相同问题的认识程度有肤浅与深刻的差异。史家所记之“事”仅仅是对史实的单纯复述,而“义”却是对史实入木三分的分析以及由此形成的深邃的历史见解。孟子以为孔子之前的史书都流于对历史事件的肤浅叙述,所谓有事无义,其文则史之流。独有孔子《春秋》卓尔不群,能够穿透纷繁复杂的历史表象,展现出对史实的深刻分析与准确判断。可见,“事”、“义”二者确有高下之分。于是,我们不禁要追问:为什么春秋战国的众多史书之中,独有孔子之史能做到事义兼备、超凡脱俗呢?孔子自己就告诉了我们答案。他说“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故刘勰《文心雕龙·体性》因之曰“事义深浅,未闻乖其学”[13]379,由此可知,“事义”之有无、深浅,系乎天才者少,系乎学养者多。
在明辨“事”、“义”之后,让我们来分析《选序》的“沉思翰藻”之说。《昭明文选序》曰:“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15]这里“综缉辞采”意指词藻,“错比文华”意指骈偶,二者都属于文章的艺术形式,是表面性质的内容,因此二者都是“事”。“沉思”当从朱自清先生说,诂作“深思”,“事出于沉思”是说史论所展现的曼妙的艺术形式如“综缉辞采”、“错比文华”之类都是经过精心构思的。“翰藻”非辞采之谓,而是“文章”的代称。“义归乎翰藻”是说正是注意到史论创作锐意追求上述镂金刻玉、精雕细琢的艺术形式,故而萧统认为它已经不再是纯粹的为史而论,更表现出了美文的艺术特质。有鉴于此,萧统才将史论这一文体从众多史部著述中遴选出来,编入《文选》。这里的“义”指的是六朝史论文学化的时代观念。
可见,萧统提出“沉思翰藻”说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说明《文选》囊括史论这一文体的原因,当然从中我们可以间接地看出《文选》对这一文体主要依据文章形式即辞采和对偶的标准进行编选。史论的编选虽然主要依照文章形式制定选文标准,但是史论文体的特殊性决定了它的编选标准未必能为其他诸多文体共用。因为史论本是史部著作,《文选》站在编选文学总集的角度编选史论,只能从文章形式上寻求评价标准,如以内容为标准则选文当归诸史部而非集部。但是在编选其他文体时,《文选》应当不仅据文章形式为标准而可能兼顾内容的要素。萧统并未就《文选》中其他文体的编选标准作出说明,但参考笔者前引李充《翰林论》的选文标准:“表宜以远大为本,不以华藻为先”,可知《翰林论》在编选表这种文体时优先考虑的就不是文章的形式要素。以此作参照,萧统编选《文选》诸文体时,也可能出现上述不以文章形式优先的编选方法。所以,在没有直接文献依据对《文选》其他文体的选文标准进行说明的情况下,为慎重起见,当以“沉思翰藻”作为史论一体的编选标准庶几更近于事实。接下来的问题是,在魏晋六朝,本为历史著述的史论,为什么会表现出“综辑辞采”、“错比文华”的审美特质因而被萧统选入《文选》呢?要解答这一问题,我们有必要对史论这一文体的演变过程作一考察。
《史通·论赞》曰:“夫拟《春秋》以成史,持论尤宜阔略。其有本无疑事,辄设论以裁之,此皆私徇笔端,苟炫文彩,嘉辞美句,寄诸简册,岂知史书之大体,删削之指归者哉?必寻其得失,考其异同,子长淡泊无味,承祚懦缓不切。贤才间出,隔世同科。孟坚辞惟温雅,理多惬当。其尤美者,有典诰之风,翩翩奕奕,良可咏也。仲豫义理虽长,失在繁复。自兹以降,流宕忘返,大抵皆华多于实,理少于文,鼓其雄辞,夸其俪事。”[16]从刘知几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春秋》以降,史论的文笔呈现出由质而文、日益华丽的发展趋势。六朝史家撰写史论,非但考虑其史学价值,还有意兼顾其文学价值。其最著之例如范晔《后汉书》。范晔《狱中与诸侄甥书》曰:“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17]对《后汉书》诸史论,范晔雅自珍重,以为比之前贤如贾谊、班固之作而无愧,他所引以为傲的正是“笔势纵放”的文章艺术,而非深刻的史学见解。
要之,《选序》“沉思翰藻”之论体现的是萧统对六朝史论文学化趋势的敏锐观察。“沉思翰藻”的价值不仅在于为《文选》提供了史论编选的标准,更重要的是对六朝史论的审美观念的新变化作出了文字性的总结。
三、阮元“沉思翰藻”说同《选序》原义之区别
《选序》“沉思翰藻”一说之所以在后世具有深远的影响力,离不开清代学者阮元的大力表彰和系统阐释。阮元《书昭明太子文选序后》及《与友人论古文书》两篇文章对于《文选序》的阐释得到后世众多研究者的重视,时至今日仍是学界研究《选序》的重要参考资料。然而通过对《揅经室集》的系统研究,笔者发现:囿于清代骈散之争的文艺格局,阮元“沉思翰藻”说的宗旨重在益时而不非述古。阮元对“沉思翰藻”的阐释在诸多方面都同《选序》原义有着显著的区别。鉴于阮元“沉思翰藻”说对当前的“选学”研究仍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故而辨明阮元文论同《选序》原义的区别,对于我们更深入地研究《文选》,同时也更准确地把握清代文论的时代精神都是不无裨益的。今试将阮元“沉思翰藻”说同《文选序》原义的区别及其形成原因分析如下。
首先,阮元“沉思翰藻”说的宗旨是为文学立界,而《文选》“沉思翰藻”说是对选录史论这一文体的解释说明。
《与友人论古文书》一文讲道:“《昭明选序》,体例甚明,后人读之,苦不加意。《选序》之法,于经史子三家不加甄录,为其以立意纪事为本,非沉思翰藻之比也。今之为古文者,以彼所弃,为我所取,立意之外,惟有纪事,是乃子史正流,终与文章有别。”[18]610阮元以为,“沉思翰藻”意在说明什么是文章并进而同经、史、子三部著作划清界限,换言之是为文学设立学科分类标准。后来章太炎先生在《文学总略》中说“(《选序》)简别三部,以文辞之封域相格”[19]正是对阮元之旨的概括。既然阮元“沉思翰藻”说是为文学立界,那么他究竟界定什么样的著作才能称之为文章呢?其《书昭明太子文选序后》一文曰:“昭明所选,名之曰‘文’。盖必文而后选也,非文则不选也。经也,子也,史也,皆不可专名之为文也,故《昭明文选序》后三段特明其不选之故。必沉思翰藻,始名之为文,始以入选也。或曰:昭明必以沉思翰藻为文,于古有征乎?曰:事当求其始。凡以言语著之简策,不必以文为本者,皆经也,子也,史也。”[18]608阮元以为必“沉思翰藻”者乃得称“文”,经、史、子之所以与“文”有别,皆因不能“以文为本”。因此“以文为本”四字便是阮元划出的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而本着“以文为本”的精神来编选文学总集就是“文而后选”,由此阮元将《文选》“沉思翰藻”说由史论一体的编选标准提升为了诸体共用的选文通则。朱自清先生在《〈文选序〉“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说》一文中引阮元《文韵说》“在声为宫商,在色为翰藻”一句来解释阮元“沉思翰藻”,训“翰藻”为“错比文华”,笔者窃以为这一观点值得商榷。《文韵说》所阐释的对象是《文心雕龙·原道》而非《选序》,关于这一点笔者将另撰专文论述。在此只是要指出:阮氏“沉思翰藻”之“翰藻”非指错比文华的文章形式而是“文学”的代称。阮元《诰授光禄大夫刑部右侍郎述庵王公神道碑》曰:“皇、熊义疏,拙于文词;陆、沈藻缋,昧于朴学。”[18]425此处“文词”与“藻缋”、“义疏”与“朴学”皆是互文见义。“藻缋”即“沉思翰藻”之“翰藻”,与“朴学”即经学对举,其义指文学。“沉思”者,专注之谓也。阮元“沉思翰藻”的真义即是专注于文或者说“以文为本”。
其次,在阐明了阮元“沉思翰藻”的涵义之后,我们不禁要深究:为什么阮元会将萧统的“沉思翰藻”改造为“以文为本”呢?学界目前的共识是:阮元的“沉思翰藻”说是为了攻击乾嘉时期的桐城古文进而为选学派争夺文章正统张目而提出的主张③。那么,我们在讨论阮元“沉思翰藻”说的针对性以及这一学说形成的历史原因时,也应当将其放在乾嘉文章正宗之争的这一文化背景下进行考量。
关于桐城古文及其与以阮元为代表的扬州学派之关系,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有这样的概括:“乾隆之初,惠、戴崛起,汉帜大张,畴昔以宋学鸣者颇无颜色。时则有方苞者,名位略似斌光地等,尊宋学,笃谨能躬行,而又好为文。方苞桐城人也,与同里姚范、刘大櫆共学文,诵法曾巩、归有光,造立所谓古文义法。号曰‘桐城派’。又好述欧阳修‘因文见道’之言,以孔孟、韩欧、程朱以来之道统自任,而与当时所谓汉学者互相轻。”[20]桐城古文以继承唐宋八家为自觉。唐宋古文最显著的特点是将文统绑缚于道统之上,即“文以载道”。原本属于经学话题的性与天道被唐宋古文强挪到文学领域来论说,“文”作为“载道”的工具,是“道”的附属品。晚清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表彰方苞之文实“六经之裔”[21],“裔”者衍生、附属之谓,正可为“文以载道”之注解。所以桐城派的文学主张可以说是“以道为本”。
以阮元为代表的扬州学派对桐城古文的攻击首先是从“道统”开始的。如梁启超先生所言,古文“道统”承祧于宋明理学。在阮元看来,宋明理学不符合孔孟的原教旨,不是儒学正宗而是掺杂释、道的杂家之流。阮元《性命古训》曰:“自昌黎、习之,言性道者几欲自成一子,接迹孔孟,此则太过。”[18]214道统既然不正,载道的文统也势必成为阮元攻击的对象。阮元《与友人论古文书》说“今之为古文者,以彼所弃,为我所取,立意之外,惟有纪事,是乃子史正流,终与文章有别”,对比刘声木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到:刘声木表彰古文为“六经之裔”,也就是说古文是遵经述古,道统是直承孔孟;反观阮元,贬斥桐城古文为“子史正流”,言下之意是一家之言,未必合乎圣训,这是否定了古文道统。“终与文章有别”即不符“沉思翰藻”之义,遂将古文排挤在文学界外,这是否定了古文文统,此即阮元“沉思翰藻”之要义也。
综上所述,阮元提出“沉思翰藻”、“以文为本”的理论,其目的是要将逐渐沦为道学附庸的文学重新独立出来,扶植与古文道统不相干的骈文,另立骈文文统,从而达到排挤桐城派以占据文章正宗的目的。阮元“沉思翰藻”一说,若论其意义,笔者窃欲比之于康有为《孔子改制考》,诚乃有裨于时事而无助于考古。阮元“沉思翰藻”说虽然在某些方面对《选序》有所继承,但是并非一意祖述萧统的文学理论,两者是应当区别对待的。
注释:
①笔者按:论、赞本为一体即史论。《文选》析之为二,盖沿挚虞《文章流别》之误。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有辨(参见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卷二《颂赞》,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73页),今从范先生之论,下文直以“史论”称之,不取析分二者之说。
②参见俞绍初:《昭明太子集校注·前言》,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4页;曹道衡:《〈文选〉对魏晋以来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文学遗产》2000年第1期。
③参见冯乾《清代文学骈散之争与阮元〈文言说〉》,《古典文献研究》第11辑,第278-294页;陈文新《论乾嘉年间的文章正宗之争》,《文艺研究》2004年第4期;穆克宏:《阮元与〈文选学〉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陈志扬《阮元骈文观嬗变及其历史意义》,《文学评论》2008年第1期。
标签:阮元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昭明文选论文; 中国古代文学论文; 春秋论文; 国学论文; 读书论文; 六朝论文; 文选论文; 古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