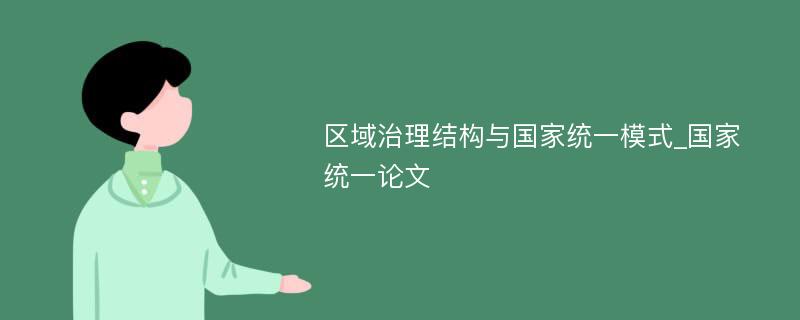
区域治理结构与国家统一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治理结构论文,区域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35 分裂国家统一(Divided-Nations or Divided-Countries Reunification)是指原本政治统一的国家分裂为分离实体状态之后,重新在主权、领土、人口、外交承认、内部机构、国内支持六大领域实现整合的过程。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国际社会先后出现了德国、越南、也门等分裂国家。1976年7月,越南民主共和国通过武力方式战胜越南共和国,宣布实现南北统一,改国名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1990年10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加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并沿用西德的国名。1990年5月,阿拉伯也门共和国与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通过一体化合作宣布统一,改国名为也门共和国。 国家统一不是“行为体取向”的单一发展,而是“结构性取向”综合作用的结果。国家层面上的政治军事与经济社会、区域层面上的区域大国以及区域组织、全球层面上的“极”的关系与意识形态,这些复合权力结构因素综合影响着国家统一及模式选择。其中,区域因素虽然不是影响国家统一与否的同质性复合权力结构因素,却是影响国家统一模式选择的重要异质性复合权力结构因素。② 截至目前,学界从区域视角对国家统一模式进行的比较研究并不多见,且不够深入。双案例比较研究包括洪承勉的《分裂国问题的再发现》③、朴光得的《从德国模式看韩国统一问题之研究》④、梁锦文的《自德国模式研究中国统一问题》⑤,这些文章虽然探讨了欧洲一体化中的德国统一进程,也对东亚区域主义未能在朝鲜半岛统一或两岸统一进程中发挥足够的影响这一问题进行了反思,但并未就区域因素深入展开。 三案例比较研究有:丘宏达(Hungdah Chiu)与道温(Robert Downen)的《多体制国家与德、韩、中的国际地位》⑥、张五岳的《分裂国家互动模式与统一政策之比较研究》⑦、金珉俊(Min Jung Kim)的《统一:对越南、也门与德国统一的比较研究》⑧。前两部专著比较分析了东西德、韩国朝鲜、大陆台湾统一问题,后一篇论文着眼于越南、也门与德国的比较。以上研究关注到了区域因素对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但所涉不深。 多案例比较研究包括:赵全胜(Quansheng Zhao)与罗伯特·萨特(Robert Sutter)的《分裂与统一:中国、韩国、德国、越南经验之比较研究》⑨、李毅臻的《统一之路与分裂之痛:二战后分裂国家统一的启示与统一国家分裂的教训》⑩、陈云林的《当代国家统一与分裂问题研究》(11)。这些书籍对德国、越南、也门、朝鲜的统一从历史角度进行了阐述,也探讨了坦桑尼亚、塞浦路斯、科索沃等国家的分裂与统一问题,其中都部分涉及区域因素。然而,以上研究采取以国别分章的体例,缺乏理论分析框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比较研究。 国内外学界在分析国家统一问题时,已经注意到了区域治理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然而,以往研究成果大多存在以下不足:第一,缺乏系统性的比较研究,难以从整体上把握区域治理对国家统一模式产生的影响。第二,缺乏针对性的类别研究,难以解析不同类型区域治理对不同类型国家统一进程的不同影响。第三,缺乏结构性的互动研究,仅从行为体的区域治理视角难以解析复杂的国家统一等变革性问题。为了弥补学术界在该问题研究中的盲点,本文尝试构建“结构性”的区域治理新理论,探讨区域治理结构对越南武力统一、德国吸收统一、也门一体化统一的不同影响效力,进而论证“区域治理结构影响国家统一模式”这一研究假设。 二、区域治理结构:解析统一问题的新视角 区域治理结构是指以区域一体化组织为基点、能在一定区域内引导并限制某个行为体行动的综合体系。依据层次标准,区域治理结构可以分为:自结构、内结构、外结构三个方面。(12) 区域治理自结构是指区域国际组织自身性质的特征结构,包括:组织成员特征,即组织成员历史文化是否同质、政治经济是否同质;组织制度设计,即组织制度是否紧密、组织一体化合作是否启动。区域治理内结构是指区域国际组织与区域内国家之间的互动结构,其内涵为组织与研究对象(分裂国家),即组织成员是否包括分裂方、组织领导者是否为分裂方;组织与区域大国,即组织成员是否包括区域大国、组织领导者是否为区域大国。区域治理外结构是指区域国际组织与全球超级大国之间的互动结构,内容为:组织与霸权兴衰,即组织是否隶属于上升霸权阵营、组织是否听从隶属霸权的安排;组织与霸权外交,即组织是否受霸权多边外交影响、组织的领导者是否与霸权结盟。若以上三个层次、六大因素、十二项指标中各项指标多偏向“是”,则该区域治理结构是一种“强结构”;若以上各项指标多偏向“否”,则该区域治理结构是一种“弱结构”;处于中间状态的则是“中度结构”。 制度强弱不同的区域治理结构对大国、中等国家、小国这三类实力强弱不同的国家的影响效力存在差别。由于强结构的影响效力显然大于弱结构,加之小国相对于大国而言更易受到外界的影响,因此,区域治理结构对国家影响的效力从弱至强呈现出五个梯度——Ⅰ度影响力:弱结构—大国;Ⅱ度影响力:中度结构—大国、弱结构—中等国家;Ⅲ度影响力:强结构—大国、中度结构—中等国家、弱结构—小国;Ⅳ度影响力:强结构—中等国家、中度结构—小国;Ⅴ度影响力:强结构—小国。在同一程度的影响效力中,各类型影响效力的差别具体视区域治理结构的十二项指标相对于不同实力的国家而定。 本研究选择东南亚治理结构之于越南武力统一、西欧治理结构之于德国吸收统一、中东治理结构之于也门一体化统一作为比较研究案例,其原因在于三个案例具有典型的相似性与差异性。从“求同法”的角度看,越南、德国与也门原来均为一个拥有共同语言、历史文化与长期统一经历的主权国家,同属于二战结束后出现的分裂国家,它们深受冷战时期美苏两极对峙的影响,也深受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立的影响。此外,三者都是二战后分裂国家中成功完成统一的案例,这是本文在案例选择中排除朝鲜半岛统一问题的重要原因。 从“求异法”的角度看,首先,三个案例分属于不同的“区域治理结构—国家”类型。东南亚治理结构中的十二项指标均偏向“否”,是典型的弱区域治理结构。越南由于拥有较强的军事实力,且能在长期的抗美战争中最终迫使美国撤军,可以视为中等国家。因此,东南亚治理结构之于越南统一,属于影响效力非常微弱的Ⅱ度“弱区域治理结构—中等国家”类型。西欧治理结构中的十二项指标均偏向“是”,是典型的强区域治理结构。德国作为欧洲大陆的经济强国与政治强国,属于大国行列。由此,西欧治理结构之于德国统一,属于影响效力较强的Ⅲ度“强区域治理结构—大国”类型。中东治理结构中十二项指标有九项指标偏向“是”,可被视为中度区域治理结构。也门无论是国家面积、人口数量,还是经济发展、军事实力,都是公认的小国。所以,中东治理结构之于也门统一,属于影响效力非常强的Ⅳ度“中度区域治理结构—小国”类型。 其次,三国选择了不同的统一模式。按照“是否使用暴力”的标准,分裂国家统一模式可以分为武力统一模式与和平统一模式。在和平模式中,若按“谁为主导力量”这一标准来分类,又可以划分为一方主导的吸收统一模式与双方共同主导的一体化统一模式。越南统一是武力模式的典型,德国统一是吸收模式的代表,也门统一是一体化模式的案例。 由上观之,对比研究越南、德国、也门统一中的区域治理结构,探寻其中的“同质性”与“异质性”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下文将从自结构、内结构、外结构三个层次,逐一解析区域治理结构对国家统一模式的影响。 三、区域组织的成员制度:“自结构”与统一模式 越南武力统一受到东南亚治理自结构的影响。东南亚治理自结构包括东盟的成员特征与东盟的制度设计。1967年8月,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和新加坡五国外长签署《曼谷宣言》,组建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东盟成员国宗教文化多元、历史经历不同、政治体制迥异、经济发展不均,是最具差异性的国家集团。东盟没有实质意义上的经济合作,也缺乏政治与法律意义上的中央决策机构。东盟成员特征的异质性与制度设计的松散化,使得区域机制无法制约越南对武力统一模式的选择。首先,东盟因成员国之间历史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异质性特征而实施不干涉政策。美国在越南溃退时曾呼吁东盟通过区域合作承担起自身防务的最基本责任,但未能改变东盟在非军事条约方面的立场。(13)东盟对越南武力统一局势也采取了观望姿态。其次,东盟制度设计松散化且一体化合作尚未启动,这都限制了其地区影响力。东盟方式强调协调一致,其实质是避免冲突而非解决冲突,并把已经导致的冲突掩盖起来。因此,在北越武力进攻南越这一既涉及领土争端又关乎国家主权的事件中,东盟无心也无力干涉此进程,只能默认武力统一的现实。 德国吸收统一受到西欧治理自结构的影响。西欧治理自结构涉及欧共体的成员特征与欧共体的制度设计。1967年7月,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组建欧洲共同体(欧共体)。随后,英国、丹麦等国加入,形成历史上的欧共体“12国”。欧共体成员国都以白人为主体,历史经历相似,宗教信仰相同,政治体制类同,经济发达且差距较小。该组织形成了以关税同盟、共同农业政策、经济与货币联盟为三大支柱的经济一体化合作。欧洲议会作为法律意义上的决策机构,拥有立法、预算、监督等权力。欧共体成员的同质性特点与欧共体制度的紧密化状态,在区域层面上影响着德国对吸收统一模式的选择。其一,欧共体因同质性特征而形成了和平主义。西德与欧洲大国及周边国家逐步建立了和平稳定的外交关系。其中,西德与法国关系、西德与波兰关系的修复尤为关键。其二,欧共体因紧密化特征而形成了非武力的冲突管理新文化(a new culture of conflict management),推动了欧共体和平共同体(peace community)的形成。德国统一前夕,“欧洲一体化已转为一种体系,布鲁塞尔的复杂谈判、政府机构的协商、各种利益集团的协调决定着欧洲和平的现在与未来的发展”。(14) 也门一体化统一受到中东治理自结构的影响。中东治理自结构包括阿盟的成员特征与阿盟的制度设计。1945年,约旦、叙利亚、沙特、伊拉克、黎巴嫩、埃及和也门(以观察员身份)7国组建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之后,利比亚、苏丹等国先后加入,形成冷战时期的阿盟“21国”。阿盟成员国均为阿拉伯民族国家,尊伊斯兰教为国教,曾沦为英法殖民地,其民族宗教与历史文化呈现出一定的同质性。阿盟内存在君主制模式与共和制模式的政治竞争。产油大国极其富有,少油或无油国家则处于贫困状态。阿盟一体化合作在冷战时虽已开启,但没有实质性的运作。阿盟的决策机构理事会只是名义上的机构,成员国首脑会议才拥有实质上的决策权与最终决定权。阿盟成员国的政治经济相异但历史文化同质、阿盟制度设计松散但一体化合作开启,这使得阿盟对也门和平的一体化统一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第一,阿盟经济一体化合作为南北也门经济交流提供了平台。在此背景下,南北也门从1977年开始陆续在农业、渔业、矿产、电力、水利、贸易、投资、石油与矿业开发等领域开展合作项目。第二,阿盟的“斡旋外交”在也门统一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阿盟的斡旋与协调下,南北也门分别于1969年达成《塔兹协定》,于1972年签订《开罗协议》,于1979年形成《科威特协议》,于1989年签署《亚丁协议》,这一系列和平协定促进了也门统一进程。 通过比较可见,影响国家对武力统一模式或和平统一模式选择的区域治理自结构为:组织成员历史文化是否同质,组织一体化合作是否启动。其中,答案为“否”时,国家偏向选择武力模式;答案为“是”时,国家偏向选择和平模式。区域治理自结构对和平统一模式中是选择吸收模式还是选择一体化模式,并没有直接的影响。 四、区域组织与地区国家:“内结构”与统一模式 东南亚治理内结构影响着越南武力统一进程。东南亚治理内结构包括:东盟与分裂双方的生存发展,涉及东盟与南北越南;东盟与区域大国,涉及东盟与中国。越南武力统一之前,南北越均未加入东盟组织。北越与东盟处于敌对状态,南越与东盟则保持友好关系。中国是影响东南亚政治的重要区域大国,但游离于东盟机制之外。敌对的南北越均处于东盟之外,中国与东盟存在政治芥蒂且处于东盟框架之外,这些东南亚治理内结构影响着越南对武力统一模式的选择。首先,组织之外的越南的局势不受东盟和平规范的制约。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北越拒绝了所有形式的和平斡旋与和平协商,迅速发动了对南越的统一战争。其次,中国处于东盟框架之外,且双方处于不信任状态,使得区域大国在越南武力统一中的影响力大大超过了东盟作用。中国是第一个承认北越的国家,并对其进行了积极的支持,“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15)1975年,获得中国大量无偿军事物资援助的北越向南越发动了武力进攻。 西欧治理内结构影响着德国吸收统一。西欧治理内结构包括:欧共体与分裂双方的生存发展,涉及欧共体与东西德国;欧共体与地区大国,涉及欧共体与法国。西德是欧共体的创始会员国与主导国家。欧共体的《罗马条约》给予了东德以“欧共体准合作国”(quasi-associate status)的地位。(16)法国在欧共体发展进程中集“创始者、推动者、合作者、阻碍者与反对者”于一身,(17)但最终形成了“法国是我们的祖国、欧洲是我们的未来”的战略。(18)和解的东西德均处于欧共体之内,欧共体创始国与主导国之一的法国改善了与东西德的关系,至此德国统一问题中所涉及的各个区域行为体均从相互视对方为“敌人”转变为相互视对方为“竞争对手”甚至“朋友”,这都影响着德国对和平的吸收模式的选择。第一,西德是欧共体的主导力量,与西德关系缓和的东德也逐渐被纳入欧共体机制。《罗马条约》从法律上确认了两德贸易属于国内交往。(19)在此框架下,东西德国陆续在捕鱼权利、水质控制、废物处理等民生领域达成了共识。(20)第二,区域大国法国与德国积极合作推动欧洲一体化建设,此良性互动进程为德国和平统一塑造了有利的周边环境。欧洲煤钢联营是法德关系改善的起点。之后双方签署了《德法友好合作条约》,共同组建了军事混合旅。法国曾一度极力通过稳定东德来阻止德国统一进程,(21)但最终务实地默认了德国统一。 中东治理内结构影响着也门一体化统一。中东治理内结构涉及:阿盟与分裂双方的生存发展,即阿盟与南北也门;阿盟与区域大国,即阿盟与沙特。北也门是阿盟的创始会员国,与阿盟长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南也门独立后不久加入了阿盟,虽一度因与苏联结盟而遭到阿盟排挤,但在统一之前改善了与阿盟的关系。沙特是阿盟的创始会员国。在美国的支持下,沙特通过宗教旗帜与石油外交逐渐成为阿盟的领导国。阿盟成员包括南北也门,阿盟领导者沙特在南北也门实施平衡外交,这些中东治理内结构特性影响着也门一体化和平统一进程。其一,南北也门同处阿盟之中,深受阿盟规范及社会化进程的影响。两次南北也门边境战争的停战及之后统一协定的达成,均是在阿盟的斡旋与调停中实现的。在阿盟合作框架下,南北也门启动了从经济合作到政治合作的统一进程。(22)其二,统一前夕北也门逐步改变了唯沙特马首是瞻的外交政策,而南也门则于1983年恢复了与沙特的外交对话。沙特与邻国南北也门的等距离温和外交,使得其在也门问题上支持一体化统一政策。 可见,影响国家对武力统一模式或和平统一模式选择的区域治理内结构为:组织成员是否包括分裂方,组织成员是否包括区域大国,区域组织领导者是否为区域大国。其中,答案为“否”时,国家偏向选择武力模式;答案为“是”时,国家偏向选择和平模式。在和平统一进程中,影响国家对吸收模式与一体化模式选择的区域治理内结构为:组织成员包括分裂“一方”或“双方”。前者影响国家对吸收模式的选择,后者影响国家对一体化模式的选择。 五、区域组织与全球霸权:“外结构”与统一模式 越南武力统一受到东南亚治理外结构的影响。东南亚治理外结构包括:东盟与全球霸权兴衰,即东盟与美苏争霸;东盟与全球霸权外交,即东盟与美国双边外交。冷战时期,东盟战略地位偏低,自身实力弱小,种族宗教不同,历史文化差异巨大,因此美国在东南亚采取的是以美菲、美泰同盟为基点的双边主义外交政策。东盟隶属于霸权劣势的美国阵营且不受美国多边主义外交的制约,这一东南亚治理外结构使得东盟在越南武力统一问题上影响甚微。其一,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从东南亚的战略撤退,削弱了东盟的地区影响力。1973年,美国签署《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逐步从越南撤出全部军队。苏联则与北越签订了近十个军事援助协定,并支持北越政府于1975年南下发起全面武力进攻。此时,偏向西方阵营的东盟对越南问题没有采取过多的干预。其二,美国的双边主义限制了东盟多边主义制度的发展,减少了东盟在区域自治构建中的意愿与努力。东盟处理内部纠纷与外部冲突的能力弱小,难以有效阻止北越对南越的武力进攻。 德国吸收统一受到西欧治理外结构的影响。西欧治理外结构包括:欧共体与全球霸权兴衰,即欧共体与美苏争霸;欧共体与全球霸权外交,涉及欧共体与美国多边外交。西欧是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地带,其经济基础雄厚、实力较为强大,加之该地区在民主政治制度、宗教种族文化、历史经历等方面与美国具有相似性,因此美国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框架下开展了对西欧国家的多边主义外交。德国统一时,欧共体隶属的美国阵营在西欧处于权力优势,美国在西欧的多边主义外交政策加强了欧共体的效力,这些西欧治理外结构均影响着德国对吸收统一模式的选择。首先,从属于美国阵营的欧共体看,其外交效力随着美国在欧洲势力的相对上升而增加。德国一再明确保证统一后将继续留在北约之内,此举最终获得了美国对统一的明确支持。其次,美国在西欧的多边主义外交增强了欧共体在德国和平统一中的效力的同时,也减轻了欧共体对德国和平统一的阻力。北约吸纳西德以及保留统一之后德国的会员国地位的举动,减少了欧共体国家对德国的恐惧。欧共体在英法德主导协商的背景下,对德国加入北约持赞成态度,有助于德国和平统一进程的推进。 也门一体化统一受到中东治理外结构的影响。中东治理外结构包括:阿盟与全球霸权兴衰,即阿盟与美苏争霸;阿盟与全球霸权外交,涉及阿盟与美国双边外交。冷战时期的中东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地位偏低,且与美国在种族、宗教、文化与历史经历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因此美国在中东地区采取的是双边主义而非多边主义的外交政策。也门统一时阿盟隶属于优势霸权方即美国阵营,且听从美国的安排,阿盟虽不受美国多边主义外交影响,但其领导者沙特与美国结盟,这些中东治理外结构因素提升了阿盟在也门一体化统一进程中的影响力。首先,偏向美国阵营的阿盟,在也门统一问题上的外交效力随着美国在中东实力相对苏联上升而增加。统一前夕,北也门为美国的友好伙伴,南也门修复了与美国的外交关系,因此偏向于美国阵营的阿盟对也门一体化持赞成与支持的态度。其次,美国在中东实施的双边主义虽然限制了阿盟的发展,但美国与沙特形成了非结盟国家之间安全合作的一种隐性模式,这使得沙特主导的阿盟在也门一体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阿盟监督委员会的强力敦促下,经历了两次边境战争的南北也门先后通过了和平的法律文件,最终开启了实质性的和平进程并实现了国家的统一。 通过对比可见,影响国家对武力统一模式或和平统一模式选择的区域治理外结构为:组织是否隶属于上升霸权的阵营,组织是否听从隶属霸权的安排,组织的领导者是否与霸权结盟。以上答案均为“否”时,国家偏向选择武力模式;答案均为“是”时,国家偏向选择和平模式。区域治理外结构对和平统一模式中是选择吸收模式还是选择一体化模式没有直接的影响。 六、结论与启示 通过对越南武力统一中的东南亚治理结构、德国吸收统一中的西欧治理结构、也门一体化统一中的中东治理结构的比较研究,我们可以论证“区域治理结构影响国家统一模式”的研究结论,并可回答下列几个问题。 第一,区域治理结构影响国家对统一模式的选择。就影响效力而言,从强至弱的排序是:“中度区域治理结构—小国”类型,“强区域治理结构—大国”类型,“弱区域治理结构—中等国家”类型。 第二,影响国家对武力统一模式或和平统一模式选择的区域治理结构为:在自结构中,组织成员历史文化是否同质,组织一体化合作是否启动;在内结构中,组织成员是否包括分裂方,组织成员是否包括区域大国,区域组织领导者是否为区域大国;在外结构中,组织是否隶属于上升霸权阵营,组织是否听从隶属霸权的安排,组织的领导者是否与霸权结盟。以上均为“否”时,国家偏向选择武力模式;均为“是”时,国家偏向选择和平模式。 第三,影响国家和平统一进程中对吸收模式与一体化模式选择的区域治理结构为:在内结构中,组织成员包括分裂“一方”或“双方”。其中,前者影响国家对吸收模式的选择,后者影响国家对一体化模式的选择。 值得关注的是,区域治理结构中的其他因素,如自结构中的组织成员政治经济是否同质、组织制度设计是否紧密、内结构中的组织领导者是否为分裂方,以及外结构中的组织是否受霸权多边外交影响,这些对国家统一模式选择没有显著影响。 以上结论对中国统一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当前区域环境与中国关系处于“弱区域治理结构—大国”类型。中国以主权国家身份、中国台湾以地区身份共同参与的区域国际组织绝大多数都属于功能主义的经济或社会专属组织,组织本身的一体化合作较弱,基本不涉及政治提议。为了更好地实践“一国两制”这一和平的一体化统一模式,今后中国在构建区域外交战略时可考虑向“中度区域治理结构—大国”类型转变,在努力成为区域国际组织的领导者的同时,将台湾以某种名义纳入其中。这不仅有助于搭建两岸深入交流的区域平台、强化和平主义的区域机制,而且有助于消除来自域外大国美国与域内大国日本的消极影响,防范和反对台湾的“台独”行为,从而有效地推动中国和平统一进程。 为此,中国在东亚区域治理结构的构建中应有以下战略考量:就自结构而言,积极构建一个成员国历史文化同质的东亚区域国际组织,并推动组织一体化合作进程;就内结构而言,将中国台湾以地区身份而非主权国身份纳入其中,在努力塑造中国自身作为组织领导者的同时,将区域大国日本纳入其间并发展两国友好关系;就外结构而言,构建起与全球霸权国美国的良性互动友好关系,以稳定美国对中国统一问题的和平偏向。 ①Gregory Henderson,Richard Ned Lebow & John S.Stoessinger(eds.),Divided Nations in a Divided World,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71,No.3,1977,p.1233.[美]约翰·鲁尔克:《世界舞台上的政治》,白云真、雷建锋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2年,第189~192页。 ②夏路:《复合权力结构与国家统一模式——对越南、德国与也门的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216~219页。 ③[韩]洪承勉:《分裂国问题的再发现》,安保统一问题研究所编:《东西德与南北韩》,东亚日报社,1973年。 ④朴光得:《从德国模式看韩国统一问题之研究》,台湾大学政治研究所硕士论文,1985年。 ⑤梁锦文:《自德国模式研究中国统一问题》,台湾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88年。 ⑥Hungdah Chiu & Robert Downen(eds.),Multi-System N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Status of Germany,Korea,and China,Occasional Pagers Reprints Series in Contemporary Asian Studies,University of Maryland School of Law,1981. ⑦张五岳:《分裂国家互动模式与统一政策之比较研究》,台湾:业强出版社,1992年,第303~308页。 ⑧Min Jung Kim,Becoming One:A Comparative Study of National Unification in Vietnam,Yemen and Germany,B.A.Paper,Washington D.C.,the Faculty of the Graduate School of Arts of Georgetown University,May 1,2009. ⑨Quansheng Zhao,Robert Sutter,Politics of Divided Nations:China,Korea,Germany and Vietnam-Unification,Conflict Resolu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Occasional Papers Reprints,1991. ⑩李毅臻主编:《统一之路与分裂之痛:二战后分裂国家统一的启示与统一国家分裂的教训》,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 (11)陈云林主编:《当代国家统一与分裂问题研究》,九州出版社,2009年。 (12)夏路:《区域国际组织理论研究述评——组织结构的视角》,《政治学研究》2013年第3期,第103页。 (13)[加]阿米塔·阿查亚:《建构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王正毅、冯怀信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4页。 (14)Fritz W.Scharpf,Games in Hierarchies and Networks,Analytical and Empirical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Governance Institutions,Westview Press Inc.,1993. (15)《中越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战斗团结——越南党政代表团访问中国文件集》,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110页。 (16)H.G.Peter Wallach & Rnald A.Francisco,United Germany:The Past,Polities,Prospects,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Inc.,1992,p.145. (17)Andrew Knapp & Vincent Wright,France and Europe,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France,5 edition,Routledge,2006,p.434. (18)Andrew Knapp & Vincent Wright,France and Europe,2006,p.440. (19)Ernest D.Plock,The Basic Treaty and the Evolution of East-West German Relations,Westview Press,1986,pp.138-140. (20)Jonathan Carr,Helmut Scbmidt:Helmsman of Germany,Palgrave Macmillan,1985,p.104. (21)Frank Roy Willis,France,Germany,and the New Europe:1945-1967,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p.340. (22)F.Halliday,Threat from the East? Soviet Policy from Afghanistan and Iran to the Horn of Africa,Penguin Boods,Revised ed.,1982,p.49.标签:国家统一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德国历史论文; 公司治理结构论文; 中东历史论文; 外交争端论文; 越南民族论文;
